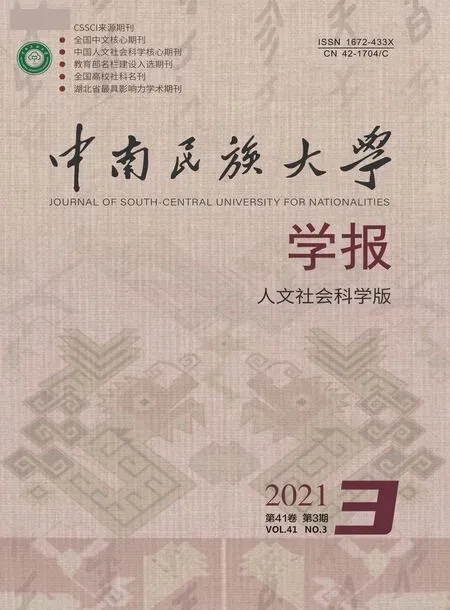曹文轩的盐城记忆及其文学意义
高 兴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作为第一位荣获“国际安徒生奖”的中国作家,曹文轩的文学创作颇受学界关注,温儒敏、陈晓明、雷达、贺绍俊、朱向前、王泉根、赵白生、安武林、北乔、徐妍等一大批学者撰文评述,他们对曹文轩的文学版图和精神世界作全方位、多层次发掘。然而,迄今为止,某些棘手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譬如曹文轩的家乡记忆问题。曹文轩多次强调童年生活记忆对其创作的深远影响,他坦言:“我虽然生活在都市,但那个空间却永恒地留存在了我的记忆中。”[1]115这个“空间”指他的家乡盐城。曹文轩自述其小说创作“依托”对象“十有八九是与童年的印象有关”[2]199,他宣称小说《草房子》“呈现出的人物、事件、景色”既是“个人的生活积淀”,也是“同代人的经历”[3]。此类作品记录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盐城民俗风情,但有人批评《草房子》含有“一些不够真实的描写”,且“没能充分地反映出时代的特征”[4]。那么,曹文轩的家乡记忆是否可信?盐城生活环境究竟给他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他的盐城记忆与文学创作有何关联?
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研究者论及曹文轩的童年记忆和家乡背景时总是语焉不详,甚至避谈“盐城”,或者套用“苏北水乡”乃至滥用“江南水乡”作为“盐城”代名词。针对曹文轩研究中的上述难点与缺漏,本文拟参考盐城地方志(《盐城市志》《盐城县志》《盐城市建设志》等)以及其他盐城史料(《盐城市航运史》《盐城杂记》等),对曹文轩、李有干、曹文芳、许正和、李锦、曹有成、张霖等盐城籍作家的作品进行“互文”式解读,以探究曹文轩的盐城记忆及其文学意义。
一、水火无情:灾难与悲悯
曹文轩认为“苦难几乎是永恒的”,希望世人养成“面对苦难时的那种处变不惊的优雅风度”(《青铜葵花·美丽的痛苦(代后记)》)[5]。他以感人肺腑的笔触写道:“这苦难也许是从天而降,使人躲闪不及……然而不久,他从苦难的承受中领略了一种升自内心深处的快感。他有了悲天悯人的情怀,有了对世界逐步明彻的看法,有了诸多超人一等的精神。”[1]185-186与此相反,曹文轩批驳“享乐主义”者“以为只有他们这个时代的人才痛苦,才在水深火热之中” 之谬见[2]202。
回溯既往,“苦难”确实不曾远离我们。就拿曹文轩的家乡盐城来说,盐城人有沉痛的历史记忆:“老辈人还记得,盐城,过去西有淮泗之水压境,东有潮卤顶托倒灌,灾害连年。”[6]盐城,濒海之城也,物产丰富,风景如画,却屡受自然灾害之肆虐,乃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结构所致。《盐城市志》这样描述:“盐城市境地处淮河入海尾闾,北、西、南三面地势较高,东北部偏低,成一簸箕形的‘洪水走廊’。洪涝之年,三面高水压境,一面海潮顶托,涨水快,退水慢,动辄洪水漫溢。大旱之年,水源缺乏,农田龟裂,禾苗枯萎。”[7]748据统计,公元1194至1949年的755年当中,盐城“水旱灾害达257次之多,平均每3年就出现一次”[7]776。1949年之后,盐城防灾抗灾工作取得成效,但自然灾害仍然不辍。就在曹文轩出生的1954年,盐城县(1983年撤县建市)夏季“连续猛降大雨”,导致“全县禾苗被淹43万多亩,死伤110多人”[8]35。同年秋季,“盐城发生百年未遇之大水”[9]23。这个气象“极端”的年份定会让曹文轩的同乡父老异常难忘。
曹文轩于1974年离开盐城去北京大学就读。从《盐城县志》的统计数据来看,1954年至1974年间的盐城经历了9次涝灾(1954、1956、1962、1963、1965、1968、1969、1970、1974),遭遇6次旱年(1953、1955、1961、1966、1967、1973),并且1962年和1965年是“旱涝交替年份”[8]109。除了水旱之灾,龙卷风(1957、1959、1962、1966)、台风和大风(1961、1965、1972)、冰雹(1958、1962、1966、1970、1972)也会招致巨大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8]37-47。曹文轩早年在盐城生活的20年,正是当地灾害爆发率极高的反常时期,为别地所罕见。
洪涝干旱已使生活充满危难,而航运事故与房屋火灾也会毁灭生命和希望。由于“盐城境内河流纵横”,再加上“近海及腹地的支流河道密如蛛网,水路交通运输条件优越”,直到1970年代以前,水路航运在盐城交通运输体系中仍占主导地位[9]1。根据《盐城市航运史》的记述,暴风袭击、航道障碍以及船工疏失等因素致使盐城水上意外事故不可避免:1951年发生24起轮木船碰撞事件,2人致命;1954年1至9月有触礁、风灾、爆炸等海损事故50起,18人死难[10]70;1958年至1965年的八年内,盐城水上交通事故共计318起,造成54人死亡、27人受伤,125艘船只沉入水中[10]106。洪水无情,烈火残酷。在往昔的盐城,遍布乡野的芦苇以及覆盖民房的茅草极易燃烧,一旦失火则迅速失控,后果极为惨烈。1924年(民国13年)盐城县城西门外的一场火灾“共烧毁147家”[8]17。1948年,盐城东台的一位老人“不小心让火引燃灶膛外的芦花”,以致殒身于火,“还把四户邻居的草房烧得片甲不留”[11]。检视盐城历史上的重重灾害,设身处地,则人同此心:火烧水淹,日烤雹击,风卷舟覆……命途多舛且无常,灾民焉能不悲歌?
灾难性事件在盐城作家的作品中比比皆是,例如李有干的长篇小说《大芦荡》详叙民国时期一场“先干后淹”的自然灾害给乡民带来的严重饥荒[12]109,他还在小说《漂流》中展现了盐城水灾的可怕现象;曹文芳的《香蒲草》提到“刮了三天三夜才停”的盐城台风[13]33;周湛军的《干草垛》回顾盐城贫民驾船去海滩割芦苇的惊险往事[14]200-201,等等。可想而知,从盐城走出去的曹文轩不会不写灾难,他创作的《青铜葵花》和《天瓢》关于洪灾场景的描写,与李有干的《大芦荡》《漂流》等小说颇为神似。不可思议的是,人们往往被曹文轩作品中的美好意境和浪漫情调所吸引,很少留意其文本镶嵌的“灾变”元素,如《阿雏》《青铜葵花》《草房子》《天瓢》中的大水场景,《草房子》《青铜葵花》《天瓢》《细米》和《根鸟》中的航运事故,《青铜葵花》《红瓦》《山羊不吃天堂草》中的火灾事件……实际上,这些“灾变”元素的叙事功能不容小觑,试想:一次意外的沉船就完全葬送了一个儿童的学业前途(《草房子》),一场突发的火灾便彻底毁掉了一位少年的人生幸福(《红瓦》),“灾变”对这些人物的家庭、天赋和人生产生不可逆转的破坏,让人如何不为之黯然神伤?“灾变”叙述为故事演变提供“变轨”的动力,又为人物刻画设置恰当的背景,且为人物性格嬗变有了逻辑依据。假如缺少这些“灾变”叙述,细马的善良、杜小康的坚韧、根鸟的机智、葵花的温婉、青铜的沉稳等便难以凸显。除此而外,曹文轩的“灾变”叙述还能激活读者对人间生活的创伤性记忆,呈现“人”的不幸与坚韧,揭示万物生存的悲壮与崇高,从而彰显文学“感动”世人的“永恒”价值。
曹文轩的“灾变”叙事不但具有组织文本的形式功能,也体现了他对盐城历史文化的深刻记忆。如上所述,曹文轩笔下的灾害类型、原因及后果与盐城地方史料的记述基本相符,也与其他盐城籍作家的灾难书写高度相似。凡间多灾多难,盐城籍作家聚焦于水火之患,非地震、雪崩、泥石流、沙尘暴之灾,自然环境影响了盐城人的集体记忆。“盐城记忆”无形中对曹文轩的“灾变”叙述发挥了潜在作用,导引他“把自己置于群体的位置来进行回忆”[15]。李锦在《盐阜家谱》中写道:“盐阜这块土地是在大自然灾难中诞生的,盐阜历史是沧海变桑田的历史。因此说,这块土地是饱经忧患的土地,是被生死存亡不断冲撞的土地。想起盐城这两个字,就觉出一种咸味,感觉出一种苦难。”[16]可见,“苦难”已深度融入了盐城作家的集体无意识。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曹文轩平静纡徐的文学话语融入了盐城的历史苦难,在他雅洁灵动的言语表层之下,能够探测到波涛汹涌的记忆暗流,由此生成的审美意境,可借用盐城作家祁鸿升的诗句来形容:“在更遥远的区域,/水与火栖进纯明,/与一些民谣呼应。”(《咸味的鸟·炼海者》)[17]80
二、重建家园:命运与道义
曹文轩指出“屋子是人类最古老的记忆”,并宣告:“屋子的出现,是跟人类对家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家就是庇护,就是温暖,就是灵魂的安置之地,就是生命延续的根本理由。”[1]5在他的作品中,“房屋”被赋予各种象征意义:油麻地小学的“草房子”校舍成为儿童乐园(《草房子》),油麻地镇中学的“红瓦房”与“黑瓦房”代表“人生的两个台阶”(《红瓦》)[18],修建茅屋的艰辛与努力体现了劳动者的坚强意志(《青铜葵花》),等等。曹文轩的作品表达了房屋之于人的宝贵价值:为了重建被毁的房子,心高气傲的青年雨中偷盗木材(《红瓦》),辍学放羊的儿童精心筹措砖木(《草房子》)。更何况,“房屋”不惟四壁,它还以“家具”的转喻形式而存在。当一位男子费尽周折地为爱侣收集幼时遭抢夺的旧家具时,他是在竭力修复永驻于心的芳馨之“屋”(《天瓢》)。
“家”不啻实体形态的屋子与家具,它离不开家人的相爱相守。在曹文轩的笔下,有不少失去或远离父母、缺乏亲人呵护的弱者形象,如《蔷薇谷》中的“她”、《远山,有座雕像》中的雅梦、《草房子》中的纸月、《细米》中的梅纹、《天瓢》中的采芹、《青铜葵花》中的葵花、《根鸟》中的金枝……这些不幸的弱者多为女性,她们的父母或亡故、或流放、或出家、或失散,在其孤苦无依之际,身边总有仁慈的长者或者友善的少年给予“厄运中的相扶、困境中的相助、孤独中的理解”(即曹文轩倡导的“道义”)[1]143,无家的孩子由此获得家庭的庇护,无助的弱者得以安身于重建的家园,相濡以沫的道义情操在民间永世弘扬,就像李有干在《大芦荡》中借人物之口所作的道德宣言:“亲帮亲,邻帮邻,远亲不如近邻。”[12]107命运不利,道义济之。
当初,为求学于远方,青年曹文轩不得不离开家庭,他的父亲曾说“儿子走得越远越有出息”[19],曹文轩却自感“无法摆脱乡村情感的追逐与纠缠”,慨叹“乡村用二十年的时间,铸就了一个注定要永远属于它的人”[20]。他盛赞李有干写活了盐城“独特的风俗”和“独特的文化”,称其作品充盈着朴厚的“乡情”[1]52-53。其实,远居北京的曹文轩又何尝不满怀“乡情”?他时常将文学视野挪回盐城,家乡从未淡出他的记忆。
曹文轩的出生地位于今天的盐城市盐都区中兴街道,属盐城“西乡”。盐都区在2004年之前为盐都县,1996年之前为盐城市郊区,1983年之前为原盐城县农村。自1958年以来,中兴街道先后被命名为:先锋人民公社、中兴人民公社、河夹寺乡、中兴乡、中兴镇。根据史料记录,中兴街道“距市区20公里”[21]。向东而行,可达盐城市区,却不见这座城市的古城墙,因该市原有的砖城城墙(始建于明永乐十六年,即公元1418年)毁于抗日战争时期,其间因日机轰炸盐城,为了“便于疏散人员”,于1939年4月拆除[8]396。盐城作家许正和(盐都人,曹文轩同乡)幼年寻访老城墙,徒然发现“没有想象中的巍峨城墙,就连一丝断垣一片残壁也没有”,不禁感到“一种莫名的心痛”[22]48。许正和未能亲眼所见的盐城老城墙,却在曹文轩的回忆与想象中得以重建。较之于曹文轩的其他作品,小说《天瓢》笔致奇崛,据说有人“问及《天瓢》中的深意时,曹文轩笑而不答”[23]。小说中的“瓢城”一词不容忽视,叙事者首先点明此地名之由来:“城离油麻地五十里路,旧时称作瓢城。”继而娓娓道出当地流行的一则传说——每当“河水倒灌”之际,瓢城人“用瓢将水出去”,遂在瓢城老屋的墙上一直挂着水瓢。至此,叙事者意犹未尽,又对瓢城景观作绘声绘色之抒写[24]。读者诸君请注意,盐城自古即有“瓢城”之称,古时所筑的土城“西狭东阔,状如葫瓢”,遂“取瓢浮于水,不被淹没之意”[25],该说广见于盐城地方历史文献。曹文轩借《天瓢》说“瓢城”,姑且勿论这是否属于“草蛇灰线”之笔法,即此一端,已能看出作者对家乡古城的刻骨记忆。非独如此,《草房子》的主人公桑桑直面恶疾之威胁,他自拟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带妹妹去看城墙,兄妹登上墙顶以远眺城内城外的风景[26]293-294。在这里,“看城墙”与“登城墙”意义非同寻常,它是故事人物极力完善生命印记的行为表达,而文本之外的作者也巧借想象之力,默然完成了重塑家乡老城郭的记忆工程,墙上的每道缝隙都填满了怀乡者的归根之情。
迈入曹文轩建构的文学王国,既能一览作者运用想象而复原的盐城旧城,又能获得一种指向家园的方位感。那个反复突现于曹文轩作品中的“油麻地”之乡,大约距离海滩和芦荡各三百里(《草房子》),即“往西三百里是芦荡,往东三百里则是大海”(《牛背上的阳光》)[27],与县城相距三十几里(《童年》《板门神》)或者正好三十里(《根鸟》)。这些空间数据略有波动,“油麻地镇”与县城的距离偶至四十余里(《红瓦》)或五十里(《天瓢》)。究其原因,它与作者感知曲线的微妙变化有关。众所周知,人类情感蕴含“主观真实性”,就像《忏悔录》所叙之事并非卢梭生平事实,而是作者与过往人生“保持的关系”[28]。曹文轩的人生记忆亦复如是。1985年冬季,曹文轩回归故里,突然感觉眼前的家乡之路竟然比记忆中的道路“短了许多”[29]190。此等情状当属正常,因为记忆的魅力本不在于信息存储的“保真”性。离乡者若能抗拒“遗忘”黑洞的吞噬,始终朝着家园方向发出持续不断的回忆之波,此举本身即为人性之美的生动阐释。
离家与归乡是人生的两种常态,思乡与流浪相互交织,正如曹文轩所言:“人类不得不流浪。流浪不仅是出于天性,也出于命运。”[1]174曹文轩刻画的流浪者几乎都经受了命运考验。以《草房子》中的杜小康为例,若非一场突如其来的水运事故致使杜家倾家荡产,未谙世事的杜小康就无须离家放鸭子。第一次离开家乡的杜小康远眺前方陌生的境域,曹文轩对这个少年内心感受的抒写令人唏嘘不已,尤以“前行是纯粹的……终于已经不可能再有回头的念头了”[26]255这几句最为精彩,它们看似平淡如水,却包含着深邃的哲理和浑厚的情感,仿佛写尽了人类“在路上”的一切复杂体验。不知1974年首次离乡赴京的曹文轩,其心情是否像盐城作家徐球荣在诗中咏叹的那样:“这个季节/只剩下/村口那棵火红的柿树/风中深情的摆动着……出外的游子/别忘了归路”(《宁静的村庄·离乡》)[17]235-236
三、风车之美:自然与教化
曹文轩的作品描绘了带有典型的盐城地方文化特征的自然风景。他称赞李有干的写景艺术:“风车、芦苇、油菜花、海滩、帆船以及苏北大平原上的一切物象,对他而言,都有说不尽的魅力。”[1]52所谓的“苏北大平原的一切物象”,在曹文轩本人的作品里,至少还包括麦地、河流、炊烟、木桥、鸭子、鱼虾、水牛、野兔、云雀、乌鸦、荷叶、菱角、菖蒲、茅草、柿子树……诸多风景元素相映成趣,共同点染盐城乡土神韵。值得注意的是,那形诸曹文轩笔端的盐城风情,绝非“江南”气象,也有别于苏北其他地区的人文图景。《盐城市志》记载:“旧时,境内地僻海边,先民们一直以渔、盐、耕种等业为主……盐城勤俭、简朴的美俗,与扬州、淮阴等邻近地区相比,这里的民风更显古朴、淳厚,表现出明显的沿海地域特征和水乡自身特色。”[7]2654盐城作家对当地景观特质了然于心,梦瑜告诉我们:“苏北平原的最大特点就是坦荡。……比起江南的柔美旖旎、婉曲精致,苏北平原是粗犷豪放,凛然洒脱。”[14]77许正和发现“江南和江北的小镇依托的地域背景也是不一样的”,江南小镇“精致细腻”,而江北小镇“粗犷坚实”[22]10。张霖赞美“盐城西乡特有的水系氛围和特有的景色”,认为“这种美不同于皖南山区的水墨写意,也不同于浙东山区的绿水青山”,感叹盐城西乡“特有的灯笼式”风车已深深植入盐城人的审美意识当中[14]174。
回眸20世纪的盐城,“50年代前后,县境串场河以西,到处可以看到似如灯式转动的八篷风车。其车身部件,有车心、车辋、主轴、跨轴、座驾、桅子、创子、槽桶等。整部车体制作,称得上‘巧夺天工’”[8]162。此种风车可谓工匠智慧与乡村美学的结晶,盐城人对它记忆至深。1945年离开盐城的薛鸿钧在时隔五十余年后,尚能清晰地复现风车影像,其忆旧之作《盐城杂记》告语世人:“风车是盐城独有的农具,也是故乡的一大特色,在其他省县,还未曾见过。……若非有经验的老木工,恐难制作得如此的巧妙而保证安全。”[30]盐城风车是否举世无双,尚待进一步考证。英国学者李约瑟编著的《中华科学文明史》认定欧洲人于1656年首次在江苏省宝应看到中国风车,猜想这种风车或许由中亚、契丹、阿拉伯等国外商人或水手传入中国,再由中国船舶技师为盐业劳动者动手制造,于是“风车的分布停留在沿海一带”[31]。在当今的江苏省地图上,扬州市的宝应县正好与盐城交界,而黄海之滨的盐城盐业更为发达。笔者据此推测:当年在宝应看见风车的欧洲人,大概没有继续东行至盐城。假若《中华科学文明史》所述不谬,那么,盐城及其周边地带很可能是中国最早制造和使用风车的区域。退一步讲,就算中国风车不由该区域的盐业劳动者首创,只要经过了当地人的技术改造以及依照中国传统美学观念作出了外形调适,其本身便构成多元文化交流的杰出成果。
盐城作家描摹盐城的历史画卷时,尤为钟情“风车”意象。邵玉田的《破风车水车及其他》断定风车是苏北里下河地区“不可缺少的一种标志物”,更重要的是,“风车与人合作,助人生存,人与车是有情感的”[32]26。陈国中的《风车》塑造了一位擅长掌控风车并且乐于助人的乡间“老车神”形象[32]65。曹文芳的《香蒲草》提及一个“哑巴”女孩从风车上摔落后又恢复“说话”能力的趣事[13]33。李有干的《大芦荡》将“风车”作为惊险刺激的乡村故事要素,内中人物“对风车熟悉得就像读一本有趣的书”[12]23。在盐城人眼里,风车既灌溉土地又滋润心田,既是无言的工具又是默契的同伴,既感应空气的节律又转变生活的光景。回想儿时常见的“一座座迎风转动”的风车,许正和心绪难平:“风车的转轴声,极像时光老人的脚步声呢,就在它发出的‘吱吱呀呀’的声音中,历史翻开了一页又一页。”[22]84在盐城作家心中,风车不惟生产器具,不啻情感载体,风车亦是穿越历史星空的记忆飞翼。
曹文轩构想的故事角色大多喜爱和亲近风车,《草房子》《根鸟》《细米》《天瓢》等作品中的人物莫不如此,就连故事中的“野风车”和“鬼风车”,最终也变成乡民正直、勇敢和仁义的见证者与对应物。《天瓢》末章关于“风车”的对话让人感慨万端,两位饱经沧桑的老对手悄然而遇,在“风车”的共同回忆中达成善意的和解。多年来,曹文轩对盐城风车记忆犹深,2006年的某一天,他在家乡偶遇“风车”模型便惊喜不已,这个“小插曲”引发安武林的沉思:“他观察到的这架风车很美,是触动了他遥远的回忆,还是他在进行对比后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和感动?”[33]曹文轩的“风车”意象绝非等闲符号,它关涉作家的家园记忆,标示作家的思维特点,隐喻作家的审美旨趣。
“风车”美在何处?概言之,它一则代表乡野物象,展现自然之美。二则呈示工匠技艺,昌明教化之仪。综观曹文轩的美学思想体系,二者水乳交融。曹文轩崇尚自然,注重情感,擅长写景,他相信“特别的河流、山川、田园风光,经过心灵的感应,会酿出不同的艺术趣味”[29]222,强调“审美”的“感化与浸染能力”[34]192,谴责世间扼杀儿童“灵性”乃至“泯灭人的良好天性”的畸形“教育”[1]127-128。曹文轩也指出文学作品中的自然风景“具有民族性和文化含义”[35]324,宣明人类的心理感觉主要由“文化造就”[29]145,提出文化教养的重要性,坚信“天下最美的气质,莫过于书卷气”[2]184。赏析曹文轩的《草房子》《细米》《青铜葵花》《蜻蜓眼》《红瓦》《山羊不吃天堂草》等文学作品,人们既陶醉于水乡泽国的自然清新,也感佩于纸月、梅纹、葵花、阿梅等花季少女的柔婉高雅,神往于蒋一轮、赵一亮、许一龙、三和尚等教师技工的心灵手巧。耐人寻味的是,纸月、梅纹、葵花等女性人物的文化教养超过了她们的男性保护者(桑桑、细米、青铜等人),她们在文字、艺术和举止等方面对男性予以教化和引导,成为男性倾心爱护的“美”之女神,与朴实浑厚的男性形象构成文化美学系统中的对位关系,曹文轩的两性审美观与他的风车情结似乎遵守同样的美学原则。料想静坐于京城学府的曹文轩,每每念及勤劳灵慧的家乡男女,眼前或许浮现盐城作家韩冰描画的那种景象:“盐城 到处都是穿针引线的女人/与硕大的棉花为伴/一代一代纺纱织布/花团锦簇地梳妆”(《堆积的盐》)[17]254
四、故乡记忆与文学范式
在当代中国文坛,曹文轩静观各种文艺浪潮汹涌向前,却为捍卫文学的“古典美”而发出呼吁:“文学的古典与现代,仅仅是两种形态,实在无所谓先进与落后,无所谓深刻与浅薄。艺术才是一切。”[29]76他郑重申明:“我在理性上是个现代主义者,而在情感与美学趣味上却是个古典主义者。”[29]76人类不能仅从时间维度审视“古典”与“现代”的关系。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说过:“在某些重要方面(虽然不是所有方面),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与亚里士多德理论的接近程度,要大于这二者与牛顿理论的接近程度。”[36]173时间无法阻断人类精神的共通感,那“本体”的“真”与“纯粹”的“美”,何曾消解于忘川之水?
曹文轩深知“一个作家当他成熟起来,他会很自然地将目光转向自己从前的生活”[29]312-313。他剖析哲学家柏格森的时间观对普鲁斯特回忆与写作的启示[34]127,赞叹博尔赫斯凭借回忆在文本中创造“一个更加丰富而高深的世界”[34]164。浏览他列出的经典作家名单(契诃夫、卡夫卡、普鲁斯特、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川端康成、鲁迅、沈从文、汪曾祺等),“记忆”型作家居多,他本人的文学观念也与之接近,组成了“家族”性的文学范式。秉持该范式的作家将客观对象转化为艺术“符号”,通过“记忆”对其“任意编排与组合”[35]187,这样的处理方式不一定必然地偏离历史事实,譬如有人认为曹文轩小说《草房子》叙写1959年至1962年的农村养猪喂牛等现象“在当时都是不可能也是政策不允许出现的事”[4]。然而,《盐城市志》确有这样的记载:盐城在1959年实行“集体养猪为主,公养私养并举”的政策,又于1961年贯彻“公私养并举,以私养为主”的方针,对农民家庭养猪给予奖励[7]702。然而,“记忆”型的文学范式向来拒绝文学上的唯“真”论,却为“善”和“美”正名。由于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使得“竞争着的范式的支持者之间,在观点上总难有完全的沟通”[36]124,曹文轩的文学范式难免会在某些方面引起争议。
本文分析了曹文轩的盐城记忆与文学范式的内部关系,认为旧时盐城灾害频仍的生活环境强化了曹文轩悲天悯人的文化情怀,扶危济困的道义精神在曹文轩身上催发了重建家园的文学“寻根”意识,从盐城“风车”意象中可以辨识曹文轩关于自然与教化相融合的审美观念,曹文轩提出的“良好的人性基础”三大关键词(即“道义感、审美意义、悲悯情怀”)[37],均与他的盐城记忆有所关联。徜徉于文学殿堂的曹文轩,以他特有的声音,与其故乡的盐城籍作家合唱一首“水乡曲”,恰如王淼的感喟:“我很依恋那/唯美的河/可是,又难舍/隐约传来的呼唤”(《记忆中的雪》)[17]45,又似孙蕙的惋叹:“麦地之外的水声开始痛疼/一些文字漂在空中/篮子里满是星光”(《等待一首诗》)[1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