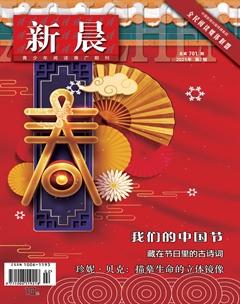回望中国节假日变迁
周叠瑶

数着日子期盼周末和假期的到来是大多数职场人的真实写照。“黑色星期一”让人沮丧,而周五下午的办公室,气氛则会轻松不少。除了周末,节假日的存在也让人们有了盼头——四月盼清明、五月盼“五一”、六月盼端午、下半年就等着九月的中秋节和“十一”黄金周,最后以新年和最受中国人重视的传统节日春节收尾,无论是三天小长假还是七天的大长假,法定节假日的存在让人们享受了难得的闲暇时光。
但如果将时间线拉长,我们的父辈、祖辈似乎远没有我们“清闲”。从建国以来,一周单休、每周48小时的工作制就持续了40多年之久,直至1994年年初才开始实行“双休—单休”循环的模式。1995年3月25日,《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将“双休—单休”循环彻底改为全年双休,由此才开始了周六和周日双休的新纪元。而法定节假日,也经历了建国时的全民7天、再到10天、11天的变迁。
40后:“一切为了集体”
今年76岁的刘美兰老人年轻时在粮食局工程队工作,也是那个时代在矿区为数不多的自己挣工资的“劳动妇女”。1970年,27岁的她为了补贴家用,参加了粮食局工程队的考试,从工地搬运小工干起,一步步转到了管理岗。“当时,我被派去管单位食堂,看似是个肥差,实则是个难事。”刘美兰回忆。当时,刘美兰从上任管理员接手食堂时,整体处于亏空状态。管理混乱、员工偷油的事时有发生。刘美兰接手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特意跑去河北焊了油桶,规范管理,所有人凭油票拿油。她还自掏腰包种菜、种庄稼节省食堂开支,不出一年就解决了亏空问题,还有了盈余。
但只有刘美兰自己知道那段时间的苦。“当时早上凌晨5点就要到食堂管灶做早饭、还要经常一个人去采购、拉粮、拉菜和酱油调料。从市场到食堂的必经之路有一段上坡路,是30度的斜坡,每次拉东西都特别费劲。”近50年过去了,刘美兰仍然能回忆起当年的很多细节。
正是这种肯吃苦的劲儿让刘美兰很快当上了工程队的党支部书记,最终调入市里工作。但由于家住在矿区,路途不便,刘美兰反而要起得更早才能按时上班。每个工作日,天不亮她就要从家里出发,倒三次公交车才能到市里的单位。一到岁末年终,还要加班晚上写报告和总结。“记得有一年是小年夜的前一天,因为连续加班,我走在路上突然晕倒了,幸亏身边有同事,把我送到了山大二附院。当时真的挺心酸的。”
20世纪60至70年代,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在集体主义精神的鼓舞下,无数像刘美兰这样的劳动者把自己的青春留给了单位的工作,但同时也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
60后:从单休盼来双休
如果按十年一代人计算,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60后”可谓是经历变革最多的一代人。无论是70年代的高考恢复、改革开放,还是90年代的下海潮,“60后”们人生的许多关键节点与共和国的发展总是高度契合。对于节假日的变迁,也是如此。叶春红出生于1961年,高中一毕业她就去粮店里当小工。在粮店打工的日子辛苦而繁忙,为了赶上卖早点的时间,叶春红凌晨五六點就要赶到粮店开始工作和面。“当时店里有四五个人,轮流换着和面,50斤一袋的面粉一天要用2~3袋,真是个卖力气的活儿。但当时年轻,也不觉得怎么累。”叶春红说起年轻时的自己,满是回忆。直到1984年,叶春红辗转来到挂面厂当出纳会计,才彻底脱离了体力劳动,工作起来稍微轻松些。但直到那时,她对节假日的概念依旧很模糊,“当时一周就星期日能休息,一般就是在家洗衣服做饭,顶多偶尔逛逛公园。”
并不是只有叶春红一个人有这样的感受。同为“60后”的孙念出生于1963年,勤奋刻苦的他如愿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1989年研究生毕业后,孙念来到国有外贸公司工作。尽管在当时,在外贸公司工作着实令人艳羡。可是对于出身农村的孙念来说,日子依旧过得紧巴巴的。工作后,孙念每个月都会给家里打钱,日后还要为孩子攒钱,因此孙念和妻子从来都不敢敞开了花工资,每一分钱都要计算着花。
说起节假日能做什么,孙念说:“那个时候哪里有节假日的概念,一来没有余钱,二来休息时间也很短,每周只休息一天。平时上班累得半死,星期日要么在家补补觉,要么抓紧时间做做家务。”据孙念回忆,交通不便、上下班路途远是个很困扰他的问题,“当时我住在一个北京二环内城的平房里,而单位却在二里庄。如果赶不上早7:00的班车,就只能自己骑车去单位。”一周连续六天,每天近两个小时耗在路上的生活让孙念疲累不堪,更没有什么心思想着周日去参加休闲活动。
90后:黄金周伴随成长
1999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袭来,为尽快摆脱经济增长乏力的状况,刺激需求、拉动内需,国务院将“五一”、“十一”放假天数分别由原来的1天和2天增加到3天,与前后周末相连组成春节、“五一”、“十一”三个7天假期,被称为“黄金周”。
1999年10月1日,全国迎来了有史以来第一个黄金周。这个久违的长假让所有劳动者第一次有机会出远门,许多人选择回家探亲,孙念也不例外。这一年,孙念的女儿已经7岁了,但却一直没有机会回老家见爷爷奶奶,孙念决定利用“十一”黄金周带着妻女开车回老家。虽然已经对预料到回老家的路不会一帆风顺,但道路的拥堵状况真的令孙念大出所料。还未出京,孙念一家就堵在了路上。但孙念还是咬着牙坚持带妻女回了老家,见到了多年未见已经年迈的父母。
在归家途中,还有一段小插曲。孙念一家在高速服务站停车休息的时候竟然碰到了一个单位的同事。同样,同事也是利用这个长假携家带口回老家探亲。两家在服务站相见,既惊讶又感到好笑。据统计,1999年国庆,也就是全国第一个黄金周,全国出游人数达28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41亿元,呈井喷式增长。
随着日子越来越宽裕,随后几年孙念一家每逢“五一”、“十一”黄金周都会去外地旅游,也会接待来北京旅游的朋友。后来,在去了一些国内热门景点以后,孙念也发现,每逢黄金周哪里都是人,“光见人、不见景”,有的地方还出现了载客欺客的现象。所以,孙念决定以后要么黄金周躲在家里,错峰旅游;要么干脆直接去国外玩。但到了后来,孙念沮丧地发现:除了春节,在黄金周时间即使去欧洲这种距离较远的地方旅行,也到处充斥着中国游客,很影响游览质量。
于是,黄金周去哪里玩成了孙念一家的难题。但很快,新的变化又出现了——2007年年底,国务院正式公布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取消了“五一”长假,改为3天小假期。法定节假日由原来的10天增加1天,与被拆分的“五一”剩余两天假期组成了清明、端午、中秋三个小假期。至此,三大长假鼎立的时代彻底终结。
从提倡集体主义、全身心投入工作,到单休变双休,再到法定节假日天数的不断增加、落实职工带薪年休假,对节假日态度的一次次转变的背后反映了我国经济的逐步发展和休闲意识的不断增强。尽管我国在保障劳动者休息权、增加法定节假日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过劳”、带薪休假得不到落实等问题仍困扰着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正如森冈孝二在书中所说:“在劳动时间问题上,全世界的员工都在与经营方进行着艰难博弈。”(来源:中国小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