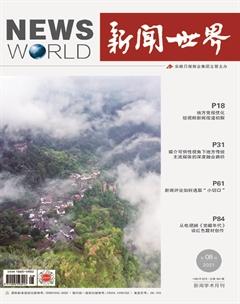从电视剧《觉醒年代》谈红色题材创作
任兵辉
【关键词】《觉醒年代》;红色题材;创作
《觉醒年代》根据历史改编,对新文化运动、巴黎和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等标志性事件进行了呈现,唤起了观众对这段历史的深切感受。该剧运用严谨的时间逻辑、暗喻等手法表现了知识分子对中国救亡图存道路的探索,阐述了那个年代为什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也是《觉醒年代》不同于以往的红色经典剧的创新之处。
一、以镜头再现社会历史
《觉醒年代》以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脉络为主线,展示了中国历史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叙述了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国人的思想觉醒与命运轨迹。对新文化运动的深入探索阐明了先进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一)红色主旋律题材的“求真”
电视剧作为一种声像结合的艺术形式,其真实性体现在道具摆放、建筑、人物对话上,这些细节是时代所造就的。觀众要从红色主旋律电视剧的镜头影像中,感受当时人民的命运坎坷及社会形态的变化,就要求电视剧不仅要尊重历史,更重要的是剧中人物神态、言语、服装设计等都要精益求精,经得起推敲。部分红色主旋律题材电视剧,为了迎合受众的审美,刻意夸大故事情节,对人物的设计天马行空。如被人民日报批评的抗战片《雷霆战将》中浮夸的表演,现代的服装设计,严重违背了历史真实。《觉醒年代》剧组为了还原“北大红楼”,多次实地考察,反复测量,最终以1:1.2比例搭建,突出了“北大红楼”作为新文化运动宣传阵地的重要性;陈独秀家门前箭轩胡同的泥泞大道,是从张家界拉回沙子一次次碾压而成的。剧中图书馆的书籍摆放,人物的服装、神态等,都让观众自然地融入到那个年代和空间之中,让红色主旋律电视剧更真实可信,生动感人。
(二)国人精神觉醒的影像演绎
纵观我国的红色主旋律题材电视剧,都集中于反映发生在1921-1937年间的故事。据《中国电视剧产业发展报告(2019)》显示,2018年生产完成并获得发行许可证的电视剧总量为323部,其中与传播红色文化直接相关的包括“军旅类”、“抗战谍战类”、“都市刑侦”类等题材的电视剧占总产量的24%,外加“年代传奇”类中也有部分电视剧展现着各历史时段的红色文化,因此与红色文化相关的电视剧年产量约80部左右。[1]如《悬崖》作为谍战剧的代表,讲述的是周乙等地下工作者面对旧社会的崩溃,外有日寇铁蹄进犯,内有不同派别势力的斗争,战火连绵,生灵涂炭,为了共同理想,对革命的坚韧和忠贞,对信仰的忠诚;如《恰同学少年》是革命青春励志剧的代表,讲述的是一代伟人毛泽东少年时期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故事。
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是红色题材电视剧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而在我国红色题材影视类作品中,关于国人觉醒的作品甚少,《觉醒年代》的出现弥补了这一空白。该剧以《新青年》杂志由上海到北京再到上海为主线,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将北大作为宣传阵地,中国的各种社会思潮相互借力,进行启蒙和唤醒。早期的觉醒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然后是知识分子的觉醒。再到山东被割让之后,大众的觉醒。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觉醒后的中国找到了振兴中华之路。正如剧中陈独秀所言,他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就是“辨析、选择、验证”出一种当代最先进的思想理论,作为改造青年和社会的指导思想,探索一条振兴中华的道路。[2]
《觉醒年代》以陈延年和陈乔年的思想变化为典例,侧面反映了国人觉醒的艰难。两人最初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奉者,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并且组织工读互助社进行验证,最终以失败告终。直到二人去法国勤工俭学,通过反复比较,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观众在对《觉醒年代》的评价中提到:这部剧的出现,真正把历史和现实连接起来,仿佛自己就是出生在那个年代,感受着时代的黑暗和人民对腐败政府的抗争。
二、艺术创作的深入挖掘
观众渴望从电视剧的艺术创作中看到最真实的历史画面,《觉醒年代》透过充满张力的影像语言,将写实与写意相结合,丰富了电视剧的意蕴。
(一)特写镜头下的情绪建构
如蚂蚁的特写前后两次在陈独秀与陈延年两父子的镜头里出现,一次是蚂蚁在陈延年手中被放生,蚂蚁的恢复生机和陈延年的哂然一笑,表现了对未来的希望。将人物和蚂蚁联系在一起,不仅是人物内心细腻的情感表达,更意味着要回归自然回到民众生活中去。另一次是陈独秀在上海震旦学院发表《新青年》创刊演说,话筒上蚂蚁爬行,但始终是一个方向。蚂蚁尚且有上下求索之心,何况人呢?不也应在困顿的命运中探索出路吗?这样一个镜头正意味着下层民众虽小如蚂蚁,但聚集起来就是中国革命的力量。
除了暗喻外,导演还擅长用无声代替有声的视听语言来建构历史和情绪氛围。地上的乞丐,牵着黄牛的农民,被观赏的金鱼,被贩卖的小孩,坐在车上吃着三明治的少爷,一个不到5秒钟的镜头把旧时代的黑暗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观众拉回到当时的情境中,更加理解历史人物的选择。一个转场镜头,更是演绎了《青年杂志》对毛泽东所产生的影响。这是艺术表现手法所产生的作用。这样精心设置的画面向观众说明面对旧时代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追随更加坚定,也更加坚定中国问题只能深入到这土地上,才能够理解透彻。同时,运用蒙太奇以及闪切的手法将陈延年和陈乔年去法国留学和数年之后的刑场相交融。这种将过去和未来连接到一起的画面,好像是父亲看到了儿子的立场又像是分别时的感情碰撞。那回眸一笑,让观众回味无穷。
(二)艺术想象的叙事结构
《觉醒年代》重要的创新之处就是借用历史典故来完成人物的出场。蔡元培三顾茅庐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学学长,第二次登门的时候,担心打扰到陈独秀休息,便搬了凳子坐在门口等。“三顾茅庐”与“程门立雪”这两个典故的相互照应,暗示了蔡元培求贤若渴的心情。
大部分红色题材电视剧都是以某一事件为主线,通过线性故事结构完成拍摄。而《觉醒年代》是在大的历史框架下,通过合理的艺术想象,影像化地展现历史,建构了诗意般的场景。陈独秀被送往上海的那一幕,黑云压城的紧迫感,难民的房子,湖边为老友送灯的老人,一句“习惯了”道出了多少苦难和委屈。贯穿全剧的木刻版画艺术的运用,深刻表现了重要的情节和故事背景,强化了主题。其次,这种叙事结构增添了电视剧的浪漫气息,这样一部以新文化运动为主线的电视剧,还原了大量的历史语录,却不显得生硬枯燥,而是在信手拈来中,赋予了观众想象空间。《觉醒年代》中辜鸿铭“论中国人精神”的系列讲座,还原了历史并引用大段演讲原文,让观众自然而然的融入到场景中。
三、平民视角下的影视演绎
《影视叙事学》将西方学者对影视叙事的理论归纳为五种特性,即“始终性、时间性、话语性、非现实性、整体性”,[3]这五个特性强调了一部电视剧整体性的重要意义。影视叙事作为一个时间和空间的呈现,完成了对故事整体性的建构。《觉醒年代》以新文化运动为主要事件,关联了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文化辩论、巴黎和会、共产党成立等一系列代表性事件,从而完成对主要情节的整体性叙说。
(一)人物的个性化表达
每个人的性格都是典型性和个别性的统一。只有把人物放在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中,才能凸显其个性。《觉醒年代》打破高大、庄严、照本宣科式的人物塑造方式,而是呈现出一个个生动、形象而鲜活的人物形象,让新一代青年观众,以第一视角感受历史人物的平易近人与亲和力,并产生对人物的认同。如剧中陈独秀和陈延年、陈乔年关系的变化,没有削弱角色的感染力,这种将为了救国的理想抱负和亲情的矛盾全盘托出,反而让观众感同身受地去体验这种牺牲精神。
电视剧中的细节运用,不仅带给观众真实感,也唤起了观众的共情感。《觉醒年代》中导演对于细节的把握极为严格,李大钊的衣服与胡适衣服的对比,表现了李大钊豪迈、简朴的个性。剧中多次出现的师生鞠躬,传达了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的平等、自由、尊重和独立精神,更呼应了我们传统社会中的礼仪。
(二)时代精神的传承
时代风采是时代精神的外化,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4]《觉醒年代》还原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过程。在影像表达中,充分凸显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种文化思潮的争论,不仅聚焦知识分子,还把目光投至北京长辛店的工人和其他平民大众。与以往的红色题材剧不同的是,《觉醒年代》淡化了政治人物之间的争斗,而聚焦于新文化运动中的北大师生,展现了他们的青春活力和家国情怀。且运用大量镜头详细描绘了作为新青年代表的陈延年、陈乔年、毛泽东的故事,彰显了独立、胸怀大志、为旧中国寻找出路的精神。这种青春气息与情怀的结合,让处于和平时期的新一代青年重温历史,引导广大青年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正如众多年轻观众的弹幕所言,观看此剧,不仅是心理上穿越时空的对话,更是精神上的洗涤。
结语
《觉醒年代》的创新不仅在于平民视角下的生活演绎,更重要的是通过影视语言还原了历史。其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艺术再现了一百年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一群热血青年演绎的一段追求真理、燃烧理想的澎湃岁月。不仅鼓舞人心,也為未来的红色题材电视剧创作提供了范本。
注释:
[1]司若.中国电视剧产业发展报告2019[D].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2020.
[2]康伟.以深刻、鲜活、丰盈的方式打开历史——电视剧《觉醒年代》观后[J].当代电视,2021(05).
[3]宋家玲.影视叙事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384.
[4]贾翔宇.电视剧中红色文化的传播优势研究[J].新闻文化建设,2020(11).
(作者: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2020级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