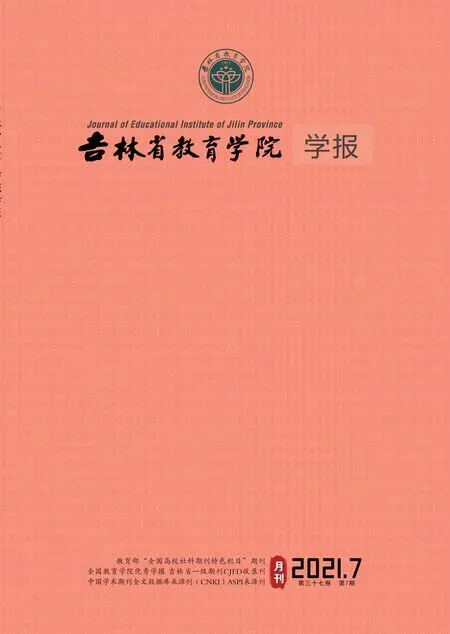一个“撄而后成”的自我完善的女性形象
——试论《聊斋志异》中婴宁性格的重大转变
侯 睿
(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
众所周知,婴宁从狐到人,从少女到少妇,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过程,在小说中是有着比较明显的脉络的。现在需要探讨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下许多流行评论都认为,婴宁由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是受到封建礼教和社会道德规范的制约,因而婴宁的性格转变是封建礼教扼杀妇女纯真天性的结果。婴宁的性格转变是礼教的悲剧,妇女的悲剧,是一个被动的、被迫的与异常痛苦的转变过程,人类为了群体的利益,不得不牺牲个人的纯真天性,成全群体性。这是人类永远也无法解脱的精神困境。因而,婴宁的性格转变具备了人类永恒精神困境的象征意义。
而通过对《婴宁》这篇小说的文本细读,笔者认为,婴宁由原来天真活泼可爱的少女形象、狡黠狠毒的狐女形象和充满了痴笑娇憨的自然人形象,通过一番尘世的磨砺,逐渐转变成一个孝敬勤劳、庄重知礼、智慧练达和富于感恩之心的少妇形象,从而完成了由狐到人、从少女到少妇、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撄而后成”的自我调整与自我完善的女性形象。
这个转变过程并不是一个被动的、被迫的和异常痛苦的过程,恰恰相反,是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与角色的转换而主动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的过程,是越来越得到周围亲戚朋友邻里乡党认同的过程,是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得心应手的一个良性转变过程。
我们可从蒲松龄对儒释道三家的理念与态度、“婴宁”一词的原意探究、蒲松龄借小说中人物之口对婴宁性格转变的评价、对文本本身的细读以及蒲松龄在小说文末的总结这五个角度切入,对这篇小说进行一番深层透视。
一、作者对儒释道三家的理念与态度:认同与敬畏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读书人绝大多数都学习和认同儒、释、道三家文化的理念,心态上是异常敬畏的。其实,蒲松龄先生也不例外,何以为证?
(一)对于儒家经典,蒲松龄自幼攻读经史,19岁时在县、府、道三次考试中均名列第一,因而获得了秀才学位。但此后考举人却屡试不第,直到71岁才补了一个贡生。贡生是秀才学位中可以获得国家助学金的秀才,也是秀才等级中唯一具备入太学读书资格的等级。也就是说,蒲松龄作为一个资深秀才,儒家经典是他的必修课,对儒家经典一定是极为熟悉的,虽然有考不中举人的不快与不平,但对于儒家经典是认同和敬畏的。
(二)对于佛家经典,自从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汉明帝派人从西域将佛教迎请回中国,中国古代社会从汉朝一直到晚清对佛教都是心存恭敬的,许多佛门的高僧大德,比如南朝梁的宝志公禅师、清朝的玉琳法师、章嘉大师等都被封为国师。所谓国师,乃是帝王和国民的老师,所以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佛陀教育是高度智慧圆满的教育,佛家经典同样具备了至高无上的崇高地位。而蒲松龄本人自号柳泉居士,而佛家的在家修行人都被尊称为居士,可见,蒲松龄的内心对佛教是尊崇和敬畏的。
(三)对于道家经典,蒲松龄也是学习且熟知的。《婴宁》这篇小说女主人公的名字就出自道家庄子的《大宗师》。作者将小说的题目和女主人公的名字都命名为婴宁,这应该是其创作《婴宁》的宗旨与初衷所在。
综上,对于儒释道三家经典蒲松龄在理念上是真心认同,在心态上则是充满了敬畏的。众所周知,五四运动时期反传统的小说里常有“名教杀人、礼教杀人”的字眼,实际上是误会了名教与礼教,名教与礼教是保证社会秩序与和谐的最低底线。所谓“名教”,就是我是什么样的“名”,我就要履行什么样的“职责的教育”。所谓“礼教”,就是我在什么位置上就要履行什么样的“礼仪、礼节和节度的教育”,这就是名的教育和礼的教育的内涵,这样的内涵是维系社会和谐之所需。而深度认同儒释道三家经典的蒲松龄先生,又怎会反对这样的“名教”与“礼教”呢?
二、“婴宁”一词原意探究
小说的女主人公名为“婴宁”,小说题目也是“婴宁”,无疑,这部小说的宗旨与创作初衷也应该是“婴宁”之意。那么“婴宁”一词的原意究竟为何?其出处是庄子的《大宗师》,南伯子葵见女偊年龄很大却色如婴儿,驻颜有术,就问何以如此?女偊则说我得道了。她讲述了自己得道的经过:“参日而后能外天下;……七日而后能外物;……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撄宁。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1]憨山德清在《庄子内篇注》中注释云:“撄者,尘劳杂乱困横拂郁挠动其心曰撄,言学道之人全从逆顺境界中做出,只到一切境界不动其心,宁定湛然。故曰撄宁。”“谓从刻苦境界中做出,故曰撄而后成者也”。“撄宁”与“婴宁”是通假,“婴宁”之意通俗地说就是经过一番尘劳杂乱困横拂郁挠动其心而后获得的宁定湛然之境界。由此我们知道,这篇小说的宗旨与初衷是说婴宁经过一番尘世的磨砺而更加完善和完美了。
三、作者借小说人物之口对婴宁性格之评价
在小说中,作者借鬼母之口说婴宁“若不笑,当为全人”。[2]如果婴宁不笑,应当是更完美了。这既是对婴宁未来性格变化的预言,同时也是对婴宁性格变化的评价。蒲松龄借王子服母亲之口也对婴宁无时无刻无忧无虑的笑做出了评价:“早知过喜而伏忧也,……人罔不笑,但须有时。”[2]意思是说,过分的欢喜伏着忧患,人没有不笑的,但应有时有晌,该笑的时候笑,不该笑的时候不笑,这才符合中道。
我们知道,在诱杀惩杀西邻子事件之后,婴宁给丈夫带来了官司,也遭到了婆母的斥责,这使婴宁意识到这里不是她以前和鬼母住在一起的荒郊野岭,她过分的笑确实在莒县罗店村这个环境里会出大问题,于是,为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和已经转换为少妇的角色,婴宁发誓不再笑了,她真的做到了终日不笑,可整日里页没有一点忧伤的神色。
那么,婴宁到底是无时无刻无忧无虑地笑接近中道,还是虽不笑但整日没有一点忧伤的神色更接近中道?无疑,应该是后者。
那么婴宁的不笑,是封建礼教扼杀了妇女的天性还是使其更完美了?作者蒲松龄先生借鬼母和王子服母亲之口的回答是:更完美了,更接近中道了。
那么,婴宁经历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撄而后成的过程呢?接下来我们通过文本细读来详细论证。
四、文本细读:一个主动自我调整与自我完善的女性形象
我们首先要梳理的是小说中若隐若现、时断时续的婴宁身世,然后再进入到婴宁性格的转变过程之中,这样,来龙去脉似乎就更为清晰了。
(一)婴宁身世
婴宁的父亲秦老先生是个人,其母则是个狐狸精,这就给婴宁带来了半人半狐、亦人亦狐的双重身份,而这双重身份使她由狐到人、由少女到少妇、由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就变得合情合理合法了。
秦老先生的正妻乃是王子服母亲的姐姐,与王子服母亲同姓吴。吴氏没有生育子女。她过世之后,秦老先生被一个狐狸精迷住了,与之媾和而生下了独生女婴宁。所以,婴宁应该是秦老先生之庶妾狐狸精所生,她应该姓秦,名婴宁。随后因为秦老先生害了虚症而辞世之后,秦氏家族中人容不下狐狸精母女,因而族人求道士画了一道符粘在墙壁之上,狐母便携同婴宁离开了秦家,将婴宁带到了荒郊野岭,即秦老先生的正妻吴氏那里,此时的吴氏已经过世为鬼,狐母将婴宁托付给鬼母吴氏,然后改嫁而去。
而此时的婴宁还是尚在襁褓中的婴儿,她的生存环境是鬼狐所居之所的荒郊野岭,又有着如此的亦人亦狐的自然的出身,因此,她的性格是自然炼就的,有其天真活泼可爱的少女性,发展到极致也就是其痴笑娇憨的人的自然性,同时亦有其狡黠狠毒的狐性的一面。
(二)婴宁转变之前的性格
我们承认,无论是人的少女性与自然性抑或是狐性都是自然炼就的,这是婴宁转变之前的性格。
最初婴宁是一个天真活泼可爱的少女,但有其人的自然性,也就是痴笑和娇憨,这是婴宁不同于一般少女的地方,一般少女的痴笑娇憨似乎有个限度,而婴宁却像一块璞玉,她的痴笑娇憨是没有边际的。
鬼母曾评价婴宁:“颇亦不钝,但少教训,嬉不知愁。”“年已十六,呆痴裁如婴儿。”[2]这一点从王子服与婴宁交往的例子可见一斑。王子服到了自己大姨妈家,吃过了中饭,大姨妈请婴宁来拜见这个姨妈家的表哥。“良久,闻户外隐有笑声”“户外嗤嗤笑不已”“婢推之以入,犹掩其口,笑不可遏”。[2]与王子服谈话间,“又大笑,……至门外,笑声始纵”。[2]在舍后小园,王子服遇到了婴宁,她在树上“狂笑欲堕”,[2]一个女人面对一个男人,不但不回避,反而放声大笑,会给这个男人以怎样的感受?无疑他觉得是受到了鼓励,且认为有机可乘,会放胆过来。于是,王子服趁她摔倒来扶她的时候,敢于暗中捏她的手腕子,而如果婴宁正色斥责,王子服定会有所收敛,而婴宁却以大笑来应对,这使王子服胆子越来越大,于是就有了接下来的爱情告白,王子服明确地向婴宁表示愿为夫妻共枕席耳,而婴宁却说“我不惯与生人睡”。[2]我们知道,王子服在鬼母门前的大石头上坐卧徘徊了四五个小时而不敢入门,由此可以看出王子服是一个守礼之人,或者说是胆小之人。而王子服何以胆子突然大起来?这一切都与婴宁的大笑与憨傻的答话有关。婴宁的笑与憨傻的答话其潜台词是什么呢?我对你有爱慕之心,而毫无戒备防范之意。
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出婴宁性格中的痴笑与娇憨的一面,也可以看出婴宁有装傻的嫌疑,那么,这就足见婴宁性格中也有狡黠的成分了。比如:她当着鬼母的面把王子服所说的爱情告白说出,令王子服非常窘迫。王子服小声责备婴宁,“此为背人语”,[2]不可与外人道也。
但婴宁真的没有做到背人语吗?其实婴宁是做到了背人语。王子服笑婴宁痴,我们笑王子服痴。王子服以为婴宁在梦中,实则是王子服在梦中。
当时在场的有三个人:鬼母、王子服和婴宁。而鬼母耳聋,婴宁的音量恰恰使鬼母根本听不到。那么,当时能听到的也就是王子服和婴宁两人。因此,婴宁实际上是做到了背人语,而王子服以为人家没有做到背人语。那么我们再回头看婴宁说完傻话对王子服的“微笑而止”,[2]则是别有深意。也就是说,婴宁实际上是和王子服开了一个小玩笑而已,亦足见其狐性之狡黠的一面。
同时她也有狐性的狡黠狠毒。西邻子只不过是为婴宁的美貌所倾倒,多看了她几眼,并未犯下必死之罪,如果婴宁回避的话,就不会有下文了。可是婴宁对待西邻子的做法是“不避而笑”,接下来“指墙底笑而下”,[2]这就让西邻子误会了,以为是告诉他约会的地点,及昏而往,随后婴宁就将西邻子诱杀惩杀了,足见其狐性的狡黠狠毒的一面。
综上,一言以蔽之,婴宁性格在转变之前,既有少女天真活泼可爱的一面,又有狐性狡黠狠毒的一面,而少女之活泼可爱发展到极致也就是人的自然性的痴笑与娇憨。而婴宁的人的少女性与人的自然性为一体之两面,是从两个角度来指向的同一个性格,那就是痴笑与娇憨。
(三)一个主动自我调整与完善的修行过程
究竟王子服和婴宁的婚恋故事是一段天意撮合的好姻缘,还是鬼母有意安排抑或鬼母和婴宁合作导演的一段将婴宁终身托付给王子服的浪漫传奇婚恋?我认为是后者。这个问题涉及到婴宁嫁给王子服是主动还是被动的问题,所以需要论证,这可以由文本中八个传奇与巧合之处为证。
1.传奇与巧合之一:母亲平常不准王子服到郊野游玩,但在那年的上元节,因为表哥吴生的盛情邀请,得到了母亲的特别允许,可没想到刚到村外,舅舅家的仆人把表哥叫走了,只剩下王子服一人,王子服因而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乘兴独游的好机会。王子服见游女如云,并不动心。唯见一女郎携一婢女,手捻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而对她一见钟情,并害了相思病,差点丢了小命,而此女郎即为婴宁。他们的相遇与一见钟情可谓传奇与巧合之极,此为第一个传奇与巧合之处。
2.传奇与巧合之二:吴生探访婴宁踪迹未果,随口欺骗王子服说:“已得之矣。……乃我姑之女。即君姨妹行,今尚待聘。……西南山中,去此可三十余里。”[2]没想到吴生随口的戏言竟成为事实,王子服到西南山中三十余里处,真的找到了自己的姨表妹,也就是这位婴宁。吴生随口的戏言竟成为事实,此为第二个传奇与巧合之处。
3.传奇与巧合之三:王子服来到了西南山中三十余里处,见“北向一家,门前皆丝柳,墙内桃杏尤繁,间以修竹”。[2]王子服考虑到这是别人家的园亭,不敢贸然闯入,回顾对门有一块光滑洁白的大石头,于是坐下来稍微休息一下,但没想到这家竟就是婴宁家,可谓巧合至极。
4.传奇与巧合之四:王子服在墙外不一会儿就听到墙内有人拉长声音呼唤“小荣”,其声娇细,这个声音文中没有说是谁发出来的,但我们可以确定是婴宁发出的。因为从下文我们知道,鬼母的住宅里只有三个女性:第一个是鬼母,其声音不可能娇细,所以排除在外。第二个是婢女小荣,她不能自己呼唤自己吧?因此呼唤小荣者只能是第三个女性,也就是婴宁这个女一号了。
而婴宁在墙内长呼小荣之后,片刻之间,婴宁就由墙内来到了墙外,由东向西,执杏花一朵,俯首自簪,抬头见到王子服,于是不再簪花,含笑捻花入门。一个人能够片刻间从墙内就来到了墙外,可见婴宁之神通变化,按照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所谓的特异功能,那么,我们似乎也可以确定婴宁对于王子服的到来也是了如指掌的,因此有意在王子服面前做此表演。
5.传奇与巧合之五:王子服被鬼母带到家中用餐歇息,攀谈起来竟然是亲戚,于是鬼母将婴宁请出来与这个表哥相认,并议及二人极相匹配,并留王子服住下来,说家中有书可读,舍后有小园可供消遣。第二天早上,王子服果然在舍后小园遇到了婴宁,鬼母的种种说法似乎有为王子服和婴宁提供接触机会与活动空间的嫌疑。
6.传奇与巧合之六:王子服在门前大石头上坐卧徘徊长达四五个小时,而不敢贸然闯入,可见,王子服是一个胆小之人,或者说是一个守礼之人,可是在舍后小园王子服却敢捏婴宁的手腕子,并且面对婴宁大胆地进行了爱情告白。王子服的胆子为什么会越来越大呢?也许是婴宁的大笑与装傻使然。而婴宁的笑声与装傻的潜台词是什么?那就是婴宁对王子服有极大的好感且对他毫无戒备。这无疑是对他的一个莫大鼓励,因而胆子越来越大。
7.传奇与巧合之七:王子服这个不速之客,探亲都不知道亲戚的姓氏,后来被鬼母请进家里,论起来竟然是亲戚。他在鬼母处吃了几顿饭,住了一宿,第二天早上归家时竟提出一个非分之请,那就是要带走这个表妹婴宁。按照常理是应该遭到鬼母拒绝的,但没想到鬼母竟然欢喜地接受了,还说了一番话,将王子服带走婴宁这件事情合理化了:“我有志,匪伊朝夕。但残躯不能远涉,得甥携妹子去,识认阿姨,大好!”[2]叫婴宁来,婴宁也是笑着来了,让她收拾装束,她也是没有丝毫迟疑、犹豫和等待,而是高高兴兴地跟着王子服到王子服家去了。
8.传奇与巧合之八:后吴生到西南山中三十余里处去寻找鬼母的住宅,却庐舍全无,只剩下零落的山花而已,鬼母的时空突然关闭了。鬼母的时空为谁而打开?为谁而关闭?为王子服而开,为吴生而闭。为何为王子服而开?因为婴宁与王子服有一段很深的情缘;为何为吴生而闭呢?因为吴生知道婴宁的底细。
以上八个传奇与巧合之处,或者说是不合常理之处,只有一种解释能够说得通,那就是鬼母与婴宁早就了解了王子服,并选定了王子服作为婴宁托付终身的对象。说得透彻一点,也就是说,鬼母抑或是鬼母和婴宁在幕后的操纵和有意的安排,导演了婴宁与王子服相遇、相识、相知、相恋的这段浪漫传奇的婚恋故事。
由此可知,是婴宁首先主动选择了王子服,然后才是王子服找到了婴宁,作者顺势写去,始终不点破,让读者思而得之,这样就收到了机巧四伏、妙趣横生的艺术效果,给人留下了思考与回味的巨大空间,同时给读者一种如坠五里云雾的朦胧美感。也就是说,婴宁是极愿意扮演王子服妻子这一角色的,也极想把这一角色演好。这就为她性格的转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主观动力。
王子服携婴宁回到了莒县罗店村之后,有两件事使婴宁性格迅速地发生了变化。
第一件事是当王子服母亲也是婴宁的姨妈让她与自己的小女儿同寝,暗中将婴宁作为自己儿媳考察对象之后,婴宁敏感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因而她马上发生了转变。每天早晚都前来向姨妈问安,合卺之后,房中事殊秘密,不肯道一语,真是庄重知礼;每值婆母忧怒,一笑即解,很是孝敬;操女红精巧绝伦,很是智慧勤劳;少女少妇争着欢迎她,非智慧练达之人大家怎会欢迎?且她知道交浅不可言深的道理,在与婆母和王子服相处日久,观察他们对自己过爱有加而无异心之后,才直言相告自己的底细——狐狸精所生,这些都足见其智慧练达的一面。此外,她还富于感恩之心,知道感恩生父和嫡养母鬼母,痛哭流涕地请求王子服帮助其将生父秦老先生与嫡养母鬼母吴氏合葬,每年的寒食节对生父养母的祭扫无缺;也知道感恩小荣,感恩她常摄饵相哺,照顾自己,所以时常挂念小荣;知道感恩自己的夫君王子服,嘱咐鬼母不要惊吓他,等等。
第二件事情就是诱杀惩杀西邻子事件之后,她的痴笑被不笑和整日未尝有忧伤的神色所取代。我们知道,婴宁被王子服母亲作为儿媳考察对象后,婴宁发生了巨大变化,唯有一个痴笑虽遭婆母斥责却总是不改变,可见,婴宁性格之倔强,如果是她认为对的事情,别人想要强迫她改变,已成为不可能。等到诱杀惩杀了西邻子事件之后,给丈夫带来了官司,也遭到了婆母的斥责,婆婆说:“早知过喜而伏忧也,……人罔不笑,但须有时。”[2]这使她意识到她的笑会给家人和自己带来困扰乃至于凶灾祸患,出于保护王子服,也出于自己能够适应新的环境与情况的变化,演好自己的角色,于是她发誓不再笑了,但她虽不笑,可整日里却也没有忧伤的神色。
婴宁的不笑,我们细心观察,绝非是被婆母强迫的,这也是她强迫不了的。如果婴宁不笑之后,内心很郁闷,很痛苦,很无奈,那是被迫的,而我们注意到,婴宁的状态是虽不笑,却没有丝毫的忧伤,那就应该是她主观愿意,是婴宁意识到自己的笑会给家人带来凶灾祸患,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而根据客观环境与情况的变化以及角色的转换,所做出的真诚的反省与主动的自我调整,这也是对王子服及家人的爱与感恩的力量使然。
婴宁的性格转变如此之快速与神奇,其核心动力乃是与她极想扮演好妻子和儿媳这两个角色的强烈主观愿望使然。也就是说,她的转变是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与角色的转换,所做出的主动自我调整与完善,而绝不是被动的、被迫的乃至于被逼无奈的痛苦过程。这些主动自我调整绝大多数都是很自然的自我调整和转变,只有痴笑和狡黠狠毒是在遇到祸患之后,意识到其巨大危害性而后做出的自我调整与完善。这个抉择正像当年她选择王子服为自己丈夫一样,是客观、冷静、理性和富于智慧的,也是主动的自我抉择、自我调整与完善。
至此,婴宁已经由一个原本天真烂漫的爱笑的少女,转变成一个孝敬勤劳、庄重知礼、智慧练达、富于感恩之心的少妇。而其狡黠狠毒的狐性和痴笑娇憨的人的自然性也消失殆尽,从而完成了从狐到人、从自然人到社会人、从少女到少妇角色的成功转型。其性格转变之清晰轨迹,如下图:

婴宁性格三角转变示意图
而以上的性格三角:狐性、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我们是从一般人所理解的角度来归纳的。而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和儒家的中庸之道并非是指上文我们所理解的人的自然性,试想婴宁无时无刻无忧无虑的笑是接近中道和回归自然本性还是不笑但整日未尝有忧伤的神色更接近中道与回归自然本性?无疑是后者。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所认为的婴宁的社会性:孝敬勤劳、庄重知礼、智慧练达和富于感恩之心,这才是儒道两家所说的人的真正的自然本性与中道。婴宁的性格三角转变的完成,才是真正地回归自然本性与接近中道。因此,婴宁也就完成了一个“撄而后成”的自我完善的女性形象。
五、总结
在小说末尾,蒲松龄先生有一段对婴宁性格转变的评价:
异史氏曰:观其孜孜憨笑,似全无心肝者。而墙下恶作剧,其黠孰甚焉。至凄恋鬼母,反笑为哭,我婴宁殆隐于笑者矣。窃闻山中有草,名“笑矣乎”,嗅之,则笑不可止。房中植此一种,则合欢、忘忧,并无颜色矣。若解语花,正嫌其作态耳。[2]
这段评价让我们读到了蒲松龄的潜台词:婴宁的性格里有痴笑与娇憨的一面,但也有狡黠狠毒的一面。婴宁从笑到不笑,再到反笑为哭,既出自其纯真天性,亦是其生存策略使然。
婴宁的笑出自她的纯真天性,同时也来自她的生存智慧。初到王子服家,婴宁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那就是大家怀疑她是狐狸精所生。婴宁如果说自己不是狐狸精所生,那她就是在说谎,那她的人品就有问题;如果婴宁承认自己是狐狸精所生,那大家就得吓死,她也就不能在莒县罗店村王子服家里住下去,这个浪漫传奇的故事也就无法演绎下去了。那么,婴宁如何应对呢?婴宁是用笑来回应的,她放声大笑,满室妇女也都被她逗笑了。那么,婴宁笑的潜台词是什么呢?不管我是不是狐狸精所生,我对大家无害,而且我还很可爱。大家一看,这个女孩似乎确实对我们无害,而且还真的很可爱,既如此,大家也就不追究她的身世了。可见,她的笑也充满了化解尴尬处境的生存智慧。
不笑也是出自她的纯真天性,也充满了生存策略。惩杀西邻子事件给丈夫带来了官司,也遭到鬼母的斥责,给家人带来了麻烦乃至于凶灾祸患,也给自己带来了困扰,为适应环境与情况的变化,婴宁发誓不再笑了,可见不笑既是出自对家人保护的纯真天性,同时也是她自身的生存需要和生存智慧使然。
而反笑为哭,既是出自凄恋鬼母的纯真天性,也是要达成将自己生父和嫡养母合葬的目的,从而引发王子服对自己的同情怜悯之心的生存智慧使然。对于“隐于笑”这句话,有人理解为“把笑隐藏起来”,其实是误读。我们将其放在句中,就会有正确的理解,应该是“隐藏在笑里”,也就是用笑来隐藏自己的真情实感。所谓以笑解忧、以笑解疑、以笑掩智、以笑惩凶,她的笑里面隐藏着高度的生存智慧。
综上,通过蒲松龄文末对婴宁性格的总结,我们看到,从笑到不笑,再到反笑为哭,既是出自其纯真天性,同时也是她的生存需要使然。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在蒲松龄心目当中,从感性上来看,蒲松龄非常喜欢婴宁这种出自于纯真天性的笑,但从理性的角度上来看,蒲松龄先生则清楚地意识到,只有不笑,才更完美,才更接近中道,才能更好地完成由狐到人,由自然人到社会人,由少女到少妇的完美转化。
《婴宁》这篇小说塑造了一个“撄而后成”的自我调整与完善的女性形象。婴宁从笑到不笑再到反笑为哭,既出自她的纯真天性,又是她的生存智慧使然。她的性格的转变是随着环境与情况的变化以及角色的转换而主动进行自我调整与自我完善的结果,而绝非被动、被迫和被逼无奈以及痛苦不堪的。
既如此,若将婴宁性格重大转变的原因,归结为封建礼教扼杀妇女的纯真天性的结果,无疑是一个相当巨大的误读。而婴宁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也并非出自蒲松龄先生反传统文化与反封建礼教的理念,恰恰相反,我们可以确定,对于《婴宁》这篇小说,蒲松龄先生完全是出自对中华传统文化赞颂的心态而写就的。而蒲松龄先生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界的翘楚,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象生动的义务宣传员。
——众说《婴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