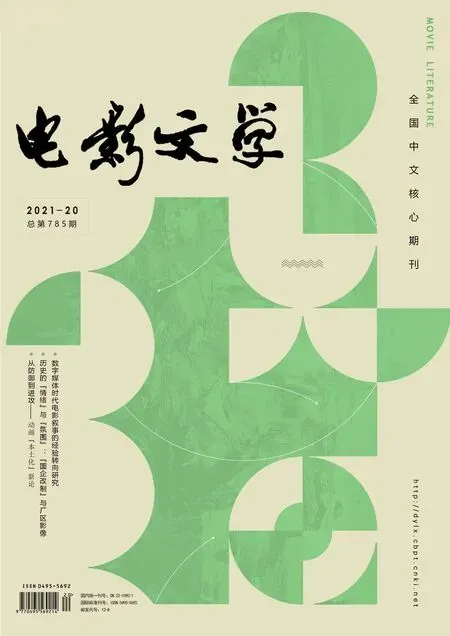历史的“情绪”与“氛围”:“国企改制”与厂区影像
周方元
(上海戏剧学院,上海 200040)
“国企改制”及其引发的工人命运跌宕,无疑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改革阶段,向市场经济转型语境下所发生的最为深刻的历史事件。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改革带来的历史阵痛逐渐消弭,曾经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开始回望反思。“国企改制”与转折期工人命运为各类创作提供了丰厚而独特的叙事资源,创作者开始以各异的文艺想象或隐或显地建构着那个时期的样子。
电影《八月》(2016)、《地久天长》(2017)在各类电影节上的优异表现,引出了近些年一个记录或反映“国企改制”与20世纪末工人命运的影像类聚。它们对“国企改制”与工人下岗的历史表达跳脱了官方预设的“大时代”视域,收缩到个人化视角。成长于20世纪末的电影人,作为亲历者的他们还原历史现场的方式是以记忆为线索,有意忽略事件本身而寻求“情绪”“氛围”等个人感知,将“国企改制”历史事件延宕后置,把工人主体情绪、生存体验、时代与空间氛围强化前移,注重感性内容的“真实”。
为了避免研究分析的泛化,我们把文本对象范围界定在近十年拍摄的影片,由此可以按时序得出一条清晰的影像序列:贾樟柯导演的《二十四城记》(2009年),王全安导演的《纺织姑娘》(2010年),张猛导演的《钢的琴》(2010年),张大磊导演的《八月》(2017年),相国强导演的《少年巴比伦》(2017年),李远导演的《六人晚餐》(2017年),董越导演的《暴雪将至》(2017),王小帅导演的《地久天长》(2018)。本研究以新历史主义对文本考察的微观理论作为参照,以情绪化工人主体与具有时代体验感的“国营厂区”耦合出的影像为支点,分析这些电影重返历史现场的路径。此外,本研究在影像释义中拓展延伸,上升到电影与历史的动力学关系的理性研究,借由罗森后现代的“实验史学”思想,分析“国企改制”电影背后所呈现的历史观念与历史文本样态。
一、虚实之间:“国企改制”的反身历史表述
“国企改制”作为一种历史事实,电影对其表达时,必须思考采用何种历史观念,如何建构历史样貌,表达怎样的历史态度等一系列问题。作为国家变革与社会转型期成长起来的电影创作者,他们不约而同形成了一套在回溯历史、建构历史原貌、宣泄历史情感等方面相似的影像表达。
个人史作为一种历史书写方式,它是指“在新的历史思潮下历史叙述者用个人化的视角进行一个历史故事、历史个体的情境表达,关注历史当中的故事、人和一切东西,尤其是那些历史中被淹没在宏大叙事之下的小人物、小故事,以及围绕着他们的被称为属于个人的历史材料,比如人物的个体记忆、情感把他们结构到叙事中”。首先,从视角来看,这种历史本身是一种个人相关性的历史叙述方式,“所表达的历史并不是一个‘鸟瞰’的时代,而是一个人眼中‘当下’的时代”。其次,从书写者和文本间关系看,个人史表述带有一定反身特征,叙述者的历史情感、经验与文本内容构成互文性成为个体“过去时”的镜像。创作者本身也是历史亲历者或旁观者,真实历史事件下借个体叙述的故事也是描述自身的记忆。最后,个人化历史在历史观念、组织史料等方面抛开严密的证伪逻辑,转向用文学化、叙事化编织出历史,强调虚构情节与真实经历混杂的历史表述中寻求一种主观性的真实,个人情绪的真切性成为明显标志——“目的不在于讲历史事件,在于寻求一种历史情感,以及历史体验,最终指向个人自身。”
电影主创们的人生轨迹几乎都与“国企改制”重叠。《钢的琴》的导演张猛、《六人晚餐》的导演李远、《八月》的导演张大磊,这些创作者是“国企改制”的亲历者,出生于工人家庭的他们目睹了父母、亲友或邻居集体性陨落,他们的童年或青春成长伴随着这场社会变革,对其有着深刻体悟。而有的曾经作为工人,这段时光成为美好记忆,对工人身份有归属感,例如《少年巴比伦》的编剧路内与导演相国强。而像董越、王全安这样的创作者,虽没有过工厂以及与“国企改制”直接相关的经历,但如董越谈到这段历史时说:“90年代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段。跟我以前的这种感受和体验不太一样了,那一时期中国经历的国企改制与工人下岗让我感觉中国社会更丰富了,然后故事更多了。”这些电影创作者个人化表述让历史游离于虚实,影片中“讲述者”视角收缩化、真实历史与虚构叙事糅合,为“情绪”的真实提供必要的路径与资源。
《纺织姑娘》就是以下岗女工李丽的视角展开的,虚构李丽身患绝症的命运悲歌同真实“国企改制”历史共同构成叙事。《钢的琴》通过钢铁厂下岗工陈桂林“造琴夺女”的故事,映射“国企改制”语境下男性工人群像式的生存轨迹与时代情绪。这一故事灵感源于他在铁岭看到的工人制作的钢琴,而张猛也通过陈桂林展现了国企工人“自己做汽车的、做自行车的,好多人都愿意做这种事”,热爱劳动、自力更生的特点。《暴雪将至》中的余国伟与燕子虚构的情感来自董越的亲眼目睹,而“燕子”这一女性形象也来自自己家附近见过的已失踪的理发店姑娘。《少年巴比伦》与《六人晚餐》则都是将个人化青春视角与“国企改制”、自身工厂经验拼贴出真实与虚构的混合故事。路小路与丁成功的青春成长都来自他们年轻时的工厂经历。
与之类似的《八月》,故事来自张大磊的童年经历,以少年小雷视角讲述了“自己”小升初假期整个家庭、工厂大院经历的下岗潮流。比如小雷家和韩胖子的关系,母亲用小勺给躺在床上的八十多岁的姥姥喂饭等。“这部电影其实就像我的一场白日梦。1994年夏天,姥姥的母亲也同样卧床……我坐在姥姥家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晒着太阳,突然感觉时间慢下来了。”而《二十四城记》作为非典型的实验化电影文本形态,它以纪录片式的镜语修辞建构具有纪实倾向的电影,这种历史叙述的实践形式同样诠释了历史真实与虚构的混合。通过采访借由职业演员扮演的“口述史”的形式把“讲述者”身份的扮演性与假定性消弭,将其转化为一种个人完全真实的历史经验。
二、“英雄迟暮”与“生而忧伤”:代际间的工人情绪
影像序列中,“下岗”成为父辈工人不能承受的“创伤”——物质缺失、权利解构、价值崩塌,导致了他们情绪的负面化。作为“创伤”的应激反应,他们或以缄默、失忆姿态承受痛苦,如《六人晚餐》中的丁伯刚与苏琴、《八月》里的父亲;或回避现世、追忆过往,如《二十四城记》里被采访的老工人、《纺织姑娘》中的李丽;或歇斯底里挣扎,如《钢的琴》里的造琴工人们、《暴雪将至》中余国伟。“无力”与“失落”成为他们在情绪上的共同症候,并以此引导情节走向。
《六人晚餐》中的丁伯刚与苏琴、《钢的琴》里的陈桂林、《纺织姑娘》里的李丽、《暴雪将至》中的余国伟都将失落与无力外化为对感情关系的难以掌控,爱情经历一番曲折后最后都无疾而终。丁伯刚和苏琴一个为了儿子工作,另一个为了儿女生活的感情结合,他们的情感命运无法由自己控制。因为下岗、子女情感等原因催化了六人家庭的解体,也导致了丁伯刚完全失忆,结尾苏琴只能望着丁伯刚远去的背影空叹。陈桂林赌上性命、金钱与尊严,歇斯底里的造琴行为没能维系与妻子的婚姻关系。此外,淑娴与王抗美两人的感情也历经波澜起伏。李丽与前男友的炙热感情更是不可言说的过去,下岗卖鱼的丈夫也始终无法让她幸福。身患绝症后她隐瞒丈夫,前往北京见到真爱后也只能叙旧怅惘。而燕子当着余国伟的面跳桥自杀,后者却无力救助,永远失去了爱人。
此外,父辈在面对子一代反叛与离心倾向时也显示出了极大的无力感。父辈权力焦虑笼罩下的两代关系在决绝反抗中,以子一代的胜利告终。例如《少年巴比伦》与《六人晚餐》里的丁成功、路小路对父亲的极力挣脱,以“逆反”的行为反抗父亲对自己的安排;《二十四城记》里,父辈面对镜头时要么无奈道出“儿女们已无能力顾及,随他们去”,要么避而不谈;而《八月》里父母的无力源于他们话语权丧失,无法为小雷的前途做出“安排”。这种失落与无力的“边缘性”体验不仅在社会中,就在家庭内部也被边缘化了。
父辈情感关系中无力、失落的“边缘性”情绪共同渗透着他们集体性的时代焦虑。他们作为“工人阶级”的虚妄以及持有“工人”身份的他们在现代社会语境中的错位、失势,在影像中呈现为一种“劳动—尊严”等同的情感逻辑。1992年《关于深化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意见》的出台,打破了“铁饭碗”“铁工资”,工人的工龄被买断,工人从英雄阶级转到凡俗个体,开始了世俗化生存。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以共产协作精神、组织性纪律性为特点的“劳动”是工人应恪守的美德与守则,同时也是实现工人自我价值的唯一途径。工人阶级内部形成了以“劳动崇拜”为内核的“劳动美学”——将劳动与个人尊严、个人价值等同。“下岗”让他们失去了劳动的权利与生活尊严,导致了他们主体地位以及主体性的丢失。正如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所说:“丢失工作的工人们也丢掉了伦理——他们成为没有工作的穷人。”
《钢的琴》里的陈桂林找“快手”的那场戏就是通过“劳动价值”与“专业性”成功说服其入伙,而季哥也执意要自己工作完成后才被警察带走,张猛通过仪式化的“交活”呈现。虽然造琴没能追回女儿,但每个人都在造琴的集体劳动中重拾自我尊严。《少年巴比伦》中“牛魔王”的工人尊严通过它的传奇过往呈现——修过日本水泵,处理过爆炸事故,还“上过天”。退休时戴着大红花,敲锣打鼓离开工厂。《暴雪将至》的余国伟作为厂保卫科工人“玩命”的歇斯底里到丧失理智的案件侦办,就想通过“劳动”来证明自我,摆脱下岗危机。此外,《八月》父亲下岗后无所事事深夜朝空气打拳的戏,在阳台“卖命高歌”的下岗工;《二十四城记》中贾樟柯对工人仍在坚持工作的镜头等叙事段落都映射出了父辈共有的劳动崇拜,他们丢失的尊严与主体意识皆想通过“劳动”的方式唤回。但由于“现代社会转型发展曾经衡量工人阶层的规范土崩瓦解,经济模式与文化模式的转变,市场与资本的逻辑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完全不同的价值系统和评判标准产生”,工人从生产创造者变为被放逐的人,“劳动—尊严”价值体系在市场化语境中变得虚妄,也注定了他们在两性以及与下一代的感情中的失势。
与父辈的失落相比,子一辈自诞生一刻就跌入了无从选择的改革阵痛与工人阶级身份。注视着父辈的“下岗”而成长,因此他们的童年与青春伴随着无法逃遁的伤痛阴影,形成了“生而忧伤”的情绪。在影像中,不同于父辈固有价值体系的崩塌、主体自我意识突然抽离而导致的情感混沌与无力,子一代始终伴随着“生而忧伤”的情绪背反。
一方面他们下意识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理性,印刻着“后工业社会”的价值特征,力图挣脱工人命名、逃离厂区、远离父辈。《六人晚餐》中林晓白、林晓蓝对于厂区的逃离,他们看到了丁成功与苏琴的落魄,家庭的破裂、厂区的混乱以及情感乱伦。因此,他们努力学习,试图逃离工厂摆脱工人称谓。《少年巴比伦》子一代的长脚、路小路拼命学习考夜大,免于厂领导安排的“三班倒”,摘掉工人帽子,进入管理层。《二十四城记》里娜娜更直接地说“我不想回那个家,那里充斥着我爸失败的氛围”。子一代与父辈产生了难以逾越的价值间隙,他们力图通过“学习”而非“劳动”寻求身份的转变。“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工人也有着代际差异,不同时代精神烙在不同个体上,因此也会产生貌合神离。”父辈的价值与理想被子一代置换,在“后工业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浸淫着新的价值标准。工人子一代更寻求一种中产阶级的命名,“即脑力劳动、有较好的工作环境,对工作对象、时间以及私人生活有支配权”。
而另一方面,伴随“国企改制”的成长岁月成为子一代不可回避的记忆,站在当下进行历史回望时,他们不由进入了对过往的迷恋怀旧以及对父辈的同情怜惜中,同理性逃离混合出“生而忧伤”情绪的复杂性,因此所有影片都以追忆铺陈叙事。比如《八月》的事件、场景以及情绪感受全来自小雷(张大磊)的儿时记忆;《六人晚餐》和《少年巴比伦》分别以林晓蓝与路小路的青春爱情记忆展开;而《二十四城记》里子一代的赵刚、玩滑板小姑娘、娜娜同父辈回忆叙述的并置等,影片内外的“故事讲述者”发生了代际交接。他们依旧处于社会转型及其带来的价值缺失与理想幻灭的当下,成长记忆与伴随的忧伤情绪成为感性怀旧资源,试图用回忆的方式追溯不能言说的过去,成熟的他们也更能够理解父辈的心境。影片中子一代与父辈形成叙事交叠,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情绪也空前达成一致。子一代的由理性逃离到感性追寻的“生而忧伤”为父辈工人提供了情感催化,并完成了认同,构成了共有的“定向过去”的怀念情绪。子一代在怅惘追怀中不仅完成对青春成长的回忆,也对父辈产生同情。
三、成长的滋味:“厂区情结”与城市化记忆
作为承载情绪个体的介质以及事件发生的场域,空间成为衡量历史现场建构真实性的重要参照。人的实践界定了空间,又在二者辩证的互动里指定了空间,空间的特点是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国营厂区”本质上就是所携带的工人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与时代氛围。这些作品里,厂区不仅是故事与人物活动的布景与道具,更作为电影结构性、叙事性的组成部分,为工人主体的情绪体验提供具体的现实落脚。
电影中琳琅满目的各类国营厂区——纺织厂、军工厂、玻璃制品厂,还原了时代感与生活感——由工厂与家属区构成的完整厂区大院生活,“将生产、生活、教育、娱乐活动与消费融为一体,是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熟人社会”。大院生活的历史体验感,被电影以流淌性的日常记录呈现出来——由同事、亲友构成的熟人社会,不经意地唤起记忆中邻里之间平淡生活与相处场景。《二十四城记》里家属院里的邻居们的寒暄问候,小花、宋卫东站在大院里对集体生活的回忆;《纺织姑娘》中女工们总是聚集在厂区俱乐部的剧场上演唱苏联歌曲;《八月》中大院里大人们在晚饭后聊天,孩子们在周围嬉戏打闹,深夜一起到小磊家观赏昙花。厂区大院内的生活化镜头让电影从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火红年代走出,进入平淡而又真实的工人生活中,呈现出工业、工厂背后更为温情、丰富的时代感。
事实上,伴随着新一轮城市化建设的高歌猛进,工人下岗、烟囱爆破与流水线拆除,大院生活也随着国营厂区的命运,不可回逆地走向“废墟”。它成为20世纪初城市化记忆的一部分,以及供人凭吊怀念的历史旧物。正如张大磊讲拍摄《八月》的初衷:“有过厂区大院生活,或者同样有过八九十年代还多少残留着社会主义的那种生活方式那种观念,是那个时代过来人的一些共性吧。”导演张猛将同样的情感称之为“厂区情结”:“我记得小时候,铁西的工人村,包括俱乐部、游泳池、酒厂,还有大的菜市场等,都是跟工厂紧密联系起来的。时刻都是你在家里边就能闻到焦炭的味道,一开窗户就能看见烟囱。厂区的这种感觉和体验不能忽略,《钢的琴》最开始是因为想缅怀那个时代。”厂区大院及其营造的“社会主义的感觉”指涉着新中国成立初期那段工业建设年代。封闭性的空间与当代中国社会区隔,形成了一种区域性的带有独特体验的,属于工人阶级的厂区文化。“工人是单位制的一部分,一旦进入厂区就像进入保险箱,衣食住行都有保障,加之各种关系重叠,客观为厂区的生活创造极强的集体感。”在其中的工人虽认同睦邻友好与人们之间的真情与人性,但在“效率—公平”引导的历史理性变革中,这种社会主义大锅饭式的“国营厂区”生态终会被新一轮现代城市发展取代。
在“国企改制”影片的创作者们无一例外地捕捉到了新一轮城市发展与土地开发对于国营厂区的摧毁,如列斐伏尔所说的,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铸造,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历史的推进中,国营厂区势必会被更适合的现代经济发展空间所替代。在影像中平静而美好的大院已经无法隔绝声色犬马的外部世界,被撕开了口子,成为嘈杂混乱的底层空间。《纺织姑娘》里的录像厅,《六人晚餐》里的音像厅、台球厅以及《二十四城记》中远处叮叮咣咣的商业楼盘建设声,预示着国营厂区的历史消亡。因此,“张大磊们”在情感上无一例外选择了为“国营厂区”所承载的昔日集体文化生活赋予温情脉脉的诗意。
更加有趣的是,《少年巴比伦》《八月》《六人晚餐》的青年视角暗合了个人成长、厂区生活与城市化变革重叠的历史,并且故事都发生在夏季。似乎夏天在每个个体的成长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夏天的艳阳下,所有情绪与感觉都异常旺盛与浓烈。《八月》中伴随着大院中不知疲倦的蝉鸣,远处叮叮咣咣的金属碰撞声依稀可辨,这意味着,城市建设正在高歌猛进又似乎悄无声息地进行,预示着个人成长中潜伏的危机与不安。此外,如电影片尾处呈现的字幕内容:“夏天过去了,开学了,我的童年也结束了。”寥寥几字包含了夏天的无限伤逝,不仅是对以“厂区”为承载容器的无忧无虑童年的追忆,也标志着这一代人初尝成长苦涩,不愿面对长大后的世界。在这些电影中,夏天标志着成长,亦因此夏天好像一切都是灰的,厂区破产,家庭变故、亲友离散,父母失业下岗,更使得浑浊的空气中流动着灰暗的味道,绝望和失落的情绪笼罩在迅速扩张的城市上空。因此在回望和感受这段与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交叠的个人历史时他们带着一种既忧愁又留恋的混杂情绪,并将其折射在对空间的指认上,书写出了独属于这一群体的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影像。
余论:让“感觉”与“情绪”重返历史现场
总的来说,影像建构的“国企改制”历史并不是一种“纪实”文本,而是基于一定的时间距离的个体回忆,文本形态上呈现出自我反身表达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降,经典理论解构引发了历史“后结构主义”转向,其根本性影响为历史书写的观念与形式变革。在大众文化语境中,历史无法显现出严肃观念与立场,“历史已放弃宏大价值与宏大视域,或者说已无力生成宏大性了”。形式上“从实证主义下居主导地位的经验验证性论述和正确逻辑性的自然科学概念与形式,转变到由以文学化叙事和文本分析的新历史形式,个体情感与感觉成为历史表现的重点”。
因此,一直致力于电影与历史交叉研究的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罗森斯通(Robert A.Rosenstone),在《再现历史:电影与新的历史结构》(Revisioning
history
:Fil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past
),《电影中的历史与历史中的电影》(History
on
Film/Film
on
History
)以及《反思历史的实验》(Experiments
in
Rethinking
History
)等论著中,对历史多种形式可能性进行思考,提出以电影作为载体的“实验史学”观念与形态。“实验史学”是指突破传统的历史叙事,采用“感知”和再现的形式唤醒过去的“在场”和“经验”,表达的是一种历史情感。在罗森斯通看来,“引入情感是一种新的历史类型,是在反思记忆、历史、个人经历和公共事件的可能性、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如何利用这些东西来了解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世界,通过特殊的‘情感’和‘体验’来了解历史”。此外,由于电影视听表意的丰富性,可以看作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状况的隐喻、寓言、表象或症候,因此罗森斯通认为电影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感载体”——“电影以影像的形式、电影的手段也是意义内容的表现形式,能胜任历史的表达,并且是传统书写不能达到的效果,影像手段是追求艺术上的真实,更能体现这种体验与历史情感。”在“实验史学”观念及其形式下,情感进入历史,但因情感无法实证化,唯一确保的是“历史感”的存在与真实性。所以这里的“历史”不是指考据学上真实发生的事件,它是我们要面对的过去,以及我们过去的那种个体状态。如果以传统史学书写的眼光审视“国企改制”影像序列,它们似乎显得太过轻浮与模糊。但毫无疑问这种充满“情绪”与“体验”的表达,重建了个体与历史、时代环境之间关系的心理想象。从创作者自身来讲,面对“国企改制”的真实历史是极为残酷的,当下缠绕在传统价值与现代理念两难困境中,他们迫不及待地逃离到绵密的情感世界内,追寻自己过往的感性“存在”与原始身份。对于有过共同生命经验的观众来说,无论是父辈工人“英雄迟暮”的情绪、子一代的“生而忧伤”还是代际共有的怀旧情感,这些都与时代体验感甚深的“国营厂区”构成了历史现场“感觉”真实的新维度,其目的重在唤醒集体记忆,让曾有共同历史体验的观众找到历史的真实感。大多数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国人,这些生命经验都是常识,是不太个体的,但同样也是个人与独特的。而这种讲述是希望提供给观众一个直观的、可见的想象空间,把自己投射其中。历史事件与语境的纷繁复杂在带有创作者注解的处理后,消弭了历史负重感,强化了感性内容的“真实”。有同样记忆的“在场者”在“情感”与“体验”上与自身经验完成对接,唤醒他们的集体无意识,而电影无意中也完成了某种“重构历史”的功能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