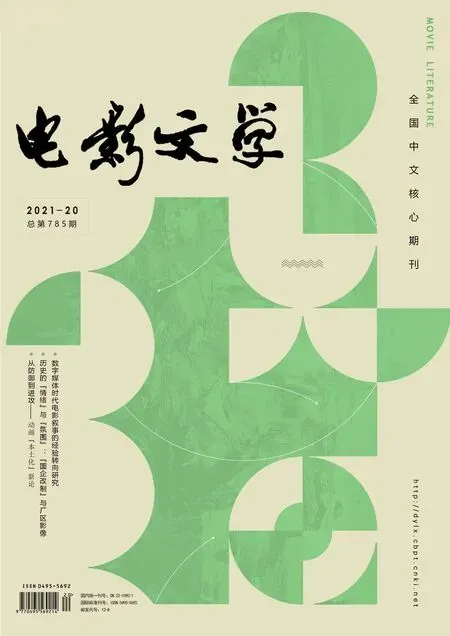论近年来国产电视剧中的多视角叙事
陈湘妍
(长江大学,湖北 荆州 434020)
“多视角”叙事较早是源于文学叙事概念,法国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在《修辞格2》一文中提出了“叙述聚焦”的概念,从叙述者的观察角度出发,提出了业界公认的叙事视角三分法,分别为:零聚焦叙事、内聚焦叙事、外聚焦叙事。他在内聚焦叙事的细分中提及多重式内聚焦的方式,即多个人物的视点多次提及同一个事件,为威廉·福克纳、芥川龙之介等作家在作品中曾运用的叙事手法立下了明确的概念。由于电影是以呈现活动画面为主的叙事媒介,与文学叙事中“认知与观看含混”的视角有所不同,电影的视角概念明显与热奈特所提出的“焦点人物绝不从外部被描述、被表示”的观点有所抵触,摄影机是电影叙事的一个特殊“视点”,它在交代叙述者的局限视点之前,又必须从外部表现出这些叙述者,因此电影研究学者安德烈·戈德罗和弗朗索瓦·若斯特在文学聚焦理论的基础上,将电影聚焦的含义进行了扩充:其一是以“视觉聚焦”表示摄影机所展现的与被认作是人物所看见的之间的关系,因考虑到声音对于电影的重要性,学者们又提出了与此相对称的“听觉聚焦”;其二是继续以热奈特指出的认知聚焦表示“叙事采取的认知焦点”。
介于文学与电影的媒介差异,文学偏向“想象性”,而电影则偏向“具象性”,多视角结构应用的广度与深度也有所差异,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内容而言,文学中的多视角应用更多是对传统的叙事手法抑或是对不堪现状的“反抗”及“叛逆”,从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及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等作品便可窥见端倪,在文学叙事中,每一次的叙述视点转换总是复杂多变的,导致创作难度增大,因此相对而言,多视角叙事在文学创作中还是较为少见的,反而多视角模式更适用于以“具象化”“感官化”为特征的影视环境,影视语言使得视角的切换更为直接清晰,多视角客观叙事使得人物形象更为立体、叙事结构更具多变趣味性,满足了受众力求呈现真实全貌的需求,而采用多视角主观叙事可以打造出一个多维空间,以每个叙述者自身的主观视角,对同一件事发表不同的声音,具有复调多义性,主观视角令观众更有代入感,每种视点代表着不同的态度,观众可以在多种视点(多种认知聚焦)当中组合、建构自身的认知判断。
虽然电影与电视有很多相似之处,常以“影视”这一概念并提相称,但是电视有自身独具的特征,电视是以大众趣味为基础的通俗艺术,其日常化、娱乐化、通俗化等属性使得媒介本身更为贴合大众,电视新闻、电视纪录片、电视节目等多样式的电视形制为电视中“真实”的原则把控提供了丰厚的经验积累,使得电视剧叙事也不自觉地带有明显的经验模式。在传统的电视叙事模式中,遵循“日常经验”是电视叙事的惯常观念,以至于忽视、遗忘了“审美体验”的意义生成。多视角叙事作为具有审美内涵的叙事手法之一,在以往的国产电视剧中很少出现,但是随着电视叙事观念的更新变化,在近年来时常会涌现出使用多视角叙事手法叙述的剧集,电视剧叙事手段的不断出新,昭示着电视叙事表现形式会呈现出新一轮变革的趋势。
一、多视角叙事盛行的社会背景
近年来在荧屏中涌现出很多运用多视角叙事手法的电视剧,分散至不同的题材内容,有洋溢家国情怀的“大选题”,例如献礼剧《大江大河》、抗疫剧《最美逆行者》《在一起》及扶贫剧《最美的乡村》《脱贫先锋》等,也有聚焦于个体心理情感的“小选题”,以《我们与恶的距离》《叹息桥》《摩天大楼》为代表的剧集均获得了豆瓣高评分及观众好口碑,“多视角叙事创作”是众剧集一致吸引观众眼球的相同标签,这些电视剧的叙述形式及内容思想都引发了观众的热议。为了更好地了解多视角叙事的应用,孕育其生长及发展的社会文化语境值得我们加以关注。
21世纪以来,在高科技的推动下,新媒体产业如同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打破了传统媒体的惯有布局,重新建构起市场的生态环境。随着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互通、移动终端的普及、媒介表达的融合,电视作为一种技术媒介,技术的发展、更新不仅影响电视制作形态、运作方式、传播效果等外在特征,而且会带来电视思维方式的深刻变化。电视思维是根据电视的本性,以电视语言符号为介质,反映和揭示电视活动的规律及过程的一种特殊主体思维方式与类型。革新电视思维是电视叙事艺术发展的根基,社会文化的语境大背景间接或直接地影响着电视的主体思维,而电视叙事更是涵盖了多层次思维及文化整体观念的架构。电视思维属性中的日常性,说明了“传受关系”对于电视叙事的重要性,而这种关系也随着电视思维的革新有了新的诠释空间,近年来引起广泛关注的互动剧无疑是最好的例子,交互关系是互动剧的本质,其核心在于观众与作品文本之间的交互。互动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传受关系,使观众在观影过程中由“真实客体”转化至“仿真主体”,使得受众的主体意识得以提升,而在互动剧中也大量运用了多视角叙事方法,从而进一步拓展了电视思维及电视叙事原有的认知,表达叙事态度更具开放性和多元性,因此也就促成了电视剧中多视角叙事手法广受欢迎的现状。
电视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建立在消费浪潮构建的特定社会语境中,电视叙事应当要敏锐地感知语境中文化的变化,唯有将自身叙事与社会文化语境紧密相连,才有可能更好地把握如今电视叙事发展的动态化进程。
二、叙述主体的本质与姿态
电视的叙事主体承载着整合社会意识、传承文化经验以及宣扬意识形态的功能作用,在以往传统的叙述话语中,电视机制背后的超级叙事者占据了绝大部分的话语权,尽管在当代电视中,超级叙事者的存在是难以避免的,但伴随着叙事媒介的广泛普及,真正的叙述主体得以突破超级叙事者的管控,因此正确地认识电视叙事主体的本质及价值有利于大众更好地把握当代电视叙事的创新趋向。
结构主义叙事学中的“叙事者”一般被定义为“陈述行为的主体”,他起到隐藏或揭示文本中人物思想的作用,令受众轻易地理解他的心理观点。而后现代叙事理论认为的“主体性”则更多隐含着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权威。对于电视叙事而言,叙述主体“我”的态度至关重要,“我”又分为“小我”和“大我”,电视叙事被视作社会的“公共领域”,是面向区域性、全球性进行扩散传播的社会性媒介,“大我”的主体位置也显得尤为关键,以往电视剧的叙述主体“小我”通常都是服从于叙事功能的建构,崇尚淡化“小我”突出“大我”,从而导致人物形象单一化、极端化、失真化等诸多问题的产生。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叙事主体的另一角度——“小我”的价值得以重新审视,在阿尔都塞看来,叙事者作为一个“主体”,实际上是一个被意识形态建构的虚幻自我,这表明“小我”与“大我”之间应是需要维持在平衡、和睦的局面,“大我”多体现为上帝视角,隐藏叙述者的痕迹,无主体或者是大主体的传播,很难与观众进行真正的叙事交流,而“小我”多体现为主观视角或主客交融视角,有叙述者明显的讲述,一般远离意识形态,却有着历史精神价值,进入叙事交流层面容易令观众产生情感共鸣,两者间功能及意义都有所不同,相互融合方能实现更好的叙述效果,如何更好地塑造“小我”形象也成为近年来电视剧所关注的重点研究的问题。
在故事策略上将“小我”更为精细地进行了叙述主体分裂化及类型化的调整。叙述主体身份的裂变是现代文化危机的具体表现,正如英国学者斯图加特·霍尔(Stuart Hal)所说:“主体在不同时间获得不同身份,再也不以统一自我为中心了。我们包含相互矛盾的身份认同,力量指向四面八方,因此我们的身份认同总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相对于电影、戏剧中以历史眼光来审视事物的叙述者而言,电视叙述主体更具鲜明性、灵活性、直接性,其经常在叙述过程中反复地现身。通过对近年来影视剧中叙述主体的观察便可得知,创作人员更为重视对叙述主体的关注,采用多视角的手法来分集集中刻画单个叙述主体,在每集的片头打出叙述主体的名字,例如《摩天大楼》和《叹息桥》均以此方式引导观众关注的目光。叙述主体身份的分裂使得一个“小我”发散出多个层面,使得在“小我”的微观格局中窥见“大我”的思想容量,作为叙述主体,可能是“故事层”中“叙述的我”,可能是“故事层”中“参与的我”,也可能是令剧中的人物直接面对镜头说话,打破“第四堵墙”,塑造出由“故事层”折射到现实中“拟像的我”。主体身份的裂变使得主体面貌呈现出多样性,更为深刻地刻画出剧中人物之间的情感羁绊,以具体叙述的声音“复调”牵引出更多人性的复杂多面性,而这些叙述复调夹杂的矛盾、悖论构成电视叙事的真实性,使得电视叙事更具人格化魅力。叙述主体的类型化须具备典型性,既要代表该群体发出真实的声音,又要与其他叙述主体共同构建统一的主题,如《我们与恶的距离》一剧中虽从不同叙述主体的立场出发,尽管每个主体发出的声音互不协调甚至相互抵触,但叙述主体的意志具有聚合性,以各自的立场正向或反向地向公众抛出了一个心灵考问:“是否每一个平庸的参与者都具有‘杀人’的潜在可能性呢?”为了使得“小我”一方面能彰显个体人格化魅力,另一方面能有效地与“大我”所极力追求的宏观意识形态紧密相连,对叙述主体进行塑造,必须将社会集体背后的生产关系、意识形态、符号规则都合理地隐藏进去,实现对叙述主体的“新建构”,以待观众在观剧过程中进行自主“解构”。
三、叙事视点的应用
华莱士·马丁在其著作《当代叙事学》中,用“视点”来建构起叙述者与故事文本的紧密联系,视点的选择代表着叙事主体的立场,是主体具体落实到文本内容的落脚点,同时也显示出构成叙事文本过程中的隐性规则与技巧。托多罗夫认为:“一个物体的各个方面都是由为我们提供的视点所决定的。”因此,叙述主体选用何种视点会极大程度地影响叙事过程中“看”与“说”的方式,进而影响叙述主体话语输出的目的成效。“视点”暗示着叙述主体在所站立位置投射出的无形目光及相对的观看视野,对于以大众文化消费为主导的电视叙事而言,荧幕上投射出叙述主体的“视点”与观众的“目光期待视线”相吻合,起到引导性、指向性的作用。在传统的电视叙事中,由于叙事主体与客体之间情感联系的脱节及叙事视点的重要性意义尚未发掘,加之背后隐含着“群体化”倾向的超级叙述者的讲述及社会集体意志趋向的动因,前期的国产电视剧通常会使用客观、主观、主客观交替等单一类型视点,主张站在固定的立场来观察、表现生活,对意识形态进行单向性的输出。随着当代多元媒介文本叙事对电视媒介传统叙事的冲击,促使其自身叙事态度的设定须与时俱进发生转变,以新的时代化眼光去重新审视电视剧中常规的叙事视点,加之影视制作者对叙事主体立场的深度“耕耘”,吸取文学、电影、游戏等其他媒介的叙事特色,逐渐构建出一种具有平等对话特征的多视点叙事。多视点叙事意为一个或多个叙述主体通过不同的单一视点观察事件,以此来展示事件主体的全貌,多视点叙事并非单纯的摄像机位置变换,更重要的是视觉聚焦、听觉聚焦以及观众的认知聚焦发生变化。叙述主体在事件中处于何样的状况、位置,也就决定了观众认知聚焦的信息来源,而多视点叙事则为观众认知聚焦提供了多样的信息获取路径。
近年来,国产影视剧中的多视点叙事应用大多围绕于营造“群体性”“多义性”“互动性”这三类叙述效果,在不同类型、题材的叙事文本中会酌情增减应用的比例。在彰显家国情怀的现实主义题材剧中,以多声部结构着力打造强大的集体凝聚力,作为向改革开放40周年致敬的主旋律献礼片《大江大河》,在剧中用宋运辉、雷东宝、杨巡三个不同人物的视点来依次代表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的三种类型声部,用不同人物的单独声部进行平等的对话交流以形成极具价值的复调思想,对社会上不同阶层的小人物进行生存境遇、命运发展的描摹,以个体发展来映射时代的风云变幻。同理,在表现国家重大新闻事件时,运用多视点叙事也能有效地将个体的力量上升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在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的特殊年份,真实事件为灵感底本的抗疫题材剧被搬上了荧屏,记录下全民在抗疫过程中众多感动的故事,以《最美逆行者》《在一起》为代表的抗疫剧采用了单元式结构,以“集”为“视点”划分的基本单位,在各集中汇入各行业“平民代表”主客观交织的视点,共同“谱写”齐心协力战胜疫情的“英雄篇章”。脱贫攻坚作为近年来国家聚焦的重大议题,为了令观众也一同了解、关注脱贫攻坚的具体工作,近距离地感受中国乡村的历史变化,广电总局推出了众多脱贫攻坚重点剧目,呼吁讲好中国故事,要时刻紧扣脱贫攻坚的主题,从不同的风格、角度、地域进行多样化发掘,电视剧《最美的乡村》运用了单元式结构构建布局,在多视角下表达出差异化,聚焦于唐天石、辛兰、石全有三位共产党员深入农户开展精准脱贫工作的故事,三个不同性格的独立人物碰撞进而产生出更多的故事,书写扶贫故事更为立体、丰富,使得观众代入感更强。多视角叙事所营造出的“群体性”效果,往往是和谐并进的,多个视点共同服务一个宏大的主题,相较于一个“大我”的宏观历史叙事,以多个“小我”的微观日常化叙事更容易被受众所接受,以“小我”群像化叙事表达“大我”主旨思想的叙事手法,也会是之后主旋律及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热衷采用的手法之一,受众可以在观看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输入。
“多义性”则引鉴了电影叙事惯常营造的叙事效果,例如黑泽明的代表作《罗生门》运用了多个人物视点进行叙述,“视点”所展现的是“感知或观念上的位置,按照这一位置,叙述的状况与事件被表现出来”,在不同的视点中出现了主体间不同的思维偏向性,以此便形成了影片的多义性。因此“多义性”与叙述主体的立场紧密相连,有利于主体立场的讲述真实度更高,反之同理,在悬疑剧中主体的立场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创作者通常会选用可靠叙述与不可靠叙述的混杂,在矛盾中制造悬疑、紧张、不安的氛围,例如《摩天大楼》通过查证多个主体叙述的真伪,将事件抽丝剥茧进而推导出事件的真凶。若是主体的立场是清晰明确的,可以利用叙述主体的论述赋予剧作多元的观点激荡,例如在台湾播出的现实主义题材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故事围绕着“李晓明杀人事件”进行展开,选取了受害者家属、加害者家属、辩护律师等多个叙述视角,全方位、多角度地呈现出“杀人事件”给不同类型的群体所造成的伤害,促使观众沉浸在多角度的认知体验中进行深发性的多义思考。也可用于叙述主体将信息传递予客体形成的错位时间差,以至于信息传达存在多义的属性,随着叙述视角的变换及影片故事进程的推动,观众的认知聚焦也随之发生“累积式”变化,由起初片面的认知逐渐归整为统一的认知体系,而这个规整的过程需要依靠观众的主动参与,将片中片面化的意义信息与自身所经历的经验体系融为一体,自觉地做出价值的判断及选择。新港剧《叹息桥》采用了多视角的手法,围绕着六个关系扑朔迷离的主角进行情节展开,将不同时空及不同人物视角间的信息量相互陈述补充,在情节的重复中表现个体心理的差异,以多视角切换微妙地表现出单独个体隐秘的心声以及主体间复杂的情感纠葛。
电视剧中的“互动性”由游戏思维拓展而来,互动剧是当下新兴的影视艺术表现形式,交互性与非线性叙事方式是其主要的特点,在操作上具有较强的游戏性,可以让观众进行自主选择,根据选择的差异可以达成不同的结果,因此互动剧更为强调受众观看过程中的“参与感”与“代入感”。与原先的创作底本《明星大侦探》不同,互动剧《明星大侦探之头号嫌疑人》中结合了多视点叙事进行讲述,在调查案件的过程中,进行多次不同视点的切入,在不同主体的讲述过程中,大多数观众与叙述主体的信息量是不对等的,因此观众可以由自己的视点切入,自行寻找事件的线索及推导出原本的真相。互动剧利用不同视角的局限性进行非线性叙事,使得案件更为错综复杂,增强了电视剧本身的趣味性及互动性,极大地拉近与受众间的距离。
四、多视角叙事创作的总结及展望
相较于单一视角,多视角选用了更宽广的维度来呈现世间百态,体现后现代哲学的多元本质观对简单的“二元分立”思维模式进行批判,更能符合当代受众的审美需求。对于影视制作者而言,首先,分叙述主体进行多视角叙事可以间接地引导观众的注意,明确人物视角使得人物叙述功能得以强化。由于电视影像叙事的叙述主体和接受主体的“观看”位置趋同,叙述态度的表现直白,叙述接收者很容易感受到影像呈现的事物本身,但由于无人引导,叙述接收者看出其中的“意义”又稍显困难,而多视角的划分可以为受众指明道路。其次,可以弥补单一视角的局限,深化叙述力度。李显杰认为“多重声”我者叙述由于包孕着“我”者叙述目光的独特、尖锐之神韵,又兼有“他”者叙述方式纵横自如……因而能达到一种主观中显示客观、对立中见出深刻的叙述境界。电视叙事可利用多视角的优势对“浅显”的剧情进行意义的深度挖掘,营造叙事的真实、多义性,由事件的核心横截面进行垂直向度的聚焦,摆脱因果关联的线性叙事,以不确定的叙述指向促使观众的思维向外发散,调动观众参与文本构建的积极性。而站在受众群体的角度观之,多视角叙事扩大受众的“认知聚焦”,满足观众天生的好奇感,在叙事文本中既存在着“功能性”的人物观,可以满足受众了解剧情的需求,又存在着“心理性”的人物观,受众能近距离地感知叙述主体的心理及思想。相比之前受众的“目光视域”大于影像中任何人物,受众与剧中人物明显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而多视角的切换无疑将受众与文本的距离进一步拉近,将受众现阶段的“目光视域”大幅缩小,为叙述接收者的信息接受增大难度,进而增强观看的审美体验感。
虽然目前大多数使用该叙事手法的作品皆获得了市场与受众的认可,但仍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亟须改进。首先,在多视角叙事中如何平衡剧情及人物的关系尤为重要,稍有不慎容易偏向剧情的戏剧性走向而忽略对人物的刻画,进而落入以往电视叙事的窠臼之中,而这一点也在《摩天大楼》中有所体现,该剧通过多个叙述者的主观视角加剧了故事的悬念性,故事的看点很多,几乎在每个叙述者的叙述中都表达出一个社会的热点话题,该剧极力追求的效果也成为其一大短板,用丰富的故事情节将庞杂的主题进行简单化的堆砌,使得人物刻画流于表面,忽略了多视角主观性叙事中表达的初衷。其次,多视角叙事特别讲究叙事的逻辑性,文本的叙事逻辑处理得是否得当,很大程度会影响与受众的情理联系,电视叙事比电影叙事在多视角应用方面要显得更为“亲民”,以集为单位清晰地划分不同主体的视角,排除了混淆人物视角的障碍,清晰系统地辨别出人物的观点,进而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倘若叙事逻辑说服力不够,也会造成叙述主体的“主观视点”与观众的“目光期待视线”无法匹配的现象,因此在剧本创作方面仍需要多下功夫。
多视角叙事具有独特的表达效果,现阶段的电视剧借用多视角叙事的形式结构进行大胆、创新的创作实践,为影视的多元化表达提供了坚定的美学基础,与此同时我们也衷心希望创作者们重视其结构的真正内涵,即多重视角与人文关怀的关联,在创作的过程中能认真地驻足倾听民意民声,进而落实到剧作之中,使电视剧叙事真正地呈现出人格化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