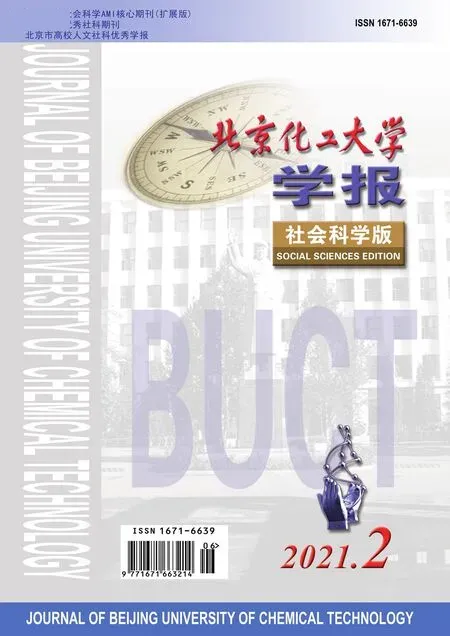上海发起组创建有关的几个问题
黄爱军
(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蚌埠233030)
随着资料的挖掘和研究的深入,对中共早期组织的研究特别是对上海发起组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有些问题学界已基本取得了共识,如发起组成立的时间、最初人数及成员、主要活动内容等,有些问题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如上海发起组发起建党的时间、发起建党人数及成员、发起时的名称、发起组的前期组织等。
一、上海发起组发起建党的时间
对上海发起组创建问题的讨论,学术界围绕发起组成立的时间问题的讨论已比较充分,且形成了5月、6月、8月等几种说法。笔者赞成6月说,因为历史文献明确记载,该组织成立于1920年年中[1]。“年中”虽不是一个十分确切的时间概念,但“年中”所指并不难把握,就是6—7月间,再笼统一些,6月或7月都可被认作是“年中”,但无论如何5月或8月都算不上“年中”,而应属于上半年或下半年。再结合俞秀松的回忆及日记、施存统的回忆及赴日行程,6月说是有道理的。
本文这里所要讨论的不是上海发起组成立的时间,而是上海发起组发起建党的时间,上述5月成立说,是误把发起建党的时间等同于成立的时间。
依据施存统的回忆,上海发起组是经过两次会议,在第二次会议上才宣告成立的[2]。施存统的说法在俞秀松的《自传》中得到了印证[3]。第一次会议没能成立,原因是戴季陶参会时声明不参加共产党,所以大家不欢而散[4]。显然,第一次会议并非是发起会,而是成立会,只是没有成立而已。如果第一次会议即是发起会,既不合情理,亦过于唐突,在这之前应有一个发起酝酿的过程,在大家基本取得共识的情况下,才有第一次成立会议的召开。第一次会议因戴季陶的原因未能开成,这也应是戴季陶退出中共创建活动的标志。资料显示,陈独秀在上海发起建党的时候,戴季陶是重要的发起人之一,早期党史著作及不少当事人的回忆均有这方面的记载。戴季陶还是最早党纲的起草者[5],戴季陶自己亦称参加了上海发起组,并参加了章程的起草[6]。这说明,发起建党的会议是在标志戴季陶退出中共创建活动的第一次会议之前召开的。
这个发起建党的会议是何时召开的?按照董必武的说法,是1920年5月,出席会议的有公认的中共两位最主要的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董必武没有出席这次会议[7]。这次会议的具体情形人们知道的不多,但董必武的说法绝非空穴来风。20世纪30年代的一则史料记载了这次会议的一些情况:维经斯基正式提议组织共产党时,即由陈独秀出面,“找北平李大钊广州谭平山到沪,与戴季陶、沈玄庐密商”[8]。此则资料还记载,在上述会议之前,维经斯基已与陈独秀进行过密商,且进行过多次磋商[9]。
无独有偶,早期党史著作在谈到上海发起组发起建党的时间时,大多指向1920年5月。蔡和森著《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10]、大革命时期社会科学研究会编印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策略(讨论大纲)》[11]、延安时期出版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12]等早期党史著作,均记载党的发起组织时间是1920年5月。1927年施存统在《悲痛中的自白》中,亦将陈独秀等发起组织共产党的时间指向1920年5月[13]。1926年苏联卡拉乔夫著《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述》记载为“1920年初”[14],1936年米夫著《英勇奋斗的十五年》的记载与之相同[15]。
早期党史著作具有的权威性当不容置疑,不仅因为这些著作完成的时间距离中共创建时期较近,还因为这些作者大多是党的早期重要负责人,有的更是直接参与了上海发起组最初发起建党的整个过程,有的则是国际代表或顾问。
另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档案资料记载:“信奉布尔什维主义的上海共产党是公历一九二零年五月,由中国人陈独秀一派创建的。其后就在暗中开展活动,共同为党的发展而努力。”[16]
再者,1920年5月初,赵世炎经上海转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沪期间,陈独秀介绍赵世炎参加了正在发起的党组织[17]。赵世炎乘船离开上海的时间是5月9日[18],这意味着上海发起组发起建党的时间不会迟于1920年5月上旬。1920年11月,北京早期组织成员张申府经上海乘船赴法国,陈独秀嘱其到法国后与赵世炎联系,开展建党工作,并给张写了介绍信[19]。
最后,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大学校[20],这个社会主义团体的人员组成与上海发起组的人员组成基本一致。社会主义大学校成立时的七人,除王仲甫外,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六人[21],均是上海发起组发起建党阶段的成员。从时间节点和人员组成来分析,社会主义大学校的成立显然与发起组的建党活动有密切联系,这个社会主义团体的成立既可视为发起组建党活动的成果,亦可视为发起组发起建党的重要标志。
综上,我们大体上可以对上海发起组从发起建党到成立的过程作如下描述:1920年4月间,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在北京作短暂停留后南下上海,很快与陈独秀取得联系,经过几次磋商,决定由陈独秀出面发起建党。这个发起会大体在1920年5月举行,以此次发起会议为标志,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建党工作全面展开。稍后或几乎同时,社会主义大学校成立,并委托戴季陶起草党纲,为发起组的正式成立作准备。不久后经由两次组党会议,于1920年6月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告了上海发起组的成立。
二、上海发起组最初的名称
1920年6月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现在人们将其称之为发起组,即负有发起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职能。这个发起组在发起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要完成两个层次的工作,第一个层次是在上海发起创建共产党早期组织,第二个层次是指导各地创建共产党早期组织。也就是说,1920年5月发起建党之始,也就是它亮相中国历史舞台之时,实际上即宣告了上海发起组的存在。这时发起组尚无具体名称,但它的存在却是真实的。正如1928年8月发布的《沈定一(沈玄庐——引者注)先生被难衷启》中所说:“由陈独秀邀集先生和李汉俊等,发起一个名称未定的社会主义的团体,这就是后来中国共产党结党的雏形。”[22]
没有具体名称,这种现象在各地早期组织亦不少见。长沙、济南两地早期组织因缺少文献资料,当事人留下的回忆资料亦少见,不仅无从考证其具体名称,就是其是否存在也成了一些人的疑问,甚至当事人的易礼容都认为其不存在[23]。旅日、旅法小组均没有具体名称。巴黎小组负责人张申府回忆,该小组成立时“没有正式名称。成立后报告了陈独秀”[24]。广州的早期组织留下了《广州共产党的报告》这份珍贵文献,但该文献并未提及组织的名称,是否就叫“广州共产党”,无从考证。作为当事人的陈公博,在1924年完成其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其中不仅通篇找不到广州早期组织的名称,甚至连该组织的踪迹也找不到,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青年团等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共产党起源的“团体”、“共产主义本源的团体”[25]。北京早期组织建立之初,也没有具体名称,张国焘、张申府二人回忆与李大钊发起创建北京早期组织时,均没有提到组织名称[26],后来在正式宣布该小组成立的会议上,也没有使用具体名称,张国焘在回忆录中使用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的名称[27]。按照张国焘的说法,该小组到1920年11月底才正式被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28]。1929年张国焘撰写的《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中,称北京早期组织“叫北京共产党”[29],但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使用的是“党部”这样的名称[30]。作为北京早期组织成员的罗章龙、刘仁静、朱务善等人,有的说“没有名义”[31],有的说“没有什么名称”[32],还有的说“北京还没有共产党的正式组织”[33]。历史文献《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使用了“共产主义组织”这一笼统的叫法。
之所以出现没有具体名称的现象,如上文已指出,这是由定名的严肃性、审慎性决定的,这说明中共发起建党的时候,就是一个十分慎重且严肃认真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组织起来的,党一开始发起成立的时候,就具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这也是最初曾参与发起建党的某些人后来很快退出的最直接原因①张东荪退出的理由是:“他原以为这个组织是学术研究性质,现在说这就是共产党,那他不能参加,因为他是研究系,他还不打算脱离研究系。”参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196.戴季陶退出的理由是:“怕违背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孙中山在世一日,他不能加入别党”。参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196.一大回忆录[C].北京:知识出版社,1980:66.包惠僧回忆:“戴季陶最初还表示同意,到了起草党纲完毕时,内中有一条:‘共产党员不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戴季陶就借口说他不能同孙先生和国民党断绝关系,声明退出这一运动。”参见:一大回忆录[C].北京:知识出版社,1980:25.北京、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退出组织,是因为他们反对党的纪律和职务分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参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共产主义小组[G].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217,679.。上海发起组成立后,肩负着在各地乃至海外发起创建共产党的任务,“组织系统和工作程序都是由上海党部拟订分到各地区的”[34]。由于中共创建工作千头万绪,陈独秀本人对党的名称一时也不能决定,并写信向北京的李大钊、张申府征询意见[35],从而也就不能给各地的建党活动“定名”给予指导,各地的建党活动又岂能超出上海发起组的指导范畴,自行其事地来一个自我“定名”?
由于没有具体名称,又由于党处于秘密状态,且党的许多活动都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开展[36],以至于若干年后,有的当事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就是上海发起组,“内部叫共产党”[37]。有的当事人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小组(共产党小组或共产主义小组都是一样的,是内部的名称)[38]。陈公博在回忆录中实际上是将青年团当作党的早期组织来加以描述:“中国各地重要都市的青年团依次秘密成立,遂有民十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沪的召集。”[39]
三、上海发起组发起建党人数及成员考
上海发起组发起建党的人数,早期党史著作有六人说、七人说、八人说,其中多持七人说,如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卡拉乔夫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述》、社会科学研究会编印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策略》、米夫的《英勇奋斗的十五年》等,六人说和八人说分别见于李立三的《党史报告》和延安时期出版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笔者认为,七人说比较可信。
上述六部早期党史著作中有四部列出了发起人的具体姓名,这些人总计11人,包括陈独秀、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施存统、陈望道、俞秀松、一个女人、沈仲九、杨明斋、李达等。这11人中基本可以确定是发起人的,有陈独秀、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施存统等5人。可列出如下理由:第一,四部早期党史著作均有陈独秀、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的名字,其中有三部有施存统的名字。第二,萧楚女在1925年所写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提到了发起人陈独秀、戴季陶、沈玄庐3人[40];施存统1927年所写的《悲痛中的自白》一文中写道,陈独秀与戴季陶等人发起组织共产党时,“我便在内”[41];1928年8月发布的《沈定一先生被难衷启》中,提到发起人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3人[42]。第三,1920年5月社会主义大学校成立时的7人中,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4人的名字。社会主义大学校与党的早期组织在人员结构上虽有差异,但基本上一致②社会主义大学校成立时的7人中有6人是人们熟悉的发起组早期成员,后来成员发展到60人。参见:中共建党前后革命活动留日档案选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235.亦与党的早期组织的成员人数近似。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29-30.,亦可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
第六位发起应该人是俞秀松。主要理由是:第一,早期党史著作有两部提到俞秀松的名字。第二,俞秀松与施存统是同学,二人离开浙江第一师范后一起赴北京,并参加了李大钊等发起组织的北京工读互助团,后又一起赴上海并加入了星期评论社,而陈独秀发起建党的主要对象,就是星期评论社的成员,俞秀松与施存统一起参加发起建党是顺理成章的。第三,俞秀松与施存统二人有关参与发起创建共产党的回忆,内容基本一致,二者之间可互相印证,亦说明二人参加建党活动的轨迹基本相同。第四,俞秀松在苏联填写的履历表中说自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和其他同志一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43]。俞秀松这里填写的“创始人之一”可能就是指最初七个发起人之一。在其它材料中称自己是“上海党的创建人之一”,“1920年与其他同志一起创建了上海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44],这显然是指上海发起组。第五,社会主义大学校成立时的7人中有俞秀松的名字。
其余五人作为第七位发起人的可能性均不大。第一位李达,具体分析如下:第一,早期党史著作只有《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提到李达的名字,称李达是发起人显然受该著作影响。第二,社会主义大学校成立时的7人中没有李达的名字。第三,上海发起组成立时的5人中没有李达的名字。第四,施存统回忆中说,他没有和李达一起讨论发起共产党[45]。第五,陈公培回忆中说,李达当时还在日本[46],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李达于当年8月中下旬才从日本返回上海。
第二位陈望道,虽有两部早期党史著作提到,但仍不足作为发起人的证据。主要理由有:第一,社会主义大学校成立时的7人中没有陈望道的名字。第二,上海发起组成立时的5人中没有陈望道的名字。第三,陈望道回忆自己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就是党。第四,施存统回忆中说,他没有和陈望道一起讨论发起创建共产党[47]。第五,陈公培回忆中说,陈望道当时在杭州[48],有两件事一定程度上可以佐证陈公培的说法。第一件是至今还在分水塘乡村间传颂的当年陈望道因专心于翻译《共产党宣言》蘸墨汁吃粽子的小故事[49],一般情况下吃粽子应在端午节期间,而1920年端午节是公历6月20日;第二件是据俞秀松日记所记,1920年6月27日晚间,陈望道让俞秀松第二天“送他所译的《共产党宣言》到独秀家去”[50]。这则日记透露了与陈望道行踪有关的两点信息,如果陈望道译好《共产党宣言》后抵达上海的时间是5月间或更早,何以要等到6月底才将译稿送交陈独秀?如果陈望道参与了陈独秀发起的建党活动,二人之间应已建立起良好的互助关系,且又住得很近,何以不直接将译稿交给陈独秀?由此笔者认为,陈望道5月或更早抵达上海的可能性很小,陈望道与陈独秀之间的联系并不热络,尚未形成“熟人”关系。
第三位沈仲九,只有一部早期党史著作提及,且既不是社会主义大学校和上海发起组成立时的成员,又不是上海早期组织的成员。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之所以把沈仲九列为发起人之一,按照蔡和森自己的说法,是因为党开始形成时,找不到足够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把沈仲九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拉进来了[51]。如果沈仲九果真是无政府主义者[52],那他就不可能参加党的早期组织,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组织起来的,上海发起组创建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北京、广州两地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的现象。沈仲九不是上海发起组成员的事实,足以说明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他不可能成为党的发起人。当然,蔡和森把沈仲九列为党的发起人之一,也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在施存统、陈公培二人的回忆中,均认为沈仲九参加了发起成立共产党的第一次会议[53],或许他还参加了此前陈独秀发起的系列座谈会。因为陈独秀发起建党联络的主要对象,就是星期评论社社员,沈仲九作为该社社员,且与沈玄庐、李汉俊、俞秀松关系密切[54],参与系列座谈会是很正常的。但参与系列座谈会与参与发起组党、参加党的早期组织,又是不同的两回事,因为星期评论社的十多名社员,后来只有一小部分参与了发起组党并参加了党的早期组织[55]。
第四位“一个女人”,早期党史著作有两部提到此女人,施存统、陈公培的回忆录中亦提及此女人,同样不知其姓名[56]。有学者认为,这个女人是杨之华回忆录中提到的星期评论社社员丁宝林,亦即俞秀松日记中提到的崇侠[57]。这一观点尚无法证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李立三《党史报告》中所提到的“一个女人”,正是俞秀松日记中提到的崇侠。《党史报告》中说,这个女的“后来因恋爱问题消极做尼姑去了”[58],俞秀松日记则记载了崇侠与沈玄庐的恋情及出家为尼之事[59]。这个女人的情况与沈仲九十分类似,即参加了陈独秀发起的系列座谈会,但并非是发起人之一。
第五位杨明斋,只有一部早期党史著作提及,既不是社会主义大学校与上海发起组成立时的成员,也没有参加发起成立共产党的两次会议[60]。不少当事人的回忆资料显示,在陈独秀发起组党的系列座谈活动中,一般均有维经斯基的身影,作为维经斯基翻译的杨明斋也应相随参加了系列座谈会,但恰恰是发起成立共产党的两次会议,均没有二位的身影。资料显示,维经斯基到上海后,除了与陈独秀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接触、磋商、座谈外,还广泛接触了其它各色社会团体负责人,这应是二人缺席两次会议的主要原因。既然杨明斋需要陪维经斯基忙于别的事务,自然不适宜作为发起人。
还有一位与中共早期创建活动有关的人物,此人为张东荪,虽然早期党史著作不曾提到,但当事人的回忆一般均有所提及。综合当事人的回忆材料,张东荪可能参加了最初的几次座谈会[61],但等到准备发起建党的时候,他退出了,所以不是第七位发起人[62]。张东荪后来亦明确说自己“始终是一个‘非党派者’”[63]。
这第七位发起者究竟是谁呢?笔者认为陈公培的可能性最大。虽然早期党史著作未提及,但陈公培是社会主义大学校和发起组成立时的成员,先后参加了发起成立共产党的两次会议。陈公培参加建党活动的情况与俞秀松、施存统相似:先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后抵上海参加建党活动,最后赴法国勤工俭学。
四、上海发起组的组织源头
一般观点认为,上海发起组是在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①参见:周子信.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小组”[J].党史资料丛刊编辑部.党史资料丛刊:第2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陈绍康.上海共产主义小组[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8:10.马连儒.风云际会:中国共产党创始录[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29.何虎生.建党伟业[M].北京: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7:192.,亦是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发起组的前期组织或源头组织。此说之所以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在前,发起组成立于后。但通过上文的考辨可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的时候,发起组在客观上已经存在。既然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是发起组的前期组织或源头组织,那么,上海发起组是否有源头组织,也就是有没有前期组织基础或条件?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这个源头组织,最重要的就是新青年社和星期评论社。
新青年社是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形成的同人群体,该社经历了安徽同人群体、北京同人群体、上海同人群体三个阶段,随着同人群体结构及办刊宗旨的变化,社团亦经历了从民主主义、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相混合、再到社会主义团体的演变,这种演变与社团发起人、负责人陈独秀的思想演变密切相关。1920年2月,陈独秀经天津转赴上海,同时将《新青年》带到上海出版发行,并且很快组成了以陈独秀、陈望道、李达、李汉俊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上海同人群体。星期评论社是以《星期评论》杂志为中心形成的同人群体,该社集结了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沈仲九、刘大白、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邵力子、杨之华、丁宝林等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或倾向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
上海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之地、诞生之地,除了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拥有几十万产业工人队伍、是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重镇这些基本原因外,更重要、更直接的原因则是,以新青年社和星期评论社为主体,集聚了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使上海成为继北京之后共产主义者的又一个大本营。维经斯基来华后把工作中心从北京转移到上海,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共产党的诞生必须具备阶级基础(工人运动的发展)、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干部条件(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其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既是党诞生的思想条件,又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产生的必备条件,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又是党诞生的最直接的干部和组织条件。五四运动对中共诞生具有重要作用和影响,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直接催生了五四社团的勃兴,创办报刊、组建社团成为五四运动后知识界活动的主要形式。正因为社团及社团刊物的大量涌现,才使新文化运动真正发展成为一场空前广泛的文化运动,才使马克思主义在较短的时间内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在此过程中,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亦迅速成长起来。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的,李大钊、杨匏安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积极提倡和宣传,其作用和贡献彪炳史册自不必多言,但如果仅仅是少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单枪匹马地提倡和宣传,绝难在短短的时间内即创建中国共产党,必须要有一种组织的力量,才能产生群体效应,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实效,这个组织力量,正是五四进步社团。
五四进步社团在中共创建进程中曾发挥过“联共小组”的作用,是孕育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摇篮[64]。早期党史著作在谈及党的诞生时总是与五四进步社团联系起来,称五四进步社团是“共产主义本源的团体”[65],是“共产党的细胞”[66]。其中与党的创建有密切关系者包括湖南的新民学会、武汉的共存社、天津的觉悟社、南昌的改造社、济南的励新学会等,而影响最大且与上海发起组的建党活动直接相关者,当数新青年社和星期评论社。
纵观上海发起组创建的整个过程不难发现,从最初的座谈酝酿,到发起建党,再到正式成立,参加的人员及人数虽有所变化波动,但有一点却始终没变,就是参加的人基本是来自新青年社或星期评论社的社员,如发起时的7人和正式成立时的5人无一例外。正是集聚在新青年社的先进分子,同时联络星期评论社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共同发起创建了党的上海发起组。
新青年社和星期评论社作为上海发起组的前期组织或源头组织,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实际,是当之无愧的,也是撰写中国共产党创建史时所不应忽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