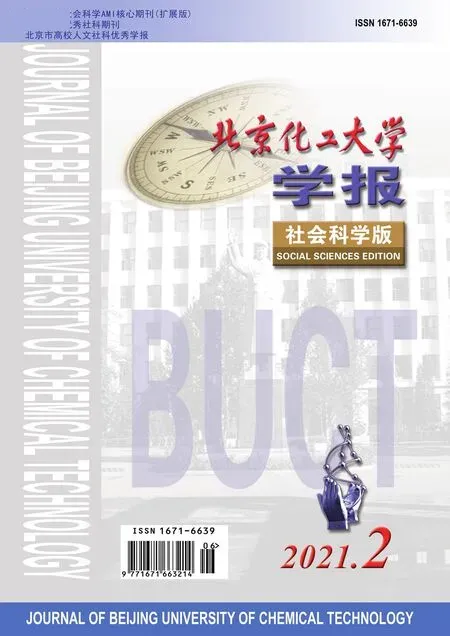论“通知—删除”规则的性质
——以平台自治为视角
林威
(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84)
一、前言——平台自治的需求与困境
《电子商务法》沿袭了《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明确了电商平台的知识产权侵权处理机制——“通知—删除”规则,这一规则又被《民法典》所吸纳。参照相关学者的总结,可以将“通知—删除”规则概括为“通知—删除—反通知—‘静默期’—恢复”的机制[1]。相关学者精辟地指出这一机制过于机械、缺乏弹性[2]。诚然,从法律条文来看,电商平台是一个机械的“接收—删除”、“转送通知”的角色,并无自主判断的空间[3]。
在电子商务兴起的背景下,这一机制开始被用于商业竞争之中。为了获取竞争利益,不乏利用“通知—删除”规则进行恶意投诉的现象①以“阿里巴巴集团知识产权保护平台”为例,该平台不但已经自发形成了一套“通知—审查—删除”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投诉处理机制,而且还制定了详细的平台管理办法。。据相关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31日,各类恶意投诉占淘宝平台知识产权投诉总量的近24%②参见:《2018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年度报告》。。此时,如果机械地执行这一机制,直接下架平台内经营者的产品,极易产生不必要的损失。特别是《电子商务法》设置的反通知之后的“静默期”长达15天,按照《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这一期间还要延长至20个工作日。这便意味着,在机械地执行这一规则的情况下,即便被投诉人“申诉成功”,其产品或者服务在长时间内仍然无法经营。显而易见,这一机制极易成为恶意投诉人的重大筹码和破坏正当竞争的工具。
在实践中,电商平台处于各种矛盾冲突的最前沿,其最了解各种矛盾冲突的形成原因和具体内容,同时也是网络争议解决方案的最初设计者和执行者[4]。在处理知识产权侵权问题时,我国的电商平台往往在积极审查的基础上,再采取相应之措施[5]。一些电商平台甚至利用其掌握的数据,建立“恶意黑名单”,不予受理恶意投诉人的后续投诉。在实际的平台治理中,这些电商平台根本不是机械的“接收—删除”者,其积极地发挥着自主判断的功能。不容否认,电商平台在知识产权侵权处理中主动地进行审查和判断、积极地行使代码空间自治权,对于实现平台空间的良性治理无疑至关重要,目前的实际效果亦比较明显。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在于,这种自主判断功能的发挥和法律规定的“通知—删除”规则在形式上产生了直接冲突。
二、问题的根源
这一问题的解决难以绕过“通知—删除”规则的性质之争议。长期以来,对“通知—删除”规则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解读:免责条款理论、归责条款理论。免责条款理论将“通知—删除”规则视为责任排除规则,即电商平台在接到通知之后,按照这一规则进行处理仅仅是责任排除的要件,未按这一规则处理仅导致不能享受这种责任排除的“优惠”,并不意味着构成侵权。免责条款理论将“通知—删除”规则的违反和侵权行为之构成区别对待,对于“平台自治”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在这种理论之下,电商平台对于“被控”侵权行为的处理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不过,免责条款理论在我国并不占主流,国内的学者普遍倾向于归责条款理论。归责条款理论将“通知—删除”规则视为侵权行为的认定规则,认为“通知—删除”规则的违反是构成侵权的充分条件。在这种理论之下,电商平台完全是“自助售货机”的角色,仅仅能机械地依照这一规则处理涉嫌侵权问题。这种理论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但是不合理地将国家的治理成本、网络用户的侵权责任转嫁到电商平台之上。
在恶意投诉现象进入公众视野、平台自治的需求开始凸显之后,关于我国“通知—删除”规则的性质之争又被重新推向台前,目前关于“通知—删除”规则的性质问题已不容回避。基于此,本文选择以“平台自治”为视角对这两种理论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试图重新对“通知—删除”规则的性质进行阐释,进而明确“通知—删除”规则的违反与侵权构成之关系。
三、免责条款理论——“看起来很美”
(一)免责条款理论的渊源
部分学者坚称“通知—删除”规则是一项免责条款,主要原因在于这一规则原型是美国版权法中的“避风港”规则。在美国版权法中,是否采取必要措施仅仅属于责任排除要件的范畴[6]。故,在美国的版权案件中,电商平台等网络服务商如果提出了“避风港”规则抗辩,法院首先需要判断网络服务商是否满足责任排除的条件,若满足则不必讨论侵权构成的问题,若不满足并非直接认定侵权,还需要进一步判断是否满足间接侵权的构成要件[7]。比如在BMG RightsManagement(US)LLC v.Cox Communications案①参见:BMG Rights Management(US)LLC v.Cox Communications,Fourth Circuit.February 1,2018881 F.3d 293.中,地区法院认定被告不满足“通知—删除”规则的条件并且构成间接侵权。而在二审中,美国联邦第四巡回法院维持了关于“通知—删除”规则的认定,但是将间接侵权的认定撤销,并发回地区法院重审。在商标和专利案件中,法院直接按照是否构成侵权的思路进行讨论②商标案件参见:Tiffany(NJ)Inc.v.eBay,Inc.576 F.Sup.2d 463(S.D.N.Y.2008);专利案件可参见:BRIAN ROBERT BLAZER v.eBay,MEMORANDUM OPINION,Case No.1:15-CV-01059-KOB.。这些案件的共同特点是在间接侵权的认定中,对于违反“避风港”规则的情况,法院并不是直接认定侵权,而是将其作为判断主观要件的事实[8]。
这种免责条款理论将“通知—删除”规则的违反与侵权认定区别对待,是否构成侵权仍然应当回到侵权法的框架进行讨论。这一理论对于“平台自治”的需求颇有迎合力,电商平台仅仅需要尽到合理的自由裁量,便不会触发侵权法上的过错之要件。在“平台自治”的需求兴起之后,一批学者又重新强调“通知—删除”规则的免责性质③参见:周学峰.“通知—移除”规则的应然定位与相关制度构造[J].比较法研究,2019(6):26.刘文杰.《电子商务法》“通知—删除”规则之检讨[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13-20.。
(二)免责条款理论的问题
诚然,我国曾仿效美国法以免责规则的形式移植了“通知—删除”规则。国务院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2006)》中采用了免责条款的形式,未予规定违反删除义务的法律后果,明确“履行删除义务”将不承担赔偿责任。不过,我国在立法中却早已偏离免责规定的形式,以2009年《侵权责任法》的出台为标志,该法第三十六条在形式上将“通知—移除”规则塑造成为了一项归责条款(具体原因请见第四章)[9]。当然,有学者主张《侵权责任法》虽然没有采用免责条款的逻辑表述,但并不妨碍其是免责条款这一事实,完全可以将其看作是免责条款“反面表述”[10]。这种观点曾被最高审判机关采纳。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凡网络服务提供行为符合法定免责条件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不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虽然不完全符合法定的免责条件,但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具有过错的,也不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不过,这种观点的缺陷也较为明显。原因在于,学界对于电商平台的过错责任原则基本呈一致的意见[11],那么,按照过错责任原则,电商平台在接到“侵权投诉”之前,若对侵权的情况并不知悉,其提供平台服务的行为并不存在过错,因而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免责规则的前提是存在侵权责任,既然电商平台并不存在侵权责任,又何以被“免责”呢?事实上,“避风港”规则在美国作为免责规则有其历史上的原因。在互联网发展早期,由于人们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地位、作用及监控能力的认识不足,因而出现适用严格责任原则之主张[12]。王迁老师指出“避风港”规则的目的仅仅是避免网络服务提供者无条件地承担严格责任[13]。而我国司法实践历来按照民法中的共同侵权规则处理相应问题,并不存在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追究严格责任的历史[14],我们并不需要采纳“免责条款”理论来对其进行“免责”。
更为致命但又被频繁忽视的一点在于《侵权责任法》的“通知—删除”规则独具特色,导致其并不一定能实现免责效果。仔细研读便可发现,美国的避风港规则不仅仅以“接到通知立即删除”为条件,“不存在明显知情的情形”亦为条件之一。相较之,我国的“通知—删除”规则并非“精细入微”,规则本身并未包含一些细化的条件。故而,即便符合我国的“通知—删除”规则,电商平台仍存在承担连带责任之可能性。这一点在司法实践中已成共识。反之,若强行按照免责条款理论理解我国的“通知—删除”规则,反而会加重电商平台的举证责任,比如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试行)(2011)》规定:“网络服务商主张免除责任,不仅要证明其按照权利人的通知进行了处理,还要证明其主观上不存在过错。”①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试行)(2011)》“41.网络服务提供者主张其符合《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规定的免除赔偿责任条件的,应对其所依据的相关事实负举证责任。42.信息存储空间服务提供者免除赔偿责任,应同时具备以下五项条件:(1)信息存储空间提供者明示为服务对象提供,并公开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名称、联系人、网络地址;(2)未从服务对象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3)信息存储空间提供者不知道或不应知用户上传内容构成侵权;(4)未改变服务对象所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5)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后,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规定删除权利人认为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49.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免除提供搜索、链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损害赔偿责任的,应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1)提供搜索、链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对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是否侵权不明知并且不应知;(2)提供搜索、链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规定断开与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
此外,《侵权责任法》、《电子商务法》以及《民法典》对于该规则的表述已经非常明确,这一免责条款理论也无法和立法的表述相协调。司法实践界的相关报告也明确否定了“免责条款理论”②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课题组.关于电商领域知识产权法律责任的调研报告[EB/OL].[2020-03-27].https://www.chinacourt.org/index.php/article/detail/2020/03/id/4871104.shtml.。因此,将“通知—删除”规则解释为免责规则既不符合相应的历史背景,也无法实现所谓的“免责”效果,更无法和立法的明确规定相协调。综上,这一免责条款理论尽管“看起来很美”,但难以为实践中“平台自治”的路径提供理论支撑。
四、归责条款理论——“另一个极端”
(一)归责条款理论分析
大部分学者则滑向另一个极端,主张我国的“通知—删除”规则是归责规则。比如吴汉东老师认为:“‘通知与删除’规则是指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侵权通知后,应按照通知进行处理,否则对损害的扩大部分承担责任,这是一种‘明知’或‘实际知道’的状态。”[15]其他的学者均持类似之观点①王迁老师也认为“通知—删除”规则在我国无法成为免责规则,不符合“通知—删除”规则的条件必然构成帮助侵权。参见:王迁.《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避风港”规则的效力[J].法学,2010(6):132.还有相关学者认为《侵权责任法》是将免责条件从正面规定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因符合这些要件而侵权的,必然也就不符合《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规定的免责条件。参见:陈锦川.关于网络服务中“避风港”性质的探讨[J].法律适用,2012(9):25-31.。在这种学说占据主流地位之后,相关学者经过对比总结,认为我国在移植美国模式过程中出现了变异,将责任排除规则转换为责任构成要件[16]。这些学者共同观点是认为不符合“通知—删除”规则必然承担侵权责任,而电商平台接到通知之后不进行处理的行为被视为其主观过错。这种观点亦大量反应在司法文件中②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3)》第八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确定其是否承担教唆、帮助侵权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包括对于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明知或者应知。”第十三条中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权利人以书信、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交的通知,未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明知相关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试行)(2011)》中也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共同侵权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是过错原则,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观过错认定可分为“明知”与“应知”两种情况。在下列情况下,可以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被诉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1)权利人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交了书面通知后,网络服务提供者仍然对侵权内容提供服务的。。按照归责条款理论的逻辑,“通知—删除”规则成为一个侵权认定的“公式”,在这个“公式”中,“权利人的通知”等于“电商平台对侵权行为的知悉”,进而“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之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等于“主观上存在过错”。
上述6个省能成为卡车司机的输出大省,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人口众多。2017年最新统计结果显示,6省人口数量均位列全国前10。二是经济相对发达。2017年江苏和山东的经济总量位居第二位和第三位,头名是广东。三是货源丰富和公路路网发达。以排名前两位的江苏和山东为例,江苏的公路密度达到了154公里/百平方公里,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山东的卡车司机主要来自物流之都——临沂。临沂是我国北方最大的商品集散中心。
(二)归责条款理论的问题
归责条款理论下的“公式”过于理想化,导致这一理论难以逻辑自洽。事实上,权利人的侵权通知或者投诉往往并不能当然地证实侵权行为的成立,基于权利人的侵权通知或者投诉直接认定电商平台对侵权行为的知悉并无合理性[17]。从侵权法的视角来看,对作为第三方的电商平台进行追责是以过错——知悉或者应当知悉用户实施侵权行为为主观要件的[18]。在归责条款理论下,这种拟制的过错导致违反“通知—删除”规则情形下的“无过错”责任。按照归责条款理论对电商平台进行机械追责的结果便是帮助侵权的认定不再符合原有的侵权构成理论。
这种机械归责也未考虑专利侵权构成的特殊性。在美国法上,由于历史上借用民法上的共同侵权理论,追究了提供通用品的第三方的侵权责任,导致了专利滥用的情况。在对专利滥用进行反思后,美国立法确定的间接侵权规则排除了提供通用品的第三方因一般过错而承担责任的可能性,将通用品情形的侵权责任限于积极引诱的情况[19]。我国司法实践在一些专利侵权案例中也有明显的限缩侵权责任的倾向。比如在SMC株式会社、乐清市中气气动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专利法意义上的帮助侵权行为并非泛指任何形式的帮助行为,而是特指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为生产经营目的将侵权专用品提供给他人以实施侵犯专利权的行为。本案中,倪天才提供个人银行账户用以收取公司货款,该行为并非提供侵权专用品,不能构成专利法意义上的帮助侵权行为。”③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199-201号民事判决书。同时,专利侵权判断兼具法律问题和技术问题,相对比较复杂,“权利人的通知”和“电商网络平台对侵权行为的知悉”难以直接划等号,比较法上亦没有对提供通用服务的平台追究连带责任的先例。因此,当前对于专利侵权适用“通知—删除”规则进行机械归责在理论上争议最多。概言之,这一归责条款理论的困境在于“通知—删除”规则无法必然转化为侵权行为的要件。
部分持归责条款理论的学者也对此进行了反思,但是反思的结果仅仅是要求对这一规则的适用进行限制。比如吴汉东老师指出:“诸如专利侵权,其专业判断难度很大;至于商业秘密侵权,其隐蔽性难以识别;而名誉侵权,则不易对事实真假作出认定。在这种情况下,被动通知的处理或主动审核的要求,对网络服务提供者都不合适宜。”[20]实际上,对于一般的人格权或者较为简单的著作权案件,其在侵权的构成要件上并不像专利案件那样具有特殊的要求,并且侵权的判断较为简单,将不遵循“通知—删除”规则进行处理的情况视为过错和平台的实际主观状态基本能够吻合。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将“通知—删除”规则作为归责规则通常不会破坏原有的侵权认定规则。不过,这一“等式”在侵权的判断较为复杂的部分——知识产权领域必然失灵,将不遵循“通知—删除”规则进行处理的情况视为过失和平台的实际主观状态难以等同,由此便可能出现侵权的认定突破了原有侵权要件之要求的情况。
(三)司法实践的调和与失能
司法实践亦多践行归责条款理论,但法院也意识到了这一理论造成的利益失衡问题,并积极地进行调和。加之法条对“通知—删除”规则中的一些“词语”未做定义,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的解释空间。因此很多法院对法条中的一些“词语”进行扩张解释,以软化法律条文的刚性。
最为常见的扩张解释便是我国法院对“必要措施”的解读,其普遍认为电商平台接到权利人的通知后所应采取的“必要措施”并不限于删除、屏蔽、断开链接[21]。在《电子商务法》生效之前,我国法院在一些案例中指出“转通知”亦是一种“必要措施”[22]。这一观点不久便被最高人民法院以指导性案例的方式背书①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第83号指导案例。。然而,《电子商务法》将“转通知”规定为一项独立的义务,随着该法的生效,这一解释方法也随之终止。司法实践界的观点也指出:必要措施和转通知被作为两个独立的动作进行规定,这就使得法院丧失了解释的空间,电子商务法中的转通知不能再被理解必要措施,否则就会架空法律的流程规定,不符合法律解释的基本原则②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课题组.关于电商领域知识产权法律责任的调研报告[EB/OL].[2020-03-27].https://www.chinacourt.org/index.php/article/detail/2020/03/id/4871104.shtml.。在《电子商务法》生效后,一些法院为了维护平台自治,充分发挥自由裁量的空间,又将“冻结保证金和店铺账户”视为必要措施③参见: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2知民初367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调研报告中也采纳了这种观点④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课题组.关于电商领域知识产权法律责任的调研报告[EB/OL].[2020-03-27].https://www.chinacourt.org/index.php/article/detail/2020/03/id/4871104.shtml.。最高人民法院亦间接地认可了这种扩张的解释,其在《关于审理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第三条中整体规定“采取的必要措施应当遵循合理审慎的原则”,第十条中直接规定“必要措施”的认定需要综合各种因素考量。
同时,法院也在“合格通知”、“及时”等词语上探索解释空间。比如2020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出:“法院在遵循法律解释基本原则,不违背立法本意的前提下,在对‘合格通知’、‘及时’等模糊的法律用语进行解释时,应当为平台自治留出空间,引导平台采取既符合自身商业逻辑、又有利于实现各方利益平衡的措施进行治理。”⑤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课题组.关于电商领域知识产权法律责任的调研报告[EB/OL].[2020-03-27].https://www.chinacourt.org/index.php/article/detail/2020/03/id/4871104.shtml.
然而,问题恰恰在于,法院在进行解释时无法保证其体现了“立法本意”,容易造成各地法院对同一词语的解释不统一。比如在电商平台对专利侵权投诉的处理中,不同地区法院曾对于“侵权对比材料”是否是“合格通知”的必要条件持相反的态度。甚至在涉案专利、案情均相同的情况下出现过不同地区的高级法院的判决截然相反的情况。比如在肇庆市衡艺实业有限公司诉深圳摩炫科技有限公司、淘宝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淘宝公司在接到衡艺公司律师函及一审诉讼材料后……仍以涉案专利技术特征比对涉及内部结构、而律师函缺少本案专利技术与被投诉商品的侵权对比信息为由,未履行诸如删除、屏蔽、断开链接以及将衡艺公司律师函转送摩炫公司等义务,客观上为本案侵权行为提供了帮助,致使损失进一步扩大。”⑥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民终1038号民事判决书。然而,在肇庆市衡艺实业有限公司诉建阳顺意贸易有限公司、阿里巴巴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中,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则认为“侵权对比材料”属于“合格的通知”的必要条件,缺乏“侵权对比材料”不是有效的投诉,阿里巴巴未进行处理不存在过错⑦参见: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闽民终1345号民事判决书。。这两个案例专利相同、案情也基本一致、裁判时间也接近,结论却完全相反。对此,最高法院虽然在《关于审理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中针对这一问题予以了明确,但是并未针对其他词语予以解释,特别是在近期刻意放大“必要措施”的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下。
另外,条文解释存在天生的局限性,无法逾越“静默期”的限制。在法律明文规定为15天的情况下,法院无法通过解释论将这一期限缩短。而电子商务具有极强的商业竞争色彩,“通知—删除”规则极易被当作恶性竞争的工具——通过失效、虚假、抢注或者未经过实质审查的知识产权证明打击对手[23]。在被投诉人申诉成功的情况下,如果电商平台不及时恢复链接,将导致被恶意投诉的经营者的巨大损失。特别是在“双十一”或“618”等大促销活动时,这一“静默期”的规定无疑是恶意投诉人勒索的重大筹码。尽管最终出台的《民法典》和最高法院《关于涉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几个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又重新启用“合理期限”的用语,但是在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侵权问题的法律适用上仍然不能忽视《电子商务法》的影响。
总之,这种解释论的路径虽在司法实践中多有运用,但其终究建立在“归责条款理论”的预设之上,缺陷较为明显,无法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失能情况。
五、我国“通知—删除”规则的性质辨析
从上述分析可见,我们既不能照搬比较法,也不能依照“通说”,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一规则的性质。我国特定的现象必然与特定的历史背景有关,因此,问题的解决无法回避历史原因。
(一)“通知—删除”规则的历史背景
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在我国兴起。伴随互联网而来的是一套开放、自由、共享的“互联网价值观”[24],一些人甚至鼓吹“网络乌托邦主义”,主张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各自独立,现实世界的法律无法渗透到网络环境[25]。因而,个人用户、互联网公司纷纷践行“拿来主义”,在互联网上免费获取和分享网络资源。在较长时间内网络侵权现象和这一套“互联网价值观”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此时的互联网公司处于起步阶段,并无足够的资源自行采访报道重大事件或者制作原创的网络文娱产品。为了获取充分的信息,以吸引流量,互联网公司有意放任用户的“拿来主义”,甚至积极参与、鼓励用户上传和分享网络资源,侵权一度成为普遍的现象,互联网成为可以免费使用一切资源的天堂[26]。在这种恶性竞争的环境下,真正从事原创或者积极购买版权的公司却难以立足,整个互联网产业落入“盗版黑洞”。当然,一些权利人也针对这些网络公司发起了维权行动,但这仅是个别现象。绝大部分权利人只能“被迫”默许:“有的作者被蒙在鼓里,作品被侵权还不知道;有的只是和网站进行了交涉和协调,并没有告上法庭;而有的则是无可奈何,没有太多的精力和资源去应付这么多的侵权事件。”[27]更为甚者,这些互联网公司也在积极鼓吹“互联网价值观”,打着“代表公众利益”的幌子,尽力渲染作者与公众之间的所谓“利益冲突”,以便从中渔利[28]。
当然,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对此均作出了回应。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对于网络平台的侵权责任按照民法的共同侵权规定进行处理。不过,这一规则的落地实施有赖于权利人发起侵权诉讼,对普遍的网络侵权现象难以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对此,行政机关也试图通过行政权力解决这一问题。2005年,国家版权局、信息产业部出台了《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其第5条也规定:“著作权人发现互联网传播的内容侵犯其著作权,向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或者其委托的其他机构发出通知后,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立即采取措施移除相关内容。”这一规定将“删除”定性为法定之义务,我国“通知—删除”规则以此为原始雏形。不过,著作权具有私权之性质,行政权力的干预建立在侵权行为损害公共利益的基础之上,故《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将违反“删除”义务的行政责任限于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形,显然这一规定的威力大大降低。仅一年后,国务院出台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其沿袭了这一强制义务之表述,但其借鉴了美国法的做法,将“通知—删除”界定作为免责条件。显而易见,这些立法在良性的网络环境下尚能发挥作用,但对于我国当时的产业背景,这一做法无疑促使网络侵权问题的解决涌向司法路径,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此外,国外的知识产权权利人集团对我国借鉴“避风港”规则极为不满,他们积极制造贸易摩擦以影响中国的立法。2008年,代表美国权利人集团的“国际知识产权联盟”(IIPA)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提交了《IIPA’s 2008 Special 301 Report》。该报告要求我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明确:“那些未能根据权利人发出的通知立即移除(侵权)内容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就是侵权者,违反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和《著作权法》。他们应当和其他侵权者一样受到相同的行政处罚。”[29]最终,USTR发布的《2018特别301报告》正式要求我国“应当以惩罚措施为后盾,提供强有力的行政监督手段,以确保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收到权利人发出的通知后,立即移除侵权内容和/或链接”[30]。毋庸置疑,这一要求并无美国法上的理论依据,完全是依据其自身利益“量身定做”的无理要求。
(二)“通知—删除”规则之目的
不容否认,2008年至2009年的《侵权责任法》立法显然受到了上述因素的影响。立法者强调需要根据网络关系的特殊性创制新的法律救济模式[31]。立法者还进一步指出:“之所以这样规定,主要是考虑到,网络具有即时性的特征……如果不赋予被侵权人及时救济的权利,会使损害后果无限扩大,连侵权人也无法控制,可能导致被侵权人无法获得充分救济。”[32]对于网络服务商而言,这一“新的法律救济模式”便是法定的“删除”义务。可见,《侵权责任法》实际上是延续了前述行政规章和行政法规的法定义务之思路,以法律条文回应了美方的要求。不过,不同点在于《侵权责任法》的“删除”义务系以民事连带责任为后盾。
由此可以看出,立法者有意改变“愈演愈烈”的网络侵权现象。将“删除”义务规定为法定义务,在很大程度上能实现其指引作用。一方面,这一做法是以国家的名义对盛行的“互联网价值观”予以否定;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当时互联网产业难以自发地形成良性自治,意图通过“通知—删除”规则促使互联网企业积极地处理侵权的问题,将大量的网络侵权案件消灭于早期,降低权利人的维权成本。
当然,这一点在我国的整体战略层面亦有印证。2008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将“盗版、假冒等侵权行为显著减少,维权成本明显下降”和“全社会特别是市场主体的知识产权意识普遍提高,知识产权文化氛围初步形成”列为五年之内的目标。同时,该战略将培育知识产权文化作为重点,强调“在全社会弘扬以创新为荣、剽窃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假冒欺骗为耻的道德观念,形成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的知识产权文化”。从这一规则近十年来的实施效果来看,其无疑是成功的。各大互联网公司依照“通知—删除”规则逐渐建立了知识产权侵权处理机制,众多网络侵权案件得以消灭在前端,权利人得以以极小的成本实现维权的目标。同时,“互联网价值观”也开始褪色,网络用户逐渐形成了付费消费的习惯。总结来看,“通知—删除”规则实实在在地发挥了法律的指引作用。
(三)“通知—删除”规则——行为规范
虽然我国选择以连带责任作为“通知—删除”规则的后盾,但就这一规则的违反是否必然构成侵权,笔者持否定态度。当然,那些持归责条款理论的学者仍然是主流。特别是在这一主流观点的影响之下,司法实践不得不采用前述解释论的路径,对一些法律用语进行“创造性”的解释。事实上,立法者未明确侵权责任的必然性,相反,其存在区分“通知—删除”规则和侵权的构成之倾向。例如,在立法的过程中,曾有反对这种法定“删除”义务的意见,不过,立法者指出:“如果发布信息的人认为其发布的信息没有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可以援引‘反通知’程序,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恢复,如果事后证明不存在侵权行为,没有侵犯发出通知的人的人格权、著作权等合法权益,发出通知的人应当对由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33]换言之,即便不存在事实上的侵权行为,立法者仍倾向于采用“电商平台先行删除,再恢复或者让通知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模式。由此可见,履行“删除义务”在一定程度上与侵权是否成立并无关系。对于电商平台而言,“通知—删除”规则实际效果是法律直接规定了配合义务,即法律明确了电商平台的行为标准——接到通知后立即删除。
这种行为具有一定的“行政强制”色彩,但在信息社会其存在很强的经济效率。在信息社会,网络技术导致信息的传播超越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同时也带来了侵权损害结果难以控制的威胁。网络也冲击着原有的社会治理结构,单纯的政府单向监管模式已难以适应互联网新业态的快速发展①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课题组.关于电商领域知识产权法律责任的调研报告[EB/OL].[2020-03-27].https://www.chinacourt.org/index.php/article/detail/2020/03/id/4871104.shtml.。而网络服务商恰好处在能够通过最小成本实现防范风险之功能的位置。就电商平台而言,其作为第三方服务提供者,对经营者的信息最为了解,可以用低成本、高效率的手段(如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阻止违法行为,相较于政府部门的规制拥有极大的优势[34]。在网络技术的环境下,“最小防范成本”理论是“通知—删除”规则的根基。从这一效果上来讲,“通知—删除”规则的目的在于通过规范网络服务商的行为来实现间接监管网络用户的最终目的,其在整体上强调于网络或者代码空间的秩序,但忽视了侵权行为之构成。
2019年生效的《电子商务法》亦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该法的起草者指出:“在互联网治理的宏观体系之中,平台采取的知识产权措施性质上不同于单纯的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限制或抗辩机制,而是前所未有的互联网治理的新举措。”[35]相关学者也认为《电子商务法》明确将电商平台的知识产权保护从侵权责任转变为“第三方义务”[36]。
六、通知删除规则与侵权认定的关系
在明确了“通知—删除”规则的性质之后,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便是这一规则的违反和侵权行为的认定之间的关系。在确实存在侵权行为的情况下,电商平台未按照权利人通知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的行为,已经满足了侵权责任的客观要件。关键在于,电商平台的侵权主观要件之认定。本章节就此问题展开讨论。
(一)理论视角的剖析
在现代民法对主观要件进行客观化的背景下,行为人主观的判断聚焦于是否违反注意义务。在实践中,对法律规定的行为标准的违反可能会被视为违反注意义务。相关学者也指出,注意义务的存在首先在于法律的明确规定,依此产生的注意义务一般较为明确、具体、容易查明和为人们所理解接受[37]。按照这种观点,如果电商平台违反了“通知—删除”规则,那么也就意味着违反了注意义务,进而存在主观过错。
事实上,注意义务的概念源于英美法系,而我国民法体系则以大陆法系为模范。在大陆法系的侵权法观念中,违法性(行为违反法律规定)仅仅是侵权的构成要件之一,仅违法性本身并不能直接触发侵权行为的成立,这种将违法性等同于侵权行为本身的做法并无理论上的依据。再者,从前文分析来看,这一“通知—删除”规则本身并非着眼于侵权行为之构成,而是要建立良性的互联网产业秩序。相关学者也指出行为规范往往并不局限于个案的得失,能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就同类问题给出处理之道,而侵权法的优势在于对个案进行个别化的斟酌考虑[38],这导致行为规范和侵权法的目的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背离。由于这种背离,加之违反行为规范的原因难以预测,因此,不能简单地将这种行为标准的违反视为注意义务的违反。
如前文所述,在我国,遵守“通知—删除”规则的行为并不能认定网络平台一定没有过错,同样,如上之理由客观违反了“通知—删除”规则的行为对于侵权法意义上的过错之认定不能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因为立法者基于特定目的确立行为标准时难以考虑到侵权法下的相关理论,更难以根据权利类型进行区别规定。
对于行为规范与侵权法理论之间冲突的协调,民法理论已经提供了较为成熟的解决方式。在民法理论中,一般将以保护他人权益为目的的规范称之为保护性规范[39],“通知—删除”规则系出于保护他人权利之目的,因此可以属于保护性规范。按照民法理论,这一规范的违反并不能等同于侵权法意义上的过错,仅仅可作为过错的证据。
这点已经在比较法上得到充分之体现。德国民法典第823条(2)规定:“违反以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者,应当对他人因此而产生的损害负赔偿义务,依照法律的内容无过错也可能违反法律的,仅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才触发赔偿义务。”该条文明确了因违反保护性规范的侵权损害责任仍然应当以过错责任为基础。德国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界通说认为,在客观要件上违反了保护性规范的情况即指示出加害人的过错,可以使得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得以减轻,加害人通常应当举证证明足以排除其过错的情况[40]。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84条第2款也规定:“违反保护他人之法律,致生损害于他人者,负赔偿责任。但能证明其行为无过失者,不在此限。”台湾地区的通说也认为违反保护性规范的侵权责任仍然属于过错责任,而非无过错责任[41]。美国《侵权法重述(二)》第86条虽然规定违反保护性规范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但是其288A条也同样规定在不存在过错的情况下可以不承担责任①Restatement(Second)of Torts§288A Excused Violations(1)An excused violation of a legislative enactment or an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is not negligence.(2)Unless the enactment or regulation is construed not to permit such excuse,its violation is excused when(a)the violation is reasonable because of the actor's incapacity;(b)he neither knows nor should know of the occasion for compliance;(c)he is unable after reasonable diligence or care to comply;(d)he is confronted by an emergency not due to his own misconduct;(e)compliance would involve a greater risk of harm to the actor or to others.。从这些规定来看,违反保护性规范的行为可以推定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但允许被控侵权人举证证明其不存在过错。
基于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违反“通知—删除”规则,在侵权法上的意义仅仅是作为行为人的主观的过错证据,其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侵权行为的认定条件。这一点也在我国实践中有反映,一些法院也存在区分“通知—删除”规则的违反和侵权认定的意识。
(二)司法实践对“法律条文”的超越
很多法院超越法律条文之外,在司法实践中将违反“通知—删除”规则的情况和侵权要件中的“过错”之认定区别对待,对于违反“通知—删除”规则的情形直接认定行为人不存在过错。
在一部分案例中,接到通知之后,电商平台未对产品进行下架,仅仅是履行了转通知等信息传递义务,法院并未采用对“必要措施”进行扩大解释的路径,而是直接认定电商平台尽到了注意义务,不存在主观过错。比如在湖南简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永康市万帆工贸有限公司、永康市奥雅贸易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中,天猫公司接到投诉后,以万帆公司和奥雅公司提交不侵权证据、无法判断侵权为由允许其继续销售,在这个过程中未曾将侵权产品下架。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该案判决书中指出:“天猫公司……通过事先要求用户签署淘宝平台服务协议等以合同形式明确约定不得发布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信息、在网站中披露卖家的真实身份,诉讼中审查涉案信息、要求卖家申诉、并在综合考虑涉案专利与被控侵权产品之间的侵权判定难度后提示原告司法诉讼解决,已尽到了其作为电商平台的合理注意义务。”①参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1民初3765号民事判决书。持类似观点的案例不在少数②比如在上海艾尔贝包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义乌市贝格塑料制品有限公司、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中,阿里巴巴公司同样仅进行了转通知。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在该案中指出:“阿里巴巴公司收到原告投诉后,及时将该投诉转达给被投诉人,在收到被投诉人的反通知后亦及时将该反通知转送给投诉人,被告阿里巴巴作为网络服务经营者,对于其关于投诉人与被投诉人提交的投诉和反通知中专利侵权与否的判断不能苛以过高要求,故原告认为被告阿里巴巴公司存在主观过错、应与被告贝格公司构成共同侵权的主张不能成立。”参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6)沪73民初841号民事判决书。在应钢峰与广东汉斯工具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中,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出:“天猫公司在收到应钢峰投诉后已经将投诉内容通知汉斯公司,并委托第三方机构就专利技术比对出具咨询意见,在第三方机构出具咨询意见认为该产品使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天猫公司对侵权产品链接未予删除。对于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天猫公司而言,其已经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不宜认定其对汉斯公司侵权行为的发生或侵权损害结果的扩大存在主观过错,其不应承担间接责任。”参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民初754号民事判决书。。
同时,也有一部分案例,电商平台甚至未采取转通知措施,其依据专业的咨询意见保留侵权链接,法院直接认定电商平台并不存在过错。比如在赵志谋与台州市冰雪儿电器有限公司、深圳市米阳生活电器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中,天猫公司收到诉状后,请浙江省知识产权研究与服务中心出具了《专利侵权判定咨询意见》,因无法得知涉案侵权商品的内部结构,无法判断是否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天猫公司保留链接等待司法裁决。2018年1月30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该案中指出:“在本案中,天猫公司虽然未删除侵权产品信息链接,但鉴于涉案专利系发明专利,侵权认定涉及侵权产品内部结构特征的比对,在天猫公司已委托浙江省知识产权研究与服务中心进行侵权比对,尚无法得出侵权结论的情况下,天猫公司未删除侵权产品链接并无过错,无需承担共同侵权责任。”③参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1民初800号民事判决书。在东莞冠威绿之宝实业有限公司与广东顺德喜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中,天猫公司在接到投诉后将相关材料交予浙江专利服务中心对相关涉案侵权进行判断,因未得到明确回复构成侵权,天猫公司并未删除链接。2017年12月29日,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在该案中指出:“本案专利权为一项发明专利权,判断被诉侵权产品是否侵权涉及技术方案的对比,要求很强的专业性,天猫公司不具有能力和责任去判断其平台上交易的单个被诉侵权产品是否落入本案专利权保护范围。天猫公司在接到冠威绿之宝公司投诉后已将相关材料交予浙江专利服务中心对相关涉案侵权进行判断,因未得到明确回复构成侵权,故天猫公司并未删除链接。天猫公司已尽到事先提醒注意义务,不存在主观过错。”④参见: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7)粤73民初2284号民事判决书。
司法实践中甚至存在电商平台接到通知后既未采取转通知措施也未咨询专业意见的情况,但法院仍然以不能证明电商平台未尽到注意义务为由,进而认定平台不存在过错。比如在深圳市宇思岸电子有限公司与郑松样、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中,宇思岸公司在2017年12月就向寻梦公司发出了投诉通知要求下架被诉侵权产品时,寻梦公司未及时受理,直到2018年1月29日“接到起诉材料”由寻梦公司予以删除。2018年11月16日,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指出:“宇思岸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寻梦公司在处理侵权投诉的过程中有故意拖延或存在其他过错行为……且专利侵权存在一定的隐蔽性,判断被诉侵权产品是否侵害涉案专利权需要依赖于专业知识,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寻梦公司未尽合理管理义务,对涉案侵权行为的发生存在主观过错。”⑤参见: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8)粤73民初1339号民事判决书。
尽管上述案例均是专利案件,但是法院在一些商标案件中也采取了同样的思路⑥参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3民初5272号民事判决书、义乌市人民法院(2018)浙0782民初8908号民事判决书。。同时,这些案例并不局限于某一地区。这说明我国司法实践界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在违背“通知—删除”规则的情形下仍不能认定存在侵权要件上的过错,在事实上赋予了电商平台一定的自治空间。当然,比较遗憾的是,在上述案例中法院并没有进一步明确违反“通知—删除”规则和过错认定之间的关系。
七、结论
在“通知—删除”规则确立后,互联网产业环境发生了良性的变化,但同时出现了恶意投诉让电商平台不胜其扰的现象。据统计,在2016年,阿里巴巴平台总计发现恶意投诉行为的权利人账户5862个,近103万商家和超过600万条商品链接遭受恶意投诉,造成的卖家损失多达1.07亿元①参见:2016阿里巴巴平台治理年报[EB/OL].[2017-03-31].http://download.taobaocdn.com/freedom/37886/pdf/p1bdauvcnh1kakdfphrg3p6mj4.pdf.。从当前的立法来看,法定义务这一模式仍然存在惯性,这一惯性已经滋生了“矫枉过正”的苗头。因而,我们更应当跳出“机械法学”的路径,以该规则所要实现的法律目的为导向,区分“通知—删除”规则的违反与侵权行为之本身,明确“通知—删除”规则仅仅是指引性的行为标准,在侵权法上的意义仅仅是作为过错之证据,所谓“连带责任”仅仅是告知违反的潜在后果。以此,方能维护平台之自治,同时又能以“反证过错”的方式要求电商平台尽到力所能及的侵权处理义务。
由此,“恶意投诉黑名单”的法律问题也便迎刃而解。对恶意投诉人进行封杀不处理其后续投诉,形式上违反“通知—删除”规则,但由于“通知—删除”规则仅仅是指引性的行为标准,不处理投诉的情形仅仅是作为电商平台存在过错的证据,电商平台可以提交恶意投诉的证明材料反证其主观上不存在过错。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电商领域知识产权法律责任的调研报告》之精神:法院在解读电子商务法规定的网络治理措施时,应当尊重平台的这种自治权限,为其开展网络治理留下可以施展拳脚的空间,使其能够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商业实际灵活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②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课题组.关于电商领域知识产权法律责任的调研报告[EB/OL].[2020-03-27].https://www.chinacourt.org/index.php/article/detail/2020/03/id/487110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