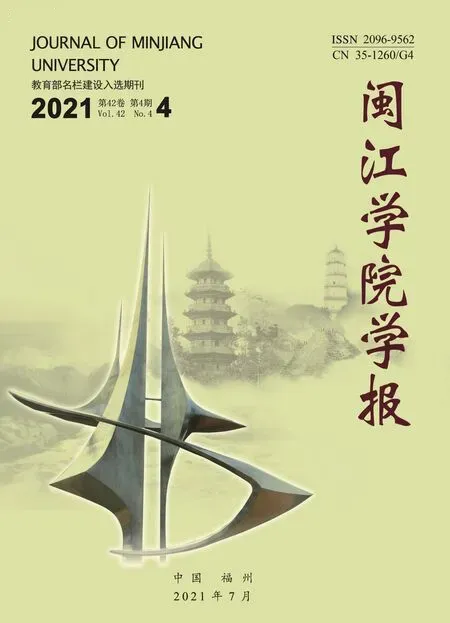关于陈第《屈宋古音义》的若干思考
陆招英
(1.福建工程学院人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8;2.福建工程学院地方文献整理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 350118)
汉语语音的变化,汉朝的刘熙已有所注意,但没有明确记载。南北朝时,人们在诵读上古韵文时,遇到不合谐的韵脚,便临时改成自己认为合谐的读音,使之谐韵,这就是所谓的叶音说。至明代时,陈第力辟“叶音说”,否认了叶音这种随意改音的做法。陈第是我国明代音韵学家,字季立,号一斋,万历初诸生,福建连江人,曾任蓟镇游击将军,坐镇蓟门10年,后致仕归里,专心研究古音,著有《毛诗古音考》《读诗拙言》《屈宋古音义》等。陈第既是一个抗倭名将,又是一个有着重要学术贡献的音韵学家。他的《屈宋古音义》是首部研究楚辞音韵的专门著作,一定程度上为清代古音学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屈宋古音义》是一部探求古音的著作,全书共分为三卷,涉及屈原、宋玉作品38篇,把屈宋文中韵字与今音不同者列出,所列字目达234个,注音达850余字。陈第所录屈原作品共24篇:《九歌》11篇,《九章》9篇,《离骚》《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未录《天问》;又取宋玉作品14篇:《九辩》9篇,《招魂》《高唐》《神女》《风赋》《登徒子好色赋》各1篇。陈第考证了234个与今音相异的韵脚古音,多引用《毛诗》及周秦汉魏以来的歌赋和典籍进行考证。他在凡例中说:“今检屈宋音与《毛诗》同者八十余字,则提其本音,直注云:详见《毛诗古音考》。”[1]凡例这234个韵脚的古音与毛诗相同的有80多字,其详情见《毛诗古音考》,另外的150多字则旁引他书为证。本文通过研究陈第关于这150多字的相关考证,阐释陈第在《屈宋古音义》中的古音考证方法以及对《楚辞》研究的贡献。
一、《屈宋古音义》的古音研究方法
陈第学识渊博,涉猎广泛,他以历史的观点考察古今音,用审慎的态度分析语言材料,提出了不同前人的观点,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研究古音的方法是科学的、有效的。(1)刘青松《陈第古音学思想形成探因》认为陈第能破除“叶音说”,并明确提出音有转移的观点,既得力于前人及同时代学者的影响,更得力于他对《诗经》《楚辞》的研究。(《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一)本证与旁证相结合
陈第在《毛诗古音考》中采用了本证、旁证相结合的方法考求古音。他在《毛诗古音考自序》中云:“于是稍为考据,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错以谐其韵。”[2]所谓本证,即以《楚辞》的押韵字自证,以考求古音之源;旁证,则采用其他先秦两汉的典籍文章和辞赋为证,如引用《周易》《老子》《文子》和王延寿《王孙赋》等。(2)孙巧云《论陈第〈屈宋古音义〉之历史地位》中谈到陈第举证古音的方法,包括《楚辞》与周秦汉魏诸典籍、文章、辞赋互证。(《邯郸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接下来举“差”字的读音为例,看看陈第是如何依据本证和旁证得出结论的。
差,音磋。今之“蹉跎”,古作“差沱”。《文子》:“水虽平,必有波;衡虽正,必有差。”严忌《哀时命》:“志怦怦而内直兮,履绳墨而不颇;执权衡而无私兮,称轻重而不差。”
《离骚》:“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登徒子好色赋》,差亦同音。[1]7
为了证明“差”的读音,陈第不仅指出现在的“蹉跎”,古音是“差沱”,而且列举了《离骚》作为本证,说明“差”“颇”押韵,同时指出《登徒子好色赋》的“差”亦同音。用《离骚》和《登徒子好色赋》韵字作为本证,在选择材料时突出了共时的特点,旁证则列出《文子》和严忌《哀时命》中的“波”“颇”“差”三字押韵。他所举的例证既有来自《离骚》内部的本证,又有时代相去不远的《文子》和严忌《哀时命》作为旁证,二者互相验证,提高了可信度。且西汉时代的语音与屈原时代相近,古音相合,选择这个时期的名家作品作为论证的基础,是从实际出发的历史语言观念。
陈第通过列举本证和旁证,确定“差”“颇”“波”押韵,如果再系联其他押韵的字,那么屈宋辞赋的一个韵部基本可以确定下来。这就相当于做屈宋辞赋韵字的系联工作,是一种依据语音实际加以比较归纳的研究方法,给后人研究古韵分部提供了方向,为古韵的归纳研究开辟了一条道路。
(二)形音义相结合
陈第在《屈宋古音义》中常引用《说文解字》(后文简称《说文》)来考证古音,他利用汉字形、音、义结合的特点,从字形和意义入手确定字的读音。汉字中大部分都是形声字,形符表义,声符表音,虽然经过长时间的历史演变,许多字的读音也发生了改变,但是在《说文》时代,形声字的读音与声符必然相同或相近,因此可以根据声符考证古音。所以陈第非常重视分析形声字在考察古音中的作用,特别注意到《说文》在古音研究上的价值,不仅在《毛诗古音考》中用《说文》分析了大量汉字,在《屈宋古音义》也仍沿用此法,从形声字来观察古音。如:
帏,音怡。《说文》:“从巾,韦声。”韦古读怡。张协《浴禊赋》:“粉葩翕习,缘阿被湄。振袖生风,接衽成帏。”梁元帝《班婕妤辞》:“婕妤初选入,含媚向罗帏。何言飞燕宠,青苔生玉墀。”
《离骚》:“椒专佞以慢慆兮,榝又欲充其佩帏。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1]11
“帏”字读音为“怡”,便是从形声字的声符“韦”字所得。陈第借助《说文》说明其形符是“巾”,声符为“韦”,而韦的古音读为“怡”,陈第认识到同谐声必定同音,推论“帏”的读音也应当读“怡”,然后再用其他韵文材料作为旁证,证明“帏”“湄”“墀”“祗”押韵。
“枫”字也是如此,除了形音结合证明同谐声必同音之外,还利用反切明确该字在诗句中应读的音:
枫,孚金切。《说文》:“从木,风声。”风,古音孚金切。张衡《西京赋》:“木则枞栝椶柟,梓棫楩枫,嘉卉灌丛,蔚若邓林。”[1]39
“枫”字没有直接注出读音,而是先采用反切法,再引用《说文》分析形声字的方法来说明该字古音。“枫”,《说文》中声符是“风”,“风”的古音为“孚金切”,陈第考虑到同谐声必同音,由此推断“枫”也是“孚金切”。
除了结合音形考证古音外,陈第还从字义入手确定字的读音,特别是对一些多音字的读音尤其慎重,这是他在语音、诗韵的考证过程中对音韵学的贡献。如:
治,音持。旧有平、去二声。凡未治而理之者,平声。已理而有效者,去声。经史皆此读。《诗》:“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尤兮。”尤音怡。
《惜往日》:“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袐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1]25
“治”有两种含义,对应不同的读音,“未治而理之”之意读平声,“已理而有效”之意读去声,他还结合了《诗经》里的例子证明《九章·惜往日》中的“虽过失犹弗治”的“治”应该读为“持”。
(三)依据前人读音
陈第除了采用本证旁证、形音义相结合的方法考证古音之外,还使用其他的方法求得古音,前贤古读是其中一种使用得比较多的手段。[3]如:
属,音注。《考工记》:“犀甲七属,兕甲六属,合甲五属。”郑玄云:“属,读如灌注之注。”
《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1]8
“属”,陈第采用了郑玄的读音,“读如灌注之注”。
还有“舍”字,其注音依据魏了翁的读音,同时还用《周易》作为旁证:
舍,音暑。魏了翁云:“六经,凡下,皆音虎。舍,皆音暑。”《易·乾象》:“潜龙勿用,下也。见龙在田,时舍也。”
《离骚》:“余固知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1]2
还有些字依据吴才老的读音,如姱:“音甫。与嫭通,吴才老读。”[1]16琼:“音强。吴才老读。”[1]38依据杜子春的读音,如壇:“音廛。《周礼·廛人》:‘故六书廛为壇。’杜子春读壇为廛。”[1]20依据高诱的读音,如络:“音路。《淮南子·览冥训》:‘黄云络络。’高诱读作‘道路’之路。”[1]37
陈第还通过辨别同音假借与前人读音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某个字的读音,如:
时,音是。古时、是通音。《尚书》“时日曷丧”,时,是也。“播时百谷”,王肃作“是”。“敛时五福”,马融作“是”。[1]5
“时”“是”古时同音,可以假借使用,王肃和马融都认为 “时”与“是”同音。因此,陈第也认为时的读音应为“是”。如:
池,音沱。徐铉曰:“池沼之池,古通作沱。今别作池,非是。”
《少司命》:“与女游兮九河,冲飚至兮水扬波。与女沐兮咸池,晞女发兮阳之阿。”[1]15
“池”读音当为“沱”,二者当为假借使用,徐铉认为二者古代能通用。但是他又说“今别作池,非是”,应该表示二者古代通用,后来由于语言的发展变化不通用了。
(四)声训材料考证
声训是指通过语音分析词义,用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解释词义并推求词义来源的方法,因此许多音韵学家利用这种汉字音同或音近的关系去考证上古汉字的读音。虽然声训解释词义有许多的主观臆测,不尽可信,但是利用这些材料可以考查古音,只取其音不用其义还是可行的。如:
索,音素。《释名》:“索,素也。”《书序》:“八卦之说,谓之八索。”徐邈音素。皋鱼引古语云:“枯鱼衔索,几何不蠧。”
《离骚》:“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1]3
陈第在探求《离骚》中“索”的读音时,直接从《释名》中的声训得到其读音为“素”,徐邈也认为“索”音为“素”,从而更加确定了“索”的读音为“素”。
进,音箭。《周官》:“其利金锡竹箭。”注云:“故书箭为进。”《释名》:“矢又谓之箭。箭,进也。”《列子》:“周穆王西巡还,道有献工人偃师,穆王荐之。”荐之,进之也。以此见古荐、进之音同。
《抽思》:“轸石崴嵬,蹇吾愿兮。超回志度,行隐进兮。”[1]22
“进”,也是直接从《释名》中的声训考证其音为“箭”,且还利用《周官》作为旁证证实“箭,进也”,二者互训;再采用《列子》中的语料进一步系联说明“荐、进、箭”是同音字。
二、《屈宋古音义》在《楚辞》古音考证方面的贡献
《毛诗古音考》和《屈宋古音义》是陈第研究古音学的重要著作,在我国古音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后者也是研究探求《楚辞》古音韵的必读之作,黄灵庚先生认为它是“首部研究楚辞音韵之专书”[1]前言一。
(一)使用材料丰富
陈第非常重视古人的研究成果和古代的文献,广泛使用这些材料并充分利用。《屈宋古音义》参考各类古书数十部,还有许多前人著作。先秦两汉的文献有《诗经》《论语》《周礼》《老子》《荀子》《战国策》《史记》《吕氏春秋》等,如“媛,音然。《诗·君子偕老》:‘子之清扬……邦之媛也。’”[1]28;“华,音敷。《周礼·形方氏》:‘正其封疆,无有华离之地。’”[1]15;“虑,音鲁。《吕氏春秋》:‘黔如作虜首。’”[1]28。还有《说文》和《释名》中的语言材料,如“惩,音长。《说文》‘从心征声。’”[1]6。还广泛引用了郑玄、陆德明、徐邈、沈约、吴才老、王肃、杜子春、高诱等人的古读,其中依吴才老的古读较多,如“姱,音甫。与嫭通,吴才老读”[1]16;“沛,音嬖。吴才老曰:‘今声浊叶队,古声清叶祭。’”[1]41。
另外还引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多位作家的作品作为旁证材料,如“云,音银。详见《毛诗古音考》。又音延。曹丕《玛瑙勒赋》:‘初伤勿用,俟庆云兮。君子穷通,亦时然兮。 ’”[1]14。引用曹丕的文章证明“云”的读音。
(二)注意区别多音字
一个字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读音,不同的读音表义不同,词性也往往不同。陈第明确认识到了多音字具有区别词义的作用,根据使用情况的不同,读音也不同。如:
蛇,音陀。详见《毛诗古音考》。古亦音怡,凡览古辞赋,在依上下文读之可也。[1]12
“蛇”一音为“陀”,其读音详解在《毛诗古音考》中,不细表;另一音为“怡”,陈第建议我们看古书时,要根据上下文读这两个音。再如:
卫,音越。详见《毛诗古音考》。按卫亦有意音。张华《尚书令箴》:“法制不修,不长厥裔。尚臣司台,敢告侍卫。”若卫读越,则厉读冽,卫读意,则厉读如字。
《远游》:“路漫漫其修远兮,徐弭节而高厉。左雨师使径侍兮,右雷公以为卫。”[1]30
“卫”字音为“越”,在《毛诗古音考》中已经有详细论证,但“卫”还有一个读音为“意”。而《远游》中的“卫”字,陈第提供两种读音,且影响了“厉”的读音,如果“卫”音为“越”,那么“厉”音为“洌”;如果“卫”音为“意”,那么“厉”读如本音。又如“瑕”字:
瑕,音蓑,亦音蒿,古音胡,后稍转矣。详见《毛诗古音考》。[1]34
“瑕”字也是个多音字,古音为“胡”,后来又转有其他读音“蓑”和“蒿”,可见语音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完全符合陈第所提出的“音有转移”这一理论认识。“瑕”字具体论证在《毛诗古音考》中,此处不再细说。
(三)不拘泥于《说文》的形声偏旁
利用形声字考证古音是非常值得称赞的做法,陈第在《毛诗古音考》中特别注意形声字的分析,从谐声关系观察古音,这种方法也应用到了《屈宋古音义》中:
横,音黄。《说文》:“从木,黄声。”苏秦语:“合从连横,兵革不藏。”扬雄《冀州箴》:“更盛更衰,载从载横。汉兴定制,改列藩王。”汉人称周举曰:“五经从横周宣光。”[1]32
“横”音“黄”,依据的材料是《说文》以及其他的旁证材料。黄,匣纽,阳部,唐韵;横,匣纽,阳部,庚韵。可见“黄”与“横”声母相同,都属阳部,韵不同。陈第依据《说文》认为“横”音“黄”,它们音值应该是非常接近的。但是还有很多时候,形声字只能反映语音系统中的大致读音,并不是具体的音值。陈第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因此注音有时采用古读,而不采用《说文》中的声符,如“肬,音怡。《说文》:‘从肉,尤声。’ 尤古读怡。”[1]17“帏,音怡。《说文》:‘从巾,韦声。’韦古读怡。”[1]11“肬”“帏”这两个字的读音用的是古读“怡”。
三、《屈宋古音义》的不足之处
陈第对古音研究的贡献非常大,黄灵庚先生称赞他“考定《屈宋古音》,当称古今第一人”[1]前言5,盛誉之下,我们也要用发展的眼光正确看待《屈宋古音义》中古音考证的遗憾。
(一)注音方式不统一
《屈宋古音义》注音方式主要是用“某音某”的直音法,如“柏”,音“博”;“雄”,音“盈”。
还有的字既有声调也有注音,如“志,平声,音芝。古有平、去二声。《易·革·小象》:‘革言三就,又何之矣。改命之吉,信志也。’”[1]17;“盘,音便,平声。古诗:‘上枝似松柏,下根据铜盘。雕文各异类,离娄自相连。’”[1]9。
但是有一些字只有声调,无注音。如“异,平声。《诗·静女》:‘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黄公绍《韵会》云:‘异可平可仄。’”[1]10。
还有些字用反切注音,如“枫,孚金切。《说文》:‘从木,风声。’风,古音孚金切。”[1]39;“寒,胡涓切。伯奇《履霜操》:‘履朝霜兮采晨寒,考不明其心兮信谗言。’”[1]37。直音法是《屈宋古音义》的主要注音方式,其间有些字用别的注音方式或许是陈第未找到最合适的注音字,也可能是别的原因,有的学者认为是避讳或遗漏造成。而只注声调未注音的这种情况极少,其原因不得而知。(3)关于拟音的问题,吴林娟、王耀东《陈第审音之功浅》谈到陈第青少年时期在离福州很近的连江度过,后又到福州讲过学,因此他的注音会受到方言的影响。(《河西学院学报》2007第6期)
(二)转音之说模糊
陈第在考证字音时,有时会认为某字后来转为某音,如:
待,音持。《易·蹇》初二《小象》:“往蹇来誉,宜待也。王臣蹇蹇,终无尤也。”尤音怡。待,后稍转为底音。[1]11
霞,音敷。司马相如《大人赋》:“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咀噍芝英兮叽琼华。”至魏、晋转为蒿音。[1]29
“待,后稍转为底音”,“霞,至魏、晋转为蒿音”, 陈第虽然注意到语音的发展变化,但并无相应的证明材料,只是提出后转为某音,即便不影响该字原本的注音,但有强转之嫌。如“霞”字,匣母,麻韵,《广韵》胡加切;“蒿”,晓母,豪韵,呼毛切。前者是麻韵,后者是豪韵,韵母有区别。
陈第在自己的理论基础上,通过分析《离骚》等其他大量资料,使人们明确了古音与今音的不同与变化,为此后我国音韵学家的上古音研究奠定了基础。其研究成果虽有不足之处,但他考求古音的方法是科学的,也被后代学者所继承,对我国的音韵学研究做出了较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