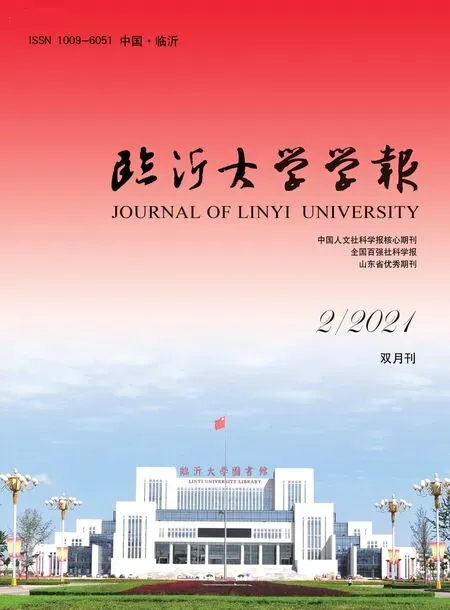从论争到建构
——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理论进路
韩 旭
(1.阜阳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阜阳236037;2.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241003)
思想进程的每一次飞跃,总是伴随着论争。通过不同派别的论争与“解蔽”,加上科学合理的逻辑思维,我们才能从中获得比较全面且符合实际的真理。 真理的发展历程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马克思主义的成长和发展同样注定不平凡,在本土受到排斥和打击,在异乡也不例外,“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1]。 在中国传播和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始终受到一些反马克思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百般歪曲和抵制。 他们一方面企图复归封建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又摆弄着西方“时尚”的种种主义,妄图泯灭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 作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艾思奇总是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对这些思想和行为给予坚决的回应。他运用其娴熟的哲学方法和清晰的哲学思维对当时社会存在的三种代表性的哲学思潮进行了无情地抵制和批判,使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缩水”,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在我国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并逐步成为我党与敌作战的一面光辉旗帜。
一、艾思奇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言论的论争
20 世纪30 年代,艾思奇论争的焦点集中在以张东荪和叶青为代表的反马克思主义和伪马克思主义派别身上。反马克思主义者张东荪认为,马克思的学说至多只能称之为“社会哲学”或者“历史哲学”,谈不上是科学,唯物辩证法是一个蚕绩蟹匡、颠倒黑白的东西。这与当时著名的穆斯林学者傅统先观点基本一致。 傅统先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多半从事政治经济及社会事业,而对于新唯物论则缺乏详细的论述。 故从唯物辩证法的“哲学”特性来看,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张至多只能称之为社会或历史哲学,永远游离于哲学之外。这是从哲学和科学的关系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污蔑和诽谤。为驳斥他们的错误观点,稳住唯物辩证法的科学地位,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区分了哲学和科学的不同。他指出,主张用科学代替哲学或者用哲学淹没科学都是不科学的。 科学是分门别类对各自的每一领域、每一范围进行研究,把这些领域、范围作为其研究对象,寻找其中的具体规律;而对世界一切范围的普遍性的认识,则是哲学的任务。 “科学认识各种有限的范围内的事物法则,而哲学则研究最普遍最一般的法则。”[2]这就从研究对象上正确区分了哲学和科学的不同。此外,在认识论、辩证法等方面,艾思奇同样给以坚决的论争,进一步宣介了马克思主义。艾思奇在同张东荪等反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论战的同时,对伪马克思主义者叶青也进行不懈地斗争。
“披着辩证法外衣的唯心论”者叶青,则以伪马克思主义“忠实维护者”的身份守护在国民党反动派左右。 在科学和哲学的关系上,叶青同张东荪等人一样,否认辩证唯物论是“哲学”。他认为,社会历史上只存在宗教、哲学和科学三种知识,而且“它们是一个产生一个;又一个代替一个的。 其次序是由宗教而哲学而科学”,辩证法唯物论是黑格尔以后的“科学”,“黑格尔以后,不再有哲学了。费尔巴哈把它消解于人类学中,马克思把它消解于社会学中。现今存在的哲学,如新观念论、新生机论、新实在论等,乃是哲学消解后的残渣”[3]。让其最引以自豪的则是他的“外铄论”。他以“外铄论”为由,不断蛊惑、诱骗国人。叶青指出,一切事物的发展溯源于外部因素,这都是“合规律的”原则。但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却“不合规律”。事实上,叶青也承认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促成的,只不过他转了一个弯,以“一般之中有特殊”为由,主张“欧洲史是合规律的……。中国则不然”[4]328。针对于此,在《关于内因论与外因论》一文中,艾思奇对叶青伪马克思主义的丑恶嘴脸进行了无情批判。 在艾思奇看来,叶青“承认辩证法之后,转一个弯又说辩证法不能适用在静态研究上一样,他也只承认了内因论的本质性的一个幌子,转一个弯又说在某些国家的发展里不能用内因说明”[4]329。 这是艾思奇对叶青企图歪曲与篡改辩证法最彻底的揭露。 另外针对叶青扬言攻击“否定外因”的论断,艾思奇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同样给予了强烈的批驳,凸显了唯物辩证法的力量。这一批判也正暴露了叶青反对中国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真实写照。
上海时期,艾思奇对叶青的“哲学消灭论”进行了深刻地驳斥。按叶青的理解,哲学和科学是一个不断展开的过程,直至科学脱离哲学而存在,而哲学则予以归寂。艾思奇针锋相对批判道,妄图用科学代替哲学是荒谬的、非科学的。因为科学研究限制在特定范围和具有特殊规律,哲学则具有宏大叙事的普遍性法则。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特殊离不开一般,一般寓于特殊之中,离开一般,特殊也就不存在了。 因此,叶青宣称的“哲学消灭论”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是完全谬论的。直至1936 年,这场论战才宣告叶青之流伪马克思主义的破产而赢得了辩证唯物论的胜利。艾思奇以一个革命理论者的姿态揭穿了叶青的真面目,强有力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阵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此期间,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有力助手,以通俗化、大众化的语言形式走进了“都市街头,在店铺内,在乡村里,给那失学者们解一解智识的饥荒,却不敢妄想一定要到尊贵的大学生们的手里,因为它不是装璜美丽的西点,只是一块干烧的大饼”[5]。 事实上,这块“干烧的大饼”却赢得了民心,获得了广泛支持,既是对反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有力武器,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力量。 诚如胡愈之夸赞道:“这本书,是青年们认识世界的一盏明灯! ”贺敬之也称誉这本书为革命的“火炬”,指引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 就连蒋介石也甘拜下风地哀叹道:“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 ”《大众哲学》走入群众,深得民心,前后出了32 版,成为广大青年积极向上的理论指南,不仅是革命的书、“救命的书”,而且也引导了有识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中国革命坚实的群众基础,树立了不朽的理论信仰。
1937 年,艾思奇到达延安后,叶青等人又抛出歪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错误言论。 艾思奇同叶青再次交锋,指出叶青把“化”诠释为“创造、改造”之意,误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本意,并强调“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坚定,“中国化”越深入、越创造,越能更正确指导中国实践,越是对马克思主义本意的科学表达。 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最一般的科学理论,我们拿来马克思主义,必须将其与中国实践、中国特点紧密结合,必须与中国现实和时代要求相结合。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叶青反驳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尚未存在“改作”“创造”的痕迹,“辩证法唯物论”在中国也纯属空谈。 他还辩解说,马克思主义可以有一般性,但不能戴上民族的帽子。 这种言论,是对“一般与特殊”的误解。艾思奇批判指出,马克思主义是跨越国际的学说,它的内容是国际的,但形式却是民族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其最好佐证。叶青攻击说,毛泽东只是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不是对“辩证唯物论”的运用。叶青逻辑矛盾的自我辩解,是拿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既然马克思主义不能有民族的形式,又怎么会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说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本身就是“唯物辩证法”与具体国情结合的产物。被迫无奈之下,叶青扔出来一句话,“中国是不需要共产主义,不需要马克思主义”[6]。 实际上,中国革命事业不断前进的事实已经证明: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事业的进步。 正如艾思奇所言,中国是否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那首先就要明确,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何能不断取得惊天地、泣鬼神的伟业,为何能不断推动中国民族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功。正因为中国有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有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在伟大实践的基础上,成就了伟大的民族事业。
艾思奇始终作战在哲学理论第一线。 1941 年8 月,在《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一文中,艾思奇对陈立夫的“唯生论”、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以及阎锡山“中”的哲学给予评析和批判。“唯生论”把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都看成机械唯物论,主张二元论,认为宇宙是心与物的综合,借以孙中山的某些话为依托,企图掩藏其代表“当权的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世界观”的阴谋。蒋介石“力行哲学”的基本理论与“唯生论”不谋而合,同样以二元论来表现,对唯物论进行歪曲和误读。“总理把精神的意义解释得很明白,他说,凡不是物质的东西统统叫做精神……所以我们承认宇宙间除了物质之外还有一种精神的东西存在。 ”(《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在阎锡山“中”的哲学方面,艾思奇认为,这种哲学是民国以来自成一系的地方政权当局者的哲学,较之以“粗燥笨拙的唯生论,它的立论的巧妙,是高出了许多”,具有“相当精致的伪装的一支思想队伍”。[7]在艾思奇那里,“中”的哲学仍然是以唯心论为主导的二元论哲学。 艾思奇对这三种哲学系统深入地批驳,使人们认清了它们的本质,给思想上陷入浑浊的人们指明了航向,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宣介与传播。
二、艾思奇与中国“文化复古主义”者的论争
“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礼记·中庸》古本)中庸之道具有合理性和真理性的一面,成为人们恒常追求的至高教义。 艾思奇指出,中庸和真理极为相像,都站在正义的立场上,保持鲜明、公允的态度。不过,它却具有很强的迷惑性。中庸并不等于真理。中庸要求人们保持中正平和,对待人和事始终持公允之态,既不偏向左,也不倾向右。一言以蔽之,秉承中庸之人,似乎把任何事情看得很开,身上少了火气,而更多的则持和气之势。 诚如中国向来以和为贵,能够从中通达一切人与事,获得其自我生存和发展的良好环境。 所以,我们认为,中庸是一种做人的哲学,更是一种有智慧的人所应持有的态度。 以至于,这样人的健康才有保障,这样的社会才能得以长存,整个社会才能得到平稳发展。 艾思奇认为,这只是看到中庸的表面和停留在中庸的表层,也是中庸保守本质的外在体现,即要求人们用僵化绝对的善固化为人类行为的尺度。在他来看,中国历来崇尚“和”的思想,然而却遭到日本法西斯的不断来袭,这就是批判中庸思想最好的证据,也是“文化复古主义”的佐证。 艾思奇对“文化复古主义”的批判,主要针对梁漱溟一流而言。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梁漱溟就已同新文化思潮分道扬镳。 新文化运动倡导德先生和赛先生,反对封建礼教,“打倒孔家店”。 梁漱溟却以一个卫道士的姿态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借此“发挥”孔子学说。 艾思奇指出,他“狂妄地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来向新文化运动挑战”[8]20,是新文化运动中的逆流。这种逆流的代表:一个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者胡适;一个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者梁漱溟。艾思奇认为,二者因其有着共同的目的,虽在枝节问题和形式问题上有差异,但实际上他们却是“相互呼应、相互配合”,只不过梁漱溟自称为“革命者”,比起公开反对革命的胡适似乎更加狡猾,他不像胡适那样背叛祖国,投靠美帝国主义;而梁漱溟却在伪装的面孔下,承认“自己总是处在统治阶级这一边”。艾思奇进一步指出,梁漱溟承认的错误,是掩人耳目,因为他没有真正承认“自己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为帝国主义服务”[8]22,他对自己的立场是有所掩蔽,需要加以“解蔽”和批判的。
在认识论方面,艾思奇在《批判梁漱溟的哲学思想》一文中,用了大量篇幅驳斥了梁漱溟“由不可知论的诡辩论引到虚无主义”的观点。 首先,梁漱溟的认识论源于对“东方”唯心主义即佛教哲学的汲取。 这就意味着,他的不可知论来源于“唯识学”(按照艾思奇的理解“唯识学”就是佛教哲学里的“不可知论”)。 在艾思奇那里,梁漱溟用“唯识学”歌颂“孔教”。这种唯心主义世界观成就了他的“生命派的哲学”。这种哲学试图从中国传统的旧书堆和柏格森哲学里去寻找信仰主义的出路,即“形而上学”的道路。 其次,在历史观上,艾思奇批判了梁漱溟开历史的倒车。 在梁漱溟看来,天才人物对历史起决定作用,历史如何发展,不是没有规律可循,而是有着其内在的规律,这种规律就是要依靠天才人物。 天才人物左右历史,掌控着历史发展的趋势。换言之,若是没有天才人物,历史可能就会失其存在的可能。从马克思主义视野来看,这种看法否认了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忽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更是否认了“客观的道理”。 后来发生的种种事实使他不得不承认“客观的道理”存在的意义,但他仍要遵循唯心主义道路,遵循他那所谓的“客观性”,认为宇宙中有一种“精神”、一种“意欲”决定历史发展的不同道路。 艾思奇则强调,梁漱溟因“意欲”分歧而产生的三条文化道路(“三步骤”),抑或“三层次”:西方化着眼于研究外界物质,崇尚“理智”,提倡科学与民主;中国式东方化着眼于研究的内界生命,推崇“直觉”“安分守己”等;印度式东方化则着眼于研究者无生本体,崇尚“厌世”“超绝”等的宗教道路。囿于主观唯心论怪圈,梁漱溟认为,印度式东方文化的意欲要求是最高步骤、最高层次的文化。 艾思奇批判说,梁漱溟开历史倒车的历史观在事实面前会碰得“头破血流”,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因为,这种“意欲”完全背离了历史发展的客观性,更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真理要求。 然而,梁漱溟却孤芳自赏,自己咀嚼得津津有味,在他的“著作里就出现了一种稀奇古怪的‘开倒车’的历史观。人类历史的必然前途原来是这么阴暗的:由科学、理性走向‘玄学’、‘直觉’、再走到宗教、‘现量’,由向前发展的要求进而‘盘旋不进’、‘安于现状’,最后是落到要‘厌世’、‘出世’”[8]65。 艾思奇反驳说,人类历史最后既然到了“厌世”“出世”,为什么中国和印度“分别走到了玄学、直觉和宗教、现量的境地,而不必经过第一和第二个‘步骤’或‘层次’呢? ”[8]66对此,梁漱溟难以回应。在他的哲学思想中,梁漱溟带着假面具的客观唯心主义始终不能掩盖他荒谬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丑恶嘴脸。
所以,艾思奇对“文化复古主义者”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他不仅从理论上驳斥这种复古缺乏理论逻辑关系,而且从历史发展的事实中进一步明确了复古的错误和荒谬,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作了深刻正名。
三、艾思奇与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者的论争
产生于 19 世纪 70 年代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是从希腊词 πραγμα(行动)派生出来的,是20 世纪中后期盛极一时的美国主流思潮。与其他流派相比,这种思潮影响更大、流传更广,对英国、意大利和中国等影响至深。五四时期,胡适第一次把“实用主义”传入中国,并运用到中国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由于它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二者产生了冲突。 为扫除马克思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艾思奇研析批判了胡适的“实用主义”,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之间的界限,清除了“实用主义”在中国社会中的错误影响。 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普及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首先,胡适“实用主义”是假装的“最新的”哲学,其本质和被列宁粉碎过的马赫主义流派一样,都是主观唯心主义。 列宁把它们称之为具有“血缘关系”的流派。 “从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马赫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差异,是像经验批判主义与经验一元论的差异一样的极琐细和极不重要的。 ”按照艾思奇的理解,“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都否认物质的客观存在性,“否认科学知识的客观真理性”[8]5,对现代科学成果进行曲解甚至颠倒,使之成为主观唯心主义的门面而加以装饰,不同的是,二者假借的对象不同。 前者打着进化论的招牌;后者借用了现代新物理学之名。“辩证唯物主义承认人的主观的能动作用,和实用主义——主观唯心主义说人能够任意地‘涂抹’、‘装扮’客观实在,任意地‘制造’客观实在的变化发展,是根本不同的。 ”[9]
其次,胡适“实用主义”抹煞了真伪标准的真理观。在《胡适实用主义批判》一文中,艾思奇认为,胡适抹煞真理的客观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主张主观真理,否认客观真理。 胡适把能够“应付环境”,可以收到“效果”的知识或思想就叫做真理。 “真理不过是对付环境的一种工具;环境变了,真理也随时改变。 ”[10]这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背道而驰,否认真理是人对客观事物及其发展的内部规律性的正确性认识;二是抹煞了真理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分界。 在《实验主义》一文中,胡适用“巧妙”的语言和“真诚”的笔调阐释了真理与实在的关系。 “真理就是同‘实在’相符合的意象。 ”[11]712在胡适看来,若是仅就此话来说,而不考虑实用主义者如何曲解这句话,这似乎是合情合理、无可非议的真理,并能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难以区分。 然而,胡适所理解的“实在”与“符合”和辩证唯物主义对这两个词的理解完全大相径庭。他所谓的“实在”并不是指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而是“主观的感觉和观念的复合”[11]712。 对于“符合”,胡适则把它释义为“应付实在”或“适应实在”,“不是临摹实在”;三是把信仰“装扮”成科学。 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胡适认为,“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正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12]。 艾思奇反驳道,胡适夸夸其谈无神论,反对神灵不灭和上帝存在,本质上他并没有要拥护科学和唯物主义,而是积极推崇宗教及其宗教信仰。一言以蔽之,他是借科学之言,背地里却在“偷偷地贩卖一种变相的、精巧‘装扮’了的宗教”[11]717。
最后,“实用主义”是一种庸俗进化论。胡适声称实用主义是进化论的产物,是进化论在哲学上的具体应用。实则不然,艾思奇指出,这是借用进化论的学说来掩盖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真面目。艾思奇进一步强调,实用主义这样做是对人类社会生活和生物进化论的曲解,是挂着“生物进化论”的羊头,贩卖着“庸俗进化论”的狗肉。 按照艾思奇的说法,这种“庸俗进化论”,纯粹是把人的社会生活完全曲解成“应付行为”,把事物的发展看成是无规律、无秩序的“一点一滴的进化”和偶然事件的组合,并试图从这些无规律、无秩序组合的材料中,引出一种变相的宗教迷信观点。在艾思奇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遵循着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决不能简单用进化论来解释。人和动物有着本质区别。人能劳动,会制造工具,有意识,能随着社会的变化做出相应的决策等;动物则不能。动物只能根据自身的本能适应环境,而不能改造它。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人类行为和动物行动有着本质区别,“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13]。人的目的在其活动之前早已预设。主体根据事物固有的属性及其提供的现实可能性,在符合人的目的的要求下,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把知和行、能和所相互统一和不断展开,从而把观念现实化,化理想为现实。即是说,主体行为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自觉活动,是在尊重客观规律基础上的能动性活动。胡适一流的实用主义者却与此相反,否认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存在,否认认识是人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坚持“一点一滴的进化论”,把事物发展看成是一大堆毫无秩序事件的偶然凑合,曲解了事物发展的状态,颠倒了必然和偶然的辩证关系,否认了必然规律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而只认为偶然性支配事物发展的一切。
总之,“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4]。 一种理论或认识正确与否,其自身不能够足以证明,而只有通过实践来检验它的真伪。批判与论争是理论发展的必要条件,又是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艾思奇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伪马克思主义、文化“复古主义”以及“实用主义”等的批判,进一步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不容置疑性,宣传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战斗中不断得到壮大与发展,能为群众所掌握,能够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正确行动指南,再次验证了其本身的实践性、革命性和科学性,也必将指引中国不断走向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