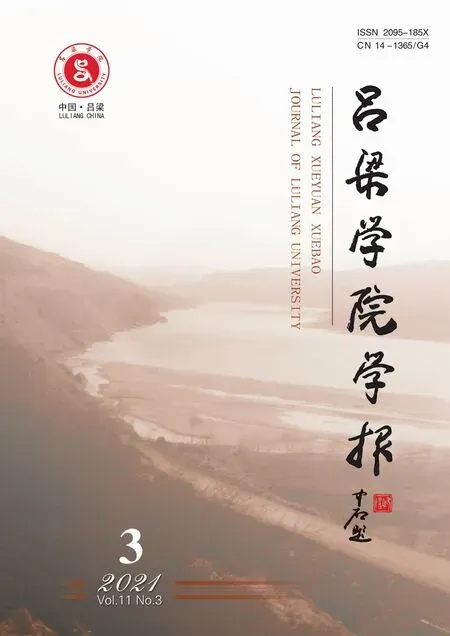论《红楼复梦》对《红楼梦》文本重建与主题再释
白 薇
(吕梁学院 中文系,山西 离石 033001)
乾隆年间,《红楼梦》问世,“嘉庆初年,《后梦》、《续梦》、《补梦》、《重梦》、《复梦》五种接踵而出。”[1]606《红楼复梦》篇幅最长,共计一百回,现存嘉庆十年(1805)的金谷园刊本、嫏嬛斋刻本、“本衙藏板”刊本等。卷首下题“红香阁小和山樵南阳氏编辑,款月楼武陵女史月文氏校订”[2]点校说明。从书前序言来看,《红楼复梦》至少于嘉庆四年(1799年)已完成,而程高本《红楼梦》告成于1792年,以此推测,作者起笔甚早。该书作者为生活于清代嘉庆时期的陈少海,“字南阳,号月香,又号红羽、品华仙史、小和山樵。钱塘人。”[3]170
《红楼复梦》接续程高本一百二十回后撰写,主要讲述贾宝玉转世为“祝梦玉”后重聚十二钗的故事:荣国府自贾政去世之后,门庭冷落,唯王夫人与李纨、宝钗、平儿相依为命。袭人重回贾家,改名为珍珠。王夫人托礼部尚书祝凤将荣府及大观园出售,携宝钗等归金陵。祝凤为镇江府丹徒县人,生于金陵望族,世代单传,祝凤弟兄三人,仅二房祝筠有一子,名梦玉。梦玉为宝玉后身,也是一位温柔多情、才思敏捷、终日在脂粉堆中厮混的翩翩佳公子。梦玉的祖母祝母希望祝家后嗣绵延,于是,祝凤兄弟三家各自为梦玉迎娶新媳。每家迎娶一正三副,完成了十二金钗之聚。王夫人将珍珠(即袭人)嫁给梦玉为妻,后又与凤妻柏氏结为姊妹,祝、贾两家亲似一家。宝钗与梦玉也十分融洽,姐弟相称。祝母将家事交给宝钗、探春掌管,两府家业日渐隆盛。岭南瑶人忽起叛乱,节度使领兵前往征讨。群芳偶游太虚幻境,幻虚仙命宝钗前往岭南平定瑶人之乱,赠乾坤再造丹一枚。宝钗胆智俱生,率领骁勇善战的众女子出征,很快凯旋回朝,封武烈夫人。此时梦玉已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在京购置府邸;贾兰袭封荣国公,贾环亦官兵备道台。宝钗买回荣府以及大观园,为梦玉及其妻妾于园中分定住处,大观园中欢声笑语一如往昔。小说以祝家为主线,以贾家为辅线,完成《红楼梦》的再创作。目前学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红楼梦》续书的整体研究上,赵建忠教授1997年出版的《<红楼梦>续书研究》是为代表作,张云教授2013年出版的《谁能炼石补苍天:清代<红楼梦>续书研究》提出要从“非经典作品”出发认识和评价《红楼梦》续书,论述颇为精当。本文即从“非经典作品”的建构角度出发,审视《红楼复梦》对《红楼梦》的文本重建与主题再释。具体而言,通过三种路径的尝试——对宝玉形象的重塑、对网状结构的重构、对“言情”主旨的重建,《红楼复梦》完成了将《红楼梦》重新纳入儒家政教体系的目的。
一、“有情无色”:对宝玉形象的重塑
《红楼复梦》对宝玉形象的重塑源于“情”“色”关系的再认识和再定位。《红楼梦》中,宝玉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鄙视各类束缚自己的封建枷锁,希望追求自己的理想和爱情。其形象是在“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4]4的底色下完成的。“情”和“色”因“空”而更具哲学意味。《红楼复梦》则抛却“空”与“色”,直接以“情”重塑宝玉,使梦玉作为宝玉的后身,呈现了“一个风流蕴藉的公子,并不贪淫嗜欲”[2]140的形象。
《红楼复梦》第十三回专意书写梦玉“多情”的一面,与宝玉之欣赏女子极为相似。宝玉认为“女子是水做的骨肉”,终日在闺阁厮混。梦玉也“最喜在姑娘、丫头们里面打交道”[2]139。但较之宝玉,梦玉不仅喜欢与姑娘、丫头们嬉闹,就连家人媳妇、老妈们,也表示尊重心疼。他将世上所有的女性都划归在以“情”观照的圈层中,把相貌丑陋的比作“香花良玉”,相貌标致的比作“玉蕊琼花”。他的世界满是“大千世界媸皮裹妍骨的女子”的情感遭际。他为古今往来天性“晶莹香洁”的女子鸣不平,挞伐以貌取人的女性观,这样唯“女子”的论断显然比宝玉要更进一层,甚而是惊世骇俗的。小说第二十六回以更长的篇幅论述了梦玉的大情之“情”,将“情”字延展发挥到极致。作者描绘梦玉是“天生成的情皮情骨、情血情肉、情心情肝、情肠情肺、情肚子情舌头,连周身的头发、寒毛都是有情的。”[2]287这是作者有意对梦玉形象的设定和提升,是对宝玉形象的重塑。在新的设定中,梦玉虽是“在情海里浸过了三千年”之人,但梦玉之“情”与“色”毫无关系。作者指出,梦玉绝不是那些贪图男欢女爱的“多情”之人,而是拥有大情之“情”:
他的多情,又是独开生面的一个样儿。他也没有别的情法,只就他自己情起。他要吃饭,想着人也是要吃饭;他要穿衣,想人家也要穿衣;他怕冷嫌热,想人家也怕冷嫌热;他欢喜大乐,想人家也欢喜大乐;他心中委屈,想人家也心中委屈。……以至那些姑娘、嫂子们见他如此一个中了情毒的道学,也就忘了他是位爷们,不拘是什么事,从不避他。那怕遇着擦身洗澡呢,大爷来就来,要去就去,听其自然[2]287。
很明显,作者所宣扬的是在“理”的范围内抽象的“情”,希图以一种精神层面的“情”和“理”,从根本上排斥人本性上的“色”和“欲”。实质上,梦玉和宝玉大有不同,二人之异不在“情”之深浅多寡,而在“情”之真实可信。宝玉多情,却有“色欲”存在。因有着生而为人的小缺陷,宝玉更像是从身边走出的真实存在之人。而梦玉认为一切女子都有可怜、可爱、可敬、可畏之处,确为“多情”,但这“多情”却完全建立在精神层面而缺失了人固有的真实感。作者一直念念不忘的是那些不能也无法逾越的伦理大道,对于女子的“情”更符合儒家提倡的“泛爱众”的思想。正如“凡例”所标榜的“以忠孝节义为本”[2]凡例3,《红楼复梦》以“有情无色”对宝玉形象予以重塑,希冀以梦玉来弥补《红楼梦》有碍观瞻的缺憾,反映了彼时读者期待“有益无碍”的接受语境。
二、“未尝遗漏”:对网状叙事的重构
《红楼复梦》“本于《红楼梦》而另立格局,与前书迥异。”[2]凡例3作者想要把《红楼梦》拉回到儒家伦理道德范围之内,并极意标榜自己的小说与《红楼梦》“迥异”,但是《红楼梦》是他永远无法摆脱的枷锁,那种欲离未离,又着意增加新内容的意图使小说逐渐走向一种“未尝遗漏”的杂沓结构。即如“凡例”部分,作者就多次将《红楼梦》与《红楼复梦》对比,说明自己重构小说的意图。
其一,穿插重构的叙事线索。《红楼复梦》在《红楼梦》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叙事线索,完成了网状结构的重构。作者于《凡例》中多次申明,此书以荣府为起点和终点,点出《红楼梦》本题,此为文中一线。此书又以大观园为起点和结点,首尾呼应,是为文中二线。作者还明确说明:“首先写珍珠作通篇之引线,以宝钗作串插之金针,以彩芝作结,章法井然,异于前书,”[2]凡例3-4是为三线。无论以荣府点题,还是从大观园入手,这些都是在《红楼梦》文本架构的基础上完成的宏观设计,但珍珠、宝钗、彩芝等则是叙事线索的新设定。这类叙事线索彼此穿插,共同构建了《红楼复梦》的网状结构,显出与《红楼梦》“欲离未离”的文本形态。
其二、纷繁细密的叙事策略。《红楼复梦》对《红楼梦》仅仅书写大观园的叙事是颇为不满的,因而提出了“细微周密未尝遗漏”的标准,以期达到“无事不书,无家不叙”的目的。为此,作者极力拓展小说细节,将纷繁杂沓的事件融为一炉,形成新的文本形态。即如“此书仿《聊斋》之意为花木作小传,非若小说家一味佳人才子,恶态可丑。”[2]凡例3-4作家将《聊斋志异》的经典情节融入小说创作。为解构原作,《红楼复梦》还有意添加新内容,如将岭南瑶人作乱作为重要内容切入小说中,突显宝钗等女将的用兵神勇。由此,小说描绘了多个世界,时而是钟鸣鼎食的贵族之家,时而是冰冷残酷的阴森地狱,时而是金戈铁马的战争世界,时空转换之间,尽显传奇之色。
“未尝遗漏”是《红楼复梦》希冀超越《红楼梦》之处,为此,作家穿插重构新的叙事线索,以纷繁细密的叙事策略处理细节,反而使小说主线不明,杂乱无章。因此,现代的文艺评论家林冠夫在《红楼梦纵横谈》中毫不客气地指出“如果说,《红楼梦》的续书大都是一些续貂的狗尾,那么,《红楼复梦》可以说是续貂的典型之作。”[5]39这种纷繁杂沓的网状结构并不是成功的尝试,但却反应了当时尽善尽美,包罗万象的读者期待。
三、“伦常节义”:对“言情”主旨的重建
作为《红楼梦》的续书,《红楼复梦》以“伦常节义”的主旨消解了原书“大旨言情”之意,将小说拉入儒家伦理道德的范围内。曹雪芹通过宝黛钗的爱情悲剧寄托自己对于封建伦理扼杀人性自由的愤恨,从而有“以情反理”的旨意,但作者陈少海并未领会和理解这一点。高鹗续本中备受称赞的悲剧结局被作家认为是最为不堪之处,他指斥“立意甚谬”,认为“收笔处更不成结局”[2]凡例3。他对不合礼教之处多有微辞,处处用“违碍忌讳”“淫亵不经”“恶俗不堪”等词直斥,同时标榜本书的优点“伦常具备”“忠孝节义”:
“伦常具备,而又广以惩劝报应之事以警其梦,亦由夫七十子之续之耳。”[2]自序1
“书中无违碍忌讳字句。”
“此书虽系小说,以忠孝节义为本,男女阅之,有益无碍。”
“此书无公子偷情、小姐私订,及传书寄柬,恶俗不堪之事。”[2]凡例3-4
由上可见,作者陈少海站在封建道统家的位置上,以当时的伦理道德逐次衡量《红楼梦》,提出诸多不合意之处,并希冀以己之力重构文本、重塑人物,最终达到重解小说主旨之意。正如陈少海在自序中所言“雪芹之梦,美人香土,燕去楼空。余感其梦之可人,又复而成其一梦,与雪芹所梦之人民城郭似是而非,此诚所谓‘复梦’也。”[2]自序1“似是而非”乃是“复梦”对原书有意的改造和超越。祝府这个上慈下孝,无不按照礼法处理得妥贴睦穆的封建大家庭,正是作者从“伦常节义”出发对《红楼梦》的“言情”主旨的消解和重建。
此外,作家还塑造一些偏离伦常的小人物,以此劝诫世人。最有代表性的是梦玉的奶妈——桑奶奶。桑奶奶因为梦玉奶妈这个特殊地位,在府中作威作福,最后偏离伦常,无可挽回。开始,桑奶奶只是对于低自己一等的人指指点点,野心渐渐膨胀,对老爷留宿何处都有干预之意。她还私通于干儿子桑进良,又撮合了桑进良和干女儿秀春成为夫妻,商量卷财外逃生活。但是干儿子桑进良骗走了她的积蓄,和秀春一起逃走了。桑奶奶真相败露,被赶出府中,落得曝尸乱葬岗的下场。桑奶奶作为祝府中的一个小人物,是社会中许多小人物的缩影。她地位低下,没有家人,得不到社会的尊重,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最终沦落于人欲横流之中,偏离了伦理道德的轨道。这样的人物有着活生生的社会真实感,以对其嬉笑怒骂的淋漓展现,作为社会价值观中消极面的代表,从反面突显了《红楼复梦》的“伦常节义”主旨。
“经典具有典范和引领作用,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文学高度,而非经典则具有彰显格局和烘托氛围的作用,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文学起点。”[6]79-80从“非经典性作品”的建构角度而言,《红楼复梦》以“有情无色”对宝玉形象予以重塑,以“未尝遗漏”对原书网状叙事加以重构,又以“伦常节义”对“言情”主旨进行重建,完成了对原作的文本重建与主题再释。这类续书被鲁迅先生称为“补其缺陷”“结以团圆”[7]171,呈现出《红楼梦》深层意旨与大众接受的悖离状态。但这些尝试却是《红楼梦》传播初期读者群审美期待的客观反映,可为学界研究《红楼梦》的阅读史和接受史提供更多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