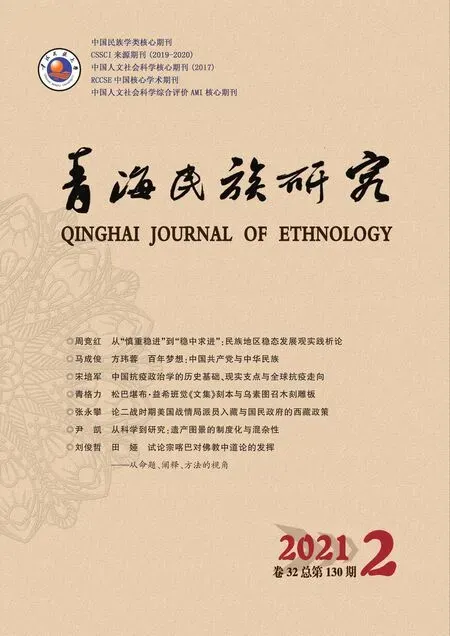文本、礼仪与场域:清王朝构建藏传佛教王朝化的路径与实践
崔欣 石娜 朱娜
(西北师范大学,甘肃 兰州 730070)
每个群体都信奉且传承着独有的“礼仪”(宗教仪式、文化仪式),此种“礼仪”是对生活在该群体内文化遵循者共同行为方式与道德准则的高度概括,保证了他们的思想信念与现实世界的联系。生活在这种“礼仪”中的人,彼此之间感觉与感知的恰如其分,情感与认知的契合,共同营造出一种标准且自然的社会氛围。作为“话语”的礼仪,预设了一个先于各个组成部分的整体,即宇宙观(或者也可称为话语基础)。
面对藏传佛教世界,清朝统治者构建王朝化的活动场域、规范礼仪文本阐述、参与文化仪式表演等方式既是寻求藏传佛教世界的文化认同,同时也是对建构王朝共同文化回忆的一种尝试,为信仰藏传佛教的各个族群提供文化认同框架,使其族群聚合成一个拥有“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的背后是带有其族群不同文化符号的社会复合存在)的文化共同体。“集体记忆”被接纳的同时,族群成员对群体自我身份的认同和文化归属认知在增强。清朝统治者借此实现王朝共同文化的建构,推动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加速民族融合,助推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形成各族共荣“中华”的局面,以及各族共有的“中华”认同。
一、仪式秩序建构与概念性的仪式阐述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正统之所寄,主要表现为一种“文化权力”及由其决定的王朝统治合法性。“正统”的本质是统治者对权力来源的阐释,是文化“建构”的结果。想要还原清王朝文化认同模式的构建方式,除分析清王朝统治者构建王朝化的藏传佛教“礼仪生活”场域和具体的活动空间外,还必须对王朝统治者以及政府官员如何定义和组织藏传佛教中最根本的“仪式”的范畴和诸多方面,以及参与这些最基本的、日常生活的行为加以分析。
清朝皇帝非常认真地对待人们常说的“天下”概念,他们精心将自己塑造成最适合的引导者。同时,他们也希望用最壮观或最广泛的礼仪表演方式把疆域的统一展现为可感知的现实,用这些仪式建立起某一文化系统内的宇宙循环,并证明他们能够在加强这一“现实”的同时呈现天地的统一,胜任现世统治。所以,清朝皇帝精心设计的供奉(神佛、雕像、法器等)不仅是对寺庙、佛堂、楼阁这些“有形”呈现的补充,帮助完成空间的构建,更是一种对“仪式”表演秩序的概念阐述。
(一)仪式秩序建构:清王朝主导的藏传佛教神佛体系建构
如果将藏传佛教的礼仪仪式视为行为性的表演,那么藏传佛教神佛体系构建和教义阐释就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概念性的仪式,二者在同一话语体系中互为表里。概念性仪式是表演者(清朝皇帝)自身概念化的行为客体,不再是独立于观察者存在的“物”。清朝统治者通过这些“概念化的客体”接近藏传佛教文化本身,同时将此仪式嵌入“文治”实践,构建普世主义的伦理标准。
随着大乘佛教的发展,佛教重新被纳入神灵崇拜的传统中,对偶像崇拜的需要便成为人们普遍的愿望。于是,造神运动一发而不可收拾,不仅数量剧增,而且各类神像千姿百态,日趋复杂。[1]因此,完备丰富的佛教神系的建立,一直以来都是藏传佛教信徒、学者所孜孜追求的。清朝以前,已有蒙藏学者开始尝试在印度传统佛教神系的基础上吸收、融合西藏本土的神佛形象,以及汉地尊神,开始建立带有本土特色的藏传佛教神佛系统。例如,明宣德六年所成《诸佛菩萨妙相番相经咒》①。但这些图像学方面的资料,应该只是在宗教信仰中重要神佛的罗列,而不是一种藏传佛教神系的完整架构展示。因此,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王朝藏传佛教文化政策需要,乾隆皇帝命三世章嘉活佛着手构建清宫藏传佛教神系,形成满、蒙、汉、藏四种文字的《诸佛菩萨圣像赞》②,为藏传佛教世界提供神系范本③:
粤稽三百六十尊佛像。乃我皇上得契金容,极晨昏之斋素;心周贝叶,溯宝相之庄严。爰命章嘉胡图克图捡藏经中诸佛宝号永宜供奉者,排集尊次,编列字号。……共三百六十尊,成二十三堂,朝夕崇祀,功德之大,直括龙藏全备之义。荷蒙眷注,亲承赏赐,祗拜之下,瞻净土为胎,宛聚沙成佛。举小见大,不盈尺而参丈六全身。斗室之中,俨觐灵山千亿。[2]
《清宫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档案材料也印证了清宫藏传佛教神系是由三世章嘉活佛在乾隆初年整理完成的记载:
乾隆十四年四月(杂活作)十一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交满洲字画佛像折子一件(上画佛像三百六十尊),传旨:着做铜模子。钦此。
于本年七月十三日员外郎白世秀、司库达子将做得悬胳膊佛模子共三百六十尊,共约估银六千五百余两;实板佛模子共三百六十尊,共约估银八千三百余两,缮写折片二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准照悬胳膊佛模子一样做。其印佛六□面像贞处照实板佛一样做,其座子照拨得腊样须泥座一样做,其于束腰上着刻乾隆年敬造,系何佛名□刻何佛名,其边线空处着添花纹,先拨样呈览。钦此。
于十六年十二月初三日七品首领萨木哈将做得佛模子,铜背板上凿得四样字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准做四样字④,底下添边线,内凿大清乾隆年制,字号准在背后刻;其阳佛模子背后亦刻字号,底下刻大清乾隆年制,俟得时,着章嘉呼图克图看次序,将佛排在□字号内。钦此。
于二十二年初十日将做得阴阳佛模子⑤七百二十尊呈进讫。[3]
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广木作)二十七日,员外郎白世秀将做得镀金阳佛模三百六十尊、阴佛模三百六十尊,随节活安在养心殿呈览,太监胡世杰传旨:将阳佛模三百六十尊交庄亲王,其阳佛模三百六十尊配做三层塔一座,每一层供一百二十尊,每一尊安一玻璃欢门,先做样呈览,钦此。[4]
乾隆二十二年正月(油木作)初六日,柏唐阿四德来说,军机处交赏达赖喇嘛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五对……印子佛⑥三百六十尊;赏班禅额尔德尼白石瓶一对、三色玻璃葫芦瓶一件……印子佛三百六十尊。[5]
乾隆十年四月(记事录)初七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于海,传新东上头层殿成造三世佛,两次间成造八大菩萨,后殿成造二十一度母。俱要增胎,着喇嘛画样,不必拨腊,及时成造。十七日三世佛,八大菩萨,二十一度母由海望与章嘉呼图克图商酌应如何供奉。[6]
从记载来看,三世章嘉最早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将整理所得藏传佛教诸神绘制成册“画佛像三百六十尊”交由乾隆皇帝审阅。经乾隆同意后,造办处方始铸造模具,并大规模用于宫廷中。甚至,乾隆皇帝还将已经系统化、成谱系的藏传佛教诸神像模板赏赐于达赖、班禅,这就使得整个藏传佛教圈中的神佛供奉都统一于一种范式。当然,在整个佛像模板的铸造过程中,作为“首席顾问”的三世章嘉还就清宫藏传佛教诸神佛的具体名称、位列部众、在佛龛中的摆放顺序,甚至如何供奉均给予大量指导。
由此,乾隆皇帝在三世章嘉的帮助下将“藏传佛教神佛系统”作为被感知和巩固历史延续性及纽带的媒介,并使其成为王朝化的藏传佛教统一践行的、标准化的范本。
(二)概念性的仪式阐述:清宫藏传佛教造像
藏传佛教的道场、祭坛、佛堂、楼阁与供奉(神佛、祭器、加持物等等)为信仰者提供宗教“礼仪活动”实践的情境化空间,这种情境化空间为信仰者提供了连接理想境界与世俗生活的文化背景,在信仰者群体内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向心力。这种情境化空间既是清朝统治者构建特定“礼仪生活”秩序的产物,也是帝王统治意识被感知的场所。供奉于藏传佛教寺庙、佛堂中的造像、法器既是“表演”的场景,也是帝王参与仪式“表演”的一种形式。
清政权建立初期,藏传佛教造像发展较为缓慢,随意性较强,且生产规模不大。即使有零星记载见于文献中,也多用于馈赠蒙古贵族。直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皇帝才命内务府设立中正殿念经处,中正殿的设立标志着清代宫廷造像活动开始规范化。⑦及至乾隆朝,乾隆皇帝一方面出于将藏传佛教密宗思想以及藏传佛教神佛体系完整、规范化地呈现;另一方面是为构建宫廷中的佛国世界,完成个人对藏传佛教仪式践行的考虑,宫廷藏传佛教造像蓬勃发展起来,清宫造办处⑧基本成为承揽宫中各式佛像、法器修造的专门机构。
藏传佛教图像带有明显的象征意义,例如,“佛足”对应的表征意义是“佛自身”,“白象”对应的是“佛降世入胎”,“莲花”对应的是“佛诞生”,“白马”对应的是“佛出家”,“菩提树”则对应“佛悟道”等等。[7]因此,乾隆皇帝为了更好地呈现这种“怪异神奇的密教与复杂多变的造型”[8]造像风格营造出神秘、肃穆的佛国世界,在位登宸极伊始,便命驻藏大臣入藏延请佛像:
(乾隆十三年五月十五日)臣索拜我来时,奉上谕:抵藏后,给达赖喇嘛、郡王珠密那木扎勒转降谕旨,着将大威德金刚、胜乐金刚、密集金刚此三佛,拣选造型高大、有大加持者带来之外,亦拣选西藏有之佛尊而京城没有之时轮金刚、金刚手、嘛哈噶喇、嘎巴拉佛、毕达扎马拉瓦齐尔巴尼佛、妙金刚佛带来。以请佛之礼,予大哈达一条、曼达一个、各色大绸九匹,即交付索拜带去,钦此,钦遵。[9]
西藏宗教上层感念于乾隆皇帝弘扬藏传佛教的决心,以及对京中尚未供奉的藏传佛教佛尊造像虔诚地渴求,欢欣感激,认为这是史无前例的绝妙好事。不仅按照乾隆谕旨仔细尽心寻找藏内完整、制造精良、毫无瑕疵的造像外,还准备八大菩萨、五方佛、佛像一套及布达拉宫及桑耶寺的建筑图样等九幅,以及璃玛苏巴尔甘、铃、素珠等[10],交由索拜一并请回,送往京中。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乾隆皇帝再次派驻藏大臣福鼐在藏地各藏传佛教寺庙中寻找佛像:
乾隆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准理藩院咨开: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十一日奉上谕,著福鼐、傅景饬交第穆呼图克图,倘有符合本处绘制咨送骑狮观音菩萨形制之琍玛佛,即交付本年前来之达赖喇嘛之使共青至北京,若无现成,照所绘形制挑选巧匠,妥为制成琍玛佛尊,仍交付本年前来之达赖喇嘛之使恭请 而至。[11]
西藏第穆呼图克图在接到福鼐转降谕旨后,诚惶诚恐,感念乾隆皇帝阐扬佛教之功德之余,开始在藏地遍寻现成骑狮观音菩萨形制之琍玛佛。因其尚不知晓西藏各寺庙中有无现成佛像,故上奏“倘有现成琍玛佛,则堪布等前往时,进献圣上;若无现成琍玛佛,则照画样尽速仔细成造,断不耽误。”
不仅如此,乾隆皇帝还多次命造办处画样人前往西藏去学画佛像,以为宫中造像之用。
乾隆十三年四月(记事录)初五日,内大臣傅恒传旨:着造办处画样人往西藏里去画样子。钦此。[12]
可即便宫中造办处已能熟练、精准地用画笔呈现佛像、佛龛等样式,但具体的成造环节在乾隆初期依旧需要藏族工匠完成。在《清宫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留有大量乾隆初期,造办处将所需造像纸样、木样送往西藏成造的记录。
乾隆二十六年十月(记事录)二十四日,郎中白世秀、员外郎寅着来说,太监胡世杰交金镶松石欢门一件,传旨:着照样画下来。钦此。
于本月二十七日员外郎白世秀、郎中寅着将金镶松石欢门一件照样画得纸样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准照样发往藏里成造。钦此。
画得交福景代往藏里去讫。[13]
在多次赴藏求教过程中,宫中造办处匠人在等待佛像修造完成的间隙,也不断地学习和掌握西藏工匠的造像技术,并最终将造像成品与学得技术一同带回北京:
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记事录)初三日,库掌五德、四德,笔帖式福庆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着交福传藏里大人们,将粘松石紧药顺便带些来。钦此。
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回明公爷交军机处寄信去讫。与三十九年三月二十日奉额驸福交藏里送到粘镶嵌用粘药四块,每块重十二两,随制方并用方折片一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着交四执事一块,其余三块交造办处粘镶嵌用。钦此。[14]
这种宫中造办处匠人向藏地工匠求教所得的粘贴镶嵌珠宝于铜像之上的配方与用量也在档案中有所记载,从当时的记录看,无论在配方还是工艺流程上,造办处工匠基本是原封不动地参照藏地配方和工艺,只是按照清宫的要求在细微处有所变化:
计开芸香(四斤),清油(一斤半),冰糖(四两)、银砂(五两),共合一处熬成膏,收贮备。用时,量其所用,将药盛入小铜钟内镕化,俟化开,点于嵌松石处,再用微火将点上之药烤热,即将松石安上。[15]
(三)仪式文本的艺术化呈现:清宫唐卡绘画
众所周知,清朝皇帝们早已得到西藏方面认同,获得“文殊师利大皇帝”称号。乾隆时,为进一步强化世间的“皇帝”与宗教中的“文殊”形象结合,使之实体化、艺术化呈现,乾隆皇帝大量尝试御容唐卡这一表现方式。
唐卡是藏传佛教艺术所独有的表现形式,也是藏传佛教中最为常见的宗教宣传品、法物,不仅为佛教的宣传和修行服务,而且因其具有极强的佛教象征意义,所以多用于藏传佛教佛法宣传并服务于修行的信众。同时,唐卡也是一种特殊的绘画艺术,其以神秘的色彩、流畅的线条以及多变的尊神特征,成为藏传佛教艺术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宫廷唐卡绘画艺术在乾隆朝得到了长足发展,进入高峰期。从清宫造办处乾隆三十六年(1711年)的档案记载来看,造办处一次就呈交唐卡100多幅,以满足承德佛楼中的供奉之需: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皮裁作)初四日,库掌四德、五德来说,太监胡世杰交热河布达拉庙六品佛楼楼上宗喀巴源流三张,楼上六品佛楼六张、楼下护法十八张,红洋锦五匹;文殊源流十七轴一堂、释迦源流十五轴、四大天王二张,共十七轴一堂,大红云龙片金一匹;释迦佛一轴、罗汉十八轴、天王四轴、无量寿佛九张、文殊、观音、普贤、地藏菩萨四张,共三十六轴一堂(系都刚殿),大红西番莲片金二匹;七臂达赖喇嘛七张(后楼)、大力金刚一张、大轮手持金刚一张(紫福有地方)、释迦牟尼佛源流十一轴(宗巴喀楼下正面挂三轴);白伞盖佛母一轴、积光佛母一轴。[16]
宫廷唐卡绘画和制作的机构与宫廷造像一致,均在中正殿和造办处完成。如前所述,中正殿本为紫禁城中一处重要的佛堂,宫中很多重要法事都在此举行,每年元旦,来京朝觐的藏传佛教高僧和驻京呼图克图都会在此为皇室祈福。同时,中正殿还是皇家寺庙的管理中心,既负责皇家佛事活动,约束喇嘛以及经费管理外,还负责成造佛想、绘制唐卡。
由于唐卡绘画带有明显的宗教功能,因此,在其绘制过程中,藏传佛教僧侣多参与其中。据罗文华先生考证:在中正殿后照殿淡远楼就专门辟有专供喇嘛绘制唐卡的三间房屋,称为中正殿画佛处。[17]这些专门从事宫廷唐卡绘制的藏传佛教高僧在清宫档案中多被称为:“画佛像喇嘛”“画佛喇嘛”“画匠喇嘛”,他们是唐卡绘制的完成者。例如:
乾隆四十三年三月(灯裁作)二十日,员外郎四德、五德来说,太监厄勒里交御容佛像一张(系中正殿画佛像喇嘛伊什画),传旨:着养心殿东暖阁大案上箱内挂像佛一样镶边成做。钦此。[18]
另一位著名的画佛像喇嘛是扎克巴尔多济,他历任画佛副达喇嘛和画佛达喇嘛。其作品主要有班禅额尔德尼像一张、释迦牟尼佛一张、吉祥天母像一张、宫室勇保护法一张等。[19]
当然,各驻京呼图克图也曾参与宫廷唐卡的绘制活动,例如三世章嘉活佛。如前文所述,三世章嘉曾为潜心修行佛法的乾隆皇帝绘制藏传佛教神佛像,完善藏传佛教诸神谱系,成为宫中绘画、造像的图像范本。由于唐卡绘制需要勾勒细致的图案线条,然后施以丰富的色彩,每一道工序都需要大量的精力投入,是一个费时费力的活动。因此,可以想象,三世章嘉并未亲身投入此项活动当中,只是凭借其超凡的艺术鉴赏力,以及对绘制藏传佛教神佛图像丰富的经验,对宫廷唐卡绘画艺术提供建议和帮助。
在唐卡绘制中,除了藏传佛教僧侣外,宫廷画像师也发挥了不可忽略的作用。他们虽然并未单独完成过一幅唐卡绘制,但是因为他们卓越的画像技术,造办处曾委派他们参与唐卡画像底稿的修改,以及协助画佛像喇嘛完成唐卡绘制的工作,其中尤以丁观鹏、姚文瀚在档案中出现次数较多。
丁观鹏,擅长画道释像、人物像,因画风细致工整,颇受乾隆皇帝赏识。他曾领旨仿画建福宫吉云楼锁仓一套罗汉像。[20]不仅如此,丁观鹏还参与热河珠源寺众香楼六品佛楼中一幅唐卡的绘制:
乾隆三十一年八月(如意馆)初四日,接得员外郎安泰、李文照押贴一件,内开:七月二十一日接到报上来带来珠源寺众香楼撤下画佛像一轴,传旨:著果报带进京去,交与养心殿内综观王成,转交丁观鹏找画齐全,再托一层,俟回銮之日,京内伺候呈览,钦此。[21]
姚文瀚[22]较丁观鹏晚入宫中成为宫廷画师,入道不久便以擅长画道释像、人物像而得到乾隆皇帝赏识,开始参与宫中唐卡绘画,也曾与入宫供职的西洋画师艾启蒙[23]共同完成唐卡绘制:
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如意馆)二十日,接得郎中李文照押贴内开:九月二十五日太监胡文杰传旨布达拉庙内勒尔经图着姚文瀚起稿,呈览,钦此。[24]
乾隆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多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时期。在唐卡绘制过程中,不仅有藏传佛教僧侣以及汉族画师参与,供职宫中的西洋画师也贡献了自己的绵薄之力,丰富了唐卡绘画的表现手法和技艺。例如,前文所提的艾启蒙就是其中代表:
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如意馆)二十日,接得郎中李文照押贴内开:九月二十一日太监胡文杰传旨:福隆安等着艾启蒙画脸像八幅钦此。[25]
鉴于个人的福寿绵长以及江山永固、帝祚绵延的期盼,乾隆皇帝如同历朝皇帝一样推崇传统的祈福文化。因此,能够满足其祈求财、福、吉祥等诉求的莲花部众诸神佛,无量寿佛、白伞盖佛母、救度佛母形象亦多出现在唐卡绘画中。
在藏传佛教中,弟子需要导师指引方可修行佛法,佛学导师的地位就显得尤其重要。所以,作为藏传佛教独有的艺术表现形式,祖师像,例如宗喀巴、达赖、班禅、章嘉、哲布尊丹巴等藏传佛教中的上师便成为乾隆朝宫廷唐卡绘制的另一重要主题。
这些供奉于热河以及宫中的藏传佛教祖师唐卡做工精美,笔法精细,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同时,它们又是对藏传佛教上师形象的再现,所以供奉于佛堂之上,还能够满足瞻仰者的怀念、追思之情。
(四)藏地传统法事活动的王朝再现:跳布扎
“跳布扎”(俗称“金刚驱魔舞”)是藏地佛教仪轨中一种较为流行的驱魔散祟、祈福迎祥的法事活动。在藏传佛教信徒的观念中,“若能观看跳布扎,则一年畅顺。”[26]清初,“跳布扎”只流行于京中各寺。据《燕京岁时记》记载,“直至雍和宫改寺后,才形成每年正月在雍和宫中表演的定制。[27]此法事活动在内地的传播,得益于乾隆皇帝对藏传佛教的推崇。雍和宫改寺之初,乾隆皇帝曾命内臣就佛教仪轨、法事等活动求教于三世章嘉活佛:
遵旨咨询章嘉呼图克图佛教仪轨之事,告称:西藏之礼,每年正月初四日始,念发愿经文,十四日朵玛咒赞礼,十五日弥勒绕转,藏人称朵玛咒为朵玛。此会乃西藏最大道场,于此请所学精湛之喇嘛等考试讲解,获大愿法会格西称号。[28]
由于“跳布扎”源于藏地,精通跳布扎的喇嘛也多出在藏地,为保证法事活动的原汁原味,乾隆皇帝曾多次命驻藏大臣在藏地寻找精通跳布扎的藏地高僧,延请其前来京中传授、培训:
现特降旨将我们土伯特地方之跳布扎乌木札特等喇嘛取用,带至京城,小僧我不胜感激。此等喇嘛,我尽量从噶乐丹、布莱布克、色拉、纳木扎尔扎仓之喇嘛内挑选年青壮年者派遣。再,跳布扎者扎什伦布为本源,从我处行文,一定挑选好的跳布扎者,从速归来。[29]
从记载来看,“跳布扎”的起源地是扎什伦布寺,而精通跳布扎的藏地高僧亦多出于此地。此外,哲蚌寺、宁塘寺等西藏寺庙中也有精于此的年轻僧侣。他们是藏传佛教文化的传播者,通过他们的传授,藏地古朴、神秘的“跳布扎”才得以在京中呈现。⑨雍和宫“跳布扎”活动的仪式流程、参与人员角色设定、服饰要求等细节也在此时形成定制:
以长教喇嘛披黄锦衣乘车持钵,诸侍从各执仪仗法器拥护;又以小番僧名班第者,衣彩胄,戴黑白头盔,手执彩棒,随意挥洒白沙;前以鼓吹导引,众番僧执曲锤柄鼓,鸣锣吹角,演念经文,绕寺周匝,迎祥驱祟。念五日,德胜门外黄寺行亦如之。[30]
二、场域:仪式生活的情境化空间建构
加巴拉耶夫认为“人把实在的、非神灵的事物现象转化为神灵的、幻想的实体。”[31]当藏传佛教信徒寰居于那些自然与人工形成的特殊场域之中,在进行神圣物及神灵的创造,寻求精神的慰藉和情感的表达,同时建立起彼此的情感共通。这种情境化空间既是文本产生和保存的场所,是帝王意识被感知的场所,更是国家对特定的“礼仪生活”秩序构建的产物。
基于这样的认识,清朝统治者很早便开始构建“王朝的藏传佛教寺庙体系”,籍此情境化的空间布局实现域内藏传佛教信徒对王朝的认同。皇太极征服察哈尔部,墨尔根喇嘛“见皇上威德遐敷,臣服诸国,旌旗西指,察哈尔汗不战自遁,知天运已归我国,于是载佛像来归。”[32]将嘛哈噶喇铜像移至盛京。清王朝接受藏传佛教护法神之首的嘛哈噶喇为护法战神,筹建实胜寺加以祭祀。
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修书与朝鲜国王,希望能够得到以示隆重的供祀建议⑩。崇德三年(1638年),皇太极“以古孟绰尔济喇嘛、嘎布楚喇嘛、冰图喇嘛及各色工匠、画匠等以绿瓦修庙。”[33]崇德三年(1638年)实胜寺落成后不久,皇太极便率内外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文武众官等参拜实胜寺。[34]崇德四年(1639年),皇太极又率和硕亲王以下宗室王公,前往实胜寺,率领文武百官以新年礼对嘛哈噶喇佛像行九跪九叩头礼。[35]这表明新年礼佛已经与堂子祭祀地位等同,纳入满清国家祭祀礼仪体系当中。此后,皇太极又根据藏传佛教僧侣建言,在盛京四城门之外,各建寺庙一座,即东门外五里建护国永光寺,建塔主尊大日如来;南门外建护国广慈寺,建塔主尊观世音菩萨;西门外建延寿寺,建塔主尊无量寿佛;北门外建法轮寺,建塔主尊时轮金刚佛。[36]并以此广布“四塔成,当一统”的舆论。皇太极此举不仅向蒙古人昭示清王朝的“天命”所归,同时也体现出清朝皇帝对蒙古诸部民众文化传统的尊崇,维系清王朝与蒙古诸部的民族情感,拉近其与藏传佛教世界的距离。
但是,清政权建立之初,强大的宗教影响力辐射西藏、天山南北以及大漠内外的广大蒙藏地区,不利于清王朝统御西藏与蒙古政治意图地实现。为增强王朝强大的向心力,加速国家一统进程和确保清王朝帝祚永昌,在继承和发扬前朝治藏经验的基础上,康、雍、乾三朝君主稳步推动各地藏传佛教寺庙的新建、复建、改建工程,最终形成一个以皇宫、北京、承德、五台山为核心的清王朝藏传佛教文化中心。在这样的空间布局里,王朝化的藏传佛教中心的“核心位置”得以凸显。同时,清王朝还在内外蒙古、青海、甘肃、新疆等地皇家兴修寺庙的一种“内聚外散”的王朝寺庙格局,输出影响,使其均成为清王朝宗教、政治场域的代表,其目的就是跨越长城,兼顾草原与农耕地带,加速融纳广大藏传佛教文化圈于清王朝国家版图的进程。如果把这些场域和具体的空间建筑理解为“表演”场景的一部分,那么它们就是“仪式”文本产生、保存和“仪式表演”的场所。
(一)雍和宫:轮奂长新的王朝学经圣地
乾隆九年(1744年),乾隆皇帝以“北京地域宽广,更应按照西昭之例创立学院,教习喇嘛,以弘扬黄教”[37]为目的,授命三世章嘉活佛,改建雍和宫为北京城中供佛及喇嘛会集之场所。拆除原官邸中汉式建筑风格的影壁、牌楼等,借鉴和吸收藏式建筑风格,重建雍和门殿、雍和宫大殿、永佑殿、法轮殿、讲经殿等殿堂,以及新建万佛阁等主体建筑。
雍和宫改建为寺不只是上述寺庙建筑的翻修和重建,乾隆皇帝还对雍和宫各殿堂中彩画装饰也极为用心:
(乾隆九年十月初八日)奴才三和奏,为请领库金事。先经奴才因雍和宫殿宇彩画并装严佛像成做背光等项,需用飞金甚多。若盖支领库金捶造,未免过费。于乾隆九年四月十二日具折奏请,将殿宇彩画应用飞金,仍于行市拣择办买应用外,其佛像装金等项应需飞金约用赤金二百六十两,请向广储司支领。……今法华殿应安鈶钑铜塔五座,并布扎衣璎 珞 什 件。[38]
雍和宫改建为寺后,在整个乾隆一朝还历经了数次的维修和殿宇新修,如《总管内务府大臣三和奏为添建雍和宫宫殿宇约估银两数目事折》记载了新修殿宇所需银两:
(乾隆十三年六月二十日)奴才遵旨雍和宫建造重复檐楼殿一座、东西次楼二座,飞桥游廊二座、拆挪绥成楼一座、后楼而是一件、太岁坛一座,及成砌墙垣铺墁甬路地面海墁散水油饰彩画,以及京山万福阁拆工运价等项所需工料用银两按例约估,通共约需银六万九千八百十二两零。[39]
由于雍和宫的重要地位,内务府各级官吏在应对其殿宇、佛楼的维修中也是尽心尽责,不敢怠慢。[40]雍和宫的改建工程贯穿乾隆朝,班禅楼、戒台楼、法轮殿等部分主体建筑是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才修缮完成的,六世班禅进京时便于此休息与讲经。[41]随着雍和宫改建工程的推进,大量佛像成造及佛像装藏⑪等活动也随之开展:
(乾隆十四年十月初四、初五日)新建万佛阁供奉佛像开光诵经所需什物:大白哈达一条、小白哈达六百四十二条、花哈达九条、棉八两三钱、粗布一丈、羊腰脂十二斤、藏香三百支、灯草花五百支、酥油八十斤、彩绸三百匹……
诵无量寿佛、甘珠尔等经大白哈达三条、小白哈达十九条、花哈达四条、长三丈粗一分五种珠儿线制作绳一根、磨金银黄铜珍珠珊瑚粉三分、苹果杏子石榴干面一两、羊腰脂六斤、红藏香九支、灯草花五百支、酥油十三斤八两……[42]
雍和宫改建为寺、经学院的设立以及金瓶掣签制度的确立,是乾隆皇帝在延续尊崇藏传佛教国策的基础上,有计划、分步骤地构建藏传佛教“王朝化”的尝试。在宗教方面,雍和宫的建立以及京中各处藏传佛教寺庙的修缮完成,构建起了乾隆皇帝追求的“王朝的寺庙体系”。它们为来京、驻京的藏传佛教信徒提供了寻求精神慰藉和宗教诉求的场所,使北京成为与拉萨分庭抗礼的另一藏传佛教中心。正如白佩君所讲:“佛教为信仰者的宗教实践提供了‘神圣空间’的文化背景,这种神圣的空间场域为信仰者的生活拥有了一种特殊的向心力,从而使他们寰居于自然与人工形成的具有信仰寄托的特殊场域之中,并进行神圣物及神灵的创造。”[43]在政治方面,乾隆皇帝此举树立了自己在藏传佛教中的宗教主体性与王朝话语权,籍此实现清王朝统御西藏与蒙古的政治意图。
(二)五台山:文殊的道场,蒙藏的连接点
五台山初为道家和地方信仰崇奉之地。唐大历四年(769年),唐代宗钦定文殊菩萨为天下寺宇殿堂的上座,普贤菩萨、观音菩萨为其侍者,五台山才被改造为佛教圣地。[44]后世的汉译佛教经典中也逐渐将文献记载中的“清凉山”坐实为五台山,坐实五台山为文殊道场。再者,五台山“耸歭于雁门云中之表,接恒岳而俯滹沱,横临朔塞,藩屏京畿。”[45]是“诸藩部倾心信仰”的“中华卫藏”的中原第一佛教名山,[46]其宗教影响力能够有效辐射整个藏传佛教文化圈。
入关不久,享有“文殊师利大皇帝”称号的清朝诸帝已经意识到并开始遵从历代帝王在五台山的礼佛传统,为强化蒙、藏、汉佛教徒以及地方的满、汉官员对其作为五台山藏传佛教的施主和文殊菩萨的化身的认同,清王朝统治者不断地重建藏传佛教寺庙、御制诗文、朝拜和举办法会,将王朝意识渗透林立群山中的各处寺庙,完成清王朝藏传佛教“礼仪生活”秩序空间建构,让世人了解清王朝对五台山佛教发展的推动,以及藏传佛教在此处的核心作用。
顺治时,崇国寺僧人阿王老藏被委派驻锡菩萨顶,“赴觐阙廷,钦承天问,即协皇情,而译事钩稽……宠贵兹多”,[47]开始统领五台山佛教。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康熙皇帝下旨重建镇海寺主体建筑,将其从禅宗道场变为藏传佛教寺院。镇海寺天王殿内正脊坊下的题记中有着这样的记载:“大清皇帝四十九年岁次庚寅孟夏吉日,敕封清修禅师乃提督五台山番汉大喇嘛鼎增坚错奉旨重修,住持朋错垂旦谨志。”[48]经过对天王殿、大雄宝殿等殿堂、僧舍的重建与修葺后,康熙皇帝在位期间,还对五台山上10余座藏传佛教寺院进行修葺,立《菩萨顶大文殊院碑文》《重修清凉山罗睺寺碑文》《广宗寺碑文》等碑文13通[49]。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继续在五台山大行修建佛寺之风,并六次朝拜五台山⑫,赐镇海寺为三世章嘉活佛的道场,命其在此驻锡、修行、讲经。“每年四月到八月,章嘉国师来这里闭关坐静,相沿成习,按时入座,不分昼夜地修习甚深秘密金刚瑜伽。”[50]同时,乾隆皇帝还将善财洞、广化寺、普乐寺、文殊寺、金刚窟等五所寺院(统称为“佛爷五处”)归其管理,使其成为五台山藏传佛教领袖,地位仅次于达赖、班禅。自此,“蒙古王公常遣其属来熬茶,布施不绝”[51]。甚至远在青海的藏传佛教高僧也前来朝礼、持戒,例如,塔尔寺第69代赤钦·嘉雅堪钦·格桑崔臣敦比尼玛前往五台山,朝供了菩萨顶、白塔寺、显通寺、殊像寺等寺庙,并在观音洞讲说“观音念修法”和“禁食斋戒仪轨”。[52]
有清一代,蒙藏各地藏传佛教信徒前往五台山礼佛的同时,以被认定为是对身为文殊菩萨化身的清朝皇帝的朝礼之旅,其行为核心和动力是基于共同文化心理的清王朝的认同。同时,也深深影响着天下诸族纷纷前来五台山朝圣,这不仅重新完成了清王朝的天下构建,也重塑了蒙藏各族的文化心理。
(三)承德外八庙:朝觐和礼佛的中心
与避暑山庄合为一体的“外八庙”是围绕避暑山庄修建的十二座皇家寺庙的统称。乾隆帝曾就兴修“外八庙”的政治考量有过这样的论述:“转无量法轮,聚无量法众。诵无量法宝,作无量法事……一切化群生,庄严从此出。西土及震旦,究竟无同异。”[53]不难看出,“外八庙”的修建与蒙古有着密切关系。康熙皇帝于五十二年(1713年),因与蒙古各部会盟于多伦,为从蒙古各部所请,兴建溥仁寺、溥善寺。二寺的兴建既是清朝“蒙古情感”的表现,同时也被赋予其特殊的政治意义:
朕思治天下之道,非奉一己之福,合天下之福为福;非私一己之安,遍天下之安为安。柔远能迩,自古难之。我朝祖功宗德,远服要荒,深仁厚泽,沦及骨髓。蒙古部落,三皇不治,五帝不服,今已中外无别矣。……念热河之地,为中外之交,朕驻跸清暑,岁以为常,因诸番来觐,瞻礼矣便。因指山庄之东,无关于耕种之荒地,特许营度为佛寺。[54]
如碑文所述,多伦会盟后,内外蒙古各部归顺清王朝,表明蒙古与清朝的关系不再是“中外有别”,归为一统。而且,热河也已划为“畿甸”,成为清朝疆域的一部分。
乾隆二十年(1755年),乾隆又于康熙所建溥仁寺、溥善寺基础上“依西藏三摩庙之式”建造了普宁寺,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建安远庙,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为供厄鲁特蒙古到承德朝觐礼佛而建普乐寺,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为庆祝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建普陀宗乘之庙。⑬正如乾隆皇帝在《普陀宗乘之庙碑记》中所述,普陀宗乘之庙虽是仿照西藏的布达拉宫所建,但同为观世音菩萨显现圣地,因此各地带有“普陀”字眼的寺庙彼此相同,只是分处各地而已。因此,以普陀宗乘之庙为代表的避暑山庄周边各藏式寺庙,都是以“如如来之本意,岂外是乎”为依据,即:如果知道了佛祖的本意,就不会对仿建有“分别心”,对西藏各寺庙进行仿建。“外八庙”的兴建与其明显仿照风格,正是清帝努力将藏传佛教的中心逐渐由西藏向北京和承德切换的尝试和智慧体现。“佛教同源”的理论拉近了承德和西藏以及新疆(西北蒙古)的距离,在同源的宗教感召下,蒙古各部的注意力从西藏转移到了承德,避暑山庄遂成为蒙古各部首领朝觐和礼佛的中心。
三、结 语
在托布勒看来,距离是影响“核心”与“边缘”的重要因素。[55]如果用这样的观点来解释清王朝与蒙、藏的关系,在相对远离王朝政治中心的边缘地区,王朝的控制力会被削弱,当地的社会将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会出现另类化倾向。因此,清王朝统治者非常注重“位置”的力量,他们不断尝试在统治疆域内确立王朝的政治、文化核心位置,使其成为相对应空间中的重心,从而使文化的边缘自然而然的面向文化核心形成向心力,在空间感觉上强化了文化核心的中心性与权威。当清王朝主导下的这种集聚式流动在一个空间中占据主导地位时,王朝统治就会表现为向心性集中的结构,王朝中心的控制力和凝聚力也就随之增强。
注释:
①一部与大宝法王得银协巴有关的经咒集,其中第一卷收录了60尊佛、菩萨插图。包括,二十一度母、三十五佛、无量寿佛等尊神,并有梵、藏、蒙、汉四体文字的赞。是目前已知的汉地刊行的第一部具有图像学意义的著作。
②现有《诸佛菩萨圣像赞》版本为国家图书馆提供,全书共收录了360尊藏传佛教尊神,分为上师、本尊、佛、菩萨、明妃、罗汉、护法等。每部尊神附汉文像赞360节,一像一赞,每赞为六言四句,涉及尊神名号、所持法器、身体姿势、法力等内容。
③罗文华在《诸佛菩萨圣像赞》导言中所述,三世章嘉活佛的贡献在于为清宫藏传佛教造像提供了一整套丰富的图像学范例、便于宫廷造佛之用。见国家图书馆提供版本:《诸佛菩萨圣像赞》,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④四样字为满、蒙、汉、藏四样字。
⑤造办处的佛模分铜镀金阳模与阴模两种,阳佛模子即尊神形象突出,能作为供奉之用,阴模则是尊神形象凹进去,用来模印泥擦擦佛像。每套各360尊。
⑥泥擦擦佛像。
⑦根据罗文华在其《龙袍与袈裟》一书中观点,他认为清代的宫中造像的开始较早,但并非经常性,直至中正殿念经处的设立,才标志着清代宫廷造像活动开始规范化。
⑧清宫造办处,因建于养心殿,又名养心殿造办处。康熙三十年(1691年)移至慈宁宫以南。造办处由皇帝特派的内务府大臣管理,各类专业作坊先后有60余个,包括玻璃厂、匣裱作、珐琅作、油木作、金玉作、如意馆等等。造办处与皇室起居息息相关,其职能除御用品制造、修缮、收藏外,还参与装修陈设、舆图绘制、兵工制造、贡品收发、罚没处置以及洋人管理等事宜,包罗之广,远远超出工艺制作的范畴,在宫中是具有实力的特殊机构。
⑨赵令志、鲍洪飞、刘军主编,赵令志、郭美兰、顾松洁、朱志美、关康译:《雍和宫满文档案译编》,北京出版社,2016年,第451页《领侍卫内大臣傅恒奏请赏赐教练跳布扎喇嘛折》内容记载:“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查得,前次正式念经做道场时,参与之呼图克图、喇嘛等皆与赏。此次不过是训练,按理尚不至赏赐,虽圣主特施恩,赏赐伊等学得快者,亦唯应议赏跳布扎之小喇嘛等。臣等看伊等审查送来之册,皆得议赏,似为不妥。既然惟应赏跳布扎之小喇嘛,则赏跳布扎一百三喇嘛每人银各二两。此内领跳者一人,跳鹿一人,加倍各赏四两,教习五人每人各赏五两。赏银从广储司支领。”
⑩“金国汗书致朝鲜国王书。我旧居兴京城有寺宇倾圮者,今将重加修理。又蒙古元世祖库必赖汗时,巴克斯巴喇嘛以千金铸佛一尊,沙尔巴胡图克图喇嘛自唐古特国携之归于大元太祖成吉思汗后裔察哈尔林丹汗。今察哈尔亡,举国来附,携此佛来时,复有诸宝妆成佛像,亦皆携至。今伊国败亡,全属皆附,此佛已至敝邦。今虔造寺宇,苦乏彩画颜料,此系敬佛,非予自奉,亦不在互市之例者。想尊释崇佛之道,贵国所稔知也,所有应用颜料,希一一发给,幸勿稽误。”见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80页。
⑪又称“装藏”或“装脏”,在藏传佛教中,佛像必须依传承的仪轨如法制作及装藏开光才能供在佛堂,由具德金刚上师依传承依轨开光,迎请智慧佛与三昧耶佛无二融入佛像,这时才具足了诸佛本尊的加持,一尊如法装藏的佛像其加持是不可思议的,可作为世代相传的珍宝。
⑫具体情况见于(清)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卷11《高宗本纪二》第390页、406页,卷12《高宗本纪三》第455页,卷14《高宗本纪五》第519页。
⑬“是则山庄之普陀,与西藏之普陀一如。然一推溯夫建庙所由来,而如不如又均可毋论。即如如来之本意,岂外是乎。”见张羽新:《清政府与喇嘛教·普陀宗乘之庙碑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