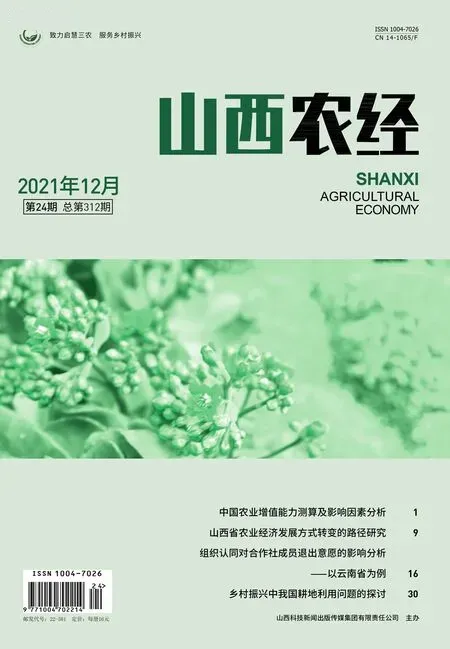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中新乡贤主体类型和功能实践实证研究
——以云南省P 市M县L村和Y村为个案
□段妍智
(玉溪师范学院 云南 玉溪 653100)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实现需要各类人才的参与,然而目前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出现了“空心化”、人才流失等现象。
新乡贤是推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重要人才之一。探讨该地区新乡贤群体的类型、特质及其功能实践,具有特殊意义。结合在云南省P 市M县L 村和Y 村的调研实践,对该地区新乡贤的类型及其在乡村振兴中价值和作用进行实证研究,以助推当地乡村振兴实践。
1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中新乡贤的内涵及主体类型
一般而言,在新时代背景下,有资产、有知识、有道德、有情怀,能影响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并愿意为之作出贡献的贤能人士[1],都可称作新乡贤。具体而言,新乡贤应具备4 个基本要素。
一是场域要素。在乡性即生活在农村,是新乡贤重要的身份要素。其中,驻村干部和大学生村官属于新乡贤主体范围,而短期居住于农村的外聘专业顾问等不属于新乡贤。
二是品德要素。新乡贤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弘扬者和践行者,能够以自身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助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根乡村[2],同时愿意为乡村振兴作出贡献。
三是才能要素。新乡贤大多事业有成,或有资本,或善管理,或懂市场,或有一技之能,或有丰富的知识。新乡贤既包括扎根于乡土社会文化德行高尚、对乡村公共事务有所贡献的本土乡贤,也包括反哺家乡且具有奉献精神的离土乡贤[3]。
四是声望要素。新乡贤不仅要得到村民的认可,同时要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新时代下,新乡贤是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引领者,不是“新乡霸”或资本代理人。
根据新乡贤是否在场、是否具有较高的身份地位,可以将其分为以下几个类型:在场精英新乡贤,如返乡的富人、企业家、退休公职干部等;不在场精英新乡贤,如在外富人及企业家、当官居城人士、专家、教授、学者、文化名人及媒体人等;在场平民新乡贤,如身边好人、道德楷模、老党员及积极分子、退休教师、退休村组干部、家庭领袖等;不在场平民新乡贤,如外出务工优秀的青壮年等[4]。
新乡贤具有地域性、先进性、内生性和非正式的特点[5],主要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依靠自身道德、文化、技能、资源等综合能力而获得村民的信任与地方政府的认可。面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的现实而言,新乡贤来源主体应为居住在乡村的“贤能型”人才或复合型精英。因此,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新乡贤主体应界定为生活在农村的贤达之士,既包括非体制内的生长并生活于农村的乡村能人、道德模范、返场投资富人、企业家等,也包括体制内的驻村干部、大学生村官等。
2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中新乡贤主体类型的功能实践分析
结合实际,对于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中的新乡贤,以“是否与乡村有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是否是精英”作为划分标准,将新乡贤在场主体划分为“内生型”精英新乡贤、“内生型”平民新乡贤、“嵌入型”精英新乡贤、“嵌入型”新乡贤平民4 种类型,如图1所示,并对新乡贤主体类型的角色认定和效能进行深入分析。
不同类型新乡贤的角色认定、参与路径、功能实践是不同的,助力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方式和效能也是不同的。因此在探讨新乡贤助力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时,不仅要认清不同新乡贤的作用和价值,还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剖析该地区新乡贤群体的类型,类别化、针对性地探索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的作用和参与路径。
2.1 “内生型”新乡贤的功能实践
这一类新乡贤是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关系网络中内生的新乡贤,主要包括乡村致富能人、“土著”村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老党员、“返场”(即返乡并在场)能人(如退休公职干部、退休教师、退休村干部)等。这类新乡贤主体与乡村有着深厚的情感联结,有着浓厚的乡亲观念、故土观念、乡愁情结,多是自发助力乡村振兴。其中,乡村致富能人、“返场”退休公职干部、道德模范属于内嵌型精英新乡贤;身边好人、“返场”退休教师、“返场”退休村干部、老党员、“土著”村干部属于内生型平民新乡贤。
具体来看,在乡的乡村种养殖大户、合作社负责人等新乡贤,可以通过技术培训、经验分享、项目承包等,助力乡村经济发展、产业振兴。在乡的在职村干部、退休公职干部、退休教师、退休村干部和民族文化传承人等新乡贤,具有较强的号召力,是推动乡村组织振兴的重要力量。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民族文化传承人、老党员等德贤,可以涵养文明家风、淳朴民风、和谐乡风、传承传统技艺、传承创新民族传统文化,助力乡村文化振兴。“返场”退休公职干部、“返场”退休教师、“返场”退休村干部等新乡贤,有着浓厚的乡愁情结和故土观念,可以充分发挥自身具备的政治、知识、品德的作用,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
乡村致富能人、“土著”村干部、民族文化传承人、道德模范、身边好人、老党员等,他们的生产生活主要在乡村内部开展,乡村的发展直接关系他们的生产、生活。因此,他们有较强的动机参与乡村振兴,对实现乡村振兴有着强烈的愿望。“返场”退休公职干部、“返场”退休教师、“返场”退休村干部有浓厚的乡愁情结,愿意为乡村发展出谋划策,但由于年龄和身体原因,精力有限。
2.2 “嵌入型”新乡贤的功能实践
这一类新乡贤与乡村、村民没有血缘、亲缘和地缘的情感联系,大多是行政介入或者其他因素“下乡”的嵌入型人才,主要包括市场-盈利导向的投资者、驻村干部、大学生村官等。
市场-盈利导向的投资者属于“嵌入型”精英新乡贤,他们以资本下乡的趋利性嵌入到乡村振兴中,通过项目投资等推动乡村产业振兴。这一类新乡贤只有当乡村具有足够经济条件和吸引力的情况下才会涌现,常出现在经济资源优越、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无论是经济资源还是文化资源都比较匮乏,“嵌入型”精英新乡贤比较稀缺。
驻村干部、大学生村官属于“嵌入型”平民新乡贤,他们多源于工作需要或政治诉求,以行政介入方式嵌入到乡村振兴中[6],通过理论知识、组织协调沟通能力等,与“土著”村干部一起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出策出力。他们个人虽然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资源,但可以全身心投入乡村治理和生态文明中。更关键的作用在于他们可以通过动员群众的方式,切实解决乡村振兴中产生的实际困难。
3 实证考察云南省P 市M 县L 村和Y 村新乡贤的主体类型及功能实践
2021 年1 月深入云南省P 市M 县L 村和Y 村进行实地调研和访谈,为探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中新乡贤的类型界定和功能实践提供一手资料。
L 村位于县城东南部,在县城与镇政府驻地之间,距县城17 km,距镇政府驻地12 km,全村国土面积28.83 km2,为哈尼族和汉族杂居。该村新乡贤主体类型和效能情况见表1。

表1 L村新乡贤主体类型和效能情况
Y 村地处县城北部,距离镇政府所在地40 km,全村国土面积23.59 km2,有15 个村民小组,常住人口为1 426 人。该村新乡贤主体类型和效能情况见表2。

表2 Y村新乡贤主体类型和效能情况
L 村和Y 村两个村虽然都有规模养殖的种植养殖大户,但规模不大,并不能形成产业规模、带动乡村产业发展,更不能带动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种植养殖大户在助力L 村和Y 村乡村振兴过程中主要是分享种植养殖经验和技术,因而属于内生型平民新乡贤。L 村引进1 家蔬菜订单农业公司,种植辣椒(野山椒)科技示范地1.33 hm2,带动群众发展辣椒(野山椒)产业10.67 hm2,但种植规模不大、产业基础设施薄弱、产业发展层次偏低。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目前L 村和Y 村的新乡贤主体类型主要是平民型新乡贤,主要效能是分享种植、养殖经验和技术,参与乡村治理,弘扬传统美德,培育文明乡风,树立良好家风。可见,云南省P 市M 县L村和Y 村新乡贤主体类型比较单一、功能实践有限。
4 结论和建议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也存在区域差异性。经济、交通和民族传统文化资源较为丰富的乡村能够吸引各种类型的新乡贤,因此新乡贤主体类型多样化。例如特色小镇旅游景区、普洱茶产区等,既可以吸引嵌入型精英新乡贤,如投资企业家、富人等,也有内生型精英新乡贤,如乡村致富产业户、民族文化传承工作室等。这些地区引导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应围绕“新乡贤怎么用”展开。需要构建各类型新乡贤合力机制,共同推动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组织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全面发展,同时要注意对新乡贤进行制约和监督,依法助力乡村振兴。
经济、交通和民族文化资源匮乏地区的乡村,缺乏吸引新乡贤的资源和物质基础,新乡贤主体类型比较单一。这些地区对人才和人力资源的需求更加迫切,可以吸纳一些“内生型”平民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通过对乡贤文化的挖掘、宣传,将新乡贤组织化,为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提供制度、场所等条件,激活“内生型”平民新乡贤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