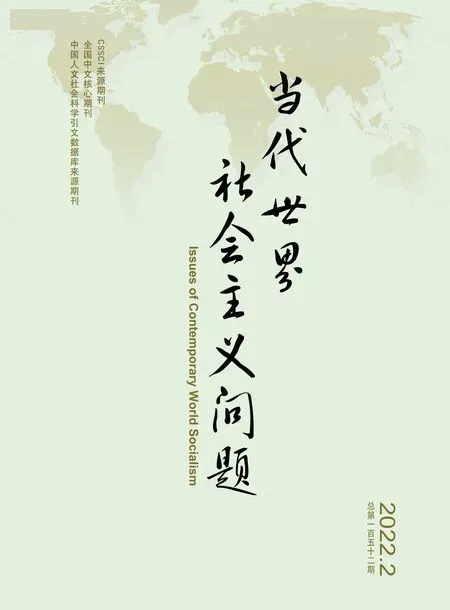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异化及其诊治
——基于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观点
韩涛泽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电信政策的助力下,美国计算机网络开始步入自由化发展阶段,由原来的军事领域和政府公共机构扩展到大众化的商业领域,并且在资本逻辑的支配和勾结之下规模迅速壮大,不断挤占传统电信行业的地盘。同时,随着美国大型跨国公司的扩张,计算机网络以强大的技术优势和经济效力被快速移植到世界各地。按照美国批判传播学者丹·希勒的看法,人们自此进入到一个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工具和动力的“数字资本主义”①“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 m),也称“信息资本主义”,主要指资本主义的数字化、信息化发展阶段,伴随着资本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发展,数字资本主义也从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其他国家渗透和扩张,借助新技术将全球纳入到数字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时代。今天,互联网成为人们生活中难以摆脱的一部分,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购物、出行、娱乐,人们都难以离开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等各式各样的电子产品以及脸书、推特、谷歌、优兔视频、优步等各式各样的网络应用。
近年来,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多集中在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文化传媒学批判等方向,从技术哲学角度对数字资本主义展开的批判性研究仍显单薄。这既不利于我们全面审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技术异化现象,也不利于合理引导互联网信息技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同为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先驱和发起人①[美]唐·伊德:《技术哲学导论》,骆月明、欧阳光明译,上海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1-102页。,一个代表了“社会-政治批判传统”,一个代表了“哲学-现象学批判传统”②吴国盛编:《技术哲学经典读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11页。,从两者开创性和互补性的技术哲学观点出发分析技术异化问题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数字资本主义问题的研究。
一、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异化现象
如果说资本主义要想存活就必须不断地进行技术变革,那么在此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技术是资本主义的核心③[加]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页。。然而,作为数字资本主义核心要素的互联网信息技术在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诸多效用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劳动剥削数字化、生活方式技术化、社会运转加速化、文化思想工具化等异化问题。
(一)劳动剥削的“数字化”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平台充当了资本运作的新场域。所谓数字平台,按照尼克·斯尔尼塞克的说法就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使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群体能够进行互动”④[加]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0页。,包括广告平台、云平台、工业平台、产品平台、精益平台等多种类型,常见的有谷歌、亚马逊、优步、声田(Spotif y)、跑腿兔(Taskrabbit)等。这些平台不仅扩宽了资本盘剥的场域,也为数字化的劳动剥削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入驻平台的用户和劳工被系统以一种精准的现代管理手段——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数字泰勒制”最大程度地算计和控制着。以西方备受诟病的亚马逊劳工系统平台为例,亚马逊不仅拥有标杆性的劳务众包平台,可以将来自美国、印度等100多个国家分散的数字劳工组织起来作为数字资本主义剥削的对象,它还针对传统员工建立了严格高效的“数字控制系统”,将仓储一线的劳工准军事化地监管和控制起来。“包装站的显示器显示着需要处理的订单以及如何处理这些订单;手持式扫描仪确定了工人穿过仓库的路线;众包平台上的应用程序可以引导工人进入特定工作的下一个步骤。”⑤[德]菲利普·斯塔布、[德]奥利弗·纳赫特韦:《数字资本主义对市场和劳动的控制》,鲁云林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3期。这种平台系统一方面借助智能算法将工作过程标准化、程式化,不断地将工作流程优化,从而节约经济成本和时间;另一方面,利用大数据技术广泛收集货物和劳工信息,全程对劳工进行精准监管和控制,管理层也可借此进行绩效考核评估,不断地将劳工的剩余价值压榨到极限。德国纪录片《可怜!亚马逊的合同工》揭露德国亚马逊对于外包工人残酷的剥削状况,并有评论斥责其为“现代奴隶制”⑥参见[英]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周延云译,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4页。!不仅如此,像谷歌、优兔网等数字平台对于用户的每一次搜索和操作都会记录,在大数据和算法分析的助力下,平台会根据用户的搜索和操作数据给予相应的反馈和导引,实施精准的广告投放。原本看似毫无价值的个人上网记录在大数据时代成了一种被资本垄断的“无偿劳动”,普通人沦为被大数据技术规训和盘剥的“数据人”。
(二)生活方式的“技术化”
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的普及,人们逐渐被带入到一种“技术化生存”当中。这种技术化生存不仅体现在经济和商业领域,而且全面渗透到了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异化效应。其一,现代信息技术对人们的日常生活表现出某种“强制性”,人们不得不接受这种互联网信息技术所规定的生活方式,从而丧失多元化的、本真的生活方式的可能。不管人们是否愿意,都得使用某些电子产品和应用软件,否则无法适应大众化的工作和生活要求。其二,互联网信息技术对人的感情表达和生活习惯进行规定和塑造,致使人陷入生命意义的虚无。脸书和推特成为“晒生活”的平台,各种电子通讯的普及也使得人的情感表达日益廉价和单一。网上聊天常用的表情包也在重塑人们的表达习惯,人们依赖通过表情包进行交流时,无形之中弱化了运用常规语言文字表达的能力。随着生活方式的技术化、扁平化和泛娱乐化,人的存在意义也被遮蔽,随之而来的则是虚无主义。其三,各种网络应用可能会对人身心带来损害。例如,一些网络游戏构建了绚丽多彩的“赛博空间”,在现代心理技术的主导下结合人的心理特点进行设计,使青少年沉浸其中不能自拔,从而吸引人的注意力、使人上瘾。尼古拉斯·卡尔曾分析过网络信息技术对人身心造成的种种损害,认为对互联网的依赖导致人身体的某些器官退化,例如出租车司机对导航系统的依赖导致人脑海马体的退化;智能信息工具的使用“增强同时也麻痹了我们自然能力中最本质、最人性化的部分——用于推理、领悟、记忆和情感的能力”①[美]尼古拉斯·卡尔:《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刘纯毅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229页。。
(三)社会运转的“加速化”
互联网信息技术在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加快了资本主义社会运转的速度和节奏,使人们明显感受到一种“瞬时性的到来”②[瑞典]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加]文森特·莫斯可主编:《马克思归来(上)》,“传播驿站”工作坊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44页。。在经济领域,人们信奉富兰克林的名言“时间就是金钱”,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无疑满足了经济活动对于“速度”的要求:它不仅极大缩短了企业内部以及企业与客户之间的信息交互时间,而且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提高了自动化、智能化和资源配置的水平,使得整个资本运转的周期大大缩短。不仅如此,这种经济领域的“加速逻辑”也扩张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方面,网络信息技术的出现打破了劳动者对于传统工作场所的依赖,使得人们在家中甚至旅途中也可以工作,这无形当中模糊了“日常生活”和“工厂劳动”的区别;另一方面,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出现使得资本家盘剥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数字劳动”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在被经济活动所侵蚀,进而也就意味着被资本的“加速逻辑”所支配。可以说,包括经济生活和日常生活的整个社会生活都进入一种“加速逻辑”当中。尽管这种“加速逻辑”在短时间内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资料,但也造成对自然的过度耗费和破坏,陷入一种海德格尔所说的无休止地生产、消费的“进步强制”③[德]海德格尔:《讨论班》,王志宏、石磊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467-470页。当中。随着社会运转的“加速化”,人沦为整个技术加速体系中的一个无法停息的、不自由的“环节”:不仅各种精神焦虑、过劳死等现代疾病随之而来,极大损害着人们的身心健康;而且人们的大量闲暇时间被占用,导致人们整个内在精神生活日益枯萎和贫乏。人们来不及沉思生命的意义就被带入到一种千篇一律的快车道当中,过着一种海德格尔所说的常人般的“沉沦”生活。
(四)文化思想的“工具化”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无论是文化教育,还是思想意识,似乎都受到一种现代技术的控制,沦为一种“工具”。文化教育和思想意识的科学化、技术化、商业化等实质上都体现了一种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集置”①集置(Ge-stell)是海德格尔技术思想的核心概念,又译“座架”,本文统一使用“集置”译名。以及马尔库塞所说的科学技术的“合理性”统治。在文化教育领域,现代信息技术充当了现代教育发展和传播的手段,各种数字设备、办公软件、网络课程和电子资源一方面提高了教育科研的效率,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支配”和“统治”问题。人们几乎习惯用一种科学的“合理性”方法来管理和规定一切,不仅用来统治自然,也用来统治人,以至于“这种合法性同化了所有文化层次”②[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26页。。例如,科研机构往往要根据学者的论文数量、项目数量、影响因子等“量化原则”进行职称评定,包括人文社会学科也越来越倾向采用“数据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追求一种自然科学的“技术性要求”。除了文化教育领域,大众思想也依然存在着被牵制的问题。法兰克福学派新一代学者安德鲁·芬伯格认为,马克思技术批判理论更为首要的应是一种“设计批判”,而非工具主义的“技术中性论”。按照这种观点,现代网络传媒的设计无疑体现了资本主义的阶级意识和目的,发挥着某种非中立的意识形态导向功能。事实上,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正是通过控制大众传媒渲染一种“有利于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制度的价值观”③[英]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周延云译,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07页。,宣扬人性自私和占有欲的合理性,从而鼓励消费,由此,思想文化沦为一种“意识工业”或“文化工业”。还有些学者指出,在数字文化中也存在着“技术的牧领权力”,人们的“思想意识”通过大数据、智能算法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被苹果、谷歌、脸书等互联网巨头公司所监督和操纵,并应用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④[瑞典]卡特琳娜·基瑞特丽·虞格仁、[瑞典]卡特琳娜·L.基隆德:《技术的牧领权力:反思数字文化中的异化》,载[瑞典]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加]文森特·莫斯可主编:《马克思归来(下)》,“传播驿站”工作坊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03-923页。。如此一来,文化思想沦为一种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合法性辩护的“意识工具”,从而丧失自身的反思和批判能力。
二、“资本主义”与“形而上学”: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异化诊断
关于技术异化的思考,马克思和海德格尔是两个绕不过去的人物。马克思主要倾向于追问技术异化的“社会-政治”根源,海德格尔主要倾向于追问技术异化的“哲学-思想”根源,由此构成了分析当代数字资本主义技术异化问题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对照性维度。
(一)资本主义:以马克思的观点分析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异化
当今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尽管和马克思所处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时代有很大差异,但本质上仍未脱离一种资本主义所统治的时代,正如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所言:“现今社会就其生产力要素的状态来说是一个信息社会;然而,与此相反的是,就其生产关系而言,当今社会依然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⑤[英]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周延云译,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01页。而马克思对于技术异化问题的思考实际上正从属于他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批判。
技术异化在马克思那里主要是指机器大工业生产当中的异化,包括生产技术的异化和分工技术的异化。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当中系统分析过工人在“机器工厂”中的异化情况:随着机器在工厂中的引进,一些成年男工面临失业的风险,他们的妻儿作为廉价劳动力被严重剥削;机器的高速运转,使得工人的身心更加紧张和焦虑;机器大生产的精细分工,使得工人沦为整个机器体系的一个僵死的、不自由的环节,从而丧失了全面发展的可能;等等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6-368页。。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深刻揭示出这种技术异化背后资本剥削的真相:资本家使用机器之后不仅没有减轻工人每天的辛劳,反而还变相缩减工人劳动时间的“有酬部分”——工资,延长工人劳动时间的“无酬部分”——剩余劳动时间,使得工人的单位劳动具有较高价值,从而增加对工人的剥削程度。显然,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剥削并非由技术自身造成,而是由技术的占有方式——资本主义造成的。在马克思那个年代,机器为资本家所占有,他们使用机器生产绝非为了减轻工人的劳动,而是为了更好地进行资本的扩张和增殖。所以马克思才认为砸毁机器的“鲁德运动”是无效的,因为它并没有触及技术背后的资本主义本身。
马克思甚至还预言过“信息社会”的到来,强调信息生产力的出现是固定资本发展的必然结果,认为“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页。。这里的“一般社会知识”和“一般智力”其实就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信息生产力的构成要素。福克斯也明确指出:“对马克思而言,信息生产力的兴起与资本通过技术途径获取更多利润积累的需要有着内在的联系。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已实现了信息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③[英]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周延云译,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02页。因此,马克思将技术异化问题归结为其背后的资本主义,这一论断在当今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仍具解释力。
首先,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方向为资本家所操控,以资本增殖为目的,而非为了减轻工人劳动和造福大多数人。互联网最初作为一种军事防御技术服务于冷战时期的美国军方,后来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助力下,才逐渐超越了军事、政府等公共领域,走向了市场化和商业化④[美]丹·希勒:《数字资本主义》,杨立平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页。。在该过程中,计算机网络成为现代资本主义进行全球性资本扩张和增殖的有效工具,资本逻辑也成为互联网信息技术进化和发展的核心逻辑。一方面,互联网信息技术无论在其所辅助的物质生产领域,还是在其新敞开的非物质生产领域,往往都被设计成为资本盘剥雇佣劳动甚至“免费劳动”的工具,剥开这种技术的外衣,资本盘剥劳动的实质并未改变;另一方面,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核心技术为美国资本主义所垄断⑤希勒就曾指出这种不平衡的现象:到1997年初,开放的互联网仍然是一种美国系统,英语成为网络系统的通用语言,赋予顶级域名以及网址的系统仍被美国人所把持。参见[美]丹·希勒:《数字资本主义》,杨立平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在全球化时代,技术后发国家沦为技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资本扩张和增殖的广阔疆域,这种技术的资本主义垄断和占有,不仅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也造成了“数字鸿沟”的问题。
其次,在日常生活领域,造成人们生活方式异化的电子产品和网络应用也多为资本家率领技术人员开发设计,从本质上看不外乎是一种“资本化技术”对人们日常生活的侵蚀,将原本不属于资本剥削的领域也开发成为资本盘剥的场域,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全面技术化。日常社交娱乐的众多互联网平台,几乎都被营利性的资本家所掌控,“下班的非工作时间中,最大的一块是卖给了广告商的受众时间”①[英]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周延云译,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18页。,人们则沦为达拉斯·斯迈思所说的“受众商品”(Audience commodity),被一种资本化的社交媒体所统治。即便是那些非商业化的技术功能也依然在重塑着人们的操作习惯和行为方式,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资本化技术”所控制的一个新的地盘。这种“资本化技术”对日常生活的侵蚀与马克思所批判的机器应用使得工人妻儿被纳入到资本剥削体系中来的情况是非常相似的,只不过由资本家所支配的技术异化不再拘泥于“生产领域”,而是扩展到“流通领域”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说,正是这种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使得互联网信息技术被设计成为使人上瘾的、广告式的、监控式的“营利工具”,而非让人全面发展的“助益性的东西”。
其三,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社会运转的加速化,表面上由信息技术的革新和普及所引发,实质上其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动力——资本在增殖过程中所要求的“加速逻辑”。“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9页。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为了实现积累和增殖就必须不断运转,运转的周期越快,其增殖的速度也就越快。资本运转周期的缩短,不外乎减少生产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或者减少资本流通所需要的时间。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互联网信息技术不仅对于生产和物流的优化、缩短信息交换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被用于挖掘网民有商业价值的个人数据和刺激个人消费,成为加速资本流通和循环、释放资本潜能的有效工具。互联网信息技术一旦以资本的“加速逻辑”为自身逻辑,势必会导致个人的日常生活和整个社会运转的加速。如此一来,自然便沦为一种可供加速攫取和破坏的资源,人则被卷入一种由资本加速逻辑所支配的“技术体系”当中,成为一个高速运转的不自由的环节。
最后,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思想文化的“工具化”,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对于信息传媒技术的占有和控制。互联网首先是作为信息交互的工具存在,所以西方批判数字资本主义的学者大多集中在传播学领域。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讯公司、广播电视、新闻媒体和出版机构均为资本家所操控,这为其宣传资本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鼓吹资本自由运作和无限扩张的合法性、重构社会大众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欲望提供了可能。在资本家的操控下,由互联网信息传媒所编织的“赛博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须臾不可离的一部分,随处可见的各种商业广告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使人们不由自主地沦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注意力经济”和“消费文化”中一枚“无思”的棋子。“一句话,今日资本主义得以存在是依赖其文化工业的胜利,这包含了全部消费品工业,在这里,一直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③[加]达拉斯·斯迈思:《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王洪喆译,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
(二)形而上学:以海德格尔的观点分析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异化
如果说马克思对于技术异化的思考从属于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那么海德格尔对于技术异化的追问则从属于他对西方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反思。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当今世界是一个技术“集置”所统治的世界,我们处在一个“技术的时代”。就构成数字资本主义核心要素的“信息技术”而言,它以一种可计算的二进制“数学语言”为基础,借此对一切事物进行筹划和谋算,本质上这正是一种“集置”,正如卢卡斯·因特罗那所言:“在现时代,信息变成了信息技术——它成为‘集置’的一种模式。”①L.DIntrona,The Question Concer ning Infor mation Technology:Thinking with Heidegger on the Essence of Infor mation Technology,IGI Global,2002,p.232.由此也能看出,当今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仍未脱离海德格尔所说的由“集置”所统治的“技术的时代”。
“集置”作为“促逼的解蔽”②[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2-37页。,是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之本质的命名,可以理解为人对自然以及人对人的“种种非本真的、干预性的、强硬的技术要求”的统称,诸如“攫取”“订造”“测算”“耗用”“加工”等技术支配方式也都归属其中,代表了现代技术世界/社会蛮横的“控制论”:自然和人通通都被纳入一种技术体系的宰制之中,沦为一种可耗用和替代的、有用性的“资源”,从而丧失事物自身的本真存在意义。这种强硬的支配方式绝不限于科技领域,而是统治着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冈特·绍伊博尔德所强调:“如果单单局限于机器技术和自然统治的领域,而不去注意技术的普遍的本质(这普遍的本质在据流行观念看来并非技术的领域中,如在政治、宗教、艺术和科学中,也盘据着,并决定着人对这些领域的存在的理解),那么,将决不能充分地思考‘技术’。”③[德]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宋祖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页。因此,无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技术形式如何变革和更新,只要该时代没有摆脱“集置”所展现的“强硬的支配方式”和“蛮横的控制论”,那么海德格尔的技术思想就依然适用。事实上,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到处都展现着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集置”:流水线员工在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数字泰勒制的支配之下,每一个动作都被严格监管和安排,沦为技术体系中被算计和压榨的对象;资本家和政客利用大数据、智能算法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人们的偏好进行分析,即时提供个性化的精准反馈,诱导人们进行消费或作出某种倾向的政治选择;自然更是在现代信息技术的中介过程中被数字化、抽象化,沦为一种“仅仅对人而言有用性的东西”——一种被全面攫取和消耗的“能源库”;等等。这些都表明,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集置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依然适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正在把一切东西都作为一种对象进行宰制,把整个世界通通都纳入到数字化的控制体系中来,使得“当代资本主义成为完全可计算的”④[法]贝尔纳·斯蒂格勒:《论数字资本主义与人类纪》,张义修译,载《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如果说技术“集置”表征着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诸种技术异化现象,那么这种技术“集置”的根源又是什么呢?马克思将技术异化作为一个社会政治问题,海德格尔则将其作为一个哲学思想问题。通过追问技术的哲学本质,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之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一的”⑤[德]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71页。,是一种“完成了的形而上学”⑥[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80页。,或者说,现代技术集置具有和现代形而上学相同的展现方式和思维结构,是现代形而上学在诸现实领域的表现形态。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技术“集置”的哲学思想根源在于一种“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是海德格尔对传统西方哲学的一种独特判定和理解,认为柏拉图以降的整个西方哲学本质上是一部执着于“存在者”而遗忘“存在”的形而上学史。这部形而上学史在柏拉图那里发端,在笛卡尔那里开启了其现代形态,在尼采那里得以完成和终结。柏拉图之所以被海德格尔称为形而上学的发端者,是因为从柏拉图开始,“存在”便落入“存在者”当中,把“存在者之存在”理解为“在场”和“根据”,开启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在场形而上学”,同时奠定了西方人对于“真理”把握的科学主义立场和技术化思维方式。笛卡尔则确立了形而上学的“主体性”,将原本作为世界根据的“基体”转变为“主体”,使得“人”从其他一切存在者当中凸显出来,成为一切存在者的“中心”和“尺度”,“存在之真理”也开始由“主体”方面得到规定。现代技术“集置”尤其体现了这种主体性形而上学,它高扬人的至上性和能动性,把一切存在者作为一种被主体所统治的客体,按照“人的尺度”进行规定和筹划。尼采更是把这种“主体性形而上学”发展到极致,宣称上帝死了,由基督教所建基的旧道德已经失效,必须按照一种主体的“权力意志”来设定真理和重估一切价值。权力意志宣称自己是“唯一正确的东西”,以一种绝对真理的“强制性”统治着技术时代的一切,自然和人沦为一种被耗用、被算计、被筹划的原材料,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宰制存在和让存在工具化的“技术控制体系”。可以说,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技术“集置”的哲学根源就在于这种形而上学,特别是现代形而上学的主体性思维、计算性思维和论证性思维,这些形而上学思维使得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控制论”——“信息技术集置”得以孕育和可能。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运作机制进一步说明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技术“集置”的形而上学基础。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数据处理的最基本单元是一种“二进制码”,无论是图像文字,还是音频视频,都可以转换成为一种计算机可以加工处理的二进制编码,这种数字编码就是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通用格式”。信息的采集过程就是将各种信息进行数字编码的过程,信息技术的运作就是基于这种数字编码进行运算和处理。从本质上看,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作为一个“信息技术时代”,正在将一切东西“数字化”——把具有“质”的差异的东西转换为一种仅具有“量”的差异的“数字编码”进行标记和采集,由此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将世界“数字化”的时代,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通过数字编码表示的,这种数字化程度之深,以至于深到了马克思所说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程度①[美]戴维·J.贡克尔、[英]保罗·A.泰勒:《海德格尔论媒介》,吴江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16页。。“数字化”是一种“同质化”的把握世界的方式,“所有物体都是相同的。没有任何运动是优越的。任何位置对于任何物体都是相同的;每一个时间点对于每个物体都是相同的时间点”②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69页。。数字化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把具有本质丰富性、能够聚集天地人神之四重整体的“物”(Ding)③在海德格尔看来,“物”不是一个冰冷、封闭、孤立静止的“客体”和“对象”,而是关联着天地人神的“敞开性的东西”。“物”有其自身存在的意义,它并不围绕着人转,把物视为一种“资源”“工具”都是对“物之物性”的遮蔽。在海德格尔后期思想中,“物”的存在意义甚至和“人”同样重要,二者都归属于天地人神之四重整体,也归属于存在之真理。单质化、抽象化和扁平化。这种数字化在海德格尔看来本质上就是一种“数学筹划”,这种数学筹划建基于笛卡尔所开显出来的“主体性形而上学”,是主体对于客体的一种“心灵设想”和“主观设定”,并没有完全尊重事物自身的存在意义④参见[德]海德格尔:《现代科学、形而上学和数学》,载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47-884页。。同时,这种数字化的信息技术语言,作为一种单义的“技术化语言”,是对于通达存在的“本真语言”的“最尖锐与最威胁的攻击”⑤[德]海德格尔:《流传的语言与技术的语言》,载孙周兴编译:《存在的天命: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文选》,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195页。。因而,它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语言,其“可计算性”正反映了一种形而上学的“计算性思维”。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仍可以得出结论: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对一切东西进行“数学筹划”的信息技术集置,其哲学思想根源乃在于一种“形而上学”。
三、“共产主义”与“存在之思”: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异化出路
“危险所在,救渡者也生长。”①《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27页。不过,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对于技术异化问题的审视角度不同,使得二者对于技术异化的拯救思路也大不相同。
(一)共产主义:马克思克服当代数字资本主义技术异化的思路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技术异化本质上源于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因此要想克服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技术异化,就要从根本上消除这种资本主义所有制,把信息技术所有权从资本家手里解放出来,交给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服务于集体和公共社会,从而构建一种“信息技术共享”的“共产主义”。马克思认为技术“在共产主义社会的使用”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使用”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并没有真正发挥出它对于人类解放的价值和作用,相反成为资本家剥削和奴役人民的有效工具;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技术才能释放它的真正价值和作用,从而成为造福人民的力量。
首先,在共产主义社会,信息技术不再是资本家剥削和奴役人的工具,而是劳动者解放自身的力量。在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中,信息技术沦为一种压榨劳动者和盘剥人们剩余劳动甚至免费劳动的顺手工具。但在共产主义所有制中,这种局面将不复存在,信息技术工具和产品将为无产阶级控制和所有,信息技术的巨大生产力将被有效地用于缩减人们的必要劳动时间、最大限度地使人们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闲暇时间,更加自由发展。
其次,在共产主义社会,分工技术的异化也将消除。马克思曾预言:“自动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但是,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自动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30页。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当中,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使得生产进入一种自动化和智能化阶段,对于人力的依赖程度降低,精细的分工将留给技术自身完成,工人可以有更多机会从事不同类型的工作,更加全面发展。
最后,在共产主义社会,信息技术摆脱了资本的逻辑,发展更加合理,将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信息技术由于屈从于资本增殖的逻辑和私人控制,所以才被设计成如此这般侵蚀人们日常生活、加速社会运转、疯狂攫取自然资源的应用产品。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信息技术摆脱了资本逻辑的桎梏和奴役,将向着非营利的共产主义方向发展,造福人类自由解放和助力自然环境的美好,而不再盲目追求一种“进步强制”,从而真正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当然,对于共产主义,我们不能仅仅把它理解为一种遥远、静态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状态”,还应该将其视为一种批判、改造现实的“实践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言:“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9页。今天,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异化进行一种共产主义的批判和改造无疑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中国作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坚持者、倡导者和引领者,无疑最有能力肩负起这种使命。所以,斯迈思在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大众传媒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用于一种自私、享乐、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路线”,以至于遮蔽了技术实践的其他路线的时候,振聋发聩地提出“自行车之后是什么”的问题,呼吁人们反思现代传媒技术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属性,倡导巨大的技术生产力为公共和集体服务,期待一种“社会主义的技术实践路线”,因此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把希望寄予了中国②[加]达拉斯·斯迈思:《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王洪喆译,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与此类似,希勒倡导将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于公共领域,增加人类的福祉,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一条符合大多数人需求的道路,需要在政治经济层面,教育并引导人们追求一种共享的、公共的生活”③[美]丹·席勒:《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翟秀凤译,王维佳校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60、253页。。福克斯则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只有以共享为基础的互联网才是一种真正和完全的‘社会媒介’,即工作的主体、客体和工作的主-客体都由整个社会控制,不再为积累资本的私人所拥有。”④[英]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周延云译,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92页。这些似乎都为我们摆脱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异化,构建一种“数字共产主义”指明了值得期待的美好前景。
不过,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可以将数字资本主义的信息技术生产力不加批判地直接移植使用,因为不同的生产力影响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而资本主义的技术生产力未必适合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言:“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页。也就是说,诸如手推磨、蒸汽磨这种技术生产力起着构建某种“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页。,进而具有支撑某种社会和政治形态的功能,所以并不是中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芬伯格尤为强调马克思技术思想中的“设计批判”。我们不能将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生产力“直接照搬”,而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一种共产主义的批判和改造。对于当今社会流行的“技术乐观主义”我们应该保持警惕,其问题不在于对新事物的乐观态度,而在于拥抱得“操之过急”,尤其在资本全球化背景下对于外来移植的新技术缺乏这种“设计批判”和“政治-意识形态批判”。事实上,能够为“数字共产主义”所使用的新技术绝非资本化的信息技术“次生产品”,而应是“原初的信息技术(原理)”。按照共产主义的目的和需要,根据这种“原初的信息技术(原理)”进行某种特殊的设计和应用,可以产生与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性质不同的技术效果。
(二)存在之思:海德格尔消解当代数字资本主义技术异化的思路
和马克思对技术异化的解决诉诸社会政治的批判改造不同,海德格尔将技术异化的解决诉诸一种新的“思想转向”。由于海德格尔从根本上将技术异化的思维根源归结为一种形而上学,按照这种思路,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诸种技术异化也依然未能摆脱这种形而上学所支配的范围。只有摆脱这种形而上学思维,唤醒一种非形而上学的思想,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技术异化所带来的危险。
当今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作为一个“技术时代”,无疑是一个思想贫乏的时代,到处存在着形而上学的主体性思维、计算性思维和论证性思维。这些思维在海德格尔看来恰恰是“无思”的,因为它无以“思索在一切存在者中起支配作用的意义”①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33页。,它让人们将一切存在者作为被算计的对象,作为某种“资源”或“原料”被筹划和订造,使得这些存在者只能按照一种“效用”的原则被占有和消耗,从而丧失了自身存在的本真意义,人也被带入一种单向度的“技术化生存”当中。真正的思想是一种通达存在的“沉思之思”,也即“存在之思”,它不同于主体性思维、计算性思维和论证性思维等“形而上学思维”,能够倾听技术时代被遮蔽的“存在的真理”,反思技术时代把“存在之真理”把握为一种狭隘的“在场的形而上学真理”的合法性。它不仅追问作为光明和显现的“在场者”,而且思及作为黑暗和庇护的“不在场者”,把二者共同把握为一种“存在之真理”的自由运作和展开。这种“存在之思”是一种主客尚未分化的本源性思想,能够克服现代技术集置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局限,使人领会到自身作为“终有一死者”的有限性和对于“存在”的归属——作为“存在”的“照料者”而非“主人”,从而尊重物自身的本真存在意义以及天地人神之四重整体的关联性、整全性,由此才能消除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技术集置的危险,使人得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不仅如此,海德格尔还提出和“存在之思”有着相同本质的真理发生方式——艺术和诗。关于艺术,海德格尔认为艺术作品能够敞开一个世界,将天地人神等周遭的一切开显出来、关联起来,从而展现其自身存在的丰富意义。真正的艺术作品绝非流水线加工制造的“产品”——这些东西已经失去了其自身存在的多种可能性,仅仅作为某种“有用的东西”而存在。真正的艺术作品能够“敞开世界”和“建立大地”,前者使得一切存在者可以“现身开显”,后者使得一切存在者得以“庇护藏身”,二者之间相互争执、相互确立、相互成全,共同构成了“存在之真理”的本真意义。关于诗,海德格尔认为,真正的“诗”和文学体裁意义上的“诗歌”并不同,前者是一种动词意义上的“诗性创造”,一种和“思”“艺术”类似的真理发生方式;后者则是一种名词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对象,一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正确的东西”而非“真实的东西”。真正的诗是一种“运思”,能够倾听存在之真理,将一切存在者带入一种敞开领域当中,达到一种存在的澄明之境。在海德格尔看来,诗的奥秘在于作为一种本真的“语言”,“语言”不单单是一种传递信息的“媒介”和表达的“工具”,而是“存在的家”,是“存在之真理”的“道说”:它敞开一个领域,使得存在和万物之本质进入其中,并且得以展开和可能。“诗”作为一种始源意义的“道说”,不同于科学-形而上学的“主观命名”,而是响应诸神的召唤,尊重一切存在者自身的神秘性和存在意义,守护着存在之真理。相反,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信息技术的二进制语言作为一种单义性、技术化的形而上学语言,是对于诸如“诗”这种“本真语言”的最大损害和遮蔽,海德格尔甚至指出,“诗原则上并不能用计算机编制程序”②[德]海德格尔:《流传的语言与技术的语言》,载孙周兴编译:《存在的天命: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文选》,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195页。。在此意义上,恢复一种非数学-逻辑的“本真的诗性语言”,可以作为一种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形而上学语言-思维、进而也是对技术“集置”的抵制和消解。
总之,从本质上说,诗也好,艺术也好,都是一种本真的思想,一种“存在之思”,都是对于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技术逻辑”的瓦解和挣脱,它们倾听存在之真理,使世界作为世界、自然成为自然,让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连根拔起的人重新找回“存在的家”。
相较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拯救方式,也许人们会对海德格尔通达存在的思想拯救方式表示怀疑,认为这种诗性的思想拯救方式难以直接有效地改变世界。然而,按照海德格尔的旨趣,这种改变世界的实用主义观点,恰恰反映了一种“主体统治的性质”①[德]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宋祖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9页。,它将“世界”作为被主体所统治的“客体”进行谋算和筹划,本质上是一种未经反思的形而上学思维。事实上,海德格尔所要摧毁的并非有形的“技术器械”,而是消解现代技术之无形的“哲学根基”,反思近代以来形而上学-科学世界观的合法性,试图面向“存在本身”,回归一种本真的、原初的、天然的存在状态,开启一种前科学的“存在真理观”,恢复一种天人合一的、主客未分的人与世界关系。这似乎是一种比康德“哥白尼式的认识论革命”更为彻底的“真理观革命”,是对柏拉图以来整个西方真理观的彻底瓦解和重建。和中国道家思想类似,海德格尔提倡“道法自然”,反对过多的人为干预,尊重事物自然的存在状态,守护世界本自具足的意义和自由,人也通过追问存在的真理获得生命意义的澄明,从而摆脱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形而上学思维的统治和束缚,以始源的思想和精神力量泰然应对现代技术集置的宰制和威胁。
(三)马克思与海德格尔技术拯救思想的当代启示
在数字资本主义技术异化到处渗透的今天,马克思也好,海德格尔也好,他们的技术拯救思想到底能为我们提供什么现实启示呢?
从马克思的技术拯救思想可以获得如下教益:首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考虑到中国现实的发展处境,尽管不能完全拒斥资本主义的积极要素,但仍要将“资本的逻辑”限制在法治的笼子里,加强对于私有制经济的引导和监管,确保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以及“人民的逻辑”至上性;其次,加强信息技术的“社会主义控制和引导”,保障国家和人民的信息数据安全,强化信息技术产品设计、研发和上市的“全过程监管”,防范资本通过信息技术对劳动者的过度剥削、对人民生活的过度侵犯以及对自然环境的过度破坏,同时致力于推动“信息技术成果的共享”,助力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最后,重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技术的新特点,特别是信息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加强网络传媒的政府管控,防范资本主义通过信息技术对大众文化和思想意识的渗透,维护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健康发展。
从海德格尔的技术拯救思想可以获得如下启示:其一,应加强人们对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哲学批判,重视关于技术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对于中性论的流俗技术观予以充分质疑和反思,挖掘技术背后的思想和文化根源,并且尽可能在学校、企业和社会开设技术哲学相关的课程讲座,深化人们对于技术本质的理解;其二,为了摆脱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技术集置”,应对其深层的形而上学保持充分的反思和批判,同时重视海德格尔所说的非形而上学、通达存在的“沉思之思”以及“诗”“艺术”等,营造一种多元宽容活泼的思想文化氛围;其三,鉴于海德格尔的存在思想曾经受到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还要充分发扬中国传统哲学中能够通达“存在之真理”的非主客对立的、天人合一的有关思想,积极开展中西哲学的比较与会通,吸收外来,又不忘本来,从而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技术思想文化提供借鉴。
结 语
对于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异化,马克思可能倾向于对其进行一种资本主义批判,从而将拯救之路诉诸扬弃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运动;海德格尔可能倾向于对其进行一种形而上学批判,从而将拯救之路诉诸瓦解形而上学的存在之思。二者构成了当代数字资本主义技术批判的双重维度。
就关注的焦点而言,马克思无疑将问题的核心放置在了“技术之外”的“资本的逻辑”——资本主义,但可能对于“技术自身的逻辑”关注还不够,正因如此,雅克·埃吕尔才指出:“我确信……如果马克思在1940年还活着,他将不再研究经济学或资本主义结构,而是研究技术。”①Jacques Ellul,Àte mps etàcontrete mps,Centurion,1981,p.155.海德格尔虽然将目光投射到了“技术自身的逻辑”——“集置”和形而上学,但似乎对技术时代的资本主义和经济学因素关注还不够,正因如此,艾尔德雷德才指出:“海德格尔不理解马克思所论资本主义中主体本质的异化,因此就错过了在与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的相同性中思考现代技术的机会。”②[德]米歇尔·艾尔德雷德:《资本与技术:马克思与海德格尔》,载孙周兴、陈家琪主编:《德意志思想评论》第三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112页。或许,“资本逻辑”和“技术集置”在“存在论”意义上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它们都在言说“现时代”的“同一的东西”③[法]科斯塔斯·阿克塞洛斯:《未来思想导论:关于马克思和海德格尔》,杨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2页。,但终究是“在相互区分的对照中”——“以不同的方式”,这就意味着它们在“存在者”层次上仍然有各自的“区分”“边界”和“限度”,所以不能简单地将“资本逻辑”和“技术集置”归为一个可以相互替代、相互化约的“一元论问题”。因此,在当今这个“资本主义”和“形而上学”相互勾结、相互缠绕、相互作用的多元复合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要想全面地理解和应对现代技术异化问题,无疑我们既需要马克思,也需要海德格尔。
就技术拯救的道路而言,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运动”,是一种“实践”;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作为一种前理论和前实践的“思”,是一种“省思”。实践基于改造世界的感性活动的“人”,思想则建基于人所倾听和守护的“存在”。由此不难看出,在马克思那里,“人”是事情的根本;而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替代“人”成为事情的根本,“人”则作为有限性的一方退居其后。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在19世纪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技术异化主要表现为人的异化,自然的异化问题还没有凸显出来;而在20世纪海德格尔所处的时代,技术异化不仅体现为人的异化,而且体现为自然的异化——由“人类中心主义”所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威胁人类自身生存的重要问题,所以海德格尔开始重新反思人之过头了的主体地位。无疑,在数字资本主义技术异化的今天,我们既需要解决“人”的异化问题,也需要重视“自然”的异化问题。在此意义上,我们既需要马克思,也需要海德格尔,把“人”安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既不至于落入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也不至于丧失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既不沉醉于技术主义的温床而忽视对技术异化的反思,也不至于陷入盲目的“反技术”的泥潭而错失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实现弯道超车的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