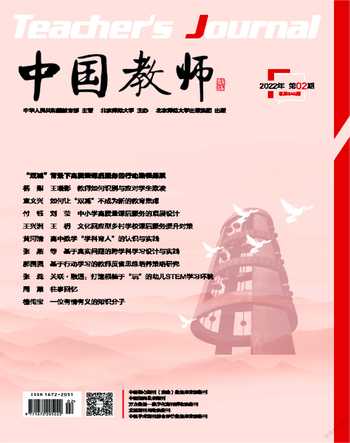一位有情有义的知识分子
檀传宝
我最早见到王逢贤老师是读博士的时候。在此之前,我们当然对先生早已心向往之。那时在德育领域里,几乎所有研究生都知道王老师等国内几个大腕级的人物。所以,我老早就知道他、读他的文章。但是真正见到他,是我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1996年6月,我们几个学生举着牌子到南京火车站接王老师和黄济老师来南京师范大学主持我们的博士论文答辩。遵照导师鲁洁教授的指示,我们把先生们从南京火车站一路接到南京师范大学的南山专家楼。那一年,我们同门一共有三个人毕业,雷鸣强博士、张乐天博士,还有我。非常荣幸,王老师是我的答辩委员会主席。我对王老师非常美好的回忆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作为我的前辈、我的老师,王先生给我留下了许多深刻而感性的印象。如果让我对这个印象做一个概括的话,我想这样表达:王逢贤教授是一位有情有义的知识分子!
比如,王老师对我们这些后辈学生非常有感情。只要是他的学生,他都关怀备至。记得在答辩会上,他反复肯定我们的学术成绩,也发自内心体谅我们学习的艰辛。他认为,在大家都热衷于“下海”赚钱的时候,我们这批甘受清贫的“傻博士”(王老师原话)非常了不起!现在博士生的待遇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们当年读博士时是非常艰苦的,助学金一个月只有两百多块钱。像我,还是已经成家的人,上有老、下有小,可谓困难重重。王老师总是基于学生的立场考虑学生的问题,他一边对我们耳提面命,指出我们研究的不足,但是更多的是对我们极其热情的鼓励和褒扬。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研究还稚嫩得很。老师褒扬我们,一部分原因是他知道我们确实努力了,更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对我们怀有深切的同情,更希望对我们在逆境中求上进的精神予以最大的肯定和鼓励。
1996年博士毕业后,我回到母校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师大”),跟从黄济教授做教育学博士后研究。其间,在北师大也见过王老师很多次。印象最深的一次,当是在我一居室的寒舍里请王老师吃饭。
我知道,在北师大或者北京市,王老师的好朋友很多,因此吃饭的应酬也很多,而且一般学术活动的食宿也都会安排周到。我一开始担心请不到他,没想到我忐忑地说“王老师有时间我请您吃饭吧”,他马上就说行。很爽快,还反过来让我说什么时间合适。博士后的住房非常小、非常窄,饭桌就在床与书桌之间。但就是在那种非常局促的环境下,王老师跟我们一起大快朵颐、谈笑风生。那顿午餐,虽然非常局促,但是非常非常愉快。一起用餐的除了我的妻子、孩子,还有现在在浙江工作的王健敏博士(王老师就是来参与她的博士论文答辩的)。在工作特别忙的情况下,王老师还能够欣然造访我那个非常非常狭小的房间,对作为小辈的我来讲,是一份莫大的情谊与鼓励。
说王老师是一位有情有义的知识分子,当然不仅仅是说王老师和我们这些后辈有着美好的私人情感。最重要的,是说他有那种忧国忧民的品质,有着对整个中华民族发展、人类文明未来的悲悯情怀。他的社会关怀意识强烈而真诚,常常禁不住溢于言表。有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电话里和我讨论我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那是一篇短文,主张要建立教育的“第三标准”。因为我觉得迄今为止的教育,比较多地考虑了“真”的标准,如教育要符合规律之类;也比较多地考虑了“善”的标准,如我们要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等。但是在教育实践中,相对来讲,我们是比较忽略“美”的标准的。因此我们不光要加强美育,还要建立教育活动的“第三标准”,即教育的“审美标准”。文章刚刚发表,我还没有拿到样报,有一天在家里就接到王老师的电话。王老师在电话那头滔滔不绝地跟我讨论那篇文章的观点,讲了好长时间!我想,如果没有真切的热情、不是发自内心地关心中国教育事业的话,对一个刚刚毕业的年轻博士、一个晚辈,他根本不可能打长途电话过来与之做如此细致的研讨。因此,我觉得王老师不仅是一个在学术上有杰出贡献的学者,而且在事业、生活中也是一个特别有情有义的人、有悲悯情怀的人。也许正是有了这种人格品质和精神境界,才能成就他比较厚重、比较有成就的人生!
形成王老师这种悲悯性的学养、修养,离不开两种重要的内在品质:一是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二是克服困难的勇气跟意志力。
像王老师那一代人,遭遇的国家苦难比我们多,个人的苦难更比我们多。王老师显然是那些不仅没有被苦难击垮,而且能够在困难中奋力前行的人。以他的人格,让他没有国家意识、没有社会担当都很难。这固然一方面是社会环境使然,但是另一方面也与王老师本人对这个世界发自内心的关怀有关系。很多时候,只要打通他的电话,几乎不需要再说什么,他就会滔滔不绝地把他对这个世界的关切,对现实教育问题的忧虑,对我们年青一代的由衷期望,非常非常坦诚地反反复复地叮嘱。而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珍贵的精神营养。我们从先生身上学到的,不仅仅是他实体的学术观点,实体的教育智慧,更多的是他学者的人格魅力以及这一人格魅力带给我们从事教学与研究的无限动力。
王老师所具有的坚强意志也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我第一次见到王老师的时候,感觉王老师很健康—高高的、瘦瘦的、神采飞扬,并不知道他的身体也有许多问题。直到1996年我即将辞别南京师范大学的时候,鲁洁老师嘱咐我要注意身体,说:“不要像王逢贤一样—胃都切除了三分之二!”那一刻,我十分震惊。难以想象,每一天他要克服多少困难才能从事他最心爱的教学与研究啊。因此我一直在心底非常钦佩王老师的顽强意志。先生一生奋斗不止,一直到他去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思考,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工作。也就是说,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在荆棘中努力前行!
在我们的研究领域,即德育原理、教育学原理领域,以我所了解的情况看,王老师当之无愧是我国现当代最重要、最杰出的教育学家之一。王老师对教育基本理论,尤其是对德育论学术研究、学科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关于德育研究的成果,有时他用理性的形式表达,如发表论文、出版专著等,有时他也会以非常幽默、感性的形式予以表达。记得有一次,为了肯定、鼓励我从事德育美学观的研究,他认真地跟我说:“你看现在社会上有人买智育,如家教;有人买体育,如学习跆拳道;有人买美育,如学钢琴。但是,从来就没有见到有人买德育!为什么?因为智育好吃、体育好吃、美育好吃,唯独德育不好吃!”王老师关于德育与人生的联系,关于社会发展关系的很多论述,对我的启发都非常大。此外,王老师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德育主体性、德育实体性的诸多论述也是非常精彩的。
如果以王老师为典型案例,我觉得一位“好的学者”的“好”,必须具备三条最重要的标准:第一,有对学术和社会最深切的关怀。王老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具有悲悯情怀的人,他对教育事业有发自内心的关切。而他的成就,实质上出自内心对于这个世界的由衷关怀。第二,有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要有批判精神。王老师常常有非常独到的学术成就,拒绝人云亦云,哪怕看报纸、看电视的时候也能保持自己对人与事最清醒的判断。他在研究上所树立的独立探索的风范,也是给后学者非常好的榜样。第三,具备理性分析问题的学术能力。王老师的理性思维是非常发达的。仔细斟酌不难发现,当他滔滔不绝地讲他自己某个想法的时候,他的“滔滔不绝”都是基于事实、有非常严密的逻辑的。以这三个标准来衡量,王老师是我的榜样,也是所有中国教育学人的榜样。
以上三条,第一条最重要。也就是说,未来的青年学者如果要有所成就的話,一定要有一个比较高的人生境界。王老师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的忧国忧民,他对后学的奖掖,他的不懈奋斗,都是基于对国家教育事业的真切关怀。青年人应该学习这种大的人生境界。因为有多大的境界就有多大的出息。
本文原为王逢贤老师去世(2013年12月13日)后依据东北师范大学有关老师对作者的访谈加工而成,访谈后收入该校编辑出版的纪念文集。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胡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