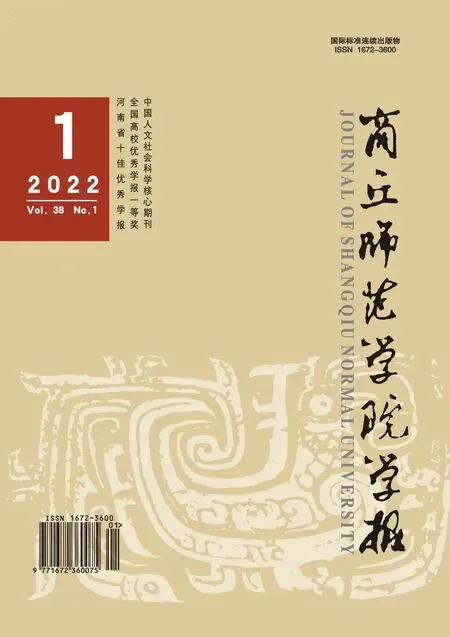《老子》:“正言若反”“不笑不足以为道”的“吊诡·反讽”之道
主对话人 任博克 赖锡三
莫加南(台湾中山大学中文系):我是台湾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老师莫加南,非常开心可以担任今天活动的主持人,今天是我们跨文化汉学共生哲学的第三场活动,非常荣幸可以再一次欢迎任博克老师跟我们一起讨论《老子》的问题。今天任博克当我们的导读人,帮我们进一步了解《老子》,讨论的题目是《〈老子〉:“正言若反”“不笑不足以为道”的“吊诡·反讽”之道》。今天与任老师对话的是赖锡三老师,非常期待他们的对话。
首先,我简单讲一下今天的流程。我们先请赖老师发言,之后直接邀请博克老师开始做报告,他报告完之后,赖老师进行回应,他们进行一个对谈。对谈结束之后,开放全场的朋友提问,像上次一样,有两种提问的方式:第一种是打开你的麦克风,直接跟老师们提问;第二种方式是运用留言的平台,如果朋友们不要看镜头,不要自己发声提问,也可以把你们的问题写下来,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对话。最后,在提问的时候,希望各位朋友可以简明扼要一些,用一两分钟的时间,直接问出你的问题,这样我们就会有更多朋友有机会参与对话。这个是今天的流程。我把时间交给赖锡三老师。
赖锡三(台湾中山大学中文系):各位朋友大家早!有一些朋友可能没有参加第一个场次,我就简单地对任博克老师再做一点补充介绍,然后请任老师进到他的讨论和导读。任老师对于天台佛学的研究相当有代表性,有一些朋友是很熟悉的;很多朋友不知道,任老师年轻的时候跟台湾有很深的因缘:在台湾学习中文、修习佛学,对台湾的文化传统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年轻的时候就从已故傅伟勋先生那边听闻过任博克这个名字。不久前,我重读任博克对天台的研究,大大地打开了我现在所做的庄子研究跟天台的关系与视野,也重新思考任博克的天台学跟牟宗三的异同,这是非常值得重估的学术议题。
任博克早期翻译了《庄子》大概三分之二篇幅的选本,去年他把《庄子》全本完整英译了,这个工程非常浩大(1)参见Brook Ziporyn,Zhuɑnɡzi:the essential writings with selections from traditional commentaries(Indianapois: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Inc.,2009).Brook Ziporyn,Zhuɑnɡzi:The Complete Writings(Indianapois: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Inc.,2020).。读《庄子》的人都知道,《庄子》很多地方像天书,要读懂都很困难,更何况要全文译为英文,可以说不亚于翻译《西游记》《红楼梦》的难度。任博克今年也即将出版《老子》的翻译,《老子》翻译的数量据说仅次于《圣经》。本来任老师觉得既然有那么多版本了,何必再翻译?但是我觉得任老师对《老子》《庄子》的理解是非常有创造性的,等一下大家就会听到非常独特的谈法,所以他对《老子》的重新翻译,有其必要,而且重要。我就补充到这里,先把时间交给博克。
任博克(芝加哥大学神学院):谢谢锡三,谢谢
大家参加这次活动,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我今天要谈有一个方法去了解《道德经》的全体,可能在问答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讨论,文本的形成如何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我的看法是,无论是哪一章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我们会发现《道德经》里头有一个多多少少的一致性,其实一致性并不是说每一章有完全共同的想法,或者写法,或者风格,或者前提,或者结论,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对比性。就是某一章是从某一个角度,另外一章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但是我觉得一以贯之的概念对我来说比较有帮助,去了解整体的思想构造,就是从“价值”跟“反价值”这两个范畴去了解。屏幕上可以看得到,我说A的范畴跟B的范畴,某些章有提到其中某些,我有时候混合在一起,有时候分别讲,但是很多地方就有这一类的东西——后代称之为“阳”,或者称之为“阴”。我们可以在问答环节再讨论。因为在我看来,阴/阳这两个范畴在《道德经》形成的时候,还不是正式的思想范畴,阴阳的系统化思想,可能是到了今天的思想演变,甚至是要反对、要推翻它的一个行动。所以我认为,为了方便我们了解这两个范畴,我想读《道德经》的人多多少少都应该认识到有这种对比。基本上就是:

A(后代称之为“阳”)B(后代称之为“阴”)器朴有无有名无名有形无形实虚男,雄,牡女,雌,牝成人婴儿高下白黑光玄荣辱有知无知道非道可道不可道
我们可以注意“器”与“朴”。我把“器”放在A(后代称之为“阳”,我称之为“价值”),“朴”就是“阴”,也就是我所谓的“反价值”,我觉得这算是很关键的秘诀,它能够理解《道德经》提出来的很特别的一些思想构造,也会解决一些可能会觉得很费解的曲折。
我先把这个摆出来,然后我们再看第41章开头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为什么要“笑之”才算得上是“道”?我觉得这个“笑”字当然很有趣,你可以看是好笑的笑,但是我觉得可能主要就是嘲笑的意思,或者鄙视、藐视被嘲笑的东西,其实也是跟“反价值”有关系。所以现在读起来,“道”就是被鄙视的无用之物,无价值的东西,我喜欢把它称之为垃圾。不被鄙视,就不是道。怎么说呢?今天我们要从第28章开始讲这个问题,上面这些范畴很多是从这一章最明显地提出来: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英文的翻译其实我不必一句一句的跟大家讲,但是也许大家可以注意下面译文内容:
To know the masculine but hold onto the feminine as well
Is to be a channel for all the world.
Being a channel for all the world,
The power of what is constant remains undivided——
A reversion to the state of a new born child.
To know the lucid but hold onto the opaque as well
It to be a model of both Polaris and the Dipper(2)Shi式.See note to Chapter 21 above,and Appendix B,“Notes on the Translation.”(编按:参见任博克即将出版的《老子》英译)for all the world.
Modeling both Polaris and Dipper for all the world,
The power of what is constant remains unwavering——
A reversion to the boundlessness of utmost absence.(3)Wuji无极.This term later comes to be combined with the term taiji 太极 from the Confucian commentaries to the Yijinɡ易经,and adopted into the founding declaration of Song dynasty Neo-Confucianism,wuji er taiji无极而太极.Here it could alternately be interpreted to mean“to the limitless,”or“to what is without polarities.”
To know the honorable but hold onto the disgraceful as well
Is to be a valley for all the world.
Being a valley for all the world,
The power of what is constant remains ever sufficient——
A reversion to the unhewn.
The unhewn gets shattered
To make vessels and tools
each with its purpose.(4)Qi器,meaning “vessels” and “tools,” is a term commonly used for a functionary in an organization who is employed because a ruler sees value in him. Confucius had famously said,“The noble man is not a tool.” 君子不器(Analects 2:12). The reference below to “functionaries” guan官—primarily meaning government officials—plays on this connection.
But when the sage puts them to use
He embodies a seniority extending beyond every such organ(5)Guan官means primarily government officials(see previous footnote),but in Chinese medicine and physiological cultivation is also a term for the physical organs of the body,conceived as structured on the model of a state. “Seniority extending beyond” translates 长; see “Notes on the Translation.”——
The great carving that does no severing.
我们从这里开始讲起好了。此章提到“雄、白、荣”,相对于“雌、黑、辱”。前三者都是当时社会所重视,被人们当时价值观所肯定的。后三者都是当时所轻视,所排斥,所避免,所否定。前者是我们以为有用、有价值、值得追求的事物,后者是以为无用、无价值、被抛弃的事物。而此章却说,虽然我们必须认出前者(就是“知其白”,光明、有价值东西)是怎么回事,甚至知道怎么做,但是并不要因此抛弃后者(黑暗、无价值的东西)。如此可为“天下溪,天下式,天下谷”。
《庄子·天下》篇有一句讲老聃的思想,引用类似这一章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6)参见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河洛图书出版社1974年版,第1095页。缺乏中间的“式”一句。所以我先问,“式”如何被插进去,跟“溪”“谷”平行,它跟这两个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构造,或者如何看待三者,至少在《庄子》或者是《庄子》以后,变成另外一个版本传统平行地放进去。
依我看来,这个“式”就是所谓的“式盘”,古代用来算命的天圆地方的模型,圆天的模型那一块中心有一个洞,挂在竖立的钉子上而可回转,显示天绕着中间的枢纽运转。大家看得到吗?(7)式盘的样式与说明,可以参考Sarah Allan,The Great One,Water,and the Lɑozi:New Light from Guodiɑn,T’ounɡ Pao 89 Fasc. 4/5(2003),pp.246—253.当然天圆的部分它会转,这个地方它是静的,汉代的时候就有这种图案,有的画北斗,但是中间又放北极星,北极星其实不在这个地方,应该在外面,但是它们都混在一个地方,它转的时候,中间跟周边都是同一个地方的枢纽,蛮特别的,我觉得按照考证,把“式”解释为“式盘”,在早期的文献,也许是比较有一点启发性的。
因为我们看看这三项(溪、谷、式),溪是水流注进去的小河、谷是水注进去的虚沟,都是处在下方或虚处,而使得在上、在实处之四方事物自然往之归或绕之转,自愿投进去,自动向之服,无为无形,地位低下而因此包含润泽应付所有来者的象征。三者合起来则有共同意思:虚而处中心位置或下方位置,无为而万物自然归的象征。因为所有中间转的归向也在其中。所以此章等于说:如果能够知道被肯定为有价值的事物都在那儿,而不抛弃被否定为无价值的事物,就会变成无为而万物自然归的那个中心,或下方的虚位。“下”“虚”很明显相应于无价值的意思,现在又加上“中、枢纽”的含义。被认为无价值的事物就是所谓“垃圾”。此章则提出此垃圾有一种未预料到的功能,就是中间枢纽的那个功能,此章称之为“常德”,也有三种说明:“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婴儿、无极、朴也都是同样意思的三面向的说明。婴儿相对于成人是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没有知识、没有能力的无价值的“垃圾”。但很明显也是有将来有价值的成人的开端、根本、来源。再进一步说,婴儿正因为如此无用而一点支配命令的能力都没有,大人都会绕着伺候他、照顾他,正像众水绕着虚谷而自宾自服。我觉得《老子》这个写法蛮幽默的吧?完全无为(不用有为、命令、支配)而自然而然大家都随他而为,无为而无不为。这是婴儿的功能。
“无极”这两个字,就是第二个无,常德的说明。有两个说法,一个是“极而彻底的无,全盘的无”,一个是“完全没有极限”。我觉得两个都可通。“全盘无”是没有东西,贫穷缺乏到底,相对于“有”的充满富有而有价值,也就是彻底无价值的垃圾的象征。“没有极限”是无形,没有形状而等于没有可用之处,当不了有价值的器物。《道德经》认为此“无”像婴儿一样:无价值而当有价值之事物的开端、根本、来源。最后就是“朴”(婴儿、无极、朴),也有同样的意思。朴是相对于下文的“器”。器是有价值的文物,无论是工具或是礼器,都是社会所肯定为有价值的有形而合乎某种目标的东西。朴乃是未刻未割的原料,就是还没有被砍成器物的木头。“朴散则为器”。朴要“散”才能为“器”,就是说那无定形、无价值的东西要被分裂才能有器物出来。《庄子·马蹄》篇有一段说明此“朴/器”关系的意思:
故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8)参见《庄子集释》,第336页。
牺尊、珪璋就是器物。“残朴以为器”很好地说明了“朴散而为器”,所以“散”字跟“残”字一样,是蛮有道理的。朴是原料,当我们从此原料挖出一个器物的形状而得到此器物所待有的价值,我们同时产生两种忽略的副作用:一则残害原来的朴;二则同时产生朴中不被采用造成器物的部分而抛之为废物,就是所谓的垃圾。你挖出那个器物的时候,同时一划就有两段,一段是肯定有价值的,就是器,你不要的那一部分就变成废物,就是垃圾。但是你创造价值之物的时候,同时在创造垃圾,一挖出一个善,就破坏原来非善非恶的朴,而同时产生了恶。
《庄子·天地》篇有一段可以更补充说明此义:“百年之木,破为牺尊,青黄而文之,其断在沟中。比牺尊于沟中之断,则美恶有间矣,其于失性一也。跖与曾、史,行义有间矣,然其失性均也。”(9)参见《庄子集释》,第453页。“牺尊”与“其断”就是器物与垃圾。其一被肯定为有价值,其一被否定为无价值,而两个都一样失去原来的朴的未分全体,而此全体才是两边的来源,当然也是器物有价值肯定为善的部分的来源。而对《道德经》来说,此来源与其说在于牺尊器物有价值那一部分,不如说在于其断、垃圾无价值的那一部分。
今天我们就要论证这个道理,这个根本思想模型在道家思想到处可以看到,含义非常广。并不只涉及价值论,也涉及很根本的存有论、认识论的模型。因为在道家那里,价值论本身就涉及存有与认识的所有问题。这层意义可以从“朴”与“名”的关系看出来。
《道德经》第32章曰:“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与江海。”这个“制”字,我们刚刚看第28章也有提到,大制不割,始制有名。“制”也是一种砍或者一种挖,但是“割”是完全割掉了,“制”就画出来一个东西,但是没有完全断掉了那个关联。一开始,制出来有名,名只有一章,知止就是不割。如果继续画,继续挖,那个东西一再地割,就是不知止,而知止所以不殆。
第37章也讲:“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你可以看名跟制、朴跟器、价值跟无价值的关系,我刚刚列出来有名/无名,名是价值的一个代号,如果看早期道家的思想,当然“名”有命名的意思,但是我觉得更根本就是所谓有名的含义,就是凸显出来并肯定有价值而出名的意思。
所以这个“名”一边是命名,定义出来、界定一个东西,画出来一个界限,但是同时把它当作被肯定的价值所追求,所以跟欲有关系。追求之欲、目标跟名有关系,跟器物有关系,跟价值有关系,相反的,有“朴”的几段,有废物、垃圾、无名、无形等“朴”的意思。
中间两句可以看出“朴”是无名的,“名”也是从“朴”“制”出来,就是像上面所说的割出来的意思,其实“名”在这脉络已经是指谓“价值”的字:光说“有名”其实就是说“有好名”。就像五色令人目盲那一类的东西,那个“色”就是“名”,那些中间的无名的颜色,是不被肯定的,你可以了解价值跟定形的关系在这里已经凸显出来。因此东西有形有象,可以被指定而看得见,被社会价值观给定位的地位与身份,合乎已经被设定肯定的界定的事物。像儒家“正名”的名,“形名”的名,名就指一个事先指定的标准,一个职业该做得到的责任,这个就是所谓正名的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就是一个价值标准。这里就含着《道德经》很大的洞见之一:一个事物被认识为一个不折不扣的“东西”,必先有一个成见标准判定它是何物,必合乎其中先有价值定位的期待位子,才算得上“有”此“物”。所以我说价值论会牵涉存有论跟认识论,换言之,“无/有”的关系,“无名/有名”的关系,都是透过“朴/器”关系而了解的。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有”是从“无”割出来的,“有形”是从“无形”割出来的,“有名”是从“无名”割出来的。割出了以后,一样会有两种副作用:一则迫害原来的无、无形、无名。二则又会产生不被采用而生下来的废物。而奇怪的是:此(二)废物与(一)原来的未刻未割的东西,两者是同一个语言,就是我刚刚念出来的“阴”的排列,它指涉所有这个名单上的字,虚/婴儿/无名/无极,一边是指废物,已经被割了以后不要的那个部分,也同时是还没有的、未刻、未割的全体,没有分有价值跟无价值,也叫作朴/无/无名等。同一个文字所指的,都是一字两义的双关语。我觉得这个才是《道德经》思想脉络的关键。未割的朴叫作无/无形/无名,而割了以后的废物也叫作“无”(贫穷,缺乏该有的)、无形(不可观,乱七八糟)、无名(没有名气)。这两个(未割未分的全体,以及割后分后的废物/一份)正好是一名两义。对我来说,这就是《道德经》所有古古怪怪的修辞的秘诀,也是道家哲学的大门。
废物,不被采取的部分,扔掉的垃圾,是跟未分的源头分辨不了的。试着指出未分的全体其实不知不觉正在指垃圾之一份,试着指垃圾之一份其实不知不觉正在指未分全体。如此则垃圾废物有一个特别功能,就是又意味着全体分散后的一份,又意味着未分全体本身。就是有这个双关的意思。如此则同时是部分,同时是全体。吾人所谓中国哲学特有的“遍中论”的开端正在此出现了。上面引用的第28章因此说“守其雌、黑、辱”(就是不被肯定的,不被采用的,扔掉的废物)才能“复归于婴儿”(就是未分的源头)。
我们既然已经活在有名、有物、有分的世界,如何了解、如何关联到未分的源头?如果说未分其实已经是有分,因为“未分”就是与“已分”分开而对立了,分了才能成立而成为有内容的指谓。如果更进一步把价值放在“未分”这一块,又重演一样的“有价值与无价值的分别”问题。如此则说什么“无分别”“未分”等话,其实只是火上加油,更增加分别,更增加价值偏见。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似乎到了一个瓶颈,不可能解决。但《道德经》就找出了一个活路。在已分的世界里,唯一的指出未分的向度就是要借上述的“一字双关”的巧合:已分世界里抛弃为废物的东西既然是跟原来的未分向度同义,我们可以直接说,废物就会免不了同时带着未分的意思。
后来的道教是不是比较忽略了这一点,我不知道,可以提这个问题。一般而说,神学、形上学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对“原初”“本体”“本真”“第一因”等完全而纯粹未分、万物之来源的幻想,以为我们的现状不完整。片面偏离、不平衡的已分世界的不满,可以透过一个直接回归的作用而重新地接触到万物的来源、未分的整体全体等,纯粹的、未分的、至善的,与之联结起来而大团结,恢复我们失去的健全感。这个冲动本身没错。失去的未分的“天地之始,万物之母”的重要性正好就是道家所要提出来,而且确实认为我们唯一可以健全活着的方法就是恢复与之联结。问题是,直接的方法是永远不可能成功的。如上所论,逻辑上的不可行是很清楚:一把“原初未分”与“现状已分”分开来了,以前者为必取而以后者为必去,就更巩固了分别的心态,一直蔓延下去而变得越来越严重。宗教、形上学的各种对己、对他的暴力都从此长出来。但是,幸好《道德经》早就有见于此问题而提出很惊人巧妙的解决方法。一边不抛弃对万物之母的追求,一边了解,因为其有内在结构吊诡,不可能直接达到。答案就在垃圾的双关意思。
何以论之?垃圾是一个分别的物吗?又是又不是。其实,“垃圾”这个词所指的并不是某某特定之物,而是广指所有现在不要的东西。除了我认定为有价值、有用的东西以外,所有剩下来的东西都算“垃圾”。我在追求某某物,或很多物,或社会价值观,或自己经历所养成的习惯、所认定为有价值的所有之物,我的意识焦点所认取为“物”的东西就限定在这些东西上,忽略任何不合乎那些先定的标准的事物,不给它任何地位,甚至于把它看成是一堆不伦不类的无定性乱块,就是所谓的垃圾。而在《道德经》来看,正因为是超出我们先定的定义界线,这些无定性的垃圾才是我们活在这已分、这价值二元世界唯一能够稍微接触到那未分有用无用、未割破的“朴”的显现。垃圾虽然是一部分,但是有特别带着全体意思的一部分。垃圾虽然是分后的、用完以后所丢掉的东西,也是回到最初的重新开始。垃圾虽然是最后来扔掉的部分,但是也是唯一恢复原初的通道。要回到纯粹而能涌现世界生生万用的天地之始,只能通过最脏、最无用、最后而最弱的垃圾。“处众人之所恶”也是《道德经》的陈述。垃圾就是新的开始的沃。
你看天地间任何一个东西,有时候都是包括在“垃圾”这个词的含义里头,所以也可以说它是真正的无形、无所不包含的一个词,所有排列为B的反价值,我觉得都有这个特点。因此非常有趣,在《道德经》的形上学,因为朴跟器的关系,有两种不同的含义。我就提醒你们一下,B,所有垃圾、反价值、朴、无那一类的东西,一边指已分的废物、不肯定的反价值,一边指还没有割的全体的朴,因此A、B的关系是不对称的。
所以我们排列出要了解的所谓的“阴”,你要把它看成是未分的,而不是包含器。其实从朴挖出来的、剩下来的东西还是朴,但同时又是废物了,就变成双重意思。因此,有很有趣的一些后果,B就有如下六个不同含义,我刚说垃圾有特别的功能,B就延伸为《道德经》的“道”的意思。
1.B is theoppositeof A,excluding A.This was its original meaning.
2.B is thesourceof A,and what it must return to.Whatever A we pinpoint,it can only have an origin in something that is non-A;thus B.However we define value,it must originate in non-value;however we define an entity,it must originate in non-entity—there is nothing else from which it can come if it comes at all.The formed originates in the formless,the carved comes out of the unhewn raw material.
3.B is actuallybothA and B,including both A and B.For B is the raw material from which A was cut,and A is still entirely made of what we now,after the cut,refer to as B.The wooden cup is still wood,so “wood” refers both to the cup and to the scraps carved away from it.
4.B is reallyneither“A” nor “B” ;true B excludes both so-called A and so-called B.For we only use the name “B” in contrast to “A,” and “A” only appears after the cut.We we name what precedes names with the name “namelessness,” but then this “namelessness” is only another name.The real namelessness is named neither “name” nor “namelessness.”
5.B is actually alwaysmoreBthan whatever we call B.Since it is neither A nor B,it is even more a negation of form and value than B,which was supposed to be the negation of all form and value(i.e.,all A),but was still itself a form and a value,precisely because it had a specific delineation(i.e.,constrast to and negation of A).It is even more “formless” than(the form we call) “formlessness,” even more indefinite than(whatever we are defining as) indefinite.The real B is beyond B,more B than B.
6.B is actually alwaysmoreAthan whatever we call A.By definition,A was supposed to be the locus of value,where value comes from,how we get value.But it turns out what really does that is B—the course,the source,the end,the stuff of A.A means the exclusion of B,but A without B turns out not to be sustainable value at all.Conversely,B includes both A and B,so B is the only true A.Dao is an A term that is here used in a new B sense,enfolding all the previous senses.B is the real A.
“B is theoppositeof A,excluding A.” 它原来是这个意思,都是相对的,所以朴就是器的相反,或者其断,或者无名,是两个对称的、互相排斥的范围。所以B原来是A的相反,但是同时我们刚刚讲那些双关语,B所有那些(无极/婴儿)都是一边是A的相反,一边是A的来源、归处。
在第5章,所谓刍狗的形状开始是无用的东西,对不对?“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刍狗原来是没有价值的,社会把它结成一个可以崇拜的、有价值的东西,然后又散掉了,被抛弃了,被丢掉了,这就是我们所谓有形的东西的形成,对不对?所以A又是相反的,是它的源出也是归宿。其实你可以在逻辑上说,原本你可以指出的东西,它的来源是什么?当然,最简单的说法,任何东西是非“这个东西”而来的,因为它基本上是起点,那在起点之前都是没有那个东西,所以如果那个东西一直指定为有价值,它是从没有那个价值的状况而出来。
这样讲来,“B is actuallybothA and B,including both A and B.”所以说,朴跟其他是B的东西,都有这两层意义,一边是原料,如果我把器刻出来,刻出来的还是木头,原来的原料还在,但也是被排斥的那个部分,就是它们共同点在于B不在于A了,这个很特别。So,The wooden cup is still wood,so “wood” refers both to the cup and to the scraps carved away from it.
但是这样讲起来,B is reallyneither“A” nor “B”,你也可以说,B是排斥A与B。一边是包含A与B,但是B同时,如果说有/无是相对、有分别的,这样子的话,无不是真正的无,这才要讲到什么“无极”等,或者说,无名跟有名是相对的,无名还是一个名,所以真正的无名是排斥无名跟有名。
更有趣的就是,B is actually alwaysmoreBthan whatever we call B.顺着刚才那个意思,无名其实必须比任何一个否定价值更进一步,在这个方向更没有名,更没有你所找的价值或者形状,或者合乎限定的标准的东西了,所以它是比B还B,可以这么说。但是《道德经》还有一个转折,有时候会说“其名不去”或者说“常名”这一类的话,我觉得这一章的转折就是说:“B is actually alwaysmoreAthan whatever we call A.”
这个就是最后的反讽,就是道家反讽思想的开端和关键的地方。其实没有价值是最有价值,而所有的价值其实都在于那个地方,所以《道德经》会说小,也会说大,它一边是最小,但另一边,比如第32章(10)《道德经》第32章:“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又是最大。大是价值,大小也是一个对称的A/B。
但是《道德经》为什么说,它那么小是因为大。因为无私而成其私,成其私就是A,就是万物归之,为什么归之?因为有大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故不去。那个不去也是它的A,所以真正的A,你也可以说更彻底的A、实在的A,其实也就是在于B。这就是我最重要的这六个意思,B是A的相反、A的开头,包含A与B,排斥A与B,比B还B了,还有比A还A,这个就是《道德经》的“道”。我觉得我就讲到这里。
莫加南:非常感谢任博克老师那么精彩的报告,让我们了解“垃圾”这个概念也很重要,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接下来有请赖锡三老师做回应和对谈。
赖锡三:任博克老师在谈《庄子》的时候,创造了一个wild card的隐喻,在谈《老子》的时候又创造了一个garbage的隐喻,实在太有趣了。博克你在陈述《老子》的垃圾哲学的时候,中间穿插《庄子》的观点,很有启发性。
我先绕一个弯路来跟你对话,就先从《庄子》开始。庄子跟惠施的三大论辩,其中一个就是有用、无用之辩。对惠施来说,庄子的主张、言论都是垃圾,无所用之,不管是树木、葫芦,只要不合乎规矩,不合乎工匠眼中的可用之材,就是无用。庄子显然某个意义下也继承《老子》的垃圾哲学,也就是“无所用之”的哲学。这个无用跟他所要展开的逍遥之道是连接在一起的,这里面有其对价值/反价值的反省,也有你说的存有论、认识论、价值论共构的问题。听完你这个报告以后,我对垃圾产生新的看法了。我这几天还在跟我太太开玩笑说,以前我会抱怨: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在倒垃圾?从现在开始,我不再抱怨了。原来垃圾可以这么富有深意!
任博克:在纽约,你知道到处都堆着垃圾。
赖锡三:垃圾是我们这两天很有趣的话题,我想到以前曾经写过一篇讨论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懒惰哲学”跟《庄子》《老子》“无为”的关系的论文(11)赖锡三《道家的逍遥美学与伦理关怀——与罗兰·巴特的“懒惰哲学”之对话》,《当代新道家——多音复调与视域融合》,台大出版中心2011年版。。罗兰·巴特有个有趣的说法,他说有两个巴特,一个是巴黎的巴特,另一个是乡村的巴特。巴黎的巴特是一个名人,一个“有用”的人,每天都在收一大堆的信,走在街上的时候常常有人要他的签名,拥有很多贴在他名字上的形容词。可是他到后来很厌烦巴黎的巴特——这个有价值的、有用的、天天被称赞的巴特。然后他找到一个仪式性的行为:逃到乡村,成了乡村的巴特。那种状态就像他到了非洲的摩洛哥:他是无用的、无名的,几乎没有人认识他。那时候他完全是个无用之人(废物一般),在那样的日子下,过着一种无欲的生活。有趣的是,他对无欲的描述,其实某个意义下也是最有欲望的。乡村时的巴特,所做的事情都是纯粹业余爱好的,而不是职业功能性的,都是无用的纯粹耗费。比如说,业余画他想画的画,谈他想谈的天,作他想作的曲,然后他发现无用的巴特、垃圾的巴特、乡村的巴特,却拥有了最大的愉悦,也处于“可欲之谓善”的自然欲望状态。
巴特当时很敏感地注意到这种状态,可以对治“现代性”的繁忙,并且连接到《老子》的无为。他很明确谈到《老子》的“无为”以及禅宗的“任让”。他说:我们应该要勇于懒惰,并将它提升到主体转化的哲学深度。这个观点可以连接到惠施与庄子关于葫芦有用没用的辩论上,惠施说葫芦长得太大了,大而无用,然后就用暴力把它剖之弃之。葫芦浪费了很多的肥料,最后还让惠施失望,当固定化的“用”失效之后,惠施就觉得这个葫芦真的成了垃圾,于是就用暴力把它给毁坏、丢弃。庄子却说,大而无用的葫芦,如果你把它重新放到另外一个新脉络的时候,就会产生新的意义与新的作用。比如说,把它绑在腰带上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大樽而可以让你浮游。庄子在谈论有用无用的时候也谈到大树,大树不一定要把它砍下来做成合乎规矩绳墨的“材”,你也可以让它树立在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这时它看似无用,却能够让自己不遭受伤害、不会中道夭折,而且还能够转化你与它的关系,让你从有心有为的用物状态,转化成泰然任之的逍遥状态。
而从任博克对垃圾的说明,尤其后面的B,是非A且非B,或者说,既是真A也是真B的那个论述里,我从中看到了非常有意思的“垃圾中道观”。什么叫作垃圾的“中道”?你刚刚谈到中国最早的遍中论,可能开端于《老子》而成熟于《庄子》,我希望等一下你再稍加阐发。
我所谓垃圾的遍中论或中道观,是这样来想象的:垃圾之为垃圾,是因为它离开原来用的脉络,例如东西用旧了、用老了、用坏了,觉得不好用了,你才把它抛弃掉。其实人类的垃圾之物,原本也曾经是个个有用的符号物,而当我们符号命名的特定功能暂时性失效后,它们才成为了一堆暂时失去用之脉络的“混沌之物”。可是当我们仔细观察“混沌”般的一堆垃圾物时,会发现一件有趣的事:如果仔细看细节,你还是可以认得出来,在一堆垃圾之中,你仍然可以发现现在的无用之物,其实仍然“若无似有”地暗示着它们过去的脉络轨迹,虽然它们现在离开了原先可用性的特殊脉络,可是它们多少也能够被找到过去的痕迹,似乎还有一个过去物“若无似有,若有似无”在暗示着。但也由于物的形式又被剥夺了原先特定使用的指涉性、整体性,所以它的有用性暂时被悬置了,成了无用的垃圾。这样的垃圾状态对我来说,虽然看似无用,却又因为解放了定用而成了最大可能性。换言之,垃圾不是纯粹的无形或无用,垃圾其实具有“即无形即有形”“即无用即有用”的中道特质,它并不是纯粹的无形,也不是纯粹的有形,而是“即无即有”的暧昧两可性。而且它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只是等待被重新脉络化,被重新放在新情境新关系中,以获得更新的活用意义。
这种“即有形即无形”“即无用即有用”的垃圾中道观,或许可以连接到你在报告里所提到的对于形上学的反省,或者对于神学的反省,以及对于无分别的绝对追求的反省。人们因为落入名以定形的定性世界中,于是在规范的硬性架构下,在分别的界线世界中,产生很多限制和困境,例如价值二元论的冲突与挣扎,所以宗教与形上学经常会渴望一种非分别的世界,企图想从中得到彻底的解脱、彻底的安顿。任博克做了很好的逻辑论证和分析,对绝对无分别的渴望与追求,事实上已经再度落入了分别,也已经离开了当下,甚至把“无分别”与“分别”作出了更难以克服的分别。而且把欲望导向绝对无分别的追求时,无分别的境界反而变成了更大的欲望对象,而产生出更精微更固化的执着了。而《老子》《庄子》谈“为无为”、谈“为腹不为目”,则是要破掉这种单纯的、对于绝对无分别的形上幻象的追求。任博克从垃圾的分析里面告诉我们:纯粹无分别跟眼下分别的超越区分,将使得无分别的追求变成另外一个新的价值高求,而宗教人经常认为应该找到更高更超越的价值去追求,例如去追求形而上的道和绝对的纯一境界。然而从任博克的分析看来,这是求不到的,而且反而会落入一种类似“同一性形上学”的暴力,以及对自身欲望的压抑或压迫的暴力。对于《老子》的吊诡表达,或者“正言若反”,任博克利用垃圾的隐喻来说明这个问题,非常有启发性。
这个观点让我想到《庄子》“下”这个概念。《知北游》的东郭子问“道在哪里?”庄子回答说:道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砾,甚至说“道在屎溺”。也就是说,道就在垃圾里,道就在最脏、最臭的粪便里。所谓“道无逃乎物”,而且“每况愈下”地回到最卑下的眼前。这就解决了形而上跟形而下的二元对立,追求形而上本来是想要治疗庸俗,可是也可能造成另外更精微也更难以对付的形上/形下的二元困局。返“下”,你也可以说是要把形而上带回到形而下,这里面就有一个形上与形下的“二而不二”,或“无”与“有”的“玄同中道”的问题。换言之,可以从垃圾谈出中道的工夫实践模式,以及破除physics与metaphysics的二分,以及二分所带来的绝对超越性追求的困境与幻象。
刚刚博克提到了遍中论,但描述得不多,等一下希望你能再进行补充说明。回到垃圾本身,它有没有超越性?它是否可以破除形而上、形而下的二元论,破除二谛论?从天台来说,天台的三谛论似乎还是不同于龙树二谛论那种真谛与俗谛所具有的那种细微的区分。一旦带有细微的区分,真谛超越性的priority就一定会存在,这个时候就会保留一种超越分别的、无名的世界,也就是“绝对沉默”的追求。而天台的遍中论似乎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对垃圾的表达同时是“双重否定”又“双重肯定”,也就是遍中论透过“双重否定”与“双重肯定”的“非A又非B”“即A又即B”,以这种吊诡思维来面对欲望,如何谈出另类的工夫论与超越性?
我觉得你刚刚的报告已经隐含了这些意涵,对于形而上学的陷阱、同一性暴力的再超越,这里也涉及所谓的“一字双关”。对于“一字双关”或者“正言若反”,也希望你能再多做解释。“一字双关”,不只是修辞的问题。一个字或者一个“真正的B”,它的双关是既关联到A也关联到B,也就是它不能离开A和B,可是它不能停留在A也不能停留在B。如此一来,“一字双关”就隐含了“反讽”的意味。
而且“反讽”如果可以涉及“垃圾的中道观”,似乎便具有一种“双边反讽”:它既反讽形上学式的绝对无分别的追求,也反讽掉入了定有那种追求有用价值的定性之僵化。也就是在追求价值的极端化过程,反而掉入了价值的偏执,遗忘了对于“非—价值”所可能带来的脉络更新与活化。所以它可能是双向反讽的,等一下希望多听你谈一谈。
如何把垃圾的中道观,连接到共生哲学来?你在描述价值与反价值的架构时,价值与非价值通常被当成是价值中心与价值边缘。价值中心比如美、善、光,是值得追求的,而非价值就被排斥了,变成一般世俗意义的垃圾。大部分人都不想成为垃圾,不想成为一个无用的人,因为他会在这个社会上一直被霸凌,一直产生价值被否定的虚无感,这个问题若连接到《老子》的垃圾哲学的中道观,或是垃圾哲学的辩证法,又要如何描述?现在的年轻人有许多虚无主义的情调,强调耍废哲学或耍废的人生,为什么?因为要立足社会,要挤到价值中心,经常难之又难,很多人在追求过程中总是有所失落,慢慢就养成了一种不追求不参与的态度,只要过着适性即逍遥的生活,甚至耍废的生活就够了。耍废姿态正在过分竞争的时代中细火蔓延开来,可是在你所描述的垃圾哲学中,真正的B不是等于B,因为B的意思有一个部分是被价值所排斥的垃圾,那是会带来价值虚无主义的。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或许可以回应《老子》和《庄子》既克服形上学的一偏,也克服了虚无主义的一偏,对两端各执一偏,都进行反讽而加以逆转。你的垃圾哲学或者废物哲学,谈出了非常有趣的妙意,可是要如何防止废物(垃圾)哲学,被时下风气的耍废情调给滥用呢?
再来就是共生,你谈价值与非价值的关系时,已经隐含了批判道德的真理化、道德的自我傲慢,可能带来的虚伪与暴力。要如何跟自我和解以形成更大的自他宽容?下一次林明照会谈《老子》第27章和第49章,如“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所隐含的共生意味。而你在报告里面也谈到,“莲花”与“污泥”两边不可偏废的问题,是不是也隐含在共生的意涵中?
最后,“遍中论”的谈法似乎可以彻底克服二元论,而在佛教的脉络底下,它也会涉及对于“体用论”的回应。体用论也是为了要克服二元论,所谓“体不离用、即用显体”。可是体用论似乎还保有一个根源的本体,作为一个超越性或规范的立理根源。这个“体”是不是隐含了一些可以澄清、可以对话的空间。很抱歉,我的回应也是抛给你问题,让你进一步回应。
任博克:这些问题很深,很重要,我觉得我们就聊一聊好了,看看能不能点到一些有趣的,也许可以再进一步去把握这个含义。我第一个要回应的就是你刚刚提的垃圾的中道意思,我觉得非常重要,而且说得很好。所以我们说无形,或者无名,或者浑成、混沌之物,我觉得说得很清楚,整个道家思想其实它是无形是混沌的,一大堆有形的东西,不伦不类的,你远看它就是模糊,没有一定的形,而且任何一块“无”你仔细看它,一大堆东西,一大堆形式,一大堆具体的东西都在那边。你刚刚讲的我觉得非常好,就是你要怎么了解它,为什么变成垃圾,就是它脱离了原来的脉络,原来的社会或个人的价值观。因为脱离了原来把它定起来,给它一个定位的脉络,它就跟周围的其他的垃圾的东西不组成一个可认出的一个形,但是其实无形中就有形了,我觉得这个方法就可以很具体地理解。
说到庄子与惠施的对话,当然也正好是提到这个问题。你看它无用,它是零件,零件也是零,但是零件也是很多小东西,可以接通很多不同的东西。所以,我总是觉得,这个文字很有趣,中文现代语“零”字的用法有这个含义的。像惠子的葫芦故事,我总是觉得,其实是在运用垃圾、无用、废物那一类的意思,因为在这个故事好像有两层,我很想问锡三的想法。就是说第一个是宋人,有人要用做不龟手之药,他先举这个例子,这个例子是把某一个小用转成一个大用,但是庄子这个葫芦好像是把一个小无用转到一个大用,在这里,大用跟大无用重叠了,为什么?因为浮于江湖,可以说也是一个用,也是一个无用。跟不龟手而战胜的用,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
我觉得,大有用与大无用其实是同一件事,也是中道的意思。小有用与小无用是分别的,天台也发挥了这个意思,很巧妙的。上周我们提到把那个东西彻底化了,它就变化了。现在西方哲学也有这种意思,量会导致质的变化,彻底化、纯粹化,大的有用,在这里不是某一个特定的用,是浮于江湖的那种更无用的一个用。但是这个大无用其实就是跟垃圾一样,很多小用在里头,很多小零件,你在浮于江湖的时候,有很多短暂的欲望或者目的,或者转化了。那些东西就像上周你谈的河流,他们不是直线的、统一的、一致的。所以也许你可以说,大无用是很多小用组成的,但是多元化的小用就是大无用,大无用就是大有用的。
我觉得还有两个问题,我绝对要回应一下,我不知道能不能解决你说的耍废,也许我们可以问大家,我有一些想法。我先讲另外一个问题,《老子》《庄子》和天台那个脉络的中道、遍中论的一些特点。我说《老子》可能是遍中论的开端,这是因为在我看来,它第一次提出有一个又是部分又是全体的一个筹码。那就是垃圾,或者朴/无/无形。因为它是分开的一半,但是同时一直双关也是整体的,因为它的否定的位置,是以价值的否定为主,“处众人所恶”“上善若水”,也是你刚刚讲《庄子》的往下的趋势。因此我觉得这个开端的可能性,以我看来,可以解决永远的无穷的追求,无分别又建立了一个分别的恶性循环的那种问题。但是《道德经》我自己认为不是同一个作者,而且也不是同一个时候所写的,是很多不同人绕着这一类的思想,收集的一些精选集。在我看来,我刚刚讲的那一类的思想构造是最有趣的。当然有很多人注意到,《道德经》一般而言是有达到“中道”的一种方式,我可以完全同意这种解释。但是中道有一个特点,第一层意义就是B是A的相反,所以否定的意思也很强,所以虽然它还是会达到非A非B与包含A和B,还有真A、真B。但是通道一般而言都是要通过B,不能透过A。在这里,我觉得《庄子》就变得活泼了,很多方向都可以通。在天台中更发挥了,因为用方便论,开权显实的那种思想和方法就多了。问题是方法多了,但是在佛教那边还是要透过一个“空”。“空”也是否定的意思,当然有明显的关系了,而在天台那边也不只是空,但是因为它还是在佛教的脉络里,有时候就处在《老子》与《庄子》之间。我觉得《老子》和《庄子》达到道枢,或者中道,或者两行,两边都可以,“可”与“不可”是平衡的、同等的,它的方法又进一步。我觉得大概就有几个地方,我刚才说“知其白,守其黑”那一类,其实已经有开始开辟另外一个道路,不是完全偏向B了,是B但是还要注意到一点A,这也是做了两边的包含。还有锡三你上周谈的第36章“将欲歙之,必固张之”等,这也是有开出另外一个活路,你的解释也可以通。如果传统的解释,就是说A可以物极必反,善用物极必反,还是用A达到B。这在《道德经》很少见,我觉得在《道德经》中一般的是要透过B才达到A与B,与非A非B,还是以B为主。
你说共生之道,提到下周林明照也要谈的善人跟不善人的说法在这里也许是最明显的。其实我应该也列出来,善/不善很明显是A与B的关系。我觉得“道者,万物之奥”(12)《道德经》第62章:“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帛书本作“道者,万物之注也”。,或者马王堆说“道者,万物之注也”,这个奥和注,跟式盘、溪、谷都可以合起来,了解这个意思。这个奥是看不到的、最内在的地方,也是注进去的那个虚,那个中位,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有共鸣的。
但是下面的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所保就是能保的意思,善人是有意识的追求,不善人不管“道”,但是“道”还是会保护他,那个就叫“善人,不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资”(13)语见《道德经》第27章:“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所以资跟师的关系很明显,强调两边,与“知其白,守其黑”的想法相通。
所以我觉得《道德经》就有这几个方法,有那个原初的洞见,从垃圾、中道可以这么说。一般大多数它是强调B,但是其实它强调的B,有的地方还没有《庄子》那么大胆,没有“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那么彻底,但是像第20章也有这种描写得很生动的,一种无用的人的生活,垃圾人的生活(14)参见《道德经》第20章:“绝学无忧,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累累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若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最后有一句对不对?“贵食母。”我觉得可能要从这里立足,当然《道德经》跟《庄子》比,有它保守的一面,可以这么说,它还没有《庄子》的彻底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它还是会定上“食母”。我对“天下之母”的解释也有一些意见,第一章的“天地之始”在“马王堆”那里是万物之始,所以是“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马王堆”两个都是万物,不是天地。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可以把它解释为无名是万物之始,如果给它一个名,那个名就是“母”,像第52章说“以为天下母”,那个“以为”有一点类似第25章说“强名”,所以天下之始、万物之始跟万物之母是同一件事情,同一个东西。但是一个是有名,一个是无名(15)《道德经》首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帛书本作“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第52章的原文是“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第25章的原文是“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比如说无名,你命它为无名,我其实应该把“母”放在B,“母”是一个空洞的生产力,但是“无名”在中国古代社会是真的无名无姓的,也不在系谱上,“无名”是指下/虚/子宫/玄牝之门之类的,我觉得这也是“耍废”,可以贴到第20章,其实它描述非常颓废的生活,但是那一句“贵食母”很重要,它的价值观、它的贵在于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不喜欢,什么都不觉得有任何价值,但是它还是会移动它的价值观在奇奇怪怪的B那个方面去,我觉得《道德经》的方法好像是认为你想要把欲望移到没有形象的东西,这个叫作无欲,它的欲望就会开始有漂浮的活动在变化,所以它描写的第15章也是很好的例子,讲那个“古之善为士者”的样子(16)《道德经》第15章:“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孰能浊以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他们行动很慢,好像很谨慎,但是其实是等他们静到一个极点,就开始慢慢萌发出来动,或者他们是非常“浊”,浊当然是B的范畴,但是“浊”彻底到“徐清”,就是慢慢清了,所以也许这个辩证的物极必反,B到底就是转变的意思,如果可以跟耍颓废的秩序对话一下,要看是不是很彻底的颓废,真的颓废到底会有一个反动,依《道德经》来看,不然的话可能无形中有一个东西还是保留在那边,把它稳定化了。它还没有碰到底、还没有hit bottom。
《道德经》这个说法,我觉得有很多有趣的问题在其中,但是我觉得可能从那个角度可以开始探讨,因为第15章和第20章我觉得可能是立足的地方,可以开始看到这种问题。你问得很丰富,很多问题我不知道有没有碰到,可能还有一些我刚刚遗漏了,但是先答到这里好了。
莫加南:非常感谢博克老师完整的回应,因为今天时间比较充裕,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赖老师可以稍微回应一下,对谈一下。
赖锡三:任博克刚刚谈到了真正的耍废,比如说西方存在主义,对于荒谬、虚无的彻底化,当你真正彻底到那种地步,很真实沉浸虚无主义到底的时候,好像内部隐含了一种虚无主义的自我克服或自我超越,或者还有另一种状况是活不下去了。
虚无主义的彻底化隐含着另外一种物极必反的生机,生命整个自我反转的可能性。如《老子》第20章说:“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大家都清清楚楚知道意义感、方向感,一起床就知道怎么样勤奋地走出人生漂亮的第一步,可是《老子》第20章把自己描述成真的像是颓废的人,完全茫然无方向。可是最后一句说“贵食母”,他是自觉的,不人云亦云地跟风向。比如说《庄子》谈到“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大家好像都知道那是光明之追求所在,但《老子》的“贵食母”,也不是宋荣子“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因为宋荣子的“定乎内外之分”,他想要找到一条完全属于内在本真的存在方式,于是把内在的本真和外在的关系给完全对立区分开来了。而《老子》的“贵食母”,并不是存在主义式地想从内在找到一绝对的自我或绝对的支点。
《老子》是在自我转化为“无—我”的前提下,才能谈“食母”,“无—我”的掏空,跟被价值抛弃的虚无感,非常不一样,它其实隐含了否定的创造性自觉和修养在其中,是一个真正行动的支点。在我看来,它是能够于各种有用、无用的价值共在时,柔软调节的“调中”“适中”能耐。
莫加南:非常感谢赖老师的补充。朋友们,我们现在时间很充分,欢迎在线的朋友提问。
黄玉真(台湾中山大学博士候选人):请任老师对于方才赖老师提到遍中论是否仍不离有一实体自性的体用论再多加说明?天台宗的遍中论是否仍属于存有的形上学呢?
任博克:有一点可以关联到我最后讲的,《老子》与《庄子》与天台的差别所在,就是说《老子》很多地方就是偏向B或者是母那个方向去解决问题,在这里可以找到一个中道,中道原来在一个特定的地方,但是如果看下去,它就是好像先要立一个吊诡的本体,以我看来,这是中国哲学第一次立了一个类似的本体(古代的天命我们另外谈),而且一提到了本体,马上是吊诡的本体,也就是无的本体、同时是无本体。我觉得,因为看到很多西方的否定神学,也有吊诡的含义,便会因此有一点忽略《道德经》系统的吊诡用途,错认西方否定神学为类似于《道德经》的“道的本体无即无本体”的意思。其实不然,因为西方否定神学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与分析的话,会发现本体的实在性与形上意义始终没有淡化,甚至是强化了。这一点从其中一律A与B关系单单限制于对比的意思,也就是我们六层意义的第一层意义而已,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来。其实此种否定神学不过是把传统神学以及柏拉图主义的“重A轻B”思想形式的极端化的一种意外副产物,始终没有改变西方哲学的二元论的价值观以及执着神圣绝对真善美的偏见。我们今天谈的就是《道德经》六种意义合一的意思,它一立了真A,就好像是真的一个本体,真的有“万物之母”听起来总是一种本体,但是如果了解全体思想的构造,把握其所以然,就知道意思完全不一样。所以虽然勉强可以说《道德经》立了一个本体,但是因为马上又要把它否定掉了,内在地包含必然即立即破的含意,所以肯定与否定是同等,甚至是同义,可以算够彻底了。
我觉得如果王弼用本、体来说明《道德经》,其实是因为他对于老子、庄子要作一个轻微的批判或者保留,他注意《道德经》的第11章“利”与“用”的差别,还有在第38章的注中又提出来而指出“舍无以为体”与“贵无以为用”的差别(17)《道德经》第11章的原文是:“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另外,王弼对《道德经》第38章的注语是“虽贵无以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不能舍无以为体,则失其为大矣,所谓失道而后德也”,参见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94页、第102页。,因此他认为如果《道德经》明明谈了一个“无”作为本体其实不够无了,孔子才是真正的体无了,无到没有无,根本不必谈无。孔子已经舍了无,不谈无,如此才表现他真的“以无为体”。《道德经》里谈了无,这不过是“以无为用”。所以,一立无为本体,无就不是本体。
所以我觉得《道德经》就算在王弼的眼中好像是要必经过的阶段,它是自我否定的,或者我们刚刚谈到颓废的自我超越、自我否定,其实已经包含在《道德经》的系统,这就是我要讲的那六个意思,它要立一个本体没有错,但是那个本体是吊诡的,又推翻了自己,到最后又立了又破了,所以到处都是。常有名/常无名、常无欲/常有欲,它要两边都可以通。
但是我觉得这个与“遍中论”还是有一些不同。我刚刚谈的问题,在天台“空”的、否定的那一面,也是有转折的特别用途,但是到最后的发挥,“假”也有可以开权的能力,不只是“中”或“空”可以开。“空”可以开权“假”与“中”,是没问题的,这与《道德经》的想法是类似的,就是彻底的“无”,还有一个自我变成“假”,所以它也会把所有原来固定的,或者有定形的,有自性的东西重新脉络化,使得任何假立之事物X当体同时显现为非X。但是在天台那边,任何假事物一被如此开权,此假事物本身也具有开权其他一切假立事物的能力,也具有开权“空”与“中”的能力。“假”也可以推翻“空”与“中”。“假”也可以立也可以破,“中”也可以破也可以立,“空”也可以破也可以立,“空”也可以绝对化,“假”也可以绝对化,这个是“圆融三谛”,“圆融三谛”已经不能用体用论来说了。而且智者大师文献中几乎都不出现典型体用模式的思想。
解释遍中论可能要比较花一些时间,但是构造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像锡三说体用论原来是要克服二元,但是它有一点不完全成功,有遗漏的一些可能性。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了解天台的不同。如果是看《庄子》内篇,我觉得就不用透过本体,直接用“滑疑之耀”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外、杂篇有的地方也比较接近老子,外、杂篇常常引用《道德经》,但有各种不同的发挥。我觉得可能真的讨论要一个一个讲,刚刚《知北游》也是一个好的例子,我觉得也是蛮接近《道德经》的。
莫加南:非常感谢任老师的回答。宋家复老师也有问题。
宋家复(台湾大学历史系):两个问题:一、这样的老子、佛家三论宗,甚至僧肇《肇论》有何不同?二、这样的老子或道家要怎么处理mysticism问题?还是根本已经没有这方面问题? In your 2012 book pp.152-153,a similar argument was made.But there seems to be a bit different from today's.Would you care for elaborating on this?(18)参见Brook Ziporyn,Ironies of Oneness and Difference:Coherence in Early Chinese Thought;Prolegomena to the Study of Li(Albany:SUNY Press,2012).
任博克:对前面两个问题我刚刚大概说了我的看法。不过,三论宗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三论宗以天台的立场来说,是一个比较符合复杂而彻底发挥的一个“但中论”,它还是有要看很多原文的地方。当然辩护三论的有很多余地,这个很复杂,但是以我看来,简单来讲,它还是把否定跟肯定一层一层先分后超,每次一样的形式,先做了一个分别;而后超越了这个分别,又继续做另一个分别,或者把分别与不分别当一个分别而后又超越它,超越此分别放在语言之外,然后又立了一样形式,分别语言与超语言,而又立了超越此分别的中,它其实给我们一个无穷的重复。以我看来,我会觉得是有一点像黑格尔说的“恶性无穷”、bad infinite,虽然它是很巧妙地处理每一层,但是我觉得它“方便”与“不方便”说的分别,到最后还是没有完全彻底地解决。
因为《道德经》不是系统化,所以比较有一些余地,里面可以包含种种不同的方法,我们做思想史的工作,方法论的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如果像我刚才那个报告,我们就要抓住很多细节,可能有很不同的地方,那六层意思当然不是在《道德经》里头,对不对?这个是我的推测分析,希望可以用这个来解读各种各样《道德经》的论述,因此跟上面来比,虽然它要提出一个本体,或者“母”或“吊诡”的目标,但是它会强调“吊诡”是比较没有系统化的,所以反而以我看来是比较活泼一点,可以有多样化的作用。就我刚才讲,在工夫论《道德经》至少有三四个不同的方向和方法。在天台来讲,变成系统化的多元方法,而且每一个方法都发挥很多细节,像别教中有无量法门的解决,圆教中保存别教的无量法门而一一开权,显示每一个都空、假、中,就是说每一个都又破又立又是无外法界(绝待而遍一切时空的实相)。这个可以讲很久……锡三好像要加入讨论。
赖锡三:我捅了一个“马蜂窝”,把佛教带进来之后,问题就会变得非常广大,可能会蔓延到很多地方去,必须把问题再拉回来一下。佛教会连接到非常庞大复杂的问题,没有办法一次性地在此聚焦讨论,我先把它拉回到刚刚宋老师提到的:《老子》《庄子》跟神秘主义的关系是什么?能不能谈神秘主义?它的超越性在哪里?
神秘主义或宗教,是一种形上学的变形,追求彻底无分别或者说神秘主义的基本命题,就是企求Holy One的合一经验,绝对同一性的证悟。当所有事物超越分别、超越语言、超越时间、超越空间之后,到最后汇归到绝对的一。任博克在报告时谈到道教问题,道教的内丹最明显是追求先天的境界,其实就是要超越一切的分别,超越语言,甚至阴阳也要超越。因为阴阳涉及变动的问题,一旦有变动就会有杂多,就会有差异化,从二到三到万,差异不断会演化出来,某个意义下就越远离“太一”。《天下》篇曾经描述老聃“主之以太一”,“太一”可以用北斗那个中心来形容,但问题在于《老子》是不是住守“太一”?是不是守住北斗的中心抱着不放?《老子》因为谈沉默、无言,讲无极、混沌,好像想要回到“母”。而要回到那个“母”,只有不断地从多回到一,甚至归零,归于没有形式,没有形象,也没有语言的绝对零,才是母,才是真正的不可道之道。一般的神秘主义,大概是采取这样的理解,所以采取逆反,要从后天返回先天,反转阴阳二分而合丹为一。内丹就把《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倒过来读,一定要从阴阳返回太极,太极再返回无极,并把它解读为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在我看来,内丹就是一个彻底的神秘主义追求的道路,取消了世界,取消了差异、杂多、变化,以为绝对无分别的东西才是终极之道。但我认为这样来理解《老子》,也只得一偏。因为《老子》的“道”无为而让开,不主、不宰、不命、不名。当“道”完全让开之后,本体其实也就吊诡地取消了根基,进入一个“即有即无”的两端不住,这样才能够“有无玄同”而成就“众妙之门”。换言之,《老子》的“母”,并不取消差异、走向超绝的“本无”,而是“即无即有,即有即无”的玄同状态。“有无玄同”,有没有神秘主义的意味?你可以说这里面其实也有神秘主义,也有超越性,可是这个神秘主义刚好破掉了无的偏执,回到万物的“万有”之中,而万物却是“即无即有即中”的玄同显现,其中的平凡即有不平凡。我认为这里面也有大奥秘,有趣的是,这种真正的大奥秘具有反讽意味,它刚好是破掉了过分神秘化的那一极端,回到了“即平凡即超越”(或者“即俗即真”)的玄同之秘。吊诡地来说,它是“破神秘的神秘”。
任博克:我要补充一下,我也很同意这个说法。我觉得锡三说得很好,我刚才说有“非A非B”那一层,如果认为彻底否定语言、否定可思议,或者否定有形、有名的那种所谓神秘主义,我觉得在老子,这一步骤绝对不可避免,但是像我刚才说的,因为未分别与已分别,这样的分别也是不稳定了,不成立了。一定要透过它这个不可避免的步骤,但是它的步骤完了,马上就会吊诡,转回到亦有亦无,亦有母亦有子,亦有名亦无名,亦有欲亦无欲。很多方面可能还没有《庄子》那么彻底,但是这里很多已经立足了。比如,我们看这六层意义,你立了其中一个,其他五个一定也会跟着来,其中一个是绝对的超越,但是这一个超越在《道德经》我们会发现又回到完全内在,双A双B。我今天讲的,跟家复提的那本书,那个时候只有五个点,现在又多了一个点,但差别没有很大。或者你觉得哪里不同?前四个是差不多的,可能第五个的说明,因为现在把它分开了,比较发挥了一点点,我不知道有没有差异很大。
莫加南:非常感谢任老师的回应。我看在留言的平台上还有两个问题,我们就先请蔡老师发言,谢谢。
蔡瑞霖(台湾警察学校):谢谢赖老师和主持人莫老师,还有任博克老师。我先做一个补充,然后请教一个问题。第一个是博克说到的“正言若反”,我非常欣赏您最后讲的B比A还A,我先就这个来说文本问题。博克老师说《老子》通行本非一人一时之作,应该是一个选集,是那一类思想的集成,我非常赞同这个看法。所以我要就第20章里面提到的“绝学无忧”来提问,如果照版本研究来讲,它应该属于上一段,后来变成为第48章的“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的这一段之开头才对。也就是说,依照未分章的竹简本的顺序,它应该归到上面去,属于上一段“日损之道”连着读。
如果要用博克所说的方式来讲,其实是要我们去掉一些学术上的支解知见,才能关联到后面的,就是分章本第20章所说的“人之所畏,亦不可不畏人”上。这个段落的重读正确了,就可以跟大会题目所说的“吊诡”,即《庄子》里面说到的“大梦之中的梦”,醒过来之后,是“觉而大觉”的状况相符合,从学术语言的泥淖中跳出来,然后才发现我们都意有所指,都是用名言、语言、名相去规定之概念游戏。如此才能体会到《庄子》说“君乎,牧乎,固哉”的灼见。君是主宰也、主体也,牧是被主宰、被动的,若都不再有主客观或主被动之分,就能巧妙回到语言游戏上面去。
如果这样的吊诡可以弄清楚,反过来看“正言若反”,也许博克所说到的以天台宗“遍中论”所提到的,B也许比A还更原始更真实,这个意思才能够被我们深刻了解。正因为这个问题非常深刻,所以就牵涉第二个问题,尽管天台“空观、假观、中观”的遍中整体论,如任博克老师书中所说的,以及刚刚锡三兄所提到的可以调中而调和调整的“调中论”,或者如儒家常讲的“执两用中”的“用中论”,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我们从整体源流来看,中观思想里面所讲的是“辩中边论”(也说辩中论或中边分别论),它的推论其实很简单,倘若不用方才五个A与B的关系加第六个来讲,而是以“辩中论”来看,就很简单了,就是“A是非A,所以是A”(A非A,所以A),这正是《中边分别论》的分别思维模式,也是般若智,即空性。所以它也是在强调一个唯名戏论,而戏论乃是佛教的一种根本教法,它也可以当作某个意思下的垃圾。在垃圾可用的时候,是调中式的用之,暂时保留地用之,按这样,它用完之后上楼抽梯、过河拆桥的动作都变成了戏论,所以佛教说这一种语言来往也可以是戏论,就可以不用多论了。所以“般若智”可以拆掉自己所走过的足迹,也因此这种说法才能够出现反讽的态度,来证成“正言若反”的恰到好处。这种反讽如任博克所提到的“垃圾之道”,也可能因为时间关系没有讲到后续的“不笑不足以为道”第41章的内容。其实“下士闻听道而大笑”,以为不足以为道,正是因为他大笑,所以他能真正了解“道”。因此,这个“反”字有一个特殊意义,正如《老子》在核心文本也就是竹简本里面所说的,“反”不仅是单纯的字面上的反。“正言若反”四个字是后来的帛书版本才加进去的。我们要了解这个“反”其实是返回的“返”字,如果非要用帛书以后的版本不可,那就要将“正言若反”的“若反”两个字当词来连用,这才是重点。“若反”可以让我们知道它不是真正的相反,它是有作用的反。如果不用帛书本的说法提“正言若反”,而是回到竹简本,那是没有这四个字的。我们应该回到《老子》本来所说竹简本里面、最原始的核心文本所提到的,也就是那一关键段落“反者,道之动也”之反(返),这个反是“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的回返的返,而且是大而远,远到无边无际,就自然整体包容起来。恰恰是这种返回自身、回到跟问题根源点的“返”(反)才是真正的关键问题。
因此才能体会博克的比喻非常巧妙,“零件”也是零,但是零件又成为“组件”,这一套套的配置,可以为组合而备用的,当它没有用的时候统称为零件。所以这个关键是很有意思的,必须请教于任博克老师,关于六个A与B的关系,如果单纯以中观思想的“辩中论”,也就是《中边分别论》来说,“A非A所以是A”的简单表述,对于“空性”的理解,或说“性空唯名论”的理解原来是一种语言游戏,这个看法不知道您怎么看呢?谢谢!
任博克:我就简单地回应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那个版本差别,真的很值得考虑。竹简本跟王弼本特别对于“反”的解释很有意思,跟绝学无忧也是,也可以跟我们今天谈的有很漂亮的一些关联。我觉得蔡老师提中观的思路很有道理,内容也很丰富。刚刚提到道家的思路跟佛家的入手方法不一样的地方,可能从这个角度是最直接的,完全没有错。我刚刚说在《道德经》我看到A跟B是不对称的,因为B是朴,而A是从朴挖出来的器,佛家的逻辑并没有这种认识论的前提。所以,在般若思想,任何A与非A原来它们是很对称的,可以直接反过来的。又透过A非A故A那种思路,又回头说B非B,故是B,然后把这两个就合起来了,其实这个思路的步骤跟《道德经》有蛮不一样的内在构造。
当然有一点像家复提的三论问题,也许一进入般若思想的系统,你可以说是很简单的秘诀,但是又使用在很多不同的方向,就变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但是我谢谢蔡老师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对称、不对称的,我觉得是一个根本的不一样。在天台开始,他们可能有一点结合起来,或者有一个新的重视,但是我觉得这个差别是应该指出来的。
赖锡三:刚才蔡瑞霖老师谈到《齐物论》的梦觉问题,而“吊诡”这个概念的第一次出现,就是在《齐物论》的梦觉脉络,而回到这个脉络里面,才能看出“吊诡”这个原创概念的深刻与丰富。其中的脉络刚刚蔡老师已经点到了,他谈梦、梦中梦,谈到梦与日常意识,最后谈到有一种叫“大觉”,可是最后孔丘依然不免“君乎牧乎,固哉”,最后庄子强调“大觉”其实依然不离梦,这个寓言太重要。在我看来,没有一个离开梦的大觉,才是真正的吊诡。对于那种追求绝对,以为可以找到终极解脱的无分别经验来作为大觉主体,或作为真君真宰的可住可依之实感,《庄子》反而说其实这依然不离梦化,还是不能离开变化。换言之,没有离开“撄”的“宁”,只有“即撄即宁”才是“吊诡”。
这样有什么用意?比如说,你不能够离开言去找一个无言,所以《庄子》强调“言无言,终日言而尽道”,这个时候,语言就变成能够不断开权显实的方便法门,不是离开语言去找一个绝对沉默的大觉。其实你是在不断的语言游戏过程中,让语言更新脉络化,而在更新脉络化的过程中,语言也已经在无穷尽的变化之中而不住于自身,可见“言无言”的吊诡用言方式,已经打开了语言自我转化的超越向度了,因此不必完全抛弃语言才能超越语言。这正是《庄子》的“吊诡”所富含的潜力,“言无言”的吊诡,同时克服“绝对无言”与“名以定形”的两边偏执,这也是从“环中”调动“两行”的能力。
Daivane(网友):感谢老师们的精彩呈现,受教良多。请教两位老师:道家“环中双行”的中道思想与佛家“双照双遮”的中道思想有什么不同?第二个问题:儒家的“执中”、道家的“不执”与佛家的“圆照”之间有什么具体区别,很想听听老师的解答。感谢!
任博克:我们好像一直在绕着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蔡老师刚刚提出一个开端,如果真的看般若思想到双照双遮思路的步骤,一开始是很整齐的、很对称的思路所累积起来的,到了一个尽头,最后那一段,就是三论跟天台的差路所在了,差别在于两家如何处理“方便”和“开权显实”的问题。如果缺乏“开权显实”那个部分,空的含意会很不一样。你看佛家对于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如果你专门讲般若,那是一回事,你讲天台又是一回事,僧肇又自成一家,三论也是,都是般若思想,但是各个又很有创造性,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其实是很复杂的。甚至对于“体用”的问题,我们刚刚谈的体用问题很重要,各家处理的方法其实蛮不一样的,很有讨论的余地,所以我觉得可能要说他们怎么不一样,你就要分开讲。
我今天讲这个不对称的朴跟器的关系,我觉得在原来的佛教,其实不是这样看否定,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对于否定特有的理解,是很有趣的。比如“无”字,你看就算在文法上,“无”字你要说一个东西存在不存在,“无”在文法上不是普通的一个动词,比如说你在白话文,有杯子、无杯子,有鬼、无鬼,但是一般中文的文法中,动词是在名词的后面。“无”跟“有”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彻底否定,没有像巴门尼德(Parmenides)的那种古希腊“有”跟“无”截然不同而不可能互通?中国古代为什么也没有创造世界的实体化创造主?我觉得,这都跟这个特有的对于否定的理解有关。其实照理,古文说“无X”是一个简称,应该是“天下无X”的简称,只是漏掉了主词。在中文的文法就没有问题。但是从此就可以看出来,提到任何一个内容,必定同时假设此一内容所出的背景,讲天地这个内容也是,必定有一个更大的还没有天地的背景先具,才可以“有”天地或“无”天地。这个背景就是周围还在的无形,就是朴,就是B。一提到本有,必定有比本有更大的背景,它就会马上转到或者变到吊诡,我觉得这个是中国特有的东西,可能要讨论得比较久。这几个问题都有关系。有/无是不对称的,在印欧的系统里头是对称的,在印欧系统否定是一个语言的文法直接简单的“有”的相反的东西。但是“无”就是无形,此无形跟肥料、玄、朴,相对于名、价值、形等等,都很有关联,我觉得那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如果你要一步一步地看,在《道德经》各章有不同的发挥,到了《庄子》当然有更大的变化。
到了中国佛教,以我看来,僧肇已经开始同时进行结合这两个系统,所以我最简单地回答你的问题,一个是对称的有无观,一个是不对称的有无观。不对称的有无观的否定,是像希腊和印度会问为什么有世界,而不是没有,像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也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不直接提了,所以“有”“无”的对称、不对称,我觉得可能最根本的不同就在这里。实际上是每一个年代的作家、思想家都会想如何处理,把那些东西组合起来等,所以这个可能讲不完。
有一个关于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的问题我很快补充一下,为什么他在西方的思想史上有突破性,其实也跟我刚刚谈“有、无”的问题有关系。虽然有很多人会把斯宾诺莎跟巴门尼德并提,认为他们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我觉得不一样。因为斯宾诺莎的实体,或者自然,或者神,有西方未曾有的含意。因为斯宾诺莎的规定就是否定,所以内容就是否定,所以无限与无内容终于在西方形上学结合起来,终于统一“有”与“无”。虽然它是存有论,但是它的存有彻底到已经连无也是有,也是中道,所以也是物极必反,那是最实体论的物极必反的一个例子,实体等同于空,空等同于实体,突破了西方实体化的形上学,我觉得斯宾诺莎重要性就在于此。
莫加南:非常感谢博克老师,不知道赖老师有没有要补充?
赖锡三:佛教讲“中”,儒家强调“中”,道家也说“环中”,而且中国本身就以“中”为名,所以中国哲学这个概念在先秦已经非常丰富了,我觉得任博克“遍中论”的提法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区分出“一中论”“但中论”,“‘遍中’并透过佛教天台的讨论谈到‘遍中’”,他把天台跟老庄归列为遍中论,印度佛教的二谛论或者华严并没有完全克服“但中”的问题。
这个问题所以重要,比如说儒家非常强调允厥执中、不偏不倚、中庸之道,发展到宋明理学更重要了。朱熹也不断在参“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未发的“中”又被视为是一个心性的本体或本源。问题在于,这个“中”很可能被当成是唯一中心,被实体化,或者被形上化、本质化了。如果你把最根源的本体、太一当成“中”,或者把“无”与“道”当成“中”,万物绕着“中”而转。如果是这样理解,《老子》的道、物的关系又会堕化为“一中论”,道变成一个绝对的中心,万物只能绕着“道”转,看起来强调“中”,可是“道”变成了价值中心的本源,或是以一御多的中心,而被固定化下来。所以如何区分一中、但中或遍中,在我的理解里,很重要的判断就是,有没有把“中”给予本体化、形上学化、本质化。再则,遍中论涉及吊诡的思维方式,这可让“中”无所住于“中”,既可以从“有”来谈“中”,也可以从“无”来谈“中”,当然也可以从“调中”的“即两边又不住两边”的“遍中”来谈“中”。以《齐物论》来说,就是“天籁”,“万物咸其自取,使其自己”,背后没有怒者,所以每一个万物都是“中”,可是每一万物都与其他万物互有依待的关系,不可能住于自己的“中”,所以它既是中心又是边缘,这样才有无所不在的“遍中”可能性被十字打开。
每个国家经常都会认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在研究“中”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在神话或宗教人的思维里,每个国家都认为自己是“地中”,而且都要找到“地中”来建立都城,认为北斗星都在他头上,拥有权力的时候你就变成是“中”。但是遍中论的“吊诡之中”,会不断地解离自我的中心化,并允许“中”无所不在。儒家的“允执厥中”,有没有达到遍中,如果从老庄来看,儒家可能没有达到遍中,可是从它也不断想谈一个活活泼泼的“中”,它是有这个倾向性的,但因为它缺乏对“无”创造性的否定思考,以至于它有一个细微的本体作为“中”的坚持,使得它可能没有达到遍中论的思维程度,这是一个值得再深入对话的有趣问题。
莫加南:非常感谢赖老师的回应,真的很有趣,我们大概还有六分钟,我觉得李志桓这个问题是可以帮我们今天做一个总结。
李志桓(台湾中山大学博士后):从这种重新看待“垃圾”“没有用”的哲学出发,怎么思考“共生哲学”?一群颓废的人,真的可以一起生活吗?颓废的人和不颓废的人,可以相安无事吗?
任博克:我先说几句,锡三可以最后说。我觉得《道德经》绝对是可以实践的,你有什么原因觉得这个是很难相信的,也是可以再讨论,你觉得它不实际。但是《道德经》提到了“不善人者,善人之资”,还有“无弃人,无弃物”,“圣人常善救人而无弃人”,等等。
也许可以谈论圣人,或者我们刚刚谈论耍废的问题有提到了,《道德经》肯定有虚无到底的自觉者的角色重要性,所谓的圣人,在《庄子》比较复杂一点,但是在《道德经》是我们说的彻底的垃圾,彻底的颓废,这是大无用,不是小无用了,是大无用就等同于大有用了。
所以我提到第15章的“浊而徐清”,“物极必反”好像有万物归之的作用,它要彻底的虚无。你看《庄子·德充符》中的一些人物,也许你可以看到这个差别所在,当然有一般的颓废人,但是真的颓废到那个程度让国王费解,把国家让给他,这是很彻底的颓废人,所以这个是“为道日损”的工夫,一般的颓废是小颓废,还不合格。这是我的想法,我不知道锡三怎么说。
赖锡三:《德充符》的例子实在有趣极了,哀骀它颓废到鲁哀公要把整个国家让给他,这实在是太反讽的说法了。而李志桓的问题,或许可以作为今天讨论的总结。社会上很多失意者、边缘人,在有用的追求下、血淋淋的竞争下,逼迫自己却又不合乎成功标准的那一大堆受伤的人,他们经常被视为失败的人生,无堪用人。但有时候我们想一想,那些所谓成功人士可能也苦不堪言,他们让自己在有用化的极致过程,把自己用尽了、耗光了,而且下不了台。平常在舞台上很累,离开舞台后又失魂落魄,其实他们也是另外一种伤心人。任博克引到《老子》的“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提供了我们思考另外一种共生哲学的中道观。平心想想,有时候边缘可能比中心保有更大做自己的空间,或者隐含一种反转的潜力,其至提出更完整的思考方式。比如说,思考女性主义,不一定只有与男权争权对抗的形式,女性主义可以从柔软的B的角度去进行批判和解放,当A的思维方式走向过分刚强、竞争的主体之后,其实它已经注定走向了片面化的危险性。所以女性除了一方面在社会中要争取公正平等的权利外,也有可能从《老子》的B那个角度,提出一种“既是A也是B”“既是非A也是非B”的更完整思考方式,也就是,在边缘中可能破开刚强主体的“一中论”思维方式,反而能达成创造性思考的“反者道之动”的新可能性。伤心失落的人也同时要去思考,如果住在废的世界太久,会错过变化的机会。事实上,“无用”到底还是有一个“用”字在,你的存在、存活本身,其实已经在影响身边,你已经以某一种方式回应这个世界。所以“无用”之中,极可能有“妙用”正在发生作用着。
莫加南:非常感谢赖老师,博克老师真的对我们非常友好,愿意跟我们开会到12点,博克老师还会参加我们下个星期的活动,所以我们也有机会跟博克老师继续谈共生哲学的问题。非常感谢任博克老师、赖老师今天那么精彩的对谈,很热烈的掌声,感谢大家!
任博克:谢谢!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