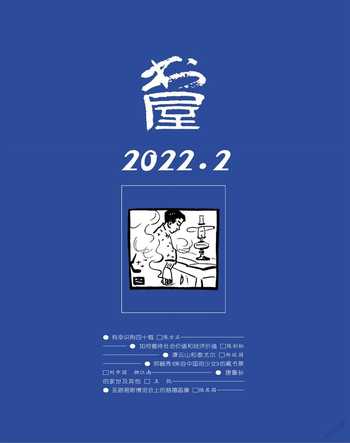食在广州的贵阳往事
周松芳
广东与贵州,珠江一水情牵。
广东人早就是贵州特别是贵阳的主客。清代以来,贵阳最著名的商贸街名为“广东街”,就是因为广东商人前往那里经营百货玉器和海产南货而得名:“随着市场的扩大和繁荣,江西帮、湖南帮、四川帮、云南帮商人也先后办货来筑,大部分在广东街安家落户。”
然而,广东人前往贵州的高潮,恐怕是在抗战时期,迄今难以逾越。因为贵州是当时的大后方,许多公私机构特别是军事机关与军事工厂都设在贵阳,特别是1938年广州沦陷后,工业相对发达的广东,很多人员机构也内迁到了贵阳。战后《申报》一则报道便说,单单“在贵阳服务美军机关的粤籍人员和技工约有万人,连家属约五万人”。那全部在贵阳的广东人,加起来没有十万也有八万吧。如果说早期“广东街”形成时代,跨区域饮食市场未兴,粤菜馆出现的可能性不大,乡味充其量由广东会馆提供,那此际如此庞大的人流物流,必然带来粤菜馆的大兴。
白天白《解放前贵阳的两广餐馆》说,首先问世的是先设在中山西路后迁至中华中路贵阳民众教育馆对面的“四海酒家”,并说主持人是曾任薛岳秘书的广东兴宁人何湘,先期来贵阳的空军方面的同乡曾剑刚也有股份。然而,薛岳的秘书为何会跑到贵阳来开餐馆?作者没交代,读者也实在想不明白。倒是曾剑刚有股份甚至是开办者主持人都有可能。杨晓林的《贵阳的飞机场与贵州航空处史话》就说,贵州军阀王家烈想办空军,1934年初在香港购回三架飞机,贵州航空处随即成立,并任命周一平为上校处长,广东人曾剑刚中校为参谋长,空勤机械等人员也多来自两广。可是1935年1、2月间,国民党中央军大兵入境,王家烈时代结束,航空处也随之夭亡,那些来自两广航空部门的空勤机械人员,因为政治前景与蒋介石势力不合而“打道回府”,但曾剑刚因为已与贵阳园艺专科学校毕业的女生曹某结婚,只好在贵阳安家落户,并改作商贾,在中华中路开设一家独特的广东味餐厅,牌名“四海酒家”。这种叙述倒颇合逻辑。
顾君毂于1939年在《贵阳杂写》中说:“(甲秀)楼旁有观音寺,再近有翠微阁,去夏四海酒家在此设立餐馆,发卖粤菜粤点,生意极盛。”这只是说四海酒家在翠微阁设立分店是在1938年夏,中华中路的四海酒家应该成立更早,但其广受欢迎,则是能充分说明的。柴晓莲先生有一首诗,在题目中已称颂其盛——《己卯(1939)秋日翠微阁晚眺,内有四海酒家,游客甚盛》。时人唱和,也多假座于此,如有诗题曰《巴壶天秘书招集四海酒家,予以太常斋禁辞退,赋诗谢之》。饮食风雅,于斯可见。1939年6月1日大夏大学十五周年校庆的庆祝午宴假座的四海酒家,就应当是中华中路总店了,翠微阁店没那么大容纳量。
有一位笔名“匪我思其”的作者,在贵阳出版的《青年阵地》半月刊1935年第七期写了一篇《前哨:“四海酒家”》,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四海酒家的地位和影响:“中国是穷的,贵州更是穷到不可再穷的一步;中国是应当作战争准备的,贵州更不可不作最大的准备!然而,有时在事实上给我们的印象却大大不然。走过了大街,一切享乐浪漫的色彩已经足以令人作呕,足以令人想到贵州不惟不曾向‘建设复兴民族根据地’的工作上面有着怎样大的进展,而且已经正在向着纸醉金迷的灭亡线上迅速的走去。尤其是到了每天深夜的时候,更使我们有着不小警策!”接着就点出了在这本应万籁俱寂的深夜,“从中华路光明路再向北来的大街西成路上,高高的三层楼,三层楼都亮着怪亮的电灯,都擅动着人影,这地方便代表了这非常的时代当中的‘复兴民族根据地’的倾向?这是多数人都不容易走进,而多数人都知道的地头,在那三盏绿色电灯光照耀之下,摆着蛮大的四个黑字:‘四—海—酒—家’”。紧接着还有酒店内外的特写:“在外,有着的是漆壳辉煌的几部‘假流线型’汽车,在电灯光下静静的对面蹲着,等待着它的主人的驱策,从那车身漆光和电灯光的反映中,发散着许多漂亮华贵的气味。在内,眼睛看得到的是:整齐排列的酒瓶,红红绿绿的纸花,堂皇精致的陈设,晶洁明亮的玻璃;耳朵听得到的是:谑浪笑傲的喧嗔,五魁八马的对抗,呼喝诃斥的威风,刀杯碗盏的交错……”读了让人感觉到这是上海至少是南京大酒家才有的气派。
继起的“五羊酒家”于1939年底在省府路创办,老板广东中山人袁秉忠也是帮会头子,担任贵阳警察局的消防队长,还兼任贵阳华南体育会会长多年。合资人是在四海酒家对门开私人诊所广东老乡文靖思。可能因为这层关系,他们请了在贵阳经销上海产儿童良药“小儿安”赚了大钱的曾泽传当经理。虽然个个都来头不小,但整个儿就像玩票似的,所以来头不小的“五羊酒家”经营一年就自动收盘了。接盘者林德三(知名跌打医生)、谭振华、林志乾几个广东高州老乡本有信心做好,特别是林志乾在桂林管理过饭店,亲任经理也顺风顺水,无奈不久因房东收回房屋另租,只好歇业。好事不过三,半年之后,林志乾找到几位金主另集资金,仍用“五羊”招牌,在中华南路租得一家商场的二楼(可以摆三十张台)重新开张,也是生意红火,日日客满,不料却因小事得罪青年军上校军官吴岱旦,被砸台,只得饮恨消歇。
歇了一头“羊”(“五羊酒家”),起了两条“龙”(“沙龙酒家”“金龙酒家”)。也是在1939年,国民党空军后勤供应处由杭州迁来贵阳,空军系统向多广东人,供应处也不例外,主任伍白夫即广东台山人。“食在广州”,皆由粤人好食。伍主任当然也好“食”,到贵阳不久即筹划在中华中路川戏院侧开了一家“沙龙酒家”。与此同时,因贵州禁烟而滞留贵阳的广东南海头号财主、前广东禁烟局(事实上的鸦片专卖局)总经理霍芝亭在贵州的鸦片代理人丁英,趁势在贵阳市场路口开设“金龙酒家”,营业一直不俗,直至1949年初才宣告结束。其间,还有一位陈姓南海人也在大西门城门口开了一间“广东酒家”,只是规模不大而已。按:根据当日报纸广告,金龙酒家似非开在市场路,而是盐行路——“金龙酒家:罐头食物,晨早粤点,广东腊肠,各地土产。地址:盐行路。”(《贵州日报》1941年11月29日第三版)
真正做成大型粤菜馆的,是1941年5月25日在市中心区大十字三山路投资二十万元开设的冠生园。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冠生园以食品工业救国为号召全面撤向西南,并得到当局的支持,而他们无论在哪里开分店,无不是当地食品与餐饮业的标杆,在贵阳自然也不例外:每天早点部門要做四五百元的生意,做糕点的白糖每个月都要耗用十万八万斤。量的背后是质:设立专门的堆糖仓库以保证生产需要,如遇购入不纯白糖则加工提炼后再用。1943年冼冠生还专门驻足贵阳经年,精心筹划事业发展之外,更严格制定落实规章制度,比如服务人员在营业时间只能站着,不准坐着,不准吸烟。珍惜有用人才,不轻易惩罚下属,并随时注意奖掖、激励认真工作者;职工自动离职后,他日要求再来,他照样收用,不予责怪。真是少见的良心企业。
名人笔下的冠生园,较早见于叶圣陶。1942年他从成都去了一趟桂林,途经贵阳,5月18日晨间,“宋玉书来,邀余与彬然同出,进茶点于冠生园”。无论在杭州、上海、武汉、重庆、昆明,都会上粤菜馆,更会上冠生园的张宗和,在他的日记中留下了战后屡上贵阳冠生园的记录;虽然评价不算高——战后冼冠生的生产经营重心回归上海,贵阳显得有些鞭长莫及,原也正常,但已经算好的了,不然,张宗和也不会屡往就食:
1947年10月7日:公共汽车(回贵大)还早,我去到冠生园吃了咖啡,点心都不高明。
1947年11月17日:在冠生园吃了两根春卷、两个叉烧包子,一点也不好。
1947年12月1日:到一点起来,在冠生园吃菜饭。
1948年4月9日:到冠生园,中饭没有吃,我也吃不了,吃一点点心。
1948年5月31日:到冠生园买预备明天请客的东西,火腿、肉松、鸭蛋、面、糖等。公共汽车没有,决定等下午的校车,于是先到冠生园喝茶,写信给文思。刚写了两句,来了个疯子,穿得很好,坐下就大骂孙中山、蒋介石,全骂,乱说,说得不停,自己又叫又唱。叫了饭吃了,走了。他走后,我才来定定心心地写信。我也要个牛肉蛋炒饭,吃了才一点半。
1948年6月5日:一同到冠生园吃早点,有戴、戴、余、昝、我五人,余其心出的钱。
但是,冠生园毕竟是上海粤菜馆出身,或者说海派粤菜的味道,真正地道的大粤菜馆,可能还数大三元酒家。据主要创办者广东高州人张祖谋自述,1944年5月长沙沦陷,衡阳紧急疏散,他在衡阳开电机米厂和南园酒家的堂兄张华球仓皇带领该店员工三十余人逃难到贵阳。困顿之中,找同乡好友李道修商量投资合伙经营广东餐馆,以便安排这批逃难者:李道修占股本三分之二当董事长,张华球当经理,他则继续负责在芷江机场运石料的三辆汽车,不参与具体事务。遂盘下紧挨大十字闹市区的中山东路华华茶厅及其后面的杏花村川菜馆,并打通装修为一体,分设四个大厅,可摆设百张餐桌,能同时容纳六七百顾客进餐,袭用原广州名扬中外的老字号“大三元酒家”作为招牌,于1944年11月开张营业,成为贵阳市当时最大的一间餐馆。生意也一时兴隆,座客常满,孰料中途也遭一厄,即抗战胜利后,军纪巡回检查团检查发现,大三元酒家供应贵阳美军面包,经手军需收受了百分之二十回扣中饱私囊,经理张华球也因此被控协助贪污罪,后虽经李道修打通关节花大价钱保释出狱,却已如惊弓之鸟,远走香港。仓促之中,张祖谋只好亲自披挂上阵,反倒开创了大三元的新时代。
在招揽顾客增加营业额上,张祖谋首先调动自己在运输行业的资源,与人合伙在大三元楼下开设“联安运输商行”,又与人合伙开办“粤桂贸易商行”代理进出口业务,让这些往来生意和业务人员多多帮衬,很快便出现排队等位现象。餐馆也进一步突出广州特色,完全按照广州茶楼酒馆方式装修。出品讲求地道,烹饪师、点心师、面包师、糖果师等大部曾在广州南园酒家、鹰园酒家,衡阳南园酒家、昌生园酒家和贵阳五羊酒家、金龙酒家等著名粤菜馆担任师傅多年。食材供应,更求地道。比如,专门培养了一位了解老广吃鸡要求的伍姓鸡贩,收购符合要求的品种,并保证长期供应。又如,专门找了几个会制沙河粉的老乡开了一间专供店(有余力才供给其他餐馆);连面条师傅都是请的会制作老广喜欢吃的鸡蛋面的钱钜,——他可曾是孙科的家厨。因此,无论山珍海味,无不制作精良,色香味俱佳;“星期美点”不仅品种丰富,所制作各种西点、面包,西人都高度认可;其他如中秋月饼,各式广东腊味、香肠、腊肉、腊鸭、金银肝、油鸡、白切鸡、烧鸡、叉烧、乳猪等外卖食品也品种丰富,供不应求。抗战胜利后,广东高要才子梁寒操来贵阳宣慰,在两廣同乡会在大三元设宴欢迎时,欣然题写了“贵阳大三元酒家”的招牌。那么喜欢上粤菜馆的张宗和,自然也是去过的:“(1947年10月19日)快到十二点,到‘大三元’吃茶,吃点心,又叫了一盘叉烧肉,也没有吃完。”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三元也引领整个贵阳粤菜馆进入了黄金时代。张祖谋说,与大三元同时的比较大型的粤菜馆,还有冠生园、五羊、金龙、百乐门、南园、东园、安乐华、桃园等八家,以及比较小的珠江、广东、银龙、岭南楼、红棉等五家。小小贵阳,一时云集至少十三家粤菜馆,堪称不小的奇迹。只是随着抗战胜利,大批留居贵阳的广东人还乡,粤菜馆渐趋低迷,只有冠生园、大三元、桃园三家坚持到新中国成立之后。
可是,张祖谋为什么一言不提赫赫有名的四海酒家呢?回忆显然是有偏颇的。而且南园也曾有颇有声名,它在《中央日报》打广告说,“名茶粤点,粉饭伊面”之外,还“每晚加奏中西音乐助兴”。百乐门也努力曾精益求精:“大十字百乐门粤菜厅讲求夏令卫生起见,特兴工整洁内部,一俟工竣,继续营业。”此外,还有大利春和生生园两家粤菜馆他根本没有提及:“本店重金聘请前五羊茶室南粤名师,精制粤点西饼及茗茶,开始为众服务,诸君请来一试。大利春饭店启。中山路贵阳大戏院西首。”“生生园二楼茶厅自下月一日起增设粤式名点,第一期名点:(咸品)岭南香肠卷、银牙滑粉筒、明炉叉烧包、冬菰蒸烧卖、荷兰鸡碌结、挂炉京鸭苏;(甜品)鸡油马拉糕、玫瑰豆沙包、鲜奶猪油包、焗牛油布甸、伊府细面。门市局另有盒装发售。中华路光明路口。”
如此一来,短短数年之间,贵阳即涌现出班班可考的粤菜馆十六家,有的还是贵阳首屈一指的大饭店,比较起天津百余年间才考证出有名目的粤菜馆十七家,也可谓“食在广州”向外传播的一道盛景了。
从以上看来,贵阳的粤菜馆与衡阳颇有渊源,而衡阳粤菜馆的记录总的来说并不多,相关情况,便一并附记于文末。衡阳的粤菜馆,其实也多因抗战而兴,因为衡阳开始属于后方,西南联大的组成学校北大、清华、南开及其他多所高校,开始都是先迁到长沙,其中一些院校因为校舍不够而分散到衡山,衡阳的酒店包括粤菜馆还曾成为他们的中转站——郑天挺先生就是:“1938年2月15日:七时入衡阳城,先至广州酒家,房屋不足,仍分住于乐园及广州酒家。”常任侠先生则明确说到这些酒店因抗战而兴的情形:“1938年9月23日晚间,乘车赴衡阳,十时抵城。沿途军用交通车辆甚多,并有修理厂。衡山新迁军事机关甚多,城内新辟马路,尚未休整。新开大饭店大酒楼无数,皆是几间臭房子,冠以酒店之名。一小房间,一宿价辄二元。”据湖南省民生日用品购销处出版的《购销旬刊》指出,到1944年4月,衡阳的“酒家已达八十家”,较战前增加八倍,更能说明这一点。文章还说到“广帮的南园酒家、白云酒家、珠江楼”等,惜未及大三元。
——宋·王安石《咏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