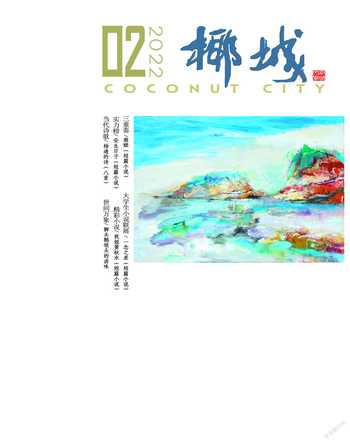残损而又凌厉的记忆(评论)


作者简介:辛泊平,70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诗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秦皇岛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曾在《人民文学》《诗刊》等海内外百余家报刊发表作品并入选数十种选本。出版有诗歌评论集《读一首诗,让时光安静》、《与诗相遇》,随笔集《怎样看一部电影》等。曾获《诗选刊》中国年度诗歌评论奖、河北省文艺评论奖等奖项。
古今中外,以儿童视角书写人生困境与尘世苦难的作品很多,那些作品,也因了儿童敏锐和独特的感受,让生命的重量与灵魂的轻盈格外醒目。从某种意义上说,儿童在人间所受的苦难与疼痛是加倍的。因为,他们的苦难与疼痛缺乏尘世的出口与社会性的安慰。比如契诃夫笔下的凡卡(也译作万卡),那个给乡下爷爷写信求助的男孩儿,比如安徒生笔下卖火柴的小女孩儿,他们的苦难与疼痛注定只能自己一点点承受和消化。慈祥的奶奶在梦幻的天国,宽厚的爷爷在寒冷的乡下。在现实中,他们的痛苦无处倾诉,也无处感受心灵的安慰。也正因如此,面对这类形式的作品,我总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沉重与悲伤。儿童所受的伤害比我们知道的要严重,儿童的孤独比我们想象的要辽阔。读孟薇的《救赎》,我再次读出了这样的印象和感受。
从小说情节的角度看《救赎》,这篇小说是缺乏看点的。因为,它没有激烈的冲突,也没有紧张的节奏,更没有让人欲罢不能的悬念与伏笔。所以,我们不必纠缠于故事的起承转合,不必纠结于故事的逆转与高潮。它只是在写童年的印象,写这种童年印象的背景,写这种童年印象关涉的各种人生。在我看来,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既不是故事的叙述者“我”,也不是其他人,而是一种记忆,是一种模糊的、不完整的但又能映照出诸多人生伤痛的记忆重构。在这种记忆重构中,所有人都没有改变什么,死者依然拥有端庄的面容,沉默的依然沉默,然而,他们又都改变了,因为,在对往事的钩沉中,已经注入了讲述者当下的打量与判断。正是因为有这种时空与感受上的交互性,整个叙事虽然扑朔迷离,但又不是没有头脑,没有章法,而是有蛛丝马迹的关联。
正如记忆的碎片化特征,这个故事从开始就仿佛没有进入一种我们习惯的因果互生,而只是一个习惯性的印象——继祖父儿子冷漠的表情和背影。但读者可以从叙述中推测因果。“我”从何而来?“我”的父母去了哪里?奶奶与继祖父因何种机缘走到了一起?继祖父和他儿子的关系呈现一种什么样的日常状态?“我”对于所有人究竟是一种怎样尴尬的存在?这一切都没有交待、没有解释,也不需要交待和解释。因为,在小说中,核心不是人,而是记忆,是“我”独特的记忆,是“我”对往事的印象。这种记忆隐藏着伤害与不安,隐藏着个体的私密经历和私密感受。所以,它无法按照正常的事件逻辑来展开,只能以打破正常逻辑的形式来呈现。
在这种虽有时空分割但又时有交叉的记忆网络中,每一个出现的人物虽然不构成主题上的打造,但却在不同的层面上完成了一种人生意味的构建。那个拥有海螺的女孩儿,她既是“我”最初的友谊理解,也是“我”对欺骗与背叛的深刻体验。因为,那个女孩儿虽然没有毫无保留地和“我”一起分享那个据说可以听到大海声音的海螺,但她还是和“我”一起度过了许多难以忘怀的时光。在那些时光里,两个孩子可能不会交流成长的心灵秘密,但对一个孩子来说,陪伴便是友谊最重要的部分。然而,就是面对这样一个“朋友”,“我”却没有坦诚以待,而是欺骗了她,背叛了她。当奶奶把女孩儿的海螺藏起来交给“我”时,“我”虽有还回去的冲动,但还是因种种原因,最终还是没有付诸行动。所以,这个曾经让人羡慕不已的海螺,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并非美好的证物,而是变成了最初的罪恶阴影,始终压抑着“我”,让“我”羞愧难当,让“我”无法释怀。
然而,我们无法谴责一个孩子的欺骗和谎言,因为,那欺骗和谎言里隐藏着成长的伤痛与代价,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都不是透明的,它有自己的逻辑和速度,有自己的忏悔与救赎。小说的名字叫“救赎”,其实也暗合了这种来自灵魂深处的裂变与反思。一切都是隐含的,觉悟是,救赎也是,甚至,绝望也是。正如《追风筝的人》中主人公和他的阿桑。当然,这绝不是为一个孩子的罪恶找借口,而是想说,在许多事情上,孩子还缺少理性的判断,他做事的出发点和行事的方式,也许只有原始的感受和原始的好恶。孩子们的世界里没有律法,但有天性。而天性,必须要经过社会的修正才能进入理性的范畴。在此之前,我们只能尝试着一点点理解孩子,一点点走进他们内心深处的暗处。在小说中,“我”对那个死人的印象饶有深意。在尘世的意义上,人们对于死亡是避讳,对死者也是避讳的,除了特殊职业的从业者,似乎没有一个人愿意走近一个遭遇车祸死亡的人,没有一个人愿意近距离地打量他的面容和身体。然而,小小的“我”,却那样痴迷地打量了那个尸体好长时间,并发现了一种不同于活人的端庄与从容,发现了一种有别于尘世的超脱与审美。
可以这样说,这些都是不合常理的。然而,在小说中,它却是成立的。因为,它从另一种意义上呈现了生命的多元与多义,呈现了生命中隐含的可能性,甚至,它还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被尘世遮蔽的罪恶与羞辱。在孩子的世界里,沉默并非无话可说,而是他们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话语去表达,不知道用什么样的修辞去描述。
读这篇小说,我不仅读出了一种残损而又凌厉的记忆,读出了一种被漠视、被伤害的生命的呻吟,更读出了一段童年的孤独与伤口。那种伤口是无法示人的,因为,懂得伤害的时候,伤口已经结了痂,甚至早已不见痕跡。也只借助记忆,那种伤害才会以一种眼神或者一个场景重现。这样的阅读可能不会带来阅读快感,但它注定会是一种阅读体验的沉淀。它需要静下心来,从情节期待中走出来,进入生命深处,进入记忆深处,进入人性深处,在那些地方,倾听来自童年细微的呼吸,并因此降下成人的身段,试着体悟被那些我们忽略但又异常凌厉的关于儿童感受和记忆的点点滴滴。
从总体看,这篇小说有散文化特征,它的语言也是诗意的,主观性很强,但并非一路蹈虚,而是有质感,有落实。也正因如此,这篇小说不仅为读者贡献了许多印象深刻的画面,还实现了一种虚实相互打开、相互印照的蒙太奇语言,呈现了写作的多维开拓与深度挖掘。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些品质,我更愿意把这篇小说当做散文来读。因为,只有当做散文来读,那些痛楚才会更加尖锐,更加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