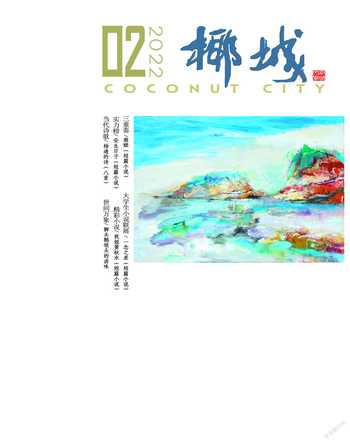安生日子(短篇小说)
作者简介:北雁,原名王灿鑫。1982年生,出版长篇小说《赶在太阳落山以前》等2部,曾在《延河》《中国铁路文艺》《滇池》《边疆文学》《大地文学》《椰城》等发表小说作品50余万字。
一只没头没脑的苍蝇往蜘蛛网上一撞,就被结结实实地粘住了,它立即奋力挣扎,头顶脚踢扇动翅膀,打弹弓一般弄得天昏地暗,却连一根蛛线都没有拉断,最终精疲力竭,就如同失重一般倒挂在网上狠狠地喘气,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躲在一边的蜘蛛出来,轻而易举地拉动几根细丝将自己紧紧缠住。
“傻啊你!明明有张网在前面还你往上撞?”杨水生在树下面的车子里看得真切,不由得在心里嘲笑起了那只苍蝇。可他还没来得及笑出声来,就看到土妹一个人从聚源商务酒店里走了出来。你还别说,穿裙子的土妹身材可真好,挺拔得像似一棵白杨,该凸的地方凸,该有的曲线也绝不打折扣。确切地说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土妹穿裙子,包括结婚那时也没给她买上什么像样的衣服,土妹跟了他这么多年真是受大委屈了。
杨水生不明白土妹一个人到聚源酒店干什么?全梅河的人都知道这可絕对不是个什么好地方。时间还有点早,昨晚又下了一夜的雨,直到现在还漂着些细丝,杨水生也就没有下车。但他也不是刚来,这不一个苍蝇坠网的过程,他都已经完整地看过了。可他之前没有见土妹进去啊!看她抬头挺胸、从容自信的样子,走着走着就摘下坤包掏出镜子,理了理头发又把镜子放回包内,继续阔步往梅河边上走去。
他准备下车跟土妹见面,可人还未动,却看见绍雄的车从聚源酒店出来。没错,那是绍雄的车。绍雄长得牛高马大,所以他那辆块头很大的哈弗H9也就有些笨笨撞撞,通过聚源酒店的地下车库门口时就似一头巨兽,咆哮一声就从地洞里拱了出来,拱到大街上却又变成了一只横行的爬蟹,摆正位置后便加大油门,只留下“呼——”的一声发动机锐响,就在梅河大道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漫天的油雾,好似他郭绍雄那张肥头大脸上时常显露的讽刺与不屑。
一切都不用解释了!杨水生望着绍雄车子远去的影子大声骂道:“臭狗熊,你他妈的欺人太甚!”狗熊是对郭绍雄的骂名。虽然和他在一起,杨水生从未这样称呼过他,但在心里他已经骂过不止一万遍。
确切地说,他的人生就是被绍雄给改变的。在当年的梅河镇街,家里开动力房的郭绍雄毫无疑问就是班里的首富,他自己也能开动磨面机和粉碎机,但在父母面前,顾客留下的加工费,他都会如数上交。但隔三岔五的,他却留得下好几块的“私房钱”,约杨水生逃学,一起来到镇街上买散烟、买零食、买玩具、买炮仗。有一次,两人在买了一包多味瓜子和一包旺旺雪饼之后还多买了一瓶酒。酒瓶上是个身材婀娜的翩翩仙子,于是酒瓶也就和那仙子一般高挑修长,拧开盖子,扑鼻的酒香如同琼浆玉液,绍雄就说喝完酒了会不会和仙子一起飞?
哪晓得一瓶酒却越喝越辣,直待瓜子和雪饼全都吃完,酒还剩下三分之二瓶。丢了吧,可惜。不丢吧,又实在喝不下了。他清楚地记得到了最后,牛高马大的绍雄是把大半杯酒给他直接灌了下去,那动作就如同镇街边角的兽医站给牛灌药一样。但兽医站有兽医站的方法技巧,把牛拉到一个双“h”型的架子中间,让人在下面一拉缰绳,牛头便只能往高处伸去,兽医把牛嘴一掰压住牛舌,就把一个长长的竹药筒直接塞到它的喉部,下面的人依然紧紧地拉着缰绳不放,源源不断的药水就直接倾倒进牛的胃里。绍雄的动作远比兽医粗暴,甚至完全可以说得上是凶蛮和狠毒,杨水生还没有反应过来,脑袋就被绍雄折叠到了脖子上,接着一个瓶子就塞到他的舌头下面,在“咕咕咕咕”的气泡声中,杨水生就只能飞快地转动喉咙,五十度的烈酒如同泄洪一般灌了进去。倾刻间,肚子里就好似被点燃了一串长长的炮仗。他感觉五脏六腑被炸碎了。灼辣、刺痛、尖刻、熬煎,各种难受自内而外地扩散开来。但又扩散不去。一时天旋地转痛不欲生,脚下一个趔趄让他差不多直接摔进了梅河里。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家又是怎么醒的。醒来之后便再不想理他大狗熊了。可他大狗熊却又很快出现在他家门口,许定给他一个报偿,便又把他带出家门,然后两人一起去胡同深处看了一场录相,那时方才五年级的他居然在录相厅里第一次流了白尿。
他一直忘记不了录相厅里污浊的空气。同时隐隐地感觉自己会被绍雄带上邪路。他本能地拒绝他,可那时他被录相里的花哨镜头充斥着大脑,最终却总是拒绝不了。于是他的辍学自然也与大狗熊无不相关。记得那是初一下学期开学的第一天,绍雄吃过午饭就来家门口等他,他迅速扒下两碗饭,揣上学费就和他一起来到学校。哪想第一节课就是英语,坐在前排的他就如同被绍雄灌了酒一般头昏脑胀,转身往后一看,就看到坐在后面的郭绍雄也好似一条即将窒息的白鱼,四目一合,就如同彼此获得了救命的泉流,一双大白眼朝他一挤,杨水生当即会意,两人就一前一后溜出了教室。
绍雄说这次带你见个大世面。杨水生不明就里。跟着绍雄在梅河镇密如蛛网的街巷里转了几个圈,来到一个古旧的老院子里。他方知道里面原来是个民间赌场。没日没夜的赌庄已经从春节一直延续到了现在。杨水生摸了摸兜里的两百块钱,出门时母亲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小心保管。他不反感母亲的唠叨,他知道那一分一厘都是父亲的血汗。所以他当场就反悔了。绍雄说没事,押上一把碰碰运气,没准还会赢。于是两人就在场边拉拉扯扯,还未拉出个结果,大门就被人一脚踢开,“举起手来!”杨水生看到十几个举着枪的民警鱼贯而入,领头那个人还往天空放了一枪。包括看门的老头在内,所有人均无一漏网,场上、地上包括各人身上揣的钱也都被当场没收。
丢死人了!杨水生记得父亲是在冒黑时分,带着哭腔把他从派出所里赎出来的。他从煤矿回来,赶了一百公里路,一身浸透煤灰和黑水的衣服也没来得及换,千恩万谢中从贴身衣兜掏出五十块钱给他交了罚款,还躬着身子把他带回到学校。“逃课、赌博、派出所抓去,这每一条罪状都够得上开除了!”那个被他们嘲弄过不知多少遍的校长,在父亲面前变得威风八面了,他脸如锅底,高高在上,站在面前的父亲却只能低头哈腰,唯唯诺诺,说话间连鼻涕都掉出来了,像极了一条尽情讨好的哈巴狗。杨水生一脸不屑,把头一扭就往外走。父亲让他站住他没站住,追出来就对他一顿打。他没有还手,却也没有回到课堂。第二天一大早,就背上个背箩和父亲一起来到大坪煤矿,每天匐下身子钻矿洞背煤。反倒是绍雄,不知找了什么门路,还一直在学校混到了初中毕业。这就是他的能耐,从小翻云覆雨,左右逢源,回到村里还能五马六猴不可一世,开个H9当个小包工头就可以在梅河坝子里招摇撞骗,换句时髦的话说,就是“家里红旗不倒,家外红旗飘飘”,每年都能把多少女人搂入怀抱。
想到这里,他突然一下子恨起了土妹。“你怎么能这样?他是个什么人你能不知道?再说能耐了你找个有钱的去,开个哈弗H9你就以为他了不得了?”他隐隐地感觉土妹变了,至少已经不再是那个单纯的土妹了。那时刚听到他说要离婚,就哭成一个泪人,鼻腔里发出一声“呜——”,就如同一把烧开的茶壶怎么都停不下。他只好继续把她紧紧抱住。“你……你不……不要我了?”她问。“我怎么能不要你?哥把你搂在怀里含在嘴里,揣在肚子里把你当心藏着!只是哥如今真没路可走了,”他重重地叹了口气,好半天才说,“当然这也只是权宜之计,如果不离婚,那我们连这房子都保不住!”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房子是父亲用命换来的。他告诉父亲,挖煤没有前途,不单高危还挣不了钱。可父亲却骂他眼高手底,我挖了这么多年这一辈子不也过来了吗?他还要申辩,父亲的耳光子就打来了,那是眼冒金星的疼,其中必定还有恨铁不成钢的失望。于是就在父子反目的第二天上午,十五岁的他便揣着堂哥的身份证随着打工大军去了广东,可他却怎么都想不到,一年之后已经漸入佳境的他却只能急火火地回来给父亲收尸了。可他却没看到父亲的尸体,甚至对那一盒骨灰都有太多的质疑。煤老板说天气炎热,害怕引发疫病就把他们直接送火化场了。他们——老板指的是父亲和八个埋在矿洞里的难友。母亲没有争辩,第一个在纸上签了字就领了十二万的赔偿。回来后告诉他说,“这钱得盖房子,不盖出一方漂亮的房子来,你爸就白死了!”
母亲自始至终没落过一滴泪。可当把杨家的那一片房屋拆除,又换成一栋亮亮堂堂的大瓦房后,母亲的头发居然全白了。杨水生结婚那天,她紧紧抱住父亲的灵位,哭天抢地,好不容易被几个妯娌劝服后,她那双明亮的眼睛就再也看不见了。杨水生就此成了这个家的当家人。
“俗话说:蛇有多大洞有多粗,你没那么大的本钱你接那生意做什么?”土妹哽咽着问他。“我这不是想让你,让咱妈、咱孩子都能过上安全日子!”当然他心里想的并非全是这些,他就是看不惯绍雄,从小到大都这么吊儿郎当的,开个什么破车回来,却非要把车停在大门口,让人出不得也进不得。母亲说你侧着点身子不行啊?“我担着粪出去呢!”他恨恨地回答母亲。母亲就说,“能耐了你,读书不成器在家做个农夫,担挑粪出门还风光了?让我给你吆喝着鸣锣开道,让左邻右舍一起让行回避啊?”
他知道母亲虽然瞎了眼,可心里却跟明镜似的。外圆内方,满遭损,谦受益。这是教了他一辈子的道理。可他就是受不住气。两家人就这么做了几十年邻居,可你郭绍雄却欺人太甚,忽一下子把老房拆了接着再盖一个四层楼出来,杨家场院里的阳光都被你全盖住了。接着听了你两年多的建筑噪声,打桩浇灌装修你还时不时地弄出个人工地震,吓都把人吓死。完了冬春干季还得陪你一起飞沙走石闻那刺鼻的油漆味,你不留什么滴檐隔界也就算了,到最后居然还直接把水沟给埋了,七八月雨水一来,杨家场院就成了汪洋大海,有一次还漫上了台阶,你说你这不是缺德吗?
“能耐了你咋不早说呢?能耐了你也盖个大房子,让他们郭家人看看!”母亲的回答让他憋了一肚子气,第二天就放下锄头去了城里。十五岁我就能闯广东我怕什么?年纪轻轻我就不相信做不出事业来。
半年后回到村子他已经被人喊作“杨副总”。带来一个操外地口音的大老板,西装笔挺皮鞋锃亮还戴着眼镜,一撮淡淡的八字胡让人感觉特别地贵气,抽烟时得先掏出个精致的烟嘴,点上火后捏在手里,人们才发现他食指上那颗大钻戒,足有指甲盖那么大,在阳光下面发出蓝晶晶的光亮。那时家里时常人出人进,老老少少对他毕恭毕敬巴结讨好,只求他在大老板面前说句好话,把他们那一份田承包了吧!越是这样的时候,杨水生反而越加小心谨慎,不张狂不骄奢,兢兢业业为老板办事,似乎过了很久,他才发觉绍雄的车不知停哪儿去了。
“现在生意做折了,你拿什么钱偿还人家?”母亲横着脸在一边问他。
“那是老板欠他们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再说市场行情有变化,老板不就是积压了些货,过不久货卖出去了能少他们半个仔?”
“都这时候了你还睁着眼睛说瞎话,几百亩大蒜没有采收,如今都已经烂在了田里。再说村人们只知道是你把人家大老板带来的,现在老板跑了他们不找你要钱找谁要?咱们都是贫家小户,这可不仅仅是一两千块的租田钱和劳工费,还是老人的药费孩子的学费,以及一个家庭一年的指望。更重要的是耽误了人家一年的收种,那可是几百亩良田啊!换作其他年份,能打一百万斤谷子,足够咱们梅河镇街的五千人口吃一年了!”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要紧的是让土妹赶紧随我去趟民政所把手续办了,到时村人们来家里要钱就把离婚协议给人家看,说咱们夫妻感情破裂决定离婚,房子家产都归了她土妹,我净身出户还得负责老人孩子的抚养费,保住这房产她土妹就是我们杨家的恩人!”
母亲终于不说话了。可杨水生却永远忘不了土妹那一脸泪水。若非情已至此,她是绝不会在协议上签字的。恰恰也是对他和杨家的赤诚,让她从此变成了一个泼妇,除了给瞎眼的婆婆留下仅需的生活必备品,她把所有能用的东西都锁到房里,此后再有村人到杨家闹事,她一个弱女子转身就往厨房里拿菜刀。二愣子杨虎就把头往她前面一伸,用手往脖子上一比划说能耐了你就往这儿砍!她丢下刀子揪住杨虎的衣服就往门外拖,杨虎挥手一拨让她摔个踉跄,她就地一瘫便开始打滚,又哭又闹,同时开始解扣子,大叫杨虎非礼了,欺负她寡妇婆娘了,吓得杨虎头也不回一溜烟跑了。
所有这些,杨水生是在电话里听母亲说的。三年多了,他出门之后便再不敢贸然回村。可他还是想土妹了。约好了在什么地方见面,却还要打游击一般鬼鬼祟祟,戴帽子戴墨镜还要戴口罩。土妹可管不了那么多,抱住他就不放手,手劲儿那个大啊!“光许你想人家就不让人家想你了?”说着就是“呜——”的一声尖嚎,依旧还是那壶烧开的水怎么都停不下来。那哪是耍什么小性子撒什么娇?那是真正的委屈真正的疼啊!多少个白天多少个不眠的夜晚,杨水生始终感觉那双眼睛也总在看着他,要不因为这双眼睛,他不被那垮塌的砖墙压死,也会被那沉重的麻袋压死,再或是被那辆疾驰而过的宝马车撞死。三年多了,他像狗一样地躲在那个暗无天日的梅城,呆过工地、管过仓库、砌过砖、当过搬运工、开过货车,在好几次事故中与死神擦肩而过,冥冥之中,他相信那是因为土妹时刻不停地为他祈祷,让他每次都化险为夷。
他说每两个月会给土妹送一次錢,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要和土妹见面。他想土妹,土妹也在想他。哪知这两次见面,他似乎发觉土妹变了,不光衣服鲜亮,还抹口红擦雪花膏,都快变成一个城市人了。是假戏真作还是入戏太深呢?更让他不可思议的是,土妹如今还不容许他动手动脚了,他拉下脸来,土妹比他变得更快,并且当场质问他“我是你什么人?咱们现在是什么关系?你有权把我呼来喊去?没能耐直不起身子还得让我为你这窝囊废受一辈子气还一辈子抬不起头?”气得杨水生恨不能直接扇她两耳光。可他怎可能打她?又怎么舍得打她?她跟你这么多年受过的委屈还少?
杨水生今天起了个大早,冒着昨夜残留的微雨,就从出租房小跑着前去开车,路过梅城大桥时他感觉那风似乎和往常不一样了,呯呯呯呯呯呯,不是连绵不断地吹来,而是以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秒的频率撞在脸上,冷当然也冷,但冷得振奋,冷得激灵,在开车前往梅河的路上,他似乎感觉那风一直不停地撞在挡风玻璃上和他的脸上,一遍遍地告诉他说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他得赶紧把这消息告诉土妹。告诉她从此再不用这么暗无天日了。可在电话里他却没说。土妹说有什么事非得见面说吗?一种爱理不理的腔调。他说必须得面对面亲口告诉她。哪想话还没说甚至人还没见上面,剧情就有了反转。事实摆在眼前,一切都不用解释了。该骂他臭狗雄还是要骂她土妹?总之全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想找把刀学一回武松或是宋江,可他翻遍了工具箱也没找到刀,才忽地感觉自己实在太激动了,便狠狠地抽了自己一个耳光说自己办的这是什么事?抽完后发觉脸角火烧火辣地疼,眼泪也就哗地流下来,便紧紧抱住方向盘哭了起来。他方才想到梅城大桥上的那阵风,是在告诉他一个冷字,好凉好透的一瓢冷水啊!
哭算什么能耐?你一个男人你流起眼泪算什么英雄好汉?骂完自己,他关掉手机发动汽车就来到梅湖边上。太阳照出来了。雨后初晴,万里无云的碧空明净得像是一块纯色玻璃。这真是一个晴朗的天。可杨水生却无心看风景。从离开梅河大道轰大油门开车过来的这一路上他都在咒着他大狗熊和土妹。
他当然不敢把车开到梅湖里,也不敢让自己跳到梅湖里,但他可以把土妹的照片丢进梅湖里。他打开钱夹,掏着那张他每时每刻都带在身边的照片。他要把它撕成粉碎,然后洒到空中,让风一刮,就如同一群远去的海鸥被风带走,消失在茫茫的视线之外。可当把照片放在手中,他却又有多么地舍不得。照片上的土妹真实起来了,一颦一笑都是那个青涩的单纯的善良的真实的土妹。
土妹是他的女人,如同一块肉长在他的心上。他哪能像他的同学和隔壁邻居郭绍雄那样,把女人当作一张照片或是一张钞票说扔就扔,或是轻轻松松地换掉?他缺钱,但他舍不得失去这么个好女人?母亲说绕山河虽然远,虽然穷,但那里的女子就是单纯,肠子里没有什么弯弯绕。能娶这样的女子是一个男人的福气。他知道母亲不是在安慰他。父亲转眼就去了十二三年,但坝子里和城里的女子,他能看上的别人却看不起他。人们也都知道,杨家就空有个亮堂的房子,而且还是杨家父亲用命换来的。于是母亲就把他的亲事拜托给了邻村的张媒公,他在山里有亲戚,时不时地回山里一转,返回时就带一两个山里的女子住到家里,自有那些娶不到媳妇的男人挤破门楣般赶来,中意了留下个介绍费和坝子里或是城里的一半彩礼,就能把人家女子带走。
尽管打了这么多年的光棍,可当时的杨水生却心气很高,根本看不上这样的手段,说难听了就跟人口买卖似的。母亲说不动他。他的偏执与倔强是出了名的。但母亲的叹息声却让他首先想到的是绍雄脸上的嘲讽和不屑。哪想几天过后,居然是张媒公主动把人给带来的。土妹比他小了七八岁,换作坝子里和城里的眼光,她还只是个读书的孩子。张媒公是个信实人,父亲在世时,他俩曾一起钻过洞挖过煤,有一次洞里塌方,是父亲把他拖到外面的。那时父亲的腿也伤着了,爬到一半的时候就爬不动了,他脖子里还存留着一丁点力气,一字一句告诉父亲说老哥你把我丢下吧,否则咱俩谁都走不脱!父亲回答说我骨子从来就少不得一个义字,咱兄弟有缘,聚在一起钻煤洞,要死一起死要生一起生,把你留在地下就不是我做人的原则。说完手脚并用地匐下身子,硬是用一口牙把他从一百多米深的地洞里拖了出来。劫后余生,他一直都把父亲当作生死兄弟。但伤愈以后就只能侧着身子走路了,硬实的父亲却最终死在了地底。
“老嫂子,做人得有良心!我这命是我哥给的,您托付我的事,我给您草率应付了,晓不得哪天在床上一躺就醒不来了,到了下面遇到我哥时我怎么跟他说?”
母亲在那时候把头点得像个小鸡啄米,几若失明的她把头伸到那女子面前看了又看,忍不住赞道,“这女子俊啊!”抹了抹眼角却抹不出眼泪。杨水生这时知道母亲的一双眼睛其实是为父亲哭瞎的。她让杨水生向张媒公磕头致谢。杨水生这时不闹腾了,规规矩矩跪在地上就按梅河的最高礼节,给张媒公行了一次三跪九拜的全礼。他在看到土妹的第一眼开始,就感觉能娶这样的女子已经是他八辈子的福份。我过自己的小日子用得着让谁说三道四?便在心底朝那张脸啐了一口。
“给个窝就行!有口饭吃就行!……”山里的人实诚,土妹从一进门就埋着红扑扑的脸盘,开口闭口都把出门时大人教导的话挂在嘴边。那年山里起了雪灾,地里长不出庄稼,也长不了草,牛马都被冻死了。土妹俨然一个逃荒的孩子,甚至不在乎你有没有房子,一副嫁给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态势,就那么两句话,她就成了杨家的媳妇他的女人。过后杨水生方才知道,土妹原来就是张媒公的亲外甥女,同时还是“他们”之中一个难友的女儿。没有这么多的理由,依他杨水生的条件咋捡得到这么好的女人?可越是这么好的女人,杨水生就越发不能失去,不光单纯,还真实、直率、善良,甚至可以为你改变她的一切。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喝了半瓶酒的杨水生其实还是清醒的。三年来他第一次这么铺张和挥霍了。他本来要学武松和宋江,吃上二斤牛肉再喝上十八碗酒,提上一把刀伸张正义去。但酒是辣的他比谁都知道。说到底他还是心疼钱。他想土妹不是和他假戏真作,而是这么多年被他宠着惯着,惯得出格了。既然这样,我又为什么又不能出格一次?他于是又把车开到了聚源酒店对面。他决心要报复土妹。下车后他摔上门就气咻咻地往酒店赶。梅河大道上的车灯忽闪忽闪,但他却走得肆无忌惮。这只不过是个五千人口的镇子,从小生活在这里,他闭着眼睛都能知道哪家的大门开往哪个方向。这几年为了发展经济修了这么条大道,但路上的车能有多少?
在繁华的梅城街道,杨水生最怕的就是过马路,他如今是个货运司机,他得每天穿梭在梅城的大街小巷。得每天无数次地横穿马路。争分夺秒地上货下货,然后背起货物再无数次地横穿马路。他赶时间,货在路的这边或是那边等他但货主却不情愿等他,或者即便每天都能遇上通情的货主,但路边的摄像头和交警不会对他通融。他不是害怕失去工作,而是怕挣不到钱。他之所以不停地换工作其实也是为了挣更多的钱。只有挣到钱了他才可以养活瞎眼的母亲和一天天长大的儿子,也才可以一次次光明正大地去见土妹。土妹说家里都不紧钱,再说通讯这么方便,实在不行你在微信里发个红包,不用每次都专门回来,还搞得就跟地下工作者似的。但他还是要回来,取上一大迭现金直接送到土妹手里。孩子老人的抚养费每个月是一千,而他给土妹的却是完整的两千。他让土妹每次都当着他的面数一遍,土妹于是也不含糊,一本正经地一张一张地数。直到亲眼看到土妹数清了揣到怀里,他才感到踏实,感到这个女人还真真实实地属于他。虽然一本如假包换的离婚证已经握在手里整整三年,但那都不作数。真正作数的还是他手里那几张货真价实的钞票。
回到梅城,他继续穿行在大街小巷。可他却时常担忧,害怕突然什么时候一辆车刹不住了,就把他重重地撞在地上,或是高高地抛在空中,接着又摔到地上,头就似撞破的汽车油箱咕咚咕咚流血。但他无所畏惧,因为他真的很赶时间。他需要挣钱,而且是加倍挣钱,因为扣除吃喝,他每个月挣四千块还是件难事。所以他只能更加起早贪黑、匆急匆忙,于是这样的担忧果真就成了事实。
那天他扛着一箱货物,和以往一样火急火燎地穿过马路,结果一辆疾驰而来的宝马X5就擦着他身子过去,他一惊,一箱货物就这么摔了下来,并且重重地砸到了宝马车的车头,里面装的是磁砖,“啪——”一声脆响,车开出十几米后就停住了,戴着墨镜的车主慢腾腾地打开车门下来,杨水生以为他可能马上就奔过来给自己一耳光。可他没有,而是从裤兜里掏出一只烟塞进一个精致的烟嘴里,再慢条斯里地点上,手上一颗指甲盖大小的钻戒就在阳光下发着蓝晶晶的光芒。
“老板!”杨水生高兴地直接跳起来,三步并着两步跑过去把他抱住。真是老板。他那点烟的动作和那颗钻戒杨水生一辈子都忘记不掉。
老板知道是他,并且知道当年大蒜市场一个断崖式的跌落,自己失联三年后却给他留下了如此惨烈的际遇,真是有些对不住他了。如今他的生意又重新红火了起来,而大蒜市场也重新火爆了起来。今年的价格甚至还是朝前几年的好几倍。所以他一直想再回梅河让杨水生重新承包土地。没想躲债三年的杨水生不单换了号,人也好似人间蒸发了一般。如今一个巧遇,老板当面承诺会把当年的余款给他,同時加付些许利息,让他赶紧回梅河抢田地,在这个秋后东山再起。
他满头答应。心里却有自己的小算盘。鬼才愿意和你东山再起。只要你把钱款如数给我,让我好生回家和土妹安居乐业,过回以往的平淡日子我就为你烧高香了。他以为老板骗他,哪想老板当天就给他卡上打了两万。于是这个把月时间里,他已经回来好几次了。他就想当面给土妹一个惊喜。可每每话到嘴边,他又咽了回去。因为老板的余款还没有打来。
左盼右盼,今天钱终于到账了。他高兴万分,他想告诉土妹,他从此就无须再那样不人不鬼了。他要和土妹马上到民政所,办完复婚手续再名正言顺地一起回家去,把欠人家的钱款挨家挨户归还人家,告诉村人们说他杨水生不是骗子。哪想他见到的却是这样一种场面。他委屈极了。他决定要报复土妹。一到聚源酒店,他就在一楼酒吧叫了个女人接着开了个房上了三楼。你不仁我不义,这一切都是你逼我的。我凭什么要为你守身如玉?他在心里骂一整天,骂得咬牙切齿。他甚至想找个大排量的摩托车骑上,把油门轰到最大就在梅河大道上一路狂飚,然后把肚子里憋了三年的晦气一起吼出来。
他利索地帮女人脱了衣服。可他却硬不起来了。女人说你到底行不行?他说当然行,可说完了依旧还是那样软巴巴的。如同一条死蛇。女人终于失去了耐心,穿上衣服后他又说行了,可女人衣服刚脱一半他又不行了。女人不看他,感觉很是晦气。他浑身汗水如注,只得扯过衣服掏开钱夹子,抽出一张钱给她。却把什么东西落到地上。女人捡起来一看是张照片。他向女人要女人没给,看了一眼后说,“这个妹子我认识,每天送完孩子就来这酒店收拾卫生。听说他男人欠了几十万后和她办了个假离婚,就自己一个人跑了。她挣到了钱却一直省吃俭用,一分一厘都为她男人还债!那感觉就像童话故事里说的什么补天还是什么填海?可天大的一个漏洞你能补得上?有好几个男人都想要帮她,包括常到这酒店耍钱的包工头郭绍雄,可她却从来不看他一眼!有一天还在楼道里用高跟脚踩了郭大头一脚,直到现在还让人家一高一矮地瘸着脚走路……”
一切都明白了。杨水生羞愧难当,恨不能把头夹到裤裆里。女人又说,“知足吧大兄弟,有这么好的女人,还做什么昧良心的事?”
门不知在什么时候关上了。杨水生像个死人一般瘫在床上。世界宁静得像是静止了一般。他突然感到有几分冷了,拉了拉被子却看到地上有一个撕开了的安全套包装袋,还有一团纸巾,里面包着一条软巴巴的死鱼。要是土妹明早来打扫卫生看到这一切该怎么办?他一下子担心了起来。赶紧起身把这两样东西捡起来扔到卫生间,不放心又捡起来扔到马桶里,使劲放水冲走。他知道自己是妄图毁灭证据。但房间里那么多指纹你毁得掉吗?网上不是常说有公安扫黄捉奸的事?要是把自己也给抓去了那可才是羞八代祖宗的事。他记得他的车还停在酒店对面,即便他没被公安抓住,明早让土妹看到了这些肮脏东西你还能解释什么?
这么一想,他赶紧穿上衣服就往外走,可前台已经熄灯。聚源酒店是个小型的商务酒店,前台兴许有人值班,兴许没有。他想喊人。可刚开口他又打住了,如果喊来些熟人,那不就被抓了个现行?
他借着灯光移动身子,蹑手蹑脚地往另一个方向走去,他知道房子边角是地下车库,他可以从那里像大狗熊的车一样钻出去。他可的脚步声却引来一阵粗壮的狗叫声,附着金属的铮铮回响,原来院子里拴了一条大狼狗,拉动着铁链就要向他扑来,吓得他差不多当场坐到地上,赶紧转身回跑,又回到了三楼。可他却回不去了,刚才走得匆忙把房卡锁在里面了!他在懊丧中却听到了楼上此起彼伏的麻将声,其中还似有似无地飘荡着绍雄充满嘲讽的笑声。一不小心让他遇上了该咋整?或者把派出所招来又该咋整?小时候记忆突地钻进脑海,越发把他惊出一身冷汗。来到楼道尽头打开窗子就利索地爬上窗台。他想从三楼跳下去。可楼下却是密集的电线,如同一张蜘蛛网结在那里。他要那么一跳,岂不就成了那只坠网的苍蝇?
夜已经很深了。他还在窗台上泪流满面。一阵冷风把他吹得浑身哆嗦。他想回去却爬不回去了,窗台那儿挺高的。他打开手机就给土妹打了过去。刚响一下土妹就在那边接听了,“你在哪里了?你不说你要回来吗?怎么还关机了一整天?”土妹又骂又哭,他没有回答,土妹又说“你倒是说话啊?”杨水生哆嗦了一下,终于艰难地向电话里问道:“你难道不知道聚源酒店是个什么地方?谁让你去哪里了?”
“我不是看着你挣钱困难嘛,就想帮一帮你!”
“那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冷淡?”
“没事你老回来做什么?我这不是心疼你花钱吗?”
“你就那么在乎钱?”
“我就想早一天让你把钱还了,回来一起过安生日子!”
2658501186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