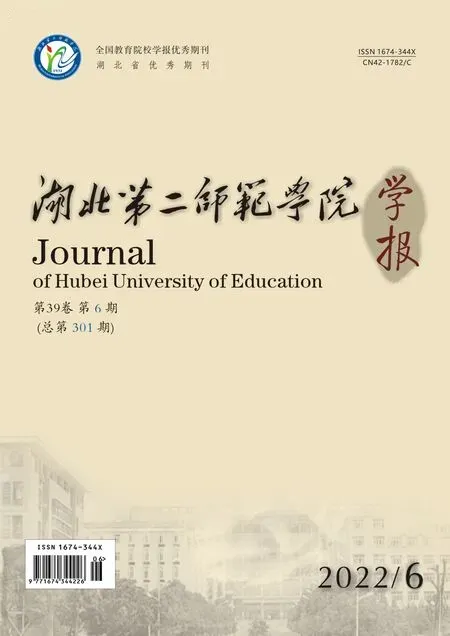国家赔偿的立法、研究的检讨与改进
黄鑫政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21530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开始实施。我国的《国家赔偿法》及其研究,可谓是“形式理性大于实质理性”。此文主要反思《国家赔偿法》的制定、修改及学术研究的不足,并提出未来《国家赔偿法》修改和研究的方法。
一、国家赔偿研究群体的“奇怪现象”
各国国家赔偿理论上的不够成熟必然导致立法的不成熟,进而给各国赔偿制度带来某些混乱。①国家赔偿法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学者们的论文、著作已有提及,不再重复。笔者硕士论文及《刑事赔偿之精神损害赔偿的新方式》[1]亦有相关的分析。大体问题包括:用语不适合,如抚慰金不恰当,应该为赔偿金;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现代立法的高潮时期,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颁布。1995年《国家赔偿法》的制定在1889年《行政诉讼法》制定之后,也在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颁布之后,《国家赔偿法》的制定受民法通则影响,②也受《行政诉讼法》影响。国家赔偿研究绕不开民法,国家赔偿研究对民法、侵权法及其哲学的借鉴几乎是必然的。但理论借鉴来自民法,不代表要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模仿。《国家赔偿法》试拟稿是由行政立法研究组起草的。《国家赔偿法》面临许多需要修改的地方。问题的根源在于立法初始存在不足,之后的修改亦没有能够解决诸多问题。
不少文章重复关于归责原则、赔偿金少的论述。不少教材、文章多用一章或节讨论归责问题,目前,继续进行类似归责方式传统问题的研究,已经过时、多余。归责问题研究是侵权法典型的话题,对归责原则研究的热衷,只是简单的民法到国家赔偿法的“法原理的移植”。国家赔偿就应该讲究“无过错原则”,即以“结果”论责任,以体现国家赔偿的主动性。国家赔偿研究,需要更多的新议题、创新,它有许多待开发的部分。缺乏与冤案防范、人权保护、人格尊严弥补的关联研究。
相比人工智能法学等议题的研究,国家赔偿研究相对冷得许多,这是有些荒诞的法学学术现象。虽然现在研究国家赔偿的教材、文章的亦不少,但真正核心的高质量文章不多。刑诉法学者、冤案防范研究学者不关注冤案赔偿问题,是非常离奇的。相对于行政法学者对行政赔偿、甚至是刑事赔偿的研究,刑诉法学者是严重失职的。宪法基本权利研究的学者、人权法学者对刑事冤案人权侵害及其救济的关注与研究,也是较为缺乏的。宪法学者中,上官丕亮教授出过述评国家赔偿研究的书,刘嗣元教授则有基本国家赔偿法专著、编著。其他宪法学者,较少关注国家赔偿。研究基本权利的学者同样如此。宪法学研究者多没有涉及国家赔偿问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王锴教授研究范围较广,包括了行政法,他有写国家赔偿法的两篇文章。当然,也有其他一些宪法学人研究到国家赔偿。行政法学者多数有研究国家赔偿的自觉,并出版了许多的国家赔偿法教程、教材、著作等。如薛刚凌、马怀德、胡锦光、余凌云、沈岿等。③研究国家赔偿法的行政法学者,还有浙江大学的朱新力教授(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蒋成旭、杜仪方。国家赔偿的研究人员,主力军之一是法院系统的法官,尤其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办和部分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办的人员。《国家赔偿办案指南》是系列的书、成果。研究国家赔偿法必然要关注几位最高院法官的文章、发言,是重要参考材料。陶凯元、江必新、刘合华、何君、刘志远、杨临萍[2]、胡仕浩、黄杰等④。地方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办人员也值得关注:如江勇。浙江高级人民法院是研究冤案赔偿比较突出的地方高级人民法院,还专门有课题组做刑事冤案精神损害赔偿的课题,并出版相关著作。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国家赔偿研究亦比较突出。
我国高校开“国家赔偿法”课程的不多,⑤也没有设置国家赔偿这个专业研究方向,这不一定说明国家赔偿研究领域小,更多的是体现学界对国家赔偿重视不够。人权研究院、人权专业方向的学生,没有关注国家赔偿,没有相应课程作为专业必修课,则是极为荒唐的事情。如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没有国家赔偿的课程,甚至没有相关的教师关注国家赔偿。反而是行政法方向的,可能设置了国家赔偿的课程(由于其国家赔偿立法参与传统,抑或国家赔偿总是习惯性与行政法挂钩)。这亦不甚应该。国内设置国家赔偿课程的法学院极少。另一方面,有一种说法:“赔偿委员会制是立法机关为规避诉讼制而产生的。”⑥赔偿委员会相关规定亦还未成熟,国家赔偿委员会相关规定不充分,缺乏规范、严格的程序、步骤等的说明。国家赔偿不应该限制时效。首先,冤案数量不多,不会达到那种累讼的境地;另外,设置时效是一种不够积极的赔偿态度,意图设置附加条件,增加受害者或其亲属的紧迫义务。甚至可能因此导致该赔偿没有赔偿,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目的。
二、立法及其立法成员组成的不足——后遗症的根源之一
国家赔偿法经过两次的修改之后,许多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足够的改进。但当我们在“疯狂地”批评国家赔偿法的漏洞与不足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追溯国家赔偿的立法,从国家赔偿法的形成和修改情况开始思考,开始研究。这是国家赔偿问题的起源、根源所在。收集资料信息有限、对其他学者的研究了解得有限,笔者更多的是探索国家赔偿法立法的经过,没有能够对两次修改的经过、修改成员等信息进行充分而详细的钩沉、分析。
学者们会追溯外国的国家赔偿法起源,但对我国国家赔偿法的当代立法史(我国国家赔偿法起草至今)却缺少关注、研究。其实我国的国家赔偿法的立法史、修改史对于国家赔偿法的研究非常重要。学者们扎堆批评国家赔偿法的诸多不足,但忘了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经过。肖峋先生的《八十一岁忆人生》一书的第十四章描述了《国家赔偿法》立法经过、行政立法组组成的情况。行政法立法小组当时基本没有刑诉法学者参与。[3]姜明安教授也描述道:“行政诉讼法颁布以后,行政立法研究组紧接着开展了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研究和试拟稿的草拟工作。”并脚注:“中国行政立法研究组于1986年成立,由行政法学者、专家及国家立法、行政、司法部门的实际工作者共14人组成,专门从事行政法的立法研究和草拟有关行政法律的试拟稿,向国家立法机关提出立法建议。”[4]整个立法组织机构不是很精密、成熟。有比较大的随意性。国家赔偿立法是仓促的,人员不够齐全。国家赔偿法的起草团队没有刑诉法学者的加入,体现了国家赔偿法起草团队的先天不足。“眉毛鼻子一把抓”是立法团队组织构成的缺陷。先天不足亦反应在立法团队对冤案赔偿不够重视,未严格区分刑事冤案赔偿与行政赔偿。也许行政法、民法与国家赔偿的“关系的亲近”有一定的原因:《民法总则》第121条规定了公务员对公民侵权需要担负民事责任,而“198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则首次专章规定了国家行政侵权赔偿责任”[5]。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没有类似的规定,也缺乏刑事冤案的专门的法律法规。但行政立法组同样没有吸收宪法学者参与制定国家赔偿法,因此,草拟《国家赔偿法》的行政立法组的人员构成是不完整的。同时,作为一部重要的法律,14 人的行政法立法组,立法组的人数亦过少。《国家赔偿法》作为一部跨越多个学科领域的法律,主体由行政法学者构成,实在有违其学科属性,这些都是国家赔偿法立法不足及后续问题的根源之一。《国家赔偿法》两次修改的人员构成及修改过程,则需要学者们更多地跟进研究、考证。这应该给我们之后的立法、修法带来足够的经验和启示,成为立法教训的典型。虽说《国家赔偿法》的出台与研究,行政法学者厥功至伟,正如他们对行政诉讼法出台的研究推动一样。某种程度上说,《国家赔偿法》是跟随着行政诉讼法产生的。[6]
《国家赔偿法》的起草,受民法影响较大,如“在确定国家承担责任的方式时,就自然地引进了本来是民法上的‘赔偿’等概念和金钱赔偿、恢复原状的赔偿手段。”[7]但国家赔偿法起草的成员中,除行政法学者、民法学者之外的学者几乎没有,导致国家赔偿法的起草的成员构成是先天不足的,遗留下诸多问题。立法的不足,后果与代价相当大,虽不是修改上的“立法者的三个更正词就可以使所有的文献称为废纸”[8],但颇为相同,立法者的一个不足,就可以造成本无必要的许多文献(包括著作和发表的论文等)的必然产生。之后的国家赔偿法修改,也没有能够大幅度改正立法上的问题。语言精细是立法、学理表达精细化的体现,富含意义,《国家赔偿法》在这方面则做得不够。如为人诟病的典型的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需要达到“严重程度”的规定,极为笼统,无法适用。《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应该秉持国家赔偿应有的立法、修法精神,主动、精细。整个国家赔偿法,程序、形式已经被足够注重,实质的关怀与温暖,还需要加强。
三、还原刑事国家赔偿应有的地位
肖峋先生指出:国家赔偿属于公法,属于国家法。“国家赔偿法与行政法有重合部分,但它不属于行政法。”[9]32这点非常重要,指明了国家赔偿法的位阶、地位。极少人有这样的认识与声明,这是肖峋先生的重要见解与呼吁,但被引用、重视、贯彻得不够。国家赔偿法作为一个特殊的法律,相对民法、刑法、民诉法、刑诉法等经典部门法,国家赔偿法条文不多,但意义同样重大,对于人权保障、司法文明、司法公正的意义,更是拱顶石的作用,国家赔偿是人权保护的最后一道重要关卡。
国家赔偿法的模块结构与研究内容,包括国家赔偿法的立法史(尽管时间不长)、国家赔偿法国内外制度历史渊源、“归责原则”(此部分的研究已经饱和,可以国家赔偿以“无过错责任”为告终)、“赔偿方式”(尤其赔礼道歉方式的研究尤其有意义,具体可以参考相关文章)、赔偿资金来源与赔偿程序(此部分形式程序方面的研究笔者亦认为相对其他国家赔偿相关的研究而言无关痛痒)等,即国家赔偿法的“本体论”研究。国家赔偿法研究,还有突出意义的是其与民法的(渊源)关系,国家赔偿法与冤案防范的关系,国家赔偿与法治文化、人权保护、司法文明的关系,亦即国家赔偿法的交叉学科研究同样重要。由于国家赔偿涉及的领域、学科多,因此多元。国家赔偿与人格尊严弥补、冤案死者人格尊严弥补、冤死者公墓制度、人权保护、矫正正义、侵权法原理与哲学的关系、意义尤其重要。包括人权研究者、刑事诉讼法学者、冤案研究者、人格研究研究者在内的研究群体,才是国家赔偿研究应有的景象。冤案赔偿与宪法关系紧密。冤案赔偿关乎政治民主、政治合法性、政治权威,也关乎宪法保障的人权。冤案赔偿应当写入宪法,是孙孝实、李昌麒提出的。[10]但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冤案赔偿是人权保护的应用分支、落实,写入宪法与人权入宪相呼应。人权入宪具有重大法治意义,但需要细化加以贯彻,不然会是一个宏观性条款被束之高阁。宪法用相当的篇幅说监察委,体现着新一代领导人对监察委的重视。相比之下,冤案赔偿在宪法里比重极小,或者说没有,说明冤案赔偿的不受重视。
国家赔偿委员会办公室是最高人民法院下设的一个独立机构,这是正常的。地方国家赔偿办公室设立在行政审判庭,比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国家赔偿办公室与省行政审判庭是同一个机构,一方面没有独立成为一个专门的审判庭,体现了国家赔偿的“依附性”。另一方面,附着于行政庭,就意味着国家赔偿偏行政赔偿而忽略司法赔偿。体现出对国家赔偿认识的不全面,对司法赔偿的忽视。江苏省赔偿委员会办公室与行政审判庭等平行,是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的独立机构。青岛中级人民法院国家赔偿办公室也是与行政审判庭合署办公。⑦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内设机构中,甚至没有能够明显找到国家赔偿办公室。市级中级人民法院,比如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样如此。⑧说明赔偿委员会办公室的机构设置没有统一规定,间接反映我们的国家赔偿还不够规范,缺乏严格、体系的设置,包括其机构设置。这也与我们的《国家赔偿法》实施历史不久,与我们的赔偿方式、幅度不够成熟一致。说明我们的国家赔偿研究与实践,都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学者们常常将国家赔偿和行政赔偿放在一起,如上面所述的体制安排一样,恰可能体现冤案赔偿的尴尬境地:被重视得不够。国家赔偿过于宽泛,冤案赔偿是最准确的提法,用刑事冤案的司法赔偿也是相同,用这类提法的学者不多。[11]就此,当学者研究的是行政赔偿的时候,应该写明行政赔偿,而不是国家赔偿,否则模棱两可地包括了刑事司法赔偿,便是一种混淆,也是一种不清楚的界定,这是学术规范和义务,这点容易被忽略,原因大致是忽视刑事赔偿的存在。总之,建议学者们在写作、立法或法律解释中,明确区分行政国家赔偿与刑事国家赔偿。国家赔偿和行政审判、行政法联系在一起,有一定的逻辑合理性:行政法解决官民矛盾,国家赔偿亦是解决国家责任与公民被侵权之间的矛盾。问题是还有刑事冤案赔偿,这种非财产性的国家侵权,是国家赔偿的半壁江山,因此不宜总是将行政赔偿等同于国家赔偿,甚至一提国家赔偿就只想到行政赔偿。
浙江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办江勇法官说道:“重新评估国家赔偿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全面提升司法赔偿工作的认识”,呼吁“改革赔偿制度,进一步加强国家赔偿立法”。[12]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冯军倡导:“探索将刑事赔偿及其他司法赔偿部分实行无过错责任、结果责任的国家赔偿事项从《国家赔偿法》中分离出来,另行立法”。[13]两个提法赋予刑事赔偿应有的地位,是好的建议。
四、未来的国家赔偿研究及修改趋势
(一)刑事国家赔偿方式需体现更细致的权利关怀
胡玉鸿教授曾言:“权利是个种类不断增加、内容日趋丰富的体系”[14]221。姚建宗教授对“新兴权利”的研究倡导与关注与此可谓不谋而合。[15]权利是个开放的范畴,随着事物、社会发展,必然可能不断增多、扩张。新型权利学说同样是这个原理。国家赔偿范围也就是国家赔偿保护的对象理论上是不断丰富的。也正因此,冤案受害者人格应该同样在国家赔偿的保护范围之内。救济途径包括精神赔偿金的增多,以及精神性的赔偿方式的丰富,比如笔者提出的冤死者公墓制度、冤案反思纪念馆、冤案反思纪念日等。未来国家赔偿法的修改方向,必然需要在赔偿方式、赔偿范围上,不断进步。不断地适时修改,会是国家赔偿法应有的情况。这也是法律富有动态性的体现。国家赔偿只有适合、满足基本权利(包括冤案受害者在蒙冤过程或者被刑讯逼供等过程中受损的人格尊严等权利)的需要,才能更好地充当司法的最后一道防线、更好地预防或减少冤案的发生。冤案的预防,恰好需要国家赔偿的多样式方式,二者相得益彰。国家赔偿的追责其实也是起到冤案预防的作用。冤案预防得越好,国家赔偿的案源也就减少,二者息息相关。过去和当下的国家赔偿研究,只有包括陶凯元、杨临萍等在内少数人员有涉及刑事冤案与国家赔偿关系的研究,国家赔偿与冤案防范,国家赔偿方式与冤案赔偿方式其实有着许多共同的功能和契合之处。笔者倡议的冤死者公墓制度、冤死者纪念碑、冤案反思纪念馆等,就是为了预防冤案,也为了为冤死者而设立的赔偿方式,希望它们能够成为国家赔偿的方式,进而为人权人格尊严保护、冤案防范、民主法治、司法文明作更多的贡献。法律、法治应该以人为本,应该注重人的尊严,“人的尊严是现代法律的伦理总纲”[14]1,弃人的尊严而不顾的法治是虚诞的,弃人的尊严的损害于不保护、弥补的国家赔偿是不充分的。
冤案死者因为刑讯逼供受损的人格尊严是一种未被重视的“旧权利”[16],也是未被重视与发现的“新兴权利”。⑨冤死者因被刑讯逼供而受损人格尊严的弥补极为重要,这是人格尊严理论的应用场域,人格尊严是康德留下来的有待继续的重要议题。⑩国家赔偿法忽视了对人格尊严的保护。民法保护的对象也多是一般的人格权: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荣誉权,侵害则进行“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无法概括到刑事冤案的人格尊严侵犯。人格尊严的弥补[17]是一个巨大、明显的空白。这也是笔者呼吁、研究的重点、难点所在。国家赔偿是人的尊严补救、维护的实践场域。现有的国家赔偿法明确集中刑事赔偿范围,对自由、生命健康等进行了列举式规定,但没有列举到人格尊严的保护,这对于冤案(刑讯逼供“高发区”)来说,这是一个明显的不足,立法的不够精细,权利保护的滞后。
《宪法》第38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国家赔偿法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中权利保障与救济的法律,同样有义务充分尊重人格尊严、保护公民人格尊严。国家赔偿实践及其立法修改,是需要有更多的权利关怀、人格尊严关怀的,体现在其修法理念、赔偿方式之中。国家赔偿与冤案防范的紧密关系也应该更充分被发现、关注、研究。类似国家赔偿构成要件、归责原则的研究与规定,相对于国家赔偿受赔人,具有“防御性”。⑪国家赔偿范围、赔偿方式的丰富与扩张,更显实质法治的内涵、主动赔偿的旨意。
(二)国家赔偿研究的相关议题及其繁荣
国家赔偿与死刑废除的关系、冤死者受损人权尊严死后可弥补、《国家赔偿法》修改理念与实践应该有更多的自然法成分注入、每日冤狱赔偿金增多[18]、丰富国家赔偿法方式等,都是有待进一步加深研究、论证、关注的问题或命题。国家赔偿不应该设置起诉时效,一来国家赔偿案件不多,二来设置起诉时效体现消极态度。取消时效设置可以以体现愿意赔偿的态度,不会导致讼累的情况。《国家赔偿法》的颁布,是国家机关保护公民个人权利免遭公权力侵,促进自身主动承担公权力责任的表现。也因此,国家赔偿法立法修法应该贯彻这一立法初衷。
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法律的颁布是法治进步的重大成就。国家赔偿法各个模块、范畴的细化、权利保护的细化,则是成就加深加大的继续。国家赔偿法及其研究,能够整合更多的法学理论,兼容并蓄,如国家责任(公权力责任、公法责任等)、侵权哲学、权利理论、人格尊严保护等,国家赔偿基本范畴⑫的研究,有理由成为法学研究的有意义的学问。的确,我们的法学研究,该走回学科融合、法学专业方向融合的方向,以更充分地研究、解决问题。国家赔偿、《国家赔偿法》的研究,不应该局限于上文提到的部分学者、法官,可以有更多的学者、法律人参与。遗憾的是,国家赔偿法立法与修改前后,有相关课题招标,但近些年,已极少国家赔偿、冤案防范的课题招标等“政策”激励国家赔偿、冤案防范研究。宪法或国家赔偿法,有必要规定“公务员”违背职责后的责任方式。
注释:
①应松年先生语。参见马怀德.国家赔偿法的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年版,序言。
②这点可以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原副主任肖峋的话来佐证。肖峋是《国家赔偿法》制定的主要参与人。“当初立法未规定精神赔偿,是因为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当时人民的权利意识尚未发展到像今天那样强烈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民事争议也很少有请求精神赔偿的,《民法通则》也无规定,《国家赔偿法》因此未开先河。”最后这句话,体现我国立法的习惯性模仿、“移植”的问题。这也是国家赔偿法的赔偿方式与民法类似的原因,以及规定归责原则的原因。其实,学者的研究也有类似模仿的特点,如对归责原则的研究,以及习惯性对权威学者的模仿。另外,肖峋先生的这句话也体现我们立法为民众意识、社会呼声所“驱使”的现实。
③国家赔偿法的立法与修改,相比于刑诉法学者,行政法学者占多数,如应松年、马怀德等。研究冤案的学者,或者刑诉法学者的集体失语令人惊讶,这本身可能是个问题。毕竟,冤案赔偿的研究,相对于行政法学者而言,更是他们的本职工作,冤案及其赔偿的研究是刑诉法学研究的拱顶石,正如宪法诉讼之于宪法学研究。宪法学学者不研究宪法诉讼、宪法监督便基本是失职、放弃核心义务议题一样。近些年的刑诉法年会很少以冤案作为主题或者分议题之一,笔者认为也是不应该的。这个问题是我们国家赔偿不成熟的一个原因与表现之一。
④法官们的国家赔偿研究往往能直击痛点重点。但研究国家赔偿的学者、法官,很少有从刑事冤案角度出发研究国家赔偿的。杨临萍法官是国家赔偿、冤案国家赔偿研究的重要人物。因此难能可贵。将刑事冤案与国家赔偿挂钩起来的不多,其实这个连接点意义重大。毕竟只有想着预防(国家赔偿的方式也有预防冤案的功能)、善后,才能更好地不再主动发生。国家赔偿的预防功能也是陶凯元法官强调的。
⑤如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苏州大学法学院等都没有开设这门课程。
⑥转引自江必新,梁凤云.国家赔偿法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49-1156页。
⑦青岛中级人民法院官方网站,内设机构情况:http://qdzy.sdcourt.gov.cn/qdzy/394621/394648/548066/index.html.
⑧法院网,组织机构部分。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网址:http://tlzy.china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18/08/id/3455137.shtml.
⑨新兴权利,是对权利本位理念的继承与发扬。近年来,姚建宗教授推出新兴权利的权利范畴,极富有意义。姚建宗、方芳:《新型权利研究的几个问题》,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03期。笔者关注冤案防范与预防和人的尊严,因而注意到了冤案受害者在刑讯逼供或者冤案中受损的人格尊严。认为其中受损的人格尊严是旧权利,只不过一直被侵犯着但未被发现、重视而已。因而也有了新的意味、是“新兴”的权利。这个权利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冤案受害者受损人格尊严的弥补是司法救济的重要环节,是司法公正、司法文明、权利保护的重要环节。同时,能够推进冤案防范、预防冤案的发生、保护人权;另外,该“新兴权利“是人格尊严研究的重要实践场域,可以作为人格尊严研究的关键靶子。具有重大的理论、实践价值。新兴或新兴权利,有两种简单的类别,一种是之前未有而随着科技、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而出现的;也可能正如上文讲到的权利一样:是一直存在着、“埋藏着”,但少为人们所见、未被人们发现、挖掘出来保护,这样意义上的新兴或新兴权利。至于未被发现的原因,取决于人们的发现力、关怀、骨子里重视与否、认识的阶段。近年来冤案逐渐被重视,平反的冤案越来越多。人格尊严同样被越来越重视。冤案过程中出现的人格尊严的损害早就非常严重,并急需被重视、保护、救济。
⑩我国的公法学者、法学理论学者对人格尊严理论逐渐有所关注,如胡玉鸿教授、林来梵教授、上官丕亮教授、侯宇教授、郑玉双博士、白斌博士等的作品。人格尊严研究,与应用挂钩、人格尊严的研究有现实关照(如冤案刑讯逼供受害者的人格尊严保护、弥补)同样是一个重要方向。
⑪整个国家赔偿法,保守的防御性还是很明显的。还体现在《国家赔偿法》第三章刑事赔偿第一节赔偿范围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的情况是列举式却没有”其他有取得赔偿的权利的情况“的规定;而十九条国家不承担责任的情况除了列举几种情况,还有一个”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的第六款作为兜底的“等”。
⑫借用法理学基本范畴、宪法学基本范畴的提法,国家赔偿基本范畴大致指国家赔偿范围、国家赔偿方式、国家赔偿的功能等各个国家赔偿理论核心的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