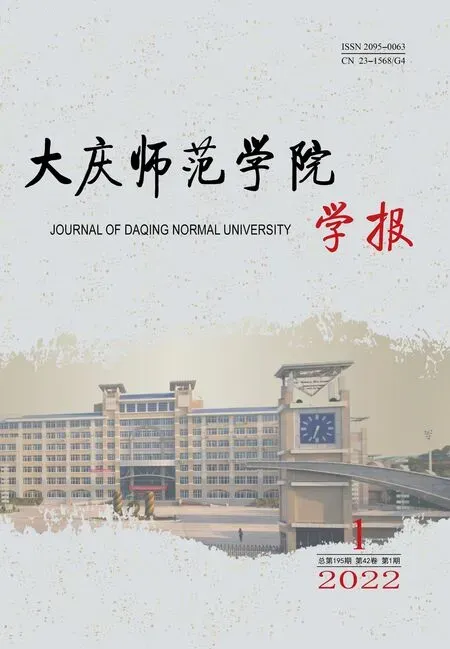世纪之交的山乡文明景象及忧思
——重读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怀念狼》
郁 勤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5;五邑大学 文学院,广东 江门 529020)
百多年来中国不断推进的现代化进程,让中国城乡社会、自然山川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单向发展理念在让中国快速步入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强国的同时,也令中国的自然生态面临着严峻的冲击与挑战,生发了水土流失、工业污染、雾霾沙尘、怪病频发等许多棘手的生态问题,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遭到了重创和撕裂。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始,在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当代许多作家以其丰富多彩的作品做出了意义深远的反思批判,如徐刚、哲夫、李青松等的生态报告文学,苇岸、李存葆、刘亮程等的生态散文,雷抒雁、于坚、郭新民等的生态诗歌,陈应松、郭雪波、迟子建等的生态小说……这些新老作家们纷纷以其多元的作品对全球化语境下“现代中国”的生态危机发出了知识分子的呐喊。
贾平凹作为当代著名作家之一,他的创作多以书写当代中国发展历程中陕西的“乡土世界”而著称。他在其系列作品中对中国现代发展中的迷失提出了自己的忧思,创作于新世纪初的长篇小说《怀念狼》即为其一。《怀念狼》在新世纪之初的出版,让贾平凹的文学生涯与当下生态文明社会的建构加强了联系,也让社会主义中国生态文明社会的建构在面向乡土、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进程中获得了更丰饶的可能性。
一、争议中的商州重返
20世纪中晚期始,世界各国逐步进入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时代。现代科学技术、工业文明让“地球村”的梦想得以实现,也带来了工业文明对传统文化、自然环境的消极效应和负面破坏。西方现代文明国家社会在遭遇一系列生态危机后,纷纷将目光转向传统、转向东方以寻求解决现代文明弊病的良方。然而,中国城乡社会在现代化发展中渐生成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交织的差序文明格局,生发了一系列不同面向的中国社会问题。
中国乡土社会的现代转型、发展及相关问题成为现当代作家们始终关切的书写之旨。向来与大自然关系最为密切的乡土社会,在百多年来的现当代文学书写历程中多以落后蒙昧、蛮荒颓败等“被启蒙”的形象呈现。鲁迅在《呐喊》《彷徨》等小说集中就阿Q、祥林嫂、闰土等老中国乡土大地上沉默灵魂的勾勒,在对“从来如此就对吗?”“救救孩子”的呐喊中开启了现代知识分子对宗法制乡土中社会问题的现代批判潮流;同时,由周作人、废名、沈从文等一批富有传统文人意识,对乡土大地饱含深情的文学家们笔下,则浸润了其对田园乡土风土美、风俗美、风情美的“桃花源”式想象。启蒙批判与唯美抒情,构成了百年来现当代文学对传统乡土社会的两极书写传统。
世纪之交,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不断推进,乡土社会中的人与自然承受着越来越多、日益严峻的现代病症。“先发展后治理”“边发展边治理”的发展观,令中国社会产生了许多摧毁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行为和后果。据《200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中国七大重点流域地表水有机污染普遍,各流域干流有 57.7%的断面满足Ⅲ类水质要求,21.6%的断面为Ⅳ类水质,6.9%的断面属Ⅴ类水质,13.8%的断面属劣Ⅴ类水质。主要湖泊富营养化问题突出。”(1)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环境保护》2001第7期,第3页。许多河流污染严重,水资源的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新世纪以来,中国乡土社会的人居环境、自然生态遭受了更严重的毁坏,许多省市地区的森林草原锐减、部分山体水土流失、大气河流污染、温室效应等各类生态问题频发。据《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2014年)可见,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 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 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 11.2%、2.3%、1.5%和 1.1%。(2)参见环境保护部、国土资源部:《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2014年4月17日),http://www.gov.cn/foot/site1/20140417/782bcb88840814ba158d01.pdf。大范围的地下水和土壤污染,使乡土社会中的相关居民承受了单向工业化所带来的身体健康代价,如相关报道中可见环境污染导致的“癌症村”也相对增多,“截止2010年有大约459个“癌症村”遍布全国,而农村的消化系统癌症远高于城市,癌症高发与水污染存在着直接关系”。(3)章罗储林:《“地球一小时”之外,如何拯救地球?》(2018年4月4日),http://nanduguancha.blog.caixin.com/archives/178707。现代乡土社会的各类生态问题日益尖锐,国家政府在持续有效地推进环境污染治理的各项工作,这也引发了当代文学界许多优秀作家的关注,贾平凹即为其一。
作为一位勤奋高产的当代知名作家,贾平凹近些年间有影响力的十多部长篇小说常有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表现,如《浮躁》《病相报告》《高老庄》《怀念狼》《秦腔》《高兴》《带灯》《老生》《山本》《暂坐》等作品纷纷激发了学界、社会的讨论与热议。这些作品对不同时期中国社会的各类问题给予了反思、批判:《高兴》的农民进城、《古炉》的人伦悲剧、《秦腔》的乡村破败等等。长篇小说《怀念狼》在新世纪初的出版,是贾平凹对自己文学创作的新尝试,开启了新世纪以“动物”为题材的生态文学新格局,更融入了他对现代中国、现代乡土发展问题的反思与批判。
贾平凹笔下的《怀念狼》以城市文人“我”(子明)与山乡猎户舅舅(傅山)、烂头(穆雷)三位男性成员组成一支商州野狼普查调研队为叙事中心,讲述了野狼调研队对野狼族群从“生态保护”到“人为灭绝”的荒诞经历。作品通过“我”所率领的这支野狼调研队在乡野山头的活动轨迹为情节主线,辅以各类灵异事件、乡野传闻、风土人情,在有限的时段空间内向读者谱写了一曲局限又广阔、具体而抽象、清晰又混沌的乡土悲歌。出版于新世纪之初的《怀念狼》,在贾平凹的系列长篇创作中颇显扎眼,学界大多认为该著是一部风格怪异、题材另类的作品,由此对该作品的批评褒贬不一。
总体而言,学界对该部作品的思想艺术的批评主要呈现为正面美誉和负面恶评的两类。批评家李建军的相关批评可为对该作品持“恶评”倾向的代表,他认为:“这是一部消极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文本;它的基本性质是虚假和苍白,它的叙述策略上的突出特点是拼凑和编造,而它对读者的态度则是戏弄和缺乏平易待人的诚意。它是一场游戏……”(4)李建军:《关于文学批评和陕西作家创作的答问》,《文艺争鸣》2000年第6期,第28页。“又读了一遍《怀念狼》,是第三遍。三次阅读一本乏味、 粗糙的失败之作,颇有些自虐的倾向……《怀念狼》炒得很热,卖得很火,是‘一种怪现象’,是‘文学腐败’的一种典型样态。”(5)李建军:《消极写作的典型文本——再评〈怀念狼〉兼论一种写作模式》,《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第45页。秉承现代启蒙理性精神的批评家李建军,对《怀念狼》中所蕴涵的荒诞怪异生态主题并未多做关注,认为该部作品存在神秘化、趣味化、游戏化的弊病,因而予以了“棒喝”。但另一些批评家则鲜明地肯定了《怀念狼》中显然的生态主旨:“作为一部带有明显象征化寓意的长篇小说,如果我们可以把小说中的‘狼’看作是大自然的某种象征的话,那么,贾平凹的《怀念狼》无疑就可以被理解为一部表现着强烈生态观念的生态小说。”(6)王春林:《对“中国问题”的关切与表现——贾平凹新世纪长篇小说主题论》,《创作与评论》2014年第8期,第6页。“《怀念狼》则从环境衰变与狼的消失中,看到了没有对抗和竞争就没有了生命力与创造力的可怕,怀念狼是怀念着勃发的生命,怀念英雄,怀念着世界的平衡。”(7)黄大军:《承受空间之重:贾平凹长篇小说的救赎美学》,《当代文坛》2018年第2期,第78页。长期以来,当代学界对贾平凹及其系列作品的批评研究存有争议,前有《废都》引发了轩然大波,诞生于世纪之交的《怀念狼》又一次触发了学界的敏感神经。学者丁帆的解读对《怀念狼》文本阐释的丰富性又增添了新的可能性:“站在世纪之交的人生十字路口上,贾平凹的小说 《怀念狼》用危言耸听的字眼,为人类生存的境遇指出了一条哲思的道路,既不是宣扬生态环境保护,又不是为了营造一个人类英雄的神话,那么,他是在返归大自然的路途中为人类寻找新的路标吗?!”(8)丁帆:《新汉语文学的尝试——怀念狼阅读断想》,《小说评论》2001年第1期,第48页。
从学界对该作品存在的争议可见该部诞生于世纪之交的长篇小说所带来的深远影响。《怀念狼》的内容、形式、风格迥异于贾平凹其他时期中的作品。世纪之交的中国乡土社会让作家究竟要表现什么?贾平凹在创作后记中向读者流露了他的心声:“《怀念狼》里,我再次做我的试验,局部的意象已不为我看重了,而是直接将情节处理成意象。……面对着要写的人与事,以物观物,使万物的本质得到具现。”(9)贾平凹:《怀念狼》,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第271页。在面对批评家对《怀念狼》中存在“概念化”、“理念大于形象”、过重“情节象征”而忽略人物等的批评时,贾平凹为这部作品辩护道:“在我认同和接受西方近现代以来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念的时候,我总是要寻到一种符合中国作派的语感与形式……这是另一路的写法。每一路数都有它的长处和短处,用这一路的写法去套另一路作品是会出现难堪的。”(10)李遇春、贾平凹:《传统暗影中的现代灵魂——贾平凹访谈录》,《小说评论》2003年6期,第24—25页。由此,可以见出《怀念狼》仍延续着贾平凹立足乡土、面向现代、拷问人性的艺术传统,但又蕴藉了作家对其创作“惯性”的突围意图。中国传统人文生态思想与西方现代生态批判精神的融合交融,汇集在贾平凹对乡土世界现代转型的新颖书写之中,“《怀念狼》包含着作者对整个文明的思考,尤其是在新的语境下对中国乡土社会现代文明进程的深度反思。”(11)刘一秀:《传统与现代的纠结:贾平凹长篇小说创作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2年,第49页。综而观之,这部作品的皮色品相及学界、社会多方的争议倒让乡土社会的“生态应然性”的题旨及相关命题不致被湮没于社会发展的尘埃中。
二、“以实写虚”:面向本土的生态叙事
“月光下东城门外黑压压一片,所有的狼眼都放着绿光,开始了叠罗汉往城墙上爬。”(12)贾平凹:《怀念狼》,第4页。《怀念狼》开篇即向读者勾勒了一个人狼对抗、惨烈紧张的历史场景,对商洛地区方志野史的详尽叙述、环境风俗的渲染,读者很快似又感受到了熟悉的“商州”氛围。然而,这次贾平凹笔下有“狼”史的商州,让故事更加玄奥神秘,弥漫着浓厚的野史遗存和血腥气息,狼灾匪患拉开了商州地界上人与自然、人与人的艰难生存史;化用“以实写虚”“以物观物”的民族传统叙事技法,编织了一个充盈着暴力与血腥、征服与和谐、神秘与庸常、圣洁与污秽、人间与万物同在的山乡日常世界。
“当今的中国文学,不关注社会和现实是不可能的,诚然关注社会和现实不一定只写现实生活题材,而即使写了现实生活并不一定就是现实主义。”(13)贾平凹:《怀念狼》,第270页。贾平凹对现实的热衷,大概与他的人生与新中国大致同步密切相关。他多年来的生活、创作大都与中国发展的各类现实问题紧密相关。他的成长轨迹中也折射出了其作品与中国乡土、现代进程的隐秘关系。贾平凹生于20个世纪50年代初的商州丹凤县棣花村,文化大革命中沦为“可教子女”,70年代初偶然性地进入了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定居于西安,从事文学编辑、写作工作。当代中国的大小事件、风波,贾平凹或远或近地参与了,对80年代和90年代的当代文坛而言更是意义深远。从乡土到城市,从农家子弟上升为知识分子阶层,从普通到盛名,从个人成长到时代社会,从革命斗争到经济建设……地域、时代、民族,才情禀赋、人生际遇,这些由内及外、大大小小的诸多变迁令贾平凹对乡土社会的体察把握有了许多同时代作家不具有的多重资源、更多自由。“人对自身在世界上的生存境遇的体验, 总要在特定的符号表意方式中表现出来, 这就构成审美表现范型问题。”(14)王一川:《“全球性”境遇中的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第23页。从现实世界出发向着更高的灵性境界,让日常生活的鸡零狗碎成为通向意象意境的圣物,从皮囊肉身的红尘翻滚中现出神灵的虚静恒常,对“言外之旨”“虚实相生”的民族叙事传统的参悟,让贾平凹近些年来的叙事逐渐生成了“以实写虚”“以物观物”的审美范式,并在《怀念狼》写作中通过对主旨生成的试验有了更魔幻的表现。有批评家提出:“这部小说的新意最鲜明地表现在对非现实的、‘虚’意因素的充满幻想和夸张的、恣肆任情的表达上。……魔幻性却是〈怀念狼〉最显眼的文本特征,是它的创新性和探索性的主要体现”。(15)薛琳:《〈怀念狼〉与魔幻性》,《外国文学》2002年第2期,第75—76页。魔幻化的叙事令《怀念狼》的生态主旨在当代多为清新优美的生态书写中显得怪诞另类,这也让认为《怀念狼》题旨暧昧、语义含混之批评得以坐实,然而作家对现代化进程中以“人与狼”关系在魔幻迷离的意象化叙事氛围下来推动作品中“显性生态主旨”的生成是否有更深广的意图?“坦率地讲,认为‘怀念狼’是‘环保文学’,多少有点望文生义,缺乏对文本的细读以及对贾平凹写作逻辑的把握”。(16)黄平:《贾平凹小说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1页。笔者也以为贾平凹在这部作品中欲借“生态”之名,而凸显乡土的现代困境之实。在生态环保的表象下,他对中国乡土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衡病变有着更多的忧思。
文本中猎人(傅山等)与狼(15只狼)相生相克的现实关系凝结为贯穿全篇的主体意象,让“生态环保”的所指牵引出如城乡挤压、身份认同、文化归属、性别冲突、种类压迫、阶层政治、贫富异化、生命苦难、边缘中心、天人相悖等更丰富多元的隐喻能指。该如何审视《怀念狼》中“以实写虚”的意象化、魔幻化叙事转向?有批评分析道:“这或许是作家对新近乡土现实把握的无奈,或许是作家无法抵御意义的诱惑,乡土对于他而言有着更多、更深的文化思考和意义承载。在这种创作冲动下,贾平凹开始‘腾空而起’了,在小说中开始意象化的营构。”(17)胡功胜:《贾平凹乡土书写的反比定律》,《宁夏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第190页。贾平凹试图通过对现代乡土的意象化书写,在互文交涉的多元主题映照中让各类风俗风情、传说歌谣、饮食污秽、男女性事等各类物象的营造使得文本题旨愈加醇厚绵韧。“物象作为客观事物而存在着,存在的本质意义是以它们的有用性显现的,而它们的有用性正是由它们的空无的空间来决定的,存在成为无的形象,无成为存在的根据。但是,当写作以整体来作为意象而处理时,则需要用具体的物事,也就是生活的流程来完成。”(18)丁帆:《新汉语文学的尝试——怀念狼阅读断想》,《小说评论》2001年第1期,第50页。在该小说中,贾平凹进一步对生活细流的“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意图为中国乡土世界保留一个‘肉身’。”(19)杨辉:《“大文学史”视域下的贾平凹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3页。贾平凹意图重构商州乡土社会的日常性、驳杂性、地域性,此地非彼地,风土人物、山乡景物等“闲笔”不仅是烘托渲染,更是增添乡土真实感的触角;那些插入摇曳的乡野传闻、生老病死等“闲笔”点缀在主线主事主要人物之外,夹叙诸多旁支杂事,回归乡土生活世界的琐碎芜杂、平庸丰富。文中汪老太的葬礼牵引出狼孩事件、生死观,刘家坝的逗留牵引出金丝猴幻化为女人的报恩、捕狼队成员成义的获罪及与傅山的恩怨、杀人恶魔尤文的传闻,生龙镇的租房引出舅舅惩戒郭财的贪欲犯法……学者陈思和以为“法自然的现实主义”是贾平凹小说笔法的重要特色,对“自然”的崇尚与亵渎暧昧交织,《怀念狼》的含混主旨也正是他对乡土世界从清新走向混沌的持续转向之表现。
商州方志史实记载的狼祸匪患在文本中凝聚为万物生灵与文明社会、现代发展间关系的历史隐喻。狼,与人同为生物链上的高级哺乳动物,人狼之间在进化之路上却渐行渐远:人类从爬行到直立行走、从丛林走向平野,以不同阶段文明的尺度建构人性的同时,建城筑寨、修城起屋,不断剥离、祛除内在的兽性;狼则始终匍匐于动物本能,但始终与人类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中国的古代思想中早有质朴的宇宙自然、万物有灵的生命意识。“《周易·系辞上》:‘一阴一阳谓之道’,作为‘生之道’,作为阴阳化成之道,必然生成并繁育万物,运演宇宙自然的无限广大。”(20)盖光:《生态批评与中国文学传统:融合与构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229页。《周易》的生态理念包涵阴阳交合、刚柔相济、动静有常等内蕴,而文本中主要人物之一烂头一路上的艳遇、纵欲经历窥见贾平凹对原始生命强力、自然人性的肯定。而小说中的烂头对神秘宝石“金香玉”的敬畏感,又可见到古人的万物有灵论宇宙观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人类的自大心理和贪婪欲望,维护了宇宙生态系统的平衡。《怀念狼》中无论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我”还是民间百姓都认同万物有灵论,并进而生发出对生命轮回、死生有命、天人感应等思想。文本中多处可见叙述人“我”对万物有灵的感悟:“在飘浮中遇见一只蜜蜂将一棵草木的花粉掺和于另一棵草木的花粉时,那灵魂就下注,新的草木就产生了,而当这新生的草木最后死亡了,灵魂又飘浮于空,恰好正碰着一只公猪和一只母猪交配,灵魂又注下,新的猪就产生了。”(21)贾平凹:《怀念狼》,第24页。作为乡土人物的代表——舅舅傅山,更持有万物有灵、天人感应观:“天上掉一颗星,地上就要死一个人的,这么多的星星在落哩,这是要发生什么灾难吗?”(22)贾平凹:《怀念狼》,第50页。于此,小说对乡土社会中的原始思维、民俗传统仍然富有坚韧的生命力予以人物心理、语言的灵活呈现。中华传统文明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把天地万物与人视为一体,反对把人类游离于自然之外或超然于自然之上,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共同生存与和谐统一。中华文明提出了道法自然、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的思想。对“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文化传统中所蕴涵的生态理念,《怀念狼》以魔幻的意象化形式、能指的生态主旨加以了征用表现和承继转化。
贾平凹在《怀念狼》中生态性与艺术性上兼具的书写,对“以实写虚”“以物观物”笔法的征用试验,让《怀念狼》作为贾平凹在新世纪初的文学创作,在内容主旨、笔法风格等层面推进了生态文学面向民族化的向度。这也让一些学者鲜明地提出应将贾平凹及其作品置于生态文学的视域中:“在笔者对当代中国生态文学持续十余年的阅读视野中,于坚、雷平阳、张炜、韩少功、叶广芩、贾平凹、姜戎、迟子建、胡发云、陈应松、雪漠、阿来、徐刚、苇岸、刘亮程、李存葆、 李松涛、过士行、杨利民等作家,都已经确立了较为自觉成熟的生态意识,进行过相应的较有影响力的生态文学创作。”(23)汪树东:《当代中国生态文学的四个局限及可能出路》,《长江文艺评论》2016年第4期,第20页。处于世纪之交的贾平凹,以《怀念狼》的意象化、魔幻化书写,为生态文学的多元可能奠定了更扎实的基础。正如研究者所言:“贾平凹在《怀念狼》中的创作思想是‘以实写虚、体无证有’。他的‘实’或叫做‘真’其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叙事内容和叙事氛围的真实性的强调和渲染上;二是对作者关于世事人生的认识的传达上。”(24)薛琳:《〈怀念狼〉与魔幻性》,《外国文学》2002年第2期,第80页。尽管学界关于该部作品的成就得失存在诸多歧义,但不容置疑的是在作品中能窥见生态文学朝向当代中国乡土的面向与路径。
三、生态山乡的可能:人的维度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家政府的发展观处于不断调整修正、转型重塑的状态。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从国家到地方的生态环保法制建设力度不断加强,推进实施力度日益增强。从早期的粗放式、耗能型、密集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到而今转向以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为主的高科技工业的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新发展理念更写进了党章和宪法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着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25)《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017年10月24日通过, https://www.12371.cn/special/zggcdzc/zggcdzcqw/,2021年8月15日。“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6)《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三十二条》,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2018年3月11日通过,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 /politics/2018lh/2018-03/11/c_1122521235.htm,2021年8月15日。新世纪以来,诞生了一系列有关增强贯彻生态环保的法律条例,重塑了当代中国的发展观及国人的观念行为。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中可窥见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重要转向:作为后发国家,我们既要发展进步又要生态和谐。从国家政府对乡土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指导中,似可窥乡土的现代化路途中“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关系及问题曾存在不和谐的现象。长期耕耘于乡土文学的贾平凹,对中国乡土发展中各类问题的熟稔洞悉,让他得以在新世纪之初率先推出了《怀念狼》这部作品,从而引领了新世纪生态文学基于乡土历史和实践的“乡土文明的生态转向”思潮。
贾平凹自1998年的《高老庄》起,已很注意表现“自然乡土”中的社会日趋凋敝颓败的现代景象。及至《怀念狼》等作品中,读者发现他对乡土社会和山野自然的丑陋粗鄙、原始狂野有了更多大胆出奇的书写。正如闻一多先生在《死水》中的诗句“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所抒发的,《怀念狼》中的乡土山野、人与狼等其它生灵,在贾平凹衔接古今的笔端下多以丑恶的、病弱的形象出现,让“田园牧歌情调”的自然乡土社会分崩离析。究其原委,笔者以为这与“自然生态的破坏、社会生态的危机和文化生态的衰颓,说到底是由于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的精神生态失衡引起的”息息相关。(27)王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当代西方生态思潮的核心问题》,《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第45页。其次,作家本身的“中年心态”也促成了作品中“乡土审丑”和“万物平等”意识的生成:“四十岁以后,我对这个世界越来越感到了恐惧,我也弄不明白是因为年龄所致还是阅读了太多战争、灾荒和高科技成果的新闻报道。如果我说对人类关怀的话,有人一定会讥笑我也患上了时髦病而庸俗与矫情,但我确确实实地如此,我甚至产生过我为什么生而为人呢的想法,若是别的,譬如一块石头,一棵树多好。这种意识曾一度很强烈,我看石头和树都好像是人变的,将凡是有生命的万物都视为一致,没有了高低贵贱区分。”(28)廖增湖、贾平凹:《贾平凹访谈录——关于〈怀念狼〉》,《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4期,第89页。《怀念狼》以狼的物种灭绝、雄耳川的村民们群变为“人狼”事件折射出“自然乡土”社会在融入当代生态文明社会建构中可能存在的“阿卡琉斯之踵”,小说结尾更通过主要人物“我”——“可我需要狼!我需要狼!”的声声呐喊中表露了作家的人文警醒和乡土忧思及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
现代西方社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二元偏误以致“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日益膨胀,人类对自我主体性的极度张扬,对大自然的挑战征服带来了现代社会物欲横流、纵欲无度等病象,健康合理的人性渐渐迷失,曾经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被破坏:“大自然向人类敲响了警钟:臭氧空洞,温室效应,全球变暖,物种灭绝,资源枯竭,大气污染,人口爆炸,土地侵蚀和沙漠化等等。这些现象已经严重地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迫使人类不得不回顾历史,反省自己,反思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发出‘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的无奈的悲叹。”(29)陈茂林:《质疑和解构人类中心主义——论生态批评在文学实践中的策略》,《当代文坛》2004年第4期,第33页。人类对“自我”历史的智性批判,让人类获得重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可能。卡西尔也提出“人”存在的意义在于“人”能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道德主体:“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批判态度中。……正是依靠这种基本的能力——对自己和他人作出回答(response)的能力,人成为一个‘有责任(responsible)’存在物,成为一个道德主体。”(30)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8—9页。在挣脱了神权束缚后的近现代、后现代人类,不断突破传统人伦道德中的禁忌,在获得人性极度解放与自由的同时也带来了人与自然关系处理的失衡问题,进而引发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不和谐。发端于自然和社会领域的生态危机,映照出现代人类精神世界的困境。
对乡土社会的发展与现实有独到体悟的贾平凹,敏锐地捕捉到了商洛山乡在现代化进程中因生态失衡带来的人类精神失衡危机,并将其通过人与狼的关系表现出来。小说中,作家通过捕狼队队长傅山及成员、村庄山民的各色刻画和言谈行为中,对乡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反思与批判。文中主要人物捕狼队队长傅山——“我”的舅舅,执拗地固守“猎人”与“狼”之间非此即彼、不可共生的二元论,认为“猎人”身份的意义只能是狩猎。这种意识将人生价值目标的实现建构在人与狼对抗斗争的基础之上,认为猎人的存在就是为了消灭猎物,否则便不是猎人。他坚持认为:“人见了狼是不能不打的,这就是人。”(31)贾平凹:《怀念狼》,第76页。傅山的这种顽固的“人类中心主义”意识有其形成的历史缘由与主观因素。从人类的发展史上而言,前现代社会中狼群的过度繁衍曾一度威胁到乡土人的正常生存,为了维护人类自身的基本生存,人对狼的猎杀具应然性。可是,当人类步入现代社会后,狼已濒临灭绝之境,对人类的生存已构不成威胁却仍固执地坚持“见狼便灭”的潜意识,此即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在作祟了。傅山及其他猎人,固守传统一味认同自我作为猎人的身份,认为狼族等非人类动物是受排斥的“他者”。小说中傅山周围的山民们大多与之类似,秉承有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对世界其他物种多抱有功利性、工具性、价值性的意识。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后现代思潮中涌现的生态思想,对现代社会中的“人类中心主义”给予了多向度的反思和批判,并进而提出了人际伦理与种际伦理关系的思考。于此期间,彼得·辛格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动物解放”强音,进一步对人类文明进程中以人类为中心的狭隘生命伦理所产生的“物种歧视”及人类加诸于同类和其它物种的恶行进行了深入犀利的批判和否定:“……那种哪怕只要有一点微小理由就进行屠杀的动物,其实就是人这种动物。我们认为狮子和狼凶残,因为它们杀生,但是,它们要不杀生就必定挨饿。而人屠杀其它动物可以只是为了运动娱乐、满足好奇心、装饰身体和享受口味。人类还因贪婪和权力的争夺而自相残杀,何况人不以屠杀而满足。从整个历史来看,人不论是对自己的同类成员,还是对同为动物的非人类动物,总是喜欢在处死对方之前加以虐待或折磨,这种行径是其他动物所没有的。”(32)彼得·辛格:《动物解放》,祖述宪译,青岛:青岛出版社,2004年,第204页。同在地球这颗星球上,人类与地球上的所有生命物种一样,都有各自存在的权利和自身的价值,应有建构“命运共同体”的可能性。人类和所有非人类的动植物生命应只有生态序列的差异,就整体有机生态圈的构成而言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中国道家“法自然”的思想对贾平凹对万物生命的认知有深远的影响,因而“丑陋”“怪诞”“病残”“异形”等非主流的人类形象和行为屡见于其20世纪90年代的作品中,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生发也推动了他对传统乡土社会从原始自然到生态文明的转向。《怀念狼》在商州的城乡山野中,各色人类和被人类圈养驯化的动物仍大多以病态孱弱、怪异残缺的形象登场,但狼等非人类野生生灵则洋溢着充沛的生气和奇幻的魔力。从乡土移植到省城的叙述者“我”,文人式病症日趋严重:荷尔蒙的匮乏、口腔溃疡和痔疮等令“我”日感作为男性的无力;大熊猫基地中艰难出世又旋即一命呜呼的大熊猫幼崽及难产而亡的母熊猫;捕狼队全体成员的各类怪病频出:主要人物“我”的荷尔蒙衰减、舅舅的“软脚症”和烂头的“头痛病”;其他次要人物也都病怏怏:大熊猫研究基地黄研究员的“精神病”,生龙镇老头的“健忘症”,老道士的晚期肝病……弥漫的“疾病”,隐喻了乡土社会原始生命活力的匮乏和现代城市物欲的挤压。从身体到精神,整篇小说中几乎没有健康的人类男性人物形象。“疾病”蔓延在商州乡土社会上,曾经健硕壮美的乡野而今毫无生机。“疾病”化的自然乡土人类暗示了乡土社会步入现代文明过程的不适应,现代城市文明的挤压、侵蚀最后会异化和规训乡民们健全的自然身躯与灵性生机。以狼为中心的非人类物种生命状态与人类的病态退化形成了鲜明对照:狼皮可以与其同类发生神奇的感应场,野狼拥有了幻化人形、奇门遁甲、驾驭其他物种的超能力,狼有与人沟通交流、知恩记仇的“人类化”情感思想。在文本中,野狼所洋溢的灵性、野性及魔性,照见出人类文明社会进程中人类生命活力的匮乏和危机。对狼族生命强力及悲剧命运的魔幻书写中,照见重构“人与自然”关系的前途:“如何解决人与自然之间‘人类中心主义’的问题,从《怀念狼》来看,贾平凹显然倾向于‘人的自然化’。‘人的自然化’所指的是把人视为组成自然界的一个部分,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它反对人类对自然的强取豪夺,他反对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无节制的利用,它主张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33)参见王振滔:《“人化的自然”到“人的自然化” ——论〈怀念狼〉》,《小说评论》2020年第6期,第33页。
贾平凹对商州乡土社会疾病的隐喻中,流露了其对世纪之交乡土文明从“自然”到“生态”转向中存在的隐忧:“农民不会像知识者那样,把土地看做一册巨大的历史文本,一方由历史遗骸积压成的文化化石。‘大地母亲’一类念头与他们无缘。这不是一块能生长出准宗教感情、形上思想的土地,它只生长五谷杂粮。土地之于农民,更是物质性的,其间关系也更具有功利性。”(34)赵园:《地之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9页。在许多知识分子笔下不断被讴歌的大地、原始自然,被赋予了超功利的审美情趣意味。但回归到具体乡土民间的历史和实践,不难发现审美乡土的乌托邦性令乡土的现代化发展瓶颈日益突出。早已扎根西安城多年的贾平凹,仍自认为“我是农民”的底色无法稀释:“十九年的农村生活,不仅塑造了作为农民的贾平凹,更塑就了作为作家的贾平凹。对那种充满屈辱、苦难、挫败与劳作的农村经验的背负,既让他爱上了土地和土地上的庄稼,又让他有机会深入洞悉农民的德性,那种与节俭、 勤苦等美德相伴生的还有贪婪、自私、狭隘、狡狯等劣性。”(35)黄大军:《承受空间之重:贾平凹长篇小说的救赎美学》,《当代文坛》2018年第2期,第75页。贾平凹在《怀念狼》中的重返商州,向读者展现了一个荒芜野蛮、粗鄙恶心的“野性商州”,有意识地将一个曾经清新美好的“乡土商州”祛魅化、撕裂化、魔幻化。“当商州以另一种被破坏、秽污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尤其作品中商州的一隅雄耳川因为人狼的出现已成为‘禁区’时,我们有理由相信,贾平凹在重新返回商州寻找文化之根的同时,也终结了商州的叙事。”(36)王军、乔世华:《重寻文学的根——谈贾平凹长篇新作〈怀念狼〉》,《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第14页。通过返观人与狼等非人类物种所存在世界的异同和影响,贾平凹对“乡土商州”的祛魅消解中提出了在新世纪建构生态乡土的命题:如何既保存质朴简单的乡土生活世界,又生成新的生态文明理念和发展意识,让生态乡土文明的建设不至于沦为又一个“乌托邦”?
结 语
人类文明自工业革命以来,在全球高速推进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令人类与大自然的冲突日益加剧。当全球各地纷纷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与打击时, 东西方先后开启了对现代性和人类中心主义持续的反思和批判, 寻求可持续发展战略, 以重新调整和谋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当代文坛中关于现代化进程中生态危机的小说创作颇成气象,涌现了一批生态性与艺术性俱佳的作家作品,如姜戎、迟子建、雪漠、阿来等创作的《狼图腾》《额尔古纳河右岸》《狼祸》《空山》长篇小说,胡发云、陈应松、叶广芩等所作的《老海失踪》《豹子最后的舞蹈》《老虎大福》中篇小说。诞生于世纪之交的《怀念狼》与这些作品汇成了新世纪以来“动物转向”类的生态乡土书写风景,壮大了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书写阵营。它们丰富了生态文学的形态和内涵,以动物环保为题材,重构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整体有机关系, 以生动丰富的文艺书写深化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警醒、重塑了人和万物关系,是极富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的生态书写。学者黄轶提出:“当下的动物题材小说无论是从生态系统的平衡出发一味声讨人性的自私、人力的猥琐,或从动物中心主义立场出发,褒扬野性的强悍、喧哗弱肉强食的既定法则,集中体现了社会转型期文化伦理的蜕变,理清这些在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中所处的理论位置,以及它对新世纪文化走向的影响,当是文学创作以及批评都应该面对的问题。”(37)黄轶:《中国当代小说的生态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1页。为此,将《怀念狼》等“乡土动物”题材的生态文学作品重新置放于历史坐标上加以宏观的审视,能更理性地坚守人文原则以透视文本内外所召唤的、所洞见的、所缺失的种种可能和不可能,以期让当代文艺为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社会建构贡献更多的经验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