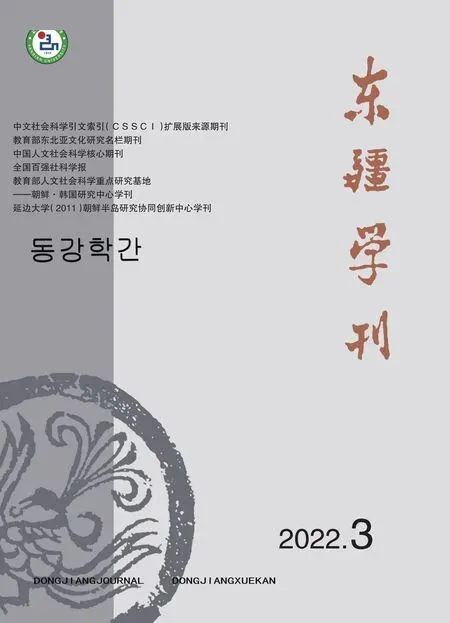明清时期“燕行录”中孟姜女传说变异考
——以“情节”和“人物”演变为例
金 哲,张慧雯
“燕行录”①此处为广义概念的“燕行录”,包括元末明初时期的“朝天录”和清朝时期的“燕行录”两个部分。是元末明初至清朝末期来华朝鲜②本文用“朝鲜”指称1945年以前的朝鲜半岛,涉及1945年后的半岛南部时用“韩国”指称。使臣撰写的一种使行记录,主要包含作者沿途经历和所见所闻,涉及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军事、风俗文化等内容。朝鲜使臣的燕行活动从13世纪末到19世纪末,持续了600多年的时间,其间,“燕行录”作为一种特殊载体持续地将中国传统文化传递到朝鲜半岛,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域外传播的一道独特风景线。孟姜女传说也正是通过这一特殊渠道较为广泛地传入朝鲜半岛,经过几代朝鲜使臣的传承记录和反复改写,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燕行录’版”孟姜女故事。
据研究,这一时期朝鲜使臣的燕行记录至少达500多部,[1](67)其中有300余部涉及到孟姜女传说,且大部分以山海关地区流行的传说为主要内容。由于受记录者身份、个人知识背景及客观条件影响,这些记录在内容和形式上存在一定差异。不过,整体来看仍较为真实地保留了明清时期山海关地区孟姜女传说的历史原貌,呈现出较高的文献与文化价值。
截至目前,中韩学界有关“燕行录”中孟姜女传说的研究成果为数较少,主要围绕传说的传播特征、文体变化等问题展开论述,对其变异情况,尤其是有关故事情节与人物构成衍化变异的探讨却鲜有涉及。一般认为,“情节”与“人物”是构成传说故事的两大核心要素。因此,本文试图以“燕行录”中有关孟姜女传说的日记和杂记等记录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比较文学接受学、变异学等相关理论方法,考察传说情节的演变特征、人物的嬗变轨迹及原因,从而更加清晰且全面地揭示孟姜女故事传承的独特魅力,以此呈现“燕行录”中的独特域外视角,彰显朝鲜使臣在中国文化域外传播过程中发挥的主体性作用,展现明清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向朝鲜半岛传播的历史情形与真实面貌,为当下中韩文化交流提供有益借鉴。
一、认同与传播:情节的记录与演变
孟姜女传说作为中国四大民间爱情故事之一,千百年来广为流传,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杞梁妻故事。[2](134)《左传》《孟子》《礼记·檀弓》《说苑》《列女传》等文献均有对杞梁妻故事的记载。后经过六朝及隋唐时期的不断演义,这一故事逐渐演变为孟姜女故事,并在唐朝时期基本定型。[3](8)据史料判断,孟姜女传说最晚在高丽朝时期已传至朝鲜半岛。统一新罗时期(中国唐朝时期),唐罗两国文化交流频繁,当时除了新罗选派大量使者、留学生赴唐之外,双方还通过民间等多种渠道进行广泛的文化交流。在这一过程中,《左传》《礼记》等中国儒家经典大量传入朝鲜半岛,为孟姜女传说传播至朝鲜半岛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就目前的史料来看,“燕行录”中有关孟姜女传说的记录最早出现于明朝中期,这与当时中国封建统治阶级重视并试图利用孟姜女故事及其烈女事迹推行儒家教化理念有密切关系。明朝中后期,中国各地兴起为孟姜女立庙的官方运动,其中山海关地区以副使张栋(1594年)、主事张时显(1596年)等为代表的地方官吏重修山海关姜女庙,并为之立碑撰文。受此影响,有关孟姜女的民间口传故事随之增多,并在当地盛传。当时,多数来华朝鲜使臣会到姜女庙参观游览,同当地人交流,并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这种文化交流现象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
为了更加清晰地梳理、阐明该时期“燕行录”中孟姜女传说“情节”的演变特征,本文将从历时性角度纵向考察其情节的演变过程。
(一)内容由简到繁
根据实际记录的情况来看,本文将明朝时期“燕行录”中的孟姜女传说记录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5世纪末16世纪初,到1594年张栋重修姜女庙,前后约百年。据现有资料统计,这一阶段仅有5条相关记录;第二阶段是从1594年到1644年明清交替,前后约五十年,约有19条记录。第二阶段的记录频次和数量均多于第一阶段,故事的情节及内容也有所丰富。从总体情节来看,该时期的记录基本沿用或照搬了山海关姜女庙石碑上的内容,大致为“贞女孟姜姓许氏,陝西同官人。夫久赴秦人长城之役,姜制衣觅送,万里艰关,天监贞烈,排岸颓城”。[4](61)故事结构单一,情节波动起伏不大,表明当时朝鲜使臣对山海关孟姜女传说尚处接触和了解阶段,掌握的信息相对较少。此外,明后期由于边疆形势不稳,朝鲜使臣来华次数减少,也导致该时期整体记录数量偏少。
到了清朝,“燕行录”中有关这一传说的记录在数量和内容上均较前代有了明显变化。经统计,该时期的相关记录达226条,并且还出现了杂录等新的记录形式。另外,朝鲜使臣吸纳山海关土人和姜女庙僧人的口传故事,并结合个人的实地体验认知与主观想象,为记录增添了不少内容,如“思其夫登家后小岩上遥望之”[5](548)“范郎隶役死于六螺山下”[6](583)“制衣携二子寻觅至此”[7](329)“收骨负而入海”[8](524~525)“土人立祠祀之”[9](243)等,使故事情节曲折复杂、生动感人。清朝中后期,部分朝鲜使臣对山海关姜女庙石碑上的故事内容提出质疑和异议,“明清以来,多立碑纪迹,而所记各异,语多近诞”[10](116)。这与传播中后期记录者对传说的熟知程度不断加深有较大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与上述新增情节一同出现的“六螺山”[8](524~525)这一地名。明朝时期,中国民间流行的孟姜女故事中曾出现过与“六螺山”同音异字“六罗山”的记载。[3](316)此外,“燕行录”中还有个别记录为“六骡山”[10](115~116)。是直接抄录了山海关姜女庙石碑上的记载。不过上述三种版本应当均由中国早期文献记载中的“乳酪山”一词衍化而来。在王重民校辑的《敦煌曲子词集》中收录了一首唐朝时期流行于民间的曲子词:“孟姜女,杞梁妻,一去烟(燕)山更不归……长城路,实难行,乳酪山下雪雰雰”[11](59)这是中国有关孟姜女传说中出现的较早关于“乳酪山”的记载。由于其汉语发音和上述明朝时期出现的“六罗山”以及山海关姜女庙石碑上刻录的“六骡山”极为相似,因此本文认为后两者很可能是在长期历史流播过程中对前者“乳酪山”的误传或误记。而自18世纪始,在“燕行录”中出现较多的“六螺山”的记录应当是域外朝鲜使臣对中国版本“六罗山”或“六骡山”的误记。
总之,从明至清,“燕行录”中孟姜女传说的情节整体上呈现出由简到繁,内容不断丰富的特点。这一变化与一代代来华朝鲜使臣对该传说的关注、认同与持续记录紧密相关。
(二)结尾呈现多元化
明清时期,“燕行录”中孟姜女传说逐渐打破初期单一化的结尾模式,呈现多元化特征。其结尾大致为三种:一是孟姜女到丈夫死去的地方,望长城痛哭而死,就地化为岩石。这是中国孟姜女传说中原有的故事结局。二是孟姜女伤心欲绝,投海自尽,之后在大海中现出两块礁石,竖立形状的是孟姜女,横躺形状的是范七郎。清代“燕行录”中的记录大部分采用了这一结尾模式。三是孟姜女在长城下失声痛哭,怀抱丈夫遗骸带儿女投海而死。数日后海中涌现出一块礁石,即姜女坟。[12](74~75)这是“燕行录”中较为精彩且独特的一种结尾模式。后两种结尾在“燕行录”中占绝大比重,均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孟姜女传说。
唐宋时期广为流传的孟姜女故事是在《孟子·告子篇》与刘向《列女传·齐杞梁妻》等唐代以前的文献记录基础上形成的。这些故事沿用了之前版本中“杞梁妻投淄水自尽”的情节。如前所述,朝鲜使臣来华,多数都要经过山海关,他们笔下所记录的孟姜女故事基本都是以当地流传的孟姜女传说为蓝本。上述后两种结尾都与海相关,因此也极有可能是在山海关地区传说影响基础上,经过朝鲜使臣进一步改写与再创造产生的,是对山海关孟姜女传说的延伸书写。
(三)修饰性数词的引入
修饰性数词的引入使用也是“燕行录”中孟姜女传说情节内容的重要变化之一,这种情况在中国传统孟姜女传说中极少见。如“其夫范郎就役十年不归……号哭不食七日而死”[13](474);“于归亦三日而其夫赴役不还”[14](42)等。笔者认为,“燕行录”孟姜女故事中出现的“十年”“七日”“三日”等,是朝鲜使臣为增强故事的趣味性和
真实感添加的,这种细节性描述使故事更加具体、生动,为文本增添了活力与魅力。不过对这些具体数字的选用并非记录者的随意之举,而是含有其深刻的文化意味。在民族文化中,受神话传说、宗教渊源或文化禁忌等历史传统的影响,某些数字具有其特殊的文化内涵。朝鲜使臣在孟姜女故事中选用的上述数字便是如此,且常出现在不同朝代的建国神话、民俗故事当中,反映出一定的民族文化心理。如数字“三”在朝鲜神话中代表着神圣、和谐,[15](151)“七”在朝鲜民俗中作为一种禁忌数字,象征着神秘,常与生死祸福等人命的大事联系在一起。
“燕行录”中孟姜女故事情节出现上述变化的原因与“传说”文体的自身特性存在一定关系。根据民间传说的内在发展规律,传说在流传过程中其原始形态往往以强大的吸附力粘合多种文化因素,构建起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新结构。[16](152)从叙事学角度而言,中国早期传统孟姜女传说叙述简短、情节单一、具有显著的开放性结构特征,不同时期的记录者和传承者能够根据自身文化价值偏好和审美取向不断添加新的内容。另外,故事中孟姜女忠贞不二,贞洁烈妇的形象满足了传统儒家伦理对女性的要求,符合同为儒教文化圈的朝鲜使臣对于女性的评价标准。可以说,孟姜女故事本身所传达的主题思想和价值理念对朝鲜使臣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感染力,这也是明清时期一代代朝鲜使臣执着地对其进行记录与书写,在原有故事情节上发挥想象进行再创造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二、想象与塑造:人物的添加与嬗变
传说在长期的口耳相传中,其情节与人物总会发生变化。[17](196~197)早期中国传统孟姜女传说故事中的人物并不多,仅“孟姜女”和“范郎”两个人物。之后,又出现了“秦始皇”“蒙恬”以及两家父母等人物形象,直到唐朝时期才基本固定下来。在明朝记录初期,“燕行录”中的孟姜女故事基本沿用了山海关姜女庙石碑的内容,部分吸纳了当地的民间传闻,其人物构成与中国本土传说相似,直至明朝后期才开始出现明显变化。
本文重点关注“燕行录”孟姜女故事中特有的人物——明后期出现的“小婢”,明清交替时期出现的“童男童女”“童子童女”以及之后的“二子”“一子一女”“二儿”等与孟姜子女有关的人物。这些人物均出现在孟姜子女寻夫过程中,是山海关姜女庙石碑碑文中所没有的。这说明,从明朝后期开始特别是明清交替以后,越来越多的朝鲜使臣不再将山海关姜女庙的碑文内容作为其记录的唯一来源,而是将既有信息与当地传闻相结合,并融入自己的想象与情感进行记述。“燕行录”中首次出现有关“小婢”的记录如下:
望夫台万里城外八里铺东南十里间,遥望一祠……祠额曰:贞女孟姜女祠。祠中设塑像,旁有一小婢抱伞侍立,乃自陕东,来时与之同行,与之同死者也。[18](498)
上述记录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小婢”的来历、同主人公的人物关系等。故事中她与孟姜女一同死去的结局令人动容。据史料判断,这一记录的时间应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作者当为黄是(1555—1626),韩国东国大学出版的《燕行录全集》中误题为黄士祐。按照这一时间来推算,“燕行录”孟姜女传说中的人物“小婢”出现在明后期张栋、张时显重修姜女庙之后不久。因此,可以推测,在这两次重修期间,曾在“孟姜女”塑像旁修建了一尊单人塑像。这种庙内实物景象的变化很可能是导致该时期文本出现新形象的原因。
到了清代,“小婢”这一人物逐渐消失,“童男童女”“童子”“童女”等代之登场,之后又出现了“二子”“一子一女”“二儿”等与孟姜子女有关的人物。下列记录较为清晰地展示了这种“人物”的嬗变轨迹:
祠正中有榻上安秦贞女许孟姜塑像旁顾低视愁容可掬,左右童女侍立一持伞一奉带。[19](231)
姜女塑像愁容皱眉宛然有垂泪形两傍立童男童女左荷雨伞右捧角带。[12](73)
姜之左右侍立童男童女俗传以为此是姜之子若女也,童女捧带以从者即七郎之遗物也,童男操伞以随者其母不计风雨而跋涉故将以庇雨云。[12](361)
塑像左右立两童子一捧带一撑雨伞似皆姜女之儿。[20](24)
其妻许孟姜制衣携二子寻觅至此闻其夫新死登此石北望恸哭。[7](329)
姜女像愁眉啼妆宛是望夫之形,其旁一子一女,男执伞盖其母负骸时从行者,女执带即其父所带之物。[21](299)
后人即其地立庙塑一女两童子侍立左右,左者持伞右者持带,两童即贞女之子。[22](274)
由上面几段引文可知,朝鲜使臣在为故事添加新人物的同时,还对其身份、性别、姿态及手持物品等进行描述,使人物的刻画更加丰满、真实。然而不同记录者对人物的描述却各不相同:如关于人物性别,有使臣记录为“左右童女”,有的则记录为“两童子”“左童男右童女”或“男一女一”。关于人物手持物品,有记录认为伞和绸带是范郎留下的遗物;有的则认为伞是孟姜冒雨迎接丈夫时所撑的伞,绸带是孟姜为丈夫缝衣而备;还有记录认为伞是儿为其母孟姜手负其父范郎骨灰时所撑的伞,绸带是其父的衣物。这些细节描述突显了朝鲜使臣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与中国传统故事中“独行寻夫”的叙述相比,这些人物形象的添加不但丰富了故事情节,使故事更加具象化,富有画面感,易于感染和打动读者,还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和传说的文学艺术性。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孟姜女传说的相关文献中很少见到上述人物。明朝张栋与张时显重修姜女庙时所题写的碑文也仅包含姜女故事的梗概、对姜女贞洁品性的赞赏以及重修庙宇的缘由等,并未提及此类人物。[4](61~65)另外,2008年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茶业口镇出土的古碑“孟姜女纪铭”较详细地记述了孟姜女的身世背景和事迹,但也未提及孟姜的后代子女。
学界普遍认为“孟姜女”传说同“杞梁妻”故事有着密切关联。因此,本文拟借助历史上“杞梁妻”后代的相关记录来推测孟姜子女的情况。经考证,多数文献均记录为“杞梁之妻无后代”。汉代刘向在《列女传·贞顺传》中云:“杞梁之妻无子,内外无五属之亲”[2](147);东汉末年,蔡邕的《琴操》(卷下)有云:“庄公袭莒,殖(按:指杞梁)战而死。妻叹曰:‘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外无所依,内无所倚’”[2](147);又有唐代名僧诗人贯休在诗歌《杞梁妻》中曰:“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鸣鸣,上无父兮中无夫,下无子兮孤複孤……”[2](146)。此外,在后唐马缟的《中华古今注》、明朝冯梦龙的《情史》中也均记载杞梁妻“下无子”[2](146)。因此,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燕行录”孟姜女传说中出现的孟姜子女等人物形象,应当视为朝鲜使臣的独特记录。这种“人物”的添加与变化是中国古代孟姜女传说域外传播过程中出现的重要且典型的变异现象。
“燕行录”中孟姜女传说出现上述“人物”添加与变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与明清时期山海关姜女庙的重修存在很大关系。由于上层阶级的重视,姜女庙在明清时期经历多次重修。
在重修过程中,庙内塑像等实物景观的变化是导致文本“人物”添加最直接的原因。二是结合了山海关当地的民间表达。朝鲜使臣来访中国,参观和考察姜女庙内实物景象,在实地体验的基础上,听取当地的民间传闻和庙中僧人的口传故事,并将其记入文本。“燕行录”中多处记载“俗传”“有云”“僧言”等类似表述便可佐证。三是融入了朝鲜使臣的个人认知、情感和想象。明清时期朝鲜使臣来访中国的记录并非机械地模仿,也非现实的复制,而是朝鲜使臣根据实地体验认知、遵从主观情感、能动地发挥想象进行“重组”与“改写”的,是对“原文本”的“创造性转变”。如故事中添加陪伴孟姜千里寻夫,最后一起投海的人物,甚至还记录孟姜育有后代子女等,流露出朝鲜使臣对主人公身世和遭遇的怜悯之情,以及对故事悲剧结尾的唏嘘之感。他们通过在文本中添加上述人物形象,将自己对故事的美好愿景以及对这位贞烈女子的同情与祝福融入到了故事当中。
三、结论
明清时期,孟姜女传说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备受朝鲜使臣的关注。他们来华途经山海关姜女庙,在参观庙内实物景象的同时听取当地民间传闻和庙中僧人的口传故事,并将这些所见所闻记录在“燕行录”中,使山海关地区孟姜女传说由口传形式转为文字记录并传承至今。
本文重点围绕“燕行录”孟姜女传说“情节”与“人物”两个方面的变化展开论述,探索以朝鲜文人的域外视角及独特方式传播到朝鲜半岛的孟姜女传说变异情况,深入考察“燕行录”中孟姜女传说“情节”的演变特征,“人物”的嬗变轨迹及其原因。在长期的接受与传播过程中,朝鲜使臣结合在中国的实地体验,吸收山海关姜女庙石碑的碑文内容和当地民间传闻,融入个人认知、情感和想象,在自身文化背景、民族心理的影响下进行记录、改写和再创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燕行录’版”孟姜女故事。
总之,“‘燕行录’版”孟姜女故事是特定时期来华朝鲜使臣对中国传统孟姜女传说进行主体性文化介入的必然结果。它是在继承和保留原有文化质素的基础上,不断融入独特变异因子,最终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产物,是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智慧结晶,为当下中国和朝鲜半岛乃至东亚各国文化交流与互动提供了历史借鉴。
——明清朝鲜使臣汉诗整理与研究(20BWW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