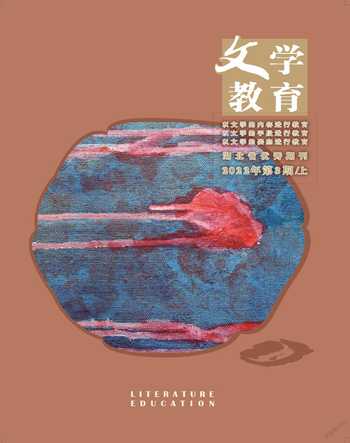余光中:东西化合的先锋写作
余光中(1928.10.21~2017.12.14),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学者、翻译家,出生于江苏南京,祖籍福建泉州永春。1947年毕业于南京青年会中学,入金陵大学外文系,1949年转厦门大学外文系,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9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余光中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被誉为文坛的"璀璨五彩笔"。驰骋文坛逾半个世纪,涉猎广泛,被誉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代表作有《白玉苦瓜》(诗集)、《记忆像铁轨一样长》(散文集)及《分水岭上:余光中评论文集》(评论集)等,其诗作如《乡愁》《乡愁四韵》,散文如《听听那冷雨》《我的四个假想敌》等,广泛收录于大陆及港台语文课本。
中国台湾“前行代”诗人余光中(1928.10.21~2017.12.14),在20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两岸诗坛影响卓著。当时正处于“两蒋威权政治时期”,岛内文化主张“全盘西化”。当时的台湾诗坛受欧美现代派各流派艺术的深刻影响,他们大多“放弃”了中华民族古典诗歌的传统,诗歌写作全面地“向西看”。1954年余光中与覃子豪、钟鼎文等人创办了“蓝星诗社”,主编《蓝星诗页》。主张中西融合的诗歌创作理念。他出版有诗集《舟子的悲歌》(1952)、《莲的联想》(1964)、《在冷战的年代》(1969)、《白玉苦瓜》(1974)、《紫荆赋》(1986)、《守夜人》(1992)等十余部。处在西化文化的包围之中,现实的乡愁和文化的乡愁,使余光中重新感悟和发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当然,余光中在重归民族古典诗学时也不忘当下文化,他要找到一种源深流长的现代诗歌风范,实现古今中外的完美化合。他的诗“在内涵上,可以说始于反传统而终于吸收传统;在形式上,可以说始于自由诗而终于较有节制的安排”。i这也就使余光中诗歌从“西化”初期至今,一直存在着区别于同时代的台湾诗人的先锋性。
余光中的早期诗歌多写留美求学生活,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中体现出一种民族文化立场坚守与对现代工业文明的警醒,象征等现代派手法的精妙运用,初步展现了他早期的诗歌主张。如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芝加哥》。
《芝加哥》表达了一种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在美欧留学的异乡情怀,充满着压抑、抗争、反省和对祖国文化的坚守精神。诗人先用“大蜘蛛”和“小昆虫”隐喻全盘西化中近代中国文明遭遇的巨大压力,同时,又用“难以消化的金甲虫”昭示了自己对于民族文化的坚守,“文明的群兽”“摩天大楼”“立体的冷淡”“阴险的几何图形”,这些都是在表明中西对立的文化交流中,诗人对西方工业文明的警省与抗争,他用“异乡人的灰目”“西望的地平线”来表达这样一种坚决的抗争。诗人清醒地指出,芝加哥这座现代工业都市使人迷茫,也指出了美国当时趁着黑暗阴谋挑起对越南的侵略战争,西方文明正在走向堕落。
芝加哥城市夜色中,爵士乐、萨克斯风在夜总会里疯狂演奏,荒淫的色情舞蹈,黑人猫王的摇滚乐也在逐渐地摧毁着宗教的生机和教化作用。严肃的艺术馆前,波斯壁画和威武的石狮子,都一动不动,无人问津。贫乏的当代艺术无法挤进这高雅严肃文艺的展馆。19世纪文艺复兴的精神还在这里流传,然而艺术家的灵魂也见证着20世纪这个大都会空虚的衰落以及它表面的繁荣喧闹。国际文化等融合中,诗人坚守东方文化的本性拒绝全盘西化,他冷静刚强。坚韧的母语文化立场。冰是借喻。世人之称,他的艺术生命是感性的,流动的,变动不拘的,在中西化合中不断的滑动。然而远离祖国文化的怀抱和光辉照耀,难以融化游子心里的西方现代文化的结晶,这抒发了诗人坚定的民族自尊心。
《芝加哥》從主题内涵到表现手法,都是中西诗学艺术的结晶,民族文化立场与现代工业都市文化的对峙与取舍,借喻、象征手法的精妙运用,互参互照,生动表达了“西化”潮流中诗人的倔强与坚守。类似的还有《我之固体化》等诗作。
余光中回到台湾工作和香港中文大学兼职期间,他的诗歌转向中国当代文化的古典意涵挖掘。诗集《白玉苦瓜》是其中的经典之作。
《白玉苦瓜》主要写故宫博物馆藏的这样一个传世艺术品,它质地圆润,色泽轻盈,造型丰满充实而新鲜,所有的这一切都建立在中华文化的背景下,是祖国文化原生滋养与哺育的结果。瓜熟蒂落,暗藏着觉醒的文化底蕴,故中国文化的乳浆使它丰满。茎须、叶掌、触角、葡萄、瓜尖,造型栩栩如生,光泽新鲜,背景是九州舆图,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哺育下,才获得了这样温润的美学底蕴。
国宝白玉苦瓜,见证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苦难的历史。它凝聚了中华文化的结晶,数历侵略者蹂躏践踏焚烧,却不曾留下岁月的伤痕,只留下了光泽透明的文化精神和对国土不舍的祝福。因此他也获得了超越时空自足的艺术生命,艺术精神得以饱满永存。艺术家用精巧的工艺引入这块翡翠白玉,雕塑打磨成了玉瓜的模样,艺术创造的甘苦使之获得了永恒的价值。
与之相通的诗作还有“周末西门町的五陵少年”(《五陵少年》),“在科学馆等吴宫采莲归来的你”(《等你,在雨中》),“歌咏黄河西来大江东去”的《戏李白》,等等。
余光中诗歌还有另一种主题:生命的再生与永恒。《火浴》就是探讨这个命题的。从古以来,人类就为时间与永恒的问题所困扰。人们不满足于生命这种有限的存在,不能不对生命的永恒充满憧憬。开始,诗人就表现了对生命“一种不灭的向往”。接着展示了两种使生命获得再生的途径,一种是“上升如凤凰,在火难中上升”,一种是“天鹅”“浮于流动的透明”。凤凰,是古老神话中的永生鸟,又称太阳鸟。天鹅则是献祭艺术之神阿波罗和美神维纳斯的圣鸟。这两只象征再生和永恒的禽鸟各有特点。凤凰的特性为“上升”“费烧“扑火”“飘扬”。天鹅的特性为“纯白”“长颈”“丰躯”“沉淀”“赴水”。前者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内在美,后者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外在美。诗人在这两种美面前心醉神迷,难以取舍,因而既“要水,也要火”“要洗濯,也需要焚烧”,这显示了诗人在选择再生之途时的困惑。第二节,诗人用对比的方法,比较了天鹅的“冰浴”和凤凰的“火浴”两种生命的净化、再生过程。从净化、再生的背景上看,天鹅的冰浴发生在“水波粼粼、似幻似真”的“冰海”,凤凰的火浴发生在“一羽太阳在颤动的永恒里上升”的“炎炎的东方”。从净化和再生的运动态势上看,天鹅的冰浴呈现为一种静止的形态,“那里冰结寂寞、寂寞结冰”;凤凰的火浴则呈现为一种不断行进的循环运动;“从火中来的仍回到火中,一步一个火种,踏着火焰”。到了第三节,诗人比较了“火浴”和“冰浴”发生的背景和运动态势,作出了情感和价值评判。“浴于冰或浴于火都是完成”,都可使生命获得再生和永恒,但相较而言,“火浴更可羡”,因为“火浴”的凤凰是个在“永恒流动、永恒的烈焰”中奋进的“勇士”,而“冰浴”的天鹅则是个在“时间静止”中摇着“白扇”的“隐士”。第四节更加表现凤凰艰难曲折而又壮怀激烈的“火浴”图景。在诗人笔下,火浴是“一座弧形的挑战”。一个真正的“勇士”,“黥面、千杖交笞”的坏运和死亡的“极刑”也无法阻挡他那“烟火的意志”,反而激发他生命进击和创造的激情,他“坦然大呼”“张扬燃烧的双臂”。于是“勇士”立于绝境却用不屈的意志和不断的行动将自我送上了绝境,他在充满活力的奋斗、拼搏和燃烧过程中,实现了生命的“飞”和“新生”。钟玲批评说,“在形式上,《火浴》是圆熟的,在意境上,《火浴》是高旷的”ii。这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这首诗在形式上意象经营上的特点。形式上,这首诗在整齐中又有变化。全诗五节,前四节均为13行,呈现出一种对称的美;后一节是结尾,却言简意赅,只有5行。现代口语的引入,不仅使诗的发展避免了单调,保持了感觉的新鲜,随着文字秩序的变化,诗歌的内蕴也得到了提升。在意象经营上,这首诗将再生原型作为意象母系统,凤凰和天鹅两种生命意象作为再生原型的子系统,两个子系统尽管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出阴与阳的对立形态,但在这种表面的对立形态背后,它们却达致了阴阳对抗中的统一,它们共同组成了震撼人心的再生和永恒的生命意境。显然,东方古典意象“凤凰”与西方文化的“天鹅”完美地融入诗意,实现了中外古今的再次化合。
相互印证的还有他的代表作《秦俑》。诗歌化用了秦腔、诗经《豳风·岂曰无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等典故,圣战不朽的秦俑像,讽刺了那些想要永生不老的秦皇汉武。诗歌先描写了秦俑出土陶俑的铠甲,弓箭,长矛,还有想象他们在三千年前沙场厮杀的威武雄姿,描写了他们的胡髭、双眼、秦腔口音,着重突出经过千年阴间的幽暗依然骁悍不驯。穿越时空的长河,诗人想到古今发生在咸阳、西安的政治变革都决定了历代王朝的命运。诗人从秦俑身边的威武黑旗和严整的纪律,浩荡的六千兵骑,回想到大秦帝国创立的丰功伟绩,战歌嘹亮,慷慨激昂。两千年后在博物馆重整队伍,眉目栩栩,肃静庄严,为大秦帝国的兴衰作证。化用文化古迹,并赋予他们现代的哲思,使古典重新活跃起来。
余光中后期诗歌以乡愁为主题,更是东西化合、诗艺抵达炉火纯青境界的系列经典。如《乡愁》《乡愁四韵》等。
《乡愁》运用递进蒙太奇手法把母爱与家国情怀剪辑放置在一起。小时候—长大后—后来——现在,这四个方面逐层推进,首先是我与母亲的亲情,我与新娘的爱情,然后升华到我和大陆之间隔不断的家国情。它是借人伦亲情隔断的苦痛来深入表达两岸骨肉被政治隔绝的残酷性,以母子亲人团聚的合情合理来期盼“浅浅的海峡”隔绝下的两岸中华儿女能够早日团聚。“乡愁”在这里已经具象为母子亲情与个人爱情的这种人伦亲情,它有一种隐喻在里面,祖国才是我们共同的母亲,从而演化出这种母子亲情被隔绝的非人性,进而抒发了对团聚的渴望,和两岸亲人和平统一的呼唤。
另外,时间上的递进从年少到年老,充满人生易老团聚艰难的辛酸。邮票、船票、坟墓、海峡在空间上的递进,由小的事物、近距离的空间逐渐拓展到海峡两岸分隔的历史格局。这种时空上的递进,也把人事的沧桑、家国的变迁暗含在全诗的抒情背景上,使这首诗具有了一种浓郁的人生变幻、国家民族历史政治演绎的沧桑感,这才是当时“乡愁”深层内涵。“小小的”“窄窄的”“矮矮的”“浅浅的”,以小驭大,由具体转喻抽象,揭示了不同时期的“乡愁”底蕴。
很明显,这种蒙太奇镜头剪辑的方法对准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乡愁”,在这样一种时空递进的氛围里,不但超越古典诗歌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的思亲主旨,还注入了80年代两岸骨肉分隔的当代“乡愁”意识。这种蒙太奇电影组接手法实际上是与超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现代手法配合在一起的,现代主义融入了东方式的人伦抒写,从而使这首诗成为东西方化合的一个“传世经典”。
类似的文化乡愁诗歌还有《布谷》。《布谷》是清明前后梦游江南秧田的乡愁写意。全诗抒写了诗人无处皈依的文化鄉愁。布谷鸟的叫声,被诗人引化为“不如归去”的音义升华,是暗含了中国古典文学中杜鹃啼血游子思乡的苦痛。儿时的田埂,江南的阡陌,清明扫墓的地方,都已经被现代的商业文化所抛弃。啤酒和挖土机消解了清明时节的杏花春雨、水墨山水、牧童牛哞的闲适。古典民族文化传统在现代工业文明面前的无力,使诗人分明地感到无处皈依的文化乡愁。
诗中叠句、摹仿、借代、拟人、叠音词的大量使用,使全诗形成一首悠扬古典乐曲,意象象征手法的融入,诗作又有一种现代韵味。
余光中还是最早以其创作和理论批评,推动了现代诗在岛内的当代发展和分化,但他和当下大多数富于先锋意识的诗人不同,他不仅是现代诗的实验者和维护者,而且是现代诗的批评者。当某些人以传统的观念否定现代诗时,他撰写了一批颇有份量的论战文章来维护现代诗的地位;当“虚无”和“晦涩”越来越成为现代诗的重症时,他最早著文批评这种“幼稚的现代病”,并宣称和“虚无”告别。他及时回归传统,却也未抛却“现代”,而是自由出入于现代与传统之间,形成现代与传统水乳交融的圆融诗风。中国当代诗歌发展早已打破了诗界以往的民族自足心态,诗人自然超越本位积习而把眼光投向环宇。余光中先生透视中西文化,并将诗歌视角从本土扩大到放眼世界。
总之,余光中通过借用古典意境、隐喻、叠音、用典、化俗为雅等手法,结合西方现代诗的象征意象、超现实主义蒙太奇等手法,创造了与中国语言文字特点相结合的民族化与先锋性融合的诗艺之美,赋予了现代新诗以先锋性活力。
参考文献
i余光中:《五陵少年——诗歌选集自序》,选自《余光中诗歌选集》(第2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7页。
ii钟玲:《文学评论集》,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第123页。
任毅,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武汉大学博士毕业,福建省写作学会副会长,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现代诗学和鲁迅传播研究,在《光明日报》《当代文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小说评论》《中国文艺评论》《鲁迅研究月刊》《福建论坛》《诗刊》《诗探索》等报刊上发表论文150余篇,出版专著《百年诗说》《0596诗篇》等多部,入选福建省闽南师大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