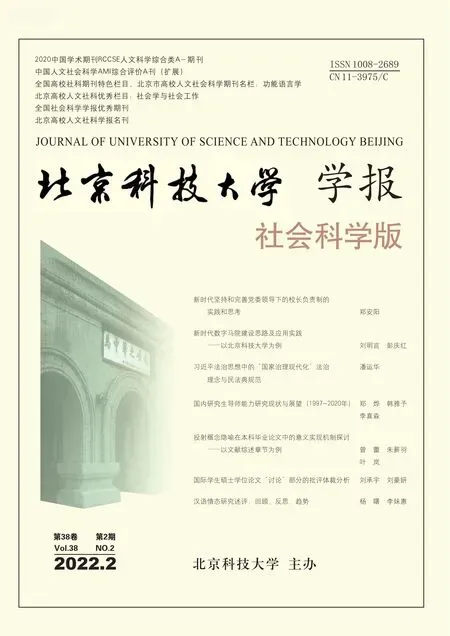汉语情态研究述评:回顾、反思、趋势
杨 曙 李妹惠
(华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州 510640)
情态是一个古老而又长青的研究话题。对情态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在模态逻辑领域对“可能性”与“必要性”概念的探讨。西方语言学的情态研究是在借鉴模态逻辑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较早关于情态的讨论可见于Jespersen。在当代,情态作为一个重要的语义和语法范畴,一直是西方语言学各领域的关注热点。它涉及到词法、句法、语义、语用等语言的各个层面,并与语言认知、语言交际等各个方面相关。
现代汉语的情态研究可追溯至《马氏文通》对“助动字”的探讨。此后,语言学家如吕叔湘、王力、高名凯等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情态”概念,但是也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情态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外学者开始借鉴西方语言学的情态研究成果,对现代汉语情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然而,与西方语言学的情态研究相比,汉语情态仍然是一个相对较为薄弱的研究领域。鉴于国内目前汉语情态的综述性论文并不多见,本文将回顾、评述汉语情态研究,以期对情态的后续研究提供参考和指引。
一、汉语情态研究回顾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内外学者陆续对汉语情态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主要的研究成果包括:Tsang、Tiee、贺阳、李明、温锁林、齐沪扬、史金生、鲁川、崔希亮、鲁晓琨、徐晶凝、彭利贞、胡波、范伟、邵敬敏。下面将从两个阶段对这些有代表性的情态研究成果进行回顾。
(一) 20世纪80−90年代的情态研究
在20世纪80−90年代,汉语学界的情态研究仍然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发表的论文不多,出版的专著则更为少见,主要着力于在汉语中建立情态范畴和讨论汉语中情态的表达形式。
Tsang详细讨论了六个情态动词“能”“可能”“会”“要”“该”“许”的语义特征。该研究旨在证明汉语中存在情态这样一个语义和语法范畴,界定的情态范畴包括言者取向的认识和道义情态,主体取向的能力和意愿情态被排除在情态概念之外。
在此之后,Tiee探讨了汉语情态的定义与分类,并总结了汉语助动词和语气词的句法特征。该研究认为情态是一个语义范畴,包括认识、道义与动力情态。认识情态表达了说话人对命题可能性的主观判断,具备言者取向特征;道义情态与行为有关,具备话语取向特征;动力情态与主体的能力与意愿有关,具备主体取向特征。该研究指出,在汉语中,情态由助动词、情态副词、情态语气词表达。汉语助动词和语气词的句法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助动词总是出现在主要动词之前,情态语气词出现在句子末尾;(2)助动词和语气词在句中可以连用;(3)助动词由否定副词“不”否定;(4)助动词强调句子谓语的情态,语气词强调句子的情态。
国内学者贺阳较早对情态展开系统研究,他把modality译为语气。他认为语气是通过语法形式表达的说话人针对句中命题的主观意识。他把汉语语气系统分为三个子系统,即功能语气系统、评判语气系统和情感语气系统。功能语气系统表明句子在言语交际中所具有的言语功能,包括陈述、疑问、祈使、感叹语气;评判语气指说话人对说话内容的态度或评价,包括认知、模态、履义、能愿语气,评判语气基本对应西方的情态范畴;情感语气表示说话人由客观环境或句中命题所引发的情绪,包括诧异、料定、领悟语气等。
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情态研究仍较为零散,研究者着力于确定汉语中存在情态这一语义和语法范畴以及初步探讨汉语情态的类型和表达形式。
(二) 21世纪之后的情态研究
进入21世纪之后,情态研究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论文、论著的数量有了大幅增加,研究内容更为深入,研究角度也不再局限于传统语法,研究者开始运用形式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理论来解释情态研究中的相关问题。从研究内容来看,21世纪之后的情态研究可划分为情态语义系统研究和情态表达形式的语义、句法特征研究。
1. 情态语义系统研究
情态作为一个跨语言的语义范畴,在汉语中包括哪些子范畴,一直是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其中,汉语学界争议较大的是情态与由句类系统体现的语气是应该两分还是置于统一的框架之内。
齐沪阳把情态置于语气的范畴下分析,把汉语语气系统划分为功能语气和意志语气两大类。功能语气指说话人使用句子要达到的交际目的,包括陈述、疑问、祈使、感叹语气。意志语气表达说话人对说话内容的态度或情感,包括可能、允许、能愿和料悟语气,主要由助动词“应该”“可以”、语气副词“大概”“也许”“一定”等体现。意志语气基本对应西方的情态范畴。不难看出,齐沪阳与贺阳都把实现交际目的汉语句类系统与表达说话人主观情感与态度的情态语义系统都置于语气的框架之内讨论。
与贺阳与齐沪阳不同的是,徐晶凝只把由汉语句类系统体现的语气系统置于情态的框架之内。徐晶凝认为现代汉语的话语情态系统包括由现代汉语句类系统体现的言语行为语气系统、由语气助词表达的传态语气系统、由情态助动词和情态副词表达的情态系统。她认为语气助词是汉语话语情态系统中语法化程度最高的表达形式,因此着重讨论了现代汉语的语气助词系统,详细描写了五个语气助词“啊、呢、嘛、吧、呗”的情态意义。
崔希亮同样把语气置于情态的框架之内讨论。该研究认为,情态是一个比时(tense)和体(aspect)更为概括的范畴。汉语的情态系统包括三个子范畴:语气范畴、能愿范畴和时体范畴。语气范畴包括疑问、祈使、感叹等子类;能愿范畴包括意愿、能力、义务、可能和禁许,由能愿动词体现;时体范畴与事件的时间属性有关,由情态副词、动词本身及动词的附加成分表达。
温锁林则认为有必要区分语气与情态,语气指说话人使用话语的功用和意图,包括陈述、疑问、祈使、感叹语气;情态表达说话人对所说话语的主观情感与态度,可分为认识情态和表现情态两大类。认识情态是说话人对所述命题的主观认识,可分为真值情态、道义情态和意愿情态。表现情态指说话人对所述命题的表情与态度,即口气,包括急促与舒缓、强调与委婉、惊异与惬意、张扬与收抑、偏执与宽容等。
鲁川也认为从语言教学和信息处理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区分语气与情态。他认为,“语气”体现说话人的交际意图,或陈述信息或疑问;“情态”则体现说话人基于固有的主观意识,是对“事情”的主观情绪与态度。情态范畴划分为“判断”与“评议”两个子范畴。其中,判断细分为推断、必要、常规、适度等子类;评议划分为评估与提议两大类。这些子范畴由情态标记词体现,例如,推断由标记词“一定”“大概”“也许”等体现,必要由标记词“该”“得”“必须”等体现。
邵敬敏认为,情态属于语义范畴,句子类型属于功能范畴,两者具有明确的分工,应当区分开来。句子类型通过多种句法手段来表示句子的用途。情态表达说话人对命题或事件的态度,通过词汇、语法、语音等形式手段来实现。情态跟主观性密切相关,是对命题或事件极为重要的补充。他甚至提出建立以主观情态为标记的句子情态系统,简称为“句态”,包括评估句与表态句等。
2. 情态表达形式的语义和句法特征研究
除了对情态范畴进行界定之外,汉语学界也有不少学者对情态表达形式如助动词、副词的语义和句法特征进行了研究。
史金生探讨了语气副词的范围和类别,从语义角度对语气副词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语气副词主要用于命题之外,表达说话人对命题的主观态度,可分为知识和义务两大类。其中知识类语气副词包括肯定和推断两个次类,前者如“绝对、当然”,后者如“大概、或许”;义务类语气副词包括意志、情感、评价三个次类,前者如“千万、宁愿”,后两者如“究竟、难道、偏偏”。在分类的基础上,他着重考察了语气副词的连用情况,总结了各类语气副词的连用顺序,并用管辖范围原则、主观程度原则、连贯原则和凸显原则对常规连用顺序和非常规连用顺序做出了解释。
鲁晓琨对现代汉语可能类、意愿类、必要类基本助动词的语义表达系统进行了详细分析,并鉴别了助动词的“非情态表现”和 “情态表现”。她认为可能类助动词语义表达的核心由“能”体现;意愿类助动词的语义表达系统可分为主动自发的意愿和回应选择的意愿,前者由“想”和“要1”体现,后者由“愿意、肯”体现;必要类助动词可划分为表达情态评价的“应该、应当”以及表达情理、现实需要的“要2、得”等三类。
彭利贞从语义与认知角度对现代汉语多义情态动词表达的语义系统进行了分析。他分析了现代汉语的多义情态动词与其他语法范畴的互动关系,着重探讨了现代汉语动词情状、体、否定等范畴与多义情态动词同现时对情态解读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了现代汉语多义情态动词情态语义的语法形式解释系统。
李明从历时语法化的角度探讨了情态助动词的历史演变过程。他从语义的角度,将助动词的各项意义归为条件类、道义类、认识类、估价类等,确立了一个较完整的语义系统。然后考察了各类助动词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着重描写了各个时期新产生或开始消亡的助动词以及助动词之间的竞争、更替,以及同一类意义的助动词的内部差别等。他还总结、揭示了助动词语义发展的规律性。
胡波从形式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了情态助动词的句法形态特征,并从论元结构、语义限制、否定、被动化等方面探讨了汉语情态助动词的提升与控制问题。认为认知情态助动词属于提升动词,道义和动力情态助动词属于强制控制动词。提升情态助动词是包含命题子句论元的一元动词,允准子句主语提升为主句主题,不限制提升主语的语义内涵,不可以用“没,没有”否定。控制情态助动词为包含事件论元和非典型施事论元的二元动词,可以用“没,没有”否定。
范伟从构式语法的角度对情态的表达形式进行了研究。她认为,情态的表达形式不局限于词类,还包括凝固性和规约性较强的构式。因此,她提出情态的表达形式包括成分情态和构式情态,前者指各种语法词类以及插入语等固定用语和句子特殊成分,后者指由两个词语形式单位构成并具有整体不可分割意义的固定格式。她还指出认识情态构式包括“不……才怪”“非……不可”“要……了”等,道义情态构式包括“随……去吧”“不要……了”等。该研究着重对 “X定”“大不了”“X不到哪儿去”情态构式的语义和语用功能进行了详细描写。
二、汉语情态研究存在的问题
综观汉语学界对情态的研究,不难发现,汉语情态研究目前仍然存在一些函待解决的问题,下面分别从研究路径和研究内容两方面进行讨论。
(一) 研究路径
从研究路径来看,问题在于从传统语法以及从历时语法化角度对情态表达形式的语义与句法特征以及情态语义系统进行描述性研究较多,而从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形式语言学等角度对情态进行的阐释性研究仍然较少。西方语言学界已从不同路径对情态这一复杂语义现象展开了深入的系统研究。例如,认知语言学从语言认知的角度解读情态语义。Sweetser采用力动态理论(force dynamics)阐释了英语情态助动词的认识和道义情态语义,Langacker从“力争控制”的角度划分情态类型并阐释了认识和有效两类情态。系统功能语言学探讨了情态在语篇中的人际交互功能。我们认为,借鉴现代语言学理论对汉语情态展开研究,有利于阐释汉语情态语义系统和解决汉语情态研究中面临的某些问题。例如,与英语的情态助动词不同,汉语的情态动词既可以位于句首位,还可以位于句末位。形式语言学主张从提升和控制的角度解释这一现象,系统功能语言学则主张从信息结构的角度阐释情态动词的这一句法表现。
此外,存在的问题还包括已往的情态研究大多局限于对汉语本体语言的研究,从共时类型学的角度把汉语情态范畴与英语以及其他语言的情态范畴进行的系统性比较研究并不多见。把汉语情态置身于世界语言中,有利于发现汉语情态的特性和共性。例如,标准英语的助动词不能连续连用;而现代汉语的助动词可以连续连用。但是,助动词的连续连用并不是汉语的特色之一,这是因为在其它语言如德语、荷兰语中情态动词的连续连用也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二) 研究内容
从研究内容来看,问题在于在情态定义、情态类型、情态与语气的关系、情态动词的划界等方面,国内汉语学界尚未达成较统一的认识,分歧较大。此外,研究内容的广度也有待提升。
首先,汉语学界对情态的定义和情态类型仍然存有争议。例如,鲁川认为,情态类型除了“推断”“必要”之外,还包括“常规”“适度”“机遇”“评估”和“提议”等次类。温锁林把情态分为认识情态和表现情态两大类,后者包括“急促与舒缓、强调与委婉、惊异与惬意”等七个子范畴。邵敬敏指出,情态到底包括哪些内容,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非常值得探讨。学者们对情态定义及类型存有争议的原因可能在于单从说话人的主观情感、态度这一定义出发来界定情态和情态类型。Halliday & Matthiessen从体现言语交际事件的命题小句(proposition)和提议小句(proposal)角度,界定了在以交换信息为语义功能的命题小句中,存在认识或可能性情态;在以交换物品或服务为语义功能的提议小句中存在道义、意愿、能力情态。我们认为,汉语的情态类型也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界定。
其次,由于对情态的定义与情态类型存有争议,汉语学界对情态与语气的关系尚未达成统一的认识。彭利贞指出,在最近现代汉语的情态研究中,存在语气与情态不分的现象。或在语气的范畴下讨论情态,或在情态的范畴下讨论语气,未对两者进行明确区分。我们赞同鲁川和温锁林的观点,即在现代汉语中,有必要区分实现言语交际功能的句类语气系统和以情态动词、副词等形式体现的情态语义范畴。值得一提的是,西方所说的语气(mood)一般指在某些语言(如拉丁语、德语、西班牙语)中以动词形态的屈折变化体现的语法特征,属于形态句法范畴,通常体现为直陈语气与虚拟语气的区分,与汉语的句子类型或语气不是同一个概念。
再者,汉语学界对情态动词的范围和划界仍然存有分歧。汉语情态动词的划界实质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情态动词与副词的划界;二是情态动词与实义动词的划界。由于汉语情态动词没有英语助动词那样明确的形式标志,而形式标志往往是识别词类最简易和显著的标准。不同的学者对情态动词进行划界时,采用的标准不一,且有些标准的有效性不足,分歧较大。例如,“可能”“一定”“肯定”到底是情态动词还是副词?“必须”是不是情态动词?实义动词“爱”“打算”“企图”应不应当列入情态动词范畴?汉语学界对此,各家说法不一。我们认为,现代汉语情态动词的范围和划界可以借鉴功能语言学或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来展开。
此外,从研究内容的广度来看,汉语情态研究对助动词的关注较多,对名词、插入语等其它情态表达形式的系统研究较少。温锁林指出,以往的情态研究范围太狭窄,现代汉语的情态表达除了情态动词和语气副词外,还有独立语、插入语、提示语和特殊句式等。以插入语、小句、名物化等方式体现的情态表达形式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被纳入情态隐喻的范畴。我们认为,从情态意义出发,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对情态的表达形式进行系统、整体的描写和阐释很有必要。
最后,汉语学界从历时语法化角度对情态助动词进行的解释性研究较多,而以大型汉语语料库为基础对当代汉语中情态词的使用情况进行的研究较少。西方语言学近年着重观察当代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中情态词的使用频率和发展趋势。Leech基于美国和英国英语的书面语和口语语料库发现,在当代英语中,核心情态助动词的使用频率在迅速减退,而半助动词(如have to)的使用频率在逐步增加,并指出语法化和口语化是造成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在语言口语化的大趋势下,当代汉语中情态词的使用情况如何,是否与英语情态词一样具有相同的发展趋势值得探讨。
三、汉语情态研究的发展方向
在汉语语法研究跟国际日益接轨的大背景下,汉语情态研究的路径、内容、方法都将呈
现新的特点,未来汉语情态研究可以朝着以下几个方面发展:
首先,研究路径的多元化。由于从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形式语言学等角度对情态进行的阐释性研究仍然较少,在尊重汉语事实的基础上,汉语情态研究可以借鉴西方语言学理论来解决汉语情态研究中面临的一些问题。在应用理论的过程中,汉语情态的研究成果也可以修正或丰富当代语言学理论。具体而言,汉语情态研究可以从形式语义学、语用学、文体学、系统功能语言学等理论中吸取营养来扩大研究的范围和视角,以达到研究的融合发展。
其次,研究内容的深化。由于汉语学界在情态定义、情态类型、情态与语气的关系、情态动词的划界等方面尚未达成较统一认识,且争议较大,未来的汉语情态研究应该着重以厘清这些问题为目标,在主要问题上达成较为统一的认识。这样有利于汉语情态研究走向世界,有利于国外学者了解和借用汉语情态研究的主要成果。
最后,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汉语情态研究可以在大型书面和口语语料库的基础上描述情态语义系统,统计情态表达形式的分布频率,以准确获取书面语和口语两种不同语域下情态表达形式的语义特征。此外,还可以通过问卷调查、实验、统计分析等方法展开研究,为情态研究增加客观性和实证性。
综上所述,回顾了汉语学界近40年的情态研究成果,并结合西方语言学的情态研究,从研究路径和研究内容两方面着重讨论了汉语情态研究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建议,并指出了未来情态研究的主要发展方向。与西方语言学的情态研究相比,汉语情态研究仍然是一个年轻且相对薄弱的领域,需要更多的学者来关注和探索。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汉语情态研究将会不断深化和系统化,促进世界范围内情态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