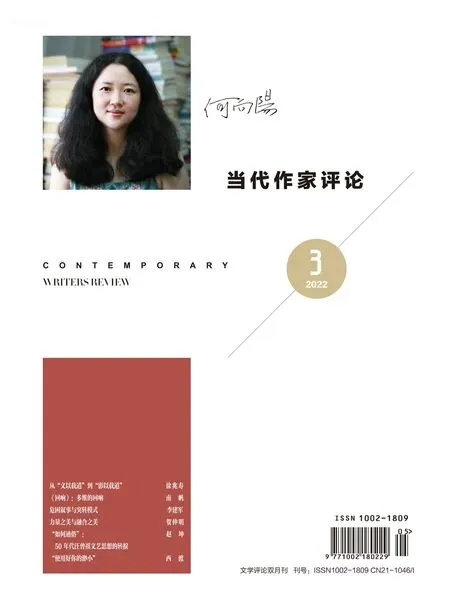诗与思的交响变奏
——略论何向阳文学批评的审美建构
何 微
在当代文学界,作为批评家的何向阳始终在场,颇具影响,却显沉静低调。她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成长于七八十年代,90年代已结下文学研究的累累硕果。何向阳经历了社会政治压力的缩紧与放开,走过文化浪潮的起伏激荡,见证了市场经济裹挟下文学及批评走向产业化。21世纪至今又以批评家、学者、作家以及诗人等多重叠加的身份参与文学实践,在中国当代文学话语场持续发散着光热。她以自身的文学批评实践成为文学批评“黄金时代”的旁证,也成为“人文精神大讨论”背景下所谓批评“无名”时期的在场者。正是在种种特殊文化环境的浸润影响下,何向阳的文学批评展现出颇具时代风貌的宏阔视野及萦绕其间的浓重的人文精神色彩。同时,何向阳的文学批评更因批评家对批评文体本身的审美建构追求而独具一格,呈现出个性化的批评风貌——在批评的空间里奏响一曲“诗”与“思”的交响变奏。
一、鲜活多样的随笔体实践
其二,何向阳的随笔体书评也是很引人注目的,数量可观,且涉猎内容广泛。这类随笔与读后感相类似,兴之所至,娓娓道来。通过随笔可见批评家广博的阅读趣味,书写对象纵横古今中外、人文艺术、历史社科。需要明确的是,何向阳的书评式批评虽结构松散,但大多数仍是精心撰写的长篇,是一种深度的鉴赏。批评家保持着共情、宽容与善意对待书籍,不偏激不尖酸,力求向读者传达成熟、深刻、负责的评价和论断。何向阳的随笔体书评,鲜明区别于90年代随着批评走向商业化之后,彼时大量泛滥的那种“快餐式”批评,即许多批评主体为了迎合报刊市场,发表一些对文学作品的即兴赏玩,这类批评文字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文艺批评应操持的学术品格。
二、诗情与理性相浑融
早在十三四岁时,何向阳已开始写诗,最初正是诗歌将其领入文学之门。迄今为止,何向阳已出版3本个人诗集《青衿》《锦瑟》和《刹那》。其中,2015年出版的《青衿》所收录的多是写于80年代的集中于何向阳在14岁至27岁间的诗作,如同一组记录她个人情感和精神自我成长史的私语“日记”。由这系列诗作中能隐约摸索到彼时诗人受“朦胧诗派”影响的影子,但其间又有自身独具一格的文雅风情和纯真的力量,被程光炜称赞为是在主流的文学史之外所不可忽视的“别样的八十年代诗歌”。2021年9月出版的《刹那》收录了写于2016年的108首诗和35幅摄影作品,它被何向阳自称为迄今为止她个人最重要的作品,其中真实记录了诗人生命中亲历的病弱、消逝、晦暗和重生,语词的力量和文字的背负同样的沉甸甸。在这部诗集里,时间放缓,肉身下沉,诗人凝视着幽暗之地,抚摸着微末之物。语言的呈现简洁,素朴,凝练,质地轻盈,而内在情感张力十足。一呼一吸的刹那之间,是她自身深处灵魂的低语。诗或许正是生命的隐喻,诗已然贯通了诗人的少年及至青年、中年,写诗成为这位批评家感怀万物的光与暗,言说爱与存在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形式。
再从批评家的本职身份出发,何向阳视野宏阔,思路活跃,治学严谨,更有文学研究员的专业文学素养加持,使得其批评实践能达到对批评对象的深入认识和从容表述。所以透过那些情感丰沛的批评文字,理性的踪迹依然清晰可见,显示着文艺批评所必不可少的客观、思辨以及不忘“求疵”的公正的批判精神。与此同时,由诗而发的热爱观照着何向阳的文学批评世界,对诗性的探索和追求鼓动着她不断探寻自我与文学、与世界的关系。她将写诗的经验熔铸进文学批评的写作,一方面是语言表达上的诗意追求,对语词的敏感滋养着批评家极富灵性的笔墨。何向阳注重批评的诗性表达,以偏重感性的抒情语言进行批评写作,通过譬喻、象征、类比等修辞方式阐说批评主体的审美体验,形成了一种情感饱满的、带着自身温度的批评语言。另一方面是“诗性思维”对批评的深入渗透。诗人的思考赋予批评更加细腻而敏锐的文学审美意识,这就扩展了批评的言说维度。何向阳以个体经验进入文本,并注重分析文本内蕴的作家的心理情感状态,在解密客体心灵的基础上寻求文本的审美性,试图建立起批评家与作家、与文本形象的情感沟通,而反对以先验的理论和凝固的标准来剪裁文学。
何向阳出色的批评篇章都是诗情与理性相浑融的产物,在批评的空间达到一种“诗”与“思”的微妙平衡。2001年,斩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理论评论奖”的批评篇章——《十二个:一九九八年的孩子》就充分彰显了“诗思交融”的个性化批评风格。作者筛选出12部小说中塑造的12个孩童角色,分节对由孩童组成的人物群像展开论述。这些被何向阳“选中”的孩子包括但不限于:莫言《拇指铐》中的阿义、王小波《绿毛水怪》中的妖妖、王安忆《忧伤的年代》中的“我”等,许多孩童角色放到如今依然是闪光的文学经典。这些孩子无一不带着悲伤的底色,在成人制定好规则的世界里碰撞得头破血流,却依然在内心为童真和良善保留了一个角落。虽大致以人物进行分节,但何向阳在论述时将不同角色进行勾连叙述,前后交互,显出结构上的随性。她完全将批评家的自我放入文本,通过“沉浸式”的批评,使得批评主体与文本、形象建立起一种灵性而微妙的,溢出批评之外的精神联系。何向阳对那些她阅读过的人物熟稔于心,当她乘坐火车途经高密乡时念及《拇指铐》中为救母流血的“阿义”,当她站在海边便无端怀念起《绿毛水怪》中永远沉入海底的向往音乐与自由的“妖妖”。小说中的孩子们似乎早已跃出纸面与批评者进行着精神上的对话。文章的整体语言是抒情的、形象的,又不乏颇具思考性的表达,呈现为一种随性随情且不乏深度的话语姿态。何向阳先从角色塑造层面进行审美赏析,又进入孩童精神世界深入剖析,最终凝结成她对这些文学作品所展现出的“母性精神”和“弱者之护”的肯定,再进一步提出批评者自身对“精神理想”和健康人性的深情呼唤,使得文章在迸发诗情的同时也不忘对文学的精神品格建构提出殷切的要求。
三、深挚、激越的文风
从整体风格出发,何向阳的批评文字呈现出深挚而激越的文风。她早期的批评文章不在数量上求多,但切入视点丰富,忧深思远,动辄就是几万字洋洋洒洒的长文,这固然需要宏阔的思想做支撑,更需要真实的关切和专注如一的热情。即便后来大量作随笔体批评,篇幅整体有所缩减,而论述从容深入,批评家主体的情感判断时时在场,使观点的机锋和文笔的飘逸相得益彰。这些都是作为“表”的风格的审美性,已然能窥见批评家的用情深挚和行文激越之处。
正因为怀着这一份深重的人文情怀去观照文学,她才会将“文学—人格”关系研究作为批评话语的中心,并且反复重申“心肠的界限”,展现出一个批评家对待作家、作品时必要的严苛与应有的宽容。纵览何向阳形形色色的文学研究篇章,从《文学:人格的投影》《不对位的人与“人”》到《人性世界的寻找》《原则、策略与知识分子个人——一个与生存、良知有关的话题》,再看她对张承志、曾卓、张宇、鲁迅、凯鲁亚克、曼殊斐尔、西蒙娜·薇依等写作者的人格个案分析,以及学术理论专著《人格论》的书写,言说形式从文学批评到文化散文再到建构自身文学理论体系的尝试,她始终将文学与人格/文化与人格关系作为批评展开的线索。透过批评文字去探寻何向阳的精神踪迹,能显见一种强烈的理想主义的道德热情,这股热情流溢于行文之中就成为人文精神价值的宣扬,显露出激越的风貌。何向阳始终伸张文学的“人格教育”意义,强调文学对知识分子精神层面的正面建构作用。这种执着自有背后的深意,从传统的眼光看,人格教化的目的在于道德养成,以现代理性的视角看,则关乎个性解放或个体的启蒙。在她的批评中,数次论及“道德”,它往往与人格、信仰、灵魂一起出现。其所理解的道德,绝非是死板僵化的束缚生命意志的戒律,而正是人性的自由解放,是落在实处地肯定生命,真挚热烈地抒发情感。何向阳的批评话语中显露出太多对文学及至所有人文造物的关心,事关孩童、弱者、人性、生命、时代、传统,无非因为这些事物都从根本的价值上牵扯着她,让她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虽然偶尔会于批判或褒扬的感怀呼号中显露出一种太“文”的书生意气,但绝少有把单薄的作品高扬化或是把丰富的作品简单化的情形。
整个90年代及至进入21世纪,何向阳以丰沛的批评能量和澎湃的创作激情活跃在当代文学话语场中,颇具代表性的文学评论集和学术随笔集都集中出版于21世纪之初。在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之后,何向阳的整体文学创作轨迹发生了变化,在她所自述的“为写作做减法”的过程中,首先是她个人的书写重心逐步转向诗歌创作,文学批评或学术随笔不再频繁而密集地产出。此外,何向阳的文学批评面貌逐渐转变,即文学理论研究主力地取代了文学批评鉴赏。随着其批评面貌整体向“偏学理、重研究”转向,相应地,其批评文风也愈发走向沉静和内敛。这或许是批评家自主选择和有意塑造的文风取向,同时也体现出一位成熟的批评家在经历了漫长的批评实践之后,理论言说走向体系化建构的必然趋势。但无论研究重心和批评文风如何变换,何向阳依旧显示着她的丰富,既是思想的开阔,也是心灵的富足。深挚、激越的文风与批评家主体精神的交相辉映,在何向阳那独具一格的、思诗交融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得到了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