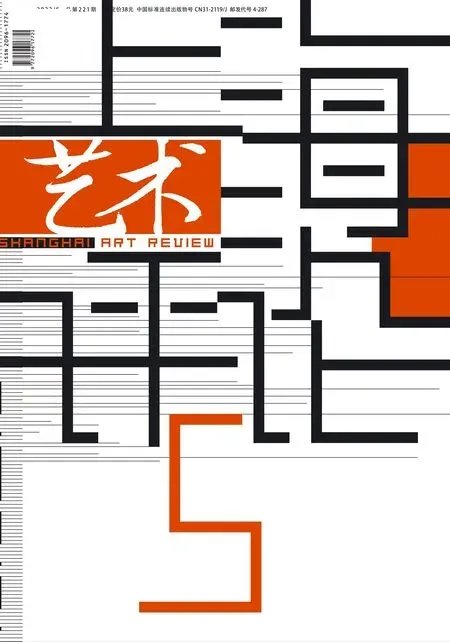海派主流电影叙事:通俗剧的命名及其通约性
黄望莉 毛旭峰
在考察“影戏观”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其影像来源和理论资源都与上海电影史有着无法分割的关系。海派电影的形成过程逐步完善出一个“超稳定”叙事系统,也就是“影戏观”。其后,围绕着这一学术观念,中国很多学者给予了更多的补充性论述。随着华语电影实践和理论发展,“通俗剧”叙事研究嫁接起“影戏观”,为我们今天重新审视中国电影创作传统中的“超稳定结构”、海派电影文化先锋性的价值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讨论空间。
“影戏观”可以认为是海派电影实践和理论体系构建过程中有着绝对价值的理论。然而,当今天重新思考“影戏观”时,正如陈犀禾所言,随着自身体系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更需要一个词汇的重新界定。回到历史现场,梳理“影戏观”的生发过程,看到其内在的“通俗叙事”的结构、价值取向和类型生产,并将视野拓展至今天的中国电影正在发生的现象,可以发现,“影戏观”是对“通俗叙事”的借鉴之后,是“中国化”的重要本体美学上的总结,因而两者之间具有通约性,而“通俗叙事”作为一种形态也成为中国百年电影叙事结构无法忽视的“超稳定系统”。
“影戏观”:早期海派电影的内在肌理
1924年,周剑云主导成立了昌明电影函授学校,他用时四年为该校编写《电影讲义》作为教材,本书分为十章,每一章都以上海方言“影戏”来命名当时的电影。书中,他极为强调“戏”的思维以及剧本的文学性,这同另一位早期电影人侯曜不谋而合:“影戏是戏剧的一种,凡戏剧所有的价值它都具备。”1正如陈犀禾所言:“‘影戏’对电影的基本认识是:戏是电影之本,而影只是完成戏的表现手段。”2近期发现的“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在上海“新舞台”的放映说明书也能说明电影与戏曲之间的关系。中国观众的“戏曲经验”成为电影嫁接最便捷的艺术形式,这张《定军山》在上海新舞台的放映说明书让我们“不仅获得了中国第一部影片的信息,更明确了一百多年前京沪两地戏曲文化的流动和转型,以及影像媒介为京沪两地,尤其是‘海派京剧’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佐证材料”。3
毫无疑问,在早期中国电影人的认知中,嫁接戏剧、戏曲的艺术经验来寻找电影这一新媒介的创作路径是一种本能,或者说是一种条件反射。除了与传统戏曲的结合之外,文明戏也为早期中国电影提供了资源。如影片《黑籍冤魂》的故事来源直接取材于同名文明戏,而且从郑正秋开始就期盼改编该戏,直到张石川、管海峰实现拍摄,并再次引起轰动。正如吴迎君在文章中所指出的:“侯曜在《影戏剧本作法》的大文本中建构的是一种‘中西互合’价值观背景,同时具有‘(大)戏剧’意识和电影本土意识的‘影戏观’知识理路。”4这再一次提醒了今天分析早期中国电影人的电影理论体系、电影观念和电影实践时,他们的戏剧活动对他们电影创作的影响。这种“大戏剧观”不仅后来体现在《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中,更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黄佐临的“大戏剧观”的创作和理论陈述中。
在考察“影戏观”的过程中,颜纯钧便对陈犀禾所提出的“影戏美学——中国电影理论中的超稳定系统”持否定态度。在陈犀禾看来,影戏美学“统治了中国的电影观念和电影实践”,并“作为一个观念系统它以自己为主体,吸收和同化外来美学的影响,作为生成和壮大自己的养料”,5在经历两次断裂之后,仍发挥着巨大影响。而颜纯钧认为:“《影戏剧本作法》整个建立在西方戏剧理论和戏剧美学的基础之上,这是显而易见的。以这样一部深受西方戏剧理论和戏剧美学影响的电影剧作理论来论证‘影戏’是中国电影美学的核心概念,认为‘影戏’观是中国电影美学的理论体系,岂非咄咄怪事!”故此,他认为“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植根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超稳定的电影美学理论体系。”6尽管颜纯钧事后承认,自己的论述有所偏颇。但是,确实也提出了一个“影戏观”理论建构中一个被忽视的面向,即:早期中国电影与好莱坞“情节剧”电影之间的关系问题。
近些年,一些海外学者通过对格里菲斯的《赖婚》一片在中国的传播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到好莱坞情节剧对中国电影叙事的影响。如何其亮教授在其文章中考察出:“沪上观影者,莫不知有《赖婚》。”“甚至上海民新电影公司二十年代末在巴黎推广其最新影片《西厢记》时,宣称《西厢记》就是中国的Way Down East。”7可见,《赖婚》对中国早期电影叙事能力的影响也同样影响了当时侯曜的创作。其后,上海影人们也据此制作了诸如同名电影《赖婚》,20世纪30年代但杜宇的《失足恨》(1932)更是照搬了《赖婚》的故事情节。由此可见,中国电影人对《赖婚》的推崇体现好莱坞通俗剧在中国的巨大影响力。
据考证,由周瘦鹃翻译的《赖婚》收益颇丰,也对当时上海通俗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冲击。从中也可以考察“鸳蝴派”文人参与电影编导,包括制片主导早期电影的生产,也对早期上海电影的故事母题和价值取向产生重大影响。具体看来,“鸳蝴派”与电影的关系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电影导演对其作品进行改编;一种是“鸳蝴派”文人独自创作的电影剧本。不仅如此,一些学者也考察到“鸳蝴派”文人投身电影界在早期中国电影史上一共有两次:一次是20世纪20年代初期到30年代初左翼电影运动兴起前;一次是孤岛电影时期,8他们不仅对爱情片,如《风雨之夜》的复杂表达,也随后对古装片、武侠片和神怪片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这些影片获得空前的市场反响。尤其是武侠片以通俗叙事,尤其是曲折离奇的情节获得较好的商业表现,也在叙事中传递家国主义。
总之,早期海派影人在总结和思考电影本体艺术形态的时候,归纳了我们今天所谓的“影戏观”创作体系,从而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充满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并吸收西方新艺术的营养的叙事模式。可以说“影戏观”是内在于中国生成出来的概念,海派电影则是呈现“影戏观”的重要窗口,它是传统戏曲与文明戏、早期好莱坞电影的以及“鸳蝴派”三者的汇集地。
“通俗现代性”:连接起时代的话语体系
在钟大丰看来:“‘影戏’理论是由这样一个双层结构的理论框架构成的:在外层是一个带有浓厚戏剧化色彩的技巧理论体系……在戏剧化外衣的掩盖下,‘影戏’理论框架的深层结构中,则孕育着一种从功能目的论出发的电影叙事本体论。”9其实,在早期电影发生的开端,电影在嫁接起文明戏的时候,《黑籍冤魂》能够吸引第一代影人的原因就在于针砭时弊,将“鸦片”对于现代国家建立的危害示于众人。此后,海派早期电影中大量的关于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教条主义的批评,表达改良主义思想,包括对封建余毒下的女性境遇的书写等,无不体现出“影戏观”中所发挥的社会批判功能。青年学者田亦洲认为,侯曜早期“影戏观”中在对西方戏剧艺术吸收和学习的过程中,也继承了两大充满现代意味的价值评判和取向:在面向现实主义创作中,一方面,在挪用“易卜生”问题剧的艺术实践过程中,也顺理成章的将为“为人生”的“易卜生主义”纳入他“影戏观”的创作中,如《玩偶之家》和《国民公敌》等;另一方面,在接受托尔斯泰“艺术不仅起源于情感,而且本身就是情感”的核心思想之后,也在自己的影像中修正“托尔斯泰主义”,着重强调“表现人生,批评人生,调和人生,美化人生”“以情化人”的崇尚“忏悔”精神来超越法律和道德的约束,10如《复活的玫瑰》等。从对侯曜的分析中,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他所代表的上海早期影人在对高度戏剧化的情节剧模式的选择目的是为了更易于通往其社会教化功能的理想之路,并且成为中国通俗叙事中的价值传统。
在汉森看来:“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上海电影代表了一种独特的白话现代主义,它生发于美国及其他外来模式的复杂交汇,同时又汲取并改变了中国戏剧、文学、绘画、印刷品文化诸方面通俗和现代主义的传统。”11侯曜对国外名剧的中国式改写从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情节剧”所具有的跨区域、跨文化传播的有效“超稳定结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其“白话性”/通俗性的价值。正如前文所论,发轫于上海的通俗剧叙事传统,既有戏剧艺术的创作经验,也融合了来自流行的“鸳蝴文学”对都市文化脉动的人文资源,更是对好莱坞的影像类型叙事等能力上的欣然接受,使得海派通俗叙事传统天然就有着都市现代性的气质。一如张真指出:“它(鸳蝴派文学)成为现代白话文化一个活跃的元素和催化剂,早期中国电影得以从这种白话文化中诞生,并转而深刻地重塑了这种文学类型”。12其后,他在描述上海早期中国电影的跨文化特性时,通过《跨国通俗剧,文艺片,以及孤儿想象》一文中追索中西方孤儿题材通俗剧跨国谱系,并指出“孤儿主题在跨国通俗剧形态,以及全球对现代经验的通俗化(或曰白话现代)表达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13在张真的分析中,能够看到通俗剧如何成为一种“跨国白话”,如何在不同国家与地区进行“在地化”变奏。张真延续着其师米莲姆·布拉图·汉森(Miriam Bratu Hansen)的思路。在汉森那里,“好莱坞不仅仅只是传播影像和声音;它还制造了一种新的感觉机制并使之全球化;它建立了或者正试图建立一系列新的主体性(主观思想)和主题”。14早期海派电影对西方电影的“翻拍”,实际上也是“现代性和现代化进程的话语翻译、杂体化并加以再创造”的过程,15而侯曜的电影也依然是“白话现代主义”中国在地化的例证。
在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1930 —— 1945)》中,将上海的叙事空间放置于都市语境下讨论,明确电影院是现代都市崛起的一种文化景观,而它又与上海电影之间相伴相生。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电影中更加凸显都市现代城市景观,如电影院;物质现代性的呈现,如唱片机、欧式家具、别针等;现代的都市欲望,如舞场、交际花等。这些景观在创作者的影像中呈现与批判并置,作为一种“感官反应场”,充斥着白话/通俗现代性体验。新中国成立后,海派电影中的都市现代性,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诸多话语体系而发生变化,并将现代性的体验和价值体系成功的植入革命的现代性体验之中。
新中国的工业化生产、商业体系的形态、社会主义现代化景观等在“十七年”初期的电影中以类型片的形态呈现出来。这里选取两个颇具代表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城”的叙事空间的影片:海燕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羊城暗哨》,以新中国成立后的商业化程度较高的广州为叙事空间,虽说广州是冷战时期谍战的桥头堡,但是影片通过侦查员的流动却向观众展现了一个现代的、社会主义的广州。人来车往的海珠桥、越秀山、永汉路骑楼和百年老字号茶楼惠如楼等具有鲜明特色的广州建筑,在明亮色调映衬下,感受着社会主义现代生活的体验。同时,影片也以工厂、烟囱、轮船及汽笛声等细节穿插加入到全球电影的冷战叙事之中,成为中国的“冷战修辞”,也充分说明了国家意志的宣传与教化。电影《国庆十点钟》,说的是某北方重型工业城市空间,以汽车驶过山间进入城市作为开始,汽车在此不仅是单纯的交通工具,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象征,司机群体作为与现代交通工具最密切的群体,他们与社会主义新生代——儿童,不仅维护着新中国昂扬的建设精神,也共同扮演着维护新中国社会安全的重任。
陈波儿曾思考:“记得二中全会后,我们曾经立刻想到反映城市工业生产建设,并联系到反特斗争。但工厂生产中所发生的事很多,我们要表现哪一个问题呢?千头万绪实在有所困难。”16“十七年”的“反特”类型片的生产,创造性地回答了陈波儿的疑问,它对传统通俗叙事的“现代化”改造,也呈现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感官反应场”,呈现出“革命现代性”的特质。

《芙蓉镇》
作为“超稳定系统”的通俗叙事
新时期的开端,谢晋《芙蓉镇》《牧马人》《天云山传奇》《高山下的花环》等反思影片所形成的文化效应,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终于引发了一场争论。其肇始者朱大可的一文《论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1986)所批评的谢晋电影中存在的四种道德问题:好人蒙冤、价值发现、道德感化和善必胜恶等“谢晋模式”。在今天看来无疑是对谢晋所代表的通俗剧叙事模式进行了完整的归纳和总结。“谢晋模式”中的“政治与道德及其置换的秘密”(汪晖语)所引发的新时期之初大众的狂欢也恰恰是“易卜生主义”与托尔斯泰的“忏悔主义”的再次胜利。在朱大可等持有先锋理念的批评者看来,“谢晋模式”在1986年之后呈现出所谓的“保守主义”,如果放到谢晋拍摄《天云山传奇》等“伤痕文学”“政治反思”盛行的时代中,他冒着政治风险拍摄的这些影片无疑是最具有“弥合”时代“创伤”的作用,也是符合时代“先进性”的。因此,在理解通俗叙事影片中“保守主义”应当是“滑动”的,是随着不同的时代语境的价值标准来评说的。
1985年,李陀与陈荒煤之间《关于“情节剧”的通信》已经暗示了在以“先锋”姿态自诩的主流创作话语下,认识到“(情节剧)是一门很大的学问。美国好莱坞制作的影片绝大多数都是情节剧,这种影片曾风靡世界,很少有人能与之抗衡”,即便存在法国诗意现实主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等流派与之抗衡,“但是,许多变革者所极力攻击的情节剧,却没有被这场变革淘汰。不是抛弃,而是扬弃。电影中的情节剧因素不断进行自我改造,顽强地生存下来”。17可见,这是李陀在思考第五代“探索片”之后,对中国电影发展的再认识,他当然不排斥影像探索,但仍重视通俗叙事的重要作用。2009年,上海大学举办题为“通俗现代性、想象中国与跨文化阐释”的谢晋电影国际学术研讨会集结了当时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大量海外学成回来的学者,如陈犀禾、马宁、孙绍谊等,将谢晋纳入到国际视野中,被置于通俗叙事的维度来重新考察。
马宁将中国通俗剧范式追溯至传统戏曲中的二元对立结构,以此来关注世俗生活和发挥伦理教化作用。因这种通俗剧手法“让广大缺乏教育的农民和百姓可以寓教于乐”,便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新社会政治秩序合法化的有力文化手段”,并在六七十年代完成了“政治通俗剧叙事范式对传统通俗剧叙事范式做了置换和变革”这一过程。18他通过对谢晋电影中女性形象的仔细分析,完成对他电影的空间性与主体性的讨论,在他看来,女性形象是解码中国通俗叙事的关键所在。几乎同时,西方学术界在七八十年代展开了对通俗剧/情节剧的研究,如斯汀·格莱德希尔(Christine Gledhill)的《家是心的安居之所:情节剧和女性电影研究》(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 Studies in Melodrama and the Woman's Film)和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s)的《情节剧想象:巴尔扎克、亨利·詹姆斯、情节剧和过度模式》(The Melodramatic Imagination: Balzac, Henry James, Melodrama, and the Mode of Excess)等著作。中西方学术界几乎同时将目光聚焦于通俗剧上,足以证明它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价值。
通俗叙事在近年来的影视创作中越来越重要。第五代导演仍旧选择通俗叙事作为基本叙事策略,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2012)将情感伦理置于前景,以此来讨论时代背景下的个人命运;张艺谋的《悬崖之上》(2021)延续了“十七年”“谍战片”的通俗叙事模式,并融合了他自己的美学特质建构了新时代话语体系下的新的类型景观。第六代导演贾樟柯的《山河故人》(2015)、《江湖儿女》(2018),王小帅的《地久天长》(2019)等也都以通俗叙事为基础,讲述了时代变迁中的个人与家庭的史诗。而通俗叙事的跨文化特性也给香港电影人北上合拍电影提供了可能,尤其是近年来的新主流电影,如《湄公河行动》(2016)、《红海行动》(2018)、《中国机长》(2019)等影片都较好地融合了通俗叙事、美学表达和主流价值观的传递。新锐导演文牧野的《我不是药神》(2018)和《奇迹·笨小孩》(2022)也以通俗叙事讲述个人如何与时代“斗争”,并完成主流价值表达。尤其是在电视剧等新媒介的影像生产上,近年来颇受观众欢迎的电视剧,包括《山海情》(2021)、《人世间》(2022)等,无不选择通俗叙事模式来呈现出个体与时代之间的张力。
结语
通过对早期“影戏观”的分析,以及简要梳理“通俗叙事”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通俗剧叙事模式在中国最初被接受为“影戏观”的过程中,实现了在地化的过程,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内在为中国的“跨文化”表达。这种“超稳定结构”,它不仅拥有中国电影的叙事传统的理论价值,更在当下中国“讲好中国故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以1907—1921年《东方杂志》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