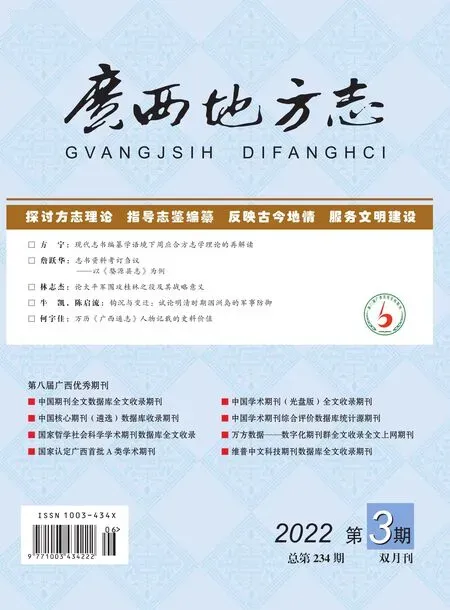现代志书编纂学语境下周应合方志学理论的再解读
方 宁
(宁波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浙江 宁波 315042)
周应合(1213—1280),字淳叟,自号溪园先生,江西省武宁县人。南宋著名的方志学家。他参与编纂的《江陵志》和景定《建康志》均享有盛名。尤其是景定《建康志》“井井有法”,被后世奉为志书编纂的圭臬,“志乘家皆宗之”。[1]学界对周应合生平与景定《建康志》均有比较深入的研究,①但对其方志学理论缺乏系统的提炼,本文通过梳理周应合的方志学理论,阐述其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为现代方志的编纂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周应合生平及其志书编纂实践
周应合为南宋隆兴府(今南昌市)武宁县人。七岁开始学习《诗经》《尚书》,便已通晓大义。十七岁时,父母相继去世,随后尽心侍奉祖父。其祖父周友贤,嘉定戊辰(1208)进士,历官敷文阁学士,“立朝劲直敢言”“遇事多所匡正”。应合深受祖父的影响。早年熟习词赋。绍定四年(1231),因以词赋应乡举不中,故摒弃辞藻华丽的词赋之学,开始研究《春秋》等经书,“结庐深密,探微索幽”,跟随他学习的士人越来越多。淳祐庚戌(1250)中进士,被选授为江陵府府学教授。待任期间,回到故乡,教授生徒。又与乡党一道设立三条乡约:一为“贷贫民”;二为“济疾苦”;三为“赈游末”。遇到饥荒之年,向贫民贷发财物,救助疾病、困苦之人和游民、手工业者和商贩。宝祐元年(1253),就任江陵府府学教授。期间,讲授经学,首选《孟子》,因其见解精辟,深受学者拥戴。期间,参与《江陵府志》的编纂,该志被认为“记载有法”。当时宣抚荆湖的赵葵欲征其为僚属,应合以志书未成而谢绝。宝祐六年(1258),马光祖为端明殿学士、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召应合为其幕僚。①据景定《建康志》《马光祖序》载:“宝祐丁巳(1257)光祖蒙恩来司留钥,因阅前志,编摩在念,一年而勤民,二年而整郡,三年而易阃荆州。”以此推算,任职京湖制置使时间应为景定元年(1260)。而据其后《行宫留守》所载“马光祖,宝祐二年(1254)八月以宝文阁直学士、安抚使兼行宫留守”,三年后,应为宝祐五年(1257)任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
开庆元年(1259),马光祖以资政殿大学士、江东安抚使兼任建康知府。②一说景定元年(1260)。据景定《建康志》《马光祖序》所载“己未(1259)重来(建康)”,又据其后《行宫留守》所载:“开庆元年(1259)三月以资政殿学士再为安抚使兼行宫留守”,可以确定任职江东安抚使、建康知府时间应为开庆元年(1259),而非景定元年(1260)。应合充江南东路安抚司干办公事兼明道书院山长,编辑《二程遗语》若干卷。景定二年(1261),受马光祖嘱托编纂《金陵府志》。期间,被召入朝廷任史馆检阅。[2]因上疏揭发丞相贾似道贪庸误国,触怒宋理宗,被贬为饶州通判。咸淳三年(1267),主管华州云台观。四年(1268),通判宁国府,大修学宫,免除输苗之不便。德祐元年(1275),任江西瑞州知州,因与安抚使意见不合,去官归里。晚年,被其子天骥接至吉州(今江西省吉安市)奉养,应合“却甘茹蔬,感慨遁迹”,在吉州颐养天年。至元十七年(1280)卒,享年六十八岁。葬于吉水县(今江西省吉水县)同水乡臻善里鹧鸪山之原。应合著有《洪崖集》和《溪园集》。时人程公许称其“理义则濂溪,章表似平园”。[3]
景定二年(1261),马光祖授意开书局于郡圃之钟山阁,主纂周应合与马光祖两人“相与研古订今”“定凡例而裒篇帙”。应合参阅乾道、庆元两部《建康志》,将其合而为一,并补充庆元至景定六十余年事,正讹补缺,历经四个多月,最终修成总计五十卷的景定《建康志》。该志首为《留都录》四卷。纲目设计按志序所载:“其次为地理图、为侯牧表、为志、为传,合为五十卷,表起于周元王四年越城长干之时,以至于今千七百载,年经类纬,曰时,曰地,曰人,曰事,类之所由分也。志凡十,一曰疆域,二曰山川,三曰城阙,四曰官守,五曰儒学,六曰文籍,七曰武卫,八曰田赋,九曰风土,十曰祠祀;传凡十,一曰正学,二曰孝悌,三曰节义,四曰忠勋,五曰直臣,六曰治行,七曰耆旧,八曰隐德,九曰儒雅,十曰正女。”[4]层次清晰,内容完备。该志被后世修志者奉为典范,也是周应合方志学理论的重要体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援据该洽,条理详明,凡所考辨,俱见典核”。[5]该志流传甚广,有宋抄本,明影宋抄本和清抄本多种,以及1985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精装二册本。[6]
二、周应合的方志编纂学理论及其新内涵
周应合在修志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方志编纂学理论,这些理论集中体现在景定《建康志》卷首的《景定修志本末》中。其一,修志首需“定凡例”,也就是确定志书的体例及其规范。要使一部志书体例完备,一方面是篇章结构的确立,另一方面是多种体裁的运用。由于建康“自吴以来,国都于此”“天禧之为潜邸”“建炎、绍兴之建行宫”,军事、政治地位重要,要记载的内容繁多,包含“显谟承烈”“凤阙龙章”等重要内容,但之前记载建康典故的乾道、宝庆志及其他历史文献,将一些重要内容“混于六朝之编,列于庶事之目”,而且“宫府杂载,君臣并纪”,归类不当,层级不明,体例不全,记载混乱。所以,周应合认为,志书的编纂确立篇目框架很重要。他在《景定修志本末》一文中阐述《建康志》的篇目结构,首先,“修留都宫城录,冠于书首”。其次,设建康地图、年表。再次,设“十志”,即疆域志、山川志、城阙志、官守志、儒学志、文籍志、武卫志、田赋志、风土志、祠祀志,疆域、山川、城阙等志下又依据内容多寡设数量不等的分目,如疆域志下设镇市、乡村、坊里、铺驿、道路、桥航、津渡、堰埭八个分目。再次,设“十传”,即正学传、孝悌传、节义传、忠勋传、直臣传、治行传、耆旧传、隐德传、儒雅传、贞女传。“传之后为拾遗,图之后为地名辨”。表之纬为四:曰时,记年世、甲子;曰地,记疆土分合、都邑更改;曰人,记牧守更代、官制因革;曰事,著成败得失之迹,以寓劝戒。又将考证、古今记咏方尺等内容以小号字附于正文之后,录、图、表、志、传卷首均设“序”。以不同文体承载不同内容,条目之下再设分目,各种文体的卷首添设序,篇目设计分类得当、层级分明。《江陵志》的“粲然有论”,《建康志》的“井井有法”,正是由于篇目设置的严谨、合理。体裁是否多样也是志书体例是否完备的重要标准。周应合在修《江陵志》时,“为图二十,附之以辨,其次为表、为志、为传、为拾遗”,[7]就已经在志书编纂中运用了多种体裁。即使如此,他还是认为“所载犹不能备”。所以,在修纂《建康志》时运用录、图、辨、表、志、传、记、序等体裁,以便承载更多的内容。由于注重多种体裁的运用,其编纂的志书体现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等特点。
现代方志编纂第一步是要确立篇章结构。篇目是志书内容的高度凝聚和概括提要,它体现志书内容的组织结构,决定志书的整体质量。设置出一个合理、严谨的篇目结构既为志书编纂奠定坚实基础,也为志书质量提供重要保障。周应合的志书篇目归类得当、层级分明,基本符合现代志书对篇目设置的要求。现代志书框架结构一般为编章节目体,卷首设有序、图、总述,每编、每章前设“概述”,另设附录,编后有记。《建康志》的框架结构不仅为旧志提供了一种典范,也为现代志书所继承和发扬。现代方志要求“体裁运用得当,以志为主”,综合运用到述、记、志、传、图、照、表、录、索引等多种体裁。而周应合的志书编纂理念中早已提及以不同体裁来记载不同内容。周应合修志理论中强调篇章结构的确立和多种体裁的运用,为现代志书编纂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其二,修志又需“广搜访”,也就是广泛地搜集资料。周应合认为,志书修纂想要内容完备,资料搜集就要尽可能的详细,这些资料包括官方、民间各种类型的案牍、文献。一是官方现存的正式公文、个人文书等档案资料。资料类型涉及到幕府、县、节镇等官方之间往来的正式公文,官方经手的寓公、诸乡士友、戎帅、将校等私人之间交往的文书,内容上包含“一事一物一诗一文”,时间上“不以早晚”,数量上“不以多寡”,“各随所得,报批本局”,将这些资料归类整理,加以考订后,再用于编纂。二是私人所有的各类文献资料。不仅包含上世家传、行状、墓志、神道碑及所著书文,还包括先世所得御札、勅书、名贤往来书牍,甚至还包括“博物洽闻之士能记古今事迹,有他人所不知者,并请具述”的口述资料。内容涵盖相当广泛,即使是“山巅、水涯古今高人、逸士有卓行而不求闻达者”,对于世外隐士的事迹也要求“冥搜详述以报本局”。另外,还注意拓宽资料搜集的渠道,让民众向修志机构自行报送资料。在府门设置资料柜,三日一开,允许“吏民父老中有记忆旧闻关于图志者”,“具述实封投柜”。并且对“闻见最博、考证最精者”,“当议优崇”;对“类呈条具最多而事迹皆实者”,“当行犒赏”。[8]对于提供资料者给予奖励。
现代志书的编纂也十分重视资料的搜集。志书资料主要包括档案资料、期刊资料、报纸资料、文献资料、口述资料、实物资料、网络资料、内部资料等。其中档案资料包涵的内容最广泛,包括已入档的社会各部门的工作总结、工作年报、各类文件等,还包括已入档的书籍、报刊、影像、音频、图照等资料。内部资料主要是指部门内部收藏的内部刊物、工作总结、工作报告、调查研究报告、年报、统计报表、各类文件通知等。文献资料主要是指已公开出版的专著、各类型读物、各类古籍与家谱、地方志等。现代志书资料征集主要有官方和民间两种渠道,也非常关注资料类型的广泛性和征集方式的多样性。周应合方志学理论中在资料范围的界定、征集渠道的拓宽、征集方式的创新等方面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其中强调“搜访不厌其详”的资料征集态度,要求“一事一物一诗一文”的资料征集范围,允许“具述实封投柜”的资料征集方式都值得现代修志者借鉴和学习。
其三,修志还需“详参订”,也就是志稿需要反复修改订正。周应合认为,志稿最少需三次修改。每卷修成初稿后,用紫袋密封送给学富才宏的诸司幕府参佐宾僚审读志稿,审稿专家将不恰当和不详尽的内容“批注行间”,编纂者根据专家意见对初稿内容进行删除、修改、订正。次稿完成后,与初稿一样,再以紫袋密封传呈专家第二次审稿,专家审完后再行修改。等到定稿形成后,送给主修马光祖钧览,“仰求笔削”,主修审改后,再将志稿出版印刷。志稿完成后,还让书吏謄抄草稿,书写样板,保存副本。现代志书编纂一般需经历“三审三校”:初稿形成后,交付专家审读,召开初审会,根据初审专家意见,修改志稿,形成复审稿;复审稿形成后,再交付专家审读,召开复审会,根据复审专家意见,修改志稿,形成终审稿;终审稿形成后,第三次交付专家审读,召开终审会,根据终审专家意见,修改志稿。最后,由主编统稿后交付出版社出版。周应合非常重视志稿的修改完善,其“详参订”的方志学理论在志稿修改流程上给现代方志的编纂提供了许多参考。在志书编纂过程中,周应合“夜考古书,朝订今事”,非常重视对原始资料的考订。对征集的资料,“以凭类聚考订增修”。对志稿的内容尽可能地“削去怪妄,订正事实”。在志稿中专设《地名辨》,“志之中各著事迹,各为考证”,[9]对志稿引用的资料考镜源流、正讹纠谬、释疑辨义,重加考证,以小号字注于正文之后。对原始资料的考订和考证方法的运用应引起现代志书编纂者的重视,这也是现代许多志书编纂所欠缺的地方。
其四,修志另需“分事任”,也就是修志需要统筹分配任务。因为《建康志》的编修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周应合认为单凭一人之力无法完成,而需“凭借众力”,才能“早有成书之期”。于是他向马光祖“乞请官十员,招士友数人”进入修志机构,“同功商榷,分项修纂”。不过这一要求未得到马光祖的许可。后来,即使应合“夜以继日,疲精书传,极力丹铅”,也无法按时完成志稿,导致“修书之稿未半,刻梓之匠已集”,于是他叫来儿子周天骥、女婿吴畴帮助修志。志稿完成后,他又请求“选差局吏两名,分管书局事务;书吏十名,謄类草稿,书写板样;客司虞候四名,以备关借文籍,传呈书稿”,专人处理抄录、书写、关借、传呈等事务。[10]现代志书特别是地方综合志书的编纂属于一项大型的文化工程,需要专门设立志书编纂班子,以各司其职、各行其事,凭借众手,方能成志。
三、结 语
周应合修纂的《江陵志》,体例完备,记载有法。而受马光祖之托修纂的景定《建康志》,亦“井井有法”,成为后世志书编纂的圭臬,其体例为后世编志者所效法。景定《建康志》还是南京市现存最早的志书,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周应合“博物洽闻,学力充赡”,擅长义理之学,兼及文章之术,而其方志学成就犹为显著,享誉后世。他在修志实践中形成“定凡例”“分事任”“广搜访”“详参订”等编纂理论,为现代修志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借鉴,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他即是一名理学家、政论家,又是一名方志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