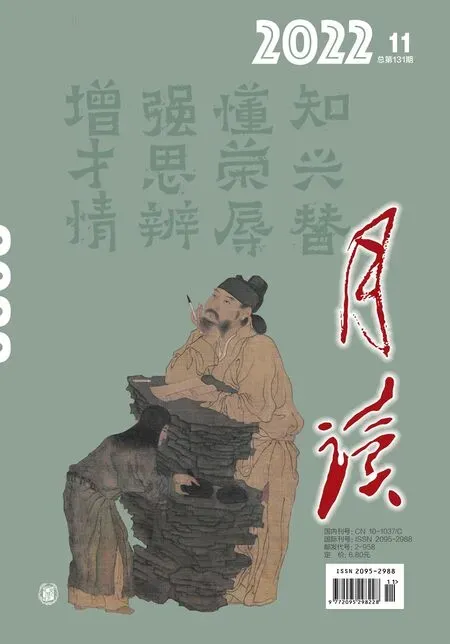《群书治要》中的德法兼治思想
◎ 刘余莉
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之间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结合《群书治要》中的德法兼治思想,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依法治国的理念。
一、禁令不明的危害与原因
《抱朴子》中讲:“禁令不明,而严刑以静乱;庙算不精,而穷兵以侵邻。犹钐禾以讨蝗虫,伐木以杀蠹蝎,食毒以中蚤虱,撤舍以逐雀鼠也。”意思是说,禁令不明确,却用严刑来平定乱象;朝廷对国家大事的谋划不当,却竭尽兵力去侵犯邻国。这就好像割掉禾苗以消灭蝗虫,砍掉树木以消灭蛀虫,吞下毒药以杀死跳蚤、虱子,拆除房舍以驱逐麻雀和老鼠一样。可见,如果遇到问题不能向内挖掘原因,从根本深入求解,而仅仅从枝末上解决问题,甚至意气用事、对外转嫁危机,就会使问题愈演愈烈,最终自取灭亡。
“禁令不明,而严刑以静乱”说明,社会出现乱象、国家得不到治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禁令不明确,礼法制度不健全,人们不知道应当提倡什么、禁止什么,就会肆意妄为;做人没有伦理道德的底线,就会导致人伦关系的混乱;国家没有礼法制度,就会出现社会秩序的混乱。可见明确的礼法制度,对于治国安邦至关重要。
社会出现礼法制度不明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无法可依。导致禁令不明的首要原因,就是没有礼法可依。人们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混乱,没有行为准则,就会出现“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墨子》)的状况。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却没有统一的道德观念。
在古代中国,一个朝代取得政权之后,一般不久就要制礼作乐,使整个国家都有礼法制度可循。一切都有了礼法标准,人人依照行为,社会才得以安定。古人做人都要遵循五伦、八德。现在人如果不学习五伦八德,就会出现悖德乱礼的行为而不知不觉。例如,曾有小偷作案被捉,警察对他说:“你这样违法乱纪是不孝的行为。”但是小偷却很不服气,说:“你怎么知道我不孝?我对父母很好。”因为他不知道“德有伤,贻亲羞”的道理,所以才会认为自己对父母好就是孝,而不知道孝包含了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慧、养父母之志等多方面的内容。这就是因为不明确孝的标准所致。
第二,朝令夕改。如果政令常常变化,而且没有连贯性,也会导致禁令不明。而朝令夕改的现象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没有抓住治国理政的根本,致使问题层出不穷,而不得不修改政令。有人不能体会古人制礼作乐是源于本性的自然之德,反而嘲笑礼乐制度是专制帝王奴役人民的工具,而师心自用的结果必然是政策的频繁更改。中国古人讲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性德,是自然之道,不仅是个人修身的标准,也是治理国家的原则;不仅在古代适用,在今天也适用。因此仁义礼智信被称为“五常”,就是因为它是常理常道。但由于今人对传统文化一度丧失了信心,不懂得遵循自然之道,而用自己的智巧制定了很多规则,却无益问题的解决,行不通时就要不断更改,致使禁令很难明确。
第三,禁令繁多。“少则得,多则惑”(《道德经》)。禁令繁复则会导致百姓迷惑。《盐铁论》中讲:“道径众,民不知所由也;法令众,人不知所避也。”道路多了,人们不知道该走哪条路;法令过多,老百姓不知道应该怎样去避免触犯法禁。“故王者之制法也,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旷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因此,圣明的君主制定法令,如日月一样昭明,所以民众不会迷惑;像大路一样清楚明白,所以民众不会困惑。“幽隐远方,折乎知之;愚夫童妇,咸知所避。”即使是偏僻幽隐的遥远之地,愚昧无知的人,乃至妇女儿童,都知道什么是不法的行为而不去触犯。“是故法令不犯,而狱犴不用也。”这样就没有人违犯法令,而监狱和刑具也都用不上了。
法令过多会使人民迷惑。而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人们误以为社会乱象丛生的原因是法律不够严密,监督机制不够健全,却没有意识到伦理道德教育的缺失才是社会问题的根本症结。因此施政者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制定法律法规上,而忽视了道德教育。
西方著名的美德伦理学家麦金泰尔在他的《追寻美德》和《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中讲到:“对于法律的应用而言,它仅仅对那些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才有可能发挥作用。”换句话说,法律和规则是由人来制定的,如果立法者没有正义的美德,他只想到小集团的利益,不可能制定出公平合理的制度;而即使正义的规则制度制定出来了,还是要由人来推行,如果执法者没有正义的美德,也不可能把合理的规则推行好。所以麦金泰尔提出:“伦理学的任务不是去设计正义的规则和制度,而是要回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把培养美德作为伦理学的主要任务。”他的观点在西方学界引起了普遍关注,也得到了强烈反响。换言之,要达到善治,既需要完善法制,也需要有德之人来推行合理的法律制度。
二、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
《荀子》中指出:“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荀子认为,法不能够独立存在,只有有了正人君子、圣贤人,它才能够发挥作用;如果没有圣贤君子,法就不可能发挥作用。所以,法律和制度是治理的开端和凭依,而圣贤君子是制定法律和推行法律的人。
在反腐败的过程中,人们一直都在争论一个问题:到底是制度更重要,还是人更重要?《傅子》用一句话就讲清了制度与人之间的本末关系:“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明智的君主一定是顺着好的制度,才能够达到天下大治的效果。“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但是,并不是说有了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够实行,达到天下大治的结果,必须还要由贤良之士来推行好的制度。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人并没有否定制度的作用,但是也不认为只要有了好的制度、礼法规则,就能达到社会和谐,还必须有圣贤君子推行好的制度,因此孔子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从历史上看,在夏、商、周三代都曾经出现过天下大治的局面,特别是“成康盛世”,周成王和周康王统治的时期,“刑错四十余年不用”,治理得确实很好。但是虽然这些礼法都记载在典籍之中,他们的后代子孙却不能身体力行这些教诲,没有按照这些礼法去要求自身,治理天下,最后也导致了夏、商、周的败亡。
所以,要认清社会乱象的根源究竟是无法可依、法规不健全,还是法律法规已经设置好,但是人们却明知故犯。如果认为社会乱象产生的原因是因为法律的不健全,于是只在法制的层面解决问题,就会导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现象,这是因为忽视了人心的治理。“不能止民恶心,而欲以刀锯禁其外,虽日刑人于市,不能制也。”(《袁子正书》)不能制止人们作恶的心,人的良心都泯灭了,欲望高度膨胀,在这种情况下,仅靠刑法止恶,即使每一天都在外面执行死刑,也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行为发生。
总之,如果重视法令的严苛,而不重视人心的治理,社会不仅治理不好,还会出现董仲舒所描述的情形,就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以薪救火,愈甚亡益也”。法律条文刚刚颁布,命令刚刚下达,欺骗、奸诈的行为就产生了。就是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结果事态会愈来愈严重。
相反,如果重视人心的治理,即使在制度不尽完善的情况之下,也能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发生。《史记》记载,汉朝兴起之后,把秦朝的严刑峻法都废除了,力求宽宥;把过分文饰的东西也丢弃了,力求质朴。当时的法网宽疏得可以把吞舟之鱼漏掉,也就是说法律制定得不具体,漏洞很多。但因为当时重视了道德教育,结果“吏治烝烝,不至于奸”,官员的道德素质高,没有人作奸犯科,黎民百姓被治理得很好,生活安定。
这说明“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腐败等社会问题的严重确实与法律监督机制不健全有关,但是人的贪欲膨胀、唯利是图,甚至良心泯灭,才是社会乱象丛生更根本的原因。
《盐铁论》上说:“古者周其礼而明其教,礼周教明,不从者,然后等之以刑。刑罚中,民不怨矣。”古代的君王,首先要完善其礼义,昭明其教化;礼义完备,教化昭明,还有不服从的人,再按照其违法犯罪的程度处以不同的刑罚,刑罚得当,老百姓就没有怨言了。“今废其德教,而责之礼义,是虐民也”,如果没有道德教化,人民因为无知而犯法,则是残害百姓,即“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盐铁论》中还对刑罚与道德教化的关系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刑法对于治理国家就像马鞭对于驾车一样,好的御手不能没有马鞭就去赶车,而是拿着马鞭却不轻易使用。圣人借助刑法来实现教化,教化成功了,刑罚便可搁置不用,这就是《尚书》所说的“刑期于无刑”。设立刑法的目的是要起到警戒、威慑的作用,期望人们不要触犯法律。所以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也判案,但是他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是要让人们化解争讼、纠纷。为什么人们能不起争讼?就是因为兴起了道德教育。
古人把地方官称为父母官,所谓的“民之父母”,本应爱民如子。《盐铁论》中说:“故为民父母,似养疾子,长恩厚而已。”作为百姓的父母官,对待犯了罪的百姓,就应该像父母对待自己有病的孩子一样,不过是增施恩惠、宽厚罢了。爱民不仅要使人民丰衣足食,更重要是教化民众、更新民风,让每个人身心和谐、家庭和谐,拥有幸福美满的人生。所以治理国家必须秉持“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理念。而道德教化的关键,是“上所施,下所效”,领导人能够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就会带动整个社会兴起良好的道德风气。因此领导人必须对教育有深刻的认知,知道“教”不仅仅是言教,更需要身教的带动。
除了领导人做表率外,推行道德教化还必须重新树立起尊师重道的观念,也就是国家领导人能够把那些有德行、有智慧的贤德之士礼请出来,甚至推为一国之师。唐太宗之所以在隋末战乱后短期内就开创了“贞观之治”,使天下太平、万国来朝,与他尊师重道并要求皇子、诸王学习《群书治要》密不可分。清朝“康乾盛世”的缔造,更与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设礼,请儒释道大德为国师、坚持讲经教学的制度相关。
天子之所以应尊师重道,因为天子的职责是践行圣道,而老师的职责是传承圣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所谓道,即圣贤相传之道。孔子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师道其所以尊严,是因为真正的明师皆不标榜自己,而只是为往圣继绝学,传承古圣先贤道脉。这种无我的精神,正是为师者所以光载千秋、万众敬仰之原因。天子唯有从师而学,才能修德明道,进而平治天下。纵观中国千年历史的兴衰,可以发现:凡是尊师重道的时期,都是政治清明,乃至盛世出现的时期;凡是轻师贱道的时期,都是王朝走向衰败和灭亡的转折点。正如《荀子》云,“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
在古代,天子能否尽早为太子选择明师教导,决定着国家的安危。这说明,国家是否有真正的后继人才,主要取决于是否有好老师的教导。所谓“天下有真教术,斯有真人材”。《淮南子》中记载,孔子“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
三、徒法不足以自行
《汉书》中说:“今废先王之德教,独用执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难成也。”圣王都是承顺天道来治理。天道都是好生恶杀,所以圣王一定是把道德教育作为要务,而把刑罚设置得非常简单。现在废除了古圣先王的道德教化,单单地用执法之吏制裁人民,还想让道德的教育化被四海,是很难成就的。
《汉书》中记载了酷吏严延年的故事。严延年身材短小,却精明强悍,办事灵活快捷。作为一郡的长官,他对忠诚奉公的属下,像对待自家人一样优待,居官办事也不顾个人得失,所以在他管辖的区域中没有什么事是他所不知道的。但是,严延年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痛恨坏人、坏事太过分了。他尤其擅长写狱词以及官府的文书。凡是他想诛杀的人,就亲手写奏折,结果上面很快就能核准判定这个人的死罪。到冬天行刑时,他命令郡下所属的各县把囚犯都押解到郡上,集中在郡府统一处死,一时血流数里。为此,郡里的人都把他称为“屠伯”。在他的辖区里,“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全郡上下一派清明。有一次,严延年的母亲从东海来看望他,本来是想和他一起行祭礼。但是,她到洛阳时,正碰上严延年处决犯人,血流数里。她很震惊,于是就住在道旁的亭舍,不肯进入郡府。严延年出城到亭舍拜见母亲,但是母亲却关门不见。他在门外脱帽叩头,过了好一阵母亲才愿意见他。见了面,母亲斥责道:“你有幸作了一郡的太守,治理方圆千里的地方,但是没有听说你以仁爱之心教化百姓,保全百姓平安,反而利用刑罚大肆杀人,以此来建立威信。难道身为百姓的父母官,就应该这样行事吗?”严延年赶忙向母亲认错,还亲自为母亲驾车,把母亲接回郡府。祭祀完毕后,母亲对严延年说:“苍天在上,明察秋毫,岂有乱杀人而不遭报应的道理?想不到我人老了,还要看着壮年的儿子身受刑戮。我要走了,回到东边的老家为你准备好葬身之地。”他的母亲回到家乡,见到同族的兄弟,也把这些话讲给他们。结果,过了一年多,严延年果然出事了。东海郡的人无不称颂严延年的母亲贤明。因为她看到儿子过分杀戮的行为就预测到他以后的结局。
古人明白“上天有好生之德”的道理,所以治国要顺应天道,以仁恕之心待民,不能过于苛刻。古人把“地方官”称为百姓的父母官,即所谓的“民之父母”,本应爱民如子,哪有父母官对儿女进行屠戮的道理?如果司法官员把人民放在了自己的对立面,把能够逮捕多少人、杀戮多少人作为自己的功绩而称颂,毫无怜悯感伤之心,这是与天道不符的。
相反,一个人即使身为执掌刑罚的司法官员,只要他有仁爱之心,不仅会受到人民的爱戴,而且还能够感化百姓。《孔子家语》记载的季羔依法惩处犯人,但之后反被此人营救的故事,就是例证。孔子评价说,季羔既能够公正,又显示了德行。
可见,徒法不足以自行。治理国家不可能只靠法律。法律法规再健全、再完备,最终还是要靠人来执行。同样是作为执法人员,但因为其德行修养不同,存心也不相同。有人用残酷的刑罚对待百姓,树立自己的威严,且以此为荣,而有人却是心存怜悯,同情人们因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而违法犯罪,结果,百姓回报他们的态度也截然不同。相信季羔以仁恕之心公正执法的典故和孔子“必也使无讼乎”的愿望会带给执法人员诸多启示。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治和德治,需要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