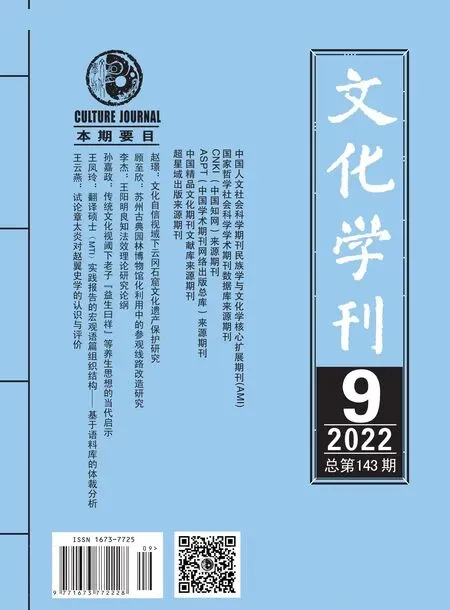简·奥斯汀小说的叙事策略研究
高 洁
简·奥斯汀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女性小说家,她的作品备受广大读者喜爱,其创作以现实主义小说为主要基调,多数内容涉及婚恋题材,而出现在作品中的青年男女又以英国乡村中产阶级家庭生活为背景,大多是在绅士与淑女之间展开。细细品读能够发现,简·奥斯汀的创作语言幽默中带着讽刺,细腻而充满道德审视,她从女性视角出发,成功创作了许多女性人物形象,用自己的笔触为当时的女性发声,聚焦婚恋问题,阐述女性观点,对数千年欧洲男性统治下的社会发起挑战。她以童话构建的模式,模拟父权社会男性对女性畸形的审美期待,又以打破童话虚构返归现实的方式,跳出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桎梏,借由童话构建的打破与颠覆来形成了独特的现实主义男女关系架构,渗透出她对女性意识觉醒的呼号,号召女性重新以新时代的社会眼光看待自我价值,积极进行自我价值探索。同时也批判了父权社会眼光下,男性对女性不合理的要求与期待终将被打破,追求女性独立。下面本文就从童话模式的构建与推翻重建,以及女性视角下的意识重构两个方面对简·奥斯汀的创作叙事策略展开剖析。
一、童话模式的构建与推翻重建
显然,从简·奥斯汀的创作中能够看到童话世界的影子,而通过仔细研读又能够发现这种童话并不等同于一般模式下读者对童话的认知,在这其中,既有简·奥斯汀对童话故事构建模式的继承,又有她在创作基础上对童话模式的推翻重建。
(一)童话模式的继承与发展
在人们熟知的童话世界中,如果让读者选择一个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女性角色,相信会有超过半数的人脱口而出“灰姑娘”的名字。实际上来看,并不是因为灰姑娘这个角色如何地深入人心,而是在于“灰姑娘”代表着童话模式构建的一种套路性人物架构,这个词不仅仅代表着“灰姑娘”这一人物本身,更多的是代表着在童话世界当中那一批为数众多的女性形象的共同特质。她们大多出身不好,或者是没有在出身不错的家庭中得到应有的待遇,首先引发了人们对她们的同情与怜悯,加上这些女性人物都有着姣好的面容,出众的身材,温顺谦恭、善良勤俭等优秀品质,极容易引发读者的共鸣,为她们的遭遇鸣不平,为她们的美好未来铺满了期待。在简·奥斯汀的作品当中也有着许多看似这样的女性角色,比如出身不高但聪慧美貌的伊丽莎白,她是《傲慢与偏见》中简·奥斯汀构建的“灰姑娘”角色[1]。从小寄人篱下,受尽冷嘲热讽的范妮,她是简·奥斯汀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构建的“灰姑娘”角色。诸如此类的还有许多,无一例外,简·奥斯汀都为自己创作中构建的“灰姑娘”角色们找到了类似童话故事中那样圆满的人生结局。比如:伊丽莎白获得了美好的爱情,范妮拥有了庄园的继承权,而凯瑟琳也在《诺桑觉寺》中收获了年轻少主的青睐。对于当时的社会而言,婚姻幸福、爱情甜蜜、有所依傍这些都是女性能够获得幸福生活的代名词,这既符合了当时社会对女性幸福生活的总体衡量标尺,又满足了简·奥斯汀对童话模式下“灰姑娘”大团圆美好结局的期待与向往,给了这些美好的女性角色以完整的人生归宿,帮助她们逃离命运的玩弄与不公,追求到一般女性都期盼得到的社会生活价值归宿。而这种对童话故事“灰姑娘”形象的塑造,也让简·奥斯汀的作品满足了一般男性对于女性形象的基本审美,他们总是渴望女性是温良恭俭的,是美貌温柔的,他们认为这样的女性才是自己适合追求的对象,也是能够得到美好生活的先决条件。因此,“灰姑娘”形象的塑造让简·奥斯汀的创作得到了不论男女大部分读者的拥护与支持,也让她更便于以此为掩护,表达内心对女性的真实期待。
客观来看,简·奥斯汀对“灰姑娘”形象的构建虽然是基于童话人物的创作模式,但是又在此基础上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继承,并且在此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世人皆知,在童话世界当中所有的“灰姑娘”都有着美丽的外貌,温柔善良的个性,这符合父权社会下男性对于女性的基本期待,无论任何时候,外貌都成为了先决条件,而仅仅拥有外貌还不够,还要懂得顺从,懂得低头,正如童话故事中“灰姑娘”一样,她们面对后妈和姐姐的欺压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只懂得默默流眼泪,没有丝毫反抗的意识,也没有为此做出过任何改变。但这在简·奥斯汀的创作中得到了发展,在她的创作中,这些“灰姑娘”形象的女性角色,美丽的外表已经不再是获得美好生活的唯一条件,她们都在一次次的受伤挫败中学习了如何成长改变,并且真实地付诸行动,在外表美貌的基础上,她们充满智慧,果敢敏锐,敢于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幸福生活的筹码。她们在生活的苦难面前变得异常坚定,能够吃苦耐劳,也能够隐忍而厚积薄发,她们通过苦难积累了更多的生活经验,有了更为独到的生存见解,并敢于为了自己的生活付出努力与实践。美貌在她们成功的道路上成为了加分项而不是必选项,这就从一定意义上将女性意识的觉醒烙印在了“灰姑娘”形象的发展道路上,让她们拥有了更多超越外在样貌的实力,以及敢于追求幸福生活的实际行动,很显然,这是简·奥斯汀在创作中看似屈从于父权社会畸形审美下对女性意识觉醒的召唤,也是对女性价值重新定义的探索过程。
(二)童话模式的推翻与重构
在当时社会,男权至上,男性成为了社会主导,他们甚至主导着女性的行为与认知,用自己的审美取向来要求女性如何立足于社会。正如童话故事当中,往往善恶都是对立存在的,仔细研读能够发现,童话故事当中有许多反派角色都是女性,她们恶毒、自私、蛮横、残忍,即便身着华服却说着泯灭人性的话,仿佛她们就是恶魔的化身,是邪恶的代名词。而对于美好的女性形象,童话故事中则将她们描绘得圣洁美好,不食人间烟火,仿佛这种美好是超脱世俗的存在,是真实世界当中女性可望而不可即的存在。但现实当中,人无完人,任何人都不可能是纯粹的存在,用中国古代的哲学体系来看,人应当都是善恶共同体,恶有恶的源头与根,恶也有限度,有克制。善亦然,任何人都做不到绝对的圣洁无瑕,善恶并存才是真理。这是人性所无法避免的,也是自然存在的客观现实。对于童话故事中绝对的善恶对立,过分的丑化和过分的美好,这在简·奥斯汀的创作中都有所纠正。总体来看,在父权社会的畸形审美下,无论是将女性过度妖魔化,还是将女性过度圣洁化、神话,这都算是对女性人格的压制与歪曲,是一种父权社会的畸形审美,更是对女性意识的损毁与践踏[2]。简·奥斯汀用自己的创作打破了这一畸形审美统治下的女性形象塑造,让童话原本构建的二元对立结构被打破,让每个角色更加丰满立体,在故事的发展中给予了每个角色过渡与成长的空间,诠释了女性独立发展、积极进取、追求自我价值的追求与成长历程,重新构建了她创作下的女性价值体系。
二、女性视角下的意识重构
女性视角下的意识重构在18世纪到20世纪的欧洲是创作中比较常见的创作方式,而对于女性视角而言,许多男性作者无法深入参透,这与其本身是男性,无法客观深入地体会女性的社会需求,也无法感同身受有着直接关系,因此,在这一时期,女性意识重构做得比较好的作家有许多都是女性,而简·奥斯汀无疑又是这些女性作家当中的佼佼者。
(一)以女性视角作为切入点
简·奥斯汀之所以能够以独特的视角进行女性婚恋题材的创作并取得极高的成就,这与她自身的成长发展密切相关。简·奥斯汀出生在一个生活条件相对优渥的家庭,她的父亲担任了40多年的教区长,家庭生活的教育气息浓郁,在这样的熏陶下,她从小就拥有比一般女孩儿更好的教育启蒙。虽然受到当时社会思想的禁锢,她并没有接受系统的学校教育,但是她却在父亲的培养教育下自幼进行写作。这让她从根底上拥有了犹如她书中创作的许多女性角色一样超前的女性意识,拥有相对独立的自我发展认知,这从根本上让她对于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不同于一般女性的认识,至少在自我意识表达这一层面上,她自小便拥有了话语权。到了20岁,简·奥斯汀结识了一生当中的重要男性勒弗罗伊,她就如同她小说中所创作的众多女性角色一样,用相对较好的家庭条件和自我修养,以及真挚的情感与热切的期盼与之相恋,他们不在乎对方家庭条件,但是受制于双方家庭的固执观念,他们最终分道扬镳,之后勒弗罗伊另组家庭,成就了终身令人艳羡的事业。临终时仍然表达了对简·奥斯汀的爱意与悔恨。而简·奥斯汀则拒绝了家世优秀的男性追求,终生未嫁。简·奥斯汀没有获得自己渴望的婚姻与家庭生活,但正是这份刻骨铭心的失去与追悔,让她能够清澈地掌握女性在家庭、婚姻生活中真正的诉求,也更加了解社会眼光与世俗枷锁下女性作为婚姻生活的牺牲品所付出的惨痛代价,她的小说才能够如此引人共鸣,如此真切动人。
(二)以“家”为轴,以小见大
在同一时期的女性视角创作的作品当中,读者们总能感受到浓郁的工业革命气息,将女性的自我觉醒与发展放在社会的洪流当中不断地拍打,不断地冲刷,甚至是鞭挞。这纵然将眼光放在了整体的人类社会发展当中,具有宏大的世界观与发展眼光,但是有的时候却让人感觉漂浮于现实生活之上,无法与作品当中的人物产生更紧密的情感链接。简·奥斯汀的创作与众不同,她抛开了这些宏大的背景,甚至也没有那么多错综复杂的人物登场,寥寥几人,简单的乡村小镇,朴实的对话与简单的故事线索,构成了简·奥斯汀的创作基调。她的创作“大道至简”,一切以最简单朴实的家庭生活为轴心,围绕简单的故事线索,清晰地展现创作中女性角色所经历的“单纯无知——遭遇挫折——自我反思——发展变化——取得成功”这样的故事发展历程,诠释女性自身对于自我观念、意识的觉醒与修正,最终实现升华[3]。在当时,许多文学界的人是看不上简·奥斯汀的创作风格的,认为她格局不大,着眼不远,脱离不了家长里短,改变不了社会现实,但在今天看来,她的作品似乎比起其他作家大格局的作品更充满了烟火气,更加与现实贴近,似乎每件事情都可能发生在当时社会的女性生活当中,既不荒诞,也不刁钻,就是真真实实地感动着读者,令每一个读她作品的女性都为之感慨,萌生出局中人就是自己的感言。而正是这样贴近生活的简单构建,反而更容易打动人,更容易给人以直接的情感共鸣和震撼,让读过作品的人为之动容。当然,简·奥斯汀作为当时时代洪流夹缝中的女性作家,这种创作反而是睿智的。因为当时的创作市场仍然以男性作家为主流,题材也都是社会化的大型题材,女性作家本就不受重视,更无从对男性为主流的市场下手,似乎用这种边缘化的创作更容易打开市场,并且作品更容易不被诟病,长久地保留并传播开来,这也是一种无奈之举。事实证明,简·奥斯汀的作品在当今社会越来越受到重视,也逐步通过研究发现了她在人物塑造方面的独到之处,她这种以小见大,以平凡见特殊的写作效果如愿以偿地得到褒奖,也成为当时社会为数不多被保存十分完整且未被诟病的女性创作。
(三)摆脱了“降男”格局的桎梏
世人总是在抬高一面的同时,就会有意无意地践踏或贬低其对立面,这在简·奥斯汀所在的时代女性意识觉醒的创作当中是十分常见的。“降男”可以理解为贬低男性,降低男性的社会形象地位,其中不乏恶意丑化和歪曲男性形象的方式方法[4]。在当时社会,许多提倡和鼓励女性意识觉醒的创作都有此通病,它们往往为了衬托女性生活的悲惨境遇,将男性恶意丑化,让他们呈现出面目可憎、奸诈狡猾、无底线下作的丑恶形象,他们刻意地蹂躏女性,践踏女性尊严,甚至玷污女性的心理和生理清白,集万千丑恶于一身。事实上,虽然在父权社会男性普遍在社会地位上高于女性,也的确存在女性被压榨、被欺侮、被剥夺话语权的情况,但这种集中化的男性丑陋嘴脸还是极少数的,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艺术再创作,纯粹的恶人形象就此诞生。而这种男性的纯粹丑恶,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衬托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欺压与伤害,为女性的觉醒创造必要条件。但实际上,在简·奥斯汀看来,这种“降男”的人物形象塑造并不是必要的,正如女性不可能绝对的善良与圣洁一样,男性当中也有着善良和大度的代表,而即使是一个看似很坏的男性,也存在人性化的一面,这就是善恶的并存。女性意识的觉醒并不以男性的压榨和欺侮为必要前提,生在这个世界上,男女本来就都是“人”,都拥有相对平等的对话权。女性的独立与觉醒并不依附于男性的丑恶,而是建立在女性自身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和体现上。首当其冲,女性千百年来最重要的社会责任就是以家庭为主战场,因此,女性的价值与追求也理所当然通过简·奥斯汀笔下的婚姻、家庭生活体现了出来,这种价值追求不以男性的鄙视和压榨为前提,仅仅是通过男女之间的情感碰撞,女性萌生了自我改变的意识,这才是平等的女性意识觉醒。
简·奥斯汀的创作以独特的女性视角为切入点,通过童话故事的继承与发展,打破了固有的女性题材创作枷锁,以“家”为主题,更加亲民,也更容易与读者产生共鸣,是难得的佳作,值得进一步剖析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