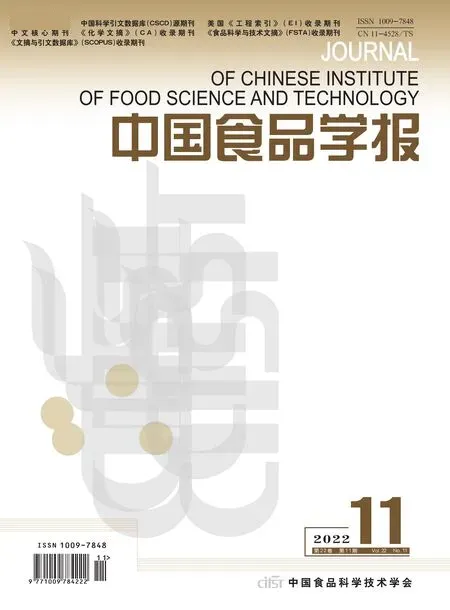后生元:肠道疾病调控新策略
郭 帅,孟和毕力格
(内蒙古农业大学 乳品生物技术与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呼和浩特 010018)
肠道是维持肠道内环境平衡和阻碍致病菌繁殖及毒素产生的先天性屏障,对于维持免疫系统和微生物群之间的健康关系至关重要。在人体肠道中存在着大量微生物,包括细菌、真核生物、病毒和古细菌[1-2],其中胃肠道内的细菌被称为“肠道微生物群”[2-4]。随着基因组测序技术的发展,微生物群对人类健康的贡献变得更加明显。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群通过宿主-微生物和微生物-微生物相互作用,来调节和维持胃肠道健康,如肠道微生物群可调节宿主的多种生理过程,包括代谢和营养稳态、免疫和肠道平衡[5-7]。
近年来各国的肠道疾病如炎症性肠病(IBD)、肠易激综合征(IBS)、结直肠癌(CRC)等患病率不断攀升,已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研究表明益生菌具有调节肠道微生物群,降低肠道炎症等功能特性,可以改善健康状况和预防肠道疾病[8]。然而,也有新的科研证据指出,益生菌的益生功效不一定和活菌有直接关系,活菌的代谢产物和菌体成分可能是促进健康的重要推手[9-10],使得后生元(即益生菌的组分和/或代谢产物)作为潜在益生菌替代物成为新的研究方向[11]。
本文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内容,概述后生元的种类及其在改善健康状况和预防疾病方面的潜在有益应用,重点综述后生元在预防肠道疾病中的生物学作用以及在临床应用中的最新进展,这对未来后生元在疾病预防中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1 后生元
1.1 后生元定义
益生菌是众所周知的非致病微生物,当摄入足够量时,会对宿主的健康产生有益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由活细菌分泌或细菌裂解后释放的可溶性因子(产物或代谢副产物)也可为益生菌提供额外的生物活性,通过与宿主细胞相互作用,从而为宿主提供局部(肠上皮)和全身(脂肪组织、肝脏、循环)的积极作用[12-14]。其中,短链脂肪酸(SCFA)、维生素、有机酸等代谢产物以及磷壁酸、胞外多糖(EPS)等细胞组分已经在体内外模型中被研究过,并且证明可以给人体健康带来益处[15]。研究人员将这些灭活的益生菌细胞(死亡细胞)、细胞组分(肽聚糖衍生的微肽、磷壁酸、内外多糖和细胞表面蛋白)或细胞代谢物(短链脂肪酸、酶、细菌素和有机酸)等益生菌细胞的非活性部分命名为“postbiotic”,中文名为后生元[16]。尽管后生元对人体健康有益的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但科学数据已经表明后生元具有保护上皮屏障、抗肿瘤、抗氧化、免疫调节等益生功能,当宿主摄入足量时,可赋予各种生理健康益处[15]。后生元可以积极影响微生物群体内平衡和(或)宿主代谢和信号通路,从而影响特定的生理、免疫、调节和代谢功能[17]。此外,后生元还具有明确的化学结构、良好的安全特性、无毒性、较长的保存期和稳定性等特性,其应用已经成为功能食品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1.2 后生元功能性成分及其生物活性
由益生菌菌株分泌的不同成分如蛋白质、肽、有机酸和其它小分子已被报道具有多种益生功效,这些成分通过调节宿主细胞代谢途径为宿主提供益处。图1 为后生元种类及其相关的益生作用。

图1 后生元种类及其潜在健康益处[18]Fig.1 The categories of postbiotics and their potential health benefits[18]
1.2.1 细胞壁成分 大量研究表明益生菌细胞壁含有较多对人体健康有益处的成分(图2)。肽聚糖(PGN)是所有细菌细胞壁的基本成分,在脂多糖(LPS)刺激的巨噬细胞模型中,研究者发现来自各种乳酸菌种类的PGN 具有阻止炎症细胞因子释放的重要能力[19]。Desrouillères 等[20]的研究证实蔓越莓果汁组分结合益生菌细胞壁成分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预防CRC 的功能化合物,并且蔓越莓组分结合益生菌细胞壁成分与单独的蔓越莓成分相比对结肠癌细胞HT-29 有更有效的抑制作用。有趣的是,Kim 等[21]发现植物乳杆菌脂磷壁酸(pLTA)也可显著抑制TNF-α 诱导HT-29 肠上皮细胞(IEC)的炎症反应,pLTA 通过调节细胞因子介导的免疫反应,抑制肠道炎症及维持肠道内环境稳态。此外,Kim 等[14]在对猪肠道上皮细胞系进行研究时发现,pLTA 在抗炎症反应方面具有显著潜力。另外,在不激活相关促炎细胞因子IL-1β、IL-8 和IL-12p40 的情况下,鼠李糖乳杆菌MLGA的PGN 可诱导鸡外周血单核细胞和脾细胞中β-防御素-9 的表达来增强先天防御反应而不引发免疫细胞的炎症反应,这说明鼠李糖乳杆菌MLGA 的PGN 具有诱导抗菌肽在机体内免疫防御的功能,有效避免了炎症反应带来的有害风险[22]。也有研究证实鼠李糖乳杆菌CRL1505 的PGN 可以调节炎症细胞因子和调节性细胞因子之间的平衡,清除肺炎球菌并且改善炎症组织损伤[23]。

图2 益生菌细胞壁成分示意图[24]Fig.2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probiotics' cell-wall constituents[24]
1.2.2 胞外多糖 胞外多糖(EPS)是微生物以紧密结合的包膜或松散附着的黏液层的形式分泌出来的胞外大分子。许多细菌虽具有合成和分泌EPS 的能力,但EPS 的组成、结构和功能各不相同。近年来,微生物EPS 因其潜在治疗活性而受到广泛关注。研究表明,EPS 可为宿主提供许多益处,包括调节免疫、抗癌、抗氧化以及降低血糖/胆固醇和高血压等多种生理功能。Xiu 等[25]在小鼠皮下注射干酪乳杆菌EPS 后发现,EPS 可通过增加血清抗体数量、T 细胞增殖能力、增强细胞因子表达和调控树突状细胞成熟来促进体液和细胞免疫应答。此外,戊糖乳杆菌LZ-R-17 的EPS 通过提高RAW264.7 巨噬细胞的活力、增强吞噬能力、提高巨噬细胞的活性,从而促进NO、TNF-α、Il-1β、IL-6 和IL-10 的分泌,显示出显著的免疫刺激活性[26]。同时,Liu 等[27]从副干酪乳杆菌NTU 101 和植物乳杆菌NTU 102 中分离得到的EPS 可促进巨噬细胞的生长,并诱导小鼠巨噬细胞RAW264.7细胞产生促炎症反应。此外,由于益生菌EPSs 产生的副作用较少,大量学者推测该物质可能作为新型抗癌剂的重要来源[28]。Zhou 等[29]研究表明,植物乳杆菌NCU116 的EPS 可通过介导小鼠肠上皮癌细胞凋亡的toll 样受体-2(TLR-2)进而提高促凋亡基因Fas、FasL 和c-Jun 的表达,而且副干酪乳杆菌的EPS 也被证明可诱导结肠癌细胞凋亡[30]。2019 年,Ale 等[31]将发酵乳杆菌Lf2 的EPS提取物与酸奶联合灌胃BALB/c 小鼠,发现短链脂肪酸如醋酸盐和丁酸盐浓度增加。众所周知,这些脂肪酸是肠道微生物产生的挥发物,具有良好的肠道抗炎特性。London 等[32]的一项研究表明,使用产生EPS 的益生菌进行饮食干预,可通过降低血清胆固醇和甘油三酯(TG)浓度来调节动脉粥样硬化小鼠模型的脂质代谢,从而改善小鼠的脂质代谢。
1.2.3 表层蛋白 表层蛋白(Surface layer protein,SLP)是许多细菌及古生菌细胞壁表面所包被的生物活性大分子,可参与调节细胞各种生理生化过程。近年来,多种乳酸菌的SLP 已被证实在抗菌活性中发挥作用。Li 等[33]研究表明,嗜酸乳杆菌ATCC 4356 的SLP 通过抑制鼠伤寒沙门氏菌诱导的Caco-2 细胞凋亡,并降低鼠伤寒沙门氏菌诱导的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1 和2(ERK1/2)磷酸化,通过诱导细胞增殖和分化介导细胞凋亡。此外,嗜酸乳杆菌NCFM 的SLP 被证明可以与树突状细胞(DC)的C 型凝集素受体(CLRs)结合,发挥免疫调节信号,减轻炎症疾病症状,增强肠道屏障功能,从而缓解小鼠结肠炎症[34-35]。另外,Rabah等[36]报道了从费氏丙酸杆菌中分离出的SLP 通过减少HT-29 细胞上TNF-α 的分泌来调节免疫系统。也有研究证实瑞士乳杆菌MIMLh5 菌株来源的SLP 可降低NF-κB 的活性,并对肠上皮细胞Caco-2 产生抗炎作用[37]。同时,来自植物乳杆菌的SLP 也被报道可保护肠致病性大肠杆菌诱导的肠上皮细胞损伤[38]。
1.2.4 细胞培养上清 益生菌细胞培养的上清液(CFS)中包含有机酸、短链脂肪酸、细菌素等活性物质,已有大量研究表明益生菌CFS 对人体健康有促进作用。Bermudez-Brito 等[39]用鼠李糖乳杆菌CNCM I-4036 及其CFS 处理大肠杆菌攻击的人树突状细胞(DC)。结果表明,在用活鼠李糖乳杆菌处理的细胞中,促炎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1β、白细胞介素-6、白细胞介素-8 和白细胞介素-12p70 的水平高于用CFS 处理的细胞,并且CFS在减少促炎细胞因子的分泌方面比益生菌更有效。短双歧杆菌CNCM I-4035 的CFS 通过激活TLR 减少伤寒沙门氏菌攻击的树突状细胞中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从而保护机体免受高传染性病原体如伤寒沙门氏菌的感染[40]。Marco 等[41]为了证实5 株益生菌菌株(嗜酸乳杆菌、干酪乳杆菌、乳酸乳球菌、罗伊氏乳杆菌和布拉氏酵母菌)的CFS对HT29 上皮细胞的抗炎作用,使用了从巨噬细胞中分化的离体人单核细胞,对CFS 的抗炎活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CFS 不仅能够下调人结肠上皮细胞HT-29 中PGE-2 和IL-8 的表达,对人巨噬细胞产生IL-1β、IL-6、TNF-α 和IL-10 也有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表现出其独特的抗炎活性。此外,研究发现鼠李糖乳杆菌CFS 对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肥胖小鼠有心脏保护作用[42],并且对急性酒精诱导的肝脂肪变性和损伤也有保护作用[43]。此外,CFS 还具有显著的抑菌功效,含细菌素的乳酸菌CFS 对不同食物基质中单增李斯特菌的生长有显著的抑制功效,而且罗伊氏乳杆菌AN417 的CFS 也被用作新型抗口腔致病菌的抗菌剂[44]。
2 后生元与肠道疾病
2.1 后生元与炎症性肠病
炎症性肠病(IBD)已经成为21 世纪全球发病率不断上升的胃肠道慢性炎症性疾病,它是由遗传易感性、环境和微生物因素驱动的慢性免疫介导的肠道炎症,其会损害胃肠器官的功能,导致腹痛、持续腹泻、痉挛、体重减轻、直肠出血和疲劳等[45-46]。IBD 可以发生于任何年龄,通常多发生于成年早期,并且各年龄段的患病率均持续上升,其临床特征在个体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包括疾病的位置、疾病的活动和行为。目前IBD 的临床表现主要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和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两种类型[47]。
为探究IBD 患者肠道代谢物的变化,Franzosa等[48]对IBD 患者粪便进行非靶向代谢组测定,结果表明IBD 患者体内许多已确定的微生物代谢物含量显著降低,其中一些代谢物和相关物种被发现具有抗炎作用,因此被认为是具有保护作用;另一方面,在IBD 患者中富集的促炎细菌代谢物和物种被认为是IBD 的病因。Thakur 等[49]通过用热灭活益生菌干酪乳杆菌Lbs2 处理IBD 小鼠,发现小鼠结肠组织中IL-12、TNF-α 和IL-17A 水平明显降低,而对效应T 细胞的增殖有抑制作用的IL-10 和TGF-β 水平升高,最终缓解了小鼠结肠炎症状。此外,益生菌的细胞壁内容物通过限制免疫炎症和氧化应激来保护LPS 诱导的小鼠结肠炎[50]。益生菌干酪乳杆菌DN-114 001 的溶解产物也可通过增强肠道屏障功能和改变肠道微环境来缓解结肠炎[51]。
研究表明许多益生菌及其CFS 具有较强的的抗炎活性,同时,其活性成分也被证明在治疗炎症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丁酸盐是一种四碳短链脂肪酸,具有抗癌和抗炎作用,并且丁酸盐对结肠黏膜健康的影响已被广泛研究。丁酸盐可以通过抑制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来诱导影响结肠功能的基因表达[52]。体外试验表明,丁酸盐还可以通过抑制NF-κB、激活和上调PPARγ 来减少炎症反应[53]。除短链脂肪酸可以缓解炎症水平外,Schirmer 等[54]发现色氨酸代谢水平降低也与IBD 中上皮屏障受损有关。色氨酸可以被细菌转化为具有生物活性的含有吲哚的分子,激活芳香烃受体并下调炎症[55]。几种消化链球菌代谢色氨酸产生代谢物吲哚丙烯酸(IA),可以促进黏液产生并抑制炎症细胞因子的产生,从而促进肠上皮屏障功能,并通过免疫细胞缓解炎症反应。同时宏基因组显示IBD 患者肠道中的吲哚丙烯酸的生物合成基因簇减少,从而可能导致屏障功能障碍[56]。此外,国外学者通过将代谢组学与微生物分类群分析相结合,发现与疾病相关的微生物和代谢产物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显示胆汁酸、鞘脂和色氨酸水平显著提高[48,57-58]。研究发现,通过调节微生物代谢物牛磺酸、组胺和精胺的水平,可以改变肠道炎症和对葡聚糖硫酸钠(DSS)诱导的结肠炎的临床反应,这突出了微生物代谢物的潜在临床相关性[59]。
2.2 后生元与肠应激综合征
肠易激综合征(IBS)是一种常见的功能性胃肠疾病,以腹痛和排便习惯改变为特征,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极大的影响。据估计,全球IBS 的患病率非常高,在所有年龄的个体中占11%。而且不同国家的患病率也不相同。研究发现,女性的IBS患病率显著高于男性,根据Rome IV 标准,IBS 临床可分为便秘(IBS-c)、腹泻(IBS-d)、混合型(便秘和腹泻)IBS(IBS-m)和非发生型IBS(IBS-u)4个亚组[60-61]。然而,由于IBS 的病因具有不确定性,目前仍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因此,阐明IBS 的机制,并建立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是十分必要的。在之前的研究中,许多因素被认为是导致IBS 的原因,包括运动性异常、内脏感觉过敏、脑肠轴相互作用、肠道菌群改变、肠道通透性改变、免疫激活和心理社会压力等[62]。
Oka 等[60]对443 名IBS 患者进行了一项为期8 周的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旨在评估非活性热灭活双歧杆菌MIMBb75 在治疗IBS 及其症状中的疗效。研究发现,接受非活性热灭活双歧杆菌MIMBb75 患者的IBS 症状有更大的缓解,包括腹痛、腹胀、不适、与排便相关的疼痛和排便频率。此外,在治疗结束时,与安慰剂相比,反映整体治疗成功的几个重要参数也有显著改善,包括与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IBS 症状评分和整体症状缓解。Wang 等[63]研究发现鼠李糖乳杆菌CFS 可上调肠上皮细胞和小鼠肠组织SERT mRNA 和SERT-P水平,从而缓解IBS 的症状。Seong 等[64]用热灭活干酪乳杆菌DKGF 7 治疗IBS 模型大鼠,与对照组比较,发现治疗组血清皮质酮水平降低,结肠炎症细胞因子水平降低,上皮中紧密连接蛋白(TJPs)表达升高,治疗组的粪便稠度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此外,Mars 等[65]对IBS 患者的粪便代谢物进行测定,发现IBS-c 患者粪便样本中短链脂肪酸丙酸、丁酸和乙酸含量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与健康对照组相比,IBS-c 组结肠黏膜活检样品中的乙酸盐也显著降低。另外,IBS-c 患者的粪便样本中的赖氨酸、尿嘧啶和次黄嘌呤均显著降低。次黄嘌呤可作为肠上皮细胞的能量来源,并促进损伤或缺氧后肠细胞屏障的发育和恢复[66-67]。IBS-c 患者的粪便样本中较低的次黄嘌呤水平可能反映了IBS 患者肠道微生物组对次黄嘌呤的产生减少或分解增加。在另一项研究中,Ponnusamy等[68]发现IBS 患者的氨基酸和酚类化合物显著增加。
2.3 后生元与结直肠癌
结直肠癌(CRC)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恶性肿瘤类型之一,每年约有100 万新发病例,超过55 万人死亡,是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癌症之一[69-70]。虽然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CRC 的确切原因和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据估计,45%的CRC 可以通过改变食物、营养、生活方式和体育活动等环境因素来预防。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肠道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可以通过治疗肠道失调、改善免疫系统来抑制癌症发生和肿瘤进展,而且还影响抗癌治疗的效果(图3)[71-73]。

图3 后生元在抗癌治疗中的作用[16]Fig.3 Role of postbiotics in anti-cancer therapy[16]
Miyamoto 等[74]证明灭活粪肠杆菌EC-12 对DSS 诱导的小鼠结肠炎和Apc 突变小鼠的小肠癌形成有保护作用。An 等[75]的结果表明植物乳杆菌CFS 可以提高5-氟尿嘧啶(5-FU)对结肠癌的治疗效果,并通过逆转抗癌药物的耐药性而减少CRC 干细胞样细胞,这意味着益生菌代谢物可能是治疗耐药大肠癌的有效的生物治疗药物。同时,Chuah 等[76]发现6 株植物乳杆菌产生的代谢物对恶性肿瘤细胞具有选择性细胞毒作用,对肿瘤细胞具有特异性的抗增殖作用和诱导凋亡作用,而对正常细胞不产生影响,该研究揭示了植物乳杆菌代谢物作为功能补充和辅助治疗癌症的巨大潜力。
最近的研究表明丁酸盐是纤维发酵过程中肠道微生物最丰富的代谢物之一,具有抑制炎症和CRC 的作用,它是结肠细胞的主要能量来源,通过在免疫、基因表达和表观遗传调控中发挥作用,进而维持上皮完整性,抑制炎症和癌症[77]。丁酸可以直接进入细胞核,抑制组蛋白去乙酰化酶的表达,导致短链酰基辅酶A 脱氢酶(SCAD)水平降低,这是催化线粒体丁酸氧化的主要过程。该过程减少了丁酸在CRC 细胞中的自氧化作用,使丁酸在癌细胞中积累,从而抑制CRC 的发展[78-79]。丁酸是研究最多的短链脂肪酸,可作为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抑制剂,抑制癌细胞增殖,触发细胞死亡[80]。除了短链脂肪酸,乳酸菌细胞质提取物和细胞壁成分对LT-97 和HT-29 癌细胞株具有抑制作用,促进凋亡反应,抑制细胞周期在S 期进展[81]。此外,植物乳杆菌70180 的EPS 已被报道对结肠癌细胞具有一定的抗肿瘤活性[82]。另外,一项动物实验表明,烟酸可以通过激活GPR109a 来预防小鼠结肠炎和CRC,其确切的分子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83]。
3 总结和展望
随着人们对肠道健康更深入的认知,益生菌对肠道疾病预防和治疗作用也被人们所认识,然而,益生菌的耐药性等安全性问题也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科学研究表明,后生元具有保护上皮屏障、抗肿瘤、免疫调节和对病原体的拮抗作用等功能,并且和益生菌相比,后生元具有很好的吸收性、代谢性、化学结构清晰和剂量参数安全等优势,已引起研究者的极大兴趣。根据该综述中显示的研究,后生元对IBD、IBS、CRC 等疾病具有很好预防作用,而且没有任何严重的不良副作用,可以作为预防肠道疾病患者有效的工具。尽管对后生元与肠道疾病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仍需要更加可靠的临床应用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其作用机制,从而揭示后生元在未来研究中的巨大潜力。同时,也为开发具有特定生理作用的食品开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