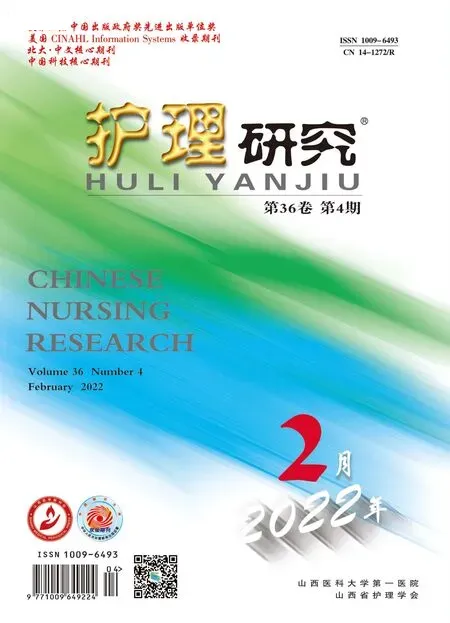重症监护病房预立医疗照护计划研究进展
粟 翠,庄碧嗓,李春韦,邓仁丽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 563000
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的病人由于病情危重或应用镇静药物常处于镇静、昏迷或意识障碍的状态,无法参与知情同意或医疗决策,病人的医疗决策往往由家属和医生代理。ICU 的治疗常以机械通气、有创穿刺、血液透析等积极治疗为主,降低了终末期病人的生活质量,也给病人家属造成了一定的经济负担及心理负担。预立医疗照护计划(advance care planing,ACP)是遵照病人的价值观和意愿让病人、家属、医务人员进行沟通后共同做出医疗决策的过程,可满足ICU 病人及家属的需求,亟须在ICU 开展。目前,ACP 在国外已开展较为成熟,我国仍处于探索阶段。现综述国外ICU 开展ACP 的研究进展,以期为我国在ICU 开展ACP 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1 ACP 概念
ACP 是指任何年龄阶段及不同健康状况的人群基于自身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活目标,与医务人员和/或其亲友就未来医疗照护意愿进行沟通的过程[1]。ACP 强调以病人为中心,旨在确保人们处于严重疾病终末期或慢性疾病期间获得与其价值观、目标及意愿一致的医疗照护[1-2]。经过ACP 讨论形成的用以阐述病人生命终末期医疗照护意愿的口头或书面文件为预立医疗指示(advance directives,ADs),也称生前预嘱(living will,LW)[3]。ACP 的实施能够有效保障病人的自主权,提高病人临终生存质量及医患双方满意度,减少过度医疗现象。
2 ICU 实 施ACP 的 必 要 性
ICU 是危重病人集中的区域,是对各类重症病人及多系统功能衰竭病人实施严密监护及抢救治疗的特殊场所[4]。由于ICU 集中了先进的医疗设备和专业的24 h 监护人员,致使ICU 的医疗费用高昂,给病人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ICU 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在给病人带来生的希望的同时,也加重了病人的痛苦[5-6]。对于许多无医治意义的终末期病人而言,只是短暂地延长了他们的生命。有研究显示,西方国家20%~30% 的病人在生命的最后1 个月被转至ICU[7]。我国ICU 病人的病死率达42%[8]。研究表明,50%的病人在死前都处于中度至重度痛苦之中[9],严重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在我国传统的医疗模式下,病人家属及医务人员注重病人的治疗效果,而忽视其自身的医疗意愿,病人所接受的医疗照护与其意愿是否一致常不得而知。此外,家属因不了解病人的意愿缺乏决策信心,导致心理压力较大。有研究指出,一旦明确治疗不能达到可接受的健康状态,此时的积极危重救治应该逐步向姑息护理过渡,以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提升病人生命末期的尊严感为治疗目标[10]。ACP 作为姑息护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ICU 实施有利于保障病人自主权,使其接受与其意愿一致的治疗,从而提高病人终末期的生活质量,减轻病人家属的经济负担及心理负担[11]。有研究表明,在病人长期经受疾病折磨、临终时想减轻自身痛苦和疾病医治无意义时支持实施ACP[10]。因此,为ICU 的病人实施ACP 是很有必要的。
3 ICU 病 人 应 用ACP 现 状
3.1 国外应用现状 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ACP 发展已经成熟且颁布了相关法律文件以支持ACP 的推进。英国政府为指导团队为生命终末期病人提供ACP 服务,2008 年提出了黄金标准框架[12]并在英国初级医疗保健中心广泛使用。ACP 是临终关怀的重要内容,也是高质量姑息照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国家ICU 的ACP 强调与临终关怀紧密协作。
3.2 我国应用现状 我国台湾地区的《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使ACP 得以立法实施[13];香港地区ACP 虽长期以非立法的形式存在,但人们对其认可度和接受度高[14];大陆对ACP 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相关的应用实践大多集中于肿瘤科,对于ICU 的ACP 探讨仍处于萌芽阶段,尽管有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但多为描述性研究[15-16]。
3.3 具体应用情况
3.3.1 ACP 的实施者 我国台湾《预立医疗照护咨询商作业办法(草案)》指出:ACP 团队应至少纳入3 名成员,包括1 名医师或护士、1 名社会工作人员或心理学家、1 名医疗人员或具有社会工作资格的专职人员。ACP 团队成员必须通过课程考核才能实施ACP。王守碧等[17]指出,护士是最常与病人及家属接触的人,易取得病人及家属的信任与理解,善于与其进行病情及缓和医疗的沟通,应成为ACP 实施的发起者。
3.3.2 干预策略 ICU 病人因病情危重或镇静药物的使用常常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的医疗决策往往都是由医生、护士主导,家属参与制定而成。美国重症医学会发布的ICU 临床实践指南[18]强调应在ICU 实施跨学科家庭会议,以促进家属共同参与决策。跨学科家庭会议是由多个临床学科成员(包括主治医生、护士及其他学科成员,如心理学家等)向病人及其家属提供信息支持的一种方式,就病人的偏好和价值观进行讨论以帮助病人做出正确决策,该会议要求在一个安静且不被打扰的私密环境内进行[19],但召开时间不统一。Lee 等[20]在ICU 对家属进行跨学科家庭会议满意度调查时发现,家属倾向于在转入ICU 24~48 h 举行会议。其主要内容包括[4]开场介绍、信息分享、讨论及总结。首先参会者自我介绍,会议主持者介绍本次会议的目标,然后医患双方就病人的病情、治疗及预后进行信息分享,了解病人对自身疾病的认知程度;其次,基于病人对疾病的了解及病人的偏好和价值观,与病人及家属共同讨论病人的照护目标和后期治疗方案;最后总结会议的内容并制订简要的计划。这一措施可以更好地满足医患双方信息一致性的需求,提高医患双方满意度,减轻家属心理负担[20-21]。
3.3.3 干预工具
3.3.3.1 展望未来:当你重病时的医疗选择[22-23]该工具是由健康对话组织开发的为数不多的帮助病人了解他们在重病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选择的决策辅助工具之一。其主要目的是为病人及家属提供医疗选择教育,鼓励与晚期疾病病人对话,制定ACP 并实施以病人和家属为中心的决策。它概述了各种形式的ACP,并强调了价值观对医疗决策的影响及选择医疗决策代理人的重要性,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35 min的DVD 和52页的手册。DVD 通过对姑息治疗医生的简短访谈,用非医学类语言描述了关键概念和问题,并穿插在临床医生和病人的现场对话中,通过对话阐述了医疗照护的一系列价值观和偏好;手册内容主要包括:①重病期不同类型的医疗照护,即治愈性治疗、姑息性治疗和临终关怀;②ADs;③病人价值观对医疗决策的相关影响。Bakitas 等[22]将“展望未来:当你重病时的医疗选择”纳入ENABLE Ⅲ[24]中(ENABLE 旨在提供解决问题、症状和自我护理管理、沟通和决策支持方面的技能和指导,从而使病人和家庭照顾者能够在他们的医疗保健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于1 周后对57 例病人和20 名家属进行访谈发现,93%的病人和100%的家属都表示他们会向其他重病病人推荐此工具;79%的病人表示越早使用该工具越好,最好在疾病诊断初期就使用。被访谈的人员均表示该工具的使用可以帮助病人提高对疾病的把控感和对姑息护理及临终关怀等不同医疗选择的认识,促使他们参与ACP 讨论并将家庭成员纳入其中。
3.3.3.2 维持生命治疗医嘱(physician orders for life sustaining treatment,POLST) POLST 是由俄勒冈州的一个医疗团队研发的用于记录危重或衰弱病人护理偏好的工具。由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发起、与病人及其家属就病人的护理价值观、信念、目标共同讨论和决策的结果,在病情危急的时候将病人的治疗意愿转化为医嘱,指示医护人员实施与其意愿一致的医疗救护[25]。POLST 主要包括6 个板块[26],前4 个板块记录病人的意愿,后2 个板块记录病人、病人决策代理人及医务人员三方的签名。有研究表明,POLST 在医务人员的使用中具有较好的依从性[25],有利于病人接受与其意愿一致的治疗[27]。目前,美国已有多个州在使用POLST,俄勒冈州、加利福尼亚州及西弗吉利亚洲的POLST 已经处于相当成熟的状态。巴西以美国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文档为源版,进行跨文化调适形成了巴西本土化的POLST 文档[28]。我国虽有与危重病人讨论治疗意愿的病危病重告知书,但讨论内容局限,建议基于我国文化背景及医疗体制,借鉴POLST 探索适合我国危重病人的意愿记录表单。
3.3.4 干预效果 ①ACP 的开展有助于促进医疗决策,提高医患双方满意度。Bakitas 等[22]用“展望未来:当你重病时的医疗选择”对病人进行ACP 干预,结果表明,ACP 的实施可帮助病人及家属充分了解重病过程中的多种治疗选择,改善了医患沟通效果,增进病人及家属对医护人员的信任与理解,提高了就医过程中医患双方的满意度。②ACP 的开展有利于降低ICU转入率,提高病人生命末期的生活质量。Detering 等[29]对老年临终病人进行ACP 干预结果表明,ACP 的实施可帮助医护人员及家属了解病人的临终意愿并遵循其意愿从而提供相应照护,减少了过度医疗现象及ICU的转入率,提升了病人生命终末期的尊严感及生活质量。③ACP 的开展有利于减少ICU 病人家属的负面情绪。研究发现,组织跨学科的ACP 家庭会议,可减少家属决策的不确定性,从而减轻家属的焦虑和抑郁程度[21]。
4 我国ICU 实施ACP 的影响因素
4.1 缺乏对疾病及ACP 的认知 ACP 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病人对ACP 缺乏认知。丁新波等对205 例ICU 病人的调查发现,仅有43.9%的病人听说过ACP,而真正了解ACP 的病人少之又少,他们并不理解ACP 的真正意义[15]。部分病人将ACP 与“安乐死”的概念混淆,他们认为一旦参与ACP 讨论,意味着医护人员会对他们产生消极的治疗倾向而对ACP产生抵触情绪[30];再者,由于病人及家属对疾病缺乏一定的认知,他们难以接受疾病的不良预后,同时也难以理解维持生命治疗的局限性和并发症,导致其对ACP讨论意愿不高[31]。此外,部分医护人员对ACP 也没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他们担心与病人展开ACP 的讨论会让其丧失斗志,失去生的希望,没有主动为病人及家属推 荐ACP 的 意 识[32-33]。
4.2 社会文化因素 我国传统文化的道教、佛教、儒家文化对人们的影响根深蒂固,“重生讳死”观念使人们对死亡往往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35-39],长此以往便构成了一种“生而不言死”的现象。由于ACP 必定会谈及生命终末期及死亡相关的一些话题,可能会让病人对ACP 采取一系列躲避及抵触的行为。再者,传统救死扶伤的医学观念使得部分医护人员认为应不惜一切挽救病人的生命,却忽略了病人疾病终末期的生活质量[34]。此外,当大多数病人失去意识无自主决策能力时,医护人员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医患纠纷,趋向于以病人家属意愿代替病人本人意愿实施医疗救治,导致ACP 开 展 受 阻[30,34]。
4.3 病人及家属因素 ACP 强调以病人为中心,病人是影响ACP 实施的重要因素之一。有研究表明,病人的年龄、文化程度、经济水平、有无丧亲或抢救经历是影响病人参与ACP 讨论的主要因素[33,39-40]。高龄、文化程度和经济水平越高,有体验过丧亲或抢救经历的病人参与ACP 讨论的意愿更高。近期有研究发现,年轻病人较高龄病人更愿意参与ACP 讨论[38],其原因可能是年轻病人受根植于传统文化中的固有生死观的影响较小,更易接受新观念。建议加强对公众的生死教育。在大多情况下,ICU 的病人由于意识障碍或长期使用镇静剂,丧失自主决策能力。此时家属便成了病人的决策代理人,由于我国儒家文化及孝亲观念的影响,无论病人生前的意愿如何,家属迫于舆论压力明知治疗的无效性仍会选择积极救治。此外,如果病人有多个家属参与决策,家属的决策意见不一致亦会影响ACP 的开展。建议多与病人家属进行病情沟通,为家属介绍ACP 相关知识并鼓励家属一同参与讨论。
4.4 医护人员因素 有研究表明,医护人员对ACP基本持赞同态度[16,41-43]。医护人员对ACP 的认可度因自身学历及职称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学历越高、职称越高对ACP 的认可度越高[44]。但ACP 在我国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尚无系统的ACP 干预模式,医护人员缺乏沟通经验、技巧,面对和(或)处理死亡的经验均可能会影响ACP 的讨论[15,31,35]。由于ICU 病人的病情与结局往往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疾病的不确定性使医护人员有时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错失了开展ACP 的正确时机。
4.5 沟通因素 沟通是ACP 的核心内容,包括疾病相关信息、患病体验、生命价值观、临终治疗意愿等[45]内容。但ACP 涉及的话题较为敏感,医护人员担心语言沟通能力不足会给病人带来负面情绪而无法把握ACP 启动的正确时机[35];沟通地点[45-46]是影响沟通的要素之一,病房内环境嘈杂且拥挤,没有设置相对隐私空间,如专门的单人会议室或ACP 沟通室;除此之外,时间缺乏[31,45-46]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ICU 医护人员工作量大且繁忙,难以有空闲时间与病人进行ACP沟通。
5 我国ICU 实施ACP 的建议
5.1 加强对公众ACP 知识的普及 认知是改变行为的关键因素,应加强对公众ACP 知识的普及。建议可采用决策辅助工具,如使用视频,制作本土化ACP 宣传手册,创办微信公众号、网站,在社区、学校等地举办公益讲座等加强公众的ACP 意识,以提高公众对ACP 的认知和行为能力,保证ACP 的顺利推广。如罗点点创办的“选择与尊严”网站致力于推广生前预嘱、尊严死等理念,并以“5 个愿望”为基础创办了适合我国国情的“我的5 个愿望”帮助病人进行临终意愿表达。邱业银等[47]团队与病人进行ACP 讨论时使用了其团队自己构建的视频决策辅助工具“杏林晚语”以帮助病人正确认识ACP 并做出合适的医疗决策。
5.2 加强对医护人员ACP 的专业培训 医护人员既是ACP 的促进者,又是决策主导者。故应加强对医护人员ACP 的专业培训,尤其注重ACP 的沟通培训,借鉴国外经验,采用情景模拟的方式进行沟通训练,增强医护人员的ACP 沟通技巧。有研究表明,使用结构化的沟通模板有利于ACP 的沟通,可结合我国的医生-家属-病人病情沟通模式,构建本土化的ACP 沟通模板[48]。此外,医学生作为医护人员的后备军,他们对ACP 的认知能力将会影响未来ACP 在临床的实施,应把ACP 纳入医学教育课程中;不连续的护理模式导致病人的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31],应严格遵循我国的责任制管床制度,将管床医生、护士纳入ACP 团队中,进行跨学科合作,培养专业的ACP 团队。
5.3 推广以家庭为中心的ACP 沟通模式 在我国传统文化影响下,家庭利益往往被置于个人利益之上[49],病人害怕自己给家庭带来负担不敢表达自己的意愿。长期以来家庭在医疗决策中起着主导作用,使得家属往往是病情告知的第一人[14],出于对病人的保护,家属不会向病人透露疾病诊断和预后的相关信息,甚至有些家属亦会要求医生对病人隐瞒病情。家属因不确定所做的决策是否为病人想要的,常会出现焦虑和抑郁症状[4,50]。但部分家属在为病人做出决策的过程中却起着支持与矫正作用,即帮助病人接受患病事实和帮助病人避免因家庭利益而做出不适决策[51]。以家庭为中心的ACP 沟通模式鼓励病人及家属共同参与ACP制定,符合我国儒家文化特点,有利于保障病人的自主权,减轻家属的心理负担[14]。以家庭为中心的ACP 沟通模式在ICU 极其重要,因为ICU 病人具有决策能力的仅占一小部分,大多数病人由于病情危重或长期使用镇静剂致自我决策能力丧失,此时需要家属参与为其做出决策。在整个沟通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病人及家属的主体地位,循序渐进地与病人及家属进行ACP 沟通,但ICU 病人病情变化快,家属的需求会随着病人病情的变化而变化,医护人员应举行多次家庭会议,及时了解病人意愿变化情况。
6 小结
由于ICU 不同于其他科室,推进ACP 显得尤为重要。随着我国安宁疗护的发展及人们的生命价值观不断完善,人们对姑息护理的需求逐步增加,ACP 是医疗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亟须普及ACP 的教育;医护人员应积极、主动地学习ACP 相关知识,提高ACP的实践应用能力,尤其是ACP 沟通技能;基于我国文化背景,构建可辅助临床实践的本土化ACP 沟通模板及决策辅助工具,促进ACP 在我国的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