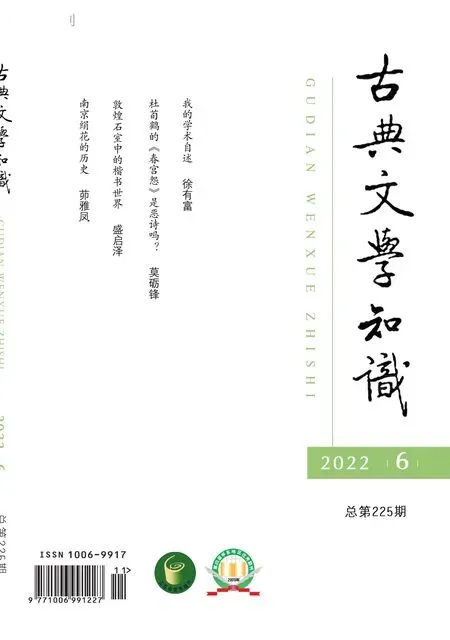“顽石”何以“点头”
——重读丘迟《与陈伯之书》
卜兴蕾
与南朝文坛上的璀璨群星相比,丘迟或许不过是小文人。南齐时,丘迟曾为徐州刺史属官,预宴乐游苑,应诏赋诗,云“小臣信多幸,投生岂酬义”(《文选》卷二十《侍宴乐游苑送张徐州应诏诗》),“小臣”即其自指。至萧衍平建康,丘迟得以入幕,“时劝进梁王及殊礼,皆迟文也”,其人虽“甚被礼遇”(《梁书·文学传》),彼时所撰劝进诸文却早已散佚不存,而为萧衍执笔“禅让文诰”的任昉(《梁书·任昉传》)之类才是当时的大文人。
然而,丘迟所作《与陈伯之书》却称得上是大手笔。史载陈伯之接到丘书之后,便“于寿阳拥众八千归”(《梁书·陈伯之传》),言下之意此书有劝降陈伯之的功劳。在后世,《与陈伯之书》更成为文章典范。非唯《文选》收入丘作,后来的总集、选本亦多留意此文。明清时期,专门的骈文选本如王志坚《四六法海》、李兆洛《骈体文钞》均载录丘书,此外,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亦收录是篇。《与陈伯之书》传诵千古,其经典性与影响力不言而喻。
丘迟这篇书信的首要读者,自然是陈伯之。然则,据《梁书》陈伯之本传记载,此人“不识书”“得文牒辞讼,惟作大诺而已”(《梁书·陈伯之传》),如此粗鄙无文的武将是否能够读解丘迟来书,以致深受感召而归降梁朝?伴随丘文的流传,这一疑问也令后世读者困惑不已。
清人张云璈即怀疑此事真伪,认为“得书即降之说,亦史家粉饰耳”(《选学胶言》卷十七)。钱锺书也曾质疑丘书效用:“迟文藻徒佳,虽宝非用,不啻明珠投暗,明眸卖瞽,伯之初不能解。”正因陈伯之“不识书”,钱氏进一步设想:“使者致书将命,另传口语,方得诱动伯之,拥众归梁。”(《管锥编》第4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这似乎是说,“诱动”陈伯之归降的乃是所谓使者“另传”的“口语”而非丘迟来书。
不过,纵使陈伯之本人“不能解”,其幕中当有识书之士为之读解。王志坚推想:“当是幕中有人,然如此《书》,正可使顽石点头。”(《四六法海》卷七)高步瀛也表示:“伯之虽不识字,岂无左右与之详为解释者?”(《南北朝文举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顾农《丘迟和他的〈与陈伯之书〉》亦持此论,《名作欣赏[鉴赏版]》2005年第10期)实则幕中文士不仅可为陈伯之读解来书,甚至可能为之代拟覆函。三国时,同样寡文的武将曹洪曾致书曹丕,其文实乃陈琳手笔(陈琳《为曹洪与魏文帝书》,收入《文选》卷四一),纵使能文如曹操者,身边也不乏阮瑀之类“捉刀”文士(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收入《文选》卷四二)。幕中文人为主解读书函乃至代作答辞,自东汉以来便是极平常之事,可觇陈伯之本人是否识书以及会否作书,殆无关紧要。
令后世读者疑惑的,与其说是陈伯之解书与否,倒不如说丘迟来书在陈伯之归梁事件中的效用究竟如何。是以钱锺书有“专恃迟《书》,必难奏效”(《管锥编》第4册)之论,要在消减丘迟一书的感召力。
读《梁书·陈伯之传》,易知陈伯之不但粗陋少文,行事更是反覆无常。正因陈伯之行事反覆、意志不坚,游说其人往往能够动摇其志:彼时陈伯之转投萧衍,便是萧衍利用苏隆之、郑伯伦反复“说”之使然;至于弃梁奔魏,则又受褚緭等人煽动所致。有此“前史”,丘迟“以书喻之”,使之归降,想来绝非难以奏效。就文学而论,寡文的陈伯之固然可视为“顽石”一块,但就性格来说,他并非坚如“顽石”,实乃颇易回转。纵然丘迟来书须经文士解说方能使陈伯之领会,但所传达的意旨也不应游离原文之外。如此看来,此事的关键在于:丘迟这封书信如何能使陈伯之“点头”?质言之,丘书到底击中了陈伯之何处要害?
陈伯之反覆无常,丘迟并非不知:
昔因机变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邪!
以丘迟代表的萧梁立场来看,陈伯之于齐、梁易代之时投靠萧衍并助其成事,随后却弃梁奔魏,这两段往事正浓缩于“壮”“劣”二字,形成强烈反差。话已至此,通常会就“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继续声讨下去。不过丘迟随即从萧梁立场换到陈伯之的角度,仅谓:
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獗,以至于此。
虽言“内”“外”二因,但之所以“不能内审诸己”,归根到底是“外受流言”所致。留有回旋的余地,这是丘迟落笔的高明之处。
既然有意招降陈伯之,势不能不表明萧梁的态度。丘迟于是直言“圣朝赦罪责功,弃瑕录用”,并用汉主纳朱鲔、魏君收张绣二事,强调萧梁“推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的决心。此处虽类比昔日朱、张之事,却有意将陈伯之与“昔人”拉开距离,即所谓“况将军无昔人之罪,而勋重于当世”,是说“昔人”尚且能够“弃瑕录用”,何况罪小而功大的陈伯之。如若伯之“迷途知返”“不远而复”,萧梁方面开出的条件是:
将军松柏不翦,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
《资治通鉴》节录丘迟此书,这一段落即在其中,且胡三省对这四条逐字解说(《资治通鉴·梁纪二·天监五年》)。遥想当时陈伯之接到丘书,身边文人对条款的说解,与注家相比,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丘迟笔下,萧梁朝堂“功臣名将,雁行有序”,而北魏政局则混乱不堪。谓之“恶积祸盈,理至燋烂”,复谓“伪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携离,酋豪猜贰”,又谓“系颈蛮邸,县首藁街”,极言恶劣。如此来看,“借命”异邦的陈伯之,确乎如同“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
行文至此,丘迟分别从归梁与在魏两方,剖析陈伯之的现实处境,说理不可谓不精湛。然而,倘若细究起来,也不无破绽。不论北魏政局如何,陈伯之投魏后,魏“以伯之为持节、都督江、郢二州诸军事、平南将军、江州刺史、曲江县开国公”(《魏书·田益宗传》附记陈伯之事迹;《梁书·陈伯之传》亦记),地位不可谓不显赫,足见北魏待陈伯之不薄。况且陈伯之素乏远见,“鱼游沸鼎,燕巢飞幕”之忧,或许暂时还无从谈起。
按履历看,陈伯之在北魏期间,以魏将身份对战梁军,均获胜仗。魏宣武帝正始元年(梁武帝天监三年,504),陈伯之“破萧衍将赵祖悦于东关”;魏正始三年(梁天监五年,506),伯之又击破萧衍将昌义之于梁城(《魏书·世宗纪》《岛夷萧衍传》;《资治通鉴·梁纪一·天监三年》《梁纪二·天监五年》)。梁军屡不敌陈伯之,或因此,就在昌义之战败后一月,萧宏北伐,再遇陈伯之“与魏军来距”,时为萧宏记室的丘迟于是“以书喻之”(《梁书·文学传》《资治通鉴·梁纪二·天监五年》)。可见,正是因为武力不敌,才换以文攻。
丘迟书中一再表示“主上屈法申恩”“当今皇帝盛明”,适与“恶积祸盈”的北魏君主形成鲜明对比。实则陈伯之归梁之后,虽复以为西豫州刺史,却“未之任”(《梁书·陈伯之传》),盖“恐其复叛也”(《资治通鉴·梁纪二·天监五年》胡三省注)。此自是后话,但陈伯之受书之时,未必不会对在手的权势与凭空的许诺轻重权衡。纯就理性层面考虑,丘迟所示恩惠或不足以劝诱陈伯之改图。
除去申明在魏与归梁的利害,丘迟来书尚有一个看似无关宏旨、却极负盛名的段落: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
经由描绘南方风物,援引廉颇、吴起故事,试图唤起陈伯之的思归之情。“将军”大可不信梁帝,也可不顾在魏的处境,然而,面对人皆有之的情感,陈伯之根本无从反驳。无怪乎《艺文类聚》编选说辞时节录丘迟此书,悉数刊落开示利害的说理笔墨,独留这段“情文”(欧阳询《艺文类聚·人部·说》),隐然标榜此节在“说”上最得“神理之数”(《文心雕龙·情采》)。与之相较,《资治通鉴》但取“寻君去就之际”“主上屈法申恩”“将军鱼游于鼎沸之中”等说理文辞,盖为史家眼光,未得文心三昧。
有感于陈伯之归降一事,晚唐诗人钱珝写下了《春恨》(其一):
负罪将军在北朝,秦淮芳草绿迢迢。高台爱妾魂销尽,始得丘迟为一招。(韦縠《才调集》卷一)
沈祖棻先生评价此诗:“完全抛开了民族、国家、政治、军事等重大方面,而只就私人生活,而且是私人生活中很小的一个方面发挥。”(《唐人七绝诗浅释》,北京出版社2021年版)这首诗与其说是写陈伯之,不如说是写丘迟笔下的陈伯之,诗中“秦淮芳草”“高台爱妾”云云,显然直接取自丘书。其实丘迟书中并非没有“民族、国家、政治、军事等重大方面”,“高台爱妾”之类也不过是权宜之计;但唯有“秦淮芳草”,像是放入文章中的一粒盐,如若没有这一粒盐,理性的劝服便少了文学的滋味,而恰恰是这一粒盐,令陈伯之这块“顽石”最终“点头”,也令后人在追忆这一政治事件时念念不忘“暮春三月”的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