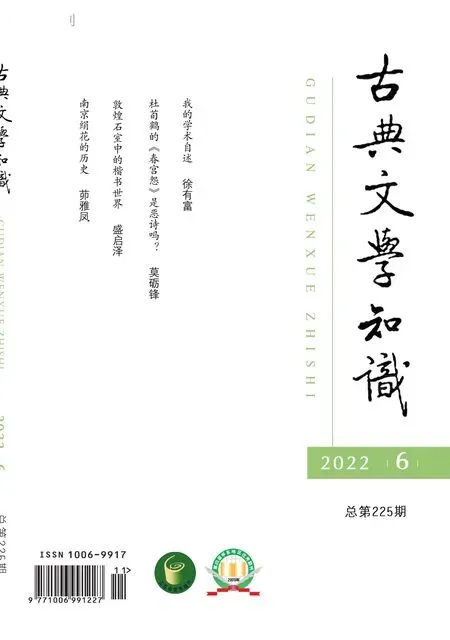《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文体与撰述方式
陈恩维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下简称《景教碑》)由景教传教士伊斯出资、景净撰述、吕秀岩书刻,于唐建中二年(781)在长安大秦寺落成,唐后期被埋入地下,1625年期间出土,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由于景教碑是最早被发现的景教文献,故自被发现以后,成为其他景教文献研究的起点,但相关研究很少涉及其文体和撰述方式。事实上,《景教碑》的文体包含了丰富的文化信息,有待进一步讨论。
一、 《景教碑》综合了多种景教文献的文体
《景教碑》碑文大致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景教的基本教义。在介绍阿罗诃为造物主之后,略述由于撒旦的诱惑,人类积昧亡途,弥施诃“戢隐真威,同人出代”,故玛利亚怀孕,而耶稣降生教化信众;最后介绍了景教的经典、仪式与得名等。对景教基本教义的介绍,曾为景教早期汉文经典《序听迷诗所经》《一神论》等所反复宣讲,只不过前者采取了布道文的形式,而这里是以碑文体式出现。换言之,《景教碑》的第一部分,也可以视为是一篇讲述基督教教义的布道文。
碑文第二部分述景教自唐太宗以来的发展历史。阳玛诺《景教流行中国碑正诠》指出:“首惟真宰,次美列宗,明国祚之所由,而以为圣教之弘功,弗可以弗志也。”道出了唐代景教在官方支持下得以发展的历史事实。碑文历数唐太宗、高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对景教的支持,同时也不讳言在武后时期的艰难发展,可以看作是一篇简短的中国教会史。这部分内容,可能参考了《教会史》的写法。《教会史》是试图重现从使徒时代到公元324年这三个世纪的教会历史,是了解早期教会和罗马帝国不可或缺的经典著作,也成了后世各地教会叙述自身历史的参照蓝本。敦煌景教写本P.3847《尊经》所列景净所译经典中有“《删可律经》”,即古罗马历史学家优西比乌所著《教会史》。这说明景净确实读到过《教会史》一书的叙利亚语版。自太宗时入华到景教碑撰写时,景教已在中国发展了近一百五十年,因而景净借撰写寺庙碑之际,参照《教会史》而叙景教在华历史,并刻意宣传了唐代皇帝对景教的支持。
碑文第三部分歌颂伊斯,依次介绍了伊斯的出身、才性、参加郭子仪平叛、获得肃宗召见的世俗经历,也择要叙述了他散财修建景教寺、参与景教仪式以及救助信众的宗教活动,称赞他为“白衣景士”,已经是一篇比较完整的圣徒传记。早期基督教人物传记,散落于《圣经》经文之中。如耶稣的传记散见之于福音书中,保罗的传记主要见于《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阿罗本所携经书中不仅有记载耶稣生平的《四福音书》,还有许多独立的使徒传记。如《尊经》著录的《报信法王经》即《施洗约翰传》,就是施洗约翰传记。由此看来,景净对使徒传记的体例应当非常熟悉。第三部分的伊斯传记,应是参考了景教文献中圣徒传记的写法。
碑文第四部分为赞文,以诗歌形式复述了前三部分的全部内容,其文体与《圣经》中的《诗篇》接近。赞文前面八句赞三位一体,明显吸收了《诗篇》中的赞美诗体裁;接下来历叙唐朝各代皇帝对景教的支持,则体现了颂词的特征;最后以四句骚体诗,总结碑文的写作目的是弘教,带有祈愿诗的特征。换言之,《景教碑》赞文部分,体现了《圣经》诗篇的体式特征。
早期景教文献大致可以分为圣经文书、仪式文书、教史、神哲学著作、历算、杂撰等6类。其中,圣经文书中最常见的就是福音书、使徒传和《诗篇》,仪式文书中最常见的是布道文和赞美诗。唐太宗时期阿罗本曾携带530部梵语景教文献到达长安,包含了以上各类文体,而景净依据传道和礼仪的需要翻译了其中最为重要的35种。由此可见,景净对于叙利亚文景教经典中的布道文、教会史和圣徒传、赞美诗的内容和体例,都是非常熟悉的。这也是《景教碑》的文体汇合了布道文、教会史、圣徒传、赞美诗等多种文体的原因所在。
二、 《景教碑》的寺庙碑体制及其作者
《景教碑》的体制,还参考了中国寺庙碑颂的写法。中国制碑的习俗历史悠久,其种类繁多,体裁各具特色,概括起来主要有功德碑和寺庙碑。唐代以前,最为著名的寺庙碑作品当属《文选》卷五十九所录王简栖《头陀寺碑》,其文辞巧丽,为世所重。《头陀寺碑》作为寺庙碑文的典范作品,在文体结构上具有范式意义。其第一部分阐述“涅槃之蕴”;第二部分叙述佛教的传播历史;第三部分介绍了时任主持释昙珍法师,说明了撰写碑文的原因是为了宣扬功德;第四部分是四言铭文,用韵文复述了碑文的内容。比较可知,《景教碑》在文体结构上明显模仿了《头陀寺碑》。《景教碑》的第一部分介绍了景教的基本教义,与《头陀寺碑》第一部分阐述“涅槃之蕴”基本对应;第二部分叙述景教在唐朝的传播并介绍大秦寺营造的过程,与《头陀寺碑》第二部分对应;第三部为伊斯传记,对应《头陀寺碑》对释昙珍法师的介绍;第四部分的赞文,也与《头陀寺碑》的碑颂对应。
除了文体结构的刻意模仿外,《景教碑》和《头陀寺碑》一样采取了工整华丽的骈文形式。如第一部分对景教仪式的介绍:“法浴水风,涤浮华而洁虚白;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无构。击木震仁惠之音,东礼趣生荣之路。存须所以有外行,削顶所以无内情。不畜臧获,均贵贱于人;不聚货财,示罄遗于我。斋以伏识而成,戒以静慎为固。”这段话介绍了景教的弥撒和礼拜仪式、斋戒习惯、衣着打扮、慈善活动等,内容相当驳杂,却以对仗工整的骈句表达,体现了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此外,《景教碑》对于典故的运用,密集而不漏痕迹,显示了作者深厚的中华文化修养。据初步统计,不到2000字的碑文中引用《易经》30处,《诗经》30处,《春秋》20处,涉及经书150处,史书100多处,子书30处(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典故的密集使用,要求作者精通中国经典,故非一般文士所能为。从景净所译《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志玄安乐经》《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来看,景净的中文虽称流利,对中国经典的了解也未达到熟谙的程度,恐无法写出如此工整华丽、意蕴深刻的骈文。因此,我们推测,《景教碑》题作大秦寺僧景净“述”而非“撰”,碑文实际上是经过中国文人的润色而成的。
《景教碑》撰成后,置于焕然一新的长安大秦寺,无疑给景教传播带来积极影响,也给其述者景净带来文学上的名声。《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卷上记载,贞元二年(786),般若三藏(法师)“乃与大秦寺波斯僧景净,依胡本《六波罗蜜》译成七卷”。三藏法师因为“不闲胡语,复未解唐言”,主要负责口头阐明经义,而他之所以找“不识梵文,复未明释教”的景净合作,应该是鉴于景净曾述写《景教碑》。不过,这次翻译的七卷本并不成功,被德宗皇帝下令重译。贞元四年(788),此经按照敕令重译,三藏法师仍然负责宣扬教义,担任了第一次翻译时同样的角色,而景净被排除在外,正义和润文的工作转由其他中国僧人负责。由此看来,第一次译经失败的责任在于景净。由于他不懂梵文,对于佛教理解不深,汉语也不够娴熟,才会使其译本招致“理昧词疏”的批评。《景教碑》撰写时间比翻译《六波罗经》早了五年,以景净翻译佛经时所体现的汉语水平和文化修养来看,他以一己之力恐不能写出像《景教碑》这样成熟的骈文。因此,《景教碑》很可能是由景净口述,而由擅长写作的僧人“文润”而成。这也很好地解释了《景教碑》为什么一方面体现了《圣经》文书和礼仪文书的文体特征,另一方面又带有鲜明的寺庙碑特征。
三、 《景教碑》撰述方式与景教经典翻译
《景教碑》一方面因为景净的口述而保留了景教文献之文体结构,另一方面则因为中国文人的润色而带有了明显的中国寺庙碑特征,实为中西文体杂糅之产物。而其由景净口述而由中国文人执笔的撰写方式,无疑启发了景教的经典的翻译。《景教碑》曾提及景教经典:“圆廿四圣有说之旧法,理家国于大猷。……经留廿七部,张元化以发灵开。”这里提到了《旧约》的24部经典和《新约》27部经典。碑文又进而表示“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这表明,在撰述景教碑时尚无景教经典翻译,但景净已经试图去翻译景教的重要经典。景净与他人合作撰写《景教碑》的经历,无疑为其景教经文翻译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事实上,景净和三藏法师合译《六波罗蜜多经》失败后,唐德宗曾下敕令曰:“且夫释氏伽蓝、大秦僧寺居止既别,行法全乖。景净应传弥尸诃教,沙门释子弘阐佛经。欲使教法区分,人无滥涉。正邪异类,泾渭殊流。若网在纲,有条不紊。天人攸仰,四众知归。”(见《贞元释教录》卷十七)可能正在这一敕令的要求下,《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在贞元四年(788)重译,而景净也与此同时开始了景教经典的翻译。《尊经》尾跋中有“后召本教大德僧景净,译得已上卅部卷”记载,由其中的“召”字可知,景净译经也是应诏而成的。
《景教碑》糅合中西文体的探索,对景净译景教经典的策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尊经》正文列举了景净所翻译的35部经典,其中《宣元至本经》《志玄安乐经》和《三威蒙度赞》流传至今。如《志玄安乐经》其实是根据《新约·彼得前书》1:6—14节的一次标题式讲道,其经文在阐发什么是安乐道以及如何得安乐的主题时,采用了引论—本论—结论的讲道文典型结构。但是,《志玄安乐经》也明显借鉴了《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的体例。如《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卷一,以“如是我闻”开篇交代薄伽梵与众多菩萨摩诃萨谈论佛法,讨论如何走上“大涅槃安隐正路”,如何“修习涅槃彼岸”,从而让“利益安乐一切有情,令得欢喜”。《志玄安乐经》不仅借用了“安乐”这一概念以及比喻的修辞,并且袭用了诸如“如是我闻”这样的讲经“套语”,模仿了《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的对话体结构。而《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虽为翻译叙利亚文《荣归上帝颂》,但其七言诗体式,模仿了十卷本《大乘理趣六波罗蜜经》卷一中所录偈颂体式。《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补入了十句原文所没有的诗句,大部分来自十卷本《大乘理趣六波罗蜜经》卷一所录偈颂。不过,在核心概念的使用上,景净仍然坚持景教的概念。如“安乐”在佛教中指涅槃解脱之乐,而《志玄安乐经》使用“安乐”的概念,则指景教信仰的最高境界。“救度”在佛家是指帮助众生脱离苦海,而《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中“救度”是指对“原罪”的救赎。上述核心概念,其名虽同,而其义实异。这表明景净遵守了“教法区分”的敕令。这种文体模仿而又“教法区分”的策略,实际上是在官方要求和景净的共同努力下,建立了一种异质文化交流而又互鉴的基本模式。
综上所述,《景教碑》是景教和佛教文体的杂糅,其由景净口述而中国文人润色而成的撰述模式,不仅推动了景教经典的翻译,甚至影响了景教经典的翻译策略,建立了一种文化交流互鉴的模式。这也是《景教碑》文体的文化意义所在。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传教士中文报刊的文体发生与文体形态研究”(批准号19BZW15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