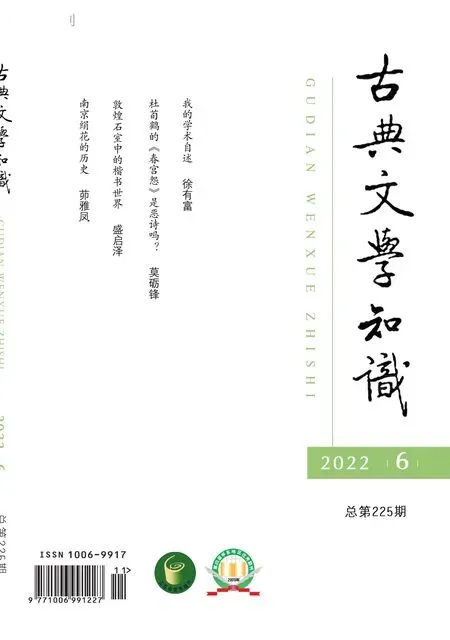戏笔谈经:袁枚《麒麟喊冤》“排郑”本末
王 楚
袁枚一生著作颇丰,涉猎甚广,蒋士铨特以“古来只此笔数枝,怪哉公以一手持”(《题随园集》)赞其博通多能。袁枚的思想亦较驳杂,其诗“郑孔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遣兴·其二二》),既不喜尊奉郑玄、孔颖达注疏的汉学,又排斥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宋学,学术立场复杂而独立。在《续子不语》中,有一篇三千余字的小说《麒麟喊冤》,即是袁枚凭借戏谑笔法讽刺汉、宋之学的奇文。尤其针对乾隆年间盛行的汉学,袁枚不惜以大量篇幅,百般挖苦汉儒的代表人物郑玄;并借小说之笔作考辨文章,庄谐并举,亦真亦幻,令人想见其手持数笔、意气纵横的神采。
《麒麟喊冤》的主要情节很简单:“奉汉排宋”的邱生于山中迷路,误入天帝藏书的文明殿,由殿前古衣冠者为其讲述郑玄之学在天庭的兴废,最后邱生有所感悟,尽弃所学。小说开端交代背景,称:
有邱生者,吴人也。幼习时文,屡试不售,怒曰:“宋儒误我!”乃尽烧其讲章语录,而从事于考据之学,奉郑康成、孔颖达为圣人,而渺视程、朱。
邱生专事考据,奉为经书作注、疏的郑、孔为圣,即谓改辙汉学。嗣后,邱生“坐古松之下,温习《仪礼注疏》”。忽而“白额虎衔之而去,行数里,乃掷于深谷中”,从而引领邱生来到文明殿前。被白额虎叼走的《仪礼注疏》一书,颇能体现清初、乾嘉时期学风,而《仪礼》文辞枯燥,韩愈已苦难读,其文风正站在袁枚“性灵派”主张的对立面,很适合邱生潜心攻读。
邱生在文明殿翻遍天帝藏书,发现竟无《六经》及其注疏。古衣冠者告诉他,这缘于汉儒“造作注疏,穿凿附会,致动上帝之怒”。邱生探问个中详曲,乃答曰:
汝可知万国九州,只有一天乎?自盘古开辟以来,三皇五帝,莫不钦若昊天,天亦安享郊牛数千年矣。忽然东汉末年,有五妖神头戴冕旒,身穿龙衮,闯入天宫,各称名号。其自称“赤熛怒”者,红面猬髯,状尤狞恶。其他兄弟四人,衣青者号“灵威仰”,衣黄者号“含枢纽”,衣白者号“白招拒”,衣黑者号“汴光纪”。竖眉昂首,哓哓嚷嚷,竟欲篡夺上帝之位,分据为五国。……适苍圣朝天,奏曰:“此五神姓名皆谶纬妖言,汉人郑玄师弟所传,但召郑玄来,则不斗而自伏矣。”……见其(玄)举止老成,饮酒三百杯不醉,遂署文明殿功曹,五妖神始帖服不动。
这篇小说有一个基本逻辑:学者们对经典的各种解释,会对现实世界造成实际影响。此段讲到赤熛怒等五帝篡夺上帝(“天”)之位,根由便在经师诠释“天”的具体内涵时出现了新说。早先,神格化的最高主宰称“天”“昊天”或“帝”,西汉方士缪忌、东汉经师马融认为“太一”为天神中最贵者。时至汉末,郑玄将原本唯一的“天”拆分为六,包括“皇天北辰耀魄宝”与“上帝太微五帝”,前者为原来的“昊天上帝”,后称“上帝”者乃赤熛怒等五帝,如此便有了六个“天”。此说在郑玄自己的诠释体系中或能自洽,但因涉及祭天大礼,提出后不久即遭到王肃猛烈抨击,后世学者也多持非议。袁枚将五帝出现的时间定在“东汉末年”,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在流行于两汉之际的纬书《春秋·文耀勾》中已有五帝名号。刻意突出这一时间,无疑意在归咎郑玄。郑玄注经常引纬书,屡为后世学者诟病。
袁枚曾撰写一篇学术札记,专论郑玄经注不妥之处,题为《经注迂谬》(以下省作《迂谬》),收在《随园随笔》之中,其中不少观点与《麒麟喊冤》相表里,文句也有部分重合,可视为《麒麟喊冤》的“学术底本”。关于“五帝”,《迂谬》就提道:“(郑玄)注‘胡然而帝也’云:‘帝,五帝也。’孔(颖达)疏便引灵威仰、赤熛怒以实之。”(同见《随园诗话》卷一)言孔氏疏不破注,直接引《文耀钩》原文襄赞康成,不免讹误益甚。在小说中,果然解铃还须系铃人,五帝顿时服帖,郑玄因此受到天帝信任,“凡郑所奏,帝亦颁行世间”。天帝不曾料到,在此之后将面临更多麻烦。
倘若学者的每一条解释、每一个观点都会“言出必行”,乃至化作千年铁则,不免令人忧惧。古衣冠者就说,郑玄之教行世既久,自有不少“必不能行”者,引得人间、天界不堪其苦。在此略举数条:
天子冕旒用玉二百八十八片,天子之头几乎压死。
此条本自《周礼·夏官·弁师》:“五采缫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郑注:“衮衣之冕十二斿,则用玉二百八十八。”贾疏:“以其十二旒,旒各十二玉,前后二十四旒,故用二百八十八。”郑玄以为冕的前后皆有旒,所以得出二百八十八之数,其实冕只有前部有旒(《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重量理应减半。复有:
夏祭地示必服大裘,天子之身几乎暍死。
“暍”即中暑。大裘是“王祀天之服”(《周礼·天官·司裘》),郑玄引郑众注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质。”贾疏云:“案《孝经·钩命诀》云:‘祭地之礼与天同。’牲玉皆不同。言同者,唯据衣服,则知昆仑神州亦用大裘可知。”若依此说,则无论冬祭、夏祭,天子都必须穿着黑羔裘。陆佃曾驳郑、贾之说(《元祐大裘议》),不表。复有:
只许每日一食,须劝再食,天子之腹几乎饿死。
事见《礼记·礼器》:“天子一食。”郑注:“谓告饱也。”孔颖达疏:“‘一食’者,食犹飧也。尊者常以德为饱,不在食味,故一飧辄告饱,而待劝之乃更飧,故云一食也。”“德”是不能饱腹的,若无人劝食,“尊者”就只好饿着。《迂谬》讥曰:“何其作伪至此!”
除了在礼仪上造成诸多不便,郑玄的经说亦引出不少无辜受害者,其中便包括前来“喊冤”的麒麟。文曰:
一日,天帝坐紫薇宫,见云中飞下一兽来,龙鳞马鬣,喊冤奏曰:“臣麒麟也。不食生虫,不践恶草,人人称为仁兽。必待圣人出,臣才下世。不料有妄人郑某、孔某者,生造注疏,说郊天必驳麒麟之皮蒙鼓,方可奏乐。信如所言,人主郊天一回,必杀一麒麟。麒麟何罪,遭此屠毒?此等议论,只好吓骗黄巾贼,见老郑便一齐下拜;使麒麟见之,必唾其面。”
“麟鼓郊天”一事,牵涉小说主旨与《随园随笔》的成书,且待后文详叙。由于郑玄曾论妇人之礼,仙妇们也大受干扰,纷纷告罪于天帝。麒麟控诉未毕,只见云中有众仙妇姗姗而来,其中一位跪奏曰:
妾姜氏,周王妃也。当时周王劝农,妾并不随行。今有妄人郑某,说天子劝农,必与王后同行。妾想妇人幽闺弱质,行不逾阈,岂有披霜冒雪出来劝农之理?北魏王肃曾言其非,唐人孔颖达将王大加呵斥,党同诬妄,一至于此!
“天子劝农,必与王后同行”的说法,出自郑玄笺《诗经·小雅·甫田》“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之语:“曾孙,谓成王也。……成王来止,谓出观农事也。亲与后、世子行,使知稼穑之艰难也。”对此,王肃曾以“妇人无阃外之事”予以驳斥,孔颖达则力辩郑玄不误,但较牵强。不过小说错将王肃身处的曹氏之“魏”写成了“北魏”,盖因二魏皆有王肃而误。想象周成王的王后、世子“披霜冒雪出来劝农”的场景,确实有些不妥。实则“曾孙”不必特指成王,朱熹就认为是“主祭者之称”,在典籍中也常代指诸侯,兹不细论。
又有“南国诸侯大夫之妻”上告郑玄另外两条罪状。二者皆是缘于郑玄的训解,使她们蒙受污名。分别是:
夫君外出,妾等心忧。“亦既觏止,我心则降”,言既见而心安,此人情也。郑训“觏”为交媾之“媾”,言交精而心降。
又训“五日为期,六日不詹”,云妇人五日不御,必有思男子而不得之病。
前者本自《诗经·召南·草虫》。因为是《召南》中的官司,所以特言仙妇为“南国诸侯大夫之妻”。《草虫》中有一句:“亦既觏止,我心则降。”郑玄援引《易·系辞下》“男女觏精,万物化生”作解,并云:“觏,合也。男女以阴阳合其精气。”(孔疏引《周易》郑注)后一条的意旨更加显豁。所谓“五日为朝,六日不詹”,出自《诗经·小雅·采绿》。毛传说:“妇人五日一御。”郑玄解释为:“妇人过于时乃怨旷。”如此说来,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难怪仙妇们会怒不可遏,声称:“妾等皆公侯淑女,不应贪淫至此!”
此时,麒麟也在一旁添油加醋。大概袁枚想到,若要尽情嘲弄郑玄,光是告倒他一人还不够,康成既然注《礼记》,殊不知编订《(小戴)礼记》的戴圣也值得好好批判一番,因而假麒麟之口笑道:
诸夫人但知责郑玄,不知责戴圣。圣造《礼经》,其罪更大。臣在周文王灵囿中,与振振公子同游,见文王宫女,原无定数,多不过二三十人,并无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之名号,亦从不见有“金环进之、银环退之”之条例。文王日昃不暇,乐而不淫,那得有工夫十五夕而御百余妇哉?
“九嫔”之说出自《礼记·昏义》:“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金环银环”云云,出自《诗经·邶风·静女》的毛传。麒麟进而揭露戴圣“本系赃吏”,私德本就有亏,难怪会“造作宫闱经典,以媚昏主”。戴圣担任九江太守时,确实“行治多不法”,事见《汉书·何武传》。学者私德本与学术是非无关,但用在攻讦文字中,威力倒也不容小觑。
听罢麒麟与仙妇的控告,天帝不免“大悔”,于是召来苍颉商量对策。苍颉审时度势,上奏天帝:“惟有召西方明心见性之人、学佛未成者来。”详询之下,范围得以缩小:“惟有少时借佛书参究一番,中年遁归周、孔者,墨行儒名,人才肯服。宋朝某某最佳。”毫无疑问,这里指的就是朱熹。尽管麒麟在旁争辩,说朱熹解经也难免对天地运行造成不便,但经过反复权衡,天帝还是接受了苍颉的举荐。相较针对汉儒的无情嘲弄,小说评论朱熹及其他宋儒的内容并不甚多,但众人的形象实在可笑。请看原文:
有褒衣博冠,手执太极圈者;有闭目指心,自称“常惺惺”者;有拈花弄月,自号“活泼泼”者。最后,四人扛一大桶,上放稻草千枝,曰:“此稻桶也,自孔、孟亡后,无人能扛此桶。唐人韩愈妄想扛桶,被我取他与大颠和尚书札,搜出真赃,把他所扛之桶多掀翻了,何况郑、孔,敢与我四人为难乎!”言未毕,果见赤熛怒、白招拒五妖神爬墙穴洞,偃旗息鼓而逃。天帝大喜,即命此四人权摄文明殿功曹。此汉学所以不昌,而文明殿之所以无注疏也。
不难发现,宋儒的滑稽形象皆根基于各人的学术主张:“手执太极圈者”是周敦颐,他曾作《太极图》与《太极图说》;“自称‘常惺惺’”的应是谢良佐,“常惺惺”本为释家语,上蔡以“常惺惺法”论“敬”;“自号‘活泼泼’者”乃程颢,他曾言:“‘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中庸》)此一段子思吃紧为人处,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孟子·公孙丑上》)之意同,活泼泼地。会得时,活泼泼地;不会得时,只是弄精神。”(《河南程氏遗书·二先生语》)剩下只闻其声、未表其形的便是朱熹,他同三位先生一起扛起了“稻桶”(道统)。朱熹以韩愈《与大颠和尚书》“掀翻所抗之桶”一事,李贽早已讥之,称其以“亹亹千余言,必使之(韩愈)不为全人而后已”(《焚书·文公著书》)。此中牵涉一段学术公案,而本文只拟讨论袁枚《麒麟喊冤》与郑玄、汉学的关系,所以就此打住。
随着宋儒的到来,“五妖神”狼狈逃窜,注疏也遭斥退,天界终于恢复了暂时的太平。为何称“暂时”?因为古衣冠者透露了后续剧情:“宋儒此座,亦恐终不能久。现在陆(九渊)、王(阳明)二姓,本朝颜习斋(元)、李刚主(塨)、毛西河(奇龄)等,都与为难。”若要说起,便是另一段学术史了。
“麟鼓郊天”作为袁枚用以挖苦的郑玄重要情节,在一噱之余,尚有文外细情需要说明。“郊天必驳麒麟之皮蒙鼓”的说法并非出自郑玄的笺、注,而是一封题名孔融的书信,内容是:
郑康成多臆说,人见其名学,为有所出也。证案大较,要在五经四部书。如非此文,近为妄矣。若子所执,以为郊天鼓必当麒麟之皮,写《孝经》本当曾子家策乎?(《与诸卿书》)
袁枚抓住这个话头,在《随园随笔·迂谬》中大肆非议郑注,还搬出多位前代大儒,用以支撑己说:
孔融执子孙之礼以事郑玄,犹不信郊天鼓必用麒麟皮之说,以为康成名重,故“多臆说”,“若郊鼓必用麟皮,是写《孝经》必用曾子家竹简也”。虞翻亦极言其纰缪,故驳正康成一百八十事,后魏王肃尤多驳正,而唐人孔颖达为之作疏,则附和穿凿,一字不敢置议矣。……同官博士马嘉运亦时时驳之,具载本传。
东吴虞翻曾“奏郑玄解《尚书》违失事目”数条,曰:“玄所注五经,违义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三国志·虞翻传》注引《翻别传》)所驳数目与袁氏所言小差,但这百六十七事早已失载,不知是否言及麟鼓。王肃极力排郑,但目力所及,未见关于此事的驳语(此处时代误作“后魏”,前文已识)。马嘉运之事,见《旧唐书·孔颖达传》:“太学博士马嘉运驳颖达所撰《正义》,诏更令详定,功竟未就。”马嘉运曾驳孔颖达不假,但若是郑玄的注中没有的内容,孔颖达不会凭空作疏,马嘉运自然也无可驳正。由此可见,“麟鼓郊天”的文献源头十分可疑,袁枚意图抓住此事大做文章,恐怕不那么容易。
清代学者敏锐地意识到了孔融《与诸卿书》可能存在的问题。王鸣盛就对此书真伪深表怀疑,说:“孔融尊崇康成特至,何得有如许妄谭?”(《蛾术编·郑氏品藻》)钱大昕直接判定此乃托名伪作,论证也有理有据。其文曰:
予谓此必非孔文举之言,殆魏晋以后习王肃学者伪托而作。晋荀勖《中经簿》始有四部之分,文举汉人,安得称“四部书”?且郑君注三《礼》,初无麒麟皮冒鼓之说也。范蔚宗书及章怀注皆无此语,不可执无稽之谈以诬盛德。(《十驾斋养新录·御览载孔融语》)
此案遂成定谳。晚出的孙诒让观点比较平和,他怀疑汉季可能有“麟鼓郊天”之说,或者孔融之说只是一时嘲戏,但“要郑诸经注,实无是义,不可诬也”(《周礼正义·地官·鼓人》)。时至今日,仍有学者欲为《与诸卿书》正名(俞绍初《建安七子集》),但要推翻钱说,似不甚有力。论述到此,郑玄迫害麒麟的罪名已经洗脱。
千余年后,袁枚在对孔融书中的“麟鼓郊天”搔首发问时,文献旧说给出的帮助相当有限,询诸友人,也未能收获满意的答复。根据《随园随笔》的记载可以推测,袁枚直到离世,对此问题的本末经纬仍旧不甚明了,但这并不妨碍他自恃文胆,将诸多对郑玄与乾隆年间学风的不满敷演成一篇《麒麟喊冤》,在嬉笑怒骂间逞一时之快。
袁枚去世两年后,其子袁通、袁迟携《随笔》书稿拜谒孙星衍,孙星衍打开书稿首卷,便见《注经迂谬》中“麟鼓郊天”一事。想起当年,自己也曾因此事受袁枚咨询,于是怀揣复杂的心情,在《随园随笔序》中如此答覆:
先生尝举“麟皮鼓郊天”及“凿尸颊饭唅”以问,时未及答。及检《汉书·王莽传》“冠麟韦之弁”,李奇注谓:“鹿皮冠。”《说文》谓麟为“大牝鹿”,与麒麟字异,知是鹿皮鼓耳。……惜不及告先生,聊书此慰挂剑之恨。(《平津馆文稿》卷下)
麟本是鹿,麟皮就是鹿皮,如果真有“麟鼓郊天”,所用不过是鹿皮鼓而已。孙星衍解释终于为这段漫长的考据画上句号,遗憾的是“不及告先生”。此番“挂剑”,犹如重新搬演萧梁时刘孝标与亡友论学的情景(《重答刘秣陵沼书》),格外令人动容。
这段争论背后,是袁枚扬性灵、抑考据的主张。《麒麟喊冤》竭力“排郑”,便是排斥考据学风。袁枚不仅自己不主张考据,对身边涉足考据的友朋、后学也多有劝诫。孙星衍早年以诗才获得高名,但其志向却系于考据。袁枚对此极为不满,特意向孙星衍言明:
日前劝足下弃考据者,总为从前奉赠“奇才”二字,横据于胸中。近日见足下之诗、之文,才竟不奇矣,不得不归咎于考据。(《小仓山房尺牍·答孙渊如观察》)
以至相与约定:“如再有一字争考据者,请罚清酒三升,飞递于三千里之外。”多年以后,孙星衍翻阅这部犹如“罪证”的考据笔记,不禁反诘:“先生弃官山居五十年,实未尝一日废书,手评各史籍字迹历历犹在,则亦未尝不时时考据。”(《随园随笔序》)袁枚所不知的是,自己用以批判考据的考据成果,复被更为严谨的考据纠正。这样的结局,应是“麟鼓郊天”这类问题的最好收场。
袁枚好学博览,又喜议论,致使他在读书、治学之时,也难免用到考据手段,不免令其内心矛盾。就好似袁枚面对《随园随笔》的态度:他似有懊恼地对孙星衍说,此书只是“因五十年来看书甚多,苦不省记,择其新奇可喜者,随时摘录”,却不意“终有类于考据”。当江苏巡抚奇丰额意欲刊刻此书时,袁枚“苦辞”不与,并“请将此刻费选刻近人散骈文两体、古文之未开雕者”,以为如此乃是“发潜德之幽光,最为功德”(《答孙渊如观察》)。这样的说辞绝非虚矫。在《麒麟喊冤》的结尾,邱生问:“上帝何好?”古衣冠者毫不犹豫地回答:“好诗文。”此种诗文,自然是袁枚标举的“天然性灵”之作。
——以“能不我知”考据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