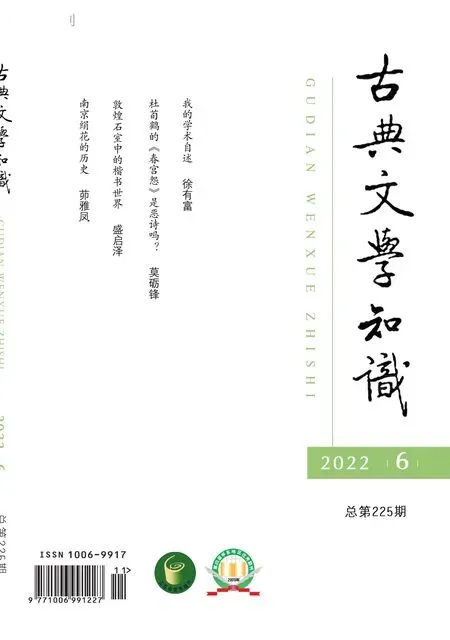敦煌石室中的楷书世界
盛启泽
唐孙过庭《书谱》开篇就说:“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唐代开始,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的墨迹就被奉为圭臬,自此一直作为学书者经典临摹学习的对象。清中叶,书法史上以二王一家独大的帖学经典系统被打破。金石之学,乾嘉以来弥盛,地不爱宝,古石旧拓,重见者日多,珍奇屡出,经过考据家、收藏家的不断整理,形成了书法史上帖学以外的另一类范本——碑学。1900年5月,在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圆箓带人清理洞窟的沙尘,无意间发现了一间石室,里面堆积了数不清的经卷、文书、绘画等物品,据斯坦因说,层层叠叠,高达十尺,石室内藏书绝大部分为写经,这些墨迹成为书法史进程中又一范本——敦煌石室墨迹(图1)。
一、 内含精光——“意临”的范本
敦煌石室墨迹躲过战火兵燹,天灾人祸,保存了纪年可考,从前秦到北宋,跨度长达七百年的古代墨迹,数量庞大,风格有迹可循。石室墨迹发现时间短,虽不能称作书法经典,但它足可以成为书法研究和临摹中重要的借鉴。敦煌石室墨迹的数量、品质、品种足以成为书法史发展过程中的范本,唐代写经占据石室墨迹中绝大部分,因而作为意临的范本,楷书部分十分重要。陶幽庭在《匠心的维度》中说创造性的再书写,或者叫作“意临”。意临给人们临摹书法提供很大的合理想象空间。
石室墨迹不仅有大量抄写的经文,还有抄经的草稿,以及磨炼书法的痕迹。敦煌地处边陲,当时寺院需要大量的抄经人才,若只从敦煌以外征集经生,很难满足当地需求,所以敦煌寺院不仅主持佛事,还兼办学校,书法教学也成为一个重要内容。学生们在寺院办的学校里练习书法,于是遗留至今的墨迹中有许多当时学生临摹名家的书法残纸。佛经的抄写,注重文字的准确,同时也在意字迹的美观,因此他们常常在抄经之前,甚至在抄写中间临摹几行前人法帖,寻找书写感觉。抄经不仅要有恭敬的虔诚心,且字迹要工整美观,大多数都以楷书完成,楷书墨迹在石室墨迹中占有绝大份额。
石室墨迹临摹的名家楷书范本不乏欧、柳的经典之作。范本就发现有欧阳询《化度寺碑》唐拓本,共十二页(图2),还有伯4503号为柳公权《金刚经》(图3)拓本卷子,无一字损坏,其后落款为“长庆四年(824)四月六日,翰林学士朝议郎,行右补阙,上轻车都尉,赐绯鱼袋柳公权为右街僧录准公书。强演、邵建和刻”。准公法名灵准,《高僧传》十一称,穆宗即位之年,“命两街僧录灵准公远斋敕旨迎请”。灵准为僧侣之总管,地位甚隆,柳公权书此,当十分卖力,此类拓本都是为当时敦煌书写者提供的经典范本。
石室墨迹以当时楷书经典作为成就的起点,一方面以准确抄写为功能,另一方面却能自由地舒展个性,遂在后世成为“意临”的范本。在同代人看来,某一种风格笔迹越纯熟、越独特越好。因为这意味着书写者有良好的修养,有正确的学习范本,也有大量的时间练习书法。敦煌石室墨迹中大量的楷书写经,其作者虽然大多数没有留下名字,但都是经过敦煌寺院中的专门学习前代或当时名家“范本”后而书写,这些楷书写经墨迹被发现后,也成为今天人们临摹经典名家范本以外的另一种选择。在传统经典中,更多体现的是书法技巧、约定俗成的书写规范,个人的发挥空间很小,但对于石室里的楷书墨迹来说,最初的目的并不是作为书法范本供后人临摹的,这些写经本来只是面向佛祖一人的“专属信件”,所以抄写时的虔诚与经文的准确性在前,其次才会尽可能地把字写得精美。今天来看,从中不仅能感受墨迹的沉静,而且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审视它们,还会获取许多书写技巧和笔迹情趣,就像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弹奏的乐谱一样,艺术家们会通过对这些石室楷书进行创造性的再解读,来展现自己掌握多种风格和个人才能的能力,从开始的“专属信件”转变为一种公共书法艺术形式。清末沈曾植从小受训于馆阁体,但石室墨迹发现不久,他以敏锐的学人眼光去关注研究石室的唐人写经,缪荃孙日记记“子培乞唐经乙片去”。沈曾植为一代硕学通儒,学高位重,但在求唐人写经时却屈身用一“乞”字,可见求知若渴,《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中,所作唐人写经跋有四篇,对唐人写经的制式、用纸都有描述,其关注从笔法、结构,更深入到了制式、材料(图4),沈曾植晚年小楷风格大变,具有在传统的钟王风格中,添加了浓厚的石室写经痕迹(图5)。
敦煌虽地处边陲,但在昔日的敦煌,这里却是一个国际大都市。汉人应劭在解释“敦煌”二字意义的时候就说:“敦,大也,煌,盛也。”敦煌的名字意味着曾经这里的繁荣。繁忙的丝绸之路和各地域的文化都涌现这里,大量的文书、经典、抄经墨迹都在石室中得以保存,虽消沉千载,但今日大放异彩。石室墨迹中以写经为主,写经又多以楷书完成,其中所存,能够完整勾勒出古代书法中楷书的演进。
二、 以偏概全——敦煌石室楷书墨迹的演进
敦煌石室墨迹从书体来分,囊括了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而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楷书,楷书在石室墨迹中比例巨大,所存楷书墨迹可以看到书法史中完整的楷书演进过程。
在石室墨迹中有一卷年款为曹魏高贵乡公甘露元年(256)的《譬喻经》(图6)既存在东汉隶书碑版的用笔痕迹,又有着明显的钟繇小楷的风格特点。中“信”“而”等字,变隶书起笔逆锋“蚕头”为露锋,顺势铺毫,收笔并不像楷书往下压,而是还保留着隶书中的“燕尾”,朝右上挑出,做横势,有飘举飞扬之状,不过没有隶书那么凌厉。“投”“复”等撇画重起细收,与下一笔,笔断意连,十分遒媚,捺画收笔粗重,一般不做出锋之势,而竖画上粗下细,尾部做悬针。这种从隶书自觉演化而成的早期楷书,并不是有意而为,其风格笔势雄浑的楷书,是“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的自觉。这种自觉又来自:凉州是北部文化的中心,而敦煌又是凉州文化的中心,儒学兴盛,建立庞大而精美的建筑群,汇集了大量艺术家,还有能工巧匠的不断推动,这些因素是这种自觉的催化剂,也是逐步摆脱实用的意义,开始走向纯美的书法艺术境界。结体上左细右粗,左轻右重,左收右放。横势突出,这种曹魏间由隶到楷的自觉转变一直到北魏统一中原以后,又有了新的变化。
太平真君三年(442),西凉李暠的孙子李宝奉表归于魏,北魏任命李宝的弟弟李怀达为敦煌太守,445年,征李宝入朝,完全控制敦煌。作为“刀剑不离身”的北魏民族,他们对刀有着特殊的感情,而在艺术上,峻利爽朗,雄奇英迈的效果有着特殊的悟性。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雕琢,人们被刀锥冲击的表现能力所震撼,龙门石窟古阳洞内有着诸多造像题记,《牛橛造像》《始平公造像》等与以前的碑版有着明显的不同,无一例外地强调刀刻的意味。在王族的欣赏和赞美中,毛笔也逐渐追求刀刻的味道,但是时过境迁,这个时期的墨迹几乎绝迹,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这种如刀刻斧劈的造像是由于刻工为了完成工作、提高效率而改变了原来书写的模样。敦煌石室所保存的这个时期的墨迹,还原了北魏时期的书写样式。斯996号为《杂阿毗昙心经卷六》卷末所题“大代太和三年,岁次己未十月己巳二十八日丙申,于洛州所书写成讫”就是当年从洛阳流入敦煌的作品,斯2660号《胜鬘义记》横画的起笔除了露锋之外,兼用侧锋,而且主要的长画大多侧锋起笔,斩截利索,锋芒外耀,精光内敛。收笔也开始向下按顿之后往回收势,显得凝重含蓄。斯5304号墨迹(图7),其风格和龙门石窟的《牛橛造像》极为相似,如出一辙。在500—540年,敦煌楷书尤重刀味,意在笔先,实用性减弱,东西关照的王族的审美价值成为书法艺术所追求的对象,同时这种西凉的刀刻意味改变了我们以往的想象。
南北朝初期,无论在碑版还是墨迹,字体的楷化进程都是南方先于北方,以后南方书风逐渐影响到北方。公元554年,西魏攻陷江陵,梁朝灭亡,书法家王褒成为俘虏,想不到他因为写得一手王羲之风格的书法而震惊北方书坛。斯1318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564年)、《大般涅槃经》(573年)等作品代表了这种发展趋势,从豪健泼辣、雄奇角出的书风,渐渐向洗练遒美靠拢,劲悍的刀刻意味中加上了笔墨的秀润清丽。石室中隋代的墨迹点画上,起笔作顿,行笔轻快,收笔重按,起、行、收三个步骤十分明显,已完全是楷书样式。结体上,横画的右端比魏碑时期明显降低,复归平正。但不是隶书的水平,右端仍旧比左端高,与撇细捺粗的点画形式相协调,追求布白的匀称。所谓的横平竖直,已不是简单的水平与垂直,而是经过艺术处理。有唐三百年,八法具备的标准唐楷墨迹随着佛教兴盛而空前繁荣,莫高窟232个唐代洞窟,规模宏大,色彩绚丽,书法随着这种氛围,承接隋代,马上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形式丰富,精美绝伦。大量的长安书家与敦煌本地互动频繁:伯4510号欧阳询《化度寺碑》和伯4503《柳公权书金刚经》楷书卷都是敦煌寺院写经的范本;写本S575(图8)与后来的颜真卿《多宝塔》风格如出一辙,可见当时敦煌长安互为影响。伯2602号《无上秘要卷第十儿》写于开元六年严谨匀称,S2056号龙朔二年(622)《阿毗昙毗婆抄卷五十二》(图9)为盛唐写经,尽管墨迹风格不同,但都是标准的唐楷范式,点画圆浑,起承转折分明,结体略长,分间布白极其匀称,技巧形式完美无缺,同其他艺术形式一起在隋唐达到了登峰造极。
晚唐五代是文化的低谷期,宦官专权,藩镇拥众,割据一方,党政激烈,国事日衰。敦煌也并不太平,张议潮带兵赶走吐蕃节度使,收复瓜、沙二州,随之到来是二百年的归义军时代。社会的动乱使人们丧失了初唐时期的创作环境和创作心态,字迹也明显潦草。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晚唐禅意识的渗透,推倒偶像,主张新变和了悟,在书法上书写者继承了隋、初唐建立的起笔作顿、行笔轻快、收笔重按的楷书用笔方式,但打破了八法绝对严谨,审美趣味上,无不追求个性自我开张和风格变化奇诡。石室墨迹中斯705号《开蒙要训》和伯3109号太平兴国八年(983)的《诸杂难字一本》(图10)体现了书写个性的张扬,摆脱初唐法度严谨的束缚,回归六朝时代那种洒脱、自适的书写状态。《诸杂难字》墨迹并没有遵循初唐楷书大小一致的书写秩序,而是在正文周围随意写画,书写二十几个“大”字的过程中,会发现书写者每写一个“大”字都在打破上一个的程式,捺画重按之后的出锋方向不断在调整,尽量找到最“自适”的状态,即落款“太平兴国”中“太”字的风格。社会环境的改变,书写者的心态和风格也随之变化,这时期是沿革初唐楷法基础上的一种蜕变。正如晚唐僧人亚栖在其所传《论书》所说:“凡书通即变。王变白云体,欧变右军体,柳变欧阳体,永禅师、褚遂良、颜真卿、李邕、虞世南等,并得书中法,后皆自变其体,以传后世,俱得垂名,若执法不变,纵能入石三分,亦被号为书奴,终非自立之体,是书家之大要。”正是说明晚唐五代中的蜕变。
三、 人生百态——法度背后的温度
敦煌石室楷书墨迹跨越了七百年的时间,丰富多彩。与碑刻相比,墨迹有着碑刻无法比拟的真实,也让我们看到了楷书写经中的精心构思、纸张精致、字迹绝美,行与行之间有悦目的乌丝栏,干净爽目,虽字字规整,却极富变化。我们已经看不到唐代褚遂良的真迹,但石室中却保存着唐人临摹褚遂良楷书《圣教序》(图11),或许这是对褚体楷书理解最准确的参照。《宣和书谱》载:经生高手创作时“修整自持”,“数千字终始如一律,不失行次”,我们看到精美的敦煌写经背后,有的是当时官方行为,指派一些楷书高手,抄写经文,也有无数经生从小努力付出的结果。
宋陈元靓《事林广记》讲:“写字时,‘上’‘大’二字,一日不得过两字。两字端正,方可换字。若贪字多,笔划老草,写的不好。写的好时,便放归。午后亦上学。”初读这一段,并没有什么稀奇,不过是讲小孩习字的一些要求,P4900号(图12),一目了然,文字的记载与图像完全契合。知道古代初学文字、楷书,先以“上”“大”开始,墨迹中明显可以看出,距离朱笔范字越近,写得越认真,越先写的越认真,相反往后居然把“三”字落掉,直接写“千”,老师检查的时候,再一次纠正、示范“千”“夫”写法时,似乎提醒学生忘记写“三”,所以又匆忙补写了几个“三”,这种儿童顽皮的心理变化不亚于名家“下笔如有神”的伟大。学生的顽皮与老师的严肃,支撑着卷卷精美、庄严楷书写经是其背后带着温度的墨迹!
石室楷书关于《千字文》的墨迹不下四十余种,不仅有唐代无名高手蒋文进临本(图13),同时也有学子、经生习字。P2647号《千字文习字》(图14),就可以让我们看到唐代人是如何认字和学习楷书书法,先由老师写字头范字,但不辅导,由学生去依样画瓢,同一个字要写许多遍;同时也有老师监督临摹,直到老师满意,最后签署姓名;也有照着经生们抄好的经文,边抄边学,种种墨迹,真是见字如面。清代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一讲:“先儒教小儿习字,先令影写赵子昂‘大字千字文’。稍长,习智永‘千字文’,每板影写十纸。既毕后,歇读书二月。以全日之力,通影写一千五百字,添至二千三千四千字,如此一二月乃止。必如此写,方能日后写多,运笔如飞,不至走样,亦是一法。”如果没有石室的这些临摹《千字文》的墨迹,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传统开始于什么时候。现在我们至少知道从唐代开始,这种模式已经开始了,一直到清代还延续。从前多数人会越俎代庖地把自己的想象当成了作品本身,而一代一代地想象下去。敦煌石室大量楷书墨迹,也改变了以往只凭想象、凭借摹本、拓本的状态,在看精美的楷书写经同时,通过其笔势和结构表现出不同的精神,也使我们很亲切地看到古人一部分生活、学习风貌。
陶秋英在《敦煌经卷题名录》曾统计各阶层共计203人。根据题记分析,抄写者除了服务于当时皇家以外,主要有三类。一是僧人,他们只抄佛经,《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题记云:“比丘惠真于甘州修多寺写。”二是学士,或称学仕(使)郎,他们所抄的大多是经典书籍,斯5441《提季布词》题记:“太平兴国三年,学仕郎阴奴儿自手写季布一卷。”三是经生,或者叫作“写生”“书手”,他们以抄书谋生,只要能换钱和粮食,什么书都抄,斯6727《大方等陀罗尼经》末题:“延昌三年……敦煌镇经生张阿胜所写。”石室墨迹《乾德四年重修北大像记》云: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在重修北大像时,因天气炎热,与夫人到莫高窟持斋避暑,“系念于千尊”,便“龛龛而每燃银灯,光明彻于空界;窟窟而常焚宝馥,香气遍于天衢”。兼请僧俗,选简二十四人,抄写《大佛名经》文。他所请来的二十四位,都是经过“选简”的当地名家。在龛龛银灯,窟窟香气,乐音与法音同奏环境中抄写经文,排场震撼。斯692号《秦妇吟》是张盛友所抄,字不好,卷末题有一小诗:“今日写书了,合有五升麦,高代(贷)不可得,还是自身灾。”因要还高利贷,抄书虽苦,但总能有些收入还债,小诗虽短,却充满了辛酸。同样是抄经,有的拿着高昂的报酬在华灯宝馥下从容书写着华丽经卷,也有为了还债而不得已去抄经谋稻粱,最后的经卷面目自然千差万别。时至今日,墨迹背后的自得与自嘲都记录了古人书写的轨迹和温度!
历史的中原,无数名家作品、先贤墨迹,历经千难,存之不过一二,而敦煌石室墨迹无论从年代,还是数量、品类来看,都是中国书法史中“即多且全”的宝库。它为穷途末路的传统“帖学”和清中期以后“碑学”书法以外开辟了新的境界,为今天书法实践提供了更多的表现形式,也为中古书法史研究弥补了史不足征的缺憾。在中国书法经典楷书墨迹流传中,小楷之祖钟繇的《荐季直表》墨迹,今日只有照片得以流传,唐代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颜真卿等名家的楷书墨迹,更是凤毛麟角,只有徐浩《朱巨川告身》、颜真卿《竹山堂连句》等几件楷书作品递传今日。过去了解书法史楷书发展,多半靠石刻拓本和书法文献只言片语的记录,往往都是书家的个人体验来代替本来作品的真实呈现。米芾《海岳名言》讲:“石刻不可学,但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己书也,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因为墨迹流传少,且极难保存,尤其名家手泽,往往只能在王公贵族及少数收藏家手中流传,大多数人只能通过刻帖来揣测所临作品的本来面目。南宋陈槱在《负暄野录》也讲:“学书须是收昔人真迹佳妙者,可以详视其先后笔势轻重往复之法,若只看碑本,则惟得字画,全不见其笔法神气,终难精进。”他们所遗憾的不能直面古人墨迹,而是通过种种以讹传讹的方式接收到间接的古人墨迹形式。今天从石室里排列出古代的楷书墨迹,这种活生生的墨迹要比过去漫无边际、随心所欲的想象来得准确。通过排列,石室墨迹中楷书部分从自觉到东西关照,又走向了成熟鼎盛,最后沿革蜕变,完整地呈现楷书字体、风格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