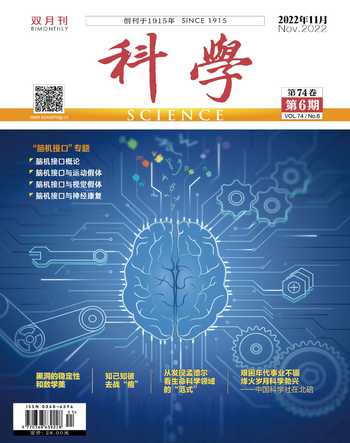知己知彼去战“痘”
高颖 王铭宇 梁小珍

猴痘是非洲部分地区的流行病,但自2022年5月初以来,猴痘传播到许多以前并无猴痘病例的国家,如欧洲和美洲的大部分区域,且大多数病例出现于以前未接种过天花疫苗的年轻男—男性行为者中。如果猴痘病毒成为广泛传播的人类病原体,则对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将会进一步增加,尤其是增加对儿童和免疫缺陷症患者等脆弱群体的潜在风险。
1958年,丹麦哥本哈根一批从新加坡进口用于脊髓灰质炎疫苗研究的食蟹猴(即长尾猴,M. fascicularis)暴发了非致命性痘样疾病,引起非人灵长类动物出现水痘样皮肤病变,故名“猴痘”。根据猴的发病症状和分离出的病毒特征分析,确定病原体为天花一类的正痘病毒,命名它为猴痘病毒(monkeypox virus, MPXV)。随后在美国、荷兰、西非和中非等地相继报道了感染猴痘病毒的动物病例。1970年,刚果共和国一名9岁的从未接种天花疫苗的儿童成为首例感染猴痘病毒的病例。此后,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尼日利亚、科特迪瓦等西非和中非国家也间断性报告了猴痘病毒感染人的病例,且越来越多。1986年,刚果流行地区首次报道猴痘病毒人传人的病例,但即使这样,由于当时传播率和致病率都较低,没有引起人们重视,因其不构成公共健康问题而一直被忽视。直到2003年在美国发生了第一次猴痘疫情,当时美国6个州都报道了因接触已感染的宠物草原犬鼠而感染人的病例。流行病学调查发现,这些感染者接触的宠物曾经与从加纳进口到美国的几种啮齿类动物关在一起,而其中一些进口动物携带了猴痘病毒。2018年9月到2019年1月,尼日利亚26个省暴发了猴痘疫情,共有311人感染,7人死亡。2018年,英国和以色列都报道了尼日利亚的输入病例。值得关注的是,当时英国还报道了一个护理人员在负责输入性感染病人过程中被感染,再次提供了猴痘病毒人传人的证据。英国和新加坡在2019年、美国和英国在2021年,都相继报道了尼日利亚输入的猴痘病例。自2022年5月以来,在欧美等若干猴痘非流行国家,已发现多例猴痘病例和聚集性病例,而且在非洲几个流行国家也不断有猴痘病例的报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至今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报告7万多病例,其中有26例死亡病例。猴痘疫情已成为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
猴痘是由猴痘病毒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主要发生在中非和西非的热带雨林地区及其周边,后来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城市中。猴痘病毒的动物宿主包括一系列啮齿动物和非人类灵长类,如睡鼠、树松鼠、长尾猴、短尾猴等。虽然猴痘病毒最早在猴身上被发现和命名,但其他动物也易于被感染,虽然目前认为其天然宿主是啮齿动物,但仍需进一步研究和确认。
人类主要通过接触受感染动物的损伤皮肤、血液或体液、被受感染动物咬伤或抓伤而受到感染。人与人的传播则通过密切接触感染者的呼吸道分泌物,也可经胎盘从母亲传给胎儿。2022年暴发的猴痘疫情主要发生在男性同性恋者中,且在精液中也检测到猴痘病毒,说明猴痘病毒存在通过性传播的可能性。
猴痘病毒是一种双链DNA病毒,呈长方形或椭圆形,与天花病毒、牛痘病毒和痘苗病毒同属痘病毒科正痘病毒属。它有2 种不同形式的感染性病毒颗粒:胞内成熟病毒颗粒(intracellular mature virion,IMV)和胞外包膜病毒颗粒(extracellular enveloped virion,EEV)。
具有不同形式的感染性病毒颗粒是大多数正痘病毒的共同特点。成熟颗粒有一个包含病毒DNA的核心,外围是侧体,侧体外还有一层内膜和表面小管。成熟颗粒最外面包上一层含有8种特异性病毒蛋白的包膜就成为带包膜的病毒颗粒。

猴痘病毒的基因组约为20万个碱基对,有190多个编码蛋白质的开放阅读框。病毒基因组包括中央保守区域、左右两边的末端区域和左右两端完全相同的反向末端重复序列。中央保守区域与其他痘病毒基因组同源性高,主要编码参与病毒复制、转录和包装的蛋白质;末端区域的异质性较高,主要编码参与宿主嗜性、病毒毒力和宿主免疫反应等病毒致病机制相关基因。反向末端重复序列包含4个功能未知的基因和一个富含腺嘌呤和胸腺嘧啶、碱基不完全配对的发夹环,后者将两条DNA链进行共价连接。除了与其他痘病毒同源、功能已知的保守基因之外,大多数基因的功能尚不清楚。通过病毒基因序列比较分析,猴痘病毒分为两个不同的遗传进化分支,即中非(刚果盆地)分支和西非分支,前者更具传染性,感染后将引起更严重的症状,病死率约10%;后者感染性相對弱一些,病死率约3.6%。
大多数DNA病毒都不编码依赖于DNA的RNA聚合酶,它们必须进入细胞核利用宿主细胞的依赖于DNA的RNA聚合酶来复制与转录病毒DNA基因组。然而,猴痘病毒所属的痘病毒科是唯一的例外,它能自己编码依赖于DNA的RNA聚合酶,这样它进入细胞后无需进入细胞核,在细胞质中就能完成病毒DNA基因组的复制与转录,从而完成生活周期。

猴痘病毒整个生活周期如何被调节,目前研究甚少。有报道高尔基相关蛋白复合体对于IMV外面包裹双层膜形成带包膜的病毒颗粒是必需的;酪氨酸蛋白激酶参与了猴痘病毒IMV释放形成EEV的过程。至于两种不同形式的病毒颗粒EEV和IMV如何感染进入细胞内,哪些病毒蛋白和细胞受体参与,目前只是通过蛋白组学以及猴痘病毒与痘苗病毒之间的同源性蛋白进行比较分析。推测猴痘病毒在吸附到细胞表面过程中,病毒蛋白A28、H3、A29和E8参与其中:A28结合细胞表面的层黏连蛋白,能与A29相互作用,A29和H3结合细胞表面的氨基多糖和肝素,而E8则与硫酸软骨素相结合。通过对痘苗病毒参与入侵细胞的进入融合复合体(entry fusion complex, EFC)的蛋白组学分析, 推测猴痘病毒与痘苗病毒的EFC中的A16、 A21、A28、F9、G3、G9、H2、I2、J5、L1、L5、O3等十几个同源蛋白,参与了猴痘病毒进入细胞的过程[1,2],但每个蛋白的具体功能还不清楚。

虽然发现猴痘病毒已有几十年了,但是猴痘病毒感染人后诱导的免疫反应还没有被广泛研究。猴痘病毒与宿主免疫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基于痘苗病毒和其他正痘病毒的研究,以及猴痘病毒在少量动物模型中的研究进行推测。先天免疫反应是抵御病毒感染的第一道防线,在病毒感染诱导的免疫反应中起关键作用。在猴痘病毒感染人的过程中,单核细胞或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自然杀伤性(NK)细胞、树突状细胞等先天免疫细胞的作用尚不清楚。体内和体外的感染模型研究表明,单核细胞是痘病毒感染的初始靶细胞,单核细胞和人M2样巨噬细胞在痘苗病毒的感染与扩散中非常重要。与此相一致,在被猴痘病毒感染后,在有肺炎症状的食蟹猴中也观察到单核细胞被招募到感染位点,说明单核细胞在猴痘病毒感染致病过程中有潜在作用。在感染猴痘病毒的恒河猴的外周血和淋巴结中观察到NK细胞显著性扩增,但是NK细胞的迁移能力和活性却被严重抑制;更重要的是,发现NK细胞数量的差异是经典实验室杂交小鼠不易感而CAST/EiJ小鼠对猴痘病毒易感的重要原因之一[3,4],这提示了NK细胞在猴痘病毒感染过程中的重要性。此外,有研究表明血液中较低的中性粒细胞也与动物感染猴痘病毒后的死亡率有相关性。这些都表明先天免疫细胞在猴痘病毒感染与致病过程中有重要作用。
除了先天免疫细胞,在感染猴痘病毒的食蟹猴和人中,都引起了系统性的细胞因子反应,IL-2、IL-6、IL-8、CCL5等细胞因子显著提高。比较严重与轻微症状的患者发现,IL-2R、 IL-10、GM-CSF和CCL5在严重的患者中明显升高,而IL-6则降低[5],提示辅助性T细胞2的免疫反应可能与猴痘病毒感染引起的疾病严重性存在一定联系。
猴痘病毒感染引起的抗体反应目前只局限于少量的临床分析。分析美国2003年暴发的猴痘疫情,发现猴痘病毒感染后,在皮疹出现的一周内,不论以前是否接种过天花疫苗,都能检测到IgM和IgG,总IgG反应在接种和未接种疫苗的人群中没有明显差别,皮疹出现100多天后还能检测到IgG。虽然IgM在未免疫的个体中反应更快,而且持续时间更长 (126天:77 天),但是反应趋势在未接种和接种过天花疫苗的人群中一样,都有一个明显的急性反应期,皮疹出现第2周IgM水平明显升高随后降低[6]。此外,相较于轻症患者,中度和严重的患者有更高的IgM反应和更低的IgG反应。对2007—2011年刚果共和国猴痘病毒感染者群体分析发现,相对于只有IgG反应的个体,同时有IgG和IgM反应的感染者有更严重的症状。这些预示猴痘病毒感染后,IgM反应可能与症状的严重程度相关。由于分析的人群数目有限,需要对更多感染人群进行分析验证。
目前缺乏关于猴痘病毒感染后诱导的T细胞免疫反应或T细胞在猴痘病毒感染致病中的作用的研究。一个HIV-1感染的患者在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后,CD4+ T细胞恢复到正常数目,虽然感染了猴痘病毒,但没有引起严重的疾病,预示CD4+ T细胞可能减轻了猴痘症状的严重程度[7]。在感染猴免疫缺陷病毒(SIV)的恒河猴中,CD4+ T细胞的数目很低(细胞数少于300/毫升),接种天花疫苗后不能产生病毒特异性的IgG,再感染猴痘病毒后导致死亡,说明CD4+ T细胞在天花疫苗免疫恒河猴后诱导保护性抗体的产生,在抵抗猴痘病毒的致死性感染中起关键作用[8]。
正痘病毒有很多基因参与病毒识别、细胞凋亡和免疫调节等免疫逃逸功能。除了编码与其他痘病毒功能同源的免疫逃逸蛋白参与调节各种信号通路之外,猴痘病毒还有其特异的免疫逃逸机制。区别于痘苗病毒,猴痘病毒在体外感染巨噬细胞、成纤维细胞、海拉细胞等各种人类细胞时,会选择性抑制激活先天免疫反应信号通路中有重要作用的宿主基因,如干扰素诱导基因的表达。而且能在I型干扰素IFN-α存在的条件下进行正常的复制。后续研究发现,猴痘病毒编码的I型干扰素结合蛋白(IFNα/βBP)能结合到宿主细胞膜上抑制I型干扰素信号通路。此外,猴痘病毒感染恒河猴后虽然能诱导NK细胞的扩增,但是明显抑制NK细胞的杀伤功能[9]。不同于痘苗病毒和牛痘病毒,猴痘病毒还能通过抑制T细胞的激活,逃逸抗病毒CD4+ T 和CD8+ T細胞的免疫识别和反应[10],可能以此用于促进病毒在感染宿主体内的扩散。随后发现猴痘病毒编码的197和D14L蛋白在抑制T细胞功能上发挥重要作用。这些研究说明猴痘病毒已经演化出多种特异的逃逸宿主先天免疫和适应性免疫的机制。
猴痘病毒从感染到出现症状的潜伏期是5~21天,感染者的临床症状类似感染天花病毒,初期有发热、头痛、肌痛等症状,发烧后会出现皮疹,主要集中在面部和四肢,也会影响口腔黏膜、生殖器结膜和角膜等处。区别于天花病毒,猴痘病毒感染表现出的最显著特征是淋巴结肿大,并诱导出更有效的免疫识别和免疫反应。
猴痘是一种自限性疾病(即无需治疗,患者会自愈),症状维持2~4周。严重病例多见于儿童和免疫缺陷的个体。猴痘并发症与后遗症包括呼吸道与胃肠道疾病、脑炎、败血症和视力丧失。与接种过天花疫苗的人群相比,未接种疫苗的个体症状更严重,并发症也相对更普遍。
虽然目前还没有猴痘病毒疫苗,但通过若干观察性研究表明,天花疫苗有很好的交叉保护效果,对预防猴痘病毒感染的有效率达85%,还能减轻猴痘症状。目前上市用于预防猴痘病毒感染的疫苗有三种:两种是美国FDA批准上市的ACAM2000和IMVAMUNE(US)/IMVANEX (Europe),前者不良反应大、在免疫缺陷人群中会引起严重疾病甚至死亡,后者不良反应相对较小、反应快且有较长的保护持久性。第三种是日本批准上市的LC16m8 ,不良反应较小。
抗病毒药研制方面,根据动物模型研究的数据,两种为预防天花研发的抗病毒药被美国FDA授予许可用于猴痘。其中Brincidofovir通过抑制病毒DNA基因组复制,起到抗病毒作用,对其他大部分双链DNA病毒也有一定效果;而Tecovirimat则是正痘病毒保守的、胞外病毒颗粒EEV形成所需的膜蛋白p37的靶向抑制剂。p37蛋白在痘苗病毒中由F13L基因编码,而在猴痘病毒中则由C19L基因编码。Tecovirimat 不会抑制和影响正痘病毒DNA基因组的复制、病毒蛋白的合成以及成熟病毒颗粒IMV的形成,只会抑制胞外病毒颗粒EEV形成和释放,从而抑制病毒在宿主体内的扩散达到抗病毒目的。2022年猴痘疫情的临床数据显示,Brincidofovir不但有严重的毒性,而且在猴痘患者中没有观察到任何有益的治疗效果。相比而言,Tecovirimat安全性更好,无明显不良反应,能降低病毒载量、加速患者康复。
经过全球疫苗接种和防控措施,天花于1980年在全球范围被宣布消灭。天花能通过接种疫苗被根除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除了人类之外,没有发现天花能感染其他动物。然而,与天花不同的是,猴痘病毒能感染各种动物,所以,很难像天花那样,经过全球接种疫苗来根除猴痘病毒。即使现有天花疫苗在猴痘病毒感染上有比较好的交叉保护作用,也还是需要对动物贸易开展猴痘病毒检测,降低人畜传播和人际传播的风险。并且加强猴痘病毒感染与致病机制的研究,优化现有疫苗,为风险人群提供更好的防疫保护措施。
[1]Senkevich T G, Ojeda S, TownsleyA, et al. Poxvirus multiprotein entry-fusion complex. Proc Natl Acad Sci, 2005, 102: 18572-18577.
[2]Manes N P, Estep R D, Mottaz H M, et al. Comparative proteomics of human monkeypox and vaccinia intracellular mature and extracellular enveloped virions. J Proteome Res, 2008, 7: 960-968.
[3]Earl P L, Americo J L, Moss B. Natural killer cells expanded in vivo or ex vivo with IL-15 overcomes the inherent susceptibility of CAST mice to lethal infection with orthopoxviruses. PLoS Pathog, 2020, 16: e1008505.
[4]Earl P L, Americo J L, Moss B. Insufficient Innate Immunity Contributes to the Susceptibility of the Castaneous Mouse to Orthopoxvirus Infection. J Virol, 2017, 91.
[5]Johnston S C, Johnson J C, Stonier S W, et al. Cytokine modulation correlates with severity of monkeypox disease in humans. J Clin Virol, 2015, 63: 42-45.
[6]Karem K L, Reynolds M, Braden Z, et al. Characterization of acutephase humoral immunity to monkeypox: use of immunoglobulin M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for detection of monkeypox infection during the 2003 North American outbreak. Clin Diagn Lab Immunol, 2005, 12: 867-872.
[7]Hammerschlag Y, MacLeod G, Papadaki G, et al. Monkeypox infection presenting as genital rash, Australia, May 2022. Euro Surveill, 2022, 27.
[8]Edghill-Smith Y, Golding H, Manischewitz J, et al. Smallpox vaccine-induced antibodies are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for protection against monkeypox virus. Nat Med, 2005, 11: 740-747.
[9]Song H, Josleyn N, Janosko K, et al. Monkeypox virus infection of rhesus macaques induces massive expansion of natural killer cells but suppresses natural killer cell functions. PLoS One,2013, 8: e77804.
[10]Hammarlund E, Dasgupta A, Pinilla C, et al. Monkeypox virus evades antiviral CD4+ and CD8+ T cell responses by suppressing cognate T cell activation. Proc Natl Acad Sci, 2008, 105: 14567-14572.
關键词:猴痘病毒 生活周期 免疫反应与逃逸 疫苗与抗病毒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