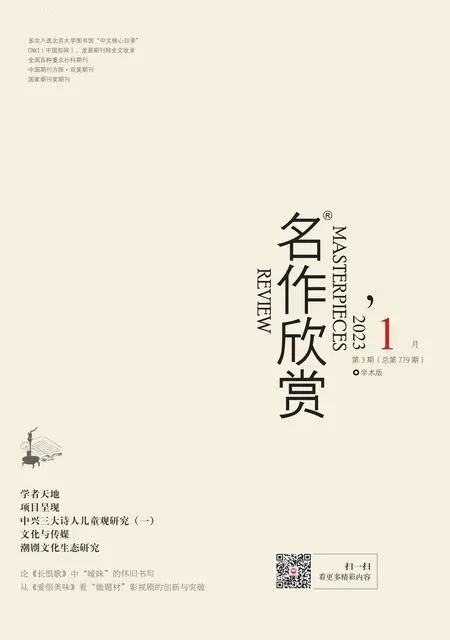古代戏曲“别梦”关目探微
——以《西厢记》《长生殿》为例
⊙孙雨欣[江苏师范大学,江苏 徐州 221100]
“别梦”指的是文学艺术中男女主人公经历生离或死别之后因相思而产生的梦境。“别梦”在前代诗词作品中便是常见的意象,较为经典的有汉末古诗《凛凛岁云暮》“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唐代张泌《寄人》“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廊回合曲阑斜”,宋人晏几道词作中“梦入江南烟水路,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等。这些诗词中的“别梦”意象凝聚了缱绻绵长、刻骨铭心的别后相思,情感真挚动人,意境朦胧柔美。古代戏曲对前代文学艺术中的“别梦”意象进行了继承与发展,形成内容更为丰富、意蕴更为深广、表现力更强的“别梦”关目,较为经典的有王实甫《西厢记》中的《草桥店梦崔莺莺》第五折“草桥惊梦”,张生离别后思念崔莺莺因而梦到她千里奔赴;洪昇《长生殿》中《雨梦》一出,唐明皇在马嵬坡事变后梦到杨贵妃未死,最终却又寻而不得;汤显祖《紫钗记》中《荣归燕喜》一出,“昨梦儿夫洛阳中式,奴家梳妆赴任,好喜也”。戏曲中的“别梦”关目凝聚了创作者奇幻瑰丽的想象,展现出独特的艺术效果,因而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与学术研究价值。现有研究成果对“涉梦戏”固定情节的模式关注不够,主要从宏观视角出发研究“涉梦戏”的分类、作用及审美意蕴。如李媛《明杂剧“涉梦戏”研究》以明杂剧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涉梦戏”的成因、分类、作用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庄清华《论古典戏曲中的梦境描写》将梦境分为灵验梦与虚幻梦,并探讨了梦与戏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借助具体作品,以《西厢记》《长生殿》为例,对“别梦”关目进行研究,力图探究其主要特征和审美内涵。
一、关目设计:现实基点与流动意识
中国古代戏曲中梦境频频出现,如《牡丹亭》“惊梦”杜丽娘梦遇柳梦梅、《长生殿》“闻乐”中玉环梦入月宫等,这些梦境往往会出现神仙鬼魂这些超自然因素,虚幻灵异,现实感较弱。“别梦”关目的独特之处在于将现实与虚幻熔于一炉,以现实为基点,又通过意识流动完成梦境构筑。
“别梦”关目呈现出因思成梦、悲景助梦、美梦成真、美梦破碎、惊惧而醒、悲景愁情的基本模式,符合现实逻辑,未出现鬼神等超自然因素。作者为“别梦”关目创设了凄清的环境,首先主人公因别后相思而成梦,入梦后因重聚或将要重聚而感到狂喜,接着梦中情形发生突转,主人公极度惊惧悲痛而醒来。以“草桥惊梦”为例,张生草桥店梦到崔莺莺不顾路途遥远独自跋涉前来相会,两人重聚欣喜若狂,但随后崔莺莺便因夜晚渡河被卒子抓走,“卒子抢旦下”,最后张生醒来,在凄清的夜景中徒增愁情。“别梦”关目的设计也十分贴合主人公心理的自然变化,其现实理据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分别后,主人公因迫切期盼重聚而暂时“美梦成真”,因别离后主人公心境的整体基调为悲伤愁苦,美梦在这种心境的感染下最终走向破碎与消亡,回归悲愁的情绪。
从现代视角去解读“别梦”,“别梦”的内容方面很好地表现了梦境意识的流动,使其鲜明地区别于现实中故事的逻辑,主要体现为梦境内容的冲突性和梦中意象的象征性。梦境内容的冲突性首先体现为与前文已经发生的故事产生矛盾,如《雨梦》中唐明皇听闻玉环未死,“只为当日个乱军中祸殃惨遭,悄地向人从里换妆隐逃”,与前文现实情况不相吻合。另外,其冲突性还表现在对规则世界、现实桎梏的突破,如唐明皇深夜微行、怒杀陈元礼等,这使得梦中叙事在潜在意义上与现实构成强烈冲突。同时,构筑梦境的意象呈现出一定的象征性。比如“草桥惊梦”中的卒子意象,在戏曲中他们象征着规则世界的约束者,将打破规则的崔莺莺重新拉入规则世界的束缚之中。再如《雨梦》一出中,唐明皇梦中场景突然从荒郊跳跃到曲江大水,“你看大水中间,又涌出一个怪物。猪首龙身,舞爪张牙,奔突而来。好怕人也”。对照剧情来看,梦中的“大水”“怪物”意象也有象征意味,大水惊涛涌动,与贵妃死后唐明皇内心的虚浮感相映照,怪物“跳上扑生,生惊奔”,则暗示着唐明皇面对现实桎梏的无力感。“别梦”关目的设计体现了古代戏曲对传统叙事的一些突破,强化了叙事的冲突性,并使得梦境内容呈现出一定的碎片化,同时利用意象符号来表达潜在的含义,使古典戏曲隐约闪烁着现代性的色彩。“别梦”关目由此在传统与创新之间达到了一个好的平衡,也为戏曲叙事的进一步突破搭设了桥梁。
二、意境之美:情与景的双重空间构筑
戏曲关目往往能在叙事的同时表情达意,“别梦”关目相比于其他关目更加侧重于抒情,似乎可以凝聚成一阙深情绵邈的抒情小令,其存在构筑了独特意境,深入表现人物的情感。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中说:“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①推之而及所有古代戏曲,意境尤为重要,戏剧关目有了意境便有了灵魂。“别梦”关目重在表情达意,关目模式又往往以景助梦,以景结梦,本身便具有融合情与境的天然优势;同时“别梦”关目设置了现实与梦境两层空间,将虚实两境缠绕融合,构筑出别具一格的意境之美。
《西厢记》“草桥惊梦”历来受到戏曲评论家的激赏,徐復祚《曲论》便将其抬到很高的位置:“且《西厢》之妙,正在于草桥一梦,似假疑真,乍离乍合,情尽而意无穷。”②“草桥惊梦”一折将草桥景色与张生离愁相互融合,意蕴悠长。情与景的一重空间即为现实空间,张生在入梦之前,“旅馆欹单枕,秋蛩鸣四野”,凄清景色与他孤独的羁旅愁思、相思愁苦水乳交融;梦醒之后,“只见一天露气,满地霜华,晓星初上,残月犹明”,依旧是悲景伴愁情。另一重空间为梦中情境,“暮雨催寒蛩,晓风吹残月,今宵酒醒何处也”是梦中莺莺孤身前来时的环境,是现实环境与张生凄冷心境相结合在梦中凝聚而成的虚幻意境。虚实两重意境相互交织,相互映衬。《长生殿》中,“雨梦”可以理解为雨夜的凄凉意境与唐明皇悲苦心境交融产生的梦。辗转难眠时是“萧萧飒飒,一齐暗把乱愁敲”的凄风苦雨;在梦中,雨声与心境融合,营造了“飒剌剌风摇树摇,啾唧唧四壁寒蛩”这般凄清萧瑟的意境;梦醒之后,仍旧是“梧桐上雨声厮闹,只隔着一个窗儿直滴到晓”。雨声在梦境和现实之间架起桥梁,烘托了梦里梦外唐明皇的愁苦心绪。
古代戏曲的“别梦”关目承接诗词中的“别梦”意象发展而来,扩大了意境的空间延展性与表现力,更加细致深入地勾勒出主人公的离别相思之苦。与戏曲中的其他梦境相比,“别梦”关目将梦前、梦中、梦醒三个情境交织串联,意境创设更为纯粹统一,同时把握住了情与景之间的内在联系,在真实自然的基础上使情与景达到高度交融。
三、叙事铺垫:平静中的蓄势待发
前文提到,“别梦”关目由全剧观之叙事性较弱,更侧重于抒情。以《西厢记》为例,其他经典关目如“佛殿相遇”“跳墙约会”“长亭送别”等都有较强的叙事意味,推动了故事展开。而在“别梦”关目中,情节发展节奏缓慢,整个故事的进度条几乎处于静止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关目在情节设计上毫无作用,相反它有着独特的结构价值。
“别梦”关目集中力量刻画人物内心,充分积蓄了人物情感,为之后的高潮情节提供了强大的情感推动力。黄天骥先生认为《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长亭送别”和第四折 “草桥惊梦”这两折戏“环绕着莺莺张生分手的情节核心,一以实写为主,一以虚写为主,真真假假,前后辉映”③,“草桥惊梦”虽然在故事情节上没有进一步发散延伸,却具有很强的抒情性,张生与莺莺之间的情感在经历种种试探、磨合、互证之后又因为离别而坠入低潮,两人的悲伤情感在“草桥惊梦”一折中积蓄到极致,从而为第五本中“金榜题名大团圆”大高潮的到来蓄势,使得全剧悲喜交错,波澜起伏。同样,《长生殿》“雨梦”也是唐明皇情绪的低谷,现实中不能与杨玉环相会,梦中又不能得见,唐明皇积蓄的悲伤之情在这一出通过“别梦”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而为之后另寻出路以及天上团圆的情节蓄势。
整体来看,“别梦”关目叙事性较弱,因而节奏平静舒缓,同时“别梦”关目情感偏向伤感,意境也较为凄清,整个关目呈现出冷色调,这与前后的情节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以《西厢记》“草桥惊梦”为例,“草桥夜梦”之前是“幽媾”“拷红”“送别”三折,张生与莺莺幽会是全剧的小高潮,“拷红”“送别”则是“幽媾”情节的余波,这三折情节紧凑,剧情发展快;“草桥夜梦”之后是第五本“张君瑞庆团圆”,叙事性强,故事节奏快,氛围较为热闹欢快。“别梦”关目在情节结构中起到调节缓冲的作用,从而使剧情节奏缓急交替,冷暖交织,带给受众更好的审美体验和接受效果。
在传统观念里,好的关目需要做到将种种矛盾冲突巧妙地容纳其中,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展现波折迭起的故事。而“别梦”关目似乎带给我们优秀戏曲关目的另一种范式,看似叙事性较弱,却以隐而不显的方式在全剧中起到过渡、铺垫、转折的作用,使戏曲情节环环相扣、缓急相宜,在完整性与流畅性方面达到较高的水平。这些结构上的作用或许也是“草桥惊梦”“雨梦”等关目成为经典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镜像呈现:从双重凝视到自我反省
封建社会女性往往处于失语状态,男性执笔创设理想中的女性形象。古典戏剧中的佳人往往才华横溢、情深义重,但女性形象的光辉出彩并不代表女性在戏剧世界有了话语权,更不代表当时女性地位真正与男性平等。清初小说《玉娇梨》中才子苏友白说:“有才无色,算不得佳人;有色无才,算不得佳人;即有才有色,而与我苏友白无一段脉脉相关之情,亦算不得我苏友白的佳人。”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佳人形象始终是男性的凝视物,被塑造成男性所期望的形象。
黄天骥先生在《〈西厢记〉创作论》中认为:“在‘惊梦’这场戏里出现的虚幻的‘莺莺’,乃是真实的莺莺性格的倒影。张生知道莺莺对他爱得深沉,爱得勇敢,主动地爱,坚持地爱。”④“草桥惊梦”确实体现了张生对莺莺爱的理解,在他心中莺莺足够勇敢和坚定,因此梦中莺莺可以跋山涉水前来相会。但换一个角度看,“别梦”关目中的莺莺作为现实莺莺的镜像,是莺莺性格的反映,同时也是从男性视角将现实莺莺进行美化与完善而得到的产物。《西厢记》在对莺莺这一佳人形象进行塑造时体现了男性的凝视,但这个佳人的塑造因为立足于现实生活,依旧受到封建社会伦理框架的束缚与桎梏,在某些方面仍旧不能符合当时男性的心理预期;而离别后的梦境恰恰能够打破规则世界,为塑造男性期盼的、对爱情更加主动更加勇敢的佳人形象提供了空间与条件,从而通过“别梦”关目完成了对女性的第二重凝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厢记》“别梦”关目与古典戏曲中的鬼魂戏有异曲同工之妙,却能够做到立足于现实,不牵涉超自然因素。现实中的女性居于深闺,极度不自由,古典戏剧中的女性被赋予一定的自由,只不过这部分自由仅仅是为了满足男性幻想而存在。
《长生殿》中的“别梦”是死别之后唐明皇的梦,其构造视角与《西厢记》不相同,它有意规避了梦中对杨贵妃的描写,转向了对男性内心世界的反映。《雨梦》一梦中唐明皇的镜像是对其现实形象进行还原复位后呈现的本我形象,梦中的他获得了依据自己想法行动的自由。在梦境中,唐明皇能够任凭自己的喜恶做出决断,可以不顾帝王身份“深夜微行”,可以不经理性权衡就赐死陈元礼,这些举动都是他自由意志的体现。而现实中,尊贵无比的皇帝宝座有时却像沉重的枷锁,使他身不由己。梦境充分展现了唐明皇自我理想与现实境遇之间的冲突,以及本我、自我、超我三者之间的不可协调性。这一梦体现了唐明皇对自我生活状态的进一步认识与对自我选择的再一次确认,使他充分认识到自我地位与自我情感追求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是男性将目光从“凝视”转向内省的一种体现,将目光投射于自我之上,深刻认识自我、反省自我。
由此可见,从《西厢记》到《长生殿》,我们可以看到“别梦”关目展现出的深层意识从“凝视”转向了自我反省。这种发展变化首先与戏剧情节设计有关,《长生殿》以唐代白居易《长恨歌》为蓝本,“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明确要求唐明皇不得在梦中与杨贵妃相聚。其次也与时代性的思想观念有一定的关联,明末思想解放与“至情说”的提出对“别梦”关目展现出内省精神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① 王国维撰、叶长海导读,《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页。
② 徐复祚:《曲论》,《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41—242页。
③④ 黄天骥:《〈西厢记〉创作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63—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