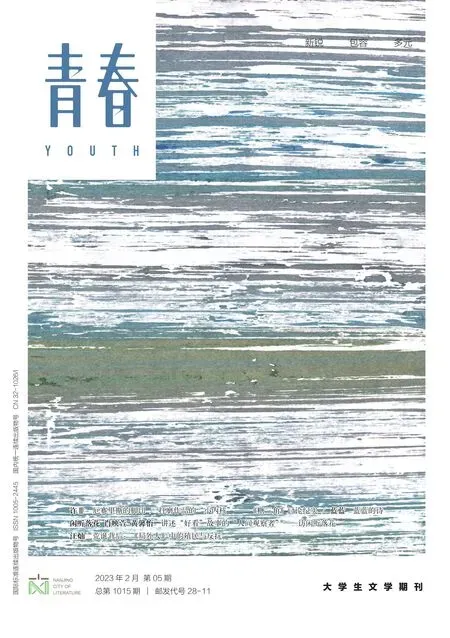觅食记
湘南学院 沈定坤
一
古语说得好,民以食为天。可不就是如此吗?细数起来,人生从婴儿时期的嗷嗷待哺,到踏入坟墓长眠的那一刻,其间都循环往复着一日三餐,但那可不是流水线般的机械僵硬,自有餐食的丰盈与饱满。但有时,讲得轻松潇洒,做起来却不是如此。只觉少数人,过度满足味蕾,徒然伺候于味蕾,只奔着吃食,那是一种劳累活,没了惬意、自在、闲适。
反之,看友人家的猫狗,优哉游哉地在阳光下打盹,不知比我闲适多少。它们不用忧心忡忡,时常在与主人的逗弄中,就把肚子填饱了,再回去睡个回笼觉,好不自在。但细想,人类与猫狗的异处,生而不仅为觅食,单单为获取填饱肚子本身,更在享受觅食过程中的见闻。
有些人,走不出这个简易版的莫比乌斯环,身心憔悴。感觉生命失去了弹性,很容易风干与脆折。这只能靠自己,走,一步步。脱困了,顿悟了;闭塞了,消弭了。只得闭一闭眼睛,静一静念头,平一平心跳,回归缘起的初心,再次邂逅理性。
觅食可以很单调也可以很精彩,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复杂,可以很享受也可以很痛苦。它有很多衍生,自然有不少选择。我们不否认,它是一个问题。但它却没有“生存还是死亡”这个命题的生硬、严肃、冷酷,而是温柔地在选择吃的立场上,给出了一定范围的选项。
怎么吃?——这便是觅食记的由来。
二
当过学生,就有在学生食堂觅食的体验,去食堂吃饭是学生时代无法磨灭的印记。毕竟,食堂之于学生,是又爱又恨。
去食堂的早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第四节课的老师,看他是否知味。到了第四节课的时候,早餐的那点餐食,早已淹没在胃酸里,萃取而出的微末能量,早已被大脑索取殆尽。若是你不理睬,肠胃能有什么坏心思,只是善意的“咕咕”声,悄悄提醒你,尽可能委婉地表达,它要“造反”的前兆,也是先礼后兵。
此时,你早已感觉到,有点饥肠辘辘了。这最后几分钟,就算老师讲得再精彩,将他所知的那些杂文轶事一股脑儿吐露,我们也“鄙视”得很。下课铃响起,知趣的老师戛然而止,调侃一句,散伙,小家伙们,吃饭去吧;不知趣的老师,则还会啰唆几分钟,说耽误一下,延迟几分钟,马上……实则遥遥无期,只得听着肚子强烈地抗议。
下了第四节课,大家以短跑的风范,奔向食堂。只因大家都明白——如果提前了几分钟,就不用大排长龙,感受人流的压迫。反之,就只好在“长蛇阵”后面缓缓挪动,僵硬的身形,像刚从冬眠中睡醒的蛇,慢慢悠悠、晃晃荡荡地扭动着它的身躯。
学生时代,在食堂的欢愉与失落,也很简单。前者,不过是邂逅了饺子、卤鸭腿和辣椒炒鸡;后者,则是与它们擦肩而过,失之交臂,特别是有一个向你炫耀的家伙,不禁咬牙切齿起来。在这种日子里,踏步声、欢呼声、碗碟敲击声夹杂其间,似门庭若市、欢呼雀跃、锣鼓齐鸣,有了些过节的意味,而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节日相随,只不过是在为调口味的庆祝罢了。
我也曾是那些无畏的冲锋者中的一员,但却时常受食堂嘈杂声响的集合体困扰。索性,在高三的长时间里,我秉着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想法,避开人流造成的魔音。只是避开了高峰,没有什么好菜,且菜都凉了。
三
食堂不止开在学校,其实有很多公司自带员工食堂,但我作为一个未毕业的大学生,自然也不可能与它们产生什么交集。不过我为照顾生病住院的祖母,曾在某地的公立医院处,吃过几次别样的堂食。
那里不同于学生食堂,来客多是老人,自然也不会有嘈杂的喧闹,只有食物的咀嚼声、吞咽声,偶尔还有戴假牙时,产生的金属与牙齿微末的碰撞声。那种声响,不似金属的击打,不怎么清脆,似敲打破洞漏风的鼓,小小的闷闷的一声。
为什么还如此安静呢?在于老人们。他们的动机很简单,来吃饭,就是为吃饭。场面不是聚会,不是狂欢,不是庆典,目的不为应酬,不为交际,自然也没有别的精力,随意耗费在其他上。
坐在那儿,静静地,端着勺,拿着筷,与餐盘碰撞,似风铃般清脆。在这一瞬间,他们周身散发着一种纯白的气,在食物间,诞生了单纯干净的联系。简单明了的动作,在此刻,变得神圣庄严。
他们大多衣着病号服,未穿的也简单朴实,他们的面容有的肃穆冷峻,有的寂然垂目,有的看不清神情。他们都默然咀嚼,因为上了年纪,咀嚼的动作也比较和缓,上下颚之间的碰撞,不像“司机餐厅”里的那些年轻人大开大合、囫囵吞枣。他们咀嚼,像蚕食桑叶,没有什么激动满足的夸张表情,也没有太大的声音,只有零星的碗筷击打声,微乎其微。
(3)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是职工安置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如德国由政府财政补贴煤矿职工养老金,这些财政措施对职工安置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一连去了大半个月,都是这种场面。有时我想,他们为医院的悲切又添上了一抹冷色调,挥之不去。当时,我的祖母愈加病重,到了依靠呼吸机维持的地步,自然也蒙上了一层阴霾,灰蒙蒙的,肆意笼罩着我。觅食的心情也消了大半,扒拉几口,便草草了事。直到之后,祖母奇迹般地转院、出院,我便未再到访过那里的食堂了。
食堂觅食,所见颇多。但在学生时代,留下不少阴影。吃食堂,每天碰上一样的菜色,时间长了,会腻。那时,日子一天天过,也满是回忆。医院食堂伙食不错,似安静平和,但身处其中,却时常忧心忡忡,难以回味。
食堂,一处没有那么多讲究的觅食之所。所见,皆是小众生相。
四
我们时常轻看古人觅食的法门,错将外卖误认为是现代人的专利。这就太小看古人的智慧了,古人可能比现代人还爱吃外卖。
通常误认的焦点,在于古代的交通不那么方便,靠步行、车马、轿辇,送外卖只靠双足卖力,怎么送得了?显然,我们小看了担食盒人的素质。就近,他们稳稳当当,小跑前往,即使走长路,举法巧妙,也不会泼泼洒洒。《老残游记》中写山东巡抚请老残入府吃饭,不久,衙役便领着两名抬着食盒的小厮前来,“揭了盖子,头屉是碟子小碗,二屉是燕窝鱼翅等大碗,第三屉是一个烧小猪,一只鸭子,还有两碗碟点心”。这顿外卖,可谓奢华。随后,还一送再送,又搬到了较远的大明湖,饭食竟然还安然无恙,甚至保留了温热。同样的外卖事件,在《浮生六记》等书中,也有不少记载。
父母这代人,对外卖始终充满警戒心。就算是现如今,这外卖蓬勃的年代,他们同样告诫我,外卖不健康,总之就一句话——不许叫外卖。那怎么办?当然,他们也爱下厨,特别是我爸,只要在家,就总要露一手。但厨房的惨状,一言难尽,油盐酱醋,瓶瓶罐罐混杂,蔬菜残叶满地。厨房的烂摊子,难以收拾,再不济,就下馆子,省时省事。小时候,和父母溜达到楼下的家常菜馆,辣椒炒肉、宫保鸡丁……在馆子里,点些所谓家常菜,他们说,贵些,但放心。
但是,最怕热汤面一类的面食,等到外卖送达,早已凝成了一坨,还原成了面糊,肯定没法吃。后来商家有所改良,包装时会把汤和面分开。这种做法,着实比连汤带面一起送要好一些。但是到手里后,汤是半温的,就算一股脑儿都浇在面里,左提右拉,上戳下叉,想要交融在一起,也拌不开。心下无奈,只得将就了,一口下去,软绵绵、湿答答的,吃起来格外尴尬。
还有一些不可控因素也在作怪。有时饭食与外卖软件上看的大相径庭,卖家秀与买家秀的差距让人气闷,有些店主为息事宁人,好声好气地答应退几个小钱,买了一阵无奈;有些店主则态度恶劣,那摆烂的架势,丝毫不想解决问题,使人烦躁,买了一顿晦气。还有就是外卖小哥送来的时机,总是那么巧合,你以为他会马上到达时,等到肚子咕咕叫,左等右等也不来;以为他会推迟一点,谁知他却飞快到达,疯狂地打电话,催促你快下楼领取……
外卖,与生俱来,满足了饭来伸手的惬意。历经千年,点外卖的冲动谁也拒绝不了。毕竟,对于外卖的需求,也照出了人生的短促,把人从苦苦累累的日子,那重重叠叠的包围中拯救出来,再来一个新的定位,让觅食简单化,也不失为一个愉快的选择。
五
怎么吃?其实还有很多,我列举不完——饭搭子,几个熟识的人共进退,每次都有聚餐的氛围,轮流做东,也有契合的幽默;独行侠,一个人觅食,游荡对应着自由,没有其他意志的左右,自己做主,随意对应着放松,逃离了高压的工作状态,透透气,但代价也显而易见,便是价格较高,难以负担……觅食的法门,就是这样。
时间的选择与空间的决定,是觅食各法的长短。没有哪一种可以傲视另外一种,在它层层累聚的加成下,一定有另一种长处。因此,我们时常在抉择的时刻,在众多选项前来回徘徊,但要一点点地找回自己,不要迷失自己。
自己的迷失,是常常深陷重复的觅食选择,将它们归类于无可回避的生活琐碎,往返着同样一个场面。那些曾经觅食的记忆,早已零零落落。却不知,那些都是真切的人生回忆,在学生食堂,是一段年龄的宝藏,在医院食堂,也是一个时期的记忆,还有往后各种各样的觅食法门,都会给人生增添别样的声色和情致。
声色和情致的交叠,有了生气,有了暖意,有了笑声。还有很多匿名的存在,引得你不得不去一一探寻。或会心微笑,或面露愧色,或门庭若市,人马喧腾,或门可罗雀,寂寥无声……觅食可以说是一种仪式,看见众生相,将人性交融,汇聚出一幅幅插图。
你将它们蕴藏在一生的潜意识中,细细描摹,徐徐勾勒,追踪觅食的踪影,堆出一些善恶的堆垒,得出一些见闻的铺陈与理解。自此,觅食也可以是求道,单纯,清醒,也自在。
我们,一直在觅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