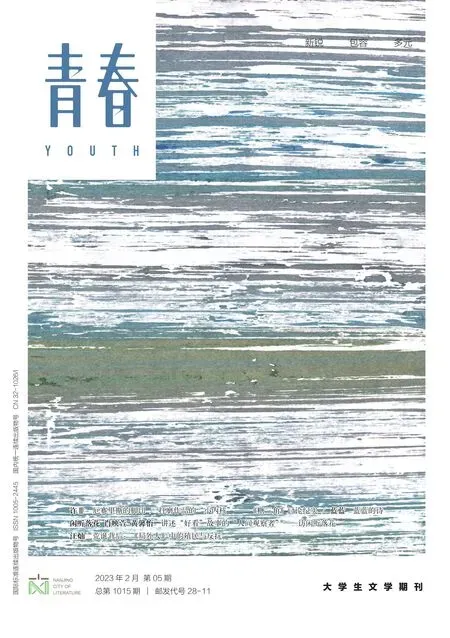十八岁一路向北
北京电影学院 徐柠
一
每座城市总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像是被高架桥横穿的十字路口,步行街上挂着的发黄的广告牌,清晨拥挤的公交车站……当黑夜降临时,相似的霓虹灯,相似的男男女女,相似的碎玻璃声和乱飞的纸屑,总能不自觉地让人忘记自己身处何地。被称作“异乡者”的他们,不停歇地徘徊在昏昏欲睡的人流中。
十八岁刚到北京的时候是一个雨天,我坐了十六个小时的火车,在北京站下车。北京站很旧,冬季凌晨四点的天空还没亮,人们挤在屋檐下和旁边的炸鸡店里,暗中竞争一个可以趴着睡觉的地方。我的行李箱也装了不少东西,拖拽起来很是费力,索性挪到一个角落里,靠着墙睡了一会儿。人群在微弱的光里变成一朵朵移动的乌云,人们很有默契地穿着暗色的羽绒服,偶尔有几个小孩子跳出来才会眼前一亮。
雨停的时候终于坐上了出租车,到了学校。司机很热情,这是我第一次与北方人说话,显得极其拘谨,司机总在叹着气让我说话声音大一些,我抱歉地笑了笑,假装要回消息的样子不停翻看微信——实际上并没有人给我发消息。快到目的地的时候,雨突然开始变大,路被栏杆封住,司机说只能送到这儿了。
时间还早,我不确定能否找到问路的人,淋雨沿着路边兜了几圈,也没能找到进去的路。我感觉刘海已经一缕缕贴在额头上,水滴顺着下巴落在了衣服上。远远地看到有个人围着红围巾在前方,还没等我过去询问,她已经走过来了。
“还是学生啊?”能听出来她不是本地人,甚至口音还有些熟悉。我点点头,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她试图把行李从我手上抢走,我说不用不用,因为她看起来有五十多岁了,让长辈帮忙拿东西总归是不太好意思的。她咂了下嘴,一副不容反驳的样子提起箱子,领着我进了学校。
“箱子放那儿。你是到得最早的,淋雨了吧?小姑娘,你一个人来的啊?”我应了下来,她忙着给我倒开水。大厅里灯光明亮,我才看清她的模样,脸上细碎的皱纹随着说话的幅度拧在一起,手腕上有常见的金手镯,红色的丝巾围住脖子,在黑色的衣服上显得很突出。她坐在我边上,还没等我说话就开始了自我介绍。
“哎呀,我也不是本地人……我是这边的阿姨,有什么事都可以找我的,你是哪里人啊?”我说我是安徽的。
“哦!那我们离得很近,我是江苏的。我儿子在……他在那个,江南大学读书,唉,我平时就在北京这边给他挣钱。”
听闻我的家乡和她的家乡很近,她一下子开心了起来,自顾自讲述起她的故事。作为年长的“北漂”,她在北京打工已久,平时在学校里干干保洁。大城市工资高,自己拮据些,儿子的生活便宽裕些,只是在当“阿姨”这一行的“北漂”中,也分个三六九等。聊到一半,人渐渐多了起来。一位看起来比她年轻些的阿姨在我们身后出现了,敲着她的桌子,大声责问着:“都几点了啊,还在这儿聊天?”我被突然的声音吓了一跳,忙回头看。年轻些的阿姨应该是主管一类的角色,气质也与其他人有所不同。她没说话,等这位主管走了之后,我们陷入一阵短暂的沉默。
“别理她。”阿姨还想继续之前的聊天,我却怕她再受指责,况且老师应该也来了,我也得去办理自己的手续了。
“好吧,小姑娘,以后再跟你聊天,有什么事都可以找我帮忙,千万别不好意思讲。”走之前她朝我笑着挤挤眼睛,仿佛我们已经是认识很久的“姐妹”了,我也点着头说好啊好啊。
二
北方的冬天是凛冽的,南方人一时难以适应裹挟着尘土盖在脸上的狂风,室内干燥的空气似乎要把水分抽干,鼻腔在呼吸之间袭来阵阵灼热感。带着对这座城市的一丝埋怨,我反抗似的想要在有限的条件里营造出南方冬天的氛围,冒着水汽的浴室、垫在被子下的热水袋,时刻播放着的电影……直到我发现学生宿舍里热水的存活时间是五分钟,暖气管苟延残喘地微微发热,无线网也只是徒有其表,网络根本连接不上。与学校沟通了一个月也没有效果,在我的强烈不满下只得答应帮我换一间房间。
搬宿舍那天早早就被敲门声吵醒了,我揉着眼睛开了门,来者解释自己是来帮忙的,顺便清理一下房间。我敷衍地应了一声,套了件外套,洗把脸开始收拾东西。来者总想帮我挑拣一些物品,我摆摆手说您坐着就行,我自己来。过了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这屋子已经保持了很久的安静,转头发现来者坐在我对面无人的床铺上,一言不发。
“你不记得我了?”穿着黑色西装外套,盘起头发的女人说。我愣愣地看了好一会儿,尴尬地笑了笑。
“啊呀,是你呀!”我夸张地说出这句话来掩饰慌张。但实际上我并没有想起来她是谁。
“我之前和你聊天的嘛,唉,不记得没事,你最近怎么样了?”她没有正对我的注视,只在最后几个字的时候才抬起头来看我。
我为自己没能认出她而感到一丝愧疚,从第一次见面到现在也隔了一个多月了,不论这期间有多少琐事影响我对她的记忆,都解释不了我的遗忘。其中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我或许是故意想要将她忘记的。在我对于“北京”这样一座城市的设想中,我会将注意力放在西装革履的白领、穿着花哨的少女、漂亮的混血女孩上,唯独面对一个与我的家乡有所关联,与我的来历相像的普通妇女才会选择遗忘。
她问我在北京过得怎么样,学习怎么样,我说,除了有些不适应天气,其他都挺好的。她小声叹了口气,看起来是要开始埋怨自己了。
“这个物业效率太低,我也跟他们讲了……”我打断了她,连声说没事,这算什么嘛,换个房间就好了。
搬好房间后,她简单打扫了一下,临走前,她拍拍我肩膀,说:“你晓得的,我们那块来北京的小孩少,难得碰见你一个,我也是把你当我小孩看……有什么事,一定跟我讲啊。”
三
学期也到了结束的时候,结课后回宿舍才发现自己将手机充电器忘在教室了,实在没办法,只能又折回去。晚上风变大了,街道涌动着乱窜的摩托车,在路灯的照射下拉扯着自己的影子。老师一看我就是来找东西的,说教室早就被清空了,他们也不知道。最后,我还是点开了微信通讯录里从没联系过的她,想问问她知不知道充电器的下落。没想到她回复很快,让我放心,她对充电器有印象,应该能找到。
第二天一早我便赶到学校,她领着我去一间办公室,却在路上又碰见了那个“主管”。
“这一大早的,又往哪儿跑啊?”她狐疑地盯着我俩,审问着。
“我……我东西忘教室了。”我心虚地回答。
“丢了就是丢了,让你们走之前收拾好,现在拿不到了。”她一声令下。与我同行的阿姨突然瞪了回去,不由分说地拉着我继续向前走,办公室里,我的充电器在杂物堆里好端端地躺着。
临走之前,她又来了我的房间,见我已经将行李打包好,反而有些无所适从起来。
“走了?”她问。
我嗯了一声,反问她:“你过年回家吗?总不能一直一个人在北京待着,这……”剩下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声音变得越来越小,到最后连我也不知道问这些的目的。
她倒是很坦然地笑了笑,“有好几年没回去了,今年想回去又碰上疫情,以后嘛,看情况,反正这边待遇也还不错……再过几年,我儿子大学毕业了就好啦。不对,毕业了他还要考研,考完研结婚还要给他买房子……”说到这,她停顿了一会儿。
“哎呀,反正能坚持几年是几年。”最后,她这么说了一句作为结尾。我听着,没再多说什么。
“你以后肯定有出息啊,还要在北京待着的吧。”她自言自语般又念叨了一句。我苦笑着摇摇头,拖着行李向她道别。
“阿姨,我走了啊。”我们向对方挥挥手,转身离开。
到了火车上,我翻看着微信里面她的那一页,准备给她加个备注,才想起自己甚至没有问过她的姓氏,她也没告诉过我。姓名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标签,我总是直接称呼她为阿姨,像呼喊其他阿姨一样,刻意地想要抹平她在我心中特殊的存在。
从干冷的北京回到湿冷的南方,熟悉的潮湿感瞬间打通了鼻腔和肺,我扑向一切能让我感受到幸福的事物,揉揉家里的猫,扫清在阴霾里堆积的灰尘,身边又环绕着我熟悉的方言,没有刺骨的寒风,没有飞扬的沙尘。我总能听见“走出去,走出去”,但缠绵于故土熟悉的气息里又是多少人的幻想,他们在梦境里与亲人拥抱,与爱人相聚,在清醒的白天里认清现实,依偎着自己的影子,寻找生活的下一个盼头。
与阿姨分别时的场景不断在脑海中闪现,十八岁的我一头扎进了浴室的热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