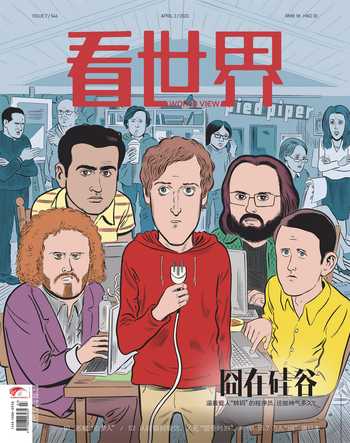忧郁症:撒旦及其糖衣炮弹

现代人经常感到忧郁,但很少有人因此觉得自己生病了。那么问题来了:忧郁情绪和忧郁症(学名抑郁症)之间的界限,究竟该如何划定呢?
诚实地说,直到今天,《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每更新一版,都会刷新此前对“忧郁症”的定义。但只要符合其中大部分描述,大概率就会被诊断为忧郁症。
这些症状大多并不新鲜。在中世纪,包括忧郁症在内的所有精神疾病患者,被认为是灵魂犯罪而遭天谴,患者体内充斥着“邪恶的黑胆汁”,是撒旦现身向人类展示它的力量。
在后现代医学突飞猛进的近500年里,关于忧郁症的认知却仍举步维艰,其发病机制至今是未解之谜。迄今为止,人们尝试了很多使自己高兴起来的方法—那并不难,但大多属于饮鸩止渴,更像是撒旦的糖衣炮弹。
人类第一次自以为找到了对抗忧郁的灵药是在18世纪。德国北威州一位名叫F. 泽尔蒂纳的药剂师助理发现,提取自罂粟的鸦片有很强的麻醉效果,能够缓解疼痛,继而尝试将其中真正具有麻醉效果的有效成分提取出来。
泽尔蒂纳成功了!1805年,他用希腊神话中的睡眠之神“吗啡斯”将这种提取自罂粟、能够使人快速进入深度睡眠的生物碱命名为“吗啡”。从此,“疼痛”这个与人类纠缠不休的恶魔算是被制服了。而忧郁症作为一种“精神疼痛”,看似也迎来了一丝曙光。因为,忧郁症和肉体疼痛之间经常形成恶性循环,后来人们才知道,那是因为两者在大脑中具有共同的化学信使。
人们有多么难以忍受疼痛(不论是生理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就有多么无法拒绝吗啡—也就失去了精神上那可贵的“自愿”。尤其是在战场上,为了使战士们尽快回到阵地,吗啡更是被大量滥用。约翰·彭伯顿就是这样一名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被滥用了吗啡的士兵,当意识到自己吗啡成瘾后,他想到一个好办法—用当时欧洲流行的古柯酒来代替吗啡。
整个19世纪,可口可乐更是享有“一口可乐,数倍快乐”的美誉,被大量推荐给忧郁症患者。

可乐发明者约翰·彭伯顿

海洛因
古柯酒的核心成分,来自一种提纯自古柯叶的生物碱“可卡因”,不但有提神效果,还能产生令人愉快的致幻效应。1886年,约翰用古柯酒戒除吗啡的同时,顺手还改进配方合成出一种新的饮料,起名为“可口可乐”。相比今天碳酸饮料的“sugar rush”,初代可口可乐才是真的上头。
整个19世纪,可卡因被大量运用于外科麻醉,可口可乐更是享有“一口可乐,数倍快乐”的美誉,被大量推荐给忧郁症患者,成为第一种得到广泛应用的抗忧郁“药物”。甚至,当时的美国神经协会宣称:“一个忧郁寡欢、沉默寡言的人,背负最深沉哀痛或是悲伤的人,在可卡因的作用之下也会停止哭泣,高兴起来。”就连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也在服用可卡因后大为赞美,称其为“富有魔力的物质”。
在可口可乐风靡的同一时期,德国拜耳公司的药剂师菲力克斯·霍夫曼,在吗啡基础上继续合成出一种具有超强镇咳和镇痛作用的物质,起名“海洛因”(heroin),意味“英雄”。其适用范围很快从最初的止咳,扩大到止痛和抗忧郁等精神疾病的治療。于是,对吗啡的滥用很快演变成对可卡因和海洛因的滥用。
但随着可卡因和海洛因成瘾性和幻觉、失眠等副作用显现,医学界不得不承认在药物研究和推广上的确过于草率。这之后,一系列禁用或管制使用的法令相继颁布。1903年,可口可乐在配方中去掉了可卡因,只保留了咖啡因这一种兴奋性物质—几乎没有成瘾性,但同时也对忧郁症不甚有效。
可卡因淡出江湖之后半个世纪,第一个专业抗忧郁药物“异烟肼”诞生于1952年。一群肺结核病人服用合成的异烟肼药物治疗肺病,却莫名地狂喜起来,这再次让忧郁症患者如获至宝。但此后,它又因出现肝损害等众多副作用而被停用。
所幸,在另一条道阻且长的路上,人类抵抗忧郁的脚步从未停止。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首次发现,忧郁症患者的脑脊液中血清素(单胺类神经递质)浓度比正常人低整整3倍。

抗忧郁药物百忧解
哪怕在今天,百忧解仍是最常用的抗忧郁药之一。
卡尔森在1969年发表的论文中提出:大脑中血清素含量是影响情绪的因素之一。至此,寻找忧郁症病因的漫漫长夜,算是迎来了一缕曙光。人们开始相信,使人患病的并不是纯粹的心理因素,忧郁症同时有其生理原因—“邪恶的黑胆汁”的面纱被撩开一角。
抓住这一缕光明的人,是美国礼来药厂的一名华裔神经化学家汪大卫。他继续以老鼠的脑细胞组织做实验,并通过把服用过合成药物的老鼠进行脑末梢神经分离,最终找到一种高含量、能阻止血清素再回收的合成物质──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如此,血清素就会在细胞之间停留更久,大脑中血清素浓度也就随之升高。
1974年,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首次在专业期刊上出现,当时估计研发这一新药需耗資3亿美元(约等值于现今的12亿美元),约为一般研发经费的3-4倍。但礼来药厂还是决定跨出这一步,汪大卫和来自不同领域的共约15人,包括化学家、医学家、药学家,甚至还有行销部门的专家,成立特殊研发小组,名为“Lilly 110140”(礼来药物编号)。
此后,长达12年的临床实验证实,这种药物的最大突破在于其安全性和非成瘾性。由于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具有“选择性”,不会影响其他神经物质的传输,也因此能够降低别种药物产生的副作用。
1986年,“百忧解”首先在比利时上市。次年12月29日,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正式核准百忧解面世。对于那些觉得自己快要没顶于精神痛苦的人们来说,虽然迟了一些,但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圣诞礼物了。
截至百忧解专利到期的2001年为止,其营业额达到220亿美元。哪怕在今天,百忧解仍是最常用的抗忧郁药之一。它让人们第一次相信忧郁症是可医治的,并不再羞于讨论它。

2021年9月1日,加拿大纳奈莫,用于提取裸盖菇素的迷幻香菇与所制成的药丸
所以,人类战胜了忧郁症吗?并没有。事情的另一面是:百忧解流行了多少年,关于百忧解的争议和疑虑就流行了多少年。
人们很早就发现,百忧解即使能立即提升病人的血清素浓度,忧郁症状却要一段时间后才会缓解,而且将近50%的病人根本没有反应。尽管人们尚不了解血清素对大脑神经的具体作用机制,但显然,忧郁症的病理并不是只有“血清素”一种解释。至于更多的,仍然没有确定的答案。
谜团未解,药还吃吗?吃!“好了伤疤忘了疼”是人之本性,也是文明之勇。一个新的趋势在于,自上世纪被封杀的致幻剂,似乎又有重回江湖之势。人们始终记得吗啡和可卡因带来的快乐,但同时,曾经的血泪经验也时刻提醒着人类:去往那神秘之境,切记谨慎。
这一次的主角是提取自迷幻香菇的裸盖菇素。61岁的癌症受试者文森说,她原本觉得人生已无意义,但在注射裸盖菇素后的6小时内,她看见了绿色与紫色构成的大海,成排的埃及船只与俄罗斯娃娃,一只小小的、奶油白的、动画风格的螃蟹跳入视线,仿佛人生中仍有幽默、美丽的一面。
美国两份最新研究显示,近八成的癌症病人在使用小剂量的裸盖菇素后,变得比较温和,心理健康与生活满意度也有明显提升,对过去的伤痛不再有感觉,这样的正向情绪持续超过6个月。
但长期服用此类致幻剂,对人体有副作用和成瘾性吗?在历史上屡次滥用致幻剂之后,人们终于谦卑地承认即便医生和患者都觉得无碍,仍有一些反应不显现于当下。另一方面,今天在忧郁症的诊疗领域,医生通常引导患者感受服药和停药期间的反差,协助其认清本来的自我,然后再将“是否要通过药物改变自身性格”的选择权交还给患者本人。
但不论是百忧解还是迷幻剂,“是否可用药物改变人格”始终是一个巨大的争议。关于忧郁症的迷思,某种程度上就是关于人类自身的迷思。千百年来,从神学家、心理学家、生理学家,到社会伦理学家,一次次地假设、提问、发现、颠覆,都在提醒人类:有关自身,我们知道了那么多,同时却还是那么少。
关于忧郁症的痛苦和绝望古今皆然,但至少,今天已经没有人再会对忧郁症患者轻佻地劝说:“做人嘛,开心最重要。”总有一些事,比开心更重要。
特约编辑姜雯 jw@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