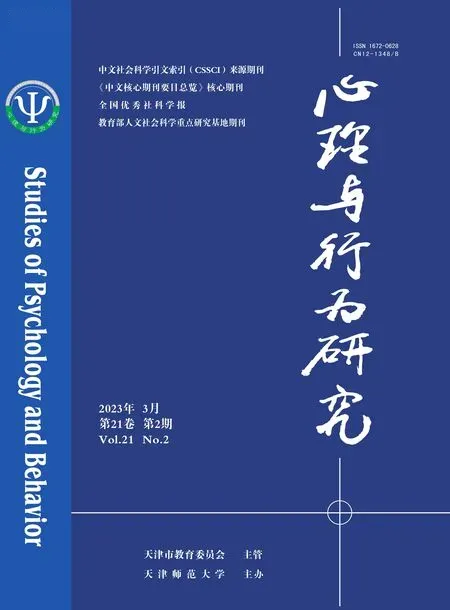3~6岁幼儿羞耻发展教师评定量表的编制 *
何明影 张献英 李玲玉 杨丽珠
(1 辽宁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大连 116029) (2 阜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学院,阜阳 236015)
1 引言
羞耻是一种自我意识情绪,由生物、个人和环境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自我评价后产生的痛苦感受(Rathbone, 2011)。其涉及自我贬低,经历羞耻的个体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微不足道,并产生逃避、退缩的倾向(Tangney & Dearing, 2002)。由于羞耻所带来的消极体验,羞耻被认为与精神病理有关,研究发现羞耻体验的频率与低自尊、敌意和心理痛苦程度相关(Velotti et al., 2017),并可以预测抑郁症状的增加(Nikolić et al., 2022)。但也有研究者认为,羞耻是作为适应的一部分进化而来,它可以促进个体社会化,在个体与他人的社会交往过程中,由羞耻所引发的消极体验可以帮助个体识别并纠正交往过程中所出现的不恰当行为,促使个体以道德上、社交上适当的方式与他人交往,以获得亲密、友好的人际关系(Muris et al., 2018)。可见,羞耻在个体道德行为发展以及精神病理学中都具有重要作用。
实际上羞耻并不是一种单一维度的构念。一方面,根据生物心理社会和进化模型,研究者提出两种类型的羞耻:内部羞耻和外部羞耻(Gilbert,2003, 2004)。前者是消极自我评价的结果,它是个体对自我属性、个性特征和行为表现的消极感受。后者关注的焦点是别人如何评价自己,相信他人会拒绝或攻击他,是一种认为别人会用消极情绪看待自己的意识。虽然这两个概念紧密相连,但感受到外部羞耻的个体不一定会感到内部羞耻,而内部羞耻涉及认同他人的负面评价,因此感到内部羞耻的个体通常会感受到外部羞耻。最近基于该理论框架,研究者开发了同时测量内部羞耻和外部羞耻的青少年和成人量表,得出自卑、孤立感、无价值和批判四因子结构(Cunha et al., 2021; Ferreira et al., 2022)。杨丽等人(2019)对外部羞耻量表的结构进行了本土化验证,与国外学者所得结构类似。另一方面,在羞耻与病理学关系的研究中,研究者侧重于羞耻在自我不同方面的指向。研究多关注身体羞耻、关系羞耻、能力羞耻和认知羞耻等几个方面(亓圣华 等, 2008; 钱铭怡等, 2000; Rizvi, 2010; Scheel et al., 2020)。以上国内外羞耻结构研究主要针对成人和青少年,并且发现青少年的羞耻结构几乎与成人无异(Malinakova et al.,2020)。
对于儿童羞耻的测量,以往研究大多采用羞耻情境判断或纸笔测验。羞耻情境判断是指实验者给儿童描述几个会产生羞耻感的场景,让儿童判断这些场景中主人公羞耻感的强度(Misailidi,2020; Olthof et al., 2000)。但这类测量是从第三人称视角进行评估的,要求儿童判断他人而不是自己的羞耻感,这对儿童心理理论要求较高,且判断他人和自己对羞耻情境的反应,儿童的判断结果可能有所不同,导致测量偏差(Misailidi, 2020)。纸笔测验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自我意识情感测验(Tests of Self-Conscious Affect, TOSCA),该测验应用情境模拟技术,评估个体包括羞耻倾向在内的自我意识情绪(Tangney, 1990)。其由平时生活中常见的15个简短情景组成,测量个体遇到每种情景之后的羞耻反应。TOSCA包括儿童、青少年和成人三个版本,其中TOSCA-C版本适用于8~12岁儿童,该量表应用广泛,被证明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高学德, 2013; Tangney et al., 1996)。但该量表将羞耻视为一种单一的结构,因此Cohen等人(2011)在TOSCA基础上,从认知和行为两维结构的理论构念出发,发展了一个新的成人羞耻量表,用于评估个体公开违规行为后的负面自我评价和退缩行为倾向。另外,研究者也采用简单任务失败范式测量羞耻,观察儿童在简单任务上失败后的羞耻反应,以此评估儿童的羞耻水平(Lewis et al., 1992)。但该方法仅考察了失败情境下的羞耻反应
由此可见,儿童阶段羞耻的测量结构较为单一,且以往研究通常以西方文化为中心概念化羞耻,将羞耻作为一种痛苦的情感体验,忽略了根植于其他传统文化的羞耻内涵,比如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羞耻的道德作用和社会功能,个体可以通过羞耻改善自我(Collardeau et al., 2022)。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羞耻既可以在失败情境下产生,也可以在违规情境下产生(Smith et al., 2002;Tangney et al., 2007)。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幼儿羞耻是指幼儿知觉到自身失败或违规时产生的一种负面自我评价或回避、退缩的行为倾向,包括失败羞耻和违规羞耻两个方面。教师是适合评价幼儿的主体,可以有效避免父母期望对评价带来的影响。以往研究使用评分者信度检验幼儿教师评价的可靠性,结果显示,教师评价与父母评价的相关性较高,教师评分者信度较高(杨丽珠 等,2015)。因此本研究编制3~6岁幼儿羞耻发展教师评定量表,并结合情境实验检验量表的效度,以期为研究幼儿羞耻提供科学有效的测评工具。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在大连市五所幼儿园以小、中、大班为单位随机选取3~6岁幼儿,幼儿分为三个年龄群组,其中3~4岁是3岁组,4~5岁是4岁组,5~6岁是5岁组。样本的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样本1。在大连市选取了五所幼儿园的46名带班教师,对46名教师发放开放式问卷,请每位教师描述所在班级3名幼儿的羞耻情境、事件和行为表现,其中有效问卷137份,问卷回收率为99.28%。
样本2。在大连市一所幼儿园选取173名幼儿用于项目分析。
样本3。从大连市五所幼儿园抽取886名幼儿,其中459名被试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427名被试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
样本4。信度分析被试,在大连一所幼儿园中选取240名幼儿。其中评分者一致性信度分析被试为120名,剩余的120名为重测信度被试。
样本5。构念效度被试,在大连市一所幼儿园选取90名幼儿。实验前取得了每名幼儿父母的知情同意。
样本2~5被试具体分布情况见表1。

表1 有效幼儿被试分布情况(单位:人)
2.2 研究程序
2.2.1 初始量表的编制
首先,请46名教师填写开放式问卷。每名教师分别选取本班三名高、中、低羞耻水平的幼儿进行羞耻情境、事件发生过程、行为表现的详细描述。其次,依据内容分析法对教师报告的幼儿羞耻事件进行归类(Kassarjian, 1977)。根据对以往羞耻研究的理论推导和对收集资料的初步整理,将羞耻事件概括为违规羞耻、失败羞耻两种类型。违规羞耻指当幼儿做出违规行为时,在他人提醒下或依赖于自身内在标准产生的羞耻体验。失败羞耻指当幼儿出现任务失败、发生失误等情况时所产生的羞耻体验。再次,请受过训练的编码员对所有事件进行类型划分,形成开放式问卷编码表(见表2)。最后,通过开放式问卷调查、幼儿园中的观察记录并依据以往的羞耻研究,形成最终的羞耻理论建构,编制量表初始题目。请心理学和学前教育博士研究生和幼儿园教师对量表内容进行评定,形成“3~6岁幼儿羞耻发展教师评定量表(第一版)”,共34个项目,采用4点计分,从1分“完全没有”到4分“经常如此”。

表2 幼儿羞耻事件开放式问卷编码表
2.2.2 预测
请幼儿教师根据第一版量表评价样本2幼儿的羞耻水平。发放量表180份,实际回收173份,量表有效回收率为96.11%。对本次施测结果做项目分析后删除5个项目,形成第二版量表。
2.2.3 正式施测
请幼儿教师根据第二版量表评价样本3幼儿的羞耻水平。发放量表900份,实际回收886份,量表有效回收率为98.44%。经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后删除4个项目,形成第三版正式量表,正式量表共包含25个项目。
2.2.4 正式量表的信效度检验
最后以样本4和样本5为研究对象,请幼儿教师根据第三版正式量表评价幼儿羞耻水平,对所得数据进行信效度检验。
2.3 统计处理
使用SPSS15.0和Amos17.0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等。
3 结果
3.1 项目分析
对初始量表的施测结果做项目分析。将校正的题总相关和平方复相关系数(R2)小于0.30的5个项目删除(戴海琦, 2015),剩余的29个项目随机编排,最后29个题项与总分相关系数在0.38~0.68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通过得分率法计算题目的难度(戴海琦, 2015),计算所有被试在该题目上的平均得分占题目满分的百分比,得出各题目的难度介于0.43~0.62之间,难度适中。
3.2 探索性因素分析
项目分析后,对剩余29个项目做探索性因素分析,KMO值为0.97,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p<0.001),适合做因素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极大方差正交旋转进行降维处理,删除双重负荷项目2个,以及载荷小于0.40的项目2个。最后得到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2个,累积解释总变异的64.02%。其中第一个因素包含13个项目,解释贡献率50.93%,为违规羞耻。第二个因素包括12个项目,解释贡献率13.09%,为失败羞耻。羞耻两个因素的载荷见表3,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与理论构想基本吻合。

表3 探索性因素分析各维度载荷和共同度(n=459)
3.3 验证性因素分析
探索性因素分析后,对剩余25个项目做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模型拟合较为理想(见表4)。25个项目的因子载荷在0.41~0.70之间,均达到0.30以上,说明探索得到的两个维度能够较好地预测各题。

表4 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拟合指数(n=427)
3.4 信度分析
对量表的分半信度、内部一致性信度、评分者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进行测量。由两名带班半年以上的教师对同一名幼儿进行羞耻评定,计算两名评分者的相关系数得到评分者一致性信度。在一个月后对120名幼儿进行再次测量,得到重测信度。信度测量结果如表5所示,所得结果表明正式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表5 幼儿羞耻发展教师评定量表的信度指标
3.5 效度分析
采用教师评定和情境实验两种方法来测量违规羞耻和失败羞耻两个维度,构建多质多法矩阵验证量表的构念效度。
3.5.1 违规实验
(1)实验材料
一张桌子和一个玩具。其中,玩具选取对幼儿有吸引力的新奇物品,即伴随音乐播放的打地鼠玩具。
(2)实验过程
在幼儿园选取一个独立且安静的房间,由已经熟悉幼儿的主试与幼儿进行情境实验。实验过程如下:主试展示准备好的玩具,等待幼儿对其产生兴趣后,邀请幼儿与其共同玩耍。一段时间后,主试告诉幼儿自己需要暂时离开一会儿,在此期间幼儿不能独自玩玩具,直到主试回来后方能继续一起玩。在主试离开的这段时间,玩具持续播放音乐。当幼儿被玩具诱惑单独开始玩玩具时,主试重新进入该房间。此时,主试需要完成两个阶段性的询问任务,第一阶段询问幼儿在离开之前主试是否说过可以玩玩具,约60秒;第二阶段询问幼儿是否按照要求去做,同样约60秒。最后,研究者通过言语安抚幼儿,旨在消除幼儿在实验中产生的沮丧和不愉快,并让幼儿继续玩一会儿(第三阶段,60秒)。实验全程使用隐蔽摄像机记录幼儿的具体行为表现,共计10~15分钟。
(3)实验计分
反复观看实验录像并对三个阶段中幼儿的羞耻行为进行编码,行为编码以5秒为一个单位,共划分成36个片断(Kochanska et al., 2002)。根据以往研究提出的幼儿羞耻发生指标(Alessandri & Lewis,1996; Lewis et al., 1992)(见表6),计算每种行为类型出现的频次,并对每一行为类型的持续时间进行加权,持续时间较长的行为频次求和乘以2,持续时间较短的频次求和乘以1,最后把这些分数标准化后相加得到羞耻总分(Kochanska et al., 2002)。

表6 幼儿羞耻发生指标
3.5.2 任务失败实验
(1)实验材料
一张桌子和两幅难易程度不同的拼图。较低难度的拼图用来帮助幼儿详细理解拼图规则,较高难度的拼图选取超过幼儿现有水平的材料,其目的在于诱发失败情境。
(2)实验过程
在幼儿进入房间后,主试首先与该幼儿共同完成一个简单的拼图游戏,保证幼儿熟悉掌握拼图规则。在确保幼儿理解规则后,主试随即邀请其完成较高难度的拼图,该拼图的图案具有一定吸引力。该阶段要求幼儿在主试规定的时间内独立完成,闹铃响代表时间截止。幼儿理解规则后,拼图游戏正式开始。在游戏进行过程中,主试不会向幼儿提供任何指导和干预,除非影响到任务的进行,即当幼儿发生注意力分散或无意继续时,主试会适当提供一定的鼓励。在幼儿只剩下两块拼图未完成时,主试趁幼儿不注意摁响闹铃,并告诉幼儿截止时间已到(第一阶段,60秒)。接下来,主试会告诉幼儿,其他小朋友玩这个游戏都能够在规定时间内顺利完成拼图,只有你一个人无法完成拼图(第二阶段,60秒)。最后,主试再告诉幼儿自己误看了时间,确实没有人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拼图,并允许幼儿继续完成拼图游戏。幼儿完成拼图后,主试给予其口头表扬(第三阶段,60秒)。实验全程使用隐蔽摄像机记录幼儿的具体行为表现,共计10~15分钟。
(3)实验计分
与违规实验相同。
根据表7的结果可知,量表测评结果与情境实验结果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90、0.77,特质之间的相关也达到了中等程度相关(0.40~0.60之间),并且聚敛效度中的相关总体上高于区分效度中的相关,说明量表有良好的构念效度。

表7 幼儿羞耻发展的多质多法矩阵
4 讨论
以往羞耻的界定和测量大多从西方文化视角出发(Collardeau et al., 2022),对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羞耻,特别是幼儿羞耻探索稍显不足,因此本研究首先在对以往羞耻研究的理论推导及对教师报告的幼儿羞耻事件和行为表现分析的基础上,形成包含失败羞耻和违规羞耻两个维度的初始量表。随后采用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形成正式量表,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对得出的幼儿羞耻结构进行验证,结果显示二因子模型拟合良好,χ2/df小于5,SRMR和RMSEA均小于0.05,CFI和TLI均大于0.90(王阳 等, 2022),表明幼儿羞耻的二因子结构合理。通过理论分析、质性分析和量化分析,本研究最终得出幼儿羞耻结构是由违规羞耻和失败羞耻两因素构成。其中,违规羞耻主要是指在违规情境中所体验到的羞耻;而失败羞耻则主要表现为幼儿不能独立完成某项任务,表现不如其他小朋友,以及因表现不佳而被其他小朋友嘲笑时所产生的沮丧、痛苦以及逃避的倾向。
研究得出的幼儿羞耻结构与一些研究者提出的羞耻的理论含义一致,羞耻分别隶属于非道德和道德两个领域(李阿特, 汪凤炎, 2013; Smith et al.,2002; Tangney et al., 2007)。一方面,羞耻由失败的普遍自我归因产生。羞耻的认知归因发展理论认为,当个体将消极的行为结果归因于自身能力不足时便会产生羞耻(高学德, 2013; Mills, 2005)。Lewis等人(1992)曾通过创设失败情境考察幼儿的羞耻感,发现在简单任务上失败,幼儿会表现出较为强烈的羞耻感。本研究通过量表得分和情境实验的观察也发现,当幼儿出现任务失败、发生失误等情况时,羞耻得分较高的幼儿会对失败进行内在自我评价,出现一定的羞耻反应,比如挠头笑、低头向下、抿嘴、扭捏等行为表现。另一方面,羞耻是一种道德情感,当面对违反规则并有他人在场时,个体会产生较多的羞耻感(Cohenet al., 2011)。本研究发现违规羞耻这一维度在整个量表中的贡献率占比更大,远高于失败羞耻,说明在中国传统文化下由违规情境引发的羞耻更为常见。这是因为中国“知耻”的传统文化更强调羞耻的道德意义(Berkson, 2021; Kwong, 2021; Schaumberg &Skowronek, 2022; Uebel, 2019)。父母在儒家知耻教育思想影响下,通常较为注重培养孩子的耻德,认为羞耻感可以作为内在动力起到制约不当行为、传递社会规范的作用(Zhang & Cross, 2011)。总之,研究强调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探讨幼儿羞耻结构和编制本土化幼儿羞耻量表的必要性。
本研究通过多种方法对量表的信效度进行检验。信度方面,总量表和分维度的分半信度、内部一致性信度、重测信度和评分者一致性信度系数均在0.60以上,大部分在0.70以上,表明编制的幼儿羞耻发展教师评定量表信度良好(吴明隆,2003)。效度方面,请心理学和学前教育博士研究生以及教学经验丰富的幼儿教师对量表项目进行评价,确保量表内容效度良好。考虑到幼儿的言语能力和自我评价能力尚未完全成熟,本研究通过教师对幼儿羞耻进行评定,并且结合情境实验法对量表的构念效度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会聚效度的相关较高,而区分效度的相关较低,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构念效度。本研究从多个角度检验了量表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证实其可以作为幼儿羞耻的有效测量工具。
5 结论
(1)3~6岁幼儿羞耻由违规羞耻和失败羞耻两个维度构成。(2)3~6岁幼儿羞耻发展教师评定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以作为测量幼儿羞耻的有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