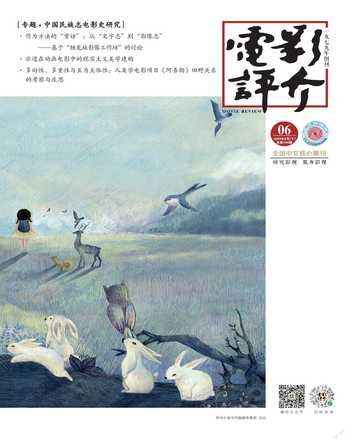作为方法的“重访”:从“文字志”到“影像志”
郭建斌 唐思诗


2021年12月,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媒体人类学研究所举办了“民族志影像工作坊——独龙族”活动①。该活动最初的设想之一是把这个学术活动放到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的某个村,向村民展示一些独龙江独龙族的老照片,并放映一些与独龙江独龙族相关的纪录影像。由于新冠病毒感染影响,这一设想未能实现,最后只在昆明简单地举办了一个活动,活动的主要内容也变成了放映与独龙江独龙族相关的影像,并邀约了其中部分影像的拍攝者。观看者除了相关影视工作者、学者、学生之外,还邀请了三位来自独龙江的独龙族普通村民,以及部分在昆工作的独龙族学者。工作坊所放映的影像,有些是沿着“重访”的思路来拍摄的,而其他影片中,也借用了一些20世纪60年代拍摄的民纪片《独龙族》(1960)中的镜头,这种借用无疑具有某种重访的意义。
在人类学中,重访并不是新鲜的话题,诸多研究者都沿着回到自己的或是前人的田野点进行再调查与再研究的路子进行研究。但是,既往的重访更多的是一种“文字志”的方式,本次工作坊的企划者之一——徐菡在对工作坊进行总结时提出了“影像志”的概念,认为“影像志”相比“纪录片”,能够更好地概括这次工作坊。②同时,“影像志”不仅仅是记录,也可以把重访的意义涵盖其中。我们认为这样一种概括是十分恰当的。
基于以上说明,本文拟对人类学史上既往的“文字志”式的重访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独龙族影像工作坊”,对“影像志”式的重访进行讨论。
一、作为“文字志”的重访研究及研究对象
本文的“文字志”概念主要是想与“影像志”这一概念相对应,其概括的是以文字形式呈现的研究成果。自20世纪40年代起,人类学界便已经开始重访实践,并主要集中于西方学界不同学者针对同一“异文化”的考察;而本身起步较晚的中国人类学,其重访实践也明显滞后于西方学界,形成了区别于西方但具有中国特点的重访实践。
(一)西方的实践
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人类学步入“科学民族志”的时代写出了《萨摩亚人的成年》,以萨摩亚人快乐悠闲的青春期来驳斥欧美社会从生物学角度提出的青春期必然是充满情绪化压力和冲突的观点。在20年代生物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之争中,米德的这一人类学个案研究将这一论争推向高潮,并吹响了文化决定论的胜利号角,直到1940年新西兰人类学家德里克·弗里曼(Derek Freeman)前往萨摩亚调研,学界包括弗里曼本人都对米德的论述深信不疑。根据弗里曼的自述,在萨摩亚调研前期,“出于对米德作品毫无条件的接受,倾向于忽略所有与她的结论相冲突的证据”[1]。到1942年年末,弗里曼愈发意识到米德关于东萨摩亚的描述明显不适用于西萨摩亚,然而东萨摩亚当地的居民则证实东、西萨摩亚的生活如出一辙,弗里曼至此才不得不把系统检验米德对萨摩亚文化的描写作为其研究的主题之一。此后的40余年,追寻事实的责任感一直驱使着弗里曼坚定不渝地反驳与论证米德关于萨摩亚的论述,并前后三次重返萨摩亚以获取第一手资料,实现了从田野规范的质疑、田野事实的驳斥到人类学范式的超越,可谓人类学重访实践的典范。这样一种实践诠释了“重访”中较为普遍的一种类型:多次前往前人的研究地点,并重新审视当地的生活与此前的研究成果。与此同类的还有韦纳(Annette B. Weiner)对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研究的特罗布里恩德岛(Trobriand Islands)的重访,发现死亡仪式中女性的特殊地位,进而将女性主义视角引入人类学的研究之中。[2]人类学史上有诸多类似实践,在此点到为止。①
另一种经典的重访实践,是人类学家们对自己田野点的回访调查。如林德夫妇(Robert Lynd and Helen Lynd)对于中镇(Middletown)的研究。1925年,林德夫妇以定量和定性结合的方式描述了中镇1890年以来的社会变迁,并于1935年重返中镇再次考察十年间中镇的变化。[3]再如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分别于1928年、1936年对蒂蔻皮亚(Tikopia)的回访,关注该岛屿在外部世界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4]概括而言,这类研究者回到自己田野点的重访实践,其目的主要是更新和积累同一个研究的资料,其关注的侧重点是历时性变化。
正如重访先行者弗里曼称其对文化决定论与生物决定论进行的学术性综合为“一个更为科学的人类学范式”[5],不论是研究者对他人研究地点的重访,还是研究者本人对一项研究的持续追踪,重访也正是基于为了让人类学的研究更具科学性的目的而被广泛应用。
(二)中国的实践
20世纪上半叶,一批海外学者和留洋学者在中国大陆进行田野调查,并产出了一批数量不多但影响力极大的民族志作品,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称为中国人类学的“古典时代”[6]。而后,中国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政治、经济、文化巨变,这些中国人类学史上的学术名村也深受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起到21世纪初,国内掀起了对这些地点进行回访和再研究的高潮,形成了以费孝通回访“江村”②为代表的中国人类学先驱者对自己田野点的回访,以及以庄孔韶重访“金翼黄村”③为代表的新一代人类学家对学术名村的再研究两种类型的“重访”。其中,庄孔韶于1999年末发起了《时空穿行——人类学重访的文化实践》策划,向国内进行“重访”实践的学人发出邀请,并将成果集结成《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一书,呈现了一场从山东台头、广东凤凰、福建义序、云南喜洲等8个著名田野点发出的跨越时空的新老对话。[7]尽管学者们身体力行实践多年,但“重访”(回访)作为概念至此才在国内被正式提出,将其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取向和极具理论价值的学术实践路径”④,并对重访价值做出一定总结:延续田野点与先驱者作品的学术生命、开辟历时研究和共时研究的新思路以及更多的声音表达与更广的理论视野。不过,回访、再研究等表达在此时仍处于混用状态。
世纪之交,对云南著名人类学田野调查地点进行重访在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的牵头下展开,包括费孝通主持的“云南三村”之禄村的调查、许烺光对大理喜洲展开的祖先崇拜研究以及田汝康对德宏傣族那目寨“摆”的研究,张宏明[8]、梁永佳[9]、褚建芳[10]三位北大博士分别从土地制度、地域崇拜和人神互惠交换三个主题对前辈的论点进行了“反思性继承”。之所以将这次的重访概括为“反思性继承”,在此次重访研究成果系列出版物之《重归“魁阁”》①一书中,王铭铭也专门做过解释,即对当时国内“追踪调查”“回访”和“再研究”的提法进行了简要的辨析,认为国内将对旧田野工作地点的再次研究应称为“跟踪调查”,而海外人类学的诸多实践则为“再研究”(restudy)。前者注重同一地点的社会变迁与发展,后者则容易陷入追求理论反驳的极端相对化。[11]沿着费孝通对他们的指导思路,“跟踪调查要么要反映被我们研究的那个社会自身的变化,要么要反映我们研究者自己的理论和心态变化”[12],王铭铭将费老提出的两种路径进行了综合发展,指出应基于前人宝贵研究的基础上增添新知识,即“反思性继承”。在他看来,这并非是一种理论而仅仅是一种学术态度,其目的是重视中国人类学“古典时代”学术成果的价值,并以历史的眼光实现传承与创新。
总之,对于中国的重访研究,学者们一方面看到了中国“古典时代”人类学作品及其田野点的学术价值,强调的是对前人的传承而非驳斥;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国内外的诸多实践存在“回访”(追踪调查)和“再研究”的区别。这种讨论虽然并未明确指出中西之间的差别,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向我们揭示了中国重访实践的特殊性。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脉络来看,中国人类学的“古典时代”不仅为中国人类学的创立打下了坚实基础,费孝通、杨懋春、林耀华、许烺光等人对本土乡村社会的研究,也使中国率先开启了人类学界“本土研究”的序幕。[13]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这些著名田野地点的重访研究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科恢复与重建的有效路径。通过重访,一方面可以继续顺應本土人类学研究的浪潮,循着前人的脚印逐步扩大国内田野点的范围;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事实,为人类学对话西方理论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经验材料。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重访实践,主要聚焦的是古典时代的著名田野地点,其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参照物,着重呈现历时性的社会变迁,力图以“小”村落窥见“大”中国。同时,面对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针对中国“古典时代”提出的“小地方的描述难以反映大社会”[14]的质疑,这样一种关注到时空变迁的重访实践,也成为新一代人类学家以“在较大的空间跨度和较广的时间深度中探讨社会运作机制”[15]进行回应的重要路径之一。
(三)迈克尔·布洛维的“重访”理论
然而,作为“文字志”的重访尽管在中西方都已经被接受为一种研究取向,但是对此的讨论并不成体系,也尚未形成较为规范的分析框架与操作化方法。直至21世纪初,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布洛维发表《重访:反思民族志的理论框架》(Revisits: an outline of a theory of reflexive ethnography)[16]一文,才较为系统地梳理了重访的理论脉络与分析框架。
不同于中国学者将回访与再研究进行区分,布洛维定义的重访(revisit)涵盖了两者,即人类学家将现时的参与观察与此前自己或他人对同一田野地点的研究进行比较。同时,布洛维进一步指出以重访进行比较分析的四个维度(参见表1)。当研究者作为观察者进入田野点之后,其身份地位及个人履历将影响研究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与他人的关系,并产生不同的工作经历,进而导致在不同时间段收集到不同的田野资料,这被称为建构主义的内部解释。同时,研究者带入田野点的不同理论也会对同一现象产生不同的理解,这被称为建构主义的外部假说。建构主义分析立场围绕的主体是研究者,而现实主义的两种解释则聚焦于研究地点本身。现实主义的内部视角认为,重访的民族志之所以不同,是因为田野点在不同时间段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外部视角则将差异的原因归结为田野点所处的更大的社会环境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基于此,布洛维为重访提供了一个较为系统的分析框架。在研究过程中,这四个维度总是交织在一起,尤其是时间跨度很长时,很难区分出田野点内部自身的变迁与外部力量的干预,这时就需要呈现详细的经验材料以描述纯粹的内部过程。
但是,若把重访只限制于同一地点的错时访问上,显然也是狭隘的。既往的重访实践,往往是从某一固定地点出发,将过去某一时间的情况与现在的情况进行比较。布洛维对此进行了一定拓展,在聚焦同一地点进行重访的模式之上补充了滚动式(rolling)、间段式(punctuated)、启发式(heuristic)、考古式(archeological)、告别式(valedictory)等五种重访模式。至此,布洛维正式将该方法作为一个可操作化的概念提出。与前文所整理的中国重访相比,布洛维的重访(revisit)概念已经超越了将重访作为方法的意义的讨论,进入了将抽象概念如何运用到实际研究中的操作化阶段,并且在提出后也有学者以这一研究框架进行研究分析。①不过,布洛维讨论的范畴仍局限于作为“文字志”的重访,对于其他形式的重访仍未引起重视。本文也正是想以“影像志”补充有关影像重访的讨论。
二、作为“影像志”的重访
随着19世纪末电影技术的发明与发展,影像技术开始成为人类学家们展开田野调查的辅助手段,用以收集、储存资料。学界普遍认为,英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哈登(Alfred Haddon)在1898年组织的“托雷斯海峡探险”考察是摄影技术应用于民族志田野调查的第一次实践。②然而,将影像应用于人类学学术研究却并未受到重视。直到20世纪30—50年代,玛格丽特·米德和格里高利·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合著完成《巴厘人的性格:照片分析》(1924)及民族志电影系列《不同文化中民族性格的形成》(1952),开创性地将照片和影像作为人类学分析的新路径来研究巴厘岛,影像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人类学领域才逐渐被接受。受米德影响,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的非州朱瓦西人(布须曼人)电影系列、蒂莫西·阿什(Timothy Asch)的雅诺玛莫人电影系列(1968—1971)也相继完成,并进一步确立了影像作为“民族志另一种形式的表征”[17]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也正在开展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除了完成文字性的调查报告外,民族学、人类学学者们也同影视工作者合作完成了16部“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的拍摄,并与文字报告一并作为调查成果留存。从20世纪80年代起,国内一些人类学者在完成自己的文字民族志的同时,陆续制作了相应的民族志影片。如庄孔韶的文字民族志《银翅》(1996)与影片《端午节》(1989)、《金翼山谷的冬至》(2017),朱晓阳的“小村故事”系列(2003,2011)③与影片《故乡》(2009)、《滇池东岸》(2013),郭净的《雪山之书》(2012)[18]与影片《卡瓦博格传奇(系列)》(1997—2003)等。总之,作为不同于文字的另一种民族志表述方式,影像民族志在不断的实践与发展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即使它们与“影像志”还有一定的区别。
(一)影像重访概述
从影像民族志的发展来看,“重访”始终伴随着20世纪50年代以来科学主义范式下民族志电影的发展,并在中西方的影像实践与发展过程中形成各具特色的几种重访类型。与“文字志”式的重访类型相似,影像重访也形成了两种重访模式:一是对自己的拍摄点进行重访;二是对他人(主要是人类学家)的田野点进行重访。
在西方,前者的代表作品有约翰·马歇尔对非洲南部朱瓦西人(布须曼人)时隔20年重访拍摄的《奈:一位昆人妇女的故事》(1978)、独立纪录片制作者菲尔·阿格兰(Phil Agland)的《雨林人家》(1987)和重访影片《巴卡:来自雨林的哭声》(2013),以及在中国拍摄的《云之南》(1993)、《上海之声》(1995)和重访影片《中国:云与梦之间》(2016)等;后者具有代表性的则是罗伯特·加德纳(Robert Gardner)重访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田野地拍摄的《努尔人》(1971)[19],以及加里·吉尔迪亚(Gary Kildea)重返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田野地拍摄的影片《特罗布里恩的板球》(1975)。
中国重访主题的影片大至分为两类模式,一是国内纪录片界较早开始对自己的拍摄对象进行重访,并以中央电视台《时间的重量——中国民间生存实录》①重访系列为代表,旨在记录时空交错下的世事变迁。其中,代表作品有孙增田的《神鹿啊,我们的神鹿》(1992,2003)、郝跃骏的《最后的马帮》(1997,2003)、梁碧波的《三节草》(1997,2003)等。第二种模式则主要集中于影视人类学界,始于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的重访拍摄。这批享誉世界的民族纪片对于中国影像民族志发展的意义重大,在上世纪末期国内掀起“文字志”重访的同时,影像重访实践也在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谭乐水的带领下在云南展开,旨在重返民纪片中涉及的6个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并以不同以往的创作手法记录社会变迁。1994年,谭乐水率先重返《西双版纳傣族农奴社会》拍摄地西双版纳曼春满,完成影片《重访曼春满》(1999)的拍摄,此后又策划“半个世纪的再追踪”系列(2006—2020)[20],拍摄完成七集系列影片:《中国民族志电影的起点》《重返班帅》《重返泸沽湖》《重返曼春满》《重返苦聪人》《走出景颇山》《重返独龙江》。受谭乐水的启发,陈学礼重返《佧佤族》(1957)所在地西盟山拍摄了《马散四章》(2008);张海则重访了《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1957)中的摩梭人,拍摄完成影片《格姆山下》(2008),后又对《独龙族》进行重访,拍摄了《独龙纪》(2010);欧阳斌则跟随谭乐水先后重访了《苦聪人》(1958)、《独龙族》,相继拍摄完成了《六搬村》(2010)和《独龙江》(2012)。这些重访的影像成果也被称为“‘重访式影像民族志”[21]。
此外,影像比文字易于理解的特点也拓展了与“分享人类学”相关的第三种类型的重访模式。与马歇尔同一时期的法国人类学家、电影导演让·鲁什(Jean Rouch)在历时性追踪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分享人类学”(a sharing anthropology)[22]的概念,倡导将影片重新带回拍摄地与拍摄对象共同观看影片,并与当地人讨论影片细节,收集反馈信息以修正影片内容,形成另一种不同形式的重访类型。在这一模式的基础上,中国进一步将其拓展为拍摄者本人或其他拍摄者将影片带回拍摄地与拍摄对象分享的实践。上世纪90年代,除了上述对大陆地区民纪片的重访放映外,在中国台湾地区,时任台北电影资料馆馆长的井迎瑞于1994年也策划了一场名为“追溯《沙鸯之钟》脚踪”的活动,将《沙鸯之钟》(1943)②这部影片带回到拍攝地点放映,反思战争与集体记忆问题。此后的2006—2013年年间,井迎瑞又借助在台南艺术大学任教时的“电影资料馆学研究”课程,每年安排学生重返拍摄地进行田野调查,除了在当地放映影像之外,还开始持续记录拍摄地点的社会变迁。[23]
总之,从时间脉络来看,早期的中国影像重访往往是后人对前人拍摄影片的再拍摄与追踪,后期才出现沿着重访思路专门进行的诸多回访与跟踪拍摄。在实践的基础上,谭乐水教授针对此类影片进一步指出,影像重访分为重访人物、事件和空间三种情况。其中,人物重访分为被拍对象和拍摄者两种视角,两者均能呈现时间线索下的变化;重访事件针对的是打破传统农业社会持续不间断的调查方式,以事件发生的时空线索进行多次的重访调查;重访空间则是将村落空间、房屋布局等从远及近的空间作为反映当地社会变迁的重要线索。③这种较为具体的重访拍摄思路也为后人的创作提供了操作指导。同时,如前所述,不同的重访类型在纪录片界和影视人类学界各有侧重,其拍摄思路也形成了一定差异。具体而言,纪录片界自本世纪初以来进行的追踪式重访拍摄,往往聚焦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某一话题来拍摄与收集素材,目的性强但视角较为单一,这种局限性在此次工作坊放映后的讨论中得到了诸多体现。而以谭乐水、郝跃骏等人为代表的影视人类学者在人类学整体性视野的指导下,对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则更倾向于“地毯式”地搜集大量素材,在对当地社会文化有较为全面认识的基础上,再针对特定话题在海量素材之中选取合适片段进行剪辑,其出发点是将影像作为一种民族志的表征。
不过,既往的影像重访研究仍主要停留于实践层面,超越影片本身进入影像知识生产过程的讨论相当匮乏。学者蔡庆同指出,影像重访并不仅仅只是在纪录片中引用或挪用历史影像,也不仅仅是回到同一个地点重拍或再拍,而是以一个旧的、特定的历史影像为蓝本,重返同一个被拍摄的对象、族群、地点或田野,借此在影像的时空与现实的时空、过去的历史影像与当下的音像纪录之间,透过差异以及比较,开启诸种对话及其反思的可能性。[24]基于“独龙族影像工作坊”这一具体经验,让我们看到了实践与反思相勾连的可能性。
(二)作为“影像志”的“独龙族影像工作坊”
在对本次工作坊进行总结时,徐菡这样讲道: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概念,就是‘影像志,通过这三天的观影,我想没有一个影片可以说是最好地、最完美地呈现出独龙族社会,而是通过不同影片的叠加,以及信息的相互交融,让我们更好地去了解一个特定的社会和特定的民族,他们的历史和文化,他们的未来和发展,这样一个‘影像志是不是能更好地和当地人展开交流和对话呢?”①
徐菡在此所提出的“影像志”概念对于理解影像重访具有重大的启发。首先,它突出了影像重返与“文字志”重返的区别;其次,“影像志”的提法也较好地体现了本次工作坊作为一种影像实践的要义。在这次工作坊展映的影片中,某一部单一的影片内容往往是独立的,但是当它们被放到一起集中展映时,则在互相补充中拓展了影片的文化意义、丰富了人物的形象层次,进而切合了“影像志”的含义。换而言之,这些影片由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主题和不同的人物故事共同构成了独龙江独龙族的“影像志”。
三天的时间里,工作坊一共放映了9部与独龙江独龙族相关的纪录影像(参见表2)。从时间上来看,其最早的拍摄于上世纪60年代,最新的素材是2021年,前后跨越60余年。并且,不同拍摄者的意图、视角等也存在较大差别。除了影像,工作坊还有一场照片展示,这些照片是拍摄者于20年前拍摄的,虽然静态的照片和动态的影像有差别,但同样可以归入“影像志”的范畴。正是因为影片之间、观看者与影片之间、观看者与观看者之间的重访,才实现了“影像志”所包含的从不同视角了解文化不同侧面的意义。
具体而言,这些影片(影像)呈现了如下几个有关重访的特点。
首先,从放映的影片来看,重访主要包含了两种类型:一为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拍摄者针对“卡雀哇”节进行拍摄的“节日志”式影片,实现了影片与影片之间的重访;二为谭乐水、张海等人以民族纪录片或是此前本人拍摄的影片为基础,时隔多年重回独龙江记录当地人、事、物的重访影片。
其次,此次工作坊虽未能到独龙江乡当地放映,但仍邀请了独龙江独龙族的村民以及部分在昆明工作的独龙族学者。从广义上来看,这些独龙族的观众都可以算作独龙族影像的拍摄对象(其中村民陈永华是影片《独龙节“卡雀瓦”》拍摄人物之一)。正因如此,在工作坊的放映空间内,所有影片几乎实现了让·鲁什所言的“分享”式重访,即所有影片与拍摄对象之间的重访,也是所有到场的影片主创者们与拍摄对象之间的重访。
进一步而言,这种重访还可以延伸至拍摄者本人对影片或照片、对拍摄地点独龙江、对拍摄对象独龙族的重访。在《最后的马帮》放映结束后,导演郝跃骏表示自己已经多年没有回看,“今天在现场重看自己也很感动”①。此外,郭建斌也在工作坊展示了20年前他在独龙江做田野调查时的照片,并发现了自己当时的田野日志与照片在内容上有许多不同,进而引发他去思考文字记录与照片记录之间的差异。正是透过这样的历史纵向性回看,能够让曾经去过独龙江、了解过独龙族的人重回“故地”,从而对当地产生更多层次和维度的新认知。
最后,本次影像工作坊本身是一次重访的实践,或许也正是因为不同影片(或影像)的集中展映,以及观影现场所激发的对话与反思,让我们看到了“独龙族影像工作坊”作为一种特定“影像志”的特殊意义。
三、“影像志”的意义
作为一种重访方法,“影像志”具有怎样的意义?本文将围绕“独龙族影像工作坊”尝试做如下讨论。
(一)“直观”
无论是纪录影像还是照片,相较于文字,更为直观。虽然此次来参加“独龙族影像工作坊”的几位村民代表均懂汉语,但是生活在独龙江的一些年纪较大的村民,他/她们是不懂汉语的。独龙族目前的文字是新创的,大多数独龙族村民也不懂。若是一种“文字志”的“重访”,当地不懂这些书写文字的人自然也无法看懂。而纪录影像和照片则不一样,虽然每个人对纪录影像和照片的解读方式不同,但他/她们是能够看懂的。在2021年12月8日下午的“影像中的独龙族传统节日”专题放映结束后,独龙族研究会会员陈建华谈到对“卡雀瓦”的感受时这样讲道:
“我们还是有一种想法,希望民族文化的东西能够通过这些影像的方式保存下来。刚才(谭乐水)说里面很多东西太具体了(指《独龙节“卡雀哇”》影片中一些仪式画面的反复出现),不太懂影像的视听语言,但是说句实话,对于独龙人来说,他看了(这些影像画面)以后就觉得是看自己的生活一样。”②
同样在2021年12月8日下午放映法国人施帝恩拍摄的《独龙节“卡雀哇”》时,作者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因为这部影片用的全是同期声,除了极少的汉语字幕,没有任何汉语解说。在整个观影过程中,来自独龙江的几位村民以及对这个仪式有所了解的人看得津津有味,而其他不懂独龙语、对这个仪式也没有具体感知的人,则有些昏昏欲睡。因此,这里所说的“直观”,更多地是从“文化持有者”的意义上来讲,如果对于某种特定的文化没有具体的认知,也同样会对“直观”感知带来影响。
(二)“时空压缩”
“独龙族影像工作坊”把不同时期的纪录影像、照片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里进行呈现,凸显了卡斯特所说的“时空压缩”。[25]同时,这也是包括纪录影像在内的电子媒介出现之后才产生的一种新的“媒介时空”,更是“文字志”“重訪”所难以企及的。此次“独龙族影像工作坊”邀请的三位村民,其中一位出现在多部影片(或照片)中,最早的在2001年年初。20多年前的他和20多年后的他同时出现在一个特定的观影空间里,对于某些观影者而言,正是现场的他把他/她们带入了纪录影像中,或者说是由他把观影者从纪录影像带回观影现场。
12月8日上午放映了20世纪60年代拍摄的民纪片《独龙族》之后,现就读于云南大学民族学专业的独龙族硕士生龙睿超这样讲道:
“通过影片了解到在我没有出生的时候,他们是怎样生活的,而我们现在的生活又是这样子的,前后有一个对比。像我们同龄人只是通过老人家口述的方式,通过他们讲的去想象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去看待他们的生活方式。就觉得以前的生活还是特别艰难的,感觉现在变化好了。现在我们本民族的文化也是渐渐地消失了,我的独龙族的同龄人,以及一些小孩子是通过观看电视自觉性地去学习汉语什么之类的,独龙语的一些比较古老的词我们就不会讲,我们就反复地问才会理解他们是什么意思。”①
从20世纪60年代到现在的60余年时间里,独龙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一种“巨变”,一方面是某些传统的迅速消逝,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某种文化(或传统)的断裂。无论上世纪60年代所拍摄的民纪片《独龙族》采取了一种什么样的视角(这通常是研究者关心的问题),但是对于当地人而言,他/她们更为关注由纪录影像所呈现出的形象,如生活环境、人物外貌(包括服饰)等,当然也包括既往的某些文化活动。
因此,“影像志”“重返”的“时空压缩”,对于当地人而言,其更为具体的意义还在于通过影像实现一种传统的延续。如前所述,因为“影像志”的“直观”,这样的延续较之“文字志”具有更重大的意义。
(三)“互释”
即便在“文字志”的“重返”中也具有“互释”的意义,但是这样一种“互释”在“影像志”中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这样一种“影像志”中的“互释”,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影片(或照片)之间的“互释”,另一方面是不同观看者之间的“互释”。下面分别说明。
1.影片之间的“互释”。在本次“独龙族影像工作坊”中,其中一个单元是三部关于“卡雀哇”的影片。这三部影片,一部是法国人施帝恩拍摄的《独龙节“卡雀哇”》,一部是云南省民族学会独龙族研究会组织拍攝的《开昌哇》,另一部是高志英教授所主持的“中国节日影像志”项目成果《中国节日影像志——卡雀哇节》。这三部影片虽然对象均是“卡雀哇”,但是具体的时空场景、对象却不同。同时,拍摄者的意图也有较大差别。因此,把这样三部影片同时放映,不同影片之间的“互释”意义就非常凸显。当然,这样一种“互释”,同样是通过观看者在对不同影片的比较中实现的。如同前文所述,对于施帝恩拍摄的那部影片,当地人看得津津有味,“局外人”则有些昏昏欲睡。对于独龙族研究会所拍摄的影片,因为有一些汉语解说(访谈),因此大多数人能够看懂;对于高志英所拍摄的《中国节日影像志——卡雀哇节》,因为有字幕,且节日的“程式化”也较为明显,其更多地是为了“展示”这个节日,因此普通观众也能看懂。正如徐菡所说“没有一个影片可以说是最好的、最完美的”,但是把这样三部影片放到一起,通过影片之间的“互释”,观看者自然能够获得一种对于“卡雀哇”的较为完整的意义。
2.观看者之间的“互释”。在本次“独龙族影像工作坊”中,每一部影片放映结束后,都会安排一个时间较为充裕的交流互动环节,这就使不同观看者之间的“互释”得以具体呈现。一方面是观看者与在场共同观影的拍摄者之间的“互释”,另一方面则是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之间的“互释”。
如前所述,在本次工作坊上,我们甚至还邀请了一些影片的拍摄者,在观影结束后与其他观众一起交流、互动。《最后的马帮》应该说是一部关于独龙江的纪录影像,无论是在纪录片圈子中还是就一般的普通观众而言,均是一部影响较大的影片。影片拍摄者郝跃骏先生也参加了影片放映,通过他的介绍以及观众的提问,观看者了解了更多的影片生产过程。这也是“互释”的一种具体体现。除了《最后的马帮》《独龙江》的导演欧阳斌,《看见看不见的独龙江》导演孙景旋也参加了观影及讨论。当看完欧阳斌所拍的《独龙江》后,几个村民心情十分沉重,因为影片中一个悲剧的主角的姐姐也在现场,在观看结束灯亮起时,大家才发现她已经泪流满面。作为旁观者,我们无法去揣测惨剧主角家属的心情,但是这样一种纪录影像的确勾起了当事人痛苦的回忆。这部纪录片在国内获得了不少奖项,甚至还在央视这样的国家级媒体上播出。这些均已超出了记录的意义。
同样在“影像中的独龙族传统节日”这一放映专题,不同民族和社会背景的人对于影片呈现的节日仪式、内容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当影片放映结束后,一名藏族学生就表示虽然这是独龙族的节日影像,却勾起了自己儿时的回忆,并从仪式中的挥剑细节引出了有关“藏边社会”的讨论,在此摘选部分讨论内容如下①:
藏族学生:“我们藏族做仪式的时候挥剑用左手,代表着驱魔,右手是对付恶魔的,然后左手是供奉神灵的。当你们用右手来挥剑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这种说法,左手和右手的作用到底有什么区别?”
陈永华:“我们独龙族自己的风俗习惯,必须要用右手,左手杀伤力很小,必须要用右手。”
藏族学生:“那么你们山神是只有一个吗?还是各种各样的都有?山神和地方神是一样的吗?”
陈永华:“不是一个。每个村都有自己的山神,有动物、植物,还有‘拉‘格蒙下面的神。”
藏族学生:“你们的‘拉是具体指山神还是神?因为我们藏语里面‘拉就是神的意思。”
陈永华:“我们叫‘拉,好几种神,专门给我们粮食的神都叫‘拉。”
郭建斌:“‘拉是一个类概念,里面还有很多具体的神,这一类神叫‘拉。”
……
藏族学生:“还有一个是‘隆达(经幡),和藏语的名字一模一样。还有祈祷的时候念的最后一句话,是吉祥的意思,和藏语相似。”
郭建斌:“康巴藏语和独龙话有很多相似的。”
陈建华:“他(指藏族学生)是指出来有很多文化的相似性,……翁乃群先生曾经说过,在喜马拉雅南麓这一带其实存在一个藏边社会,包括独龙族、尼泊尔的古隆(Gurung),还有四川那边的嘉绒,这些人实际上都属于藏边社会。他们就借鉴了自己周边的强势民族的一些信仰体系,加以改造,拿过来用。独龙族也有这个因素,比如为什么藏族是‘拉,我们也是‘拉,其实是属于同一个文化带。”
这种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无疑也是我们所说的“互释”。此外,这样一种影片之间、观看者之间,尤其是拍摄者与观看者之间的“互释”,也只有在这样的“影像志”实践中,才能更好地凸显出来。
(四)自反性
重访对于影片涉及的拍摄者与拍摄对象而言,都具有某种程度的自反性。前文已有所论述,在此再补充说明两点。在映后讨论过程中,一方面,一部影片的创作者需要接受被拍者以及其他拍摄者的提问甚至有时候也是一种质询。比如在《独龙江》映后的讨论环节,其中一个村民仅对这部影片提了一个问题,大致的意思是片中有几个村子周边村民乱扔垃圾的镜头,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因为村里会组织村民定期进行清理。导演对此做了解释,但是于村民而言,似乎并未完全释怀。再如面对冗长的影片,史凯仁、孙景旋也受到“对画面每一个镜头的功能不清楚”的批评,甚至还出现了观众误读的情况。面对如何更加立体与客观地呈现研究对象的疑问,重访也不失为一种有效路径;另一方面,作为拍摄对象的当地人跟随影片进入“压缩时空”,也让他们跳出了此前的生活空间而重新回看自己的家乡,引发其对本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以及如何发展当地旅游经济的思考。总之,借由重访,可以为影像打开诸多对话与反思的空间。
结语
本文从人类学意义上的“重访”入手,首先对“文字志”式的重访进行了简要梳理,然后对迈克爾·布洛维的“重访”理论进行了扼要说明。继而,又对“影像志”的重访进行了概述,在此基础上,结合“独龙族影像工作坊”对“影像志”重访进行了具体讨论。较之“文字志”重访,“影像志”重访具有特定的意义。同时,“影像志”重访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纪录片(或影像民族志)又有所不同。“影像志”重访,具有“直观”“时空压缩”“互释”“自反性”等意义。同时,“影像志”重访强调把影像带回原文化中,以实现更好地传承、延续文化,这也是一般意义上的纪录影像难以做到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独龙族影像工作坊”仅仅是我们的一种尝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影像志”的概念。这一概念更为丰富、完整的意义,还有待更多类似的实践不断来完善。同时,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这样一种“影像志”实践或许也有需要不断完善的地方。
参考文献:
[1][5][澳]德里克·弗里曼.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M].夏循祥,徐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0,258.
[2]Weiner,Annette B.Women of Value,Men of Renown:New Perspectives in Trobriand Exchange[M].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76.
[3]Lynd,Robert S.Knowledge for What:The Place of Social Science in American Culture[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39.
[4]Firth,Raymond.We,the Tikopia:A Sociological Study of Kinship in Primitive Polynesia[M].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Ltd,1936.
[6]潘守永.重返中国人类学的“古典时代”——重访台头[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02):20-26.
[7]庄孔韶,编.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8]张宏明.土地象征——禄村再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9]梁永佳.地域的等级——一个大理村镇的仪式与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0]褚建芳.人神之间——云南芒市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生活、经济伦理与等级秩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1][12]潘乃谷,王铭铭编.重归“魁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52-191,159.
[13]费孝通.江村经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7-9.
[14][15]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36.
[16]Burawoy M.Revisits:An outline of a theory of reflexive ethnography[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03: 645-679.
[17][19]徐菡.西方民族志电影经典:人类学、电影与知识生产[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3,122-125,237-238,235.
[18]郭净.雪山之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
[20]郭净,徐菡,徐何珊编.云南纪录影像口述史(第一卷)[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68-69.
[21]王磊.对民纪片的“重访式”影像民族志研究[D].昆明:云南艺术学院,2020.
[22][美]保罗·霍金斯,编.影视人类学原理[M].王筑生,等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181.
[23]井迎瑞.重返作为方法:影片《沙鸯之钟》的观看之道[ J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4(01):9-14.
[24]蔡庆同.“重返”作为纪录的方法及其反思:以中国1950年代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为例[ J ].南艺学报,2020(20):63-84.
[25][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531.
——独龙族纹面女
——人间天堂独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