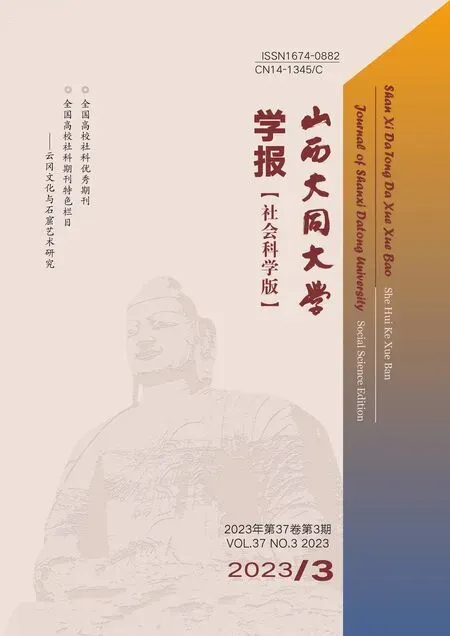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自然美学观
宦 燃,宫文华
(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论诗三十首》是元好问以七言绝句形式写成的诗歌史,涵盖了魏晋至两宋千余载间的名诗人及诗歌流派。按论述内容的时代划分,其中第一至七首的主要线索在于魏晋至隋代的名诗人,并对魏晋文学作出了极高的评价,由此确立了整个《论诗三十首》的审美风向标;第八至二十首的主要线索在于唐代,以推尊唐人诗歌来讨论今人应当如何艺术构思;第二十一至三十首则在于较为晚近的宋代,批评了因循蹈袭、过分雕琢的时弊。
郭绍虞曾作出过“论诗重内容而不重形式,重自然而不重刻琢”[1](P59)的评价,精准地点出了元好问诗歌美学的核心诉求——自然。而元好问的“自然”追求具有多重蕴涵,既是对艺术创造之本源问题的思索,也是对慷慨豪壮之审美风格的追求,还对如何创作进行了阐释。
一、诗歌从“自然”中得来
“所谓自然,有天地之自然,有人心之自然。”[2]“天地之自然”主要指审美对象,包含了两方面:一是山花海树、烟石云霞等自然景观,一是有形的楼台街市与无形的社会历史、时代精神等组成的人文景观。“人心之自然”则要复杂幽微且不可明见,主要指审美意识对天地自然“照亮”后产生的思想、情感等。诗歌等艺术作品即从这两个“自然”的相互交融中得来,生成于人与自然间的对话中。
(一)取材于“天地之自然”以《论诗三十首》本身为例,其生成过程本身就受到了元代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与青年元好问个人经历等因素的影响。
从时代背景来看,《论诗三十首》作于兴定元年(1217 年),元好问时年二十八岁,因避战乱而客居河南三乡。此时正当金元政权更迭之时,处于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不断冲突与融合的阶段,过往的社会秩序被破坏而新的规则尚未成形,因此,总体看来“元代文人没有唐代文人那样强烈的功名意识,也没有宋代文人那样沉重的历史使命意识。在元代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多数文人愿意自然地活着。诗人自然地写诗,追求诗之自然。”[2]
在这样崇尚自然率真的文化氛围中,兴定元年在野的文人士大夫,仍能够处于相对平和的环境中,摆在他们面前的最大问题尚且不是国家兴亡,而是诗歌如何摆脱僵局继续向前发展。是以郭绍虞认为《论诗三十首》是“就诗论诗,非由激愤,更无寄托”,[1](P57)是纯粹的、探讨诗学理论的作品。
其次,《论诗三十首》有其现世的辩论对象——江西诗派。诗从先秦两汉萌芽,成长于魏晋,盛放于唐,发展到宋代苏轼、黄庭坚之后,整个诗坛被江西诗派把持,复古有余而推新较少,更缺少欧阳修、苏轼那样的盟主式大家,长此以往,诗坛难免陷入困局。如何推陈出新是文人士大夫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元好问指出当时诗坛上最大的困境是失真,诗坛之弊端在于因片面重视形式且拘泥于古人而缺少生命力:“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1](P82)
在元好问看来,江西后学模仿杜甫、李商隐等人却只得皮相不得骨髓,学到的不是杜子美的“古雅”李义山的“精纯”,而是他们的语言形式,乃至于诗中填充的也是古人的情感思想,失去了当代精神的模仿只是在为古人发声,不是在为自己、为现世发声。再者,古人已经有了投入真情实感的作品,今人为古人发声没有必要。若要推动诗歌发展,则不能继续走江西诗派的路。
追求自然率真的时代精神与诗坛时弊共同组成了元好问所生存世界中的人文社会景观,是他在创作《论诗三十首》之时所见之景,是创作取材的“天地之自然”,无论其中寄寓的情感与志趣如何取舍,它们都不得不根植于此。
(二)成全于“人心之自然”在《论诗三十首》中,元好问本人也强调从“天地之自然”中取材:“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郭绍虞认为“‘亲到长安’,与近人所谓‘体验生活’,大有不同。近人所指,重在社会生活之现实生活,而元氏所言,只是自然界之景色而已。故其所论与主张模拟,仅能暗中摸索者相较,固高一着,而由于脱离社会生活,亦只能走上神韵一路而已。”[1](P67)
一方面,此诗是对脱离实际之模仿的批评。且不说在交通条件有限的时代,囿于书斋馆阁的诗人们鲜少真正到得了长安,亲眼见过、亲身感受过“秦川景”,所谓“暗中摸索”一定程度上是脱离了对现实景物风光之体验的,如若模仿前人之作难免陷入拾人牙慧、为人代言的境地。或者,即便亲眼见过景,若只是模仿眼中风光,将所见之景原原本本复制、再现出来,那也是未得神韵的死物。因为进行这两种模仿之时,创造者本人的情感、思绪并未得到充分释放,缺少了“人心之自然”也就难以令人产生美感。
另一方面,元好问追求艺术创作中的“神”,从艺术构思的角度来讲,此诗重心当在“眼处心生”四字上,诗歌要有神韵,就需要适当的想象与虚构。至于作者本人是否“亲到长安”并非关键问题。只有从眼前之物上出发,感荡心灵、激发出真情实感,再选择最适合的物象去表达出来才能真正令诗歌传神。正如刘勰讨论如何谋篇布局:“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3](P493)
诗人构思之时,精神的活动极度自由、遥无边际,时间与空间的距离都不能限制诗人的精神,千秋百代的人物、事件和远近风物都摆在诗人眼前,供诗人驱策剪裁,而后择其精粹来表现情志。这就是想象的魅力。想象力自由驰骋之时,难免会意造出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即便是未曾亲身到过长安,只要适于表现“人心之自然”,以之入诗未尝不可。
再者,“长安”在唐代不仅是一座都城,在众多文人墨客笔力加持下,已然成为一种成熟的审美意象,如同其他意象(如烟、柳、灞陵、桃花源等)一样成了某种象征性的精神符号,经过作者筛查之后落于笔端,就是虚构。恰到好处的虚构恰恰才能做到逼真。如科林伍德所说:“老练的画家才真正懂得怎样做到逼真,即他知道,他必须通过恰到好处的夸张,才能产生情感上正确的逼真。”[4](P54)
总的来说,好的诗歌不仅需要从天地自然中取材,更是需要经过人心中审美意识之交融才能生成。创作者应当投入到真实而广阔的社会生活与自然风景中去,注重真实体验。
二、慷慨真挚的审美价值取向
古人论诗、今人论文艺作品,都不免要强调其一方面宣泄作者内心思想情感与志趣,另一方面也陶冶读者情操、影响人的性情。如:“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3](P65)
诗歌作为一种艺术,是人类情感存储的冰箱;但是唯独有生命力的情感才能长远保鲜,也使得冰箱本身与时俱进、延长冰箱的使用寿命。以作品为媒介,某种性情可以轻易地超越时空界限,对人产生影响。故而作者在拥有了大量的材料之后,梳理材料与作出取舍时不得不慎重对待且有所倾向。
《论诗三十首》前七首俨然将魏晋审美取向作为标杆。宗白华说,魏晋时代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倾向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哲学的美。”[5](P209)因此,元好问也推崇在诗歌等作品中表现慷慨多气、大胆书写胸中真意的美。
(一)用情须慷慨豪放 首先,元好问强调诗歌中要寄托有生命力的、积极向上的情感:
慷慨悲歌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洲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1](P63)
这一首诗在第一部分最后,总结整个魏晋南北朝的风流为“慷慨悲歌”与“天然”。魏晋时代的总体特点是乱与篡,是真正礼崩乐坏的时代,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王公贵族,都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但是,生存方面的危机反而催生出了豪情与希望之光,使人有了向上的生命力。
同是胸中有块垒,阮籍与孟郊的表现全然不同:
纵横诗笔见高情,何物能浇块垒平?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1](P62)
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在元龙百尺楼。[1](P71)
阮籍八十二首《咏怀》,旨意遥深,心中有怨而不至于乱,文辞典雅自然;而孟郊“食芥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1](P71)心怀不如阮籍开阔,用情用语皆苦涩,有山穷水尽的极端压抑感,却无柳暗花明的生命感,故而不为元好问推崇。
元好问崇尚自然、反对过分的人为。就人生境遇而言,这里的自然又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山林”,一是“衣冠”。
出处殊涂听所安,山林何得贱衣冠。华歆一掷金随重,大是渠侬被眼谩。[1](P69)
看待文章以山林隐逸为高古超尘,以热衷功名利禄为不登大雅之堂,是不够客观公正的。“自然物的审美价值是有高低之分的。这种审美价值高低的区分,不仅与自然风景本身的特性有关,而且和人的审美意识以及审美活动的具体情境有关。”[6](P187)人各有志趣取向,无论是居于庙堂之高,还是处于江湖之远,只要艺术创作是出于真情实感就是语出天然的优秀作品。山水清音是自然,追求功名利禄也是自然,都是有生命力的,二者并无高下之分。
(二)用情须出自真心 作品是由人创造出来的,其中的情感也是因人而生、为人赏玩品评而存在的,文字导向的应是一个绝假纯真的审美意象世界。故而元好问强调诗歌创作时投入的情感要足够真挚:
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
七言绝句言简意赅,给后来的读者们留下了大片的空白点与不定式,一般从贬斥潘岳人不如文的角度来解读:强调诗歌或者说文学艺术应当与作者的道德修养挂钩,有什么样的人品就应当有什么样的文章,如果作者的人品有缺陷,他的文章也就是虚伪的,失真的,是不自然的,因而就不值得提倡。太康诗人潘岳的《闲居赋》表达林泉高卧的隐逸之思,潘岳的实际作为却是以谄媚之姿侍奉权臣贾谧。言语上的高洁与德行上的卑下形成巨大的反差,同宰予昼寝一样,其人其作是完全不可取并且要遭到严厉批评的。
然而这种解读有自相矛盾之处,元好问用了“高情”一词形容《闲居赋》,反而是高度肯定了其艺术造诣。再来看元好问对潘岳的态度:第一部分(第一至七首),元好问自任“诗中疏凿手”,对曹植、刘桢、刘琨、张华、陶渊明、阮籍等人的诗歌以及民歌《敕勒歌》作出了极高的评价。潘岳夹在阮籍与《敕勒歌》之间,若说前后皆是赞扬,唯独在这里贬斥潘岳,未免前后衔接不当,也与整体上的赞扬基调不符。
再看《论诗三十首》第九首谈及潘岳:
斗靡夸多费览观,陆文犹恨冗于潘。心声只要传心了,布谷澜翻可是难。[1](P64)
显见此诗主旨在于批判形式上的过度争奇斗艳,贬斥的是文辞繁复、以辞害意之弊,甚至于陆机在文辞修饰上所花的工夫比潘岳还要多。因此,仅就《论诗三十首》而言,元好问对潘岳的态度并不全是批判,甚至可以说有一部分的肯定。
品评艺术作品不等于品评作者个人的道德修养,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惟有作品才使艺术家以一位艺术大师的身份出现。艺术家是作品的本源。作品是艺术家的本源。彼此不可或缺。但任何一方都不能全部包含了另一方。”“从作品中浮现出来的被创作存在并不意味着,根据作品就可以发现它出自某个艺术大师之手。创作品不可作为某位高手的成就来证明,其他完成者也不能因此被提升到公众声望中去。要公布出来的并不是姓名不详的作者。”[7](P1-57)
只要作者在创作时确实是真情流露,那么整个作品中的情感就是自然的、符合审美规律的。无论是作者本人还是作品本身,都只是真理澄明于读者心中的媒介,它们不是真理或某种境界本身,不具备普遍、永恒的特征。哪怕是作者本人,也没有办法永远停留在最接近真理的那一刹那。当作者本人的认知因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发生变化之后,文字材料作为相对稳固的媒介却并未发生较大的变化,仍旧为后世读者提供着一条通往世界本真面貌的曲折之路。
三、“锻炼而归于自然”:艺术创造的手段
在回答了诗歌艺术从何而来、审美价值为何的问题之后,还面临着具体的创作如何进行的问题。《论诗三十首》在事实上给出了艺术创造中应“锻炼而归于自然”[8]的回答,体现在学古人而自出新词与着意人工而不露雕琢痕迹两方面。
(一)师法古人而超越古人 第一方面,元好问虽极力避免因循蹈袭、拾人牙慧,但也不是说从此把古人之作都丢开来,而是说要做到学习古人但不拘泥于古人,并在学习过程中进行符合时代精神的创新。
针对宋人刻意为诗、脱离现实的现象,元好问作了不少反思与批评:
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1](P63)
斗靡夸多费览观,陆文犹恨冗于潘。[1](P64)
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趺。[1](P65)
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1](P67)
切响浮声发巧深,研摩虽苦果何心?浪翁水乐无宫徵,自是云山韶濩音。[1](P70)
宋初诗坛承接晚唐余绪,偏爱华美艳丽的“西昆体”、引经据典的“台阁体”,正如唐初诗坛承续齐梁时代文辞繁缛富丽、讲究声韵格律的作风,全然未脱前人之形,仍旧处于“暗中摸索”的失真阶段,并没有跟上世事变化的脚步。直到陈子昂的出现,才扫清了颓靡、铺张做派,重现英豪阔大之风。
宋人模仿李商隐、模仿杜甫,也只在字句推敲、音律是否合规、叙事是否用典上下功夫,并没有认识到李商隐的朦胧隐晦与其身处党争夹缝的现实相关,而杜甫历经唐由盛转衰,早已将自身的学识教养同丰富的现实生活融为一体,所以杜甫的排律、用典是事实上的有来处、知去处,两人的风格是筑基在深刻的现实基础之上的。但后人将他们神化,只着意模仿古人的经历、用他们的事迹,却不投入到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为自己的真实体验发声;也无意去超越古人的成就,难免又陷入执着于文辞、声律和典故的僵局。
其次,对作品而言,他们的最终完成需要读者的介入。每个作者在创作时都为自己设定了隐含读者,没有哪一位盼望自己的作品沦落到故纸堆中无人问津。但是,对于人类而言,人事变迁过于迅速,眼下的通俗易懂很容易就变成了后世的佶屈聱牙。因此,每个时代都需要为本代发声的诗人,要求这些诗人有广博的学识与见闻,又要不拘泥于古人的权威之言,能在不断地学习与经历之中将时代的精神风貌融入到作品中去,为作品注入生命力。
(二)超越人工,回归自然 在诗歌的语言文字层面上,元好问追求质朴古雅,严厉批评雕饰繁缛的风气。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拒绝人工雕琢,而是意味着他在追求雕琢效果的浑然天成。
首先,元好问的论诗从建安诗人开始说起,并以他们为标准。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评价建安众人: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3](P513)
建安诗人是一个群体,他们有两大共同点:一是有丰富的社会活动,文人之间、文人与王权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往来,文治武功等现世的成就将文人们刺激得心潮澎湃,因而他们表现得情感真挚而热切;二是文人们表现情感的手段,不在细密纤巧上下功夫,而着力于将事件或者风景描绘得清楚明白,不需要纤毫毕现的完美写真,只需要恰到好处地配合真情涌现。元好问说:“心声只要传心了,布谷澜翻可是难。”[1](P67)即是此意。
其次,元好问对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炼字用语极为推崇:
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自注:“柳子厚,唐之谢灵运;陶渊明,晋之白乐天。”)[1](P60)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1](P84)
这是说谢灵运凭借“池塘生春草”五个字便能在可以预见的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笔。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陶渊明与白居易都因以明白晓畅的语言写深情著称,谢灵运与柳宗元因写活了山水而流芳。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以自然风物入诗,不仅有深情而且还能将其用平白质朴但不失风雅的语言表现出来。以景语作情语且不露雕琢痕迹,简单的语言中蕴含了无限的意味,哪怕经历了无数的岁月变迁也能让后代读者品读出原本的意蕴。
究其根源,还在此句塑造了一个将自然景观与人融为一体的意象世界,这“是有生命的世界,是人在其中生存的生活世界,是人与万物一体的世界,是充满了意味和情趣的人生世界。”[9]此中人与物是平等对话的主体,且每一位读者都能亲身体验到这对话的过程,感受到诗意生成的过程。而这一切玄妙的体验都要归功于一个“生”字,正因为谢灵运选择了这个字,才能真正实现了风格上冲淡自然而神存富贵,最大限度地表现了人情与物景的和谐一致,使人工雕琢的痕迹潜藏起来,把一个浑成的自然世界摆在人们眼前。这便是超越人工、重新回归自然的魅力。
总的来说,优秀的诗歌应当情感真挚自然而寄寓深远,当情感趋于饱满时,不露痕迹地将情绪整合成文,文辞音律方面要明白晓畅。如此才能避免拘忌声病、过分关心辞采之华美,令情志与文采结合地恰到好处、达到圆融浑成、无雕琢痕迹的自然之境。
四、结语
身处后工业时代,艺术生产逐渐像物质资料生产一样有了相当完备的产业模式,作品中“人”的含量逐步降低,艺术世界能够提供的超脱感与自由感趋于不足。因此,重提“自然”是有必要的:它能在熟套的机械复制品之外带来清新的生机与活力,还人所生存的世界以本来面貌。甚至于重新肯定人自身的价值、艺术作品的价值及真理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