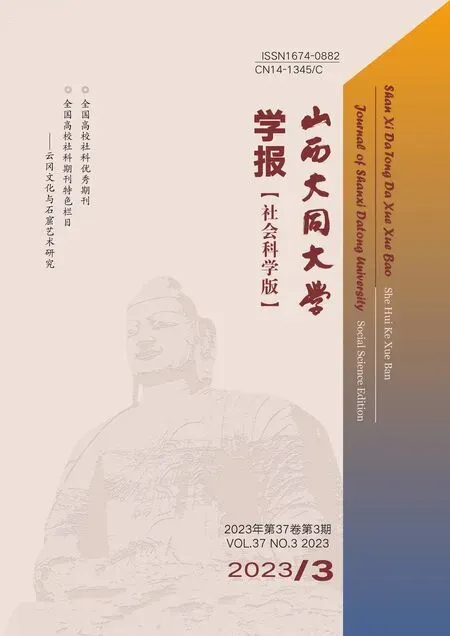元好问海棠诗的审美特质
周冰潇,裴兴荣
(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元好问为金元文学史上的名家,其诗歌在继承前贤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为历代学者所重视。其海棠诗虽然数量不多,但颇具特色,在内容上或描花形,传花神,或抒情,或言志;在写作上运用比拟、对比、用典等表现手法,想象奇特丰富,颇具艺术魅力。
海棠,蔷薇科,落叶乔木,春天四至五月开花,作为观赏花卉,是由海外流传而来的品种。[1](P58)在汉代,海棠因其花开似锦、绮丽风雅而进入宫廷内苑。在唐代,海棠的种植范围扩大,栽培技术改进,观赏价值进一步提升,文学书写更加普遍。在唐德宗贞元年间,贾耽编著《百花谱》一书,开始使用“海棠”之名,并美誉其为“花中神仙”,然而此书今已亡佚。两宋时期,海棠书写达到顶峰,出现了《海棠记》和《海棠谱》等专门书写海棠的专著。其中,《海棠记》为沈立著,明代时已散佚,《海棠谱》为陈思所撰,版本较多,且此书收入《海棠记》部分内容,杂取诸家并汇次唐以来咏海棠诗句,为研究海棠的重要史料。[2](P127)海棠诗的创作也迎来了巅峰时刻,宋代帝王如宋太宗、宋真宗、宋光宗等以及著名文人王安石、苏轼、李清照、陆游、杨万里等皆有脍炙人口的咏海棠名篇传世。至金元时期,人们对海棠的喜爱只增不减。元好问的海棠诗极具个人特色,自然流畅,构思奇特,融情于景,流露出借花自慰、物我一体的情绪。
一、自然美:对海棠花叶的描绘
元好问生于秀容(今山西忻州),一生历经山西、山东、河南、河北、陕西等地,其海棠诗多创作于观赏海棠的直接经验,着重描绘海棠花叶。海棠花色多变,逸态嫣然,其中“木本春海棠”和“草本秋海棠”是元好问海棠诗的主要描绘对象。此类诗真切自然、韵致超绝。
(一)红艳夺目,层次多变《全芳备祖·海棠》载:“其花五出,初则极红,如胭脂点点;及开则渐成缬晕,至落则若宿妆淡粉。”[3]诗人对海棠颜色的书写,一方面为目遇成色的体验式创作,表达对海棠花蕾的偏爱,另一方面较多对前人海棠诗的借鉴,其中尤以苏轼为最,多体现为对海棠花色层次变化的刻画及“红妆”在咏花诗中的使用。
红色,在元好问诗作中,是海棠的代表色。诗人从整体入手,以一“红”字对海棠进行直接描绘,用字俭省,如《俳体雪香亭杂咏十五首·一二》:“苦才多思是春风,偏近骚人怅望中。啼尽杜鹃枝上血,海棠明日更应红。”[4](P631)诗人将海棠花色与杜鹃之血相提并论,用“红”字直接描绘海棠,突出其花色之艳。
《同儿辈赋未开海棠二首·其一》:“翠叶轻笼豆颗匀,胭脂浓抹蜡痕新。殷勤留着花梢露,滴下生红可惜春。”[4](P1657)此诗为元好问晚年返乡后与家中子侄辈欢聚时所作,描绘了一幅生机勃勃的春日海棠花蕾图,绘形绘色,生动如画。前两句着重描绘海棠花蕾之形色,第一句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从外形入手,将花蕾比作颗粒分明的“豆子”,第二句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从花色入手,将花蕾比作上了妆的女子,以“胭脂浓抹”暗写花蕾之红。后两句“滴下生红”四字,运用夸张的手法,花蕾将花梢的“露水”都染红了,极力描摹海棠花蕾颗颗伫立枝头的艳丽景象。
另外,此诗还描绘了海棠花色的层次变化。海棠“花朵数簇生呈伞形总状花序,花两性,花蕾初带红色,开放时粉红色或白色”[2](P76)。“胭脂浓抹蜡痕新”[4](P1657)一句中,“浓抹”突出颜色之深,为大红,“蜡痕新”突出颜色之浅,为淡红,深浅变化,层次分明。关于海棠花色的层次变化,苏轼也曾对其进行着重描绘,如诗歌《寓居定慧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士人不知贵也》:“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5](P1036)将海棠拟人化,通过书写饮酒后,红晕自“朱唇”向“双颊”逐渐晕染的过程,喻指海棠花色的层层变化,极富动态美感。
以“红妆”喻指艳丽的花卉,常常出现于咏荷花、梅花、牡丹等诗歌中。元好问模仿苏轼,将“红妆”引入诗中,侧重对海棠艳丽花色进行描绘。苏轼咏海棠名篇《海棠·东风袅袅泛崇光》:“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濛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5](P1186)描绘了夜间海棠,开篇从视觉和嗅觉写起,后两句“只恐”二字,写出了苏轼对赏花无果的担忧心理,“烧”和“照”为动作描写,表达了诗人对海棠花的喜爱和怜惜之情。
在元好问咏花诗中,“红妆”一共出现三次,其中两处皆化用了苏轼此首海棠诗。《同梅溪赋秋日海棠二章·其二》:“翠袖红妆又一新,秋风秋露发清真。丹青写入梅溪笔,桃李从今不算春。”[4](P1887)为元好问与友人共赏秋日海棠时所作。诗人着眼于海棠红艳的花色,将海棠拟人化,以“红妆”喻写海棠花色艳丽,“又一新”加深对海棠花色的渲染,盛开的桃李较之友人所绘的海棠大为逊色。《杏花落后分韵得归字》:“獭髓能医病颊肥,鸾胶无那片红飞。残阳淡淡不肯下,流水溶溶何处归。煮酒青林寒食过,明妆高烛赏心违。写生正有徐熙在,汉苑招魂果是非。”[4](P714)此诗颈联连用两个典故,前半句出自《三国演义》中的“青梅煮酒论英雄”,交代寒食节令,后半句化用苏轼诗“故烧高烛照红妆”[5](P1186)句,借咏海棠之诗句咏赞杏花,别出新意。《杏花杂诗十三首·其二》:“露华浥浥泛晴光,睡足东风倚绿窗。试遣红妆映银烛,湘桃争合伴仙郎。”[4](P577)其中所谓“红妆映银烛”同样化用了苏轼诗句。可见苏轼海棠诗对元好问咏花诗之影响。
(二)花叶和谐,逸态嫣然 元好问在描写海棠花时,给予海棠叶子较多关注,构思精巧,婉言微词。诗人往往着眼于形色两个角度将海棠的花叶进行对比书写。
《同儿辈赋未开海棠二首·其二》“枝间新绿一重重,小蕾深藏数点红。爱心芳心莫轻吐,且教桃李闹春风。”[4](P1657)前两句运用点面结合的手法,先写海棠绿叶重重,再写这片新绿中隐藏着的点点红蕾。“重重”写出了绿叶的繁茂,“数点”写出了花蕾的小而密,两者相互映衬,形成了一幅姿态和谐的画卷。“藏”字使用了拟人手法,既写出了花蕾含苞待放之态,又体现了诗人观察之细致,表达了诗人对海棠的喜爱之情。
借代修辞的使用在此诗中较为突出,以“红”代“花蕾”,用“绿”代“新叶”,与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中的“应是绿肥红瘦”[6]有异曲同工之妙。李清照运用借代和对比的修辞手法,形象生动地描绘雨后海棠之形态。元好问描摹海棠花叶,同样大量运用借代和对比,如“翠袖红妆又一新,秋风秋露发清真。”[4](P1887)诗人以“翠袖”代“海棠叶”,以“红妆”代“海棠花”,将海棠喻为“红妆”佳人,绿叶则是佳人华裳之“翠袖”。七绝组诗《赋瓶中杂花七首·其四》:“红抹兰膏绿染衣,绿娇红小两相宜。花边剩有清香在,木石痴儿自不知。”[4](P1007)语言凝练,虽未提花叶二字,但仅以“绿娇红小”便清晰明了地刻画出海棠花叶各自之情状。由此可见,诗人对海棠之喜爱,对自然观照之真切。
值得关注的是,元好问对海棠颜色的书写与其偏好的海棠形态密切相关。诗人主要描写了两种状态下的海棠:一种是全开海棠,另一种是未开海棠。全开海棠,花开似锦。海棠花象征着美好春天,在“海棠一株春一国,燕燕莺莺作寒食”[4](P952)中,“春”字点出了海棠的时令,一株海棠便渲染了一国春色,以点带面,以少胜多,凸显了海棠花繁茂密集、色彩艳丽的特点。未开海棠,即海棠花蕾,是元好问海棠诗的主要描写对象。诗中常常以“红点”“豆颗匀”“数点红”等来描绘海棠的花苞,将其比作豆子,于颜色和形状的配合处集中笔墨,具体可感,如在眼前。
二、情韵美:对海棠意象的深化
元好问一生多坎坷磨难,所作咏花诗较少纯粹的工笔刻画。其海棠诗亦是如此,往往以己观物,情韵流动。诗人从自身经历出发,赋予海棠多种象征意蕴,其中亡国之痛、飘零之苦和对女性的赞美之情三个方面最为突出。
(一)表达亡国之痛 海棠因其艳美高雅、寓意美好,多种植于皇家园林之中,并且常与玉兰、牡丹、桂花相搭配,寓意“玉堂富贵”(“堂”与“棠”同音)。故历代文人多以海棠锦簇喻皇家园林之热闹华贵,如“海棠一株春一国……千古万古开元日”[4](P952)中,诗人将海棠与开元盛世相联系,以花开灿烂喻指盛世之景。
此外,元好问在海棠诗中丰富了海棠意象,将娇艳鲜活的海棠与荒凉颓败的汴京故宫相联系,反衬国家将亡的悲凉,海棠也因此染上了一抹凄凉的色彩。
天兴二年(1233)四月两宫北迁后,元好问至汴京故宫,内心悲痛,于金国灭亡之际,作七绝组诗《俳体雪香亭杂咏十五首》。[7](P174)其中第十二首云:“苦才多思是春风,偏近骚人怅望中。啼尽杜鹃枝上血,海棠明日更应红。”[4](P631)诗人以“怅望”二字抒发内心慨叹,引用“杜鹃啼血”的典故,并选取“海棠”这一物象,赋予其哀痛之情。诗人想象海棠染上杜鹃之血明日花开应该愈发灿烂,那时的汴京皇宫除了这些花木大概已经一片荒凉了吧。此诗虚实结合,以乐景写哀情,抒发诗人内心的悲痛之情。
(二)抒发飘零之苦“落花”因其凋零、委落枝头,给人一种短暂、忧伤的感觉,是历代诗人偏爱的借物抒情的寄托物。“落花”作为中国古典诗词中常见的意象之一,历代文人常常借以感慨美好景物易逝,抒发伤春之情。如孟浩然《春晓》:“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8]晏殊《浣溪沙》:“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9]秦观《画堂春》:“落红铺径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杏园憔悴杜鹃啼,无奈春归。”[9]南宋曹豳《春暮》:“门外无人问落花,绿阴冉冉遍天涯。”[10](P54)等等。
元好问在海棠诗中,不仅以落花纷飞喻美景消逝,而且通过对家乡春日花事的书写,表达对故乡的热爱及思念之情,寄寓人生漂泊之苦。
七绝组诗《赋瓶中杂花七首》创作于诗人晚年奔波时期,叙写了元好问归乡后于忻州读书山赏花插花的日常生活。组诗涉及海棠、杏花、丁香、桃花、兔葵等多种花卉,描绘了花卉的颜色、形态、气味、盛开时间等。在经历了亡国、好友及家人相继逝世后,诗人晚年愈发偏好以灿烂盛景来驱散生命中的悲凉静寂,组诗第一首:“老眼惊看节物新,今年更与酒杯亲。东山一道花如绣,从此他乡不是春。”[4](P1007)直抒胸臆,奠定了组诗的感情基调。开篇的“老眼”及“惊”字写出了诗人漂泊大半生,晚年目睹家乡春色的激动心情。后两句在描绘家乡读书山花团锦簇的同时,将家乡春日与以往所游之地作比,突出“他乡不是春”,衬托家乡春日之美。此诗借景抒情,饱含诗人的思乡之情与漂泊之苦。
组诗第三首和第七首着重对海棠进行描绘。《赋瓶中杂花七首·其三》:“生红点点弄娇妍,半拆花房更可怜。传语春风好将护,莫教容易作银钱。”[4](P1007)《赋瓶中杂花七首·其七》:“古铜瓶子满芳枝,裁剪春风入小诗。看看海棠如有语,杏花也到退房时。”[4](P1007)第三首中,前两句通过“生红点点”和“半拆花房”交代了此时的海棠为未开海棠,颜色鲜艳、形态娇小。“可怜”即可爱,表达对海棠花蕾的喜爱之情。花卉、春风本是自然之物,在诗人的笔下“无情之物变为有情”。[4]后半句中,诗人忧心海棠花期短暂,将“春风”拟人化,嘱咐其用心看护花蕾,延长花期,莫让海棠过早凋谢,随风飘飞,如同银钱般四处辗转,透出人生如寄之慨。第七首围绕花器“古铜瓶子”写海棠与杏花的花期交错。前两句描绘了诗人剪裁花枝,插满花瓶的场景。诗人称“裁剪花枝”为“裁剪春风”,语言极具诗意,体现插花之趣,为乐景。后两句是诗歌的重点,杏花较海棠花期早,故海棠将开预示着杏花的凋零。众多花卉聚于一瓶之中,鲜艳与凋零分外鲜明,诗人的视角由“满芳枝”转移到“退房时”,为哀景。在诗人对花期关注的视角下,乐景变哀景,蕴含伤春之情。
另外,落花意象在诗人的其他咏花诗中亦时时出现,如《纪子正杏园燕集》:“落花着衣红缤纷,四坐惨淡伤精魂。花开花落十日耳,对花不饮花应嗔。”[4](P711)描绘了诗人在欢乐的聚会中,因落花纷飞而触发的黯然伤魂的感伤之情,表达了诗人对自然美景转瞬即逝的惋惜之情。《荆棘中杏花》:“阿娇新宠贮金屋,明妃远嫁愁清笳。落花萦帘拂床席,亦有飘泊沾泥沙。”[4](P430)前两句连用金屋藏娇典和明妃远嫁典,后两句揭示并对比了落花的两种遭遇:与竹帘床席为伴或漂泊沾污于泥沙之中,并将之与阿娇和明妃对应,既表达其对落花“飘泊沾泥沙”的怜惜之情,又抒发其对明妃远嫁的同情之意。
(三)赞美女性之意 在历代诗词中,花与女子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两者交相辉映,光彩照人。元好问的海棠诗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加以创新,赋予海棠更加丰富的女性意象,表达其对海棠的喜爱之情及对所咏女子的赞美之意。
以海棠喻指女子,始于“海棠春睡”之典,其中“海棠”专指杨玉环。典故出自惠洪《冷斋夜话》,此书载《太真外传》事,“上皇登沉香亭,召太真妃,于时卯醉未醒,命力士使侍儿扶掖而至,妃子醉颜残妆,鬓乱钗横,不能再拜,上皇笑曰,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11](P11)苏轼《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林深雾暗晓光迟,日暖风轻春睡足。”[5](P1036)使用“海棠春睡”典,夸赞海棠风姿之盛。元好问受其影响,暗用此典,作《题商孟卿家明皇合曲图》:“海棠一株春一国,燕燕莺莺作寒食,千古万古开元日。三郎搦管仰面吹,天公大笑嗔不得。宁王天人玉不如,番绰乐句不可无。宫腰不案羽衣谱,疾舞底用牧猪奴。风声水声閟清都,梦中令人羡华胥。何时却并宫墙听,恨不将身作李谟。”[4](P952)商挺,字孟卿,曾与元好问、杨奂一同北走游历,元好问与商家交往甚密,曾为其父商平叔撰写墓志。此诗作于诗人羁管山东期间初至东平(今山东东平)商挺家。[7]《明皇合曲图》为商家所藏之画,元好问观之,击节称叹,遂作此诗。此诗虚实结合,描绘春日美景下明皇合曲的奏乐场景。诗人匠心独妙,于百花中选取“海棠”,以之起兴,美人与美景相伴,暗写宴会的热闹场面,突出唐朝鼎盛时期“开元盛世”的繁华。首句暗用“海棠春睡”典故,以海棠喻指杨玉环,赞其百媚千娇,与后文的“三郎”李隆基前后呼应,暗写两人爱情。题诗与画作内容相谐,突出体现了元诗对苏诗的继承和创新。
苏轼之后,海棠意象进一步扩大,宋人多以海棠之美象征世间一切女子。元好问作为爱花咏花之人,不仅继承了前代海棠诗的美人意象,而且丰富了宋人对海棠的书写,侧重于挖掘女子之神态与海棠的相似之处。《同漕司诸人赋红梨花二首·其二》:“琼枝玉蕊静年芳,知是何人与点妆。可道海棠羞欲死,能红能白更能香。”[4](P1198)此诗为蒙古乃马真后四年(1245)元好问在汴京(今河南开封)所作,“漕司,官名。宋置诸道转运使,管催征赋税,出纳钱粮,办理上供及漕运等事。”[7]此诗前两句以美玉喻写海棠的枝叶花蕊,称海棠之色为“点妆”之故。诗人以“静”字概括海棠仪态,塑造一位安静娴雅的女子形象。后两句紧承前文,设想男子添妆、女子娇羞之场景,与前文“何人”二字交相呼应。“羞”字运用了拟人手法,将海棠比作上妆的娇羞女子,并以“能红能白”之语称赞海棠颜色丰富。
此外,元好问在海棠诗中对海棠意象进行创新,以未开之海棠喻赞女童。《德华小女五岁,能诵予诗数首,以此诗为赠送》:“牙牙娇语总堪夸,学念新诗似小茶。好个通家女兄弟,海棠红点紫兰芽。(唐人以茶为小女美称)”[4](P1038)韩德华,燕京人,元好问好友,曾官汝州倅,后携家东平。蒙古太宗十年(1238)元好问出东平归冠氏时,韩德华相送,诗人作五古《酬韩德华送归之作》以酬谢,[7](P224)诗中有“良朋满东州,岁月见忠悃。韩侯晚相值,意气尤恳恳。”[4](P851)句。此首海棠诗当蒙古太宗十三年(1241),元好问晚年游东平时所作。[7]韩德华小女能诵元好问诗数首,诗人见闻遂作此诗以赠。诗歌前两句叙写友人小女“学念新诗”,后两句中,“海棠红点”指海棠花苞,此处喻指女童,“紫兰芽”暗用“芝兰玉树”典,典出《晋书·谢安传》:“安尝戒约子侄,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12]“芝兰玉树”喻子弟挺秀,此处为夸赞女童之语。此外,海棠有万事吉祥的美好寓意,故在夸赞之外诗人还借海棠为德华小女送上祝福。
三、理趣美:对人生哲理的品味
所谓“理趣”,即用诗来说理,又有诗味。[13]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诠释:“若夫理趣,则理寓物中,物包理内,物秉理成,理因物显。”[14]元好问在海棠诗的创作中,不仅以诗言志,将自身感情融入其中,而且能够在对海棠的观赏和吟咏中,融入自身丰富的阅历,表达对于生命的认识和感悟,达到人生的超脱。
(一)花看半开,理寓物中 海棠以花开灿烂、姿态潇洒著称,素有“国艳”之誉,更有“百花之尊”“花之贵妃”的美称。纵观历代海棠诗,大多对海棠花开之盛景挥毫泼墨,如薛涛《海棠溪》:“春教风景驻仙霞,水面鱼身总带花。人世不思灵卉异,竞将红缬染轻纱。”[15]咏赞海棠盛开的美艳场景。陆游《驿舍见故屏风画海棠有感》:“猩红鹦绿极天巧,叠萼重跗眩朝日。”[16]刻画海棠鲜艳繁茂与朝日争辉的形象。
元好问作海棠诗偏爱半开海棠,集中笔墨描绘花蕾,如:“生红点点弄娇妍,半拆花房更可怜”,[4](P1007)“翠叶轻笼豆颗匀,胭脂浓抹蜡痕新”,[4](P1657)“枝间新绿一重重,小蕾深藏数点红”[4](P1657)等,体现出诗人别具一格的审美意识。花看半开,意即赏花的最佳时刻是含苞待放之时。宋人邵雍在《安乐窝中吟》诗中慨叹:“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这般意思难名状,只恐人间都未知。”[17]元好问以实际创作回应邵雍之问,以海棠诗证实“好花看半开”的人生哲理。花看半开,彰显了诗人的人生态度,体现出元好问对人生的哲学思考,即为人处世要张弛有度,明白物极必反的道理。
(二)花事人生,物包理内 元好问作咏花诗,常常将花的一生与人的一生相照应,绿叶间花蕾点点为天真女童,枝头上花开灿烂为二八少女,深秋中菊花萎顿为迟暮老人……花事也常与人事相交融,头冠上朵朵杏花为人生得意,风尘中片片飞花喻人生漂泊。
“清霜淅淅散银沙,惊见芳丛阅岁华。”[4](P890)人的一生和花一样,都要经历生死。不同的是,人的寿命往往远远超出花的寿命,因此,通过观察花的一生时常能感悟人生奥妙,体会生命真谛。元好问常常通过对比海棠与其他花卉,表达对人生的体悟。如《同儿辈赋未开海棠二首·其二》:“枝间新绿一重重,小蕾深藏数点红。爱惜芳心莫轻吐,且教桃李闹春风。”[4](P1657)元好问晚年与家中子侄辈欢聚时,念及后辈的教育问题遂作海棠组诗,此诗为第二首。诗人将海棠与桃李作比教育并警戒小辈,言浅意深,含蓄隽永。前两句写海棠枝繁叶茂,生机勃勃,花蕾小巧俏丽,惹人怜爱。末尾两句堪称千古名句,表面上看似是诗人与未开海棠的对话,实则咏物言志,联系实际,教育后辈。诗人将“桃李”争芳斗艳之举与“海棠”无意争春之态作比,衬托海棠花深藏不露、爱惜芳心、不与群芳争艳的优良秉性。一方面赋予海棠低调内敛、遗世独立的人格力量,赞美其洁身自爱,坚守自我的品性·另一方面告诫后辈为人处世要淡泊名利,保持内心的纯洁。《梨花海棠二首·其一》:“梨花如静女,寂寞出春暮。春工惜天真,玉颊洗风露。素月澹相映,萧然见风度。恨无尘外人,为续雪香句。孤芳忌太洁,莫遣凡卉妒。”[4](P1733)最后两句为主旨句。此诗章法严整,意在言外。诗人看似批评梨花“太过高洁”,实则夸赞其甘于寂寞,在百花凋零的“春暮”依然能默默绽放,委婉表达自己甘守寂寞,不与俗同的处世之道。
元好问在诗歌创作中,对海棠审美特质的书写,既是对前人海棠诗的继承,又能够独出机杼,发前人所未发。他的海棠诗虽然在量上不能够称之为最,但是在质上却有着卓越的贡献。对于海棠的外形,诗人着重描绘花与叶在颜色和形态之间的和谐关系,并以插花的文人闲趣表达对于花卉和自然的亲近之意。“诗与实际的人生世相之关系,妙处惟在不即不离。惟其‘不离’,所以有真实感;惟其‘不即’,所以新鲜有趣。”[18](P45)元好问以海棠的特征和风貌作为情感抒发的源头和志意书写的铺垫,在“不即不离”中,将自身境遇与海棠花事联系起来,抒发亡国之痛和飘零之苦,并结合生活经验将海棠的女性象征义进一步扩大。诗人对前人海棠诗的超越,主要体现在对人生哲理的体悟,以辩证和类推的思维赏花、咏花,将诗意与理趣相结合,以此达到前人所未达到之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