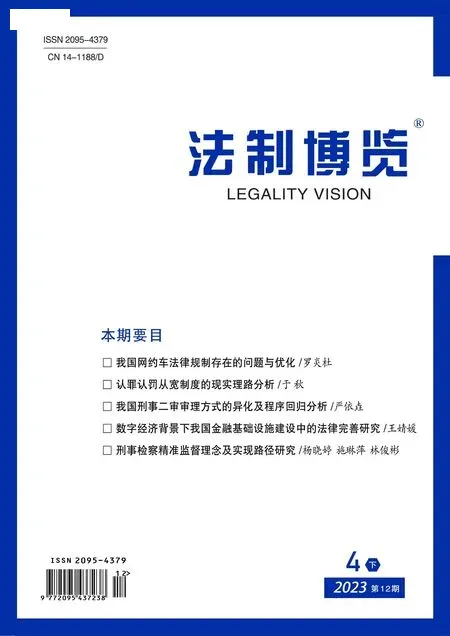《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背景下违规披露犯罪的精准打击
——从义务主体、义务边界出发
闫 蕾
辽宁科技大学经济与法律学院,辽宁 鞍山 114000
一、信息披露犯罪刑法规制的背景
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迅速,市场上投资者类型越来越多,大众对信息的需求呈现多样化和差异化,而披露主要涉及的公司行业类型也越来越多元化,这对我国较传统的制度体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经过学者专家多年多次的研究和改革,2019 年我国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进行了修订,并于2020 年开始实行证券市场注册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也于2020 年进行了相应的修订,对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大修订,正是基于《证券法》的修订和我国刚刚开始注册制的现实需要,也是一种尝试解决信息披露司法困境的重要举措。
当前,我国在刑法领域对信息披露的治理仍然存在缺位,不能起到很好的保障作用,难以发挥最后一道防线的震慑作用[1],这种治理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该罪行为模式信息披露的义务主体和义务边界模糊,因此,我国应当在法律层面对信息披露的义务主体和义务边界进行更细更有效的划分和规定,从根源上提高违规披露信息的犯罪成本,加大对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制裁力度,完善刑法规制,构建良好的经济市场秩序、保障证券市场的投资者们的合法权益。
二、义务主体和义务边界的重要性
随着市场经济迅速发展,有关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案件数量呈现上升趋势,但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适用却没有随着信息披露案件数量的增加而增加。[2]在目前的证券市场和司法案件中,信息披露的义务范围模糊、义务主体范围不清而导致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对该类行为违法纠正不能的情况层出不穷,更不乏很多人钻法律空子来规避自己的责任。明确信息披露的义务主体和义务边界有利于建设完善披露制度,且能通过完整全面的规定来震慑义务主体,从而实现信息披露有效规制。
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十一)》)已经有了对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犯罪行为内容和主体的相关规定,可是法条关于义务、主体的规定还是相对模糊,不够系统化。目前我国对该罪涉及的重要信息认定主要依据主客观两个方面,主观角度是将“重要信息”认定为一种会对投资者的商业判断具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客观角度是将“重要信息”认作为社会对公司、企业产生巨大影响、巨大变化的事项和信息。由于目前我国对违规披露内容规定的不明确,所以只有确定义务主体和主体义务边界问题才能更好、更精准地去预防和惩戒犯罪。
三、违规披露义务主体的界定
(一)义务主体概述
信息披露制度作为证券市场公开原则的法律规则化表达形式,背后蕴藏着深厚的法律理论基础。如果想要对该罪更加深入地了解,首先我们应当明确信息披露行为的义务主体是什么,学者程茂军在书中提到,信息披露的义务主体是以自身名义,对与其相关的经营、财务、交易等重要信息应当披露的当事人。那什么人是应当进行信息披露的当事人呢?在笔者看来,当事人首先应当是公司和企业。其次,当事人应当是上市公司的破产重整管理人和负有义务的董监高和其他参与公司编制相关报告的主要管理人员。
在证券市场下,信息披露实际上义务主体应当是多于《刑法》规定的行为主体的,我国修订前的《刑法》仅仅规定直接责任人员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实施该犯罪行为的主体,而《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也纳入了追责范围。
(二)经典案件分析
1.某新公司信息披露造假案
某新公司自2018 年的其中一个季度的财务报告中显示该公司账面的货币和现金分别超过100亿元,但是该公司即使拥有近300 亿元的资金额,却一直没有偿还仅仅10 亿元的短期债务,随着财务报告的披露和外界的关注,该事件引起证监会和投资者们的警觉。后查证到该公司的确涉嫌信息披露违规,因此对其进行了立案调查,在调查中会计事务所也出具了不能表达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长钟某则是想尽办法辞去在公司内担任的各种职务,其股票也于不久后被实行了“退市风险警示”的处理,最后钟某因涉嫌犯罪被警方采取了强制措施。
该公司信息披露违规造假一事受到了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更是成为信息披露相关的经典案例。而某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钟某在公司担任董事长并兼任数职,明显是信息披露的义务主体。他在证监会对其公司进行调查之际,敏锐察觉到了问题,以各种个人理由快速辞去相关职务,可其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却始终不能被隐藏起来,终是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3]而作为负责某新公司审计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在该案中没有帮助该公司出具虚假的审计报告。在实务中,一个准确的审计报告也是有力地证明该公司信息披露造假的证据材料。因此笔者认为虽然违规披露行为是公司方作出,但类似会计事务所这类中介机构在信息披露中扮演的角色也十分重要。
2.某特公司信息披露造假案
某特公司由于2013 年前后经济需求放缓,市场竞争严峻等原因,该公司的业绩下滑严重,净利润持续下降。2015 年9 月,该公司凭借27 亿的估值做出了对2015-2017 年净利润目标的相关承诺。但事后对外公开的净利润均是依靠财务造假虚增出来的。因该公司为电力相关公司,涉及企业过多,此事甚至惊动了外交部,但即使该案社会危害性巨大,可参与了公司造假过程的关键人员李某松却还是由于证据问题,最终未对他进行处罚。
如果当时可以顺利查证到李某松作为义务主体的证据和造假的证据,那么他大概率不会逃脱法律制裁,当年未对他处罚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关于信息披露的法律大环境和机制不够完全和严格。
(三)明确披露义务主体的主观方面
在注册制的大背景下,信息披露的义务主体在该市场中是处于一个相对强势、优势的地位,他们会掌握着投资者和社会大众无法掌握的信息资料,因此他们的信息披露举动会对投资者和社会大众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现行《刑法》明确规定了披露信息不许存在隐瞒和编造,如果主体在披露的过程中涉及隐瞒和编造,那么可以侧面显示出他的主观意图是故意的,但如果主体实施披露的过程中明显是过失心理,那么是否应该利用刑法去追责呢?犯罪构成的二阶层理论分为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在《刑法》中明确规定,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犯罪行为人的主观应当是故意而非过失,可是司法实践经常会出现行为人虽有违规披露信息的行为却辩称其不知情,不具有犯罪故意的情况。针对此类义务主体狡辩自己不知情从而尝试逃脱法律制裁的情况,立法方面规定不明,司法解释不全面。
四、披露义务的边界界定
(一)披露义务概述
公司向投资者进行信息披露,二者之间存在信息披露的信义义务关系[4],当投资者和公司之间存在利益相关,那么作为公司就有向投资者进行信息披露的义务。随着公司经营权由股东会为绝对中心慢慢到由董事会为绝对中心最后再到现在经理层逐渐成为中心的演变,董事和经理这类管理层也开始有了事实权力和法律权利。而投资者的地位随着公司在市场上占据地位的上升变得逐渐降低,其经常会面对各种风险。
纵观全球,但凡是发达一些的国家,他们的法律几乎都会要求公司真实、全面、完整地披露相关信息,同时可以减少市场欺诈行为和市场失灵行为,从而使投资者和公司管理层相对平等地接触重要信息,使二者关系保持一种平衡性。
因此,信息披露义务在证券市场中显得格外重要,关于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的认定,司法主体需要完全掌握披露义务的边界问题,笔者认为该边界不是简单的范围定义,而是从各个方面去仔细分析义务相关问题。基于此,本文将从义务性质、内容范围、行为方式这三个方面来进行探析,从而达到对信息披露义务边界法律问题的研究和思考。
(二)披露义务的性质
信息披露义务是法律规定的义务主体应当实施的法定义务,[5]如果违规披露,那么除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以外,还可能会构成民法上的侵权,当事人很可能会提起侵权之诉,因此保证披露义务实施的完全性是十分重要的。
信息披露义务的性质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公平性,公平性是指信息义务披露人在公开披露重大信息时,应当面向所有投资者公开,保证投资者们可以同时平等地知悉相同的信息,公平性是保障证券市场投资者权益的首要基础;二是真实性和完整性,披露人应当保证披露百分百真实、百分百完整的重要信息,如果只披露义务人想要让大众看到的信息,刻意隐瞒不想让大众看到的信息,那么就无法保障投资者权益和市场的健康发展,义务主体也存在触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可能性,所以在披露过程中披露的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也是检验义务主体披露义务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三是及时性,义务主体在保证信息披露真实、完整、公平的同时也要保证信息披露的及时,要按照法律规定的时间进行披露和公开。
(三)信息披露义务的行为方式
明确信息披露的行为方式是掌握披露义务边界的重要方式。
我国将刑法上的犯罪行为规定为行为主体实施的违反《刑法》规定,并因此对社会产生危害性的行为,行为的两种基本形式是作为和不作为。[6]对于第二点类型界定,国内的学者持不同意见,有些学者认为故意遗漏应当披露的信息是一种作为型犯罪方式,以积极的方式去实施不披露行为;有些学者认为企业实施的行为不论是违规披露还是不披露都是一种对其所应当承担的义务的一种漠视和放弃,本质符合《刑法》规定的不作为。
(四)明确披露义务的内容范围
明确披露义务内容会更便于司法或行政主体对违规披露行为人进行精准追责,我国《刑法》对披露义务主要规定了两方面内容,一是提供虚假的或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二是不按法律规定披露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2019 年《证券法》在第八十四条中对自愿披露进行了规定:“除依法应当披露的信息以外,义务主体可以自愿披露其他信息,但是自愿披露的信息应当是重要的,与投资者投资判断相关的且不能和依法披露的信息内容相矛盾,更不可以披露不真实或有偏颇的信息来误导大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也明确规定公司应当按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且该报告应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
关于“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是指报告对应当披露的内容进行不真实的记载和虚构甚至隐瞒重要情况。需要披露的财务会计报告是指企业提供的用来对外反映其内部财务情况、经营结果、现金状况的文件,可分为年度、半年度、季度、月度四种报告。国务院出台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中明确规定了财务会计报告的主要类别和基本要素,是司法实务中判断文件是否属于该类报告的重要依据和指引。
通过相关法规可以看出,在信息披露机制中财务会计报告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小觑,更不用说我国在第一次尝试相关立法时主要进行规制的就是财务会计报告,所以在现实当中司法、行政机关会重点关注该证据。
2.不按照规定披露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
“不按照规定披露”需要法律和实务相结合来分析。[7]首先在我国法律中,《证券法》对其的含义进行了规定:“未按照法律规定报送或履行披露义务,或是虽然进行了报送或履行但是有信息重大遗落等行为。”其次在实务中。披露义务也需要关注两点,一是其他重要信息的认定,二是依法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重要信息的危害行为的类型界定。
对于第一点,虽然《刑法修正案(十一)》还未明确界定“重要信息”的含义和范围,但是由于该部分规定的修改是基于2019 年《证券法》和新注册制的大背景,因此笔者认为,如果从与改革目的相适应的角度出发,那么该信息应该可以被理解成证券市场的投资性信息。
综上所述,由于违规披露信息类犯罪一旦发生,实际涉及的金额往往非常大,企业虚构利润或报表项目动辄数千万,有的甚至达到数亿或数十亿,其社会危害和社会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只有完全把握好披露的义务主体和义务边界才能精准打击证券市场犯罪主体,惩戒犯罪从而保障良好的经济秩序,也能从该方面保护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