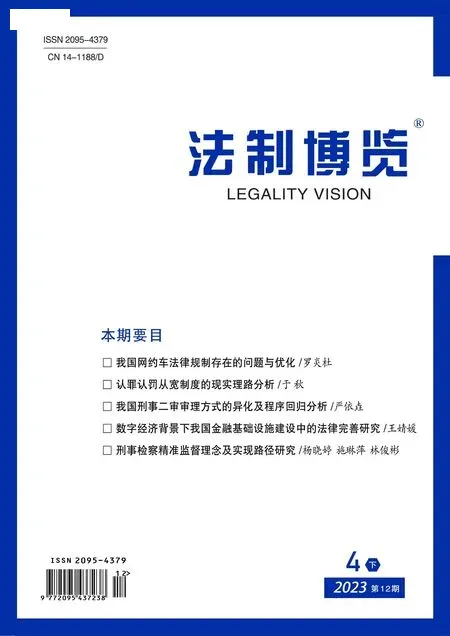表演形象及其法律保护研究
王晨照
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福建 福州 350001
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下,人们通过便捷的信息技术手段对表演形象进行编辑、配音,制造娱乐焦点,一些个媒体通过剪辑软件轻易实现了对表演者表演形象的“恶搞”以吸引流量,歪曲性的剪切、篡改使表演者对于保护其表演形象不受歪曲的权利需求日益凸显。2020 年新《著作权法》的修正增加了第四十条的规定,此项规定保障了职务表演演员的权利,为表演身份以及演员表演的形象提供了法律保护。
一、表演形象保护的历史背景
作为大众娱乐衍生品的表情包、恶搞短视频,借助各个短视频娱乐网站的崛起,以其幽默轻松迅速成为流行,并深受大众喜爱。但因其缺少故事及深度,想要形成像迪士尼、漫威那样庞大的衍生链条,却是十分困难的。但如果有同样的文化产品,以热播剧、高票房电影为背书,情况就不同了。换句话说,若能让表情包携带着综艺特质进行跨界将有助大众形成更多共鸣话题。例如“洪荒之力”傅某慧等作为常见话题主角,早已使表情的使用不再仅仅限定于官方设定的情节范围,形成“剧情外文化”。文娱产业为了迎合大众口味,任意破坏艺术形象,导致部分低俗文化产生,并形成跟风,一时间法律意识淡薄的行为人恶意扭曲表演者形象成风。若演员所扮演的是历史真实人物,将对原人物所承载的品格产生极大伤害,甚至对其名誉造成严重损害,例如“利用董存瑞形象进行恶搞”事件,严重打击了其所承载的历史情怀和优秀品格,对当代社会风气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笔者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与表演形象保护的无力和无奈有着密切关系,若任其发展“以丑为美、以恶为荣”,将逐渐侵蚀作品的独创性和审美意义[1]。
二、当前对表演形象的法律保护路径
当前我国针对演员表演形象的保护方式具有多种途径,保护方式主要包括对表演形象的保护、形象商标的保护、防止不正当竞争的保护以及表演形象肖像的保护等等。
当他人不当利用视听表演形象作为商标,背离了形象的原始样貌造成形象的歪曲,是否可以根据《商标法》进行保护?由于《商标法》自身的特殊性,导致侵犯形象的判断标准必须考虑更多的因素。首先,商标是否侵犯在先权利应当以是否产生混淆为基本原则。如果未经授权使用他人肖像,可能误导相关公众认为肖像主体与商品存在关联关系,则可以构成侵权。其次,肖像的使用应当考虑公序良俗与公共利益。因为部分肖像作为与主体紧密不可分的符号,可能含有特殊的社会、政治与文化意义。如涉及近现代历史人物案件,都必须考虑作为商标使用,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的不良影响。再如“某知名喜剧演员的肖像商标案”中,将肖像注册在钱包等商品上,应考虑是否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或者是否对他人的合法在先权利造成影响,该案中:A 和B 两公司主张其作为该演员肖像权和表演人员艺术形象权的利害关系人对涉及演员形象的商标方面存在的争议提起刑事诉讼,所以通过这一案例可知,上文提到的两个公司在此次刑事诉讼提到了的在先权利,这不仅包括演员本人形象的肖像权,而且还包括演员的艺术形象权利。经过法院判决,两公司的在先权利涉及表演人员的艺术形象权利,但是艺术形象权利并不是法定的权利,根据A 公司和B 公司在诉讼中的相关陈述及其证据,其主张的该项权利应包含演员作为电影演员所享有的表演者权以及对其所表演的角色形象拥有的相关权益。表演者权属于与著作权相关的权利[2]。根据2010 年《著作权法》,争议商标并未侵犯演员的表演者权,故法院对原告的主张不予认可。表演形象的法律保护这一问题跨领域、跨国界,法律解释与社会紧密关联,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该肖像商标一案,则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表演形象著作权法保护领域与商标权交织的法律复杂性。
在商标方面,若他人将演员的表演形象作为商标进行使用,并对原有的表演形象进行改变以及歪曲,是否可以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保护?但若要启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前提要求存在不正当的竞争关系。但是在众多案例中发现,将表演形象作为商标后仅仅涉及普通的商业宣传,且并不伴随着商业不正当竞争的现象,且即便是在一些生产产品当中,所使用的表演形象商标也并未出现同一市场竞争现象,因此以竞争关系为前提的保护方式不能覆盖性地保护表演形象的商业价值。以某被制成表情包而广为传播的表演形象为例,过度使用该表演形象偏离了人物塑造的原始定位,但我们以其为关键词对案例进行搜索,可以发现,行业范围涉及批发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金融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可以看出,使用该形象的表演形象进行商业宣传的产品并不一定存在于同一市场竞争关系中,若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视听表演形象进行保护显得力量不足。
再以最常见的将表演形象归入肖像权的保护范围而言,笔者认为,应当充分肯定肖像权中的财产利益,且他人在未经过肖像权人同意的情况下,严禁将权利人的肖像应用于各类具有商业价值的活动当中,在这一方面比较著名的则是“六小龄童案”,六小龄童与某科技有限公司一案主要围绕人格纠纷展开,《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童因某科技有限公司在其开发的游戏中加入孙悟空形象,且游戏中孙悟空的人物形象并不符合作品《西游记》中的形象设定,尤其是游戏中孙悟空出现与白骨精恋爱等违背、扭曲作品的情节,所以,孙悟空扮演者六小龄童认为,某科技有限公司这一做法对孙悟空扮演者的人格和精神产生了严重影响。经过法院二审判决将六小龄童所表演的孙悟空形象纳入到肖像权中,并得到法律保护,判决认为,当某一形象能够达到反映个人体型和容貌时,观众在接触这一形象过程中会自然地进行与形象相对应的关系,所以,即便是扮演角色的尊严和价值,同样应当视作形象扮演者的尊严和价值。在审判过程中,法庭将与六小龄童有关的形象归结到了肖像权当中,有效地将法律文本与现实情况相契合,且这一措施能够有效地解决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与法律条文之间的脱节问题,同时该案件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对于表演人员所表演形象的法律保护比较缺失的问题。
就表演者而言,本人与所表演的形象并非两个独立的存在,就如六小龄童所表演的孙悟空形象已经深入人心,所以演员本人与扮演的孙悟空形象应当视作具有对应关系,所以这一特性也决定了表演形象的保护范围。以表演者和表演形象对应性为角度,理论界认为,可以将表演形象分为四种:不为大众所熟悉的演员扮演虚构人物;不为大众所熟悉的演员表演真实人物(拥有特定的外在形象);知名演员(面部特征为大众所熟悉)扮演虚构人物;知名演员扮演真实人物[3]。这四种类型中,虚构人物与扮演者间并不必然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不同的扮演者赋予表演对象以不同的艺术特质,第一种和第三种情况更有可能侵犯表演者自身的肖像权,以一般观众为标准,第一种情况下需要通过视觉的逐渐累积才能形成侵犯演员可识别性的可能性。另一个极端则是第三种情况,因知名演员具有极高的可识别性,天然具有表演者肖像权。但是在第二、四类情况中,扮演者所扮演的对象均是真实的人物,所以这就要求扮演者必须要融合极具特征的表演方式,并充分展示出扮演真实人物的特征,赋予角色生命力后具有极高辨识度而获得一定社会评价,才有可能获得肖像权的保护。但是无论是真实还是虚拟人物,在表演过程中均需要融合表演者的劳动,这种使用方式虽然没有侵害作品本身的著作权,但严重侵害了表演者创造性的劳动成果,这对现代艺术形式的创新和艺术改良作品的创造形成冲击,侵害了艺术形象所承载的艺术声誉,将表演形象作为保护对象进行单独保护是必要的,也亟需细化。
真人表演人物形象的作品性并未得到我国法律的认可,但是从几起案件中可以看出,通过真人扮演的动漫人物同样具有作品的属性,其中比较典型的案件有“MC 某龙案”,“某龙”为历史人物,在该案中原告将“MC 某龙”的形象进行创造,创造后的人物形象特征比较明显,如右手持枪,左手持录音机,且形象中从盔甲至衣着均有着非常强烈、鲜明的特征,“MC 某龙”的形象由某位演员扮演并首次对外展现,但是本案的被告又雇佣该演员制作并发布了“MC 某龙”形象,审理过程中,经过比对后发现被告所发布的形象与原告发布的形象高度一致,所以经过法院的判决,认定案件中的被告存在侵犯被告著作权的行为。
三、新《著作权法》下表演形象保护的困境
1996 年,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首次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了表演者所享有的精神权利,且在WPPT 中对表演者的精神权利进行细化,即表演者具备表演形象不受歪曲的权利,并且认为修改权是表演者精神权利的一种,自WPPT 对表演者的精神权利进行规定后,开创了国际条约保护表演者表演形象不受扭曲的先例,各国开始对此种保护越来越重视,但其保护范围仅限于录音表演者的现场有声表演和录音制品,这种重视还远达不到现实的需求[4]。
2020 年4 月28 日生效的《视听表演北京条约》明确规定了“视听录制品”的定义,同时也规定了表演者就视听录制品享有的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在第5 条精神权利中,《视听表演北京条约》延续了WPPT 中关于表演者的两项精神权利的规定,但是将保护范围扩大到了视听录制品之上。此外,《视听表演北京条约》对于保护表演形象不受歪曲权还进行了一定限制:“但同时应对视听录制品的特点予以适当考虑”。目前,我国赋予表演者的精神权利与WPPT 和《视听表演北京条约》基本一致,两者均有效保证了表演者所展示的形象不受歪曲的权利。但是从众多案例来看,在表演者身份权和表演形象的保护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难题。
(一)主体保护范围亟需明确
新《著作权法》让“视听作品”进入人们视野,改变了《著作权法》只是对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既往规定,拓宽了《著作权法》的保护对象范围,已囊括民间许多蕴含各地、各民族艺术作品的表演者以及即兴表演等非文学艺术作品的表演。立法者或许正因为考虑到随着科技的发展,在立法中若将视听作品使用的技术、概念予以限定,很可能无法顺应时代的需要,无法面对未来未知的衍生出的视听作品类型。但立法者保有余地的做法对司法实践中作品的判定带来疑惑,为表演形象的保护树起藩篱,新法缺失对于视听作品的明确定义,也为表演形象不受歪曲的权利带来了不确定性。因此,对于著作权主体的保护范围亟需进一步明确[5]。
(二)个体保护的无力
虽然在2013 年修订的《著作权法》中对表演形象进行了保护,但是通过案例搜索不难发现,绝大部分表演者在选择保护途径时依然选择肖像权保护方式。究其原因,一方面,在大众娱乐、各媒体大量兴起的状况下,个体往往无法通过自己对抗大众群体对形象趣味性的剪辑拼接,在“歪曲标准”的界定、主体保护对象未明确的前提下,表演者若选择著作权方式维权显得单薄无力,选择传统肖像权的保护实属无奈。另一方面,网络传播速度极快,表演者个体无法通过一己之力迅速拦截,对该侵权行为进行惩罚,此时也早已远远偏离了对表演形象原本的角色定位,并对形象的塑造产生了影响,所造成的庸俗化风气并不会在呵呵一乐之后完全消逝。最终侵权人会对被侵权人作出停止侵害行为、精神赔偿以及赔礼道歉等行为,但是由于侵权行为已经形成,且在社会中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即便是进行处理后也为时已晚。
(三)“歪曲行为”认定的标准不明确
从字面意思来看,对于表演形象的歪曲行为使得其脱离本质,经过歪曲后的表演形象与形象的本意相悖,或者对表演的形象进行侮辱。但如何对“恶意”进行认定,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歪曲行为”的主观条件,则显得十分困难。对主观方面的认定困难在司法实践中会形成天然的争议性。表演者成为权利人后,需要证明侵权行为对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造成消极、负面的影响,客观证明这点对于权利人来说是十分困难的。笔者认为,表演形象虽然具有了人格应有之义,但其与艺术形象顺应时代进行改良和变更的分界线如何确定,以及超出何种合理范围使用表演形象会构成不当使用,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这同时也决定着注意义务在权利人和侵权人之间的分配问题。同时,如何区分一个形象属于表演者自身的肖像权还是偏离表演形象的角色定位,尤其在两者具有紧密连接的对应性的作品中,例如前述的第一种情况中,本来不被大众熟知的表演者和所演绎的虚构形象合而为一地出现在大众视野中,表演者的成名与形象角色的塑造具有紧密的联结性。以一般人的眼光进行评价,表演者的外在形象与所演绎的形象从诞生初期便具有统一性,似乎无法区分侵权行为是给表演者还是表演形象带来负面影响。不得不提到判决中还存在着因明星知名度、损害后果等难以量化而导致损失赔偿标准不确定,需要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予以确定而出现的类案异判问题。
四、保证表演形象不受歪曲的措施分析
(一)明确视听作品的定义
本文认为,视听作品是指能够借助电磁、光电、电子计算机等科学技术手段记载和再现,可以直接为人的视觉、听觉所感知的声音、图像、影像等数据。视听作品定义的明确,有助于表演形象的固定和再现,明确表演形象的保护范围。
(二)建立表演者权集体管理组织
由于个体保护存在局限性,因此需要集合表演者集体力量形成保护组织以摆正大众审美,确保表演形象所承载品格和风气的正确性。在理论和实务界早已出现呼声,建议建立表演者权集体管理组织,能够对表演者权益进行整体保护,成为个人表演者的后盾。参考境外立法,在《日本著作权法》中关于表演者的规定非常广泛,表演者不仅包括表演文学作品的演员,而且表演非文学作品的演员同样受到《日本著作权法》的保护,所以对表演者的保护范围较大;相对于日本,德国对于表演者各项权利的保护同样非常完善,具体规定为:为保护表演者的表演形象不受歪曲,他人不得对表演者所表演的形象进行歪曲,且协助表演活动的人也在表演者的范围内。在我国,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是我国的第一家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且在2004 年我国又制订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条例》,该条例的出台表明国内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开始步入正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尚未构建起专门针对表演者权利的集体管理组织,建议应尽早建立表演者权集体保护组织,以弥补表演形象、表演者权保护的空白[6]。
(三)明晰“歪曲行为”的内涵
《伯尔尼公约》对歪曲的规定为:当他人对表演者的作品进行歪曲,且作品作者的名誉受到侵犯时才构成歪曲行为;在《英国著作权法》中关于歪曲行为的定义是:当侵权行为人对他人的作品造成歪曲,且作品作者的名誉以及评价受到影响后,可以判定这种行为已经达到侵害作品完整性的地步。关于歪曲行为各国确定的标准不同,如在法国等国家多采用“主观说”方式,该判断方式以作品中是否出现歪曲等行为进行衡量,且以作者对于被歪曲作品的反应程度作为主要依据[7]。结合境外立法分析,保护表演形象不受歪曲的判断标准,应是使用人在公共政策的指导下,不能影响表演者的利益价值,在符合表演者合法利益的基础下合理、合法使用表演形象,从歪曲表演形象的判断标准来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侵权人借助于文字、语言等行为恶意贬低表演形象的行为,这一行为可以判定为歪曲性解读;二是将表演者的形象运用到以社会一般认知为不良的环境中,对表演形象进行贬损。通过对具体行为的分析与界定,才能更好将其运用在对侵权行为的处罚中,完善对表演形象的具体保护。
五、结语
表演形象是表演者智力创造成果的体现,若对表演形象进行侵犯,则会影响到表演者的社会名誉以及艺术声誉等等,当前社会上存在众多表演形象歪曲问题,这一方面会对表演者的声望造成影响,而另一方面还会降低社会对于表演者的评价,并使其产生经济损失。所以,为了使得表演者享受到表演形象的基本权利,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著作权法》中关于表演形象歪曲的认定,通过多方面、多角度评价他人的行为是否对表演人员的表演形象造成歪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