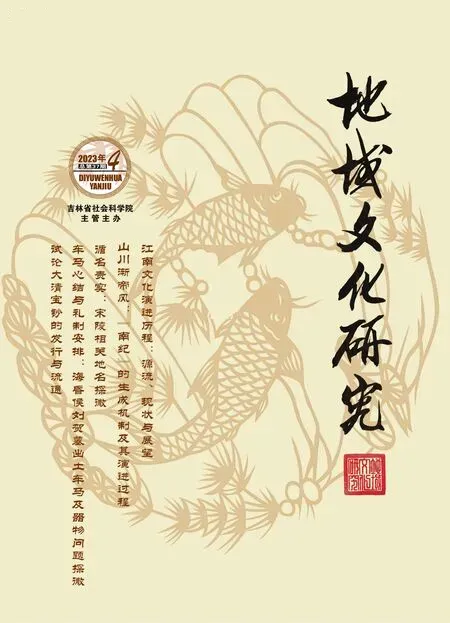车马心结与礼制安排:海昏侯刘贺墓出土车马及器物问题探微
王 刚
在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文物中,制作考究的车马器备受关注。依据有关资料,相关器物分别出土于两处,一是主墓西侧的外藏车马坑,“车马坑为真车马陪葬坑,出土实用高等级安车5辆,马匹20匹。”二是主墓甬道两侧的车马库,对其出土器物的情况,最初认为是这样的:“南侧两个车库,发现了多部偶车以及随侍木俑;甬道中发现了十分珍贵的三马双辕彩车和模型乐车,乐车上有实用的青铜錞于和建鼓,以及4件青铜铙。”①江西省博物馆编:《惊世大发现:南昌汉代海昏侯侯国考古成果展》,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18 年,第20 页、第22页。但后来经过鉴定,其中两件铙应为镯,它们与錞于,以及在甬道中新发现的一件甬钟组合在一起,“为配套使用的乐器。”②王清雷等:《海昏侯刘贺墓青铜乐器测音报告》,《音乐研究》2022年第5期。
随着刘贺墓车马资料的逐渐披露,学界也对于相关问题展开了学术考察。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大多围绕着文物保护,以及相关器物,尤其是当卢等的历史或艺术价值进行专门研究。③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蔡毓真等:《海昏侯墓车马坑出土鎏金青铜当卢铜、锡元素迁移变化研究》,《南方文物》2020年第6期;黄希等:《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车马坑出土车马器研究性保护修复》,《南方文物》2021年第6期;张红燕等:《从海昏侯墓外藏椁出土车马饰件的工艺统计看马车类型》,《南方文物》2021年第6期;宋姣、祝艳琴:《海昏侯墓出土的车马器造型艺术研究》,《艺术生活》2017年第4期;章义和、陈俏巧:《南昌西汉海昏侯墓新出土当卢初探》,《地方文化研究》2016年第3期;曹柯平、王小盾、徐长青:《海昏侯墓地符号世界:当卢纹饰研究》,《江汉考古》2018年第2期;江珊:《南昌海昏侯墓出土西汉当卢研究——以三件青铜错金当卢为例》,湖北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等。这类研究当然有其意义,但倘要进入历史文化的核心地带,在以物见史中获得新的见解,那么,一个不可绕过的层面是:礼制。质言之,汉代贵族的车马是重要礼器,①刘增贵指出:“车作为政治社会地位的象征,在汉隋之间非常重要,尤其是古代鼎彝等器失去作用之后,其重要性更为凸显。”见氏著《汉隋之间的车驾制度》,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秦汉卷》,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677页。要考察刘贺墓的车马随葬问题,这一层面不可或缺。但以笔者目力所及,在相关研究中,礼制问题的讨论大多散在各种片言只语之中,专题性的论文仅见2篇,②朱一、周洪:《海昏侯刘贺墓部分出土文物的礼制分析——以棺椁、随葬车马和琉璃席为对象》,载赵明、温乐平主编《畅论海昏——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五届年会海昏历史文化研究论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方良朱:《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偶乐车》,载浙江省博物馆编《东方博物》第70辑,北京:中国书店,2019年。进一步拓展和深入的空间颇大。
毫无疑问,对刘贺墓车马器问题进行专题性的考察,对于理解西汉时代的政治文化及经济社会的真实面貌,有着深入的意义及价值。与此同时,车马又是刘贺极为钟情之物。对于它们的研究,不仅可以深入到刘贺的内心世界之中,带动墓葬考古等相关问题的研究,而且还连接着刘贺立废前后的历史走向及个人心路,对于昭、宣政治和刘贺的内在心理,亦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窗口。也就是说,刘贺本具车马心结,对于车马及相关器物有着不一样的情愫。加之命运的跌宕起伏,在礼制安排之时,心路与往事往往交杂鼓荡。延此理路细加观察随葬的车马及器物,就可以发现,不管是出于刘贺的遗愿还是家人的安排,其间所透现的个人命运与礼制变化;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在在皆是,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由此,以礼制的角度,历史的眼光来展开相关研究,实为题中应有之义。下面,笔者就不揣浅陋,对此作一初步的分析。
一、从“驱驰国中”到慨口之叹:刘贺政治命运转换视角下的车马问题
刘贺墓出土的车马及其器物属于陪葬品。既然是陪葬,自然有着礼制要求,须遵从一定的规范。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与一般王侯不同,刘贺有着由王而帝;由帝而民,最后改封海昏的跌宕经历。加之随着刘贺的戴罪而殁,海昏侯国被除,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车马及器物以何种规格下葬成为饶有趣味的问题,还可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它们在刘贺生前使用过吗?如何使用?在哪里使用?为什么最后要将其随葬?由于刘贺身份变化之巨,进行何等具体的处置,牵扯着种种力量的博弈,以及往昔与现实因素的交杂纠缠。
更为重要的是,刘贺在年少之时对于驾驭车马极为痴迷。车马,不仅伴随着诸侯王刘贺度过了值得留恋的青春时光,甚至在立废前后,从七乘传赴京到在皇宫中“驱驰”游乐,既是刘贺一生的高光时刻,也是其命运转换中极为重要的图景。并经此转折,墓主最终来到车马难通的海昏侯国,郁郁地了此一生。可以说,车马及其器物是刘贺墓葬礼制安排中的难点,它们不仅是充满着温暖感的重要载体,也承载着难堪的记忆,是刘贺的一大心结所在。由此,当它们随葬之时,所寄托的意义就不是一般仪程所能限定,而应有着更为丰富的内容。也由此,对于刘贺墓出土车马及器物的考察,就不能仅作由物及物的简单讨论,对墓主个人命运及心路历程的考察,亦应纳入视野之中。
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可注意的是,当刘贺立而旋废时,很重要的借口是违背礼制,即所谓“荒淫迷惑,失帝王礼仪,乱汉制度。”其中与车马相关的“罪行”是:“驾法驾,皮轩鸾旗,驱驰北官、桂宫,弄彘斗虎。召皇太后御小马车,使官奴骑乘游戏掖庭中。”①《汉书》卷68《霍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44页、第2940页。这样的罪行是否可以成立呢?刘贺所乘法驾为天子车马,小马车为皇太后所用器物,它们皆为宫中之物。作为新皇帝,一入宫中即以此驱驰游乐,或许在观感上给人于不妥之感,但就礼制而言,似乎也不算太出格。
由此回到历史的现场,可以发现,当刘贺在内宫“车九流,驱驰东西”之际,故臣龚遂曾对昌邑相安乐说道:“今哀痛未尽”,“所为悖道”,希望安乐能对刘贺的相关举动加以规劝。②《汉书》卷89《循吏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38页。然而,细绎龚说,并非是在指责刘贺违背汉制,而是认为他“悖道”,理由在于“今哀痛未尽”。也即是,此刻尚处于昭帝丧期,应表现得有所哀痛,而不应如此兴高采烈地驱驰游乐。这种情形的发生,固然与刘贺的青春年少,喜好玩乐有关。加之昭帝并非亲生父亲,所以,虽然昭帝为先帝,但刘贺对于这位比自己稍微年长的叔辈,不仅没有什么哀痛之情,发自内心的反倒是初登皇位的新奇与欢喜。稚嫩与不成熟使刘贺失去了自控,当然也在此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在听闻龚遂之言后,安乐为什么不去加以劝谏呢?或许在他看来,这也并非什么大过。在内宫之中,皇帝驱驰是一种正常之举。至少在制度范围之内,对其还没有明确的法律限定。
但进一步的问题是,刘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呢?是以此来表达某种政治姿态吗?答案是否定的。这样的举动,应该是个人爱好的延伸。
青年时代的刘贺是车马游猎的爱好者,史载:“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对于这种“好游猎,驱驰国中,动作亡节”以及“驰骋不止”的行为,昌邑中尉王吉曾加以力谏,并获得了刘贺的“敬礼”,刘贺还为此表彰道:“中尉甚忠,数辅吾过。”然而,由于青年人的自控力不够,最终结果是“其后复放从(纵)自若。”③《汉书》卷72《王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58-3061页。
不仅如此,当汉廷以七乘传征召刘贺入京即位之时,“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④《汉书》卷63《武五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64页。根据这段材料,王子今推算,“乘车的车速可以达到每小时45 至67.5 里”,“驰车速度可以超过骑者。”⑤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0页。后来根据道路及尺度的实际情形,王氏又提出了几种不同的数据,⑥参见王子今:《刘贺昌邑—长安行程考》,载赵明、温乐平主编《畅论海昏——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五届年会海昏历史文化研究论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34-235页。但车马速度之快以及御术之高超,是确凿无疑的事实。须知刘贺入京的随从有200多人,这还不包括中途裁撤的50多人,昌邑王国车马之盛、之精良由此可见一斑。
结合本论题,可注意的是,虽说刘贺因“驱驰国中”受到儒臣的劝谏,但那属于“动作亡节”,并非实在的违制。如果刘贺在车马问题上的“放纵”行为与礼制要求相差甚远,他在继承皇位时,就将失去合法性,至少受到汉廷巨大的非议,不可能这么顺利地入朝。笔者曾经指出,霍光立刘贺为帝,与其年轻不更事有着巨大关系,为了继续控制朝政,霍光不希望有一位成熟有实力的皇帝。⑦关于这一问题,可参看拙文:《身体与政治:南昌海昏侯墓器物所见刘贺废立及命运问题蠡测》,《史林》2016年第4期;拙文:《宗庙与刘贺政治命运探微》,《人文杂志》2017年第8期。或许当初立刘贺之时,这种“驱驰”反倒是霍光所看重的一面,是刘贺得以即位的加分项。所以,入京的车马虽然繁盛,但未闻汉廷的劝谏之声,至于皇宫中车马游乐,或许正如王子今所指出的:“似乎是将‘驰骋’或说‘驱驰国中’的贵族游戏提升到更高的皇家消费等级了。”①王子今:《刘贺昌邑—长安行程考》,载赵明、温乐平主编《畅论海昏——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五届年会海昏历史文化研究论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37页。综合来看,以上种种本不足于构成霍光集团态度上的巨大转换,从而对刘贺立而旋废。也就是说,所谓的违制、违礼并非是被废主因,而只是为了使刘贺下台而罗织的罪名。
但是,当罪名成立之后,罢黜帝位的刘贺转眼间已物是人非,车马问题随之成为一个微妙的存在。
查考史籍,刘贺被废之后回到了昌邑王国,在长达十年有余的时间里,被软禁于当年的王宫之中。史载:“闭大门,开小门,廉吏二人为领钱物市买,朝内食物,它不得出入。督盗一人别主徼循,察往来者。以王家钱取卒,迾宫清中备盗贼。”②《汉书》卷63《武五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67页。在荒草丛生的故王宫,刘贺成为身患“风痺疾”的病夫,也即所谓“疾痿”。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要与当年一样再去驱驰车马,自然是不可能之事,刘贺的病情,与禁足于此或许就有着某种关联,是重要的致病之因。③关于这一问题,可参看拙文:《身体与政治:南昌海昏侯墓器物所见刘贺废立及命运问题蠡测》,《史林》2016年第4期。
十余年后,获得解禁的刘贺成为新的海昏侯,更重要的是,他不再被软禁于王宫,看起来,他自由了。此刻,刘贺能像以往那样再一次“驱驰国中”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
查核史籍,刘贺被废时,皇太后曾下令“故王家财物皆与贺。”④《汉书》卷63《武五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65页。作为列侯的刘贺随葬品如此之丰富,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昌邑王时期的物品被带入了海昏。此点已为出土文物所证明,无须赘述。由本论题出发,需要提问的是,既然昌邑王国有着车马之盛,刘贺是否将其悉数带入了海昏呢?受限于材料,现在已无法复原全部的事实。但由刘贺墓出土的诸多车马及器物,可以证明的是,刘贺在海昏应该有着驾驭车马的权力及事实,这些车马器物应大多来自于昌邑王国。关于这一问题,后面还会进一步展开,现在要解答的问题是,刘贺不再能恢复当年的车马之盛,从而重现当年“驱驰国中”的原因何在。
揆之于史,不管刘贺带了多少车马及器物进入海昏,也不管他如何钟爱这些物品,有两大外在要素制约着车马器物的使用。
一是身体条件。作为病夫,刘贺想一如当年“驱驰国中”,那是不可想象的。
二是环境的制约。与昌邑王国及京师长安不同,海昏侯国地处鄱阳湖畔,江南大片的水域环绕其间,这里的交通工具以舟船为主。尤其是在魏晋之前,江南一带未获得大开发,道路整治没有大规模展开,车马驰骋在此必然极受限制。由此,不要说刘贺,就是普通的北方人,惯于车马驱驰之后,进入此地,因交通方式的转换,皆会感到不便。在三国时代,著名的赤壁之战发生时,孙、刘联军敢于抗衡曹操大军,地理上的底气所在,就是此地的舟楫之用成为北方大军的短板,诚如周瑜所言:“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①《三国志》卷54《吴书·周瑜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61页。
山川之变,影响着刘贺的出行。车马之盛只能在昌邑王国起作用,在海昏侯国,它们难有用武之地。不仅如此,刘贺入居此地,大水围城,可谓形同禁锢。
《水经注》卷三九《赣水》载:
又有缭水入焉。其水导源建昌县,汉元帝永光二年,分海昏立。缭水东径新吴县,汉中平中立。缭水又迳海昏县,王莽更名“宜生”,谓之“上缭水”,又谓之“海昏江”,分为二水。县东津上有亭,为济渡之要。其水东北径昌邑城而东出豫章大江,谓之“慨口”。昔汉昌邑王之封海昏也,每乘流东望,辄愤慨而还。世因名焉。②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订:《水经注校订》,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922页。
所谓的“慨口”,是否因刘贺之叹而得名,非本论题所关注。但这一名称所折射的地理状况,形象地反映了刘贺的微妙处境。从特定视角来看,较之此前被禁锢于昌邑王宫,海昏侯国不过是扩大了的幽禁之地。这样的情形得以发生,当然不是偶然,而应该是汉廷的有意安排,以天然形胜控制住刘贺是核心要义所在。刘贺之叹是否发生虽不可考,但其内在的忧愤是可以想见的。
有了这样的安排,当然也就限制住了刘贺的车马驰骋。更重要的是,它还带着某种政治的暗示。也即是,安分守己地待在水边。如果刘贺不甘心于此,在海昏侯国城内大肆“驱驰”,则无疑有着示威和不满的意蕴。智力稍微正常者,都将收敛此种行为。更何况,刘贺入居海昏之后,以避祸为基本态度。在出土的孔子衣镜中,刘贺明确表示:“修容侍侧兮辟非常”③王意乐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此后在海昏的日子里,总的来说,刘贺小心谨慎,但最终还是因为一次私人谈话,而遭到削户之惩,最终抱憾而终。④《汉书》卷63《武五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69-2770页。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要谨守礼制,以深自抑损为常态。在这样的情势下,当年在昌邑的车马即便悉数运至海昏,也不过是用来满足一般的车乘需要,由于为帝、为王的经历,在沿用旧物时或许会有某些身份性的突破,但绝不可能招摇过市。或许它们大部分就存于库房,成为刘贺流连追忆的物事。
在这样的心态下,随葬的车马及器物就不会只反映着列侯的规格,它们应包容着此前为帝、为王时代的若干内容,在生前难以实现的梦想,也或许会通过地下的陪殉加以曲折展现。这些车马器物可延展至昌邑王时代,成为刘贺及其家族抒发忧愤的载体。
二、车马器物的性质、来源及相关问题
众所周知,刘贺墓中的车马及器物属于陪葬品。但倘细加分析,接下来的问题则是,它们属于什么性质的陪葬品?有哪些类型呢?又是如何来到海昏侯国,直至随葬于地下的呢?对于这些相关问题展开有针对性的解读,有助于出入器物之间,对其所蕴涵的历史文化问题获得进一步的理解。
由前已知,相关车马及器物出土于两处,一是车马坑;二是主墓甬道两侧的车马库。其中,前者为真车马,作为生前的实用器,依据“事死如事生”的原则入葬于地下。而后者的主体——偶车马是专为陪葬而制作的明器,与之配套的金、鼓则是实用器。也就是说,两处器物的性质有所不同,一是车马坑中的生器;另一类虽有生前实物加以匹配,但总的来说为明器性质。明器问题可先置而勿论,在此所聚焦的问题是:那些在刘贺生前所拥有的车马器物属于什么性质?来源于何处呢?在笔者看来,它们应该是刘贺的私人物品,来自于昌邑王国。它们随葬于地下,一方面反映了刘贺生前用具的真实面貌,另一方面,故王与今侯的身份重叠,也造成了礼制层面的某些冲突与包容。不了解这些,在进行必要的研判时,就会造成困扰,甚至是误判。下面,来进行具体的分析。
循着以上的问题意识来再审车马坑的随葬状况时,可以注意到如下的现象,
一是:随葬的5 辆木质彩绘车,都是生活中实用的高等级安车。陪葬的20匹马,都是宰杀后完整埋入的,骨架已经腐朽成泥。马车在埋入的时候经过了拆解,被拆卸下的车马器装入彩绘髹漆木箱内,放置在椁底板上。
二是:制作极其考究,器物上错金银、包金、鎏金等工艺复杂,与《后汉书·舆服志》所载“龙首衔轭”、皇太子、皇子所乘“朱班轮,青盖,金华蚤,黑虡文,画轓文辀,金涂五末”的“王青盖车”相似。①江西省博物馆编:《惊世大发现:南昌汉代海昏侯侯国考古成果展》,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18 年,第60 页、第61页。
将这两种现象加以综合考察,可以确认,随葬车马及器物的确是刘贺生前所用实物,而且来自于昌邑王国。理由在于:
1.现象一所反映的是葬俗中的拆车葬,它的核心寓意是,将生器的功能加以消解,完成它在世间的最后任务,从而随侍主人于地下。
关于拆车葬问题,练春海有过专门的研究,他认为,这一“在西汉中期已经进入尾声”的葬俗在先秦时期已经产生,在北方地区具有“悠久的传统”。“拆车”的思想源头有可能是“生器文而不功”。也即是,当生器随葬之后,其在世间的作用已经完成,在消除其原有的实际功用的同时,凸显丧葬礼仪的一面。不仅随葬真车马如此,沿此思路,甚至在汉代图像中亦可见所谓的“无轮”之车,所反映的正是与拆车葬的关联。在练氏看来,“‘无轮’也可视为‘拆去了轮’,是对拆车葬礼仪的图像式继承。”②练春海:《汉代车马形像研究——以御礼为中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0-165页。当刘贺下葬时,其家族沿用这一葬俗,一方面是对北方传统的延承;另一方面,在对车马功能的消解中,或许还有着别样的心境与态度。
笔者注意到,在巨野红土山西汉墓中,随葬车马有“木车一辆、生马四匹和大量铜车马饰。”③山东省菏泽地区汉墓发掘小组:《巨野红土山西汉墓》,《考古学报》1983年第4期。此墓地处汉代昌邑王国一带,根据性质和规模,学界一般认为,这很可能是第一代昌邑王——刘贺父亲刘髆的墓地。虽然它们都是真车马陪葬,但较之刘贺墓的随葬物,此墓中的陪葬数量及质量都不可并论。那么,何以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
就生器的价值功用而言,除了陪葬,遗留子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选择。相较之下,红土山汉墓的“寒酸”或许就有这样的考量,也即是,多留些给在世的亲人。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海昏侯国迷茫的未来与昌邑王国尚有期待不可同日而语。刘贺死后不久,两个可以接位的儿子接连去世,汉廷由此废去了海昏侯国,根据现有的资料及研究,“当年刘贺父子葬仪中,是先行葬埋了刘贺两子,然后再埋葬刘贺的。”①张仲立:《海昏侯刘贺墓园五号墓初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年第4期。由于无人接续爵位,倘严格按照礼制要求,列侯以上的车马及器物无人再有使用资格。毫无疑问,当给刘贺最后下葬时,国除子亡,几乎看不到希望,处在极为绝望的氛围之下。再说刘贺的车马故事中所留存的并非是赫赫往事,而有着屈辱不堪的过去。既然这样,他的家人们又何必大量地留存它们呢?将这些作为伤心载体的车马及器物大量随葬于地下,也就不难理解了。
2.这些车马器物的精美及品级,不是海昏侯这一级别所应拥有的。研究者认为,这些器物与皇子所乘车马有相似性,而我们则以为,这种品级的器物,应是在刘贺为昌邑王时代所具。就当时的政治情形来看,刘贺虽位居列侯,但依然有着罪人的标签,甚至参与宗庙之礼的资格都被排除。②关于这一问题,可参看拙文:《宗庙与刘贺政治命运探微》,《人文杂志》2017年第8期。由此而观,这些器物不可能是在刘贺成为海昏侯时所制作或赐予,只能是由昌邑带来。也由此,我们注意到了信立祥的一个分析:
“这批车马文物,可分为实用车马和偶车马两类。实用车马出土于外藏椁,共有五车二十匹马,应皆为驷马安车。同出的3000余件车马铜饰件,相当一部分有华丽的错金银图像,其精美豪华令人叹为观止,远远超过富平侯张安世墓所出的同类器物。可以断言,这种贵族专用的高等级用车,肯定是刘贺为昌邑王时所使用的。”③信立祥:《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墓考古发掘的价值及意义略论》,《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信氏所论,其基本依据是,器物的精美不符合海昏侯的身份,而只能匹配昌邑王的规格。这样的推断是可以信服的。但倘深入于刘贺家族的心态之中,又可以发现的是,将当年念兹在兹的车马及器物随葬于地下,并以拆车葬加以执行时,或许也是对昌邑王时代及刘贺梦想的一个消解。
前已论及,因海昏侯身份及政治限制的存在,可以推断的是,相关器物不可能产自于海昏本地,而应该是“为昌邑王时所使用”。加之江南少有良马,联系到当年昌邑的车马之盛,与相关器物一样,马匹很可能也都是由昌邑转运而来。但前又论及,不仅因身份所限,以身体及地理状况而言,并不适合刘贺在此驱驰车马。那么,刘贺何以要将它们转运至大泽之畔呢?除了钟情和留恋的情感因素之外,很重要的一条乃在于,他希望这些故物可以在日后派上用场。
但这些精美的车马器物在海昏侯国具体如何使用呢?是经常使用,还是锁在大库之中?使用频率有多高?这些细节都不得而知。尤为重要的是,如果依据严格的礼法,作为列侯,使用这些器物似乎还颇有些僭越之嫌。在这样的思路下,有学者在对汉代相关墓葬情况作分析比较之后,认为:“比较以上考古成果,刘贺墓的车马具装饰级别也更与诸侯王的规格相符,明显超过列侯。”“海昏侯刘贺在丧葬仪节的关键之处还是谨守礼制的,如棺椁的数量和敛服;但是在有操作空间之处如车马饰,则有逾制之举。这说明刘贺一方面还是在顽强地表现曾经的天子荣耀。”④朱一、周洪:《海昏侯刘贺墓部分出土文物的礼制分析——以棺椁、随葬车马和琉璃席为对象》,载赵明、温乐平主编《畅论海昏——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五届年会海昏历史文化研究论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02页、第310页。“与诸侯王的规格相符”云云,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些器物真的“逾制”了吗?如果真的这样,它们何以会存在“有操作空间之处”呢?难道棺椁、敛服等就不可以挤占出“操作空间”吗?如果认为棺椁、敛服等联结着“关键之处”,难道车马及器物就不关键吗?
事实上,车马及器物也是礼制的关键依托。只不过当它们延伸到生前之礼的范畴时,与棺椁、敛服等限定在列侯的礼法系统中不同的是,车马器物的制度安排可由列侯突破至诸侯王的规格。也就是说,在刘贺的礼制安排中,尤其是在礼器的具体使用中有两种类型,一是成为海昏侯之后,所制作使用的匹配礼器,它们当然属于列侯一级的物品。二是延承诸侯王时代的礼器,在使用中“王气”依然,与现有身份之间有着某种距离。以这样的思路来加以观察,可以说的是,礼制并不都是硬性指标,它也有软性之处。如果说这里面存在操作空间的话,操作空间本身其实也是礼制精神的一部分。落实到本论题则是,刘贺“故王”的身份为其提供了继续使用“故物”的便利及权利,这的确不是常态下的情形,但严格说起来,它并不逾制违礼。
由前已知,当刘贺被废时,皇太后曾下令“故王家财物皆与贺。”①《汉书》卷63《武五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65页。这是刘贺拥有大量财物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他的很多金银财宝都是当年昌邑王时代的留存,甚至可能还有一些他父亲留下的财富,对于这些物品的拥有,使其财气十足。不要说作为列侯的刘贺,就是在封侯之前,作为平民的他都依然享有当年诸侯王所有的种种物权。质言之,在刘贺的种种身份中,诸侯王是不可忽略的一面。因为它的存在,在废黜之后,无论为民还是为侯,刘贺可凭借“故王”的身份拥有和使用“故物”,相应的礼器由此就属于可享用范围。落实于本论题中,车马器是礼器的一种,作为“故王”之物被带入了海昏,根据曾经的“故王”资历及朝廷的特许,刘贺可以使用它们。倘仅仅停留于僭越层面去作单线观察,就会失之于简单。
但进一步的问题是,这毕竟属于非常态的情形,多多少少有些名不正而言不顺。而且如果一直使用这种规格的车马器物,也容易招来猜忌及祸患,对于力求避祸的刘贺来说,在使用这些车马器物时,必然处在尴尬和谨慎的状态之下。
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可注意的是,在刘贺墓中出土了一枚“海”字铜印,相较其他印章,它明显大了不少,无论是形制、印文还是印纽,与一般汉代官印很不一样。后晓荣敏锐地发现,“‘海’字印不是一般的汉代官印”,而是“一枚西汉烙马印。”他进一步指出:“汉代烙马印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往往冠有地名或全称或省称。这枚‘海’字印中‘海’字实际为‘海昏’省称,就是一枚典型的省称印章。”“海昏侯生前养马不少,‘海’字印实为海昏侯实施马政管理之物。”②后晓荣:《海昏侯墓出土文物研究三则》,载江西师范大学海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编《纵论海昏——“南昌海昏侯墓发掘暨秦汉区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121-123页。
对于这一结论,笔者表示赞同。但需要补充的是,烙马印在省称中,往往会保留完整的地名,而且还往往会将马厩或官名补上。③关于这一问题,可参看王裕昌、宋琪:《汉代的马政与养马高峰》,《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6期。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著名的汉代王侯烙马印——“灵丘骑马”印。陈直曾作过这样的分析:
灵丘骑马《雪堂藏古器物簿》金二,十一页。“原物系烙印,按灵丘属代郡,骑马令属太仆,可能系文帝为代王时,或赵隐王赵幽王所置骑马令烙印之物。因文帝封代王,疆域的范围不详,灵丘在战国时属于赵地。以上封泥及印文,皆王国自置的属官。”①陈直:《汉代的马政》,氏著:《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26-327页。
由上可知,“灵丘骑马”印也是烙马印,但名称较完整,可以看出属地与属官。在昌邑王时代,应有着类似的情形。也即是,在昌邑王国应该有负责马政的官员,也一定会有相关的烙马印。但这些器物都没有在刘贺墓中出现。它们是没有带入海昏,还是被刘贺所丢弃,现在已不得而知。但由“海”字印可以知道的是,刘贺重制了印章,以作为马政管理之物。由此还可以知道的是,虽然车马及器物可以转运而来,但在马政管理方面应该进行了重建,原有的规格及人员应该不再至少不能全盘保留。
甚至笔者怀疑,海昏可能没有官家性质的马厩及马官。一则这里的地理条件不适合养马,像北方那样大量设置马厩及管理人员,不太符合实际。二则,更重要的是,既未见官方烙马印,“海”字印亦与官印不相符合,这其实乃是一枚私印。也即是,刘贺在对自己的私人马匹做管理时,以此印为依凭。进一步言之,这些马匹及器物乃是作为故王之物转运而来,但就海昏侯的身份而言,并不具有匹配诸侯王品级的官方管理机构及人员。对于这些车马及器物,刘贺应该是以私人财物的性质来加以管理和处置。由此,烙马印呈现私人性质。②吴方浪也认为“海”字印为私印。但由于认定汉代的烙马印皆为官方印信,由此在否定后晓荣主张的基础上提出:“退一步讲,如为海昏侯管理马政之物,作为日常行政管理印信为何不留给下一代海昏侯继续行马政使用,而是选择随葬于第一代海昏侯刘贺墓中。”(氏著:《南昌海昏侯墓出土“海”字铜印考释》,《文博》2019年第1期)然而,故王之物的特殊性,使得刘贺能够以私印来进行马政管理,这是一种特例。
而且,需要进一步注意的是,印章简单到只有一个字,或许反映着刘贺对于海昏侯身份的不认可。对于刘贺来说,他的梦想是“南藩”身份,海昏侯只是一个过渡,在此地成为豫章王,才是最终的梦想。③关于这一问题,可参看拙文:《宗庙与刘贺政治命运探微》,《人文杂志》2017年第8期。从这一视角来看,这些车马器物终究不是海昏侯所应有的用具,它们是为豫章王隆重登场而进行的准备。待到那时,礼法尴尬得以消解,才算在名正言顺中完成了人生之梦。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我们就能理解“海”字烙马印的特异。它后面所呈现的,应该是刘贺的政治期待。然而,历史不仅没有给刘贺这个机会,甚至最后削户受责,直至身亡国除。当刘贺下葬之时,以拆车葬的形式加以处理,就不仅是对于生器的功能消解,也是诸侯王之梦的彻底消解。破碎的希望及绝望的心境,伴随着车马及其器物的下葬,从官家之物到私人器物,从昌邑到海昏,掩埋了荣光和辛酸,也尘封了一段历史……
三、“安车驷马”与“五马”问题
依据多年的考古成果及发掘资料,对于西汉的车马陪葬问题,学界一般认为:1.“从目前所发掘的墓看,只有诸侯王一级的才有大型实用真车马,列侯以下未见。可见真车马的殉葬体现了诸侯王的身份等级。”2.“西汉诸侯王墓基本以殉葬3 辆车马为定制。”④高崇文:《西汉诸侯王墓车马殉葬制度探讨》,《文物》1992年第2期。但刘贺墓的情形打破了以上两个结论。前已论及,刘贺墓葬中的车马器物来自于昌邑王国,属于诸侯王规格。但因刘贺特殊的身份,这种对于列侯规制的突破,可视为合规的变例。白云翔在细审相关车马器物之后,也明确提出:
制作极其考究,与《续汉书·舆服志》所载“皇太子、皇子皆安车,朱班轮,青盖,金华蚤,黑虡文,画轓文辀,金涂五末。皇子为王,赐以乘之,故曰王青盖车”中的“王青盖车”相似。看来,刘贺是把他做昌邑王时的车马用来陪葬了。①白云翔:《西汉王侯陵墓考古视野下海昏侯刘贺墓的观察》,《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然而,进一步的问题是,昌邑王时代车马繁盛,绝非只有这些物品。那么,车马坑中的随葬品是出于何种目的而被挑选出来的呢?它们具体属于何种性质的车马呢?又何以随葬了5辆呢?白云翔认为,由于刘贺曲折的经历及悲剧性的结局,临终前无疑充满了愤懑、忧郁、无助、无望之心。也正是这样的心结,加之刘贺死后朝中大臣“皆以为不宜为立嗣,国除”,使得刘贺去世后埋葬之时,将其生前所有几乎全部进行陪葬,随他而去。车马钟鼓如此,金银财宝如此,奏章副本等统统如此。②白云翔:《西汉王侯陵墓考古视野下海昏侯刘贺墓的观察》,《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这样的分析在大体上可以成立。但落实到本论题,有些细部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讨论。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几乎全部进行陪葬”,不代表刘贺的所有物品都随葬于地下,其间有着一定的挑选空间。而且由前可知的是,在车马坑中“出土实用高等级安车5辆,马匹20匹。”刘贺不可能只有20匹马,也不可能拥有的车型如此统一规整——5辆实用高等级安车。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车马配置,正好是一车四马,即所谓“安车驷马”。笔者以为,这属于当时的一种车制安排。这一安排,也即所谓“五马”出行——以五辆“安车驷马”构成一组系列。
所谓安车,为坐乘之车,或因其行进中安稳之故,被称之为安车。③《汉书·霍光传》载:“韦絮荐轮。”颜注引晋灼曰:“御辈以韦缘轮,著之以絮。”并进一步解释道:“取其行安,不动摇也。”使车安稳而行,是当时的重要考量。《礼记·曲礼上》载,当臣下年岁大了之后,君主“则必赐之几杖,行役以妇人。适四方,乘安车。”郑玄注曰:“安车,所以养身体也。”又曰:“安车,坐乘,若今小车。”清儒孙希旦亦云:“小车也,亦老人所宜然,此养老之具。”④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5页。但沿着郑玄的解释系统,将安车等同于小车,或许只是先秦时代的事情。在西汉,除了包括刘贺墓在内的出土实物可以对其形成反证,与本论题相关的一个文本证据是,“安车驷马”是汉廷的重要赏赐物。例如,仅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下》,在昭、宣时代以来,朝廷对于致仕官员的“安车驷马”之赐就有10 次。但孙机指出:“汉代的小车并不驾四匹马。”也就是说,作为当时的一个标配,四匹马的“驷马”所匹配的是大车。由此,西汉时代的安车并非就是小车,更多的或许还是高大的,配以四匹马的车型。不仅如此,这种“安车驷马”更代表着身份与品级。孙机进一步指出,在孝堂山石祠所刻的出行图中,榜题所谓的“大王车”,“是自图像中见到的汉代最豪华之车”,“应为诸侯王所乘之安车。”⑤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1页、第114页。而现在实物对应的“大王车”,则是刘贺墓车马坑所见之物了。也就是说,“安车驷马”是体现诸侯王身份的重要载体。
但刘贺墓出现“安车驷马”,不仅仅是为了凸显曾经的诸侯王身份,或许更出于现实的选择,以及“循礼”的政治要求。考察刘贺的过往,此种车型并非其年少时所惯乘。因为当刘贺驰骋于昌邑王国时,臣下曾有这样的劝谏:
身劳乎车舆;朝则冒雾露,昼则被尘埃,夏则为大暑之所暴炙,冬则为风寒之所偃薄。数以耎脆之玉体犯勤劳之烦毒,非所以全寿命之宗也,又非所以进仁义之隆也。①《汉书》卷72《王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59页。
在这番话中,固然包含着礼制层面的规劝,希望刘贺的行为更符合诸侯王的身份,并为许多年后“修容侍侧兮辟非常”提供了历史的教训。但就本论题出发,更值得注意的是“驰骋不止”所带来的身体伤害。前已论及,刘贺患有“风痺疾”,致病之主因,固然在于政治的禁锢及身外环境的恶化,但年少时的“驰骋不止”是否也是早期病因之一呢?对于这样的问题,罹疾之后的刘贺不可能不做出某种反思。
由此来考察安车的功能,可以发现,安车之“安”,不仅仅在于安稳,还有着抵御风寒的作用。《盐铁论·取下》曰:“衣轻暖,被英裘,处温室,载安车,不知乘边城,飘胡、代、乡清风之危寒也。”②桓宽撰集,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63页。质言之,保暖御寒是其重要功能。这一功能,正契合着海昏时代刘贺的身体状况。相较之下,由“朝则冒雾露,昼则被尘埃”云云,可以推知,刘贺在昌邑所乘之车,绝不是那种既安稳,且御风寒的安车。它们速度快,十分拉风,很是符合年轻人的个性。然而,事过境移之后,刘贺早就不是那个可以“冒雾露”“被尘埃”,飞扬青春于疾风快马中的少年王,他是一名需要安养的病夫。
也就是说,来到海昏之后,防范病情的进一步加剧成为极为严峻的问题。如果还像年少时那样“驱驰国中”,且不说在海昏侯国行车不便,在潮湿的环境中,“为风寒之所偃薄”的风险也是难以承受的。年少时能尽情驱驰,那时可以将“非所以全寿命之宗也”不放在心上,但海昏侯国的病夫,岂能受得了此种折腾?更何况,通过“修容侍侧”以低调避祸,是当时的言行方针。用诸侯王车马之物、车马之礼,虽然有着制度及政治的许可空间,也是刘贺的心结所在,但毕竟其间还有着种种冲突和尴尬,现在倘再驾驶着快马之车,于身体;于礼制方面的避祸,有百害而无一利。
总之,综合以上的各种要素,可以肯定的是,以“安车驷马”缓缓出行,而不是快马疾驰,当成为刘贺在海昏侯国的常态。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刘贺墓为什么不以3 车加以随葬呢?在论及3车随葬的这一“规律”时,甚至有学者还特意对刘贺所在的宣帝时代加以强调:“皆殉葬3辆车,尤其是宣、元时期的诸侯王墓无一例外。”③高崇文:《西汉诸侯王墓车马殉葬制度探讨》,《文物》1992年第2期。由此而论,刘贺墓葬的情形会是一个特例吗?
以3 车随葬的事实多有出现,当然值得高度重视。但另一面的事实是,除了刘贺墓之外,红土山汉墓以1车随葬,文帝时代的临淄齐王墓以4车,武帝时代的满城汉墓以6车、4车随葬,3车随葬从来就没有一统天下。限于材料,3车随葬是否为当时的基本规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由本论题出发,更需要注意的是,3 车随葬时,车型往往并不统一。刘尊志说:“车马器方面,西汉早中期的车马器组合较为复杂,特别是在早期偏晚至中期偏早阶段达到鼎盛,一墓之内有多种类型的同一车马器。”④刘尊志:《西汉诸侯王墓陪葬车马及相关问题探讨》,《华夏考古》2013年第4期。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上,对于3车随葬的原因,学界往往认为:“西汉诸侯王墓中的3车多是精粗不同、所配马匹多寡各异,反映了3车有主次之分,与先秦乘、道、槁3车的情况大体相似。”⑤高崇文:《西汉诸侯王墓车马殉葬制度探讨》,《文物》1992年第2期。
但这样的功能划分,不符合刘贺墓的情形。与所谓的“乘、道、槁3车”不同的是,随葬车马坑中都是统一的驷马安车,当这样的车制出现时,展现的是出行时的状况。也就是说,因目标及功能的差异,刘贺墓无须遵循3车的葬俗。更重要的是,当这样的一支车队出行时,“五马”,即5辆马车往往是重要的独立单位。
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由诗歌《陌上桑》所云的“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为切入口,来进行讨论。作为乐府名篇,中国人对于《陌上桑》大多耳熟能详。但是,为什么使君是“五马”呢?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使君”为高级别的刺史,他所乘坐的是五匹马所驾驭之车,与六马驾驭的帝王车驾稍有区别。但问题是,无论是文献还是实物,皇帝以下的诸侯王等往往是以四马来驾车,也即所谓“驷马”。五匹马所驾的马车,并没有礼制及实物材料的佐证。阎步克经过深入研究,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诗歌主角实际上是一个带有出使任务的小官吏,反映的是小人得志的嘴脸,也即是:这个“五马”非必“一车之马”,更可能是“一队之马”;基于汉代使者制度和传车制度,那位“使君”不妨推定为谒者、郎官或掾史之类的低级使者,即秩级三百石上下的官吏;不管其车队如何构成,不管有几辆车、几名骑从,总之一共五马。①阎步克:《乐府诗〈陌上桑〉中的“使君”与“五马”——兼论两汉南北朝车驾等级制的若干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年第2期。阎氏所论理据充沛,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在阎说的基础上,可以发现的是,刘贺墓的情形正与“五马”之论相映证。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陌上桑》的主角作为低级官吏可以趾高气扬,乃在于“五马”是一种高规格的车制,我们以为,它就是“安车驷马”之制。依据有关学者的研究,这种“安车驷马”的驾乘者主要有五类,1.封王;2.封公、列侯;3.二千石以上大吏;4.受到特殊礼遇的长者与贤者;5.使者安车。②李强:《安车与车舆制度》,《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6年第1期。前四类身份高贵,而使者无此身份,不过是因为衔王命而得以附骥其间,这正与《陌上桑》“使君”云云的讥讽语境相契合。
而且,车制以5为单位,本就具有悠久传统。按照礼典,先秦时代王车有所谓“五路”之制,汉代沿袭和发展这一传统,还有着所谓的“五时车,安、立皆如之,各如方色,马亦如之”的规定。③《续汉志·舆服上》,《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644页。依据这样的记载,安车中有所谓的五时车,也即五色车,按照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的颜色——青、白、赤、黑、黄来对应5乘车马。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我们注意到,车马坑的器物在颜色上也有着一定讲究,研究者指出:“海昏侯墓外藏椁出土车马饰件虽然都叠压混杂在一起,但是根据已有的同一辆车是同一种装饰工艺的现象,初步推测海昏侯墓外藏椁中应有一辆错金银工艺马车,有一辆黄色通体鎏金马车,有一辆白色通体鎏金银合金马车,有一辆是银质马车。也可能还有双色鎏金和缝隙鎏金工艺的马车。”④张红燕等:《从海昏侯墓外藏椁出土车马饰件的工艺统计看马车类型》,《南方文物》2021年第6期。这样的色彩配套是否有着一定的内在要求,并与“五色”有关,因材料所限,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五车或五马之制的存在,应是不争的事实,是值得重视的一个车制现象。
四、偶乐车及相关问题
与车马坑中的实用器不同,在刘贺墓室中,还出土了明器性质的偶车马。
信立祥指出:“偶车马分为偶轺车和偶乐车。”“轺车是一种级别较低的立乘小车,驾一马,可以个人拥有,在高官贵族的车马出行队列中只能作为导车和从车使用。两辆乐车中,一辆为载有实用建鼓的鼓车,另一辆为载有实用铜錞于和铜编铙的金车。”①信立祥:《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墓考古发掘的价值及意义略论》,《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根据这些材料,有学者将刘贺墓的车马文物分为三类,一是车马坑中的实用车马器,第二类是偶轺车及相配套的随侍木俑,“推测此处的轺车应为刘贺出行的导车或从车,随侍木俑应象征着随行人员。”第三类则是两辆偶乐车,属于珍贵的三马双辕彩车和模型乐车。②方良朱:《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偶乐车》,浙江省博物馆编:《东方博物》第70辑,第81-82页。
车马坑的问题在前面已经作了讨论。当聚焦于偶车马问题时,可以发现的是,对于偶轺车的争议不大,但对于偶乐车问题,则往往见仁见智,后面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那么,偶乐车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器物呢?为什么会随葬于地下?有哪些相关问题呢?
《周礼·地官·鼓人》载:“以金錞和鼓。”郑玄注:“錞,錞于也。”《淮南子·兵略训》曰:“两军相当,鼓錞相望。”《广雅》则曰:“以金铙止鼓。”根据这样的文本,结合出土情形,信立祥认为:先秦时期,鼓与錞于、编铙相配,用于军旅中,在行军作战时,指挥军队进退,属于军礼乐器。击鼓进军,击錞于和编铙止鼓退军。刘贺将这种军礼乐车用于出行,显然是借用了军礼。刘贺墓出土的这些车马文物组合起来,就构成了一套完整的西汉王侯贵族的出行车队:王侯乘坐的主车即驷马安车居中,最前面以数辆轺车为导车,导车之后、主车之前为鼓车和金车,主车之后为以数辆轺车为从车。击鼓则车行,击錞于和编铙则车停。当然,实际的西汉王侯车马出行队列要复杂得多,还要加上等级较高的属官的属车和大量的骑卒及步卒。③信立祥:《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墓考古发掘的价值及意义略论》,《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接续这一观点,方良朱肯定了偶乐车为“出行的军礼乐车”之性质,进而认为:“这两辆偶乐车实际上代表着先秦兵车‘王之五路’中用于军事指挥的革路。”并据此引申道:“革路随葬,应该有着特别的意义。一方面,它象征着使用者身份的尊贵。另一方面,将本用于军事指挥中的革路随葬,似暗示着废帝刘贺后半生始终郁郁不得志,希望在另一个世界称王称霸、征伐四方的心愿。”④方良朱:《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偶乐车》,浙江省博物馆编:《东方博物》第70辑,第81页、第82页。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如果深入于刘贺当时的处境,再结合相关出土文物细加详考,可以发现的是,这样的结论不易成立。偶乐车的关键所在是乐,或者说,它们是表现王者之乐的载体。金鼓固然可以和军礼发生若干联系,但落实于刘贺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它们不仅不能是,至少核心所在,不能指向于军礼。因为刘贺的特殊身份,与军事相关者乃是政治禁忌所在,在墓葬时是需要加以提防和回避的要素。至于说“称王称霸、征伐四方”云云,则不仅是极为忌惮之念,倘真如是,那简直是不将朝廷放在眼里了。
回到历史的现场,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刘贺作为曾经的帝王,废居于海昏侯国,身边都是监临的耳目。因为这样的缘故,一言不慎,就被削户受惩,最终郁郁而终。在刘贺墓出土的《海昏侯国除诏书》中,汉廷对“饮酒醉歌”以及鼓瑟都严加切责,将其作为“无恐惧之心”,“不悔过自责”的罪状。①杨博:《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海昏侯国除诏书〉》,《文物》2021年第12期。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刘贺的家人应该是惶惶不安的。怎么会,又怎么敢突显军事方面的元素呢?难道刘贺的家人们要挑战汉廷权威,置自己于死地吗?即便如此憨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汉廷也不可能让他们得其所欲。可注意的是,在其他诸侯王的随葬车马中,往往还有着各种武器,以及狩猎的猎犬等。例如,“从刘胜墓的6 辆车可以看出,基本是其生前出门的乘舆狩猎或征战用的车,车上配弩机、承弓器、配刀等武器。车随从大批狩猎用犬,犬也佩戴络头衔镰、颈牵铁索随车前后十分壮观。”②郑滦明:《西汉诸侯王墓所见的车马殉葬制度》,《考古》2002年第1期。“六号车旁3 匹马中2 匹可能为战马,另外1匹及其他车旁的马则基本为牵引挽乘的畜力。”③刘尊志:《西汉诸侯王墓陪葬车马及相关问题探讨》,《华夏考古》2013年第4期。也就是说,军事及田猎之物往往伴随着车马一起出土。但这些器物在刘贺墓的车马陪葬物中未见踪迹。
所谓事死如事生。陪葬物所反映的,其实是墓主的生活镜像,至少以其为蓝本来加以附会或拓展。那么,刘贺生前不喜这样的勇武风格吗?当然不是。由前已知,当他以快马驱驰于昌邑国中,招致“动作亡节”的指责时,正是由其“好游猎”的习性所驱使。依此而论,与刘胜墓一样,在刘贺墓中,武器、战车、猎犬等也应一一出现于车马之旁。但它们都消失了。为什么呢?除了海昏侯国的生活环境发生了改变,更重要的是避祸的需求,为了生存,刘贺只能远离它们,这是相关物品在出土物中缺席的核心原因。
要之,我们并不彻底否定金鼓相配的军事意义。但它们的出现必须符合刘贺当时的处境,这样的物品不能直接指向于军事层面,否则就有了挑衅汉廷的意味,这是基本的大前提。那么,刘贺墓中何以要出现这样的乐车呢?由前已知,按照信立祥的思路,它有着“用于出行”的寓意,并“借用了军礼”,而且,墓室中的车马与车马坑中的器物可以组合为一个系列,也即是:“刘贺墓出土的这些车马文物组合起来,就构成了一套完整的西汉王侯贵族的出行车队。”依此而论,金、鼓相配,加之安车驷马,反映了刘贺生前浩浩荡荡的出行场面。
但我们的问题是,如果它们原本是一个整体,为什么要分而置之?难道乐车不可以并入到车马坑的“安车驷马”之中吗?
笔者以为,将这些车马器分置于两处,并非是随意为之,而是因类型的不同所造就。进一步言之,作为车马器,它们都与出行有关,但车马坑中的安车驷马是实际生活的写照,而在墓室之中的器物或许只是一种寄托,并非是实际生活的反映。理由在于,墓室中的车马是以明器模式出现,而不是真车马,它们本来就是专用陪葬物。尤为重要的是,作为实用器的建鼓和青铜錞于及青铜铙、镯等,与明器性质功能有别,它们本可以在车马坑中与安车驷马相配。但它们移之于明器之上的情形正可说明,在日常生活中,它们或许并没有得到实际的运用。
史载,汉初名臣陆贾“常安车驷马,从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④《史记》卷97《郦生陆贾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99页。由此可知,安车驷马配之于金鼓之乐,是一个很有牌面的事情。另外,当刘贺在短暂为帝之时,曾“发乐府乐器,引内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会下还,上前殿,击钟磬,召内泰壹宗庙乐人辇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众乐。……驾法驾,皮轩鸾旗,驱驰北官、桂宫,弄彘斗虎。”①《汉书》卷68《霍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40页。由此亦知的是,这样金、鼓齐鸣的场面不仅是刘贺当年的常态,由“引内昌邑乐人”云云,更可知的是,他在为昌邑王时,就有“击鼓歌吹”“击钟磬”的乐人为之服务。那么,在进入海昏之后,如果刘贺要继续维系这种排场,钟鼓及乐人就可以一并南下,与陆贾一样,从于安车驷马之后,作为出行的常态。但是,它们终究移出了车马坑,而与明器放置在了一起。这不是有些奇怪吗?
前已论及,在海昏时期刘贺低调行事,以避祸为基本取向。笔者猜想,刘贺在实际出行时应该撤下了金鼓等鼓吹之物,至少要将声响和动静尽可能地降下来,安车驷马仅作代步工具,不可太过显摆。如此,才符合当时的境况。
还可注意的是,按照当时的习惯,即便是出行时配以乐车,一般来说,有鼓车而无金车。在山东长清孝堂山祠堂的“大王车出行图”上,就呈现出了这样的情形。在前引信立祥之论中,已论及了这一点。由于“大王车出行图”是东汉图像,在比较刘贺墓中金鼓齐全的现象后,信氏认为,刘贺墓所反映的“是西汉王侯的车舆制度,到东汉时期稍有变化。”在“大王车出行图”之上,“大王即诸侯王乘坐的驷马安车主车前,只有鼓车而没有金车,应是东汉时期诸侯王的车舆制度。”②信立祥:《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墓考古发掘的价值及意义略论》,《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但验之于史,如果认为,西汉诸侯王及高等官员出行时金、鼓齐全,至东汉时,方发生了“只有鼓车而没有金车”的变化。那么,这样的构想与事实并不相符。
我们先从东汉时代的情况说起,汉安二年(143),顺帝在接见匈奴单于时,曾赐予他“青盖驾驷、鼓车、安车”等器物。③《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62页。这与“大王车出行图”中有鼓车、安车,而无金车的情形正相契合。但问题是,这不是东汉的特例。史载,王莽时代也曾对于单于“赐安车、鼓车各一,黄金千斤。”④《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23页。都是有鼓车,而无金车。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刘贺所在的宣帝元康年间,对于龟兹王也是如此,“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⑤《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916页。亦有鼓而无金。此外,宣、元时代的大臣韩延寿在出行时有着“鼓车、歌车”的排场,但也未见金车一类的器物。⑥《汉书》卷76下《韩延寿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214页。也就是说,在两汉时代,当出行之时,鼓车是常备物,金车则未必。两汉之间一体承之,没有明显的变化。不能因为刘贺墓中金、鼓齐全,就认为,这是西汉时代的出行标准。
当然为了声势浩大,有些诸侯王或许也会金、鼓齐备,但这样的做法没有制度上的要求,对于刘贺而言,更是需要避免的一种排场。事实上,墓室中的车马与器物搭配,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寄托,而不是实际生活的反映。这种寄托是什么呢?它当然不可能指向于军事层面,更不可能是展现“在另一个世界称王称霸、征伐四方的心愿”。在笔者看来,更多的是对过去岁月的留恋。
理由在于,金、鼓作为实用器配置于车马之上,不是在海昏时代所具有的现象,而应该是昌邑王时的旧物。或许它们就在海昏侯国的大库之中,没有实际运用于刘贺的生活之中,并最终随葬于地下。那么,当年的它们又在何种情况下会配之于车马呢?存在两种可能。
一是应该是田猎之时,参照军礼,金、鼓相配合以协同行动。由前已知,年轻时的刘贺“驱驰国中”与“好游猎”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当田猎之时,为了声势浩大以及步调一致,也即是,为了疾驰者与缓慢者不至于脱离队伍,借用军礼,依鼓前进,鸣金止行,实为一种常态。
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的三号坑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作为兵器依仗坑,里面除了大量的武器之外,还发现了若干的依仗器,其中,“西部中间置铜錞于和甬钟各一件。”①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而在临近的二号坑则是殉狗坑,其中应该有不少属于猎犬一类。由物见事,齐王墓所展现的,乃是诸侯王游猎之时,兵器与金鼓相配的情景。同样的,昌邑王时代的刘贺亦当有这样的场面。由于禁忌所在,不能将兵器等展现在墓葬之中。但金车的呈现,或许能对此起到一个弥补的作用。
二是作为歌舞音乐的伴奏器。在前引韩延寿的故事中,鼓车之后就是所谓的“歌车”,也就是说,击鼓主要不是为了歌唱,而是以壮出行时的气势,歌车中应该另有乐器。这些乐器有些是吹奏乐,构成了所谓的歌唱与“鼓吹”,《东观汉记·载记·刘盆子》载,刘盆子出行时,在车驾后面即有着所谓的“歌吹者”。②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898页。但既然是“歌吹”,有“吹”亦有“歌”,单靠吹奏乐器是不够的。回观前引陆贾的材料,当陆氏车马出行时,“从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鼓琴瑟”,即说明有弹奏琴瑟者。但那时的乐器岂止只有琴瑟?刘贺墓金车上的錞于和铙等是重要的乐器。在马王堆所出的一枚简上有“击屯(錞)于、铙、铎各一人”(简一五)的记载。后晓荣等学者指出:“这枚简不仅记载了当时这种乐器的使用情况,还反映了当时与錞于组合使用的,还有铙、铎等乐器的情况。”③后晓荣、胡婷婷:《南昌海昏侯墓出土青铜錞于属性等相关问题讨论》,《南方文物》2019年第6期。更何况,錞于与镯以及甬钟已被证明,“为配套使用的乐器。”④王清雷等:《海昏侯刘贺墓青铜乐器测音报告》,《音乐研究》2022年第5期。那么,刘贺金车作为“歌车”,以承担歌吹任务,或许也是一种可能。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与鼓车、金车相配的,不是出行的安车驷马,而是三马双辕彩车。这样的彩车,应该不是实际生活中所用之物,它的呈现,或许也是别有情怀的安排。
与安车驷马不同,这种车制属于所谓的“骖驾”,在汉代,此种驾式,再配之于歌舞鼓吹,往往是王车的规格。与安车驷马适用面广泛不同,它为皇子、皇孙以上所拥有,为重要的身份标志物。据《后汉书·刘盆子传》,西汉末年被赤眉军奉为汉主的刘盆子就曾有过“乘王车,驾三马”的经历,李贤注引《续汉志》曰:“王车,朱班轮,青盖,左右騑,驾三马。”⑤《后汉书》卷11《刘盆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83页、第484页。再据《续汉志·舆服上》,这样的王车不仅“皇子为王”时可乘,皇孙亦可乘,与公及列侯的安车之制有所区分。⑥《后汉书》卷119《续汉志·舆服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647页。
对于刘贺而言,与皇帝相关者皆为禁忌,在随葬品中,要尽量避免发生礼制上的正面冲撞。但刘贺曾经的诸侯王身份,也即汉廷对“故王”的承认,使得他可以使用诸侯王一级的物品。再加之刘贺同时是武帝之孙,正宗的皇孙身份,骖驾自然在其使用范围之内。但前已反复论及,安车驷马为刘贺的主要出行方式,此种皇子、皇孙色彩更为浓厚的骖驾,或许并没有实际采用过。于是,当陪葬之时,以明器形式随之于地下,并将当年田猎时的金、鼓配之于车马之上,其间所反映的心境,应该是复杂而多维的。
结 论
刘贺墓出土的车马及器物不仅是礼制的重要载体,也是墓主的心结所在。它们联结着刘贺的身份及命运的变化,也体现着西汉政治文化的某些侧面,是由物见史的重要材料。经考察笔者认为:
一、作为从昌邑王国转运而来的车马及其器物,当它们作为生前实用器来到海昏侯国之后,虽然由于故王的身份可加以使用,为刘贺所拥有,并使得可采用的礼器被分成了两种类型,一是与海昏侯相匹配的礼器,如随葬的棺椁、敛服等,属于列侯一级的物品。二是延承诸侯王时代的礼器,如车马等。在冲突和包容中,展现了汉代礼制的软性之处,故而不存在僭越问题。但由于身份的尴尬及低调避祸的需要,这些器物未必都能加以实际使用,并由此呈现出私人性的特点。而当它们以拆车葬的形式随葬于地下之时,则不仅是对于生器的功能消解,也在绝望的心境中,埋葬了再次车马之盛的诸侯王之梦。
二、作为列侯一级的墓葬,刘贺墓不仅存在车马陪葬,而且比之一般的诸侯王,其精美程度有远过之而无不及,并打破了3辆马车殉葬的所谓“定制”。这固然与刘贺的特殊身份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因目标及功能的差异,刘贺墓无须遵循3 车的葬俗。随葬车马坑中都是统一的“驷马安车”,当这样的车制出现时,展现的是出行时的状况。它的出现,由当时刘贺的身体状况及海昏侯国地理条件所决定,也是当时政治态势下的一种避祸选择。刘贺墓的情形还说明,“五马”,即5 辆马车往往是出行时重要的独立单位。
三、墓室中的车马器以明器模式出现,与车马坑中的器物有着不同的功能性质。虽然建鼓和青铜錞于及青铜铙是实用器,但与安车驷马的分离可以说明,在日常生活中,它们或许并没有得到实际的运用。主要原因于,由于政治禁忌的存在,墓室中的偶车马不能直接指向于军事层面,为了避祸的需要,刘贺在实际出行时应该撤下了金鼓等鼓吹之物。而就礼制而言,鼓车为出行的必备物,金车则未必。刘贺墓中鼓车、金车的并存,不是两汉之间在制度上有了历史的变化,而是或许有着游猎的目的,以及金车作为歌车功能的需要。
——海昏侯的“Two Faces”(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