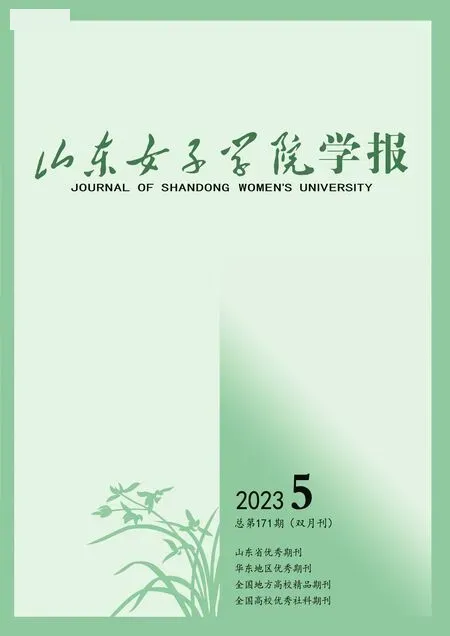清末民初“自由女”谫论
马 龙
(南开大学,天津 300071)
“自由女”是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学界目前也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如李兰萍《清末民初“自由女”现象分析》一文采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探讨还原这一现象得以产生的真实原因[1]。陈伯海、袁进主编的《上海近代文学史》辟有《觉醒与逃避》一章,其中指认民初言情小说中出现的“新女性”(自由女)为当时社会的实情[2]。傅建安的博士论文《20世纪中国文学都市“巫女”形象论》将民初言情小说作家笔下的“都市自由女”列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巫女”形象谱系中进行考察[3]。张勐的《清末民初社会小说的思想蕴藉》一文借对清末民初社会小说中“自由女”形象的聚焦来窥视新旧道德的冲突交融[4]。黄湘金的《史事与传奇——清末民初小说内外的女学生》一书专列《走上歧途的“自由女”》一节,对出入于其间的“自由女”形象进行了大致勾勒[5]。胡雪莲的《“自由”的边界:民国民法颁行初年广州的“自由女”报道》从广州商办报纸的“自由女”报道这一微观角度剖析报业所涉“自由”的多层内涵及其态度[6]。然而,这些研究仍留下一些空白点值得挖掘。比如,在追索“自由女”的广东起源时未曾前进一步,思考其出现的基本背景与条件,作为一个独具时代特色的性别符码,“自由女”这一概念(所包容的内涵与外延)是一成不变的吗?如果不是,那么经历了何种变化?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何在?文学作品中呈现的“自由女”形象,与画报记录、报刊报道中的“自由女”形象是重合还是背离?在这背后又能反映出什么?本文试图解决上述提出的若干问题。
一、起源广东:“自由女”的女学背景
“自由女”及“自由女”一词始于何时何地?根据已有资料,可推知其最早出现于清末民初的广东一带,是娼界对于“女学生”的一种切口或粤人针对“女学生”的方言代称。如《中国秘语行话词典》对于“自由女”的解释:“自由女,清末民初粤妓称女学生。《切口·娼妓·粤妓》:‘自由女,女学生也。’系就当时女学生为冲破封建传统礼教的束缚而言。”[7]徐珂《清稗类钞·广州方言》也有类似的说明:“自由女,女学生也。”[8]于是,民国通俗小说家何海鸣写作《求幸福斋随笔》时将“自由女”一说归之于粤人,便不足为怪:“在中国今日半开化之时代,亦有一种女子,曾为学生,自命开通,喜尚文明,而粤之人目之曰‘自由女’”[9]144。另,查阅晚清报刊数据库会发现,在广州的刊物《祖国文明报》1906年第1期的文章标题中最早使用了“自由女”一词,原题为《看看看!自由女害及亚扎仔》,至此可断定,广州确为“自由女”和“自由女”一词的起源地。接下来的问题是,“自由女”为何率先出现于清末民初的广州?因其在广东地域文化中主要与“女学生”身份发生联系,所以应与该地区女子教育的发达不无关系。
谈论近代女子教育的分布地域,广州是不可绕过的重镇。作为鸦片战争以后被允许开放的五处通商口岸之一,广州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早开风气,“西学”能够以锐不可当之势顺势涌入,新式女学自然也获得了相应的发展空间。按照梁启超总结的“教会所至,女塾接轨”[10]的基本规律,外国传教士不仅在广州设立教会、宣传教义,更率先开办了不少教会女学校,《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曾经做出如下统计:“于一八四四年至一八六〇年之间,又有十一教会女学校,设立于此通商之五埠焉”[11]。此后又有不少教会女校相继问世,如1872年美国女传教士那夏理在广州沙基金利埠创办的真光书院,以及1888年美国南方浸信会女传道会第一届联会委派女传教士容懿美在广州五仙门创办的培道女学等。迟至1920年,据《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修订)》一书的统计数据,广东一省就读于基督教教会学校的女生达7845 人[12],位居全国之冠,而省内自然以广州女生为最多。仅就教会女校数量以及女学生在教会学校所占比重而言,广州堪为地方翘楚,而本土女校的发展更值得注意。经甲午一役,国族危机日益深重,女子教育之于国族生死存亡的重要意义开始为部分有识之士所关注,加上先前外国人在中国兴办女学难免触发一定的民族主义情绪,最终促使国人走上自办女学之路。以1907年为例,据本年学部总务司所编《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显示,全国共创设女学堂(不含教会学校)428所,虽然此时的广东女校仅有6所,但广州为主要的集中地,如育贤女学、培英女学、广东公益女子师范学校、坤维女学等[13]。况且,官方公布的数据未必全然准确,一个较为明显的证据,是在1907年初学部尚未颁行《奏定女学堂章程》,女子教育仍缺乏官方意识形态庇护之际,广东提学司即已发现“粤省风气渐开,民立女学,不下十余所”[14]。“对于今人之直接触摸‘晚清’起决定性作用”[15]的画报记录,也能够补充说明这一问题。作为广东最早的石印画报,《时事画报》于1907年第6期刊载图画《惠女文明》,描绘惠州一少女呼吁兴办女学堂的情形,图中附带的文字从一个侧面折射了广州女学之发达:“惠州每逢二月十九日,各家妇女皆联会筵,祝观音宝诞。今岁有某少女不愿赴会,向人演说,谓省中女学林立,日有进步,我等犹甘为废人,实觉可耻。今提学司札县,提倡女学,我辈当联名禀请,使吾惠女学自此振兴云”[16]148。
在广州本土女学的发展过程中,张竹君与杜清持二人之名值得大书特书。早在庚子(1900)、辛丑(1901)年间,张氏即已成名于广州,当时一般志士咸称之曰妇女界之梁启超[17]221。后世对她的关注多集中在“中国第一女西医”的特殊身份和与之相伴随的医学活动,以及在性别解放这一问题上为女性启蒙者们所提供的“中间路径”[18]。然而,其热心倡办女学的教育成就也不容忽视,尤其是早年身处广州的办学经历。据马君武的《女士张竹君传》一文记载,此女幼年罹患“脑筋病”,幸得美国医师嘉约翰救助,这段经历使其与西医结缘,长大后入博济医学堂学习,学成归来自办南福医院济世,1902年又“改南福医院为小女学堂(即育贤女学——引者注)”[19],此校的创办甚至被誉为“全粤女学之先声”[17]219。1904年,张竹君创办了专业性更强的广州女子工艺学校,聘请专人教授学生纺织、刺绣等技艺,与此前成立的育贤女学一道,为本地的女性教育贡献切实的力量。被时人誉为“贞德之返魂”的杜清持[20],同样积极投身于晚清广州的女学事务,根据黄湘金的细致考证,她曾先后主持(或参与)移风女学校、广东女学堂、公益女学校、坤维女学校和公益女子师范学校的相关工作[21]。两位女士的心血和功劳,被时人付诸文字:“二氏之不避忌讳,破除积习,以提倡女学,固为吾粤女学界中铮铮占一席位者也”[22]。
可以说,教会女校与本土女校的共同发力,张竹君和杜清持两位女士的通力合作,造就了广州相对别地而言更为可观的女学生数量。另外,此一群体所接受的社会化的学校教育,使得她们无论从行为举止还是性情气质,皆与那些深居“内闱”且注重“德性”培养的传统闺秀相区别。陈撷芬描述20世纪初上海女学生意气风姿的文字,可以平移至广州女学生之身而无丝毫扞格:“一个个神清气爽,磊落大方,脸上洁净本色”[23]。1906年广州《赏奇画报》第7期刊载的图画《女学昌明》中,所配文字则为透视本地女学生全新的校园生活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剪影:“每日课余,体操之略,各教员带仝各学生在园内,或则秋千,或则击球,或乘脚踏车,戏弄诸技,取其开拓性灵,而活动肢体”[16]102。更为关键的是,依托女学堂的教育与庇护,借助报刊这一晚清最为流行的大众媒介,这批年轻的广州女学生得以公开向社会发声。比如,在杜清持的引领下,“广东女学堂”的学生曾加入清末著名女报《女子世界》的作者队伍,其中十六岁的张肩任表现最为亮眼,总共写下《欲倡平等先兴女学论》《急救甲辰年女子之方法》《破毁誉论》三篇文章,其余的彭维省、彭维点、阮素容等人则分别发表《论侵人自由与放弃自由之罪》《竞渡之损益论》两篇、《论朝廷与国家之异》《论敬惜字纸》两篇及《砭俗论》一篇。这些作品,单从选题来看已经颇为广泛,内容方面则或陈述女学之紧要,或表达体育在女学中的重要地位,抑或以自由、国家、敬惜字纸这类具体话题为专论,表现出极其宽广的写作视野与丰富的知识积累(1)彭维省的《论侵入自由与放弃自由之罪》一文的中心论点,原出于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中《放弃自由之罪》,彭维点的《论朝廷与国家之异》也可明显见出梁启超观点的影响。参见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21~122页;黄湘金:《杜清持与近代广州女子教育——从最新发现的史料说起》,载《中国地方志》2020年第5期,第78~86页。。如此种种倘若放诸局外人之眼,自是“皆享自由幸福,前此所未有”[24],足够引发时人为其打上“自由女”的标签。
二、概念嬗变:“自由女”概念的历史演进
在广东的地域文化中,所谓“自由女”,主要以受教育的女学生为指称对象。这一点在广州《赏奇画报》1906年第5期刊载的图画《冒充女学生败露》中可得到验证。此图描绘了广州一暗娼冒充女学生却遭识破败露的情形,图中附带文字写道:“娼妇梁亚玲向业皮肉生涯,近作时世妆,冒充自由女以投俗好,并携刼袋书包,装作柔济医院女学生,藉高声价”[16]211。此处使用的“自由女”,正是女学生之代称。有意味的地方在于,即便是在同一刊物,针对“自由女”的概念使用也不偏于一义,正如《赏奇画报》同年第6期刊载的图画《好一般自由女》中,原图的说明文字又将“自由女”指认为一类不守法律规定、以较为负面的形象出现的女性:“女子自由,不守法律,弄出种种怪剧,不可思议。某日,有自由女四人往大沙头花舫,呼妓侑酒。夜深时突来暴客数人,问谁为妓女、谁为自由女,问明后将自由女四人一并掳去。后得水巡追截,载回三人,其一竟被掳去。今之女子好讲自由者,请以此四人为龟鉴”[16]42。而“自由女”实施的所谓“自由”,在晚清的时代背景之下应更多地指女子自由出行、交游甚至恋爱而言。于是,对“自由女”这一名词的使用,又自然而然地以努力摆脱封建礼法束缚的时新(时髦)女性为落脚点。如《北京画报》有《自由女潜逃》一图,描绘北京一位十七岁女子自由结交(男性)友人受阻,一气之下竟不辞而别的情景;《赏奇画报》1906年第6期和第7期分别刊载《险些溺毙自由女》和《男女同行被辱》,前图以三位闺秀于某寺内方塘泛棹嬉戏却险遭溺毙为描述中心,后图描绘广州新派男女青年街上同行遭市民取笑的情形,其中后者的附记文字值得略作引用:“前月廿八日,有一新少年与一自由女并肩而行,言笑自若,复有数十无赖辈尾其后,一路喧哗,而警丁又不弹压。见之者多谓无赖之不礼,而警丁亦放弃责任云”[16]157。考虑到晚清新旧交杂的社会文化心态,以及男女社交公开在彼时主要是作为文明开化的一种国外现象而在报刊上加以推介(力图进行观念上的启蒙)[25],那么上述女子的亲身实践不啻为“绝对”意义的自由之举。
除却画报文字的记录言说,与“自由女”相关的报刊报道也值得注意。上节曾提及,“自由女”一词最早出现于1906年在广州创刊的《祖国文明报》,该刊创刊号上发布《看看看!自由女害及亚扎仔》一篇评论文章,主要讲述一男子受欧西文明熏染,让女儿放足,后因听说“自由女”的种种恶劣行径,担心女儿变成“自由女”,转而又令其重新缠足的故事。文章作者汉铎将此种悲剧的发生,完全归咎于“自由女”之身。在他看来,彼时之“自由女”,“非所谓救世之女志士哉”,虽“热心女权”“多倡自由之说”,但实际上“放挞不拘”“持身不能端正”,更不知自我检点和约束,所行自由实为“伪自由”“野蛮自由”,最终“使女界之堕落,更甚于昔日”[26]。可以看出,此处的“自由女”在其语境使用中带有明显的负面意思,与前述画报中指涉的、不含褒贬色彩的“女学生”“时新女性”等含义可谓大相径庭。与之相类似,1910年5月3日的《申报》刊登一则广州新闻《自由女竟一至于此耶》,讲述二女在公众场合购买春宫画,引得众人围观的故事,“自由女”在此又被描述为行为放浪不羁、有伤社会风化的女性。较之以往的画报记录和报刊报道,这则新闻的特殊之处在于,谈论“自由女”,不仅着眼于基本表现,还为其外表赋形,从中透露出某种都市现代性的气息:“额伏留海,手持绢伞,革履橐橐”[27]。由此可见,在清末时期,凭借公共媒介(如报刊、画报等)的他者言说,“自由女”被建构成一个颇为立体多维的概念体系,充满着丰盈复杂的内涵和外延,并随实际言说语境的变化而不断焕发新义。
然而,这些关于“自由女”的定义、解释和使用所构成的“众声喧哗”的局面,终至民国初年被彻底打破。1913年2月,近代著名教育家陆费逵自广东返回上海,途经香港候船住宿期间,“闲居无聊,手日报读之,见某报载有自由女现形记,某某报屡载自由男自由女纪事”[28],于是有感而作《论今日风化之坏及其挽救之法》一篇,发表于《中华教育界》1913年第4期。此文的记载,透露出两个关键信息:一是“自由女”在民初的报刊报道中频繁出现,且在使用这一语词时多带贬义,甚至可以由此推测整个民初社会媒介仿佛众口一词般对其大加责难;二是借助此文的一般描述可窥见时人对于“自由女”的基本认知:“华服敷粉,竞尚修饰,主其事者不惟不加禁抑,或更以身作则。此风女校极盛,男校亦不免焉。商埠都会,女学生与妓女实难判别,无怪人之指摘。”[28]民初对于“自由女”一词的使用,由此共同指向了以负面形象出现的时髦女学生。她们“涂脂抹粉”,既不事运动、音乐,也不阅览书报,而将饮食男女之事视为自己的消遣之法——“于是桑间濮上之行,行于稠人广众之中”[28],甚至收容她们的学校也被视作专为导淫而建,作者进而拈出一例时事新闻和两例粤报短评,以此进行说明:“最近广东曾封闭一校,即办学渔色者也……日前某粤报短评,言近日少年无不衣裳楚楚,冀奔走自由女之后,而得其一睐。又言近日少年,尾自由女后,装腔做势,尚觉可观”[28]。以“失德女学生”面目出现在民初报刊的“自由女”,成为作者借以抨击社会风气之坏的靶子。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清末还是民初,相关论者以女学生为基点而认定的“自由女”,若依现代眼光来看,其实并不具备真正“自由”的资格,因为“刚刚从闺阁教育进入社会(男性世界)的女学生们,缺乏与异性相处的经验,在社交中,她们往往居于客体的地位,被动而易受到伤害;无论精神还是身体,她们都是不自由的”[29]。
民国初年对于“自由女”的指摘责备,除上述所论的外表妖冶、容易引人误解为“娼妓”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其以“自由恋爱”作为游戏:“此种自由女,出没社会,颇喜与男子为恋爱之交与,间亦为一种文明结婚。考其实际,此种女子亦未尝无些许之阅历与知识,但其用情每不真挚,不过摭拾一二恋爱自由之名词,为应用之品,久之,遂为此种表面上之口头禅,汩没其真性”[9]144-145。如果说此时的“自由女”虽被一致指斥为失德,但尚且与“女学生”身份发生关联,那么之后随着时间的更迭,“自由女”这一概念逐步与“女学生”渐行渐远,其意蕴也基本固定下来——几近成为妓女的代名词。1921年,《游戏世界》刊载托名李伯元的遗著《为女学生讨自由女檄》一篇,将“自由女”与“女学生”做出明确的区划。在作者看来,彼时所谓之“自由女”,“品非纯粹,性实浮嚣,始则略染新风,冀以混充女士。洎成形式,竟肆招摇,大贻女界之羞”,所行所为不过“阴窃学堂之誉,足拖革履,文明不肯让人,口袭新词,茹吐偏能惑众,度歌谣于巷口,饮花酒于楼头”,实质是“啸聚私窝,暗营丑业”的妓女[30]。作为一种极具开放性的话语能指,“自由女”一直处在公共媒介(如报刊、画报等)的不断建构中,最终产生了多层次的意义所指。从清末到民国,这一概念的污名化程度不断加重,内涵与外延历经一个渐趋窄化的发展过程。
上述转变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民国这一历史时期“自由”之说开始遭遇更多的质疑或批评。如果说,身处晚清时代的梁启超在写作《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时已经预感到无所顾忌的“自由”可能带来巨大的破坏力(2)梁启超在《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中将罗兰夫人的临终之言引在传首,原话如下:“呜呼!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此法国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临终之言也”。参见中国之新民:《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载《新民丛报》1902年第17~18号。,那么到了民初,这一破坏力则尽可能地被知识文人加以渲染放大。时人或言“自由之说行,重婚不为羞,平等之说行,伦常可泯灭”[31],视其为重婚现象得以发生的元凶;或作《自由歌》以讽刺,所谓“自由梦,何日醒?两字误人真可怜……自由梦,快快醒,大家听我唱歌儿”[32];或绘新闻画《自由毒》,以字画结合的形式抨击“自由”恶习;或在报道香山某女子因自由结婚而遭兄长枪击的骇人事迹时,径直冠以《一出自由毒》的醒目标题。一时间以警惕自由为写作主旨的小说纷纷问世,较具代表性的如吴绮缘的《自由毒》、汪剑虹的《自由误》、徐枕亚的《自由鉴》、是龙的《(哀情小说)自由果》、沦落女子的《(哀情小说)落花怨》、许指严的《(哀情小说)墓门鸮》等,仅从部分标题即可见创作者的基本态度,而李定夷将原定的小说题目《自由花》更名为《自由毒》的举动更具象征意义,它无疑代表了一种价值观念的转变——从晚清时期的拥抱自由(自由花)到民初时期的拒绝自由(自由毒)。于是,以“自由”为内核的“自由女”,逐渐演化为一个负载太多道德评判的贬义概念。女学生对公共领域的涉足(容易引起男性对其性道德的怀疑),“女学生”本身所包含的一定色情意味(致使其从诞生之初便一直处在被凝视、被注目的位置上),甚至于女学生在自由恋爱后堕入烟花的真实故事,也是推动该词词义转变(从女学生向妓女转换)不可忽视的因素。
三、文学书写:“自由女”的形象呈现
晚清社会变动的剧烈和新闻报道的快捷,使作家易有强烈的现实感,比之以往各时代,作品更贴近生活。而重大事件先已有报刊的渲染、铺垫,引人注目,因此也常常成为文学创作的热点[33]。频繁涌现于清末民初公共媒介的“自由女”话题,虽不属于什么重大事件,但经由报刊、画报的接连记载,确实已逐渐凝定为此一历史时期特定的性别符码,吸引文学界的关注与书写自是理所当然。据笔者所见,仅以此命题的作品就有张春帆的《自由女》、笑梅的《自由女乎?龌龊儿乎?》、是龙的《自由女之新婚谈》、一笑的《自由女游花地》、粤语作家廖恩焘的《录旧十四首·自由女》等,这些作品包含小说、诗歌等多种体裁,以丰富的文体形式对“自由女”形象加以呈现。
从《申报》1909年11月16日开始连载的《自由女》,终刊于同年12月31日,共十二回,为长篇章回小说,最先在报端出现时未署作者姓名,后于1914年由上海三省轩出版单行本时,作者署名“漱六山房”,即张春帆。该作以“商贾云集,百货流通”的热闹广州为基本背景,主要讲述男主人公江镜波及其朋友与珠江第一楼的“自由女”们相与往来的故事,而在小说结尾处,叙述者径直出面对“自由女”进行定义:“看官们且住,在下做书的说了半天,究竟这个自由女是什么东西,原来这个自由女,简直就是个变法改良的妓女”[34]。也正因为“自由女”被小说家张春帆预设为“变法改良的妓女”,所以在其中我们会发现一些较为明显的叙事策略:首先是物化的修辞。在这部小说中,男性主人公几乎是唯一的感知主体,女性只不过是被感知的“他者”。“自由女”的躯体在男性欲望的目光中常常被作家以充满玩味的态度进行静态描述。例如:“江镜波放出眼力,仔仔细细地看了一回,只见那些小影,一个个都是水眼山眉,明眸皓齿。”[35]“江镜波举目看时,只见这两个女子并肩立在那里,亭亭袅袅好似一支并蒂莲花的一般。”[36]“江镜波趁势走上去,紧紧地握住了那丽人的纤手,只觉得春葱十指,入握如棉。”[37]“江镜波看着左瑶瑟丰神淡荡,体态温存,春色横眉,红云透颊,那一种清扬的姿态,好似那烟笼芍药,雨洗芙蓉。”[38]“江镜波借着那珠江第一楼门外一盏电灯的光线,恰恰看得十分清楚。只见那两个女子两颊飞红,星眸双合……四个佣妇紧紧地两边扶着,一步一歪,一步一颠,好似那雨打桃花,风吹杨柳。”[39]在这里,女性是静止的“物”,是男性审美的欲望对象,男性居高临下的把玩姿态一览无余。并且,叙述者使用的物化修辞不过是古典文学中惯用的审美套式,“在这种人体取物品之美的转喻中,性欲或两性关系实际上已发生了一个微妙转变,它不仅表现或象征着一种对女性的欲望,而且借助物象形式摒除了女性自身的欲望”[40]。于是,这些“自由女”不仅成为男性主人公“绝佳”的色情凝视对象,而且这种将女性物化的书写显然折射了作者潜意识中物化女性,视女性为尤物的男性中心意识。其次是较为典型的“溢恶”(3)“溢恶”这一概念来自鲁迅,主要指狭邪小说对主要人物的写法,特别是对妓女的写法。参见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国小说史略》,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06页。写法,使得小说中的部分“自由女”成为名副其实的“恶女”。其中,在伍闺英和赵碧秋二人的身上,“溢恶”的笔法表现得最明显:伍闺英先是厚颜无耻地与“嫖客”许星彩约法三章,要求其必须一心一意爱自己、供给自己所需的所有费用,但又不能干涉自己的“自由”。后来她和许的“奸情”被丈夫当场撞破,面对丈夫的盛怒及指责,伍闺英脸不红、心不跳,反而巧言诡辩。另一女子赵碧秋,一开始以“交换戒指”的神圣名义,想要骗取江镜波的男性友人袁直齐的钱财,后来又大大地敲了袁氏一笔竹杠[41]。小说一方面直写她们“无耻”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也借助其他人物的反应来表达对她们的鄙视与厌弃。总体而言,张春帆笔下的“自由女”是被否定、被批判的对象,她们作为滋生于“社会”(广州)的恶之花,承担起负罪的责任,接受叙述者、读者乃至隐含作者的三重道德审判。
如果说张春帆笔下的“自由女”大致与倚门卖笑的“妓女”形象重合,那么笑梅笔下的“自由女”则是“失德女学生”的化身。他的《自由女乎?龌龊儿乎?》发表于1915年《礼拜六》杂志第48期,署“社会小说”。作品主要讲述张氏女十六岁时,遵从父亲之命,与同村名费生者订立婚约,后来她“留学沪上,近以暑假归里,时装眩目,前后已判若两人”[42]。忽有一日,张氏女向县署递交秉辞,以“费生不务正业、日日与流氓为伍”为由要求离婚,虽然在公堂之上“女殊倜傥,无羞缩态,侃侃谈自由神圣”[42],但因证据不完全之故请求被驳回,而后张氏女又上诉,在将臆造之恶名继续加诸费生之身的同时,更言辞激烈地表示“我心匪石,必不可转。婚姻自由,父母亦无禁止权,必欲余与龌龊儿结婚姻,余愿以颈血溅地”[42]。最后,台下有一老人(实为费生家里的义仆周诚)上台道出张氏女要求离婚的真相——原来此女早与其表兄有染且私生一子,“以吾家贫而欲别抱琵琶耶”[42]。小说中的“张氏女”,正为标题所示的“自由女”,而其行使的所谓“自由”,却是“养汉子、匿私男”,小说标题的设置方式也是在有意引领读者,将“自由女”与“龌龊儿”画上等号,可见写作者对于“自由女”的鄙薄态度。无独有偶,清末民初的粤语作家廖恩焘也将“自由女”视为不道德的女学生之流,他曾作诗一首如此讽刺:“姑娘呷饱自由风,想话文明栋[拣]老公。唔去学堂销暑假,专嚟旅馆睇春宫”[43]。
然而,“自由女”也不尽然是以上述完全负面的形象出现,《自由女之新婚谈》《自由女游花地》提供了不一样的例证。是龙的《自由女之新婚谈》发表于1912年9月19日《申报》的“小说”栏,主要讲述三位已完成“自由结婚”的女士友人,聚在一起针对“自由结婚的便利”“订婚之手续”等问题交流意见、比较优劣。乙女士认为“装饰便利”“登舆便利”“礼仪便利”是为自由结婚的三大便利,丙女士在此基础上又补充“饮食便利”“语言便利”“上床便利”这样几条,最后由甲女士进行总结,而在“订婚之手续”这一问题上,三位女士却出现了较大分歧:甲女士与丈夫素未谋面,亦无交际,由媒人介绍认识、经父母同意后行新式婚礼(丙女士认为这是半截自由),乙女士与丈夫“始而相识,继以礼交,后以情合,两相体察默示订婚之意,乃由介绍人互定婚约”[44](丙女士认为这虽足称自由,然未达自由之极点),丙女士与丈夫在结婚两个月前相遇于某会场,“悦其风流俊美,翼日乃往访之,谈次甚恰。从此互相往来,约一星期乃偕之出游,同宿于旅邸者半月,历久而爱情不变,乃始订盟”[44]。甲乙二女认为丙女“纵欲在先”,所行不过是“伪自由”,丙女不悦竟与二位绝交。虽然三位女士在“订婚手续”这一问题上表现出分歧(由此引出对于“自由”的不同理解),但她们都选择“自由婚礼出阁”“不蹈从前旧习”[44],可见在作家的心目中,“自由结婚”恰是“自由女”最为重要的精神内核。关于这一点,写作“板眼”《自由女游花地》的作者应该心有戚戚焉。《自由女游花地》出现在1908年《中外小说林》第5期,作者署名“一笑”,它以现实中严苏主动追求巡目梁海的故事为底本,叙说二人游览“花地”的经过,文末则发出“但係人想自由,须要自便,首先要跳出,个个专制圈”[45]的感慨。对于女主角“严苏”而言,她恰是“努力跳出专制圈”的代表,而写作者以“自由女”之名予之,说明这一名号又被用来形容形象正面的时新女性。
可以看出,尽管都是以“自由女”为书写对象的文学作品,但不同文本之间却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性:在张春帆那里,“自由女”是“妓女”的变体形象;在笑梅、廖恩焘那里,“自由女”是“不道德”女学生的化身;而在是龙、一笑那里,“自由女”又代表了以“自由恋爱”“自由结婚”为志业的新派女性。并且,这些姿态迥异、作为文学形象而存在的“自由女”,也与前述画报记录、报刊报道等社会媒介所呈现的“自由女”形象大体吻合,从而表现出二者之间和谐共生的互动态势。
四、结语
本文先是自考证入手,追索清末民初“自由女”的起源问题,并对其率先出现于广东的女学背景进行一番考察,后又从大众传媒与社会互动的视角展开研究,重返历史现场,立足于社会文化史角度,经过爬梳、整理和比对,发掘出原本立体多维的 “自由女”概念体系,从清末到民初历经的渐趋窄化的发展过程,并具体分析这种嬗变得以发生的原因。与此同时,也揭示了文学创作中的“自由女”形象与社会媒介报道中的“自由女”相吻合的基本规律,而这背后反映的正是二者之间互动共生的生存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