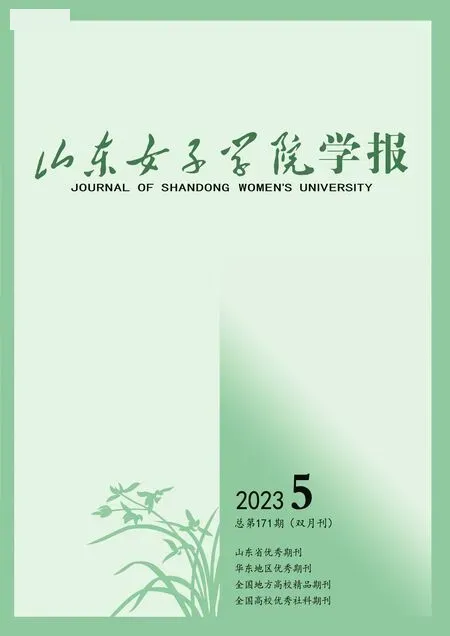将贫困问题纳入反歧视法的路径及其促进性别平等的意义
武文扬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0091)
一、问题的提出
全球疫情、武装冲突、经济衰退等挑战使贫困问题进一步恶化,女性在权利保障、自身发展和社会参与等方面面临更加不利的处境。能否通过将贫困纳入反歧视法来反映和解决贫困女性的不利地位,受到了更多关注。
无论在世界哪个区域,女性的贫困率(依据每日生活费不足1.9美元、3.2美元、5.5美元、国家贫困线)都要高于男性[1]。1995年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将女性与贫困视为重要关切领域,并指出妇女正变得更加贫穷,而贫穷又会表现为遭受社会歧视与排斥。继2000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之后,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和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再次被纳入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创建“一个每个妇女和女童都充分享有性别平等和一切阻碍女性权能的法律、社会和经济障碍都被消除的世界”(1)参见U.N.Doc.A/RES/70/1。。
但受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全球减贫步伐不进反退,使女性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全球贫困率(每日生活费不足1.9美元)由2019年的8.3%上升至2020年的9.2%,极端贫困率出现1998年以来的首次回升,导致女性工作时数和薪资减少,加剧了其不成比例的工作贫困率[2]。当美国在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时,有超过2500万人在两个月内失业,其中女性失业人数为不成比例的1340万人,一度有超过一半的成年女性没有工作[3]。根据欧盟贫困和社会排斥风险标准(at risk of poverty or social exclusion)的统计(2)“AROPE”群体指有陷入贫困风险、严重的物质和社会剥夺,或身处极低工作强度率家庭的人。其中贫困风险依据社会转移支付后收入中位数的60%判断;严重的物质和社会剥夺则依据是否能承担至少13项指标(6项关乎个人、7项关乎家庭)中的7项来判断,如家庭是否有能力面对意外支出、每隔一天购买肉类烹饪,个人是否有能力上网、购买新的衣服、至少拥有两双合脚的鞋等;身处极低工作强度率的家庭根据处于工作年龄的家庭成员(18~64岁,除18~24岁学生和已退休等成员)的工作时间是否等于或少于其工作时间潜力的20%来判断。,女性在此方面长期受到不成比例的影响。女性,尤其是65岁以上、有残障、属于少数族裔、受教育水平较低或具有移民背景的女性十分脆弱,更容易在教育、医疗、工作、社会服务等方面受到交叉歧视(3)参见European Parliament:Women’s Poverty in Europe,P9_TA(2022)0274。。反过来,歧视也更容易导致贫困,使包括妇女在内的特定群体难以摆脱不利处境。
虽然女性囿于贫困会加剧性别不平等、形成恶性循环,且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家层面都已出现通过反歧视法应对贫困特别是女性贫困的实践,但此议题仍然充满争议。贫困对于反歧视法来说依旧比较陌生,也较少会有反歧视法将贫困、无家可归、饥饿或营养不良等特征作为歧视事由[4]。即便如此,这些有限实践还是为重新认识贫困的性质和反歧视法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其所采取的不同路径体现出对将贫困纳入反歧视法的不同观点。本文认为有必要梳理有关此问题的核心争论和主要路径,探索其对促进性别平等的意义。
二、将贫困纳入反歧视法的核心争论
将贫困纳入反歧视法的核心争论主要围绕贫困是否适合纳入以及如何纳入反歧视法展开。对于是否应该纳入,支持者认为反歧视法并不局限于解决身份不平等,也可以用于干预和解决社会经济不平等的问题。对于如何纳入,支持将贫困作为一项歧视事由的观点认为,贫困满足歧视事由,包括对不可改变性的要求,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划分特定群体的特征。另有观点认为,将贫困作为一个情境因素而非歧视事由,也是一条可行甚至更有发展空间的路径。
第一个争论,反歧视法是否适合解决社会经济不平等的问题。传统上来说,反歧视法解决的是有关“承认”(recognition)而不是和贫困相关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问题。承认与社会身份相关,身份群体的界定并非依据生产关系,而是依据承认关系,即此群体和其他群体相比是否在社会中享有尊重和声望[5]。因此,有学者认为,反歧视法不适合也无法解决此类物质不平等问题[6]。但也有学者认为,物质不平等对人权事业和社会进步的阻碍愈发明显,此问题不应被反歧视法所忽视。桑德拉·弗里德曼(Sandra Fredman)指出,发达国家通常用社会政策和政治体系来解决社会经济不平等(socio-economic inequalities)问题,通过宪法和反歧视法来解决基于性别、种族等原因的身份不平等(status-based inequalities)问题,但事实证明将这两者分开的做法不可持续,对实质平等的追求应同时囊括这两方面[7]。玛莎·杰克曼(Martha Jackman)则表示,贫困使实质平等的承诺变得毫无意义,应将贫困视为一项法律禁止的歧视事由,并认识到贫困是一个基本的人权问题[8]。
第二个争论,贫困是否具有不可改变性,以及这一点是否影响其成为一项歧视事由。传统的歧视事由,如与生俱来的生理性别、种族和肤色,通常具有不可改变性(immutability)。但贫困似乎与个人选择更为相关,一个人完全可能因自身原因陷入贫困或摆脱贫困。不过随着科技发展,不可改变性的界限已变得越发模糊,个人可以通过手术等途径改变眼睛颜色、肤色,甚至性别。其次,有学者认为,传统的歧视事由也并非都具有不可改变性,如宗教信仰就是个人选择的(4)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宗教信仰是个人在不同环境和因素的影响下逐渐摸索和确定的,不完全属于个人的主观决定或是能随时改变的选择,参见Zoe Adams,John Adenitire:Ideological Neutrality in the Workplace,载Modern Law Review 2018年第2期,第337~360页。。而且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实践表明,不可改变性已不再是判断歧视事由的必要标准。美国部分州的反歧视法就不再坚持要求不可改变性,而是将注意力转向无家可归、有不良信用记录等特征。再者,单靠自身努力和选择并不一定就能摆脱贫困。有学者指出,美国人总相信个人能改变命运,但事实并非如此,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只有1%的可能进入收入前5%的梯队,这种低代际流动水平说明父母的收入水平基本决定了其子女的收入水平[9]。
第三个争论,如何准确划分“贫困”群体。传统的歧视事由,如生理女性或黑色皮肤,可以较为准确地进行识别和划分,但贫困的标准似乎并不是很明朗,在哪里划界就成为一个问题。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实践中,低收入群体就曾被认为是一个“极其不固定的群体,会随着时间和环境而改变”,从而无法单独成为一个类别(5)参见Lujan v.Colorado State Bd.of Educ.,649 P.2d 1005 (Colo.1982)。。不过有学者认为此观点并不成立,因为所有对歧视的判断都是相对的,即使是性别、肤色这种通常被认为存在“自然边界”的传统歧视事由也无法满足边界清晰的标准,肤色更深或更浅,更男人或更女人都有可能遭受歧视[10]。基于年龄的歧视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划分点,但这也不影响其成为一项公认的歧视事由。对于贫困,法院完全可以依据不同情况和预期保护的群体来划定界限,既可以参考国际、区域和国家层面的极端贫困或相对贫困的划分标准,也可以依据案情设定一个更为具体的界限(如无能力缴纳学费或相关费用的人),或是像美国1967年《就业年龄歧视法》只保护40岁及以上的年龄群体一样,只就一部分群体提供保护(如只保护中等或以下收入的人)。
第四个争论,将贫困作为一项歧视事由是否为将其纳入反歧视法的唯一或最佳路径。有学者认为,将贫困作为一项歧视事由,如通过对个人过去、现阶段和将来的经济资源来判断基于贫困的歧视,完全具有可行性和积极的实践意义[10]。但也有学者认为,鉴于现阶段此种实践仍较为有限,可以考虑通过其他路径将贫困纳入反歧视法,如将其作为一个情境因素纳入对女性交叉歧视的分析。在反歧视法领域提出交叉性理论的金伯利·克伦肖(Kimberlé Crenshaw)最初的出发点就是保护遭受性别、种族、贫困等因素交叉歧视的女性,其在1989年的代表性文章中用交叉性理论分析了非洲裔女性被美国反歧视法所忽视的处境,指出此群体的求职困境既有别于白人女性,也有别于非洲裔男性,单一的种族或性别歧视,或两者的简单叠加都不能准确表达其境遇[11]。施芮娅·阿特雷(Shreya Atrey)也指出,如果反歧视法想在贫困领域有所突破,应进一步纳入交叉性视角,不能把贫困视为一个简单、碎片化的经济再分配问题,而应将其视为一个与各种不利地位相关联的问题[4]。阿特雷认为,可以参考南非宪法法院的实践,将贫困作为一个情境因素纳入综合考量,而不再纠结于歧视事由的问题。
基于以上不同观点,现阶段的实践主要形成了两种将贫困纳入反歧视法的路径,即作为一项歧视事由和作为一个情境因素。本文通过分析南非、美国和欧洲区域层面采用的不同路径,提出将贫困纳入反歧视法的可能及其会对性别平等带来的积极意义。
三、将贫困纳入反歧视法的主要路径
将贫困作为一项歧视事由是将贫困纳入反歧视法最直接的路径。由此一来,贫困女性可以直接选择基于贫困而非性别或其他歧视事由进行申诉。另一路径是将贫困作为一个情境因素纳入对案件的综合考量,此路径要求法院全方面分析贫困女性的复杂处境。后者虽然回避了歧视事由的问题,但有助于识别和解决交叉歧视下女性的特殊困境,其被接纳的前景也更为乐观。
(一)将贫困作为一项歧视事由
对歧视事由采用开放或非穷尽列举模式进行规定的宪法和其他法律文书为此路径提供了可能。在开放模式下,法条不列举具体的歧视事由,法官可以自由裁量;在非穷尽列举模式下,法条虽列举部分歧视事由,但法官仍可在适当情形下进行扩充[12]。前者,如未列举任何歧视事由的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后者,如南非2000年的《促进平等和防止不公平歧视法》(PromotionofEqualityandPreventionofUnfairDiscriminationAmendmentAct,简称《平等法案》),围绕此法案的突破性实践为此路径提供了难得的参考。
1.南非《平等法案》的实践:贫困构成歧视事由。《平等法案》旨在落实南非宪法第9条有关“平等”的规定与精神。除明确列举的歧视事由外,《平等法案》也禁止满足以下要求的其他歧视:造成或延续系统性的不利;侵害人的尊严;或对个人享受其权利和自由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平等法案》第七章第34条还专门指出,鉴于社会经济地位与系统性不利地位的关系及其所带来的歧视,应对其给予特别考虑。而“社会经济地位”包括个人因贫困、低就业、教育缺失所处的不利状况。2018年12月14日,南非平等法院在“社会正义联盟诉警察部部长”案(SocialJusticeCoalitionandOthersv.MinisterofPoliceandOthers)中首次依据《平等法案》认定贫困构成此法案下未被明确列举的歧视事由(6)参见Social Justice Coalition and Others v.Minister of Police and Others,EC03/2016 (2018)。。
在此案中,原告称警察署采用的警力资源分配系统构成了基于种族和贫困的歧视,而贫困属于《平等法案》未明确列出的歧视事由。原告指出,贫困符合《平等法案》对歧视事由的要求。首先,贫困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南非的历史和经济系统造成了贫困,使贫困群体身处脆弱处境。其次,贫困侵害人的尊严,属于难以改变的特征,基于贫困的区别对待有违平等关怀和尊重的理念。再次,基于贫困的歧视就像《平等法案》明确禁止的歧视事由一样,会严重影响权利和自由的享受,尤其是宪法保护的社会和经济权利。对此,南非平等法院首先表示承认新的歧视事由,并引用了“哈克森诉莱恩”案(Harksenv.Lane)。主笔此案多数意见的理查德·戈德斯通大法官(Richard Goldstone)明确指出受制于单一、特定歧视事由的局限性,其认为歧视事由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应抵制将这些因素强行归于某个类别的诱惑,一项歧视事由不应因未被列明就被拒绝(7)参见Harksen v.Lane NO and Others,1998 (1) SA 300 (CC)。。回到本案,南非平等法院在充分考虑贫困带来的影响后认为,贫困符合歧视事由的标准,警察署人力资源的现有分配体系表面上有利于非洲裔为主的贫困地区,实际上却向更加富有的白人居住区倾斜,构成了基于种族和贫困的不公歧视。
2.《欧洲社会宪章》的实践:搭配具体权利适用。在欧洲区域层面,于1961年通过、1996年修订的《欧洲社会宪章》(EuropeanSocialCharter[Revised],简称《宪章》)第E条禁止歧视条款也为非穷尽列举模式,其同样禁止未被明确列举但基于“其他情况”的歧视。不过此条具有附属性,需要结合宪章下的其他具体权利适用,如第30条“免于贫困与社会排斥的权利”(the right to protection against 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此条要求缔约国帮助处于或有风险处于贫困或社会排斥的人及其家庭,使其有获得雇佣、住房、培训、教育、文化、社会及医疗救助的途径。
随着《宪章》下集体申诉机制的建立,第E条得以积累了宝贵的实践。在“第四世界扶贫国际运动组织诉法国”案(InternationalMovementATDFourthWorldv.France)中,贫困家庭无法获得住房或处于恶劣居住环境的问题就得到了关注。原告指出,有三百万合法处于法国境内的人没有住所或居住环境恶劣,而政府的一些做法或不作为使其处境更加困难(8)参见International Movement ATD Fourth World v.France,Complaint No.33/2006 (2007)。。其指出,失去或缺少住房会恶化旅居者的社会不安全感,影响其获得或保住一份工作的能力,并给健康、教育、家庭等领域带来负面结果,使其在获取社会权利方面受到歧视。经过分析,欧洲社会权利委员会认为,法国并未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免于贫困的权利,也没有为贫困群体制定充分的住房政策,因此同时违反第30条免于贫困与社会排斥权、第31条住房权及第E条禁止歧视条款。不过,鉴于免于贫困与社会排斥在《宪章》中已被规定为一项实体性权利,附属性的第E条在实践中难免会受到忽视,欧洲社会权利委员会在一些决定中甚至没有再花时间讨论是否存在歧视的问题[13]。此外,集体申诉机制并不接收个人申诉,无法为个人提供司法保护,欧洲社会权利委员会做出的决定也不具备法律约束力。
3.美国联邦宪法的实践:贫困难入嫌疑归类。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属于开放模式,其未列举任何具体歧视事由,但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实践可知,基于某些事由的区别对待可能构成违宪。法院针对不同事由会采取不同的审查标准,如对种族、国籍、宗教的“嫌疑归类”(suspect class)适用严格审查标准;对性别、父母的婚姻状态(保护非婚生子女)的“半嫌疑归类”(quasi-suspect class)适用中度审查标准;其他适用较为宽松的合理审查标准。法院判断嫌疑归类的标准大致包括:某离散且孤立的少数群体是否受到歧视;是否存在被歧视的历史;是否有政治无力感;群体的决定性特征是否具有不可改变性;特征的关联性(9)至于嫌疑归类是要满足以上所有要素,还是部分或个别要素,以及哪些要素更为重要,尚无统一定论。参见Marcy Strauss:Reevaluating Suspect Classifications,载Seattle University Law Review 2011年第1期第135~174页。。
虽然歧视事由处于开放状态,但美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不会将贫穷作为一种新的嫌疑归类。有学者认为,1973年的“圣安东尼独立学区诉罗德归兹”案(SanAntonioIndependentSchoolDistrictv.Rodriguez)已经断绝了这种可能[14]。在此案中,得克萨斯州对公立学校的资助计划受到违宪指控,这些学校除了接受州政府资助,还依赖地方房产税运行。原告认为,此种资助计划违反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对住在贫困街区的学生不利,因为他们的学校无法像富有街区的学校那样得到大量房产税支持,由此会导致教育质量上的巨大差异。虽然最初联邦地区法院认为此案存在基于财富的歧视,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却认为,地区法院没能明确勾勒出案件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最后,最高法院以五比四判定此案不构成违宪(10)参见San Antonio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v.Rodriguez,411 U.S.1 (1973)。。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此判决并未完全否认贫困作为歧视事由的可能,这仍是一个开放性的宪法问题[15]。因为此案只是判定原告没能成功形容和证明出一个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而没有直接对贫困是否能构成歧视事由给出明确的答案。
4.美国部分州法案的实践:尝试纳入贫困相关特征。相比于宪法修正案,美国部分州的立法和实践展现出更多可能性,虽然没有直接就贫困做出规定,但却开始尝试将与贫困相关的社会经济特征作为歧视事由。2012年,为了全面应对经济低迷和缺少住房的问题,罗得岛州率先通过《无家可归者权利法案》(HomelessBillofRights),并引得多个州争相效仿。此法案明确提出,无家可归者应得到所有州和市机构的平等对待,不因其住房状态在接受紧急医疗救助和雇佣中受到歧视(11)参见R.I.GEN.LAWS ANN.§34-37.1-3 (West 2006 &Supp.2013)。。此法案作为罗得岛州《公平住房实践法案》(FairHousingPracticesAct)的修正案通过,这也使后者禁止的歧视事由在种族、肤色、宗教、性别等事由之上,又突破性地增加了“住房状态”。
此外,基于2007年华盛顿州的先例,美国多个州通过法律禁止雇主在招聘中基于求职者信用记录的歧视。为了提升就业率,伊利诺伊州的《雇员信用隐私法案》(EmployeeCreditPrivacyAct)规定,雇主不能因某人的信用历史或报告对其进行歧视(12)参见ILL.COMP.STAT.ANN.70/10 (West Supp.2013)。。推动此法案的州参议员表示,很多伊利诺伊州人因失业陷入信用危机,又因信用记录无法获得工作,陷入恶性循环。因此,雇主除了不能考虑性别、种族等传统因素外,也不应考虑信用记录(13)参见Senate Transcript,96th General Assembly,2010 Reg.Sess.119 (2010)。。由此可见,虽然不良信用记录不属于与生俱来的特征,但其对个人和社会的负面影响已经达到了需要反歧视法干预的程度。这种将信用记录与性别、种族等歧视事由相提并论的做法,不再坚持对不可改变性的要求,这虽与传统反歧视法有所不同,却已成为多个州立法的重要论据[16]。除信用记录,纽约州等州还禁止基于求职者失业状态的歧视。由此可见,类似法案已跳脱了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平等保护条款对嫌疑归类的判断标准。虽然贫困仍没有被直接作为一项歧视事由,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具体的无家可归、失业等状态,但此趋势展现出反歧视法已不单用于解决身份不平等问题,而是会就社会经济不平等问题做出回应。
(二)将贫困作为一个情境因素
即使贫困没能成为一项歧视事由或嫌疑分类,其仍有可能被纳入反歧视法的实践,使女性的处境得到全方位审视。加拿大最高法院和南非宪法法院采用的情境途径(contextual approach)就是此种路径的代表,不过相较加拿大基于单一歧视事由的实践,南非基于多个歧视事由的实践更具开拓性。
1.加拿大的实践:情境的单一事由歧视。2002年,加拿大最高法院对“戈瑟林诉魁北克”案(Gosselinv.Québec)的判决体现了对“情境的单一事由歧视”的适用,并提出了对贫困因素的考量(14)参见Gosselin v.Quebec (Attorney General),4 SCR 429 (2002)。。此案涉及一项基于1984年社会救助法案(SocialAidAct)制定的社会救助计划。根据此计划,相比于30岁及以上的人,30岁以下的接受救济者得到的基本救济金额只有前者的1/3。原告认为,此种区别对待有违《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第15条第1款有关平等保护的非穷尽式规定,魁北克政府应补偿30岁以下接受救济者因不平等对待缺失的救济金。虽然最终法院以五比四的微弱优势认定此案不构成违宪,但持异议的法官提出,戈瑟林女士的不利处境不单涉及年龄,还涉及贫困、性别等多个因素。其所代表的接受救济群体,并非因为个人选择和懒惰才无法在特定经济背景下找到工作。
其中,杜贝法官(L’Heureux Dubé J.)指出,原告的贫困处境没能得到充分考虑。原告遭受的区别对待使其暴露于极度贫困的风险中,几度生活在政府设定的最低生活标准线下,在尊严、心理和生理上都受到了侵犯,无法充分参与到社会中去。因此,根据“个人或群体受到影响的利益性质和范围”判断,此案足以构成歧视(15)这里所引的标准来自“劳诉加拿大”案(Law v.Canada)判决列出的四项非穷尽的情境判断标准:(1)个人或群体是否在此前遭受不利处境、刻板印象或偏见;(2)诉求事由与提出诉求者的实际需求、能力或处境间的对应;(3)相关法律是否目的中立;(4)个人或群体受到影响的利益性质和范围。参见Law v.Canada (Minister of Employment and Immigration),1 RCS 497 (1999)。。巴斯特罗什法官(Bastarache J.)则指出,戈瑟林女士的成长环境贫穷且复杂,根据“诉求事由与提出诉求者的实际需求、能力或处境间的对应”判断,此案中的区别对待并未考虑到30岁以下群体的实际处境,导致他们仅因年龄就被置于不合标准的生存环境。该法官认为,这种区别对待致使原告和与她有同样处境的人陷入危险和不适合生活的处境,其作为完人的尊严没有得到尊重。部分女性甚至会转向其他犯罪,如选择卖淫等方式来维持生计。由此可见,虽然此案围绕年龄这一单一歧视事由展开,但贫困也是不能忽视的因素之一。
2.南非的实践:情境的多事由交叉歧视。南非宪法第9(3)条为非穷尽式禁止歧视条款,其跳脱了单一歧视事由的局限,禁止基于一个或多个事由的直接或间接歧视。在判断是否存在不公歧视时,南非宪法法院通常会考量以下因素:(1)个人和团体的社会经济条件;(2)所涉及条款对社会模式和系统性不利地位的影响,及申诉者及其群体受到的影响;(3)从交叉性角度分析特定群体不利地位复杂、复合的性质;(4)案件的历史背景。南非宪法法院前大法官萨科斯(Sachs J.)曾表示,承认不平等歧视的事由会出现交叉,并要求对歧视性影响进行全局、情境的分析,而非分别、抽象的分析,其目的是通过质化而非量化的方式判断某群体受到的伤害是否已严重到需要宪法干预的程度(16)参见National Coalition for Gay and Lesbian Equality v.Minister of Justice,1998 (1) SA 6 (CC)。。这种情境途径有助于全方位地分析特定个人或团体的境遇,而贫困也得以被纳入法官的考量当中。
南非宪法法院在涉及女性家政人员的“马兰古诉劳动部长”案(Mahlanguv.MinisterofLabour)中就体现了在种族、性别和社会性别多个歧视事由的基础上,对贫困因素的考量。此案中的非洲裔女性马兰古女士生前为一名家政服务人员,其于工作期间在雇主家的泳池溺水身亡。然而,南非的《工伤与职业病补偿法》(CompensationforOccupationalInjuriesandDiseasesAct,简称“COIDA”)明确将家政人员排除在“雇员”的定义之外,这使得马兰古女士的女儿无法获得赔偿。其女儿作为第一原告提起诉讼,称《工伤与职业病补偿法》有违宪法第9(3)条,构成“基于种族、性别和/或社会性别的歧视”(17)参见Mahlangu and Another v.Minister of Labour and Others,2021(2) SA 54 (CC)。。其还提出,应以交叉视角分析此案,家政人员在南非备受社会地位和阶级等因素造成的交叉歧视,如将此群体排除在职业病补偿之外,会使其陷入贫困循环。
多数意见的主笔法官维克多(Victor A J.)表示,鉴于种族和性别都是宪法明确列出的歧视事由,法院完全可以在此之上推定存在不公,但其不想止步于此,而是想说明各因素的共同作用加剧了本案的歧视。其认为,从事家政服务的非洲裔女性不仅要面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社会性别不平等和阶层分化,还会因工作不稳定受到他人的轻视,处于多重压迫的交叉点。首先,非洲裔女性处于南非社会等级的最底层,此群体受到种族隔离法和父权习惯法的压迫,委身于白人男性、白人女性及黑人男性之下。此外,各项控制人员流动和移民劳工的法律对非洲裔女性的工作带来严重阻碍。这些因素共同限制了非洲裔女性获得工作的机会,使其只能做一些技术含量低、薪资低且不稳定的工作,或只能依赖丈夫和儿子,由此造成的性别化、种族化的贫困体系使非洲裔女性处境堪忧。而其中家政人员的不利处境尤为严重。在种族隔离的历史中,家政人员就被排除在公平的劳工标准之外,而现在其依旧身处贫困。提出协同意见的玛兰塔法官(Mhlantla J.)也表示,从事家政工作的女性通常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而由女性支撑的家庭更容易陷入贫困。何况在非洲的语境下,家庭是个更大的概念,妇女可能要供养她的孩子、孙子女和其他亲戚,甚至亲戚以外的人。受各种因素影响,此群体历来处于劣势地位,她们撑起了无数家庭,自己却被困在贫困的循环里。总体来说,此案首次明确强调南非宪法禁止交叉歧视,并将其视为解释宪法的一般理论。法院在情境途径下对交叉歧视的审视,使贫困与性别、种族、特定职业共同产生的负面作用得到了全面分析。
除以上实践外,此领域还存在一些尝试和探索,虽然尚无法将其归为某一路径,却同样体现出对贫困、性别等因素带来的不利地位的关注。例如,在国际层面,负责监督《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落实的条约机构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在关于老年妇女问题和保护其人权的第27号一般性建议中提出,老年妇女经历的歧视是多方面的,其年龄因素会恶化基于贫困程度、族裔、残障等因素的歧视(18)参见U.N.Doc.CEDAW/C/GC/27。。这种将贫困同族裔、残障等事由一道列出的做法,被认为是在暗示贫困应被视为一项歧视事由或起码是造成歧视的重要原因[17]。在我国,2022年10月30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五十二条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加强贫困妇女、老龄妇女、残疾妇女等困难妇女的权益保障”。贫困与年龄、残障等不利因素一同得到了强调与重视。这不仅体现出中国对贫困女性问题的关切与敏感度,也为后续将贫困纳入反歧视法的考量,尤其是涉及贫困女性的实践提供了可能。
四、将贫困纳入反歧视法对性别平等的意义
以上路径及其代表的趋势,体现出对贫困问题本身以及反歧视法能否在此领域有所作为的探索。无论是对传统歧视事由的拓展,还是对交叉性理论的承认和适用,都有助于聚焦女性面临的社会经济不平等问题,为正视和消除女性遭受的交叉歧视提供新的视角,促进实质性的性别平等。
(一)促进社会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
将贫困或相关特征纳入反歧视法,有利于应对贫困女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面临的不成比例的挑战。例如,在美国,女性无家可归者人数的增长比例已超过男性,这些女性面临身体和精神健康的危害、无法购买卫生用品、无法照顾其子女等问题。其还会受到雇主、警察等人员的歧视和骚扰。据统计,在美国超过80%经历过无家可归且有子女的女性,同样遭受过家庭暴力[18]。因此,无家可归女性的问题,不仅是贫困的问题,从性别角度来看也涉及经济独立、暴力等问题。加上大众通常对无家可归者有自甘堕落、不愿付出劳动或不具备工作能力的偏见,使此群体在生活和工作中被更加边缘化。
然而,实际上,此群体尤其是女性,并非全部为大众所想的游手好闲者。在纽约市无家可归救助站里,有28%的家庭拥有至少一位在工作的成年人,单身的成年人中也有16%在工作,这其中大部分都是从事低薪工作的女性[19]。此群体并非不具备工作意愿和能力,她们身兼数职,在艰难维系工作的同时担心无家可归的状态会影响其职业形象和机会[20]。但因住房短缺、政策改变以及信用记录不佳等原因,这些女性难以凭借一己之力改变现状,摆脱曾经因职场或生活变故陷入的贫困处境。因此,无论是禁止基于无家可归、不良信用记录、失业等状态的歧视,还是直接将贫困作为一项歧视事由的路径,都有助于为贫困女性寻求保护和救济提供新的选择,使女性即使在不承认多种或交叉歧视的实践中,也能单独选择贫困或与贫困相关的事由作为最适合描述其不利地位的特征来提出诉求,并以此来促进社会经济领域的实质性性别平等。
有观点认为,虽然女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面临实际的、有别于男性且不成比例的挑战,但这种困境不适合通过反歧视法解决,而是应该通过相关政策和福利制度解决。本文认为,反歧视法是否适合解决此问题,以及在此问题上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取决于一国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以及文化和历史背景。虽然通过反歧视法解决身份不平等而非社会经济不平等在西方学术界和实践中仍是较为主流的观点,但南非《平等法案》的制定和实践已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基于南非自身的历史发展,尤其是种族、贫困等因素的交织,此法案的设立初衷就是解决贫困问题、促进大规模再分配计划,以达成实质性的平等[21]。其毫不避讳甚至着重强调了贫困与系统性不利地位的关系,并最终承认贫困为一项未被明确列举的歧视事由。在“社会正义联盟诉警察部部长”案中,原告也强调贫困在南非是个系统性的问题,属于难以改变的特征。这与西方传统反歧视法将贫困理解为一项由个人造成且可以由个人改变的特征完全不同。此外,虽然此案的争议点主要围绕贫困和种族展开,但偏向富有白人区的警力分配势必会对处于贫困区的非洲裔女性带来影响。案中的法庭之友妇女法律中心信托基金会(Women’s Legal Centre Trust)就提出了女性遭受暴力和交叉歧视的问题。
当然,即使不通过反歧视法,女性也能从相关政策和福利制度中获得帮助来应对贫困问题。但这种帮助基于需求而非权利,其和反歧视法所提供的保护意义并不相同,也难以识别和纠正贫困女性所面临困境的深层次原因。何况,部分国家的政策和措施虽然能保障生存,却无法改变社会排斥与歧视,还会加重污名化和性别不平等的情况[7]。例如,一些社会福利会默认男人才是养家糊口之人,只要有助于男性的福利都将惠及其家庭中的女性和儿童。基于这种观念的社会福利制度和措施反而会加重女性地位的不平等,使女性受困于家庭收入的不公分配。
(二)正视和消除女性遭受的交叉歧视
将贫困或相关特征纳入反歧视法有助于更好地识别和消除贫困女性遭受的交叉歧视。正如金伯利·克伦肖所提出的,交叉歧视的影响不是一种量变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质变的独特困境。在实践中,性别与贫困的交叉也会使特定群体陷入独特的不利地位。在1977年涉及女性堕胎问题的“马厄诉罗”案(Maherv.Roe)中,美国康涅狄格州对使用联邦和州政府的医疗补助(medicaid)进行流产做出了“医疗必要”的限制,致使两名贫困女性无法堕胎(19)参见Maher v.Roe,432 U.S.464 (1977)。。两人认为此规定违反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案中两名原告的困境既有别于能独立承担堕胎费用的其他女性,也有别于不受堕胎问题困扰的贫困男性。对此,虽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表示其没有过单纯将经济需求作为嫌疑归类的先例,但也承认拒绝给予贫困者相应的福利会造成基于财富的归类(wealth classification),因为不贫困的人可以自己承担相应的物质和服务。
1980年的“哈里斯诉麦克雷”案(Harrisv.McRae)再次涉及这个问题。案中原告对限制通过医疗补助堕胎的规定即《海德修正案》(HydeAmendment)(20)1976年通过的《海德修正案》禁止使用联邦医疗补助支付流产费用,禁止的例外依年份不同而有所改变。如最初的《海德修正案》,也就是“哈里斯诉麦克雷”案中的版本仅允许一个例外,即孕妇面临生命危险。提出了挑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承认,《海德修正案》所带来的主要影响确实都落在了贫困者的身上(21)参见Harris v.McRae,448 U.S.297 (1980)。,也就是贫困女性的身上。但其仍没有选择开启将贫困纳入嫌疑归类的先河。由此可见,现有单一的歧视事由,有时并不能有效展示出特定群体所处的不利地位。虽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出于某些顾虑没有在宪法层面将贫困作为一项歧视事由,但其明显已经意识到贫困在这两个案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果将贫困纳入反歧视法,那么在此类案件中,这些受贫困和性别因素共同影响的女性的处境就能得到重视。
此外,关注和禁止交叉歧视,包括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歧视,已经成为相关联合国核心人权条约机构解读条约的趋势。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对《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二条“缔约国义务”进行解释时指出,交叉性是理解此条的“根本概念”,“缔约国必须从法律上承认这些交叉形式的歧视以及对相关妇女的综合负面影响,并禁止这类歧视”(22)参见U.N.Doc.CEDAW/C/GC/28。。此委员会还在第25号一般性意见中指出,除性别外,妇女群体“还受到基于种族、族裔或宗教、残疾、年龄、 阶级、种姓或其他因素的多种形式的歧视”;缔约国需要采取暂行特别措施“消除对妇女的多种形式的歧视及其对妇女产生的复合不利影响”。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也在一般性意见中表示,“《残疾人权利公约》确认残疾妇女由于性别和残疾的原因可能遭受多重和交叉歧视”(23)参见U.N.Doc.CRPD/C/GC/1。。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对《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不歧视的内容进行解释时承认,一些个人或群体正面临一种以上的歧视,这些歧视会带来“独特的具体影响,需要给予特别的注意和补救”(24)参见U.N.Doc.E/C.12/GC/20。。这些条约机构对交叉歧视的阐述(虽然用词不同),部分与追求实质性平等的更大议题相连,部分仅是提醒缔约国要注意歧视的复杂性[22]。但无论如何,其实践体现出在国际人权法的体系下,对女性所遭受歧视的理解应该更加全面和综合,而非孤立和单一。
从中国的视角出发,将贫困作为一个情境因素带来的启示可能更具现实意义。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减贫成果,在促进妇女权益保障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贫困女性仍是一个需要关注的群体。此群体处在贫困和性别两个问题的交叉领域,难以单独通过任一边来完全解决其困境。自精准脱贫政策实施以来,中国城乡贫困人口大量减少,但根据2010—2017年间的数据,男性低保人口数量减少了逾 1800 万人,女性低保人口数量则减少不到500万人;男性贫困发生率下降了 2.84%,而女性对应的数据仅为0.71%,呈现出“女性贫困化”特征[23]。零散分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等法律中的禁止歧视条款,明确禁止的歧视事由包括性别,却不包括贫困。虽然就业促进法就“劳动就业者,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的规定为开放性条款,并未将贫困作为一项歧视事由的路径封死,但鉴于司法实践对其中“等”的判断更偏向于与生俱来、难以选择的“先赋因素”(25)用人单位如果基于劳动者的性别、户籍、身份、地域、年龄、外貌、民族、种族、宗教等与“工作内在要求”没有必然联系的“先赋因素”进行选择,就可能构成法律禁止的不合理就业歧视。参见刘小楠、杨一帆:《中国平等就业权纠纷案件法律问题研析》,载《人权研究》2021年第3期。,该路径在未来被接纳的前景并不乐观。因此,将较为有争议性,且在传统视角里属于“自获因素”的贫困作为一个情境因素纳入考量,在实践中更有可能成为一种迂回地为贫困女性提供司法救济的途径。这不仅与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对加强贫困妇女权益保障的要求和精神相符,也与中国批准的联合国核心人权公约对女性遭受的交叉性歧视的关注相一致。
五、结语
性别等传统歧视事由已无法准确描述和展现贫困女性的处境。而贫困,也不再仅是收入多少的问题,而是一个极易与性别、种族、残障、年龄等歧视事由交叉,造成和加剧女性不利处境、危害女性尊严的因素。虽然有些贫困处境完全由个人造成,但有些贫困处境有更深层次和历史性的原因,难以凭借个人的努力和选择来改变,长此以往会成为特定群体的发展瓶颈,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将贫困纳入反歧视法,无论是将其视为一项歧视事由,还是一个情境因素,都是对现有歧视事由范围和标准以及反歧视法定位的突破。
虽然现阶段两种路径的实践都较为有限,但比较而言,将贫困作为一个情境因素的路径更有被逐渐接受的可能。因为将贫困作为一项正式的歧视事由通常会引发是否会影响歧视事由的判断标准、打开诉讼闸门、不利于市场自由竞争等顾虑。而将贫困作为一个情境因素,虽然看似是一种妥协或迂回的路径,但其能通过回避歧视事由的问题,将贫困带来的影响充分纳入对案件的综合考量。尤其是承认情境的多事由交叉歧视的司法实践,能就贫困与其他因素造成的不利地位进行全方位的分析,更好地识别和解决贫困女性面临的复杂挑战,帮助其摆脱交叉歧视带来的特殊困境,推动社会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