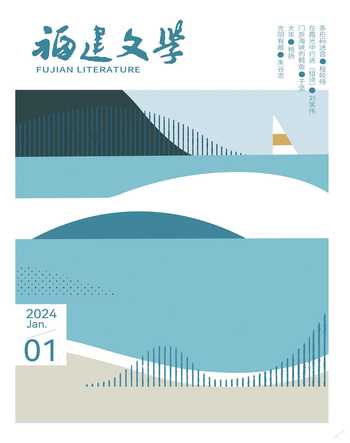矿工旧事
陈君英
1
福建的煤矿是依山而立的。建矿初期,每一座煤矿的山头上或是山腰间,都杂乱无章地盖起茅草屋或是简易板房,这就是矿工的居所。条件好一些的则能住上黄土夯实的土瓦房,这样的土瓦房很少;一到春来時或是秋风起,这些草屋、板房、土瓦房的房顶上便会或大或小地漏下雨水,房内难免会有积水。春秋两季,矿工家中经常是锅里煮着饭,房顶的雨珠滴滴答答地打在铝制锅盖上;有的人家一不留神,床上便会泡满雨水,那烧着火的煤炉子也会被雨水浇灭。改革开放后,矿井建起楼房、砖房,矿工的居住条件逐渐改善;但在山林中居住,也难免有惊恐的事发生,比如在睡梦中,一条花蛇环绕在蚊帐钩子上,或是缠绕在矿工、矿嫂的脚脖子上,也有蜈蚣爬到饭桌上或是游走于房内泥地上。矿工的家具很简单,床架是几根木头支起的,床板是几块板皮扎起来,饭桌既是餐桌也是茶几,同样也是简单制作的,几块板皮几条木支架、几根铁钉就能完成制作;当然,这饭桌还是孩子日常的作业台,我小时候,就是在这样的饭桌上识字,晚上停电了,便点上蜡烛,涂鸦几字就停下手中的铅笔开始玩耍,很自然,那些残留的蜡烛油也就成了我的玩物,趁着蜡烛油还没完全凝固,可以捏成许多东西,如微小的手枪、飞刀……也可以把毛线卷进蜡烛油里,再度使用。
在山林里居住,我身边有很多人都经历过被毒虫侵害的事件,而我没有经历过,有人说,毒虫是选择性地寻找侵害对象,或许我有天生的免疫力?这自然是无稽之谈。进矿时,父母便记住了一些防范毒虫的方法,比如在板房四周撒上石灰粉,会到山中或田野里采摘艾草等驱虫草药。也有人会在房间内洒几滴风油精,放几片生姜;有些矿工无视山林虫害,自然很难摆脱毒虫侵扰。有矿工搬进土房、砖房、楼房时,以为万事大吉不再惧怕毒虫了,很多防范措施便不使用;却不知,山林里的蜈蚣、老鼠、花蛇毒蛇还能钻缝爬楼,从门缝爬进来,从下水道钻上来,夜深人静时,时常有人会发出毛骨悚然、歇斯底里的惊叫声……
清晨时分,矿工或家属、孩童,是不用闹钟报时的;窗外、房顶上有准时叫人起床的麻雀、斑鸠、山鸡、野鸡,特别是山间灌木丛中,那些野鸡的叫声十分响亮,无论是蒙蒙细雨还是朝阳初抬头,它们都会跟随在麻雀、斑鸠后头引吭高歌,矿工哪怕睡意再浓,也都会被这甜美、清脆的声调惊扰。这些鸟类似乎是上工上学的天然闹钟,一到时间,就会这边哼几声,那边唱几调,一副你不起床,它不罢休的状态。矿区孩童时常是揉着眼睛爬起床,很不情愿地匆匆吃了早饭,然后就到了学校趴在课桌上补觉;课余时间,顽皮的学童自然会掏出弹弓对那些固执、扰人的麻雀下狠手,或摆起簸箕逮麻雀,也会在田间地头追着弹击。当然,我们这些矿山孩童也会拿着红苕在野外烧烤,更多的时候,则是就地取材。香喷喷的烤红苕味道会飘到空旷的原野上,招来更多孩童和手持小竹枝的矿工或矿嫂一顿猛抽。
野外也成了矿工孩子们最惬意最完美的游戏场所,挖泥鳅、溪中抓鱼、田地捉迷藏等,到了夏秋时节,便是爬山采野生杨梅。山里的杨梅树有青梅、海梅。青杨梅树很高,能有十多米的高度,果实只是微微有点红斑,果肉多酸微甜。海梅则是树矮,果实大颗饱满且味甜汁多,树干与地面垂直高度也就两三米,但海梅是在深山里,数量不多,很少人能寻到海梅,更多的是碰到毒蛇、蜈蚣之类的。夏秋是孩童最喜欢的季节,可以进山采杨梅,也可以在农家房前屋后采桑葚摘李子等,但凡有了目标,矿山的孩童总会去尝试。在山中,孩童也会碰见穿山甲、大蟒蛇、千足虫、野猪等动物,还有很多叫不出名字的猛兽、昆虫,所幸,孩童没有受到侵害。
那时候交通不发达,北方煤炭很难调运到福建来,提倡“自力更生”。没有能源,福建各地按照专家的指点,便各自组织队伍到大山深处寻找煤炭。老一辈矿工说,最原始的找煤方式,便是在深山里寻找褐色的石头,或是在地表上挖出一块褐色石头,再分析石头成分,一旦确定是煤炭后,便组织队伍开挖。不管煤炭品质怎样,只要是煤炭,矿工就能兴奋地抡起锄头开始刨山挖洞。我的父母也和队员们一同扎根于煤矿,整日劳作而无暇顾及我们这些矿山孩童。
2
轨道就是煤矿的生命线,是煤矿生命的刻度,轨道延伸到哪,煤矿的生命就到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而煤矿的生命随着轨道延伸不断向前,每一位矿工的青春和生命不断地锻造出轨道的坚强,轨道就像一条坚强的血脉支撑着煤矿走向更远的明天。
很小的时候,我是没有感觉到什么是困苦的,天真与烂漫抵御了所有贫困。20世纪80年代初期,矿井生活条件很差,又处在山林中,缺少生活物资时,矿工们总能想出许多方法应对生活危机。我还记着,小时候,家里虽少肉缺油,但总会有惊喜出现。比如,冷不丁地,饭桌会摆上一盘鱼,或者肉;我父亲会和其他矿工一样,各施“法门”到山里寻找野味。下班时候,这些男性矿工会到野外去寻找野兔、野猪、大蛇或是在溪流中垂钓。我父亲有一手垂钓的技艺,一个晚上能钓一桶的大鱼,挨家挨户分了一些;其他矿工抓到野味,也会给各家各户都分一些,矿工人家自然亲近许多。有些矿工喜欢到田间或山腰上的草坪上抓野兔,一到晚上,就带了几盏矿灯或手电筒,到处寻觅野兔,发现野兔就把灯光对着野兔照射。这些野兔被灯光照射后,便会憨憨地与灯光对视,身手好的矿工一块小石子便能砸得野兔晕倒在地,一晚上,能抓好几只野兔。
时间,对于一颗煤来说,是一份等候;时间,对于矿工来说,是一个探奇的过程,坚硬的岩石只是一个陪衬。矿工前进的脚步随着轨道延伸而不断改变,在井巷每一处有煤炭的地方,矿工总是用力地把煤炭从岩石的怀中拽出来,这道工序已定格在矿工的意识中。尽管,生活和工作条件很差,但阻止不了矿工在井巷前进的脚步。
早期,矿井的轨道并不是铁轨,矿井也没有铁制运输工具,临时轨道是几块木板,矿车是战争年代传承下来的独轮车、板车;井巷挖煤还是嘴叼煤油灯一镐一镐地掘出煤炭,然后,矿工肩上拽了一根麻绳,一步一步地把煤炭拽出井口。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矿井才用上了简易的金属轨道和矿车皮。到了90年代,矿井已经开始蜕变了,浸泡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煤矿犹如凤凰涅槃,展现出新的笑容;亮锃锃的宽大铁轨和火车专用枕木也逐渐在煤矿普及运用。
孩童时,我与许多同龄人一样,经常跑到矸石场去,给在矸石山或煤台劳作的母亲送饭或是到井口山头采摘野果。我们时常会在轨道上玩耍,蹦蹦跳跳地感受轨道跳动的节律,微微颤抖的声响好像是轨道的心跳。我们也会坐在矸石上,看着一列一列的矿车在轨道上飞驰而过,轨道欢快地发出“哐当哐当”的声音,一列列满载矸石或煤炭的矿车从井巷深处爬了出来,与卸下矸石和煤炭的空车皮擦肩而过。有时候,我们这些孩童看见父亲或是矿工们脸上涂着一抹黝黑的煤粉走出井口,张开嘴时,白色的牙齿与一脸黑色形成了鲜明的色彩差。我看着轨道向洞内延伸,看着黑漆漆的井巷,以及渐渐被黑漆漆井巷淹没的轨道,时常会产生疑惑,不知道一辆辆矿车是如何爬上轨道,又是如何钻进幽深的井巷中,地层深处的井巷是否闪耀着光芒,又或者父亲是以怎样的姿势在井巷劳作。
经过矿车轮不断地碾压、撞击的铁轨格外锃亮,在太阳照射下,时常会折射出耀眼光芒,这道光会射向很远的地方,即便我们这些顽皮的孩子窜进矿区周边的山林中,也会被这道光照射,被召唤。
轨道,是一份神圣使命的象征,它背负着经济发展的使命,也承载着矿工对未来的期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受交通影响,省内能源短缺,福建在寻求经济发展中,强烈地渴求能源产品,以摆脱经济困境。于是,轨道闪耀的光辉也让矿工有了一份荣耀,在煤矿工作的人们,不辞辛苦远离家乡扎根于矿山。我母亲曾是海防民兵,到了矿山便加入了矿井建设中,每每回家乡,亲人总是不断地夸耀父母有本事。早期,家乡经济落后,多地主要是农耕或出海打鱼,收入有限,农家人生活并不富裕,煤矿工人的身份便十分光荣。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家乡才逐步改善经济发展环境,一车车煤炭从煤矿运出去,家乡很多工厂的烟囱上冒出了一股股黑烟。
轨道的光芒辉映在绿色山峦中,我们矿山孩童沉迷于山里的逍遥快乐,在轨道间穿梭,在树林中玩耍,采摘杨梅、野柿子、树莓等,或追野兔、抓麻雀,或是田中掏泥鳅、黄鳝,也会蹚水到溪中捕鱼等;女孩们会跟随男孩到山林中采摘野果,或是采几束映山红(杜鹃花),年纪稍大的女孩则会在规定时间内督促孩子们回家,她们还得回去淘米下锅煮饭。忙碌于煤矿建设的父母,很少有时间照顾孩童,这给了我们无拘无束的玩耍空间,直到我们这些孩童长大成人,穿上蓝工装沿着前辈的脚印走向深邃的井巷。
于我来说,井巷是神秘的。
刚踏进井口,我的心激烈地跳动,前方有蓝光在跳动,我以为是鬼魂在游荡,不敢放肆,脚步带着忐忑与恐惧,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那蓝光是井巷里的老鼠。很长时间里,我一度怀疑井巷的牢固性,总以为稍稍用些力气,就能把井巷踩垮了,胶靴踏出的响声,好像能扩散到地球的表面。
轨道延伸的方向,是一层又一层的夜幕,耀眼的矿灯,刺不穿古老的幽深。我甚至认为,所有爆破的巨响,都足以震动地球,波及一切生灵。心怀敬畏走入井巷,即便是顶部的岩石,滴落一颗水珠,也会以清脆而敏捷的动作,穿入我耳膜,产生一道震波。
在入井后,我总是畏惧井巷,害怕井巷的幽深。等到内心被恐惧塞满后,便无奈地接纳了井巷,开始从沉默中去读取一颗煤的故事,关于岩石与煤炭的爱情,关于矿工与井巷的情感。我相信每一颗煤炭的眼泪都是痛苦的,在煤粒的身上,依稀还沾着一些岩石的吻痕,即使是热烈的阳光,也无法褪去这个深情的物质,洗不净这份情感。而我日复一日地做着这样的事,在矿灯的照射下,于黑暗中,走千米井巷,只为阻止煤炭与岩石的亘古爱恋;自从深入地层,这爱恋就成为煤炭、岩石、人类的情感交织。
3
人们会习惯地认为井巷是男人劳作的地方;事实上,矿井也曾出现一群女子组成的女子掘进队。“谁言女子不如男,敢叫一巷幽深綻光芒!”这是曾经的煤矿女子掘进队喊出的口号,她们和男性职工一样,从事井巷最艰苦的工作。到井巷去工作,对女性来说已然是不小的挑战,更别说是到一线去作业,对于女性职工来说,下井作业是巨大的挑战!改革开放初期,煤矿生产设施很简陋,工艺落后,生产环境不容乐观。一盏灯弱弱地挑开幽暗,在铁轨的引领下,她们不断地向前行走,直至作业现场,幽深的井巷渐渐被这些女性征服了,恐惧也随之消失。
女子掘进队多是年轻矿嫂、知青,为了能获得一份煤矿工人的正式身份,已婚的或是未婚的矿工女子纷纷加入这支队伍中。
“男人能干的,咱们也能干!”一顶矿帽,一盏矿灯,一身蓝工装,一双长胶鞋,这群年轻的女性以一股豪情走向井下,她们有的背着炸药,有的扛着生产工具,奔赴井巷作业现场。矿帽遮不住那一束秀发飘逸,更挡不住女性的娇美身躯,这群女性掘进队员在煤矿走出了一道靓丽风景线。
入井之后,这些年轻女职工便勤于学习井巷的各项操作技能,如打钻布置炮孔、装药、支护等,但凡男性职工干的活儿,这些女掘进工们都得学会。井巷掘进作业,最耗体能的就是清理矸石。正常情况下,每一茬爆破需要出矸石十多车。早先,井巷运输煤炭、矸石的矿车是漏斗状的,一车估摸能装一吨左右的矸石或煤炭,女子掘进队员两人一组用手工进行清理,正常情况下,清理一车矸石或煤炭,需要花费十几分钟时间,一茬爆破的矸石量要花费两个多小时,体能消耗非常大,如果碰到岩层破碎的,整个班都是在进行这项清理工作。这幽深的井巷里,不知浸透了多少矿山女性的汗水,煤海巾帼用芳华抒写她们的传奇人生!
其实,矿山女性是最坚韧的群体,她们不仅要面对恶劣的工作环境,还得打理家庭事务。很小的时候,我就经常看着这些矿山女性走向山林,她们是去寻觅食材,寻找野味。建矿初期,物资匮乏,普通矿工生活条件又差,一个矿工家庭孩子又多,两三个孩子很常见,孩子多了,家庭负担自然会大一些。空闲时,这些矿工女性便会到山林里寻找食材,比如蕨菜、竹笋、野山葱、野菜、草菇、蘑菇什么的,当然,也会寻找一些野果,如野生杨梅、野生柿子等,有时还能找到一些野鸡野鸭蛋回家。劳作后,矿山女性会在矿区周边开荒种上一些时令果蔬,矿山也有了浓厚的生活底蕴。自然界总是这么阔绰,对这些矿山女性毫不吝啬,山林里很多新鲜的食材都会无偿赠送给人们。春天来临,矿山女性们携家带口,扛上锄头,夹着麻袋,纷纷奔向山野,从山脚到山腰,到处寻觅春笋,到处寻觅野菜、蕨菜,有些孩子也加入其中。
我在上学的年纪,也经常跟随母亲,到山边的田地里去翻找红苕。这里的红苕其实是类似于洋芋的本地物种,果肉是白色的,煮熟后的果肉不像红苕那么松软,口味也不是那么香甜。尽管如此,等到农家挖完红苕后,矿工家属便会抡起锄头再次翻垦土地,也能找到一些被黄土掩盖的红苕来。翻垦土地的活一般是大人干的,这是体力活,女孩多是到山边或是田边地头寻找车前草、野菜什么的。那些如草根的红苕则会带回去喂鸡鸭。但凡从山林中或是田间地头找来的食材,皆是有用的,人畜分享。到秋收时节,附近的田间都会挤满人,有矿山家庭主妇,有矿山孩童,也有穿工装的男性职工,大家都在田间捡拾稻穗,也有人在挖泥鳅、掏泥鳅黄鳝。在这里,大家各显神通,各取所需,最大限度地攫取大自然的给予。
有一次,我无意间发现了一块已被挖完的红苕地边上,还留下一棵完整的红苕,是农家人在挖地时疏忽了。从茎看,这是一棵很大的红苕,我轻轻地用手翻开泥土,一个硕大的红苕露了出来。我如获至宝地趴在这堆土上,一旁的男孩急忙推开我,抡起锄头就挖了下去,我爬起身想挡住,拙笨地趴在红苕上,那柄锄头便砸在了我的脑袋上!顿时,我的脑袋上鲜血直流……
4
时间荏苒,我也不再年轻了!煤矿往事历历在目,但对于久远的建矿时期的人和事难免会遗忘一些。
2017年夏天的一个早上,我像往常一样,坐在办公室里正准备泡茶,忽然,电话声响起,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是一个陌生电话。尽管是陌生电话,我还是接通了电话,工作职责不允许我遗漏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位中年男子口音,询问进矿的路径。
我在煤矿工会工作,负责工会具体事务,比如伤病慰问、退休老职工慰问、组织矿井文体活动、抚恤费发放等。很多退休老职工离开煤矿,分散在莆田、泉州、福州等城市或乡下生活,有些事都是电话联系的。所以,一旦有电话打来,我都得接,以免怠慢了这些老职工,这是我养成的工作习惯,也是对这些退休老职工的尊重。
过了几分钟,一辆小车就停在了办公楼前,车上下了三个人。
到了我办公室里,带头的中年男子盯着我看了几秒,好像与我似曾见过。他没说出此行何意,先是问我:你是矿二代吗?我回答:是!他便说:我想你应该是矿二代,有印象。这样的开场白,有些怪异,我猜眼前的这三人一定是这座矿井的熟人,或许也是矿山子弟。果不其然,这位中年男子自报家门了,说是姓廖,与我是同乡,随行的是他的两位妹妹,都曾经与父母在矿里工作,父亲退休后,他们也陆续回到家乡。看着眼前的兄妹,虽是老乡,但我有些眼生,毕竟眼前这三人年纪比我大许多。当我提及我退休的父亲时,老廖便惊叫道:你就是阿群呀!怪不得眼熟。一旁的女子也报了名字,还准确地说出我父母的名字,她说起自己曾经和我母亲一起在煤台上倒矸、撬矿车,语气中充满了自豪。我们矿山子弟自幼受环境影响,很少去外面,大都满山乱跑,对很多矿山的事印象比较深刻,老廖等人的描述,与印象中的事都能吻合。兄妹俩说,进矿的路原先是土路,在他们当矿工时挖的,如今是一条新的水泥路,和进村的路相连。
我在工会工作中经常会接触到患有尘肺病的老矿工,很多早年的矿工有职业病。在我印象中,发放的尘肺病补助中就有老廖父亲的名字,而且还是三级的。我经手的职业病等级里,老廖父亲是最严重的,很多矿工要么是一级,要么是二级,三级尘肺病少之又少。老廖父亲是谁?我已记不住他的容颜,只是从父母的口中隐约勾勒出一点轮廓,模模糊糊的一点印象。
“老廖父亲好像是军人,上过战场的老军人,干活跟拼命似的,在井巷里一直冲在最前面……”父亲这么描述廖老,他的语气中充满对老廖父亲的敬爱。“廖老?”我隐隐约约记得有这么一位老矿工,我模糊地想起还未完全忘记的童年小故事:那个夏天,一位老矿工拖出了一箱东西,把箱内的一件件衣服、笔记本和被褥摆在木板房前接受紫外线的暴晒。矿区多在山林中,湿气较重,每逢艳阳高照时,矿区里到处都是五颜六色的被单。说是五颜六色,有些夸张,那些被套里装着的棉絮有的是发黄(老棉被)的,有的是崭新的,有的则是黑色的。我那时还是七八岁的孩子,顽皮得很,和一群矿山孩子这家走走,那家遛遛。等到老矿工进屋时,我便窜进这位老矿工屋内玩耍,趁着老矿工打理房间卫生的时候,在箱子里翻找好玩的东西。有一句俗话说:好料沉底!在箱底,我翻出了一个用红布包裹的东西,解开红布,几枚沉甸甸的奖章赫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幼小的我哪懂得什么奖章军功章,只是觉得新奇而已,奖章上的字和图案并不是那时我的兴趣点,以为像很久以前的革命像章,一个个地拿出来玩耍。这位老矿工就是廖老!
聊到那些奖章,老廖便拿出相片指着勋章告诉我说,父亲获得的奖章,有渡江战役纪念章、抗美援朝纪念章等,这些纪念章就说明了父亲参加过许多战役,但父亲从未在外炫耀,他总觉得与那些牺牲的战友相比,自己是幸运的。
老廖妹妹说,父亲是在观看国庆阅兵时,悄无声息地走的。
5
从小在矿区长大,交通不便,我們好些年才回家乡一次。我们很难弄清楚乡愁的内涵是啥。我时常会从味觉中去理解乡愁,即在时光里酿出的带着荔枝味的乡愁。
在莆田的老家,一到夏季,荔枝便露出了红彤彤的肚兜,解开这身红肚兜,一股香甜的果汁和白嫩嫩的果肉就呈现出来,这就是让杨贵妃嘴馋的荔枝!从6月左右开始,村里一些荔枝树上的果子就陆续露出了一点点娇羞的微红,像是少女娇羞的面容,随风晃动。有时候,我一度怀疑是夕阳和晚霞的戏弄,一夜间会把青青的荔枝拨弄出一色羞红;夕阳披身的荔枝很是俏美,红红的果壳以及白嫩的果肉、甜甜的果汁皆是诱惑。
每次品尝荔枝时,矿工们很快就会说出荔枝的产地,我的家乡。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家乡的水土不仅养出了勤劳的人们,还培育出特殊的荔枝香味。不仅家乡人能品尝出乡愁,即便外地人也很快就能分辨出荔枝的口味。
有一次,一矿工从外地买了几斤荔枝给工友们品尝,说是莆田荔枝,但拿出荔枝时,很多人便开始怀疑了,怀疑荔枝的产地。等到果肉入口,大家便没了品尝的欲望,面容尽显不满。我也拿了一颗荔枝,用鼻子嗅了嗅,便知道不是家乡的荔枝,没有剥开便放了回去。那位矿工见瞒不住了,便说出了实情。这种带着乡愁的味道是烙在味觉记忆中的,一旦散发出来,便会让人印象深刻。这便是我对味觉乡愁的理解。
早些年,交通不发达,回家乡的次数屈指可数。因地理条件影响,家乡还处于农耕时代,除了一些农产品,别无优势。父母回家乡返回时,多数会带来一筐两筐的荔枝,拨开鲜叶,那股荔枝的香味便会扑鼻而来,勾起很多矿工的食欲。
每到荔枝红透时,家乡的公路边、乡村土路上就会停满车辆,邻近县市或北京、上海等地的人都会慕名来现场采购荔枝。看农家人摆舟登梯采摘荔枝,一边看一边品尝,嘴角难免滴落来不及入口的果汁,河渠水面上多了许多鲜红的荔枝果壳在游荡。
一到夏季,家乡总会弥漫着阵阵荔枝香味,从村头到村尾,从田野到公路,香味一阵一阵,如潮涌动在这块土地上。每每随父母回去时,我总是喜欢走在这样的乡间道路上,用嗅觉去感触乡愁。
很多矿工都尝试在矿区培育荔枝果树,以我家乡荔枝果核发芽的幼苗做试验,寄望几年后能在矿区吃上新鲜的莆田荔枝。似乎验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话,不管怎么去浇水施肥,荔枝幼苗在礦区就是很难生长。直到所有的荔枝幼苗枯死,矿工才宣告种植试验失败!
或许,这份特殊的味觉乡愁是众多矿工共同的感触,否则,也就不会有许多矿工去试验培育荔枝苗。在远离家乡的地方种植荔枝树,并非一时兴起或无知的表现,而是矿工内心的那份乡愁诱发的。
在矿区,有一株橄榄树结出了橄榄,这是离我家乡不远的隔壁乡镇才有的果树。每到橄榄树结果,矿工便会按照家乡人采摘橄榄的方法,用脚使劲踹树干,橄榄便会一颗一颗地掉下来。这些矿工在下井作业时,会含上一颗橄榄,惬意地走入幽深的井巷。当然,对于很多外地的或矿区周边的农家人来说,橄榄是另类的果子,很难入口,他们尝试几次后,慢慢地适应了橄榄的口味,适应了“先苦后甜”的味觉转换。家乡的水果品种多,但受地域影响,多是分散种植。如这橄榄,在我家乡是稀罕的果树,根本种植不活的,而其他地区也很难种植荔枝果树,即便种活了也很难结果。这应该是各方水土不同所致吧?每次回矿区,父母总会带些家乡的特产,如菱角、荔枝、花生等,一看到这些特产,矿工就知道我家乡所处的地域,即便新来的矿工也能猜出大致的地方。沿海人家多是带些鱼干、虾米、海参干等海味,一众乡亲用各自的特产在矿区诠释着各自的味觉乡愁。
福建煤矿,很多矿工来自莆仙地域。那个年代,莆田、泉州、福州的人组织了大量的人员建设煤矿,而莆仙一带是一批接一批,形成较为壮观的队伍。
当你走进矿工人家,一些特殊的口音、家居摆设或是食品就会告诉你,这户人家是哪个地方来的,是城市郊区的还是沿海的,或是山区的。他们都有各自的特产、独特的生活习俗,虽口音相似,但还是有细微的差异。矿区,使得来自省内外的人彼此熟悉起来,融合起来,但这些生活习俗、口音是很难改变很难融合的。或许,自始至终,我们都属于那个遥远的家乡。
责任编辑陈美者